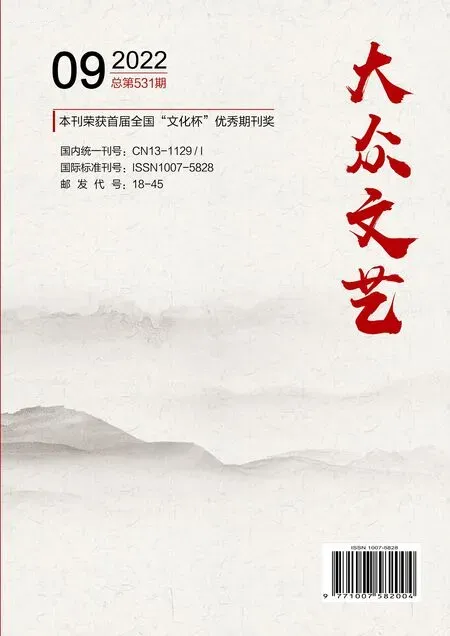“传神者,必以形”
——以董希文1954—1961年藏区风景画作品为例
李奕铭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100048)
一
董希文1914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光华溇村,少年时期曾先后在苏州美专、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专进行学习,对江南地区的风土人情极为熟悉,1938年因抗战之故,辗转于江西、湖南、云南、贵州、重庆、甘肃、北京等地求学生活。这样的经历让董希文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有了对江南、西南、西北地区自然风貌的深入体会。董希文个人丰富的成长经历和动荡的时局都给他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动力和多种表达形式,观者能从其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作品中感受到他想要用自然表达一种民族情怀和生活感受,他从不同景象、不同民族中获得的精神体悟在作品里不断映照出来并在其后的创作中得到深层延续和开展。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文艺界担负起了空前的历史责任,人民经历了战争的摧残和生活的艰难,他们对解放了的新中国充满美好的向往与期待。1950年创刊的《人民美术》在其发刊词中即指明新中国美术家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国家进行宣传工作并在宣传过程中发挥各自专业特长,如何重新将自然景象纳入新的历史语境之中,如何让表现对象与社会主义建设高度融汇,都成为新形势下不得不面对的创作任务。这种时代革命要求、社会氛围使董希文的创作思想获得滋养、艺术精神进一步打开,他的作品逐渐突破绘画形式的束缚,自然被渗入一种全新的意义。
建国后,董希文曾三次进入藏区写生,其原因来自国家对于展现新社会面貌的创作要求,同时,画家对民族绘画形式语言取得的初步探索经验和深入边区的生活经历也给他的藏区绘画作品带来了巨大的创作动力和情感印痕。青藏高原在进入董希文视野的时候,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建设过程中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将个人的理想注入到新社会事业之中的执着追求,都赋予了董希文藏区绘画作品更丰富的思想性内涵。
1954年2月5日,董希文开始了首次进藏写生活动,他参加了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第三总团前往四川康藏。新中国成立时西藏是唯一没有近代道路和近代交通工具的地区,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为促进西藏地区发展调动了巨大资源建设公路,几十万筑路大军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峭壁上开山劈路,董希文慰问途中将解放军的坚强意志收入眼里,记录着建设的状况。
《春到西藏》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它并不着意表现开车典礼或施工状况,而是选择大片自然景象。观者可以从画面中感受到西藏这片古老土地上散发出的新鲜气息。作品构思之初与传统山水画就有内在关联性,画家不仅采用中国画里常见的之字形构图,并大胆使用类似“平远”式的表现方法把画面切割成土地、远山和天空三部分。画面中随着公路的伸展能看到运输车队、雪山、天空,层层传递十分流畅。
董希文此画的构图处理、空间表现都融入了古代传统绘画手段,他想要抛开自然景观的表象向传统绘画学习,去追求对象的生命本质,董希文早在少年时期就形成了深厚的文人画素养,他在技法上追求“油画中国风”的同时,更在作品中融入传统文人“寄情于景”的情怀,他希望创作出饱含真挚情感的作品。
二
董希文通过《春到西藏》把他对于新中国的精神体会借助自然景观获得抒发,而这种通过自然流露出的人文主义温情也更加饱满地展现在他二次进藏的写生作品中。1955年,中国军事博物馆向董希文发出创作“长征题材”革命历史画的约稿,同年,董随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进行写生,历时半年之久,写生创作达二百五十余幅,这段岁月也成为了他个人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从现有资料来看,长征路线风景写生作品,可分为革命历史题材的风景画创作和单纯风景写生。可以说,在二次进藏过程中董希文通过自然风情重构了历史精神和中国的新形象。
董希文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进行了一系列革命历史画创作,《北平入城式》(1949)、《抗美援朝》(1951)、《开国大典》(1952)等作品都是根据主题需要而设定的形式语言,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主题,因此更具理性意味。与此不同的是,他的长征路线写生作品从现场感受出发,将革命足迹和自然风景结合起来,把大自然的意象转化为一种历史的诉说和民族精神的体悟,正是通过这种对景写生我们能够看出他彼时内心情绪的迸发。
泸定桥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的大渡河上,位于此地的泸定铁索桥是四川入藏的军事要津,飞夺泸定桥更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决定性战斗。从《大渡河泸定铁索桥》的构图上看,桥身贯穿整个画面透视非常深,桥面上有许多来往的行人,近处的藏民背着背篓,有些三两成群的交谈着,颇具生活气息,对岸房屋瓦舍中红旗迎风飘扬,种种展现都是典型的新中国模样。画面河水近景的笔触带有强烈炫动感,使人感到水流滚滚、湍急异常,画家仿佛把红军强渡时内心的坚定勇敢和理想信念诉说给了观者。
长征题材创作中针对泸定桥的主体表现产生过一批作品,李宗津和刘国枢在1950年代也进行了同样的尝试。两者的《强夺泸定桥》和《飞夺泸定桥》都将战士们的举手投足做了精心安排,且更倾向于展现战争发生时的壮烈境况,以最大限度去强调主题性和叙事性。同样描绘泸定铁索桥的董希文却把昔日红军长征的足迹转化为祖国山河图景,把革命性转化为抒情性。“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意义与董希文写生作品所呈现出的刚健、纯朴、明朗格调交相呼应,形成了生机磅礴的民族精神象征。
董希文的长征路线写生,除了有对红军历史足迹追溯的革命题材作品外,还有通过同时代事件展现新中国氛围与人心面貌的历史画作品。毛儿盖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松潘县的西部,曾是千里无烟的荒草地,经过藏族儿女的辛勤劳动,已然变成了郁郁葱葱的麦田和漫山遍野的牛羊。《毛儿盖盛会》表现了藏族人民为庆祝丰收在寺院广场上举行集会的场景,画面中人声鼎沸,寺院、服饰、帐篷以及正在表演的藏戏都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味。江丰评价:“它那阔笔涂刷的强烈对比而又显得十分和谐的色彩处理,非有高明老练的技巧和大胆果断的魄力,是绝不能办到的。”
“抒情性小品”是二次进藏风景画作品中另一种重要的内容表现形式,相对于历史性题材的画作,这类作品倾向于作者自身感情的抒发,独立性更强。从这些画作里观者可以更多地读到董希文的“造化”与“心源”,风景画无论是色彩语言还是形式结构,都展现出了他对藏区风物和高原净土的向往,他不断地用手中的画笔塑造着自己的“心迹”。
董希文的风景小品虽为写生也画得十分细腻。他在《班佑河畔高草地》和《草地烂泥坑》这两幅小品中有意忽视了西洋画法里复杂的色阶变化,特别抓住了草地和天空的鲜明本色。画家并不在意描绘的是不是或像不像眼前的景物,而是传达一种情绪,这种不在意形象客观逼真性的处理方法,在《二郎山看日出》《二郎山远眺大渡河》《大雪山仓德梁子》等作品中也同样体现出来。长征路线的写生不仅是一次对革命史的追忆,对董希文来说,则更是审美情感、思想境界的提升,他以无比的热情和执着的精神将风景画创作与艺术感情成功融汇,并表现在自己的作品里。
三
如果说,首次进藏作品是董希文风景画抒情的发轫,长征路线写生是一次生动明朗的咏唱,那么时隔6年之后的第三次进藏写生作品,就是董希文艺术创作中的一支豪情壮怀的浩歌。1961年7月,“董希文与吴冠中、邵晶坤一同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的西藏写生活动,第三次到达藏区,深入日喀则、江孜、帕里、亚东等众多牧区,”此行藏区情况发生巨大变化,自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画家的主要任务是表现翻身农奴,歌颂他们成为主人后的社会新气象。董希文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协助下,深入了解当地农村、牧场,和藏族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历时三个多月,创作作品40余幅。
翻看这次写生中为数不多的风景画,可发现作品的造型更概括,笔触厚重有力,色彩单纯浓郁,画面内在表现更具张力,表现内容融入了更多的浪漫主义精神。《喜马拉雅山朵琼湖边》在简单廓形中,画家更注重抓取特点,西藏阳光很强,自然景观的远近感就弱些,所以董把色彩处理的肯定、结实,加强明暗对比,画出雪山的透明感。通过清新爽朗的画面效果,观者可以想见董希文在经历了家庭和工作双重困扰时的刚毅态度,面对宽舒的自然,他的心灵感到抚慰。
董的另一幅作品《喜马拉雅山颂》更具一番意味,真实地反映出他对西藏非一般的感情。他的学生刘秉江对此画做了如下回忆:“董先生凝视这画稿说了许多话。但是只有一句我记得最牢:‘我的感情始终是与这样的情调相通的’。”喜马拉雅山下清澈的雅鲁藏布江,草原上成群的藏羊似在聆听笛声,每只羊都有着黄色的眸子,是那么明亮,整幅画面显得如此静谧,只有那藏民的笛声悠扬。董希文在艺术中融入了他深邃的情感,真实的表现却在动静中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藏区那自然与人文天然亲近的关系,令他动容。
观者能从董希文的风景画作品中体会到他超越叙事性的个人状态,以及他对民族情韵的捕捉。他在真切的自然景观和平凡的现实生活中发掘自我情感,入藏期间的多幅作品皆能体现出他的“寄情”意图。这些作品能促使我们思考新的绘画语言与传统绘画精神之间的关联性,更令人感受到自然风景画带给观者精神上的感受力度。这样的作品能体现出早期新中国艺术家们对画作刻苦钻研的精神品质,和他们勇于承担时代要求的决心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