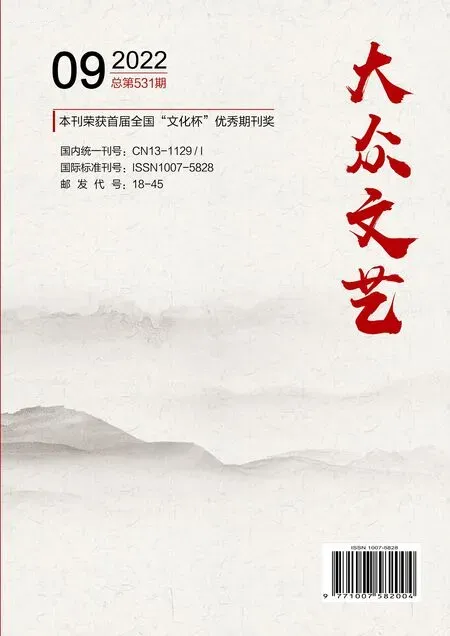战争与爱情
——陈妙常的双重人格与身份转换
程子玥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100080)
一、名字与双重身份
名字是人的代号,而具有比代号更丰富的意义。通常来说,一个人的姓名均是父母给予,承载着血缘与人际关系,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二者则很大程度与其身份地位相对等。人冠此姓名在人世间活动,其处境受到身份地位的影响,其行为需得符合名字所承载的身份,因而表现出与其身份相称的行事风格与态度,换言之,一个姓名对应着其人在社会中的坐标,也一定程度上对应着一种性格。在中国古代社会,改换姓名实际上意味着旧姓名所承载的人际关系和身份地位等随着姓名的变改而发生变化,甚至被放弃,因而在文学作品中书写姓名的变改,背后时常是命运的重大变化。在话本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女主人公莘瑶琴在开封时是良家女儿,一家生活和美;而罹经战乱到临安改名为王美娘时,则是风尘女子,孤身一人;当与秦重结合寻回父母,重新成为良家妇女而一家团聚时,名字也便改回莘瑶琴。由此可见,在文学作品中,姓名具有强烈的象征性,不同的姓名往往意味着迥异的人生。
在《玉簪记》中,女主人公的两个姓名也象征着迥异的两重身份。首先是血缘与人际关系:陈娇莲是已经许婚的闺阁女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陈妙常则是孤身一人无亲无故,其所具备的人际关系只是道观中的观主及道姑等人,婚约在道观中已经无法生效。其次是身份地位:陈娇莲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也是正值二八芳华的妙龄女子,与凡尘可有所接触;陈妙常则是靖康之难后的遗民,是出家脱离俗世的“仙姑”。最后是行为与性格:陈娇莲自可具有少女的一切情感与行为,而陈妙常则在清规戒律之下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姿态,即不理凡尘俗务,也不备凡人之情。或被动或主动,前二者都可随姓名变易而彻底完成变化,但行为与性格却难以通过名字的改换达成一蹴而就的变化,因而陈娇莲与陈妙常二者的行事风格实际上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着缠绕和交错,外在表现和内在情感之间也就不得不因此有了错位。而两重人格和身份的转换,正是从这种交错出入之间寻到突破而达成的。
二、战争:身份的第一重跳跃
从战争本身的属性来看,它自然而然地具有动荡和变革的语义,通过一个混乱的外部环境,一切已有的既定的情景有了推倒重建的可能,因而适用于身份突变的情节,并且赋予这种变化以快速、剧烈而彻底的特点。《玉簪记》中陈娇莲变为陈妙常的过程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战乱以直接且猛烈的方式将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即陈娇莲在旧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拆散,而将陈娇莲置于孤女的境地。
除了剧烈与彻底,战争导致的身份变革还往往充斥着被动与主体的别无选择:战乱中的孤女,一无栖身之所,二不识前往未来公婆家的路,可谓走投无路,通常不是被迫走入风尘就是脱离红尘,莘瑶琴是前者,而陈娇莲则成了后者。在这种急速的外力驱使下,陈娇莲以非主动的方式完成了从闺阁小姐到出尘仙姑的转变,而正是由于过程的急促和动机的非主动,旧身份无法实现完全的脱离,身份的第一重跳跃于此已为新旧身份之间的拉锯和角力埋下伏笔。
三、爱情:身份的第二重跳跃
潘陈二人的爱情自然是《玉簪记》书写的核心,也基本遵循了《西厢记》以来的才子佳人故事结构,但从陈妙常身份转变的视角看,潘陈二人之间的爱情反倒是陈妙常回到陈娇莲的最重要途径与契机。与第一次身份转变的急促与被动相比,由爱情促成的身份回归似乎是缓慢的、递进式的,甚至带有主动选择意味的。
《玉簪记》开头便已道出潘陈二人之间早有婚约,因此二人虽不相识,但潘必正实际上已经存在于陈娇莲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即便二人在相识相恋的过程中并不知晓这一层隐含的人际关系,但潘必正这一人物确实承担起了提示陈妙常旧身份的功能,他携带着陈妙常旧日生活的种种印记,唤起其新旧身份之间的拉锯,并最终帮助陈妙常完成了旧身份的回归。
下文将结合文本,细谈第二次身份转换是如何随着爱情的进展而完成的。
(一)爱情发生之前
在潘陈二人爱情发生之前,陈妙常也有一段类似才子佳人故事的经历,即《玉簪记》本事中“张于湖宿女贞观”故事,这段故事实际颇具反讽效果,作为一部以才子佳人故事为主线的作品中的一段支线故事,“张于湖宿女贞观”亦是按才子佳人故事展开,而最终竟未能成形。张于湖与陈妙常的相遇是极富浪漫色彩的抚琴留诗以待相逢,并不比潘陈二人的初遇逊色,甚至带点文人风雅趣味,但刚进入新身份的陈妙常回应:“相公,我意絮沾泥心炼铁,从来不爱闲风月。莫把杨枝作柳枝,多情还向章台折。”1陈妙常刚刚成为道姑不久,却说自己“从来不爱闲风月”,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而此处陈妙常此语此举实际上在刻画她进入新身份后所呈现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状态。
作为道姑的陈妙常,理应表现出远离凡俗甚至不近人情的超尘之气,行为上应避免与俗世中人过从甚密,心理上也应拒绝一切可能的男女之情。在与张于湖的故事中,陈妙常断然拒绝张于湖,无疑是对新身份的适应与自我规诫,甚至是自觉地披上了作为“仙姑”的人格,因此,张于湖与陈妙常这段有才子佳人雏形的故事未能继续。但另一方面她又并未抗拒与张于湖的独处,甚至与他对弈,也可视作旧身份在陈妙常身上的一丝留存,为潘必正重新萌发她的旧身份提供了可能。
(二)爱情的发生
潘陈爱情发生与确定的过程是陈妙常内心所藏陈妙莲的情感与人格逐步复萌的过程,到〈词媾〉一出二人确定关系时,陈妙常已经放开了内心对道姑身份的纠结与犹疑,而是将陈妙莲所具有的少女情思悉数放出,成为一个披着道姑身份的实实在在的俗世少女。这一过程的实现,与潘必正作为陈妙常旧日人际关系与今时处境相连的纽带,而达成逐步释放陈妙莲人格的效果密切相关。
〈下第〉一出二人初遇,陈妙常虽有“相公,看你眸含星电,气吞霜剑”2等表示欣赏之语,后文〈幽情〉也提示了陈妙常其实对潘必正于初见已有所留意,但始终维持在正常的距离范围之内,也并未描写陈妙常的心动之发生,可以说此时她仍然谨遵道姑应有的行事风格。
〈幽情〉一节,二人在陈妙常处小聚,潘必正以“独守长门”“红新绿嫩”“蜂衙蝶阵”3等传统闺阁伤春题材中常见之语相勾,固然是对仙姑之挑逗,但更加是唤起作为闺阁女子的陈娇莲对青春的感叹,是借潘必正之口诉说旧身份的应有之情,也是潜藏在仙姑人格之下的二八少女旧身份的第一次呼唤。但“仙姑”陈妙常却仍然谨遵着一个出家之人应有的“不管春愁恨”,以“免劳魂”对潘必正的挑逗予以拒绝,展现出与前文拒绝张于湖时近似的道姑人格。虽然其外在表现如此,但从下文〈寄弄〉不难发现此时陈妙常心中已有触动。
〈寄弄〉写陈妙常抚琴,实则隐约展露了其外在言行之下的内心想法,由“朱弦声沓恨溶溶,长叹空随几阵风”能够窥见时时保持道姑做派的陈妙常心中已有变化发生,旧身份遗留的情感与新身份应有的行为和人格之间出现了错位。陈妙常以琴声为载体的私人情感入了潘必正之耳,其心中刚刚萌发的一点属于旧身份的少女心性被潘必正撞破,书生已经知道此时“仙姑”之态是她适应新身份而不得已的伪装,因而“露冷霜凝,衾儿枕儿谁共温?”4之语即是设身处地替她道出作为“仙姑”的无奈,亦是令陈妙常正视旧身份遗留情感的尝试。
潘生临走时陈妙常偷偷道出 “岂无春意恋尘凡”5,嘱托一句“潘相公,花阴深处,仔细行走”6,这是陈娇莲在她身上的一次闪现,而当潘必正见状说要借灯时,陈妙常又故意急急关门,此处的纠结与态度的摇摆,无疑是新旧身份之间的一次角力,少女陈娇莲想尽情表达,而道姑陈妙常则竭力压制着前者的春心和冲动,然而最终她还是承认,道姑的孤清不过是“脸儿假狠,口儿里装做硬”7。于此,陈妙常独处时几乎已经承认了心理层面上旧身份的回归,然而面对潘必正却仍要摆出道姑身份。
旧身份在心理上的彻底回归最终在〈词媾〉一节中完成,此前〈叱谢〉中陈妙常独自一人时已将内心的少女情思释放,并外化记录在词作中,而词作又恰好被潘必正见到,终于令陈妙常在面对潘必正时也不再需要伪装出道姑做派,而是以陈妙莲的少女身份和情感与之相处。于此,借助代表旧身份人际关系的潘必正,陈妙常完成了从认识不到新旧身份的情感错位,到正视情感,再到面对爱人时以旧身份人格相处的过程,是心理层面上旧身份的全面复活。
(三)爱情的结果
心理上陈娇莲的回归和现实中陈娇莲的回归之间,相差的就是象征二人旧日婚约的信物玉簪与扇坠,〈追别〉一出中,二人临别之际互赠家传信物,是订立新的婚姻契约,但由于对象和信物与旧日契约完全一致,因而也是对旧日婚姻契约的重建,同时为陈妙常变回陈娇莲提供了社会伦理上的可能。婚后道姑身份从外在角度瓦解,到潘陈二人回家拜见父母,两相核对信物后,社会身份为潘夫人的陈妙常与母亲相认,完全回归到陈娇莲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身份上。
四、总结
将陈妙常的两次身份转换相对比,战争导致的身份突变迅猛剧烈而被动,也因此在心理身份和性格上难以彻底改变,指向短时而猛烈的痛苦和不稳定的身份人格;爱情选择下的身份改变则相对主动和漫长,但却是旧身份逐步复萌的彻底变化,指向的是自主选择下,稳定且幸福的大团圆结局。
注释:
1.高濂撰《玉簪记》(明汲古阁刊本,下同),卷上,第26页上。
2.高濂撰《玉簪记》,卷上,第34页下。
3.高濂撰《玉簪记》,卷上,第41页下。
4.高濂撰《玉簪记》,卷下,第3页上。
5.同4。
6.同4。
7.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