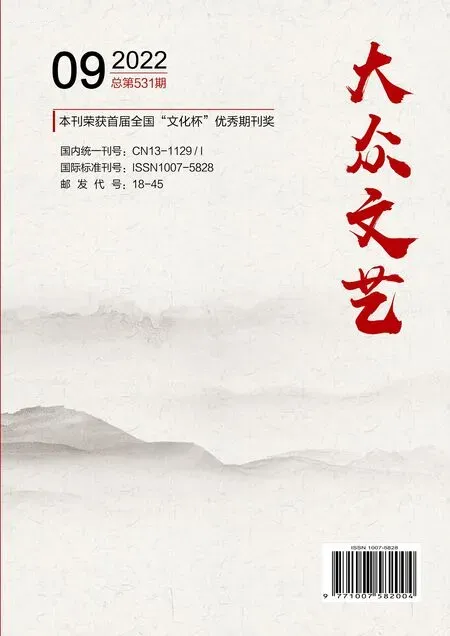由“死”向“生”的诗意栖息
杨梅李楠 薛钰琪 田孝引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430079)
死亡和失意带来的创伤是人生历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何消化生活带来的绝望与悲痛是人们需要穷尽一生去领悟学习的。海子与狄金森所谱写的死亡诗作奏出了不同凡响的人生乐章,两位诗人在由“死”向“生”途中的徐徐吟唱是生命尊严、意义与价值的映照。
一、向死而生——海子的诗歌创作及其死亡意识
海子的诗歌创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终于80年代末,期间海子共进行了九年诗歌写作。诗人王家新说这一时期是“一个荒凉的,从漫漫长夜中醒来的年代”。生长于乡村的海子饱尝了长夜浩劫之后整个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瘠,时下愈发物质化的世俗观念还使海子这样追求理想主义的诗人感受到了时代的精神危机,对自我生存的价值与实质产生怀疑,陷入到迷茫、失落与痛苦当中。秉持理想精神的文化信念及英雄姿态的海子致力于通过诗歌来拯救时代的精神危机。然而遗憾的是,他的诗歌在这一时期不仅面对着社会的质疑,还遭受着先锋文学内部的抵抗和排挤。在乡间生活了15年的海子与“根”之间的复杂羁绊也是他后期痛苦与创作灵感的来源。乡村对于他来说,既是其灵魂精神的寄托与归处,又是摆脱不掉的枷锁和束缚。在他进行创作的时期,中国文学界正掀起一波“寻根狂潮”,敏感的诗歌创作者们对传统价值观的流失感到不安与彷徨,于是开始寻求灵魂之“根”的所在。海子也将这样的冲动注入到诗歌中,创造出了他特有的家园意识,这使得海子能够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创造并尝试从中找寻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归属感。然而,物质世界中的“根”难寻,在爱情世界中海子也没有找到心之归处。四次爱情经历给了海子甜蜜与动力,而更多的是爱而不得的痛苦与绝望。爱情和理想以悲剧与灾难收场,“根”的缺失使得海子对生活的温柔吟唱逐渐变为了怅然若失的唳唳悲歌。
除了现实遭遇,宗教也给海子带来了灵魂与思想上的鸣击。道家的“方死方生,方生方死”强调人的生命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死亡与新生是同质的。海子也在《高原节奏》中写道“让无用的躯体去填充狂暴的生命/撕裂声是对死亡和过去最好的期待”——生命是不断延续的,肉体的撕裂与消亡是一定意义上的结束和告别,但也是另一个开始。
同时,海子的生命气质和心灵结构与叶赛宁、荷尔德林等他所喜爱的诗人有极高的相似度。从海子的角度看来,他与“诗歌王子”们都经历了在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灵魂、生与死之间的精神苦斗,而这些诗人对生死实质的思考与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海子对生死的看法。譬如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即是走向死亡的过程,死亡实际上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这与海子认为死亡实则是生命的另一种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契合。前人的意志与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海子做出了“终结肉体以寻灵魂自由”的选择。“怀抱心上人摔坏的一盏旧灯/怀抱悬崖上幸福的花草纵身而下”(《不幸》)中从悬崖上纵身而下的不是赫尔德里,也不是海子,而是他们二人的合体。
总的来说,海子一生都在处理生命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关系,二者之间越来越大的间裂不断地给他带来撕裂感与不真实感,他也逐渐从一开始追求二者合一的状态变为了在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之间、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肉体存在与精神永恒之间摇摆不定的挣扎状态。从理想到绝望、爱情到孤独,包括其在后期对自身存在的否定以及其精神领袖的死亡,都使得海子开始对生命及肉体在形式上存在的意义有所怀疑,转而寻求更高、更纯粹的生命形式与存在状态——死亡。在海子看来,死亡是必定的,是肉体的消解,同时也是精神与灵魂的解放,这能使他的精神挣脱物质的束缚,自由地去追寻远方——死亡是灵魂的新生,是另一个崭新的开始。正如“我的自由的尸体在山上将我遮盖 放出花朵的/羞涩香味”(《答复》)所传达的,海子并不惧怕死亡,纵使肉体死去,他也会像山间花朵一般给人间带来香气。
二、诗意栖息——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创作及其死亡意识
18世纪60年代爆发的美国内战和疾病的肆虐给狄金森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起居室正对着镇中墓地的狄金森目睹了许多生命最后的终结,这让她对死亡的感触无比深刻。此外,生活在主张女子应成为谦卑的“第二性”的时代的狄金森选择了追求自我张扬、自我独立的抒情诗这一文学形式,因此她的创作并不受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屡次打击使得诗人对生活的美好憧憬终被现实逐一打破,内心难以排解的苦楚和沮丧让狄金森对死亡有了不同的思考。另外,敬爱的导师牛顿和沃兹渥斯的去世、父母亲友的相继辞世使得狄金森更深刻地感知到了死亡的痛苦,在这不断重复又看似无尽的悲伤中,狄金森的灵魂似乎在她的肉体真正消逝前已死去了无数次,痛苦又无力的诗人悲叹道“我经常想到坟墓,想到它距我有多远,想到我能否阻止它夺去我的亲人。”
和海子一样,狄金森的生死意识也受到了宗教的影响。狄金森生活在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小镇,人们都坚信万能的上帝从人出生开始就已安排好了一切,且每个个体都可获得指引和解救。在这种宗教氛围的熏陶下,狄金森一开始对上帝和生活都充满了憧憬。然而随着死亡与苦难一次次地降临,她的内心开始滋生困惑与矛盾。一方面,她认为上帝应带给虔诚之人以永生;另一方面,她又认为上帝是冷酷无情的,她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上帝会剥夺自己所爱之人的生命。这样的冲突是她痛苦与寂寞的根源之一,也成为了她创作“死亡诗歌”的灵感。
无论如何,社会的不认可、爱情的无望以及死亡气息的笼罩使得狄金森最终选择了漫长孤寂的避世隐居生活。“独”成为了狄金森逃避痛苦、寻求安宁的方式,她投身于孤而静的状态,并参透了于她自身而言的生命真谛。在世人看来,生与死处于对立的位置;而在狄金森看来,“死亡”与“永生”是同一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反而是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狄金森的死亡诗摒弃了恐怖、阴森与瘆人,写满了诗意、浪漫和梦幻。这苦楚的人世间中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因而狄金森不仅不畏惧, 相反还对死亡有一种亲切感。她敏锐地感知死亡的临近,并伴以欣赏无畏之心吟唱了绝美独特的生命曲调。狄金森在临终前留下一张字条,上书“Called back”(归)。这一“归”字,书明了诗人的态度:死亡是生命的一种回归,生即死,死亦生。
三、死亡如歌——海子与艾米莉·狄金森的死亡意识对比分析
海子与狄金森对死亡在很多时候都是从容不惧的态度。海子在《自杀者之歌》中写到“肉体,水面的宝石/是对半分裂的瓶子/瓶里的水不能分裂/伏在一具斧子上/像伏在一具琴上。”诗中一共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自杀法,斧子只是其中之一。然而,海子在描写这样绝望悲痛之事时流露出的感情却并不悲观。相反,他将斧子比作乐器,暗示着死亡如歌。另在其诗歌《肉体》(之二)中海子强调“肉体美丽/肉体是树林中/唯一活着的肉体/死在树林里/迎着墓地/肉体美丽”,诗的最后两节道出了肉体勇敢地选择死亡,这美丽的时刻既不凄惨也无不舍,最后一节中“迎着墓地”四字更是显示了诗人的决心。
同样地,《我不能为死停留》一诗“我不能为死停留/他便和善地为我止步/……我们缓缓前行/他知道不必着急/……我终于想到马头应是朝着/——无尽无止”描绘了一位温文尔雅的死神。死神好心地为诗人停下,缓缓驾着马车载着走向永恒。狄金森眼中的死亡是永生的开始,不可避免也无需逃避,而她自然也就对死亡坦然无惧。
此外,死亡在二人看来都是一个轮回。海子用一种辩证轮回的思维看待生死,认为生殖与死亡是不断相互转化的过程。其在《土地 忧郁 死亡》中道:“黄昏,我流着血污的脉管不能使大羊生殖/黎明,我仿佛从子宫中升起,……”诗中的黎明代表新生,夜晚象征死亡,而白天预示生命的进行也不过是走向死亡。同样地,狄金森在此也不约而同地体现了一种对死亡的辩证与洒脱。《在我之后-永恒下沉-》一诗中,狄金森用“东方既白-白日-西方落日”来隐喻生命的“前世-现世-后世”。生命在不断发展,从日出前东方一缕灰色开始,到太阳升起生命绽放,再到正午生命达到鼎盛,直至太阳西移黄昏,生命结束。新的轮回在夜晚的黑暗中重新孕育,生生不息。
然而,二人的死亡意识也并非完全一致。海子对死亡无惧甚至是向往的原由之一是其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无法实现的打击,狄金森对死亡的无畏赞美则主要源自于苦痛世事与短暂欢愉的交杂。有诗为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是海子对理想生活的追求,“马”即是追求理想的工具。而现实世界并不允许海子如此超脱,因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八字表面柔软温暖,实则被赋予了沉重的内涵:追随理想,燃烧生命。反观狄金森则更着眼于现实世界,美好时光的易逝更是她常叹的内容,在《假如最美的时光能够久长》一诗中狄金森道“假如最美的时光能够久长/那必将取代天堂”,人世间最美的时光可以取代天堂,可惜转瞬即逝,只有少数人能得到,这种极致欢乐只会在绝望时刻给人带来些许刺激罢了。字里行间弥漫着狄金的失落感,而这种体验或将人引向绝望与孤寂。
可以看出,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家庭和宗教等外部因素与个人成长经历、个人心境等内部因素对于个体的死亡意识形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压抑的社会环境、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事业的受挫、感情的坎坷及无法避免的亲朋逝世等都会让人产生丧失、绝望等消极情绪,进而导致内心创伤体验的增加与个体身份认同的崩塌。消极情绪得不到舒缓,逃避情绪不断加剧放大,当这样的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个体就会挣扎于无限的痛苦和悲伤之中。海子与狄金森便是因为“生”时的忧伤困顿无法排解而转向了对“死”的思考探寻。
四、结语
海子与狄金森究其一生都在寻找生命价值所在,其中充满了愁闷以及困惑。他们在苦痛和迷茫中探求死亡的含义,认真品味生活之艰辛,对于死亡的内在渊思寂虑;他们越过生命的极限谈论死亡,对于死亡的到来安然而又超脱。但是,死亡不是逃避的去向,也不是绝望的终点,除却社会文化背景与家庭环境等不可控因素之外,个人心境与意识观念是可以控制、可以改变的:如何用更理智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生活、对待死亡、对待生命,在有限的人生路上更美好的绽放自我,是每个人穷其一生的所追所寻。海子与狄金森的思想恰好可以引导人们由“死”观“生”,认识到死亡之于生命的意义——死亡或许是永恒的开始,亦或是永远的结束,而如何令当下的人生绽放出它独特绚烂的色彩才是生命之浪漫勇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