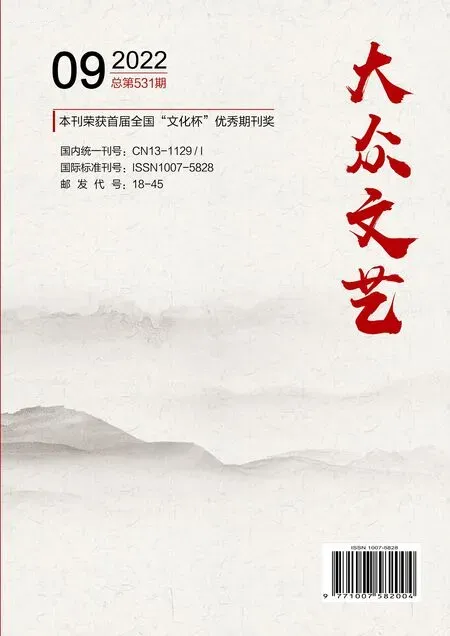福柯权力理论视角下格兰西《舞伴》解读
丁曙婷 邹惠玲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21000)
戴安娜·格兰西(Diane Glancy,1941—)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本土裔剧作家、小说家、诗人。格兰西是切诺基和德裔美国人混血儿,出生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其作品《舞伴》( The Dance Partner, 2005)是一部由历史期刊、创作性非小说、当代神话和日记节选组成的小说,内容涵盖鬼舞运动、苏族起义、大平原印第人历史事件以及当代印第安人生活状况等,表现了白人权力下的印第安人的生活境遇。
本文以格兰西的《舞伴》为研究文本,借助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解读该作品中白人殖民者利用话语和规训权力对印第安人进行土地掠夺和文化摧毁,最终导致印第安人精神的迷失;本文认为格兰西在《舞伴》不但展现了白人权力对印第安人的权力压迫,而且表现了印第安人严重的精神危机。
一、白人的权力压迫
在《舞伴》中,白人的权力压迫主要表现为对印第安生存空间的占领与印第安文化空间的压缩。换言之,白人利用权力剥夺印第安土地、破坏印第安文化。本节主要探究白人如何利用权力剥夺印第安土地、破坏印第安文化以及对印第安人精神与文化所造成的伤害。
1.印第安生存空间的占领
福柯在《安全、领土、人口》中指出:“空间是权力运行的基础”(25-26)。因此,对于白人殖民者来说,土地扩张能够巩固和增强其权力。因此,土地作为重要的权力与生存空间,是造成白人殖民者与印第安人冲突的主要原因。在《舞伴》中,白人殖民者掌握权力,采取不同的权力手段,迫使印第安人签署割让土地的不平等条约。格兰西讲到,《印第安迁移法案》使印第安踏上了“血泪之路”,将印第安人推向了密西西比河以西,并将为印第安人划定了保留地,限制其活动范围。印第安人将白人称为“在印第安土地上圈划保留地人”(Glancy 2),并且“白人成群结对的来了——政府的军队”(Glancy,19)。格兰西将白人殖民者比喻为政府的军队,暗示了白人殖民者在北美的权势不断扩大。1887年美国政府颁布了《道斯法案》,其目的是增加白人的土地,并对印第安人进行同化,进一步缩小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空间。在土地分配过程中,白人殖民者掌握着绝对的分配权力,他们为印第安人划定土地的大小,将最贫瘠的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同时,伴随白人殖民者而来的是,火车的通行和铁路的修建,这不仅暗示了白人殖民者权力的扩张,而且展现了白人殖民者可以攫取了更多的印第安土地。总言之,格兰西揭示了白人殖民者以一种霸权主义的方式,占领印第安人的生存空间,将印第安人推向了边缘地位。
在占领印第安人土地的同时,白人殖民者试图控制印第安人的活动,以防止印第安人的行为威胁到他们的权力。白人殖民者划定了保留地的边界,并要求印第安人不要越过边界。正如福柯所说,在空间中,最细微的运动都受到监督,所有的事件都被记录在案,每个人都不断地被定位、检查和分布(195)。在保留地中,印第安人不仅受到白人殖民者的摆布,而且还受到白人殖民者的监视。在《舞伴》中格兰西塑造了一位印第安人,他带着行李去乘飞机,但在下机时必须要接受白人殖民者的“搜查”,然而这个被监视的过程给他带来了“恐惧”和“不安”(Glancy,6)。格兰西进一步指出,“天国的山川平原”,“你想去的地方”,是无法到达的,因为“地球上到处都是边界和屏障以及安全门”(Glancy 7),这表明白人殖民者是靠边界、屏障和安全门阻止美国印第安人返回家园。同时,这也揭示了白人殖民者切断了印第安人和土地之间的联系。然而,面对白人殖民者的权力压迫与土地占领,“印第安人秘密交谈。他们在黑暗中交谈”(Glancy 2)。换言之,由于对白人殖民者的无情剥夺,印第安人一无所有,他们只有保持沉默,无法为失去的土地发声。总而言之,格兰西强调,保留制度不仅使印第安人失去了他们原来的土地,而且使他们生活在白人殖民者的控制之下。
2.印第安文化空间的破坏
关于文化与空间的关系,邦尼米森指出,文化空间是地域的基础,是人类空间的基础,是每个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基础(45)。格兰西在《舞伴》中介绍了白人殖民者的同化政策,强调了寄宿学校和教堂的建立破坏了印第安文化,切断了印第安人与其传统文化的联系,破坏了印第安人的文化空间。
格兰西在《舞伴》中表现了印第安人不仅隔断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而且被迫在寄宿学校和教堂接受基督教文化,强调了寄宿学校和教堂在某种程度上,摧毁印第安文化,使印第安人陷入了精神危机。白人殖民者强迫把印第安人的孩子送到遥远的寄宿学校;他们的父母好几年都没有见到他们,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已对部族与家人感到十分的陌生(Glancy 19)。此外,在寄宿学校里,白人殖民者强迫印第安儿童接受西方文化,禁止使用印第安语言。格兰西在讲到,寄宿学校的修女讲述天堂和地狱的故事,展示了天堂和地狱的画面,目的是将印第安人基督化。同时,在寄宿学校里,印第安人受到白人殖民者军事化管理;如若不遵守寄宿学校的纪律,他们将受到残酷的惩罚,这表明寄宿学校严格的纪律给印第安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因此,对印第安人来说,寄宿学校是“鞭子学校”“皮带学校”(Glancy 77),揭示了白人殖民者的目的都是使印第安儿童基督化,最终导致了对印第安部落习俗和文化的破坏。
此外,白人殖民者将基督教传播给印第安人,并要求他们皈依基督教,这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印第安人的文化。正如格兰西所说,传教士“上帝的军队”穿着“黑袍”来到这里,他们建造了“带尖塔的方形教堂(Glancy,19);在方形的建筑中,传教士不断改变基督的故事,以迎合印第安人的心理需求,并引诱他们皈依基督教。换言之,传教士以同化美国印第安人为目的,通过编造不同的故事,将基督教传授给美国印第安人。最后,“像野花一样绽放的白色十字架”(Glancy,7)。格兰西将白色十字架比作野花,暗示了基督教在美洲大地传播的广泛性,综上所述,白人殖民者侵占印第安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把基督教作为驯服美国印第安人的有力武器,给印第安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总而言之,格兰西在《舞伴》中揭示了白人殖民者对侵占印第安文化空间所采取的不同措施。为了在文化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白人殖民者为印第安人建造了寄宿学校和教堂,强迫印第安人接受白人文化。为此,格兰西谴责白人的霸权主义行为在身份、思维方式、文化以及语言等方面对印第安人造成了深刻的创伤。
二、印第安人精神危机
白人殖民者的权力压迫导致印第安人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日益缩小,一些印第安人变得越来越沮丧。在《舞伴》中,由于长期遭受白人殖民者的权力压迫,印第安人选择酗酒、自杀、暴力等自我毁灭行为,反映出他们所承受的恐惧、焦虑、怨恨和绝望等精神压力。
在《舞伴》中,格兰西以印第安孩子的视角,展现了一个醉酒的父亲形象。早晨喝醉的父亲把酒瓶打翻,跌跌撞撞地走进房间。当父亲跌倒在地上时,他便嚎啕大哭起来。格兰西通过对这种场景的描写,强调了精神错乱的父亲只会选择整天酗酒来排解内心痛苦之情,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印第安人颓废的生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印第安人文化的丧失是现存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而与之相联系的是酒精的滥用”(Beauvais 256)。孩子们告诉他,“基督已在任何地方,哪怕是我们生活中”(Glancy 80),这表明白人权力就像一张网,而美国印第安人困在其中。
《舞伴》的“一块绿旧布编织的地毯”这一部分以二十世纪60年代将印第安孩子寄养在白人家庭的“掏空”运动为背景,讲述一个印第安男孩,名叫卡迪诺,被白人家庭收养,多次试图自杀的故事。在寄养在白人家庭家庭中,他不仅为白人主人劳作,而且还要接受白人文化,这让他感到“孤独和沮丧”(Glancy 86),最终他选择了死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正如学者所说,自杀是反抗的最终行为,反映了被困和囚禁的灵魂的绝望和不愿意继续受苦(Lafromboise and Bigfoot 139)。因此,对于印第安儿童来讲,寄养于白人家庭不仅意味着切断了与家庭的联系,而且意味着接受白人文化。丧失文化身份的卡迪诺不堪精神的折磨,选择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暴力也是印第安人的精神危机的表现。在小说中,一群印第安人经过白人的农场,其中一印第安人建议杀死这个白人和他的家人。印第安人之所以选择暴力,是由于白人开垦土地威胁了印第安人身份的构建。白人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耕种,破坏了原始的景观,因为土地、树洞、洞穴和湖泊在构建印第安人身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印第安人“射杀了所有从此地经过的人”(Glancy 46),其中包括商人、职员和医生。在这些人死后,这群印第安人也不断地“刺杀”他们死去的身体。这些印第安人近乎疯狂的暴力行为暴露了他们的精神危机。显而易见,白人带来的痛苦迫使印第安人对白人的压迫使用暴力。因此,对印第安人来说,诉诸暴力表达了他们对白人的怨恨,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所承受的精神危机。
格兰西在《舞伴》中表现了,由于白人权力的无情压迫,导致许多印第安人已经失去了面对悲惨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走向了社会边缘化。综上所述,印第安人因酒精、自杀和暴力等自我毁灭行为,反映了印第安人主体性的丧失,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
三、总结
通过对格兰西《舞伴》中白人的权力压迫和印第安人的精神危机的分析,本文揭示了白人殖民者利用话语权力与规训权力掠夺印第安人土地、摧毁印第安文化,导致印第安人的丧失了自我主体性、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危机。据此,《舞伴》不但表达作者了对白人权力压迫的愤恨之情,而且表现出她对印第安人精神危机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