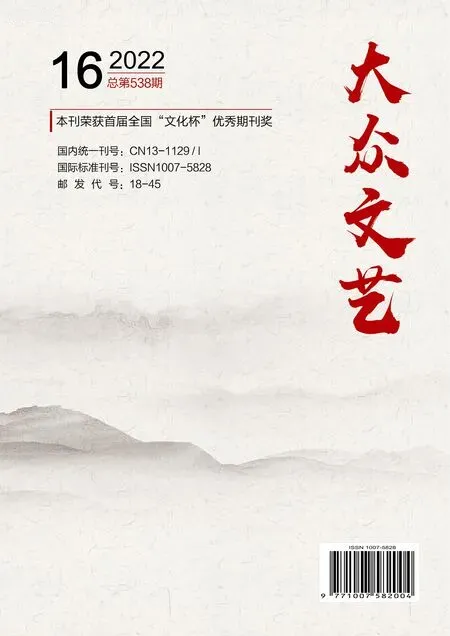油画创作的多可能性:卡拉瓦乔的颠覆与创造
——试论卡拉瓦乔绘画的现代性
(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济南 250014)
意大利评论家达里奥·福曾说:“卡拉瓦乔是被魔鬼控制的天才艺术家。”[1]卡拉瓦乔以其独具创造性的画作,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影响。他的叛逆性与作品的多向度使其很难被简单地归并到某一个画派中,而成为一个绘画时代的开启者,被称为推开17世纪艺术大门的艺术家。在他复杂的绘画中,可以发现其中的现代性的批判继承思维和审美现代性的选择和自由想象。而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modern)不同,后者一般有着较为清晰的时间指向,而前者则是一个较为模糊的词汇。关于现代性的认知,福柯曾谈道:“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2]随着波德莱尔、本雅明以及福柯等学者对于理论文本分析的努力,现代性的范围空前拓展起来。
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卡拉瓦乔在自己狂傲不羁的39年短促生命历程中,经历过名噪一时的幸福享乐也经历过杀人犯罪的惨淡逃离,是与时代进行博弈的反叛者形象。卡拉瓦乔以其疯狂的一生和跌宕起伏的绘画风格,在文艺复兴时期描绘出一系列“人”的形象,与“人文主义”相呼应。但在其具体的绘画作品中,其对于宗教题材人物形象的颠覆、底层绘画的心里展现以及后期暗黑风格的画法,呈现出现代性因素,展现出先锋性与独立性的一面。
一、宗教神话题材的人物形象颠覆
在卡拉瓦乔的宗教题材的画作中,“突出捕绘暴力的斗争、奇异的斩首、拷打和死亡等内容。……拉瓦乔作品的强烈戏剧性被人们赞赏的同时,也有一些人接受不了他的现实主义风格,甚至有些人认为他的作品很粗俗。”[3]在众多艺术评论中,人们对于卡拉瓦乔作品现实主义倾向是持肯定态度的,越看越真实,真实到仿佛现实是虚伪的,只有在他的画作中才能看到真实,这种强烈的真实感使得一些评论家将其论说为自然主义。在文学方面,自然主义又以其绝对的表现现实为揭开了现代主义的一角。在卡拉瓦乔的宗教绘画中,如果抛去宗教的故事外壳,再去注视这些人物时,鲜活的现世气息便会扑面而来,喜怒哀乐、恐惧和阴谋得到了交织显现。
在他在米兰的画作中,《生病的酒神巴库斯》赫赫有名,画中的酒神脸呈银灰色,双唇泛白,支撑身体的右臂呈现出勉强支撑的感觉——因为肌肉紧绷性不强,皮肤苍白,举着葡萄却仿佛没有胃口,这是由于病痛而导致的虚弱。很多评论家曾谈到这取材于病中的画家自己,神作为神的完美面纱被揭开,酒神不再只是充满着激情饱满、疯狂与浪漫的神性色彩,不再是传统绘画中描绘出的生命的张扬和旺盛,黑色的背景成了人物的背景,而不是当时流行的明朗。人物整体的色调呈现出昏暗感,在光的强烈对比下,一个鲜活的人走了出来,带着病态的生命力,给人一种颓废感。“一旦你获得了发现颓废症状的敏锐眼光,你也就理解了道德——理解了在它至为神圣的名义和价值准则之下暗藏着什么:贫困的生活,终结的意志,高度的倦怠。道德否定生活。”[4]画中酒神的倦怠、颓废,展现了在病痛下神性的瓦解和人性的昭示。体现出卡拉瓦乔的大胆洞察。《圣母之死》画中的圣母不再是传统宗教绘画中沉睡的状态,而是如同凡人妇女无二差别的死亡描绘,画中的圣母既是基督之母,也是做模特的高级妓女,这一切都展现出对传统认知的颠覆。而他本人也“嫌恶罗马那些所谓伟大艺术的价值……他拒绝描绘凭自己想象力杜撰的关于历史的画作。”[5]卡拉瓦乔的画作中,神性让位于人性,而人性又展现出痛苦下的人性的颓废和受难,在静穆的神像之下打破了神圣世界和世俗生活的厚壁,人性得以复归,构成极大的艺术张力,展示了富有自由选择和个性颠覆的现代性。
二、现实题材与静物画的独特视角
卡拉瓦乔出身贫穷,对于穷困潦倒的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他的现实题材的画作常常是一些平凡人物的刹那剪影,在瞬间捕获人物神态和细微动作,潜藏无数的故事和丰富的戏剧性。这种戏剧化给人一种梅尼普体的即时感,巴赫金曾详细论述:“梅尼普体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表现为其中自由的幻想、象征,偶尔还有神秘的宗教因素,同极端的而又粗俗(据我们的观点看)的贫民窟自然主义,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真理在人世间的种种探险奇遇,都发生在通衙大道上”。[6]巧的是,卡拉瓦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都曾在赌场流连忘返,对于赌徒这一形象,陀氏曾写过《赌徒》,卡拉瓦乔的《诈赌者》也是一副传神之作,年轻的赌手涉世未深,作为老手的诈赌者面朝着年轻人,眼神却游离于焦点之外,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在他背后的牌中,中年男人瞪大了双眼直视者年轻人的牌。我们仿佛可以推测出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背后的画家远远看着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情节,不同的人物在此交织,在交流中产生丰富的心理活动,细微动作体现出一种精神颤抖的狂欢感。卡拉瓦乔甚至会充当画作中的角色,与其中的人物表演、对话,呈现出创作者和被创造者的融合交汇。
在静物图中,卡拉瓦乔也展现出他的写实绘画的别出心裁之处,在《水果篮》这幅画中,他的写实达到了让人瞠目的境地,从苹果上的虫印,叶子上的虫洞咬痕到葡萄上的白霜,现实的残酷性和萎谢的隐喻在此明确地表达出来,又一次体现了卡拉瓦乔这一集疯子与天才于一体的破坏性和颠覆性。同样,在酒神手下的水果景物,即使是供神享用的水果,也有蔫了一半或有轻微划痕的情况,如在神的光辉下露出了现实的洞,卡拉瓦乔的反叛性也就在此得到了彰显。
三、巴洛克、恐怖题材与唯美主义
在名盛一时的同时,卡拉瓦乔的出格行为和绘画手法也招致了许多反对者,他的很多画作都面对着被拒或者被修改的处境。然而他的绘画作品的绝对细腻为后世的巴洛克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后世的巴洛克却没有完好地继承卡拉瓦乔的写实性的倾向,而是走向了华美的炫技。但无论如何,“现代性的特征是批判:新的东西要超过和反对旧的东西,而正是这种不断的对立才构成了传统的延续……在巴洛克艺术中,它是一种夸张,”[7]卡拉瓦乔和巴洛克风格一起,体现出艺术风格创新一以贯之的叛逆性——细节的精美与过分的夸张。卡拉瓦乔的绘画作品中的历史人物或者教会人物服饰精美,果篮纹理细致甚至包含了光影的二重性,人物不再死板,而是恐惧、悲哀与不安等感情的交织混杂。
卡拉瓦乔一生经历坎坷,在大富大贵和至贫至穷之间来回周旋,饱尝生命的大起大落,他画作中对于死亡、头颅的等宗教题材的关注也体现出卡拉瓦乔的特殊选择,这样一系列恐怖意象和殉难、死亡的场景让人不得不想起后世的一位唯美主义画家——恐怖美学和死亡美学的代表者爱伦坡。“在现代视野中,唯美主义艺术精神……用感性对抗理性,用本能对抗理智,用主体对抗客体,用个人对抗社会,用个体自由代替社会承担。”[8]而同样把卡拉瓦乔在追求写实的同时还呈现出对死亡场景的偏爱,圣母之死、耶稣殉难、圣马太殉难等一系列殉难死亡题材被卡拉瓦乔刻画勾勒,其中的神圣宗教人物在死亡之前呈现出现世死亡的一般场景——阴暗、失去呼吸、皮肤变色、血液飞溅等等。《大卫手持歌利亚的头》以及《莎乐美收到施洗约翰的头颅》这个让人不禁想起王尔德的《莎乐美》中的死亡美的追求。此外,人头骨在《沉思中的圣弗朗西斯》《圣杰罗姆在写作》《圣杰罗姆》等宗教画作中都有出现,并占据了画作明亮面,思考与创作在人的头脑中进行,而把头颅拿出来放在画面上,则把创作与构思和死亡与永恒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卡拉瓦乔的绘画的叛逆性在此得到了清晰的体现。这些恐怖的场景体现出卡拉瓦乔对于宗教故事现场的自主性看法和一种叛逆性的创造。
卡拉瓦乔的画作严肃、真实、精致,人物表情鲜明,明暗对比强烈。在他的画作中,我们常常看到的背景是黑色的,仿佛是诗人的底色一般,充满着黑色的神秘与叛逆,在这这股神秘与叛逆中,作者参与到整个画面中来,或是在明面,照亮人物的侧影,在他们眼神的光泽中进行心理的大胆想象与绘画。他的叛逆性与作品的多向度使其很难被简单地归并到某一个画派中,而成为一个绘画时代的开启者,因而在他复杂的绘画中,可以发现其中的现代性的批判继承思维和审美现代性的选择和自由想象。他和中国魏晋时期的嵇康一样追求主体性,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传神地展现出人物心理世界,他阴暗的画风和强烈的明暗对比给人一种波德莱尔低沉感,对人物的精心绘制又为后来的巴洛克风格开了先河。卡拉瓦乔常常将自己融入画作中去,充当画作中的人物,与宗教神话人物交流并参与到历史和神话中,试图以一种永恒的姿态继续发现画面中人物的内心。他的画作影响了后世的艺术创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转向提供了有力的推动力。而这种病态又真实、多重可能性的创造、对于传统叛逆与颠覆以及对于颓废恐惧等题材的大胆绘制,正式其现代性品质的最明显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