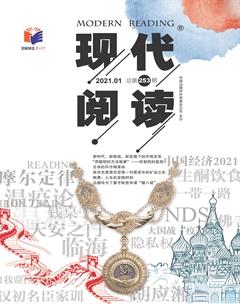语言差与时间差
谢天振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出去”,成为从国家领导到普通百姓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但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不是要搞“文化输出”,更不是要搞“文化侵略”,而是希望通过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学,在世界各国的译介,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从而让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建设一个更和谐的世界。众所周知,文学和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形象、最生动的反映,通过文学和文化了解其他民族,也是最便捷的途径之一。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国家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一个认识误区,即将其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翻译问题,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和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学和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问题当然并非如此简单。
最近几十年来的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理论和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都已经揭示,翻译不是一个在真空中发生的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行为,而是一个受到译入语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时代语境、民族审美情趣等许多因素制约的文化交际行为。因此,想要让翻译取得预期的效果,产生应有的影响,我们的目光必须从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跳出来,关注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包括翻译与文化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的传播方式、途径、接受心态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借助译介学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我们就会注意到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某些做法存在的问题。譬如,以国家、政府的名义,编辑和发行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月刊,向外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以国家出版社的名义,翻译、出版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熊猫丛书》等。这些做法其效果究竟如何,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有哪些经验和教训等,都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总结。
限于篇幅,本文仅提出其中两个被我们忽视的问题,一个是语言差问题,另一个是时间差问题。
所謂语言差,指的是使用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现代西方语言并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方面,比使用英、法、德、俄等西方现代语言的各西方国家的人民学习、掌握汉语及理解中国文化要来得容易。
所谓时间差,指的是中国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西方、了解西方,积极主动地译介西方文化至今已经持续一百多年了;而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这二三十年的时间罢了。具体而言,自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并带来了西方文化;清末民初,中国人更是兴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与之相对的,西方开始有比较多的人积极主动地来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还是最近这二三十年的事。
由于语言差的存在,因此虽然在中国能够有很多精通英、法、德、俄等西方语言并理解相关文化的专家学者,我们却不可能指望在西方同样有许多精通汉语并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更不可能指望有大批能够直接阅读中文作品,并能比较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普通读者。而由于时间差的存在,中国拥有比较丰厚的西方文化积累,也拥有一大批对西方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他们都能较轻松地阅读和理解译自西方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当代西方则不具备我们这样的优势,更缺乏相当数量的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译自中文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的读者。某种程度上,当今西方各国阅读中国作品的普通读者,大致相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年代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明乎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当今西方国家的翻译家们在翻译中国作品时,多会采取归化的手法,且会对原本有不同程度的删节;而我国出版社提供的无疑更加忠实于原文、更加完整的译本,在西方却会遭到冷遇。只要回想一下,我们国家在清末民初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时,也经常对原文进行大幅度的删节,甚至还要把外国的长篇小说“改造”成章回体小说,这样才能被当时的中国读者所接受,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今天中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化典籍在西方的遭遇了。
有人也许会质疑上述“时间差”问题,认为西方对中文的译介也有很悠久的历史,有不少传教士早在16世纪就已经译介中国文化典籍了,譬如利玛窦。理雅各也在19世纪中叶译介了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典籍。这当然是事实,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另一个事实,即最近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已经发展成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多数西方读者满足于自身的文化,对他者文化缺乏兴趣和热情,这从翻译出版物在西方各国出版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即可看出:在美、英等国,翻译作品只占这些国家总出版物数量的百分之三五,与翻译作品占总出版物数量将近一半的中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语言差”和“时间差”问题的存在,提醒我们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必须关注当代西方读者在接受中国文学和文化时的以上特点。我们在向外译介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时,不要操之过急,一味贪多、贪大、贪全,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一些节译本、改写本,这样做的效果恐怕要比推出那些“逐字照译”的全译本、大而全的“文库”的效果还要来得好,投入的经济成本还可低一些。
“语言差”和“时间差”问题的存在,也恰好证明了国内从事中译外工作的翻译家还是大有可为的。我们以前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接受他国、他民族的文化主要依靠的是本民族的翻译家,是从文化的跨语言、跨民族传播与接受的一般规律出发而言的,譬如我们接受西方文化,或者东南亚各国接受中国文化,就是如此。但是由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语言差”和“时间差”,我们不可能指望西方也拥有众多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因此,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方式,中国的中译外翻译工作者完全可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事发挥他们的作用,作出他们的贡献。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海上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