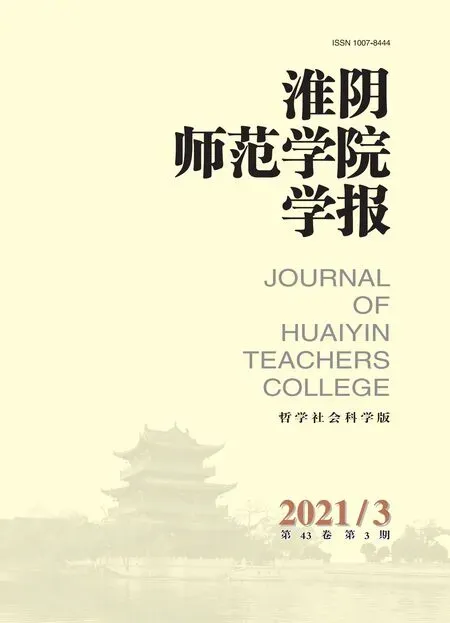不可误读的《天启淮安府志》和《先府宾墓志铭》
——兼谈《西游记》作者之争的学理与方法论
蔡铁鹰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尽管还是有人不断质疑吴承恩《西游记》作者的身份,但我个人认为,经过近百年来几代人的努力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长达十余年的充分讨论,围绕《西游记》作者的主要质疑已经得到澄清,吴承恩具有作者(写定者)身份的新的证据链已经形成,作品与时代、社会互通解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可以预见,《西游记》作为神话魔幻文学的顶级样本,“西游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吴承恩作为文学巨匠的绝代风标,都会在不久迎来三月阳春、四月芳菲的好时光。当然这个判断可能会被质疑——最新被举出的例证就是陈大康先生发表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西游记〉非吴承恩作别解》[1],其“别解”的意思就是否定。
发表否定的意见本身没有问题,学术的要义之一就是广泛的讨论商榷。但讨论商榷应该讲究证据、遵循规范、符合学理,可惜陈先生的文章在此方面让人失望。当初拜读了陈文之后,笔者随即向《复旦学报》发去了一则“读者反馈”,大意是说:这篇文章的内容没有涉及近二三十年的新意见,没有反映新的研究成果。陈先生判定吴承恩的父亲是赘婿,生活条件和精神状态都不很好,吴承恩一定受此影响生出心结,而《西游记》中有若干讥笑挖苦赘婿的情节,因此他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这个判断的基础就是《先府宾墓志铭》中吴锐“婚于徐氏”4个字,由这4个字就延伸出上述的推衍,怎么都算不上严谨。
对陈大康先生这一意见,河南大学曹炳建先生条分缕析,予以争鸣。曹先生在研究上心细如发,稳重有据,逐一考订陈大康先生推演[2]。因此本文不述及此问题,只想指出陈先生误读《先府宾墓志铭》的几个要点,更多的是借此机会,在话题中穿插笔者对于《西游记》作者之争的一些观点和有关学理方法论方面的一些粗浅看法,以与所有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共同探讨。
一、回顾问题:全面客观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基础
很多人在讨论作者问题时,都要回顾一下历史,因为全面客观的回顾,是正确结论的基础。
明万历二十年(1592),南京金陵世德堂书坊发售一种新的唐僧取经故事书《西游记》,此书20分卷,每卷5回,计100回。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百回本《西游记》,通称为“世德堂本”。原书没有标注作者,只是在标题之后,刻有“华阳洞天主人校”一行。书的正文前,有一篇“秣陵陈元之”应邀所作的《序》,其中提到,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这习惯上被称为“三个或曰”。此后作者之争不断:
1.明末市面上流行的各种版本,基本都是世德堂本的翻刻,不署作者姓名,现今将这类翻刻都称为世本系统。由于该刻本首页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因此也产生了若干对“华阳洞天主人”的猜测,如其人是李春芳、是吴承恩,等等。但李春芳、吴承恩都没有用过这个别号,与这个别号沾边的又与《西游记》没有关系,因此与此有关的各说始终未入主流。
2.清初道教中人汪澹漪刻成一部《西游证道书》,前有元人虞集署名的《序》,首次提到《西游记》作者为“丘长春真君”,并称其所据者为久已失传的大略堂古本西游,这造成了“丘处机说”两百多年的流行。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所谓的“大略堂古本”子虚乌有,虞集《序》则是一本正经的伪造。此说早已翻篇,时至今日还会有人提到“丘处机说”,但显然已经有醉翁之意了,在此不作讨论。
3.清中叶,纪昀、钱大昕等学者已经看出汪澹漪主张“丘处机说”乃故意作伪以自神其教的把戏,指出丘的《西游记》其实另有其书——丘处机弟子李志常记录这位道长追逐成吉思汗远行中亚的一部行纪,应该算是一本地理游记,与唐僧取经的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又有淮籍名学者如阮葵生、吴玉搢、丁晏等根据《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和其中方言,指出流行的《西游记》作者实为淮安乡前辈吴承恩。但他们交流的圈子都很小,没有形成实际的学术影响,因而有清一代“丘处机说”仍是主流。
4.进入19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等开始关注《西游记》研究,对于他们这样的学者,把《西游记》植名于丘处机名下显然是很容易被识别的错误。他们跟踪线索追寻到《天启淮安府志》,认为其中“吴承恩 西游记”的记录当属可信,这就定下了“吴著说”的基调,稍后,董作宾、郑振铎等附议。1929年故宫发现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1936年赵景深撰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1957年刘修业完成《吴承恩诗文集》笺注,1980年苏兴出版《吴承恩年谱》《吴承恩小传》,又有历年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西游记》“明 吴承恩著”的署名,都促成了近数十年来“吴著说”的一统天下之势。
5.到20世纪80年代,章培恒先生以一篇长文《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对吴著说表示怀疑。其意见集海内外学者疑问之大成,大要认为《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一个孤证,且并不能指实为是一本通俗小说,而很可能属于地理游记;其中又有吴地方言,因此写百回本《西游记》的也许另有其人。此说一经提出,即刻便引起广泛关注,又引出“西游记”可能是“西湖记”之误,通俗小说不算杂记,旧例不入方志,等等,包括陈大康先生的“赘婿”高论。争论前后延续十余年,逐步形成了“疑吴”“否吴”的观点。(1)疑吴否吴的观点主要体现在: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章培恒《再论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复旦学报》1986年第1期;杨秉琪《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所作》,《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李安纲《再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唐都学刊》2004年第4期。挺吴的主要观点体现在: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苏兴《吴承恩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期;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又研究》,淮安市西游记研究会会刊《西游记研究》第2辑,1988;蔡铁鹰《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的思考与辩证》,《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3—4期合刊;刘振农《“八公之徒”斯人考》,《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刘振农《再论〈西游记〉的作者与性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蔡铁鹰《〈西游记〉作者确为吴承恩辨》,《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杨俊《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回顾及我见》(上、下),《淮海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2006年第1期;以及刘怀玉及淮阴师院颜景常等多位先生的方言研究;等等。为简洁起见,以下引用时会对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概括,如有必要则介绍观点持有人姓名,其余则不再一一详注。
以笔者之见,最初对于“吴著说”的质疑,是正常的学术研究,经过10多年轰轰烈烈的争辩,讨论实际上在进入新世纪时已经结束。理由是:新的有利于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证据不断出现,当年章培恒等各位先生提出的质疑意见,经过各种角度的讨论,已经有了明确的答复,再也没有新的具有实质学术意义的证据出现,有价值的讨论已经结束。当然,明确的答复不一定就是指附议赞同,驳回、搁置也都算得上是一种答复。
二、请拿出证据来,质疑也要讲学理
近30年来,有具有学术意义、来路可靠、可以否定吴承恩作者身份的证据出现吗?没有。既然没有,那么现在研究者关注的质疑理由都已经在30年前讨论过了?是的。
但是在你来我往的商榷中,我们对那些讨论过的问题没有作“回头看”式的小结,没有上升到学理和方法论的层面上回顾,因此难免会有反复。我们无法阻止各种各样的炒冷饭——当然更无权阻止别人发表意见。但笔者可以声明自己的主张,即和任何正面主张需要证据一样,任何质疑也都需要证据,也需要讲学理,不可选择性忽略、无视,甚至刻意误读。
下面我们看看这些年各式“否吴”的观点和质疑的依据。
确定吴承恩具有作者身份的主要文献证据来自《天启淮安府志》(2)[明]宋祖舜、方尚祖编撰《天启淮安府志》,有荀德麟等校点本,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涉及吴承恩和《西游记》的著录有两处:
1.卷一九“艺文志·一”著录:
吴承恩 射阳集四册□卷 春秋列传序 西游记
2.卷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围绕这两处资料,产生了粗暴的误读。所谓“粗暴的误读”,指根本不认真琢磨其中的应有之义,甚至明明白白的文字都不愿多看一眼,就信口开河地放飞自己的想象。先列举几点比较简单的:
观点1:吴承恩有《西湖记》,但《西游记》系《天启淮安府志》的笔误。此观点的发明者是北京图书馆的沈承庆先生,他的《话说吴承恩》[3],其要点就是否定吴承恩《西游记》作者的身份。真不清楚老先生如何就知道吴承恩有本《西湖记》了(倒是有西湖诗)?又凭什么确定《天启淮安府志》所记是“笔误”,就凭比较书法中的各体写法吗?刻印府志用的可是正正规规的宋体,可是要经过若干次校正的。更不明白既然老先生不看好吴承恩,为何又用“吴承恩”入书名?离开《西游记》的吴承恩还值得老先生牵挂吗?
观点2:《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并未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本什么性质的著述,这就有了同名异书的可能。此说经常有人引用。如前所说,指出《天启淮安府志》的缺憾本来还属于学术质疑范畴,在理论上这种可能性有,但“吴著说”研究者已提供很多证据说明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并不存在。然而有些研究者就此咬定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同名异书,似乎这就是定海神针般的铁定事实。这个态度就不科学了。请问,异书在哪儿?如果要指实怀疑,必须找出“异书”作为证据,就像当年钱大昕从《道藏》中找出丘处机的地理《西游记》,立刻就让“丘处机说”现形一样!而这类证据我们始终没有看到。
观点3:《西游记》属于通俗小说,通俗小说按照旧例不入方志。此说也经常有人引用,好像是来自日本,很像一个特别高端、底气特足的根本无法反对的理由。但怎么清代学者阮葵生、吴玉搢、丁晏,近代学者鲁迅、胡适、董作宾、郑振铎,当代学者刘修业、苏兴都没发现还有这么一回事?谁定的旧例?有多少样本为证据?就在笔者完成《吴承恩与〈西游记〉》一书时,中州古籍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张弦生先生随手补了一个证据:清道光《宝丰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收入李绿园的《歧路灯》[4]18。“旧例”说还能成立吗?
观点4:清人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将“吴承恩 西游记”归入地理类,说明它应该是一本地理著作。这是章培恒先生首先发现的,似乎很有影响力,后来者经常宣称:“章培恒先生说过,《西游记》可能是本地理游记。”但30年前各路大神就已经对其中的各种可能性作了详尽探讨(3)请参见前注所引章培恒、谢巍、苏兴等诸位先生的论述。,留给笔者的印象是:《千顷堂书目》的著录属实,但如天马行空,来去缥缈,实际上是一个有问题的孤证,其书(地理的《西游记》)无法证明,甚至黄虞稷见到这本书的途径也没法证实,极可能是黄虞稷见到《天启淮安府志》后想当然的误记。还是那句话,否定也要有证据,拿不出吴承恩地理著作的《西游记》,猜测就不能成为实证。而且此说是建立在《天启淮安府志》表述不明的基础上的,事实上这是误读《天启淮安府志》的意思很明确(下详),排除了误读,“地理书”之类便没有空间。
观点5:《西游记》中有吴方言,因此其作者极有可能是吴语区人。这也是章培恒先生首先发现的,同样后来者也经常宣称:“章培恒先生说过,《西游记》的作者是吴语区人。”说实在的,我们不必为尊者讳,当年用10个吴方言词证明《西游记》作者是吴方言区人,是章先生的一个失误。很多研究者已经充分说明了《西游记》中包含有吴方言词的原因,除章先生之外,至今也没有另外哪位语言学家或者研究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得出《西游记》使用吴方言的结论。如果有兴趣,读者可以翻看一下拙著《〈西游记〉的诞生》[5]和《吴承恩与〈西游记〉》[4],其中有专节介绍各方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理由;或者还可以查一下语言学家颜景常先生的文章《〈西游记〉的诗歌韵类与作者问题》[6]和淮安地方文史研究者刘怀玉先生的研究。颜先生取出《西游记》韵语(诗歌)的数百个韵类进行统计,并与元、明以来的中原韵对照,再用与《西游记》基本同期的典型吴语小说《醒世恒言》比较,得出《西游记》的作者完全不可能出自吴语区的结论;而操一口土得掉渣的淮安方言的刘怀玉先生,先后从《西游记》中整理出近千个江淮方言词。今天还坚持章先生当初的表述,其实是对章先生真正的不尊重。
三、不可误读:吴氏“赘婿”家世纯是臆想
现在讨论一下陈大康先生《别解》的问题。《别解》通篇围绕吴承恩的《先府宾墓志铭》,阐述吴家因为有“赘婿”(倒插门)的心结,因此不可能写出《西游记》——因为《西游记》嘲笑了倒插门的女婿。但是,吴承恩说了他父亲吴锐是倒插门的女婿吗?没有!如果陈先生再仔细阅读《先府宾墓志铭》,就会发现吴锐入赘倒插门的事根本就不存在。对于《先府宾墓志铭》,陈先生有太多的误读。
吴承恩曾为父亲撰写过一篇《先府宾墓志铭》(4)[明]吴承恩《先府宾墓志铭》,收入《射阳先生存稿》卷三;1975年又有墓石出土,藏南京博物院。有关详情,请见蔡铁鹰《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蔡铁鹰《吴承恩集笺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其中有关于自己家世的叙述:
先君讳锐字廷器。先世涟水人,然不知何时徙山阳。遭家穷孤,失谱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详也。曾祖讳鼎;祖讳铭,余姚训导;皇考讳贞,仁和教谕。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方仁和君教谕仁和时,先君四岁矣。……弱冠昏于徐氏。徐氏世卖采缕文觳,先君遂袭徐氏业,坐肆中。
误读之一:《墓志铭》说吴锐“弱冠昏于徐氏”,然后“袭”徐氏卖小饰品的业务,也成了小老板。但“昏于”并不等于入赘,查《尔雅》《礼记》《广韵》《白虎通》,没见哪一家说“昏于”就是入赘;“袭”既可能指继承家产,也可能只是指吴锐从事了这个行业——《墓志铭》中说“时卖采缕文觳者,肆相比”,既然如此,增加一家又何妨。所谓吴承恩不愿直接写“入赘徐氏”而用“昏于”,是为了“尽量淡化地作委婉表述”,纯是陈先生的想象。
误读之二:《墓志铭》说得很明白,吴家两世为学官,但三代单传。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吴锐入赘的可能。虽然入赘是解决穷人家孩子婚姻的方法之一,不算少见,但一般都发生在多子孙人家,士农工商哪一家都必须以保证自家不绝户为前提,何况吴锐念念在兹的是身在学官之家却无缘读书不能光宗耀祖。他和他的家族、家庭想要什么,应当是非常清楚的。
误读之三:《墓志铭》说徐家把产业交给吴锐“袭”了,这说明徐家也是子嗣困难,这种情况下如果徐家设定招赘入户,一般会要求改姓,但事实是“徐夫人生一女承嘉,适同君沈山”,不但吴承恩没有改姓,连徐夫人亲生女儿也没有改姓。至少到目前,各类相关资料,没有见到任何吴承恩改姓的信息。
误读之四:《墓志铭》还说,吴锐“壮岁时,置侧室张,实生承恩,娶叶氏”。请注意,这里用的是“置侧室”,而不是继娶、续弦、再婚、填房之类,说明徐氏夫人当时还在,吴承恩生母的身份是妾。这种情况下吴承嘉、吴承恩姐弟都姓吴,又哪来的赘婿的事?吴承恩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姐吴承嘉长其约10岁,在这个家庭里,嫡出、庶出有很大差别吗,影响大到足以使吴承恩产生心结而不能写《西游记》吗?
四、《淮安府志》是相互印证而非孤证
在各种质疑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条,是说《淮安府志》的著录是一条孤证。孤证不立,这似乎挺有说服力。笔者尽管属于挺吴者,但也曾经认为《天启淮安府志》确有缺憾。但其实这是误读,或者说是思维上的错觉,也包括当时的笔者在内。
明明白白《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是相互印证的两条,怎么能说是孤证?难道就因为它们两条出于同一本书?同一本书的两条著录不正好可以相互印证吗?出现这种误读,其实是出于对地方志的修纂程序性和严肃性认识不够,因此产生出许多想当然。
为了说清楚该问题,我们把话题拉开一点。明朝从立国起就比较重视地方志的修纂,并基本上形成了省府长官领衔主修,副职或当地学士名流主纂的格局,算得上是地方政府的一件政事。有句俗语叫“盛世修志”,讲的就是地方志修纂的传统与背景。
现在知道的明代《淮安府志》有4部,但其中成化《淮安府志》已亡佚,实存3部(5)《正德淮安府志》和《天启淮安府志》有新出校点本,荀德麟等点校,方志出版社2009年出版。:
《正德淮安府志》16卷,知府魏县薛赟修,山阳教谕陈艮山纂;
《万历淮安府志》20卷,知府沔阳陈文烛修,同知博县郭大纶纂;
《天启淮安府志》24卷,知府东平宋祖舜修,同知莆田方尚祖纂。
这三部《淮安府志》都是地方主官知府领衔,副官府同知等实际操作,典型的政府修志格局;当然,还会有一个由地方耆宿士绅和府学生员组成的运作班子;还得请更大的官员作序题字,如《天启淮安府志》就请了知府的同乡、时任山东布政使高登龙作序,序中又说到有生员杨时藩、唐禶修、刘一炤等参与。
修志一般不需要重起炉灶,基本上都是针对旧志修订编纂,每部志的间隔时间通常在三五十年。以上几部《淮安府志》,分别编纂于正德十三年(1518)、万历元年(1573)、天启五年(1625),间隔都是50年左右。府县修志的任务就是将上一时期内的重要的时政、人事、赋税、物产的变化增补进新志。一般说来,旧志的分野、疆域、山川、河流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必须注意的是时政、人口、赋税、灾害的实时记录,还有增删替换一些乡贤、名宦、英烈、艺文各类人物,补充他们的事迹和作品。删掉哪些,增补哪些,替换哪些人,标榜哪些事,当然不可以随心所欲,都得经过一个提名、核实、商讨、确认的过程,需要府县主官和士绅乡耆取得一致意见,也会像现代修志一样,开很多会,请很多人发表意见,然后才形成方案,诉诸文字。
明白这些程序,就知道修订方志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现在想来,说《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是笔误、同名异书、随手著录,又说什么旧例,等等,是不严肃且不严谨的。
了解了修志的严肃性,再看《天启淮安府志》关于“吴承恩射阳集”、《西游记》的著录,就有意思了。
先看“艺文志”收入“吴承恩”,这属于实至名归,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吴承恩虽然官职不高,仅八品,但晚年卖文为生,文名很高。“射阳集四册□卷”就是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7],由丘度即“丘少司徒”搜集刻印。丘度,吴承嘉的外孙,吴承恩的表外孙,是能与吴氏家族、与儒业沾点边的唯一男丁。早期读书的状况不太好,40岁还是个老秀才。吴承恩隆庆四年(1570)卸荆府纪善任回乡后,在丘度身上着实下了点功夫,有人称他们的关系“亲犹表孙,义近高弟”[8];为了能给丘度争取良好环境,吴承恩与知府邵元哲交往频繁,甚至代丘度以郡学生领袖的身份写文章为邵元哲祝寿(详见《射阳先生存稿》中相关篇章)。丘度万历四年(1576)乡试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后任职至光禄寺卿。万历十八年(1590)在职期间,丘度率领本地一帮文士、生员整理刻印了《射阳先生存稿》,用这种中国士子最为看重的方式回报了他的舅公和恩师。致仕后大约在万历四十年(1612)又重新整理翻刻一次,现在保存在台北的存世孤本就是这次的刻印本。当是时也,丘度就是那个阶段淮安官职最高的乡绅,也是淮安的文人领袖。修纂天启《淮安府志》时,丘度刚刚去世,但他的影响在不在?他身边那些参与整理《射阳先生存稿》的文士在不在?可以想象。
再看“人物志”对吴承恩的介绍。“艺文志”在吴承恩名下收入通俗小说《西游记》,也许会有点争议,所以在“人物志·近代文苑”中就有了详细说明:说吴承恩文采出众,“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说吴承恩官运不畅,举业做得不好,只得了副县级的小官,“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但是又说他“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时”。这就值得玩味了!他擅长的“谐剧”指什么?所著的“杂记”是什么?“名震一时”的又是什么?不就是《西游记》么,这段文字不就是对“艺文志”在“吴承恩”名下收入“《西游记》”的解释或者追加说明么?如果不是,吴承恩擅长的“谐剧”,所著的“杂记”,影响大到“名震一时”的作品,如何指实?总不能说《天启淮安府志》玩了个不着调的花活吧?
还有个背景要交代一下。吴承恩的介绍被安排在《天启淮安府志》“人物志”下面的一个专有栏目“近代文苑”里,这很特别。此前的正德志、万历志,此后的乾隆志、光绪志中,“近代文苑”都没有出现。这是“唯一”一次出现(或设置)。而天启志的这个栏目,只记载了两个人,除吴承恩外,另一位也是“英敏博学,议论风生,然不耐举子业”,最后在府衙做点文字服务,提学使者为他题了块匾,称“外史问奇”,看样子也是位仕途不得志的才子。这大有点特设专栏的意思。显然,由于《西游记》的“名震一时”,天启的修志班子决定在“艺文志”里收录。但考虑到社会影响,于是又在“人物志”里设一个专栏,对官职不高的吴承恩和另外一位同类专门介绍,其实质也就是对收录《西游记》做一个解释。
这简直就是精心设计的一组相互映照,哪是什么孤证!在了解修治地方志的严整过程和严肃性之后,还能认为《天启淮安府志》莫名其妙地就录了一个来路不明的《西游记》?还能认为它莫名其妙地来了一通漫无所指的“善谐剧”“名震一时”吗?还敢说《天启淮安府志》和我们开历史玩笑,收录的《西游记》是一本异书、是一本地理书吗?那样一来,府志的问题就大了——它越界梦魇了。
五、综合评判才是确认作者的正途
所谓学理,既不虚无,也不缥缈。就《西游记》作者之争而言,在没有更多文献资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作品”与“作者”两者间可能发生联系的各个方面的综合评判,包括作者的生活经历、文学修养、人生道义、语言风格;影响作品主题和内蕴形成的社会、文化、宗教倾向、历史背景;渗透着现实生活元素的故事来源和情节。当所有这些方面都显示出共同的指向性时,质疑也许就消失了。
(一)以作者的人生经历构建新的证据链
构建一条从世德堂本陈元之《序》开始,到吴承恩任荆府纪善结束的新的证据链,向来是“吴著说”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前面说到了三个“或曰”,由于有些研究者对这句话还会误读,所以这里再“翻译”一下:
《西游记》这本书,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听说出自当今皇家某位侯王的王府,还有人说是王爷的清客幕僚们所为,也有人说是王爷自己所作。
这很重要,是整个证据链下桩立柱的第一环;吴承恩确实有过“荆府纪善”的任命,也就是在荆王府担任纪善这个八品官职,这没有争议,它是证据链另一端的环节;但它与第一个环节之间还缺少一个连接,就是:吴承恩他到任了吗?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证明吴承恩确实到了湖北荆王府,做了具有清客意味和八公之徒一般的纪善,并且描写了荆王府。这就补齐了证据链中间的缺失环节,指实了吴承恩把自己的经历写进《西游记》的问题。
这段经历在《西游记》里就是“玉华国”的故事。《西游记》里的那些人间国度,国王非昏即庸,只有一个贤明,那就是玉华国国王——具体情节请读者翻查原著。为什么说这玉华国就是吴承恩眼里的荆王府呢?笔者在《〈西游记〉的诞生》和《吴承恩与〈西游记〉》里都有详细的考订,这里限于篇幅,仅说结论。
首先,看玉华王的身份。《西游记》说玉华王为皇室宗裔,封在此地玉华县或称玉华州为王,自称“孤在此城,今已五代”,“也颇有个贤名在外”。再看吴承恩服务的荆王,自然是皇亲,府邸在湖北蕲州,到吴承恩任“荆府纪善”的隆庆初年时,其在蕲州恰是五代,也有贤名,这在《明史》里有记载。
其次,看玉华国的地位。这玉华国虽然称国,但却是个藩国,即诸侯国,所以必须有个明确的落脚封地。《西游记》里一会儿称它是玉华州,一会又称它是玉华县,正是指封地的建制。荆王府所在的蕲州,在明代恰也是既称州,又称县。
第三,看玉华国的名称。我们近年发现了一部叫《荆藩家乘》的蕲州朱氏族谱。其中“荆王宫殿考”中记载荆王府的主宫殿就叫“玉华宫”,这一条实际上已经不能有任何其他解释了,“玉华国”的名称其实就是荆王府的代名词;而另一座宫殿“谨身殿”,在《西游记》中则是比丘国王的寝宫。
第四,看玉华国的建制。《西游记》说玉华王王府“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这是典型的王府配置,与《荆藩家乘》“荆藩职官考”的描述几乎连顺序都一样。王府并非各地都有,王府的制度也并非常识,如果没有王府的任职经历,能有如此精确的描述吗?
第五,看吴承恩的地位。《西游记》说玉华王府有3位小王子,因仰慕而拜唐僧师徒为师,而荆王府恰也有3位小王子。更巧的是,玉华国3位小王子拜唐僧师徒为师,而荆王府的3位小王子恰恰是吴承恩名义上的学生,《明史》说“凡宗室年十岁以上,入宗学,教授与纪善为之师”可证。
旧时工匠逢有得意之作,总会郑重其事地留下题款。碰到不适宜留款的东西,也会设法在隐蔽处留一点自己的印记,比如在画卷的山水枝叶里写下自己的名字,在陶瓷器具的里壁敲一个印章,这都很容易理解,毕竟是自己的心血。在《西游记》中,吴承恩忍不住弄了点痕迹:他把荆王府写进了《西游记》,他也用了自己的方式,在《西游记》中为旧日东家恩主荆王府留了一个千古“贤名”。
(二)以作者的文学素养作为强力佐证
对于读者来说,《西游记》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由于主题的深邃、人物的精彩、情节的丰富、语言的特色等而跻身名著行列。很自然,其作者必须全方位地具备完成这些创造的文学素养。
具体可以转化为一个问题:谁能写得了《西游记》?其实《西游记》的文本已经提供了若干硬性的支撑。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所有被提名的作者候选人没有一位具有写作《西游记》的文学资格。笔者看过丘处机的所谓“西游记”,也读过另一位候选作者李春芳的文集,结论与神话《西游记》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
我们理解《西游记》的作者,从文学上来说,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首先,《西游记》具有儒释道三教色彩却不改变世俗文学作品的本质:题材来自佛教,但作者于佛理并不精通;配角道士始终出现,但作者的态度甚为不恭;儒家的道德不显山不露水,但却是无处不在的最终评判标准。这是作者的三观。
其次,《西游记》的情节奇特如幻,语言幽默诙谐,性格鲜明滑稽,往往有匪夷所思的神来之笔,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绝无混淆之虞。这些方面的特色是天生成就,并不是等闲的读书人可以做到的。连模仿都做不到。
再次,《西游记》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很多方面,如写到了围棋、绘画,谈到了诗词,引用了神话,而且均非泛泛,其根底的深厚在行家眼里一目了然;在不经意中,涉及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堪称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其生活氛围的复杂性全在其中。
吴承恩恰恰具备了完成《西游记》的最合适的文学条件——少年神童,官民惊艳,笔走龙蛇,上下九天,那种俊逸豪迈,前人已经评价与李白、苏轼走了同一条路子;而又“善谐剧”,写过一些“名震一时”包括志怪故事在内的“谐剧”“杂记”。在其他人身上能寻找到这种素质吗?
(三)作者的社会与文学意识不容忽视
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必然有一些显著的特色和内蕴,这主要由作者的社会意识以及提供这些社会意识的环境所决定——有什么作者才有什么样的书,这些都是研究作品与作者关系的切入点。
《西游记》对社会的映射方式和其他的名著是不一样的:它既不正面描述所谓天下兴亡如《三国演义》,也不去揭华丽外衣后面的脓疮如《红楼梦》;既不“诲盗”如《水浒传》,也不“诲淫”如《金瓶梅》。它昭示的是唐僧虔诚的信念追求,悟空善恶分明的暴力。如果不是八戒有点小市民的恶俗,一部《西游记》简直就是满满的正能量;但即使有猪八戒的市侩狡猾,有孙悟空的暴力倾向,有盘丝洞那么一点小小的色情,我们也不能说《西游记》就不深刻,就不隽永。《西游记》的作者在人生态度上,总体上是积极正面的。
《西游记》的作者显然又不是罗贯中那样的江湖艺人,《西游记》情节虽神奇,但却有很多文人情调和诗词歌赋,不适宜在酒楼茶馆开讲;作者显然也不是张士诚、施耐庵那样的暴政批评者,因此没有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戾气,没有喊一声“逼上梁山”的勇气,虽有批评,不过开个“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玩笑;他也不是曹雪芹那样的世家贵公子,所以《西游记》里的各级宴会,也没有大观园的茄鲞和妙玉那般饮茶。所谓的皇宫筵席也不过是泛泛一说而已。他甚至不是秦楼楚馆的留恋者,更不会是帮派黑社会的参与者。《西游记》社会百姓的主体都是很干净规矩的生意人或者读书人,如旅店老板、寇员外等。我们不能说这和作者的身份地位、社会环境没有关系。
其实吴承恩正是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人。为什么他会有完成《西游记》的念头?吴承恩曾经正面为我们提供过答案。在他的《射阳先生存稿》中,有一篇不长的《禹鼎志序》[9],非常值得注意:他自称从小就爱读杂书,积攒零花钱偷偷地买,还往往要躲起来读以逃避父师的呵责;尤其喜爱讲神鬼故事如《酉阳杂俎》《玄怪录》那样的志怪;为什么喜爱?因为其“善摹写物情”,也就是使用了文学的手段,天性喜欢;时间长了,自己就立志写一本,这种文学的冲动一直延续到需要为科举奔忙的中年,“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多么明确的文学激情!他的目标是“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时纪人间变异”,“微有鉴戒寓焉”,又是多么明确的文学标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立志要做一个使读兹编者“戃愯然易虑”的“野史氏”。这样一个人,划归《西游记》名下不是很适宜吗?很可惜,《禹鼎志序》往往被忽视,有时甚至是故意被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