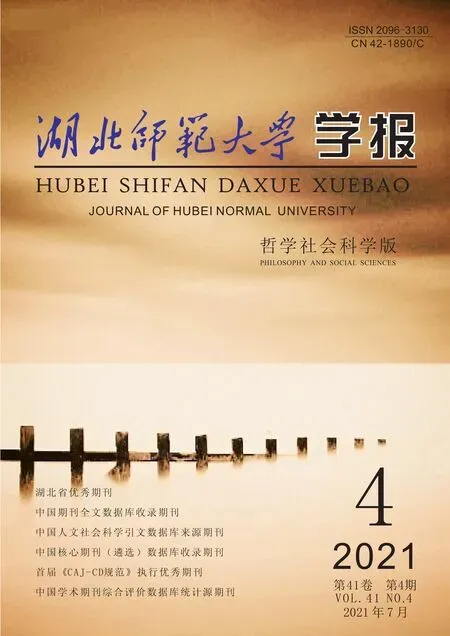善的故事
——明清劝善小说的劝世价值及当代德育启示
李文静
(青岛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明清时期特别重视道德教化。为达到教化的目的,帝王敕撰以劝善惩恶的道德教化为目的的训谕或训诫,御敕善书与民间社会流行的“三教合一”的善书相结合,促进了劝善运动的兴起。善书作者为使善书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借助通俗小说的艺术形式和写作手法编写善书。有的善书讲述行善获福、作恶遭谴的感应故事,可作小说观,被称为“善书小说”。与此同时,产生了大量以劝善为目的的小说,这些小说或从善书中取材,或体现善书中的思想观念,可称为劝善小说。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大量出现的劝善小说多以善恶报应构思情节,教育读者行善惩恶,有着大量的读者群,是对善书教化理论的形象阐释,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道德教化效果。明清劝善小说自觉的道德教化和社会责任担当,对今天的道德教育和文学创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善的内核:明清劝善小说的教化内容与教感模式
(一)从“孝”到“忠”的逻辑转向
孔子在《论语》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孝”是中国古代伦理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后世家训和善书的重要内容。在明清时期的善书和劝善小说中,涉及“孝”的故事占有很大的比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孝的文化内涵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明清劝善小说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孝子,各种感人至深的孝行。《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2]明清劝善小说中描写的孝行多种多样。在生活中奉养父母是尽孝最基本的要求,如《喻世明言》卷三十八中的任孝子、《鸳鸯针》第一卷第四回中的任小姐夫妇、《西湖二集》第六卷中的姚伯华等都用心孝养父母。扬名显亲则是给予父母心灵上的安慰,如《石点头》第一卷中的郭乔,《喻世明言》卷四中的陈宗阮等。以身孝亲类的孝子奉献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救治父母。《型世言》第四回中的陈妙珍切肝救祖母,是以身孝亲的极端形式。为父报仇型的孝子为了维护尊严,为父亲找回公道,忍辱负重,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九中的谢小娥女扮男装,为父亲和丈夫复仇。千里寻父是明清劝善小说中孝子故事的一大类型。明清时期商业发展,很多人千里求财,万里宦游,那个时候交通不便,音信不通,加上战乱盗贼,家长一去多年,生死未知,于是有孝子千里寻父的故事,如《石点头》第三卷写王本立天涯求父,《娱目醒心编》卷一写曹士元不远万里寻找父亲骸骨。
劝善小说中的孝子或加官封爵,或多子多福,或为后世传颂,都获得了好报。而不孝之子则受到惩罚恶报,甚至被判死刑。在劝善小说中,孝悌常常相联,如《醒世恒言》卷十中的刘方、刘奇兄友弟恭,《醒世恒言》卷二中的许武为了养育两位弟弟而不急于娶妻。有时节孝结合,如《型世言》第六回中的唐贵梅自缢而死,既保全了自己的节,又替婆婆遮盖丑行,节孝两全。孝还与忠义相连。如《型世言》第七回中的王翠翘为替父偿还官债卖身为妾,后来劝徐明山归降朝廷,在徐明山被背信弃义的朝廷处死后又沉海而死以报,可谓孝、忠、义三全。
(二)义夫节妇的时代特征
家庭伦理是一切伦理的基础,夫妻是家庭的核心。出于维护家庭和社会和谐的需要,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贞节的要求比较严格。贞节观念真正达到顶峰是在明清时期,也就在这个时期,劝善小说中塑造了大量贞节烈女的形象,试图以道德符号化的人物教化风俗。明清劝善小说中的贞洁烈妇形象,或者贫病相守,如《八洞天》卷三中的晁七襄,《西湖二集》第三卷中的葛氏等;或者在丈夫去世后,坚持守节,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五中的颜氏,《型世言》第十六回中的吴氏等;或者在乱世遇袭时极力反抗,誓死守住贞节,如《警世通言》卷十二中的吕顺哥,《五色石》卷三中的周氏等。
与传统善书相比,劝善小说中的贞洁烈妇故事有更鲜明的时代特点。明代中后期,由于“心学”的影响和市民阶层价值观的变化,劝善小说对不幸失身的女子多表示同情和宽容,如《喻世明言》卷一中作者对王三巧的失节宽容得多;《醒世恒言》卷三十二中的韩玉娥守节更多的是出于情感的驱使。有的小说主张贞节要兼顾人情、实利,应该“取重略轻”,如果能够既保全贞节,又保全性命,就可以选择暂时屈从,有朝一日还能够与丈夫团圆;为了保全丈夫的子嗣,失节是可以谅解的,如《十二楼·奉先楼》中的舒娘子,《喻世明言》卷四中的陈玉兰。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劝善小说中,夫妇伦理是平等的,女性的节是建立在男子的义之上的。劝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义夫形象,如《喻世明言》卷十七中迎娶已沦落为官妓的未婚妻春娘的单符郎,《人中画·寒彻骨》中不嫌弃失明未婚妻的柳春荫等等。义夫们坚守婚姻承诺,不因对方沦落、残疾甚至死亡而另娶他人,实际上是对女性守贞行为的回报,也是男女平等的时代诉求。相反,劝善小说中的不义之夫大多不得善终,如《醉醒石》第十三回中背弃诺言,骗钱骗色的董文甫,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或恶报。
(三)仁民爱物的君子情怀
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中,“仁”是“五常”之首。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端之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3]恻隐之心就是仁,仁爱是最重要的善,具有实践特性。
明清劝善小说中有很多对富人乐善好施的描写,包括出资殉葬、施药赈灾等,如《醒世姻缘传》中的晁夫人一心向善,遇到饥荒之年,拿出家中的粮食救济饥民,还救了孤儿小琏哥。有的小说描写普通民众的轻财仗义,助人为乐,如《娱目醒心编》卷三写席秀才无意听到一户人家婆媳两人无以度日,倾囊帮助她们,而自己东挪西借度日。在贫富差距加大的特殊背景下,慈善可以使不同阶级的利益关系进行适度调整,从而维持既有的社会秩序。普通民众发善心做善事,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明清劝善小说以果报劝人行善,行善的人都有好报。《石点头》第一卷中的郭乔得以与失散多年的儿子相聚,并同时考中进士;《醒世姻缘传》中的晁夫人一百零五岁无疾而终,还被封为峄山神;《雨花香》第二十二种《宽厚富》中的陈之鼎活到九十一岁,子孙满堂。
助人是善行,救助其他有生命的动物,特别是放生,也被认为是仁慈的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放生观念由来已久。儒家强调仁民爱物,孟子有“君子远庖厨”之说,道家和道教都主张爱惜生命,反对杀生。但后世的放生受佛教影响最大。晚明放生活动大兴,与佛教高僧推动、居士文人参与、佛教世俗化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等诸多因素有关。与此同时,清初归庄认为放生的“慈悲心”是极仁人之用心[4]。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认为,教育孩子从小善待动物,可以培养他们善良的心性,预防、抑制恶念恶行。[5]明清劝善小说比如《西湖二集》《喻世明言》《聊斋志异》等中有很多关于放生和杀生的故事。人对动物施以恩惠,放生动物,会得到善报,如《西湖二集》第二十三卷中的杨维桢、《喻世明言》卷三十四中的李元因放生而获得了功名富贵。相反,杀生则会受到恶报。《警世通言》卷二十中计押番不顾金鳗的请求,将金鳗吃了,后来金鳗投胎为庆奴,使计押番家破人亡。
(四)诚信不欺的处世之道
诚信是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孔子多次讲到诚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6]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明清时期的诚信观呈现出新的特征,诚信不仅存在于普通交往领域,更是商业经营中的重要伦理。明清劝善小说中有大量关于诚信的描写,诚信被认为是为人处世之道,从商之本。在很多小说中,商人对顾客讲诚信,童叟无欺,生意越来越兴隆,如《醒世恒言》卷五中的韦德之父、《醒世恒言》卷三中的秦重等。合作伙伴之间也要讲诚信,这样才能建立可信赖的长期合作关系。如《警世通言》卷五中的吕玉、《醒世恒言》卷十八中的施复。
诚信体现在君臣关系上就是朱熹所说的“忠信”,体现在朋友关系上就是信守约定,如《喻世明言》卷十六中的范巨卿为赴朋友张劭鸡黍之约,自刎而死,以魂魄赴约。诚信体现在爱情婚姻关系中就是信守婚姻承诺,忠贞不二。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九中的速哥失里在未婚夫拜住家破人亡后,誓死坚守婚约。
明清劝善小说一方面对坚守婚姻盟约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对背信弃义的行为加以谴责。明清劝善小说中有很多批判“嫌贫毁约”的故事,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中的徽州商人金朝奉为逃避选秀女,急忙把女儿许配给秀才韩子文,后又嫌韩生贫穷,企图赖婚。《十二楼·拂云楼》中的裴翁,《醒梦骈言》第六回中的温州富户张维城的大女儿月英,《跻春台·双金钏》 中的富户方仕贵等等,都是嫌男方贫穷,欲毁约退亲。在爱情婚姻中背信弃义的人都受到了惩罚。《警世通言》卷三十四中的周廷章背弃盟约,为攀高枝而另结新欢,无情无义,最后被乱棒打杀。《醉醒石》第十三回中的董文甫背弃诺言,骗钱骗色,最后被索命而死。
(五)私欲节制的冲突调和
明代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社会风尚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受个性解放思潮影响,人的欲望得到肯定,走向极端,就是纵欲主义,甚至造成社会风气、社会道德的堕落腐化。明末世风日下,一些小说家以道德教化为己任,追求道德至上主义,试图以劝善小说警醒痴顽、教化风俗、挽救世道人心。
个人私欲首先反映在情欲追求上。明清时期的小说在肯定情欲的同时,又描写情欲的沉溺放纵带来的危险,或受到惩罚,以此警示世人节制欲望。在《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初刻拍案惊奇》等小说中,沉溺于情欲中的男男女女都得到了相应的惩罚,家财荡散,有的甚至招致杀身之祸。《金瓶梅》中淫欲无度的人物都没有好结局,在《续金瓶梅》等几部续书中又继续受到严厉的果应。清前期的小说《姑妄言》也是一篇果报文字,“以淫为报应,具一片婆心”[7]。
明清时代商业发展,对财富的追求被认为很正常,但过度贪婪、重利忘义则受到批判。明清劝善小说中,有的人为了争夺家产而不顾亲情,有的人为了财货而害人性命,为了满足贪欲无所不用其极。《喻世明言·滕大尹鬼断家私》《醒世恒言·张廷秀逃生救父》《生绡剪·有缘结蚁三朝子,无意逢人双担金》等都写到了家产争夺。《石点头·贪婪汉六院卖风流》中的贪官吾爱陶贪财到了极致,最后受到了报应,名声恶臭,无处容身。对财物的垂涎觊觎、无礼占有会招致灾祸,重义轻利,放弃意外之财则会带来好名和福泽,如《警世通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吕玉,《醒世恒言·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中的三孝廉。
此外,恩报也是明清劝善小说的重要主题,恩报逻辑成为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力。知恩善报是正常的道德行为,而如果受人恩惠,不仅不思报答,反而恩将仇报,则是大恶,必然会受到惩罚。而这种借助于因果联系塑造故事情节以传达主流价值观念的手段,也在明清劝善小说中达至顶峰。
二、善的旨趣:明清劝善小说的劝世价值
静恬主人在《金石缘序》中强调小说作为劝善惩恶手段的重要性:“但作者先须立定主见,……做得锦簇花团,方使阅者称奇,听者忘倦。”[8]明清劝善小说对社会现实问题表达了强烈的关注,以鲜活的善恶分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曲折的劝善情节的构思,吸引读者,达到劝善目的。书坊主从劝善对象出发,刊刻和传播劝善小说,对劝善小说进行包装宣传,扩大了劝善小说的影响。劝善小说对明清时期的劝善运动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是推动明清慈善事业兴盛的因素之一。
(一)劝善小说的劝善方式
明清劝善小说对社会现实问题表达了强烈的关注。文人雅士可一居士在《醒世恒言序》中称之为“天醉”的“浊乱之世”[9]5,和《西游记》中所说的“贪淫乐祸,多杀多争”的凶场恶海[10],针对现实中出现的道德问题,担负起劝善惩恶的道德教化责任,将改善世道风化的希望寄于小说之中,希望小说能够在教化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共成风化之美”,“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9]5。明清劝善小说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睡乡祭酒在《连城璧序》中说:“迷而不知悟,江河日下而不可返。此等世界,惩不能得之于夏楚,劝亦不能得之于道铎。每在文人笔端,能使好善之心苏苏而动,恶恶之念油油而生。”[11]1作者的“深心”与小说的巨大感染力结合在一起,使读者阅读小说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熏染:“其深心具见于是,极人情诡变,天道渺微,从巧心慧舌,笔笔勾出,使观者于心焰烧腾之时,忽如冷水浃背,不自知好善心生,恶恶念起。”[11]3这种教育是潜移默化的,相较于其他的宣教方法更为深入人心。
明清劝善小说善于塑造善恶分明的鲜活人物形象,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像照镜子一样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说:“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12]明清劝善小说极力描摹善恶两种样子来“与人看”。蠡庵居士在《女开科传跋》中说,读了《女开科传》,不觉拍案大叫,因为这部小说“游戏三昧,已成劝惩”,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劝善惩恶:“说中说文人、说才女、说清官、说贞友,能使天下之人,俱愿合掌俯首,敬之拜之而已。至装腔之娈童、设骗之阇黎、狠毒之讼师、多事之丐婆、拚命之驿丞,种种诸人,何异一部因果、一部爰书、一部小史记、一部续艳异。……若仅以小说视之,亦可谓不善读是说矣。”[13]有的小说如《醒世姻缘传》将善恶劝惩归于“天”或“神”的主宰,忽视了故事情节发展的现实逻辑性,削弱了故事本身的说服力,但是这类作品却因为鲜活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引起读者的关注,从而取得意料之外的劝善效果。
明清劝善小说善于构思曲折的故事情节。明清劝善小说虽以劝善惩恶为出发点,但由于教化对象的广泛性,劝善小说通常倾向于解释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在具体事件中又强调中庸或权变,在宣扬道德伦理的时候兼顾人情,在义利之间权衡轻重,对改过自新给以宽容谅解,特别是认错和改错的过程,权衡义利轻重时的矛盾纠葛,使情节变得曲折。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阶级立场以及利益关系,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如《姑妄言》中,白金重因为势利贪财而受到惩罚,托生为娼妓钱贵,双目失明,但她此生“一遇钟情,即矢贞不二嫁”[7],后来双目复明,嫁给了才子钟情,并喜得贵子。小说用这样的情节说明守节忠贞,不贪不淫的果报,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增强了劝善的说服力。
(二)劝善小说的包装和传播
明清劝善小说从不同传播对象的需求出发,不仅在故事内容上精心构思,而且在小说的形式上精心包装,吸引不同层次的读者,彰显劝善小说的独特魅力。明清时期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作为主要劝善对象的市民阶层整体文化素质不高,针对这一现状,为了增加销量,进行劝善主旨的宣传,书坊往往在小说中增加插图,图文结合,更加形象直观,能够更好地传递劝善主旨,满足受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明代中期的图文排版主要是“上图下文”,交相辉映的图画与文字可以激发读者的兴趣,增进读者对于劝善故事的理解,提高阅读效果。特别是全幅大版插图和双面连式插图能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如天许斋刊《全像古今小说》、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叶敬池刊《绘像古今小说醒世恒言》等都是采用双面连式的插图,突出人物,具有很强的舞台艺术效果。小说中的插图常常选取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场面,或者人物形象最为突出的情景进行刻画,使读者能够快速地抓住故事的主旨。
为了宣传小说,书坊采用多种广告方式与传播手段,广告方式包括识语广告、标题广告和凡例广告等。劝善小说的识语广告一般篇幅比较短,通常都位于特别醒目的位置,一方面突出本书坊的优势与特色,提升书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以劝诫和讽世的词句,突出劝善意味,具有很好的宣传效果。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中的识语就是典型的例子。兼善堂刊印的《警世通言识语》中说:“自昔博洽鸿儒,兼采稗官野史,而通俗演义一种,尤便于下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淫词,大伤雅道。本坊耻之。兹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庶几木铎老人之遗意,或亦士君子所不弃也。”[14]
凡例广告也是明清劝善小说宣传的重要手段,凡例一般位于小说的卷首,揭示小说的内容、创作主旨等,如崇祯元年尚友堂刊刻的《拍案惊奇》的《凡例》中说:“是编矢不为风雅罪人,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此自笔墨雅道,当然非迂腐道学能也。”[15]这则凡例说明了小说的内容渊源,强调本书的教化特点,推动劝善主旨的宣传。标题广告则是将劝善主旨呈现在标题上,在书名前面加上限定和修饰词语来突出小说的特殊价值。可以发现,明清劝善小说的刊刻传播不仅提高了劝善小说的地位,也对当时的劝善思维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三)劝善小说的劝善效果
明清劝善小说的作者主要是熟悉民众心理的士人或乡绅,他们将传统的伦理道德用劝善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以此来影响民众。士人根据善书中的观念写作劝善小说,以小说对善恶观念进行形象化的阐释,同时士人群体也是劝善小说的教化对象,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了劝善小说的写作和传播。明清劝善小说也非常重视作品受众的广泛性,“妇孺皆知”是其目标。雅俗共赏的劝善小说使得各个阶层的女性都能阅读,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推动劝善小说的劝善主旨的宣传。女性群体并非单方面接受教化,有的善书序跋显示女性通过阅读影响周围男性的思想和行为。此外,深入浅出的劝善书籍和劝善小说还被用于童蒙教育。同时,各个书坊也针对不同的劝善对象群体的需求进行劝善小说的选材编写,调整出版规模,避免资源浪费。
明清时期的士绅将编写刊刻劝善小说当作行善的一种方式。善书主张垂训教人,劝人为善。《了凡四训》解释“劝人为善”时,引韩愈“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语[16],劝导人们以著述劝人为善。《太微仙君功过格》中说:“以文章诗词诫劝于众,一篇为一功。”[17]177《文昌帝君功过格》中说:“以德行文章相劝勉,一次一功。”[17]213明清之际的小说家多将自己的小说视为劝善书,以小说承载劝善理念。丁耀亢作《续金瓶梅》,公开宣称是借小说作《感应篇》注。冯梦龙将《石点头》视为高僧说法:“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怅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18]其小说命名或直接说明或暗示小说的喻世、醒世、警世、觉世、型世等功能。
劝善小说又对慈善行为起到了引导作用,从而推进了明清时期的慈善事业。有的劝善小说记述了当时的慈善活动,如《型世言》第二十八回写张秀才夫妻为求子,“遂立了一个行善簿,上边逐日写去”[19]。明清时期,民间与官办的慈善机构共同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清代成立了全国性的善会善堂,善会善堂经常刊刻传播包括劝善小说在内的劝善书籍。包括劝善小说在内的劝善书与善会善堂存在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慈善的制度化、组织化和慈善机构的完整化、体系化。从善会救济的内容来看,有救援落水者的救生局,有救济孤寡老人的安济堂,有收容难民的牺流所,有收养被抛弃孤儿的育婴堂、留婴堂等,甚至还有管教不孝子的归善局,体恤万物生灵的放生局等等,这些慈善组织机构基本上涵盖了劝善小说所劝之善的方方面面,是包括劝善小说在内的劝善书中的劝善理论在现实中的实践。
三、善的转化与重构:明清劝善小说的当代启示
劝善小说借日用寻常之事,达劝善惩恶之意,以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的故事情节和主旨鲜明的劝善逻辑引起世人的思考。劝善小说将道德因素蕴含在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中,在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中表达道德观念和道德理想,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形成多法并用的劝善方式体系。但由于劝善小说写作时代的局限,劝善小说不可避免地存在精华与糟粕混杂的现象,在借鉴劝善小说进行道德教育宣传时就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在吸收与转化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方向引导,秉持古为今用的原则,重新审视古代劝善教化中的问题,完善道德教化思想体系,探索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德育方式,为当代的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一)劝善小说的教化思维
天下“至理名言”,无外乎是“日用寻常之事”。借日用寻常之事,达劝善惩恶之意,是明清劝善小说的重要特点。明清劝善小说以“街坊问题”“邻里纠纷”“甲是乙非”的坊间轶事为素材构思情节,最终目的是借耳目习近之事,为劝善惩恶之具。在表达劝善主旨时,小说作者强调以日常语言写日常之事,拉近与劝善对象之间的距离,“假一二逸事,可以振聋聩挽凋敝者,为之描声而绘影。笔舌之间,情事曲传”,这样才可以“令有心者读之,怒可喜,喜可怒,醉可醒,醒可醉”。[20]在大多数劝善小说中,道德因素蕴含在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中,道德倾向从真实生动的故事情节中表现出来。劝善小说对当今的文学创作以重要的启示。作家创作要注意紧贴现实,从平常生活琐事中提炼道德教育主题,避免抽象化教条式的宣传。读者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会对那些专注于教化而无艺术形象的作品产生厌倦,这样不仅无法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还容易引起教化对象的逆反心理。
反映日常现实,表达道德教化主旨,是文学的根本特质。作家的小说写作应该有责任意识和道德使命感,但道德教育又不能是简单的说教,更不能只是在作品中点缀一些道德说辞,社会责任和使命感应该是文学创作“内蕴的”。如现代作家吴芳吉所说:“文学作品譬如园中之花,道德譬如花下之土,彼游园者固意在赏花而非以赏土,然使无膏土,则不足以滋养名花,土虽不足供赏,而花所托根,在于土也。道德虽于文学不必昭示于外,而作品所寄,仍道德也。”[21]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应该是外在的、机械的联系,作品所宣扬的道德观念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不能违背人情物理。从外面强加给文学,为说明某种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而编造虚假的故事情节,利用不相干的事件来进行道德说教,作品就会变为如意大利批评家德·桑克梯斯所说的:“蒙着故事情节的面纱的道德和政治教本”,这类作品就会如福楼拜所说:“宣扬美德的书是枯燥和虚伪的。”
和善书一样,明清劝善小说构建了多法并用的劝善方法体系。劝善小说实际上是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教化形式,将劝善思想融入故事情节中,提出向善勿恶的做人标准。明清劝善小说紧密结合实际,演绎劝善主旨,根据劝善对象的群体层次差异,利用各种方法进行教化。比如对文人士子的劝善教育,强调功名和善恶的关系。明末清初的唐孙华为善书《丹桂籍》作序时说:“文昌帝君,实主科名之籍,每岁大比,考核士人所为之善恶而升降黜陟之。”[22]《清夜钟》第十三回中用周孝廉和王孝廉正反两个故事说明善事善行对科第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富人的劝善教育,则劝导富人乐善好施,如《富贵家费钱功德例》劝导富人“施贫人及无主尸骸棺木”“不能殡葬者助之”“倩人拾遗骸,禀官瘗埋”“葬无主柩”等[17]4-5。明清劝善小说多描写慈善,如小说《石点头》第一卷中,郭乔因替米天禄“完纳钱粮”,得以考上科举以及与失散多年的儿子相聚。对于普罗大众的教化,劝善小说不仅将关注点放在孝行诚信节俭等传统美德上,而且强调善行的现世善报,报的方式是市井大众所渴望和追求的发财、生子等。针对普罗大众的教化还强调善行中“心”的因素,强调以心向善,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同时强调人情,权衡利害轻重,允许知过改过,这些都与心学思想、“三教合一”背景下的宗教世俗化以及市井社会人生观念的变化有关。
(二)劝善小说的当代转化
明清劝善小说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古代曾发挥重要的道德教化作用,其中的许多思想在今天的道德实践中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但劝善小说又是良莠不齐、瑕瑜互见的,在阅读和借鉴明清劝善小说,对其中的劝善思想进行现代转化时,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引导。劝善小说中所体现的伦理道德,既有超越时空的普适性价值,也有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因素;即使是某些表面正向的理念,还是有与现代社会无法接轨的成分。因此必须将劝善小说中的基本理念、内容与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结合,探讨古代劝善思维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明清劝善小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成果,要实现其正确转化,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对劝善小说中的基本伦理规范进行取舍整合,对其中所表现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现代转化,为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寻求资源。
对明清劝善小说的劝善思想进行现代转化时,需要因时利导。明清劝善小说是特定时代的文化成果,因为时代的变迁,必须对劝善小说重新审视。劝善小说所构筑的道德教育体系涉及面很广,是一种以人格完善为导向的生活教育。明清劝善小说的意义重构必须避免机械化的观念套用。比如古代的忠孝观,因为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结构的变化,忠孝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当代社会,需要将忠的价值观转化为爱国主义,培养爱国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劝善小说中反复强调的孝,在当代社会也有了新的内涵,孝不仅仅是家庭问题,也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而且还是社会责任问题和法律问题,孝养父母是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如今中国出现了老龄化趋势,老龄人口占很大比例,养老问题凸显。以孝为善,倡导尊亲敬老,对解决社会养老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健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劝善小说中强调的仁爱、诚信等基本道德观念,表面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敬业、友善等有高度的关联,然而每个概念都是复杂的,其深层内涵并不完全一致。
在对明清劝善小说的道德劝化体系进行当代转化时,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在长期发展中,包括劝善小说在内的善书积累了丰富的教化资源,形成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劝善方法。但是由于善书兴盛于封建时代,不可避免地存在精华与糟粕混杂的现象。劝善小说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教化方式,在新时代进行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在借鉴古代教化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观念的转化和体系的重构。比如封建时代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应该适应时代加以转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内容相契合。善书中的糟粕主要是迷信观念和功利主义,这在劝善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很多劝善小说宣扬因果报应,以地狱恶报恐吓,以功名富贵福报诱惑,忽视了对终极价值意义的追求。比如《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小说以因果报应构思情节,因果报应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种劝善逻辑是存在问题的。劝善惩恶应当是基于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而进行的教化活动,然而因果报应说的渲染,使小说笼罩了一层迷信色彩,掩盖了劝善惩恶本来具有的积极意义。当代作家应该将传统善的观念与新时代新事物结合,摒弃因果报应的迷信说教,贴近现实,发现问题,以现实生活逻辑进行劝善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