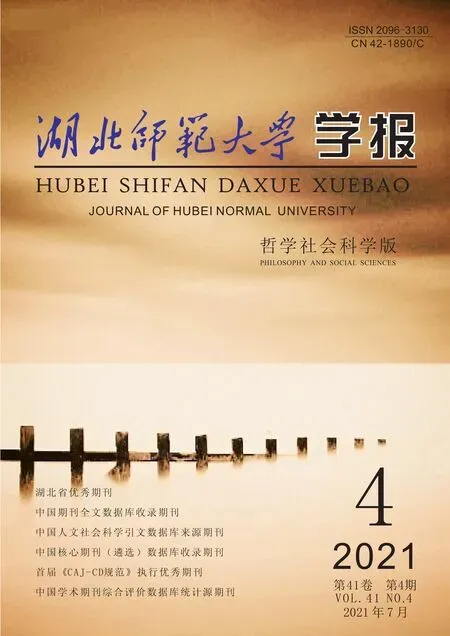从《楮记室》所录“本朝”异闻管见《西游记》的创作生态
李春光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一个生动的怪奇形象或者一个成型的怪奇故事,很有可能在前代的文化传统之中找到原型。历时性的怪奇文化积累,必然会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意涵范畴。可以想见,在漫长的流播过程中,以异域和灵怪为主要呈现方式的传说,一部分走入史书并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传说历史化以及封建正史相对开放包容的佐证;绝大部分则只能依靠民间的口耳相传以及学界的廋奇猎异得以保存,并在历史的洪流中熠熠生辉。日本学者柳田国男称:
(传说)象草木一样,根子在古代,却繁荣滋长,有时枝丫枯竭,或又扭偏了。又象海滩渚水,既有沉沙,又有潮涨潮落。仔细地观察时,从这当中可以窥见时间的进展给予人类社会巨大的变革的某些痕迹。[1]
怪奇小说的集大成者《西游记》中的很多怪奇形象的演变过程虽已无从得知,但均可以在《山海经》中觅见端倪。例如,牛魔王的原型很可能是《北山经》中的“诸怀”与《西山经》中的“獓固”,九头虫的原型很可能是《海外北经》中的“相柳”与《大荒北经》中的“相繇”等。故清人王韬在《新说西游记图像序》一文中称《西游记》“能于山经海录中别树一帜,一若宇宙间自有此种异事”[2]。可以说,《西游记》不仅是一部导源于“山经海录”的怪奇传说,更是一部“别树一帜”的怪奇新创。下面,以女儿国为代表的异域和以孙悟空为代表的灵怪为例,管见怪奇小说创作的历时性文化生态。
一
女儿国传说的部分资料如下:
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郭璞注: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姙矣。若生男子,三岁辄死。(《山海经·海外西经》)
海中有女人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则生子。(《后汉书·东沃沮传》)
方江之上暑隰,生男子三年而死,有黄水,妇人入浴,出则乳矣。(《外国图》)
女子之国,浴于黄水,乃娠乃字,生男则死。(郭璞《女子国赞》)
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至二三月,竞入水则妊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梁书·扶桑国传》)
以今所知,女国有六。何者?北海之东,方夷之北,有女国。天女下降为其君,国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国。其女悍而男恭,女为人君,以贵男为夫,置男为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东南,绝徼之外,有女国。以猿为夫,生男类父,而入山谷,昼伏夜游,生女则巢居穴处。南海东南有女国。举国惟以鬼为夫,夫致饮食禽兽以养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国。方百里,山出石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举国无夫,并蛇六矣。昔狗国之南有女国。当汉章帝时,其国王死,妻代知国,近百年,时称女国,后子孙还为君。(《太平广记·梁四公》)[3]
至此,即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年),中原地区的四邻八界、海山异境,几乎都存在着女国。这些女国绵延子嗣的方式基本上是“浴水而孕”。“窥井而孕”乃是上古灵感神话的变体,其实质仍是“遇水而孕”。此后,除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称“女人国,视井而生育”[4]外,《北史·女国列传》《隋书·女国列传》《旧唐书·东女国传》《唐会要》《大唐西域记》《岭外代答》《诸蕃志》《元史·世祖本纪》《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古籍均有刻意模糊、淡化女人国生子之怪奇之谈。也就是说,从《北史》开始,直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前的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女国”的故事虽然在不停地“繁荣滋长”,但作为怪奇传说的“浴水而孕”的情节却处于“枝丫枯竭”的状态。究其原因,在纂史文化日趋系统的大背景下,怪奇传说难以有效融入封建正史、方志、舆地志等著作的话语系统之中。《四库全书总目》称汪大渊“尝附贾舶浮海越数十国,纪所闻见成此书……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即便《岛夷志略》一书“足资考证”,但在正统的编史文化背景之下,“窥井而孕”这种怪奇情节的出现,也只能是我国古代传说历史化现象的一种潜在遗存乃至无意识的接受。
吴承恩“西梁女国”故事的建构,很有可能是在历代关于女国生子的怪奇传说的基础上完成的。可是,女国传说中并没有男人饮水而孕的情节。这便出现了一个难题。师徒四人途径女儿国,饮水怀孕的根据是什么?黄水之水,能够使女子怀孕,自然也能够让男子怀孕;可女性的生理结构毕竟与男性不同,男子怀孕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这时便需要一个异闻传说来触发吴承恩的灵感,巧合的是,一则名叫“男子生儿”的明朝“本朝”异闻出现在了吴承恩的视阈之内。同样,孙悟空的原型,也能上溯到《山海经》中的“巫支祁”。而“巫支祁”则在历代史书、方志、笔记、杂剧中逐渐演化为淮河水怪甚或是猿猴精。民间怪奇传说中,存在着大量的“石生人”故事,如《太平御览》卷五十一引《随巢子》“禹产于琨石,启生于石”。那么,如何把“石生人”的母题转化为“石生猴”的故事,这时便需要几个异闻传说来触发吴承恩的灵感,巧合的是,名叫“淮河水怪”“石中男女”“石神”的明朝“本朝”异闻出现在了吴承恩的视阈之内。更巧合的是,这几则巧合的明朝“本朝”异闻均出自一本名叫《楮记室》的书中。而此书的作者,便是与吴承恩私交甚笃的同乡前辈潘埙。
二
吴承恩与潘埙的交游问题,笔者曾撰文专述,略可参见[5]。现有几点问题,需额外强调:
其一,吴承恩与胡琏,既是亲属关系,又是师生关系。而围绕在胡琏周围,也存在着一些异闻,如“南津胡侍郎琏,为广东副使日,有治民得疾,伏枕甚久。忽嗜食生物,鱼肉之类,命家人不得烹煮。久之,两足生毛,次及股,次及满身,皆变成虎形,惟首尚人。求观者众,乃伏于床下,命家人勿听人入。已而两颊生毛,跳跃欲去。里甲告官,笞杀之。”[6]此等异闻,在当时非同小可。吴承恩作为胡琏的晚辈和学生,对于胡琏治下之事应该有所耳闻。另外,历朝历代的野史异闻中均不乏“人化虎”的故事,如《太平广记》就设专节列举了很多“虎化人”和“人化虎”的奇谈。胡琏治下这则“人化虎”的异闻,很有可能会成为《西游记》中宝象国黄袍怪变唐僧为虎这一故事的创作触媒。
其二,吴承恩有可能看过《楮记室》。吴承恩曾为潘埙的八世祖潘思诚作传,题为《淮安路医学教授古逸先生传》。此“传”中有“野史氏曰:余尝于先生八世孙中丞熙台公家拜先生画像”云云,且吴承恩曾于《禹鼎志序》中自称“野史氏”。可见,吴承恩曾到访过潘埙家,亦应该对潘家藏书、藏画有所了解。据苏兴先生考证,《淮安路医学教授古逸先生传》一文收录于潘埙所著《淮郡文献志》卷六,故而,此文应作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之前。又“野史氏”与《禹鼎志序》中吴承恩的自称相同,故而此传应作于《禹鼎志》成书之前后。另据蔡铁鹰先生考证,《禹鼎志》最晚成书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因此,《淮安路医学教授古逸先生传》一文大约完成于嘉靖二十一年到三十四年这十四年间。《楮记室》序后署“嘉靖庚申春三月朔”,故此书抄本完成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是书卷一左侧提款云“平田野老纂集,不肖孙潘蔓梓行”。潘埙于嘉靖四十一年去世,吴承恩于嘉靖四十三年应潘蔓之邀作《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潘公神道碑》,且吴承恩曾于嘉靖三十四年之前拜访过潘家,故可以推断,吴承恩接触过《楮记室》的可能性极大。
其三,《楮记室》一书的定位。是书序中,潘埙家姓楮的“记室”员说:“公拾古人遗唾多矣,乐乎?”潘埙认为:“当此耄年,日偃仰田舍,得闻所欲闻,见所未见,岂不乐哉?”显然,潘埙对搜集楮记室眼中所谓“遗唾”颇有些不遗余力、乐此不疲。四库馆臣在提要《楮记室》时有云:“大抵抄撮而成,冗杂特甚,又多附录前明事实,间以委巷之语,尤有乖雅驯也。”[7]《楮记室》“有乖雅驯”的“委巷之语”的定位,决定了此书所录内容的非正规性。潘埙也曾给这些所谓“遗唾”以明确定位,即“理有契于心,事有感于时,或切于用”的“闻所欲闻,见所未见”之事。那么,《楮记室》到底“抄撮”了什么?表一拈出《楮记室》中十则与《西游记》故事相类的异闻,标明异闻发生年代及引书出处,并标明《四库全书总目》对所引之书的评价:

表1
可以想见,从天顺到嘉靖的一百余年里,与《西游记》故事相类似的故事应该不止这十种,发幽怪、记灾祥、阐阴阳的“乖谬”之书又何止这五部。四库馆臣在提要《续说郛》时称,“正嘉以上,淳朴未漓,犹颇存宋元说部遗意。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8]吴承恩(1500-1582年)生平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其文学创作正处于明代中后叶“说部”文风巨变的转型期。正嘉以上尚且出现如此之多与《西游记》情节相类似的故事情节,隆万以后的情况,也是可以推想的。
在古代小说情节发展的历程中,枝繁蔓衍的“影响—接受”模式,似乎成了建构小说现有情节与初始原型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殊不知,怪奇情节在需要初始原型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小说家的天才构思也是不可忽视的。“想象胜于意志,胜于生命的冲力,它是精神创造力的化身……想象划定了我们精神领域的最后限界。”[9]在现有文化传统与天才构思之间,便需要一种“触媒”。毋庸置疑,上述《楮记室》中的十个怪奇情节与《湖海搜奇》中“人化虎”的怪奇情节,便是促成旧有文化传统转向新的怪奇故事的重要且直观的外部“触媒”,并最终决定了小说家“精神领域的最后限界”。
三
潘埙的《楮记室》载录了许多历时性的“闻所欲闻,见所未见”之事,而其中的类乎共时性的“本朝”(即明代)异闻,尤为值得关注。一部杂体小说集中,如果出现一个引发《西游记》怪奇故事的“触媒”并不足为虑,那么出现为数不少的引发《西游记》怪奇故事的“触媒”便不可等闲视之了。现略择其要,分而述之。
其一,女儿国怀孕故事的“触媒”——“男子生儿”(本朝)。
嘉靖巳酉,横泾傭农孔方忽患膨腹,尽日愦愦,几数月,产一肉块,剖视之,一儿身,肢体毛发悉具,而裸处其中。如史载“牝马生驹”,未省何异,姑记此矣,知者辩之。[10]
横泾位于江苏省高邮市东北部,距淮安不远。既是“男子生儿”,便应是“牡马生驹”,“牝马生驹”疑为抄脱之误。“牡马生驹”典见《汉书·五行志》:“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马生驹,三足,随群饮食,太守以闻。马,国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11]班固借用谶纬之学,比附西汉末期董贤专宠、王莽干政之事。干宝《搜神记》卷六亦搜罗此事。“男子生儿”发生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的横泾,又属于骇人听闻的“幽怪之事”,加之历代女国“浴水而孕”的怪奇情节传统,因此,“男子生儿”类的本朝异闻很有可能是吴承恩构建女儿国猪八戒、唐僧怀孕之事的“触媒”。
其二,孙悟空身世故事的“触媒”。
异闻一:“淮河水怪”(本朝)。
淮水与淝水合流,经寿春城而北汇为荆山湖,又北为荆涂两山,东为峡,出峡而东北会涡水,以东入海。自神禹道淮,锁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几千年,淮绝无患。弘治十六、七年内,荆涂峡间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峡口,淮水不得泄,则壅而旁溢。春、六、濠、颍之间,田庐多侵。商船至湖,时遇怪风浪,多颠覆;往来棹浪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风起,即大浪三四掀逐而来,人艇俱没。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赶浪”,相讳不敢犯。又或夜静月明,梢人见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际,方报告惊谛,则倏然入水,风波迭作,于是又名“神木”。如是者盖四、五年。正德以后,患息,人复见于涡河中。乙巳岁,予经历蒙城,渡涡水,则干涸,通骑矣。相传又徙于颍水,今颍水复涸。或又传入黄河中。予度此物或即巫支祈也,世俗寡识,妄谓“赶浪”、“神木”云耳。盖此物锁于龟山,唐时为渔者掣出水,常一献形,计今必尚存。而龟山至涡水口,旧窟路且近,涡南十余里即荆涂峡口,淮淝所由也。其出而作祟孽于此,故当然者,岂气机衰泄,圣神功力有时亦匮,而妖渗之物因得逃脱,天械复出,而鱼鳖生民耶?虽然《南史》载,梁武帝筑堰壅淮水以灌寿春,未几,溃,水大下响如雷,鱼头鬼面之怪下以万数。然则淮渎之中,自昔固多怪矣。泗州龟山寺前有巨井,大铁索满其内。予尝泊舟山麓,登寺眺览,命左右戏引,将百丈而不竭,井中有声蓬蓬然,俱而命止。寺僧与土人皆云,昔大圣降伏水母,锁之井中,索其旧物也。后会泗州二守张君锡讯其事。张云:“弘治末年,岁大旱,淮水清浅,龟山居人或见铁索亘河底,然以其神物,无感动也。”予记《岳渎经》云:“禹得涡河水神巫支祈,锁之龟山之下,淮乃安流。”今世俗所谓“大圣降水母”,即此事而后人传误耶?抑别有说也。但禹锁支祈于山麓水中,唐时犹有钓者掣见此物,今河底铁索,疑为故物,井中所有则在山顶,理势想不通,得无后人因前事而伪设欤?抑桑海变更,水洲涨与山一,或井中别有窍道,与外河通贯欤?[12]
据《两山墨谈》的作者陈霆所录,弘治十六、七年间(1503年-1504年),淮河中有妖异,即土人所谓“赶浪”“神木”。此水怪先后辗转流窜于淮河、涡河、颍水、黄河之中,使得陈霆认为此怪很可能是巫支祈。另据《南史·康绚传》载,梁武帝曾筑浮山堰,后堰溃,淮水“奔流于海,杀数万人。其声若雷,闻三百里。水中怪物,随流而下,或人头鱼身,或龙形马首,殊类诡状,不可胜名。”[13]宋人秦观所做《浮山堰赋》中“若然犀之照渚兮,旅百怪而争遒;马孛马怒而嘘蹀兮,虎蛟冤而相纠”一句亦本于此事。是赋“并引”有言:“梁武帝天监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计,欲以淮水灌寿阳,乃假太子右卫康绚,节督卒二十万,作浮山堰于钟离,……未几,淮暴涨,堰坏奔于海,有声如雷,水之怪祅蔽流而下,死者数十万人。”[14]明初人钱子义在《寿春》一诗中云:“硖石嵯峨锦树秋,兴亡得失两悠悠。浮山堰下蛟龙宅,冷雨腥风动客愁。”[15]而陈霆所谓“鱼头鬼面之怪”,便是由先代文化中那些“或人头鱼身、或龙形马首”(特别是“蛟龙”)的“争遒”“百怪”演化而来。
陈霆曾游览泗州龟山寺,而寺前巨井中的巨索据当地僧人与土人所言,乃是当年“大圣降伏水母”时所遗留的旧物。陈霆又从泗州张君锡处得知,弘治末年,龟山附近之人曾看见铁索横亘在因干旱而显得清浅的淮河中。这些见闻,不禁让陈霆想起了《古岳渎经》中大禹锁巫支祈于龟山的掌故,并进而认为市面上流传的“大圣降水母”的传说,便是此类事件在民间以讹传讹的产物。“大圣降水母”的故事不仅在民间流布广泛,而且在元明文人的文学创作之中亦变成了绝佳的素材。元人高文秀的《泗州大圣锁水母》杂剧,明初须子寿的《泗州大圣淹水母》杂剧,《宝文堂书目》亦著录有《泗州大圣降水母》杂剧,当为同一题材。吴承恩的挚友朱曰藩曾在金陵友人处看见过元人小说《大圣降水母》,朱曰藩在《跋姚氏所藏大圣降水母图》一文中曾言:“丙申夏,客金陵,于友人几上,见元人《大圣降水母》小说,甚奇,为读一过。乃今葵谷赞府视此图,云李龙眠所作变相种种,较之小说益奇矣。”[16]嘉靖十五年(1536年),朱曰藩不仅看到了小说,还看到北宋画家李公麟所画的(或为摹本)、类似于连环画的“变相”《大圣降水母图》,而且“变相”比小说更加新奇颖异。关于泗水龟山附近的水母在文学作品中则变成了母猴精。刻印于嘉靖年间的《清平山堂话本》中有《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一文,文中梅岭申阳洞有猢狲精兄妹四人,其中小妹便是泗州圣母。元明之交无名氏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中,猴精齐天大圣的姐姐便是龟山水母。元人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孙行者的二妹便是巫枝祗圣母。可见,在元明的小说杂剧之中,泗水龟山附近的水母已经成为“泗州圣母”“龟山水母”以及“巫枝祗圣母”,成为猴精家族中的一员。
民间传说与文人创作是互为表里的。民间传说为文人创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而文学作品的传播必将在民间产生新的变异的传说。二者共同变成了吴承恩耳濡目染的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吴承恩《西游记》的创作。《西游记》中,鹰愁涧孽龙变作白龙马,流沙河妖精变作沙悟净,黑水河的鼍龙,通天河的金鱼精,碧波潭的九头驸马等,都是河中妖异,均可以看做是“赶浪”“神木”“人头鱼身”“龙形马首”之类的淮河水怪在《西游记》中的变种,而距离淮安不远的、泗水龟山附近的、传说中的水母很有可能就是孙悟空的原型。
异闻二:“石中男女”(本朝)。
成化间,漕河筑堤。一石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状,长仅寸许,手足肢体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邮卫某指挥得之,以献平江伯陈公锐,锐以为珍,藏焉。此等事,虽善格物者,莫能究其所以。[17]
关于平江伯陈锐,《明史》无传。据《明史·孝宗本纪》载,弘治七年(1494年),“夏,五月甲辰,命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同刘大夏治张秋决河”[18],《明史·河渠志》亦有记载。张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明万历年间礼部尚书、大学士,东阿人于慎行在《安平镇志序》中称“漕渠出齐鲁之郊,旋之若带,张秋有结也”。由于张秋的存亡决定着漕运的通畅程度,所以陈锐的使命更为重大。另据明人田汝城《西湖游览志余》记载:“钟狂客禧,南海人,甚有诗名。成化中,淮南督理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公锐,取归幕下。”[19]由此可知,陈锐的官职是“淮南督理漕运总兵”。陈锐结交甚广,可谓名满天下。据国史总裁兼经筵官杨廷和所撰《明故驸马都尉樊公墓志铭》载,陈锐曾和明宪宗的女婿、广德长公主的夫君樊凯有所交游。樊凯“与人交有终始,人亦乐与之友。每朝下,与都尉周公景、平江伯陈公锐辈,酌酒赋诗为乐,相规以善,世俗声利之言,绝不出口,声名流闻缙绅间”。陈锐不但有才名,而且有武功。据2002年广西梧州出土的明成化六年两广总督韩雍所撰《建总府记》石碑(现藏于梧州白鹤观)载:“未几,复以平江伯陈公锐挂征蛮将军印,克总兵官司镇守两广,同开总府于梧,便宜行事,两广副将以下俱听节制。”由此可见,平江伯陈锐曾到过山东、淮河沿线以及两广地区,可谓文韬武略、名满天下。
《楮记室》转录《菽园杂记》的“石中男女”的故事,便发生在距离淮安不远的高邮,且与时任“淮南督理漕运总兵”的陈锐有直接关系。故而,“石中男女”的故事必然会成为淮安一带乃至淮河沿线的重要谈资。吴承恩也确实去过高邮。嘉靖十六年(1537年),“夏秋间,吴承恩由水路经高邮赴南京应试。朱曰藩(子价)在高邮作《露筋祠》五律送别,吴承恩同赋《露筋祠同朱子价》”[20]。
异闻三:“石神”(本朝)。
山西泽州有一石神,妖物也。淫具悉备,妇人凡求子者,不别贵贱,辄往就之,即妊焉。嘉靖初,东御史郊谪判于此,令民碎之。[21]
这则故事可以视为明代中后期生殖崇拜甚或是男根崇拜的一大佐证。我国的名山洞府之间,存在着很多类似于男根的石山、石柱、石壁画。如:广东丹霞山的阳元石柱、内蒙古西部峡谷的人根峰、江西龙虎山的金枪峰、云南阿庐古洞的天然钟乳石;新疆呼图壁、内蒙古的阴山和桌子山、广西的左右江、宁夏的贺兰山发现的石壁画等。而类似的“石神”在亚洲诸国也很是常见。韩国济州岛的吉祥物“石头爷爷”、起源于日本江户时代的“金魔罗祭”、泰国Nai Lert公园的Lingam Shrine(男根庙)等,每年都会吸引众多的善男信女前来祝求生育、消灾祈福。而我国江淮一带的民间也有男根崇拜的风俗。方纪生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一书中说:“皖南南陵、宣城数县,田地里有所谓石和尚者,其性器特大,土人谓是以辟邪,实即男根崇拜之遗留。”[22]淮北市临泉县博物馆春秋沈子国古遗址中有一个小铜人,通身高1.92厘米,裸体,可是其男根巨大。无独有偶,浙江绍兴禹陵的窆石亭中有一块窆石,亭旁有明代天顺年间的碑刻《禹陵重建窆石亭记》:“窆石者,窆下棺也,或谓下棺之后以此石镇之。”窆石略呈圆椎状,高两米,底围两米有余,顶端有一圆孔。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会稽禹庙窆石考》一文中详细地考证了这块窆石的源流:“盖碣自秦以来有之,孙皓记功其上,皓好刻图,禅国山,天玺纪功诸刻皆然。岂以无有圭角,似出天然,故以为瑞石与?晋宋时不测所从来,乃以为石船,宋元又谓之窆石,至于今不改矣。”[23]而这块所谓的“瑞石”,由于其形状特异,酷似男根,亦引来许多妇女向“穿”中投掷钱币、石块等物,以卜生育。由此可见,类似于《西樵野记》中的“石神”形象,在我国江淮、江浙一带自古有之,且深得民众推崇。
综合上述三则异闻,不难想见,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首先想到的是在淮河水中兴风作浪的水怪,但由于泗州龟山附近的水母传说乃是母猴精之幻化,加之前代文学作品中关于齐天大圣、孙行者的描述多为公猴精,故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猴精形象是看不出性别的。“石中男女”折射出我国古代的“野合”故事。《诗经》中的《郑风·褰裳》和《召南·野有死麇》便已经出现了最早的野合,而《史记》中,孔子便是野合诞下的圣人。《史记·孔子世家》云:“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24]而这石中野合之事,为石头能够孕育生命提供了无限遐想的空间。“石神”故事,则暗示男根形石柱具有强大的生殖能力。进而可以解释,孙悟空是从石头中蹦出而非他物。因为,在明人的思维当中,石头尤其是状似男根的石头有孕育繁殖的异能。故而,上述三则异闻成为吴承恩建构“石生猴”情节模式的“触媒”。
四
吴承恩曾在《禹鼎志序》一文中自称:“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25]可以想见,《湖海搜奇》中胡琏治下“人化虎”的异闻,《楮记室》中“男子生儿”“淮河水怪”等异闻,便是吴承恩一生中“偷市”“旁求”的、并最终“贮满胸中”的、众多的“野言稗史”中的例子。美国学者诺夫乔伊认为:
有一些含蓄的或不完全清楚的设定,或者在个体或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思想习惯。正是这些如此理所当然的信念,它们宁可心照不宣地被假定,也不要正式地被表述和加以论证,这些看似如此自然和不可避免的思想方法,不被逻辑的自我意识所细察,而常常对于哲学家的学说的特征具有最为决定性的作用,更为经常地决定一个时代的理智的倾向。[26]
吴承恩曾经搜求的那些作为共时性文化触媒的“野言稗史”,不仅是一种“含蓄的设定”,更是一种在“一代人的思想中”形成惯性作用的“心照不宣”且“不可避免”的“思想习惯”。“幽怪之事”甚夥且“风气日偷”的嘉、隆“说部”文坛,俨然成为作意好奇之人肆意逞才的文学疆场。那些无处不在的怪奇“触媒”,必然会成为小说家们不可多得的创作催化剂。反过来说,那些为数甚巨的“乖谬殊甚”的发幽怪、记灾祥、阐阴阳的“委巷之语”,必然会以缀点成面的方式建构起以《西游记》为代表的怪奇小说的“不被逻辑的自我意识所细察”的创作生态。推而广之,不难发现,很多怪奇小说的作者,都有作意好奇的性格特点,参见表二。而在怪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某些表现形式不一的“触媒”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为最终的成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创作生态。

表二
谷神子言:“夫习谶谭妖,其来久矣……语其虚则源流具在,定其实则姓氏罔差。”[27]在为虚语“定实”的过程中,在作意好奇性格(对怪奇事件、著作的偏好)的观照下,有些小说家以潜意识活动作为触媒,有些小说家则以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怪奇之事作为触媒。而触媒的大宗,则是以高子业、谢凤仪们为代表的“好事者”“诸君子”“四方同人”“文字交游”们为小说家提供的不经之谈。因此,上述《楮记室》与吴承恩的关系,四则异闻与《西游记》情节之间的关系,应该不是个案,类似关系应该存在于以“异域+灵怪”为表征的怪奇小说的情节艺术史的发展进程中。可以认为,一部怪奇小说情节艺术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便是一部外部触媒持续产生作用的历史。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在《现在,为什么要谈文学史?》一文中称:“作品,是在历时坐标轴和共时坐标轴的交叉点上,加上作者的个性因素,诞生在三次元空间的,这是今后也不会改变的。所以,作品的成立少不了文学史的因素。如果这就叫文学史的话,那么,文学史就是文学作品的内涵。”[28]不可否认,在怪奇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作家的天才想象是形成小说情节的重要推力;而诸如《山海经》等怪奇地理学著作提供的原型,如何转化成小说家所要传达的情节认同,不仅需要天才想象,更需要较为直观的外部触媒。从前述女儿国故事的形成过程不难看出,历代有关“女国”的文献传录,生成于小说史上的“历时坐标轴”;明朝本朝的“男子生儿”异闻,生成于小说史上的“共时坐标轴”。再加上吴承恩“好奇闻”的“个性因素”,一部怪奇名著便在小说史的洪流中应运而生了。通过对吴承恩《西游记》共时性创作生态的研究,古代怪奇小说史的书写,是有可能朝着聚焦于“共时坐标轴”的小说生态史观迈进的。这种小说生态史观,虽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偶然性,但是的确有可能有效地析出怪奇小说的创作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