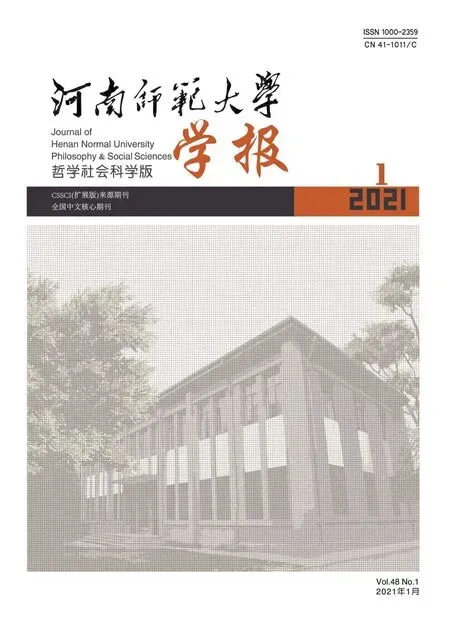鸦片战争与第一次阿富汗抗英战争比较研究
——以军事素养、国民性与交通为中心的考察
刘 澍,周少川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阿富汗被称作“帝国坟墓”(the tomb of the empire),二百年来,英国、苏联、美国等世界强国均在此折戟沉沙,损兵折将后颗粒无收。就英国而言,阿富汗与英国发生过三次战争, 1839年至1842年阿富汗进行第一次抗英战争,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与英国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导火索的鸦片也正是来源于阿富汗和印度。就抵抗国人口而言,1850年时阿富汗人口3750000人(1)科林·麦科伊韦迪,理查德·琼斯:《世界人口历史图集》,陈海宏、刘文涛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178页。因缺乏第一次阿富汗抗英战争时期阿富汗人口数据,故以1850年数据暂代。,1839年时清朝人口410850639人(2)此数字不包括湖南、福建、台湾人口,据《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329,《清实录》第37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188页。,清朝人口是阿富汗的110倍。就侵略军人数而言,英军侵略阿富汗的人数为1.7万人(3)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38页。,英军侵略大清帝国的人数最多时为2万人(4)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52页。,然而两场战争的结局让人大跌眼镜。马克思曾这样记载第一次阿富汗抗英战争的结局:“1842年1月13日,贾拉尔阿巴德(Jalalabad)城墙上的哨兵们眺望到一个穿英国军服的人,褴褛不堪,骑在一匹瘦马上,马和骑者都受重伤;这人就是布莱敦(Brydon)医生,是三个星期以前从喀布尔退出的15000人中的唯一幸存者。”(5)马克思:《印度编年史稿(664—1858)》,张之毅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5页。与阿富汗的辉煌战绩相比,清军战绩惨不忍睹,按照张莉的计算,在鸦片战争的12次主要战役中清军死约3100人,伤约4000余人,英军死71人,伤400余人(6)张莉:《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队的伤亡及其影响》,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页。。其中第一次定海之战英军无伤亡,除镇江之战外,每一次战役英军死伤人数都不超过百人,而清军除死伤外,还有大量溃散、失踪人员未统计在册。
大清帝国人口在阿富汗110倍的情况下,被英军打得一败涂地,阿富汗在以部落为主体的情况下打得英军几乎全军覆没,个中缘由值得深思。到目前为止,中文世界鲜见研究阿富汗抗英战争胜利之因的成果,更无任何学术文章对这两场战争作比较研究。笔者试从军事素养、国民性、交通条件三个方面对这两场战争进行对比,探析其胜败之因。
一、军事素养对比:虎狼之师与乌合之众
就战争能力而言,阿富汗山地兵久经战阵,在面对英军时,表现出非常高的战术素养,下面拟从军队阵形、战术素养、武器射程三个方面对阿富汗、大清帝国、英国三支军队作对比。
其一,军队阵形。以1841年11月20日的战斗为例,阿富汗指挥官米尔·马斯吉迪在英军的临时军营上方高地集结,他们挖堑壕、筑胸墙,彻底切断英国人来自其他地方的粮秣补给,随后开始用火炮轰炸临时军营(7)威廉·达尔林普尔:《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 1839—1842》,何畅炜、李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71页。。史料记载:“眼见情况危急,英军旅长立即把步兵分成两个方队,让骑兵挤在两个步兵方队之间,然后等待敌人发起进攻。他相信,这个曾经赢得滑铁卢战役的战术在这里也会奏效。但阿富汗人并没有发起冲锋,而是在与英军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用阿富汗长滑膛枪向编队密集的英军猛烈开火。身穿艳红色宽松外衣的英军士兵成了活靶子,而他们手中枪膛较短的滑膛枪却打不到敌人,这让他们无比懊恼。通常情况下旅长会先将大炮对向阿富汗人,造成对方大量伤亡后再下令骑兵冲锋收拾残敌。然而正如凯伊评论的那样,似乎‘上帝的诅咒降临到这些不幸的人身上’,因为他们唯一的那门野战炮还是因为炮膛太热而无法使用,否则就有爆炸的风险。成批的英军士兵就这样不断倒在阿富汗人的枪口下。这时在山下兵营里观战的英军惊愕地发现,一大队敌军正沿着山坡上的溪谷向山上毫无察觉的英国部队匍匐前进。到达山顶后他们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挥舞着长刀,出其不意地向英军猛扑过去,躲藏在岩石后面的同伙也不停向英军射击。英军再也无法承受了,他们彻底崩溃。”(8)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张望、岸青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第275—276页。
面对阿富汗的火炮轰击,英军采取滑铁卢战役对付拿破仑的阵形,即把步兵摆成空心方阵。这种阵法是前面一排士兵持刺刀和长矛蹲下,构筑成最外防线,又称刺猬空心阵。后面一排士兵站立射击,以交叉立姿用滑膛枪稳住阵脚,再后面还有负责装填的战士和预备队,方阵中间则是空心,有时会把各种辎重或指挥系统保护在其中。这种方阵在面对骑兵冲锋时可以起到很大作用,敌军骑兵纵然攻破方阵一角,也会陷入重围,从而很快被歼灭(9)唐纳德·索默维尔:《革命战争和法国战争》,范洁译,青岛出版社,2003年,第52页。。英军以为阿富汗会发动骑兵冲锋,故而摆这样的方阵。然而阿富汗人在英军射程外,他们以滑膛枪对英军进行齐射,英军却根本打不到阿富汗人。“方阵前列不得不三度才被拼集齐整,毫不夸张地说,前排队伍被全部射杀”(10)威廉·达尔林普尔:《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 1839—1842》,何畅炜、李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72页。。在与敌军骑兵作战时,英军惯用战术就是打防守反击,先用步兵方阵守住阵脚,抵挡住敌军骑兵前锋,然后用火炮轰炸敌军骑兵中坚,最后自己骑兵反冲锋收拾残敌。不过,由于阿富汗千沟万壑的地形,英军重火炮根本无法长距离运输,剩下的轻型火炮则无法对阿富汗人进行大规模杀伤,这使得英军战术完全破产。阿富汗人在与英军正面交战时,也派出部队侧面迂回,自“山坡上的溪谷”而上,用长刀砍杀英军,最终英军惨败。
英军的阵形在面对阿富汗山地兵时,遭到惨败,而清军阵形在面对英军时,亦暴露出极大缺陷。清军作战单位为百人哨,每哨编10个小队,火枪手和持冷兵器者各半,前排是20名抬枪手,中间是30名鸟枪手,后面是50名手持藤牌、长枪、刀、弓箭的冷兵器手。战斗时,前排以卧姿,中间以跪姿,后排以立姿。齐射完毕后,前排左退到后排左,前排右退到后排右,重新装填火药和弹丸,准备二次发射(11)李湘棻:《筹备英夷议二十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286页。。临敌时,远距离者以火炮攻击,稍近再放抬枪,再近的以鸟枪打击,最后以冷兵器肉搏厮杀。为协同冷兵器和火器部队,清军整个队列只能以缓慢速度移动,战术机动性相当差,很难运动到能最大限度发挥火力的有利位置。鸦片战争时灵活的英军队形往往能成功地通过迂回等机动动作对清军最薄弱处实施攻击。清军的队形排列过于密集,一旦被英军火炮击中,就成片倒下,队形崩溃。而英军是空心方阵,被轰炸时只是外围的一角受损,相比之下队形基本不受影响。
其二,战术素养。以1841年10月12日的战斗为例,英军通过库尔德喀布尔山口时,“阿富汗人极为精通遭遇战战术,若不是借着火绳枪发出的闪光,根本无从判断狙击手身处何方。岩石和石块看起来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掩护……他们蹲踞着,只有轻型燧发枪的长枪管和包头巾顶端高出绝壁危崖露了出来。他们精准瞄射、弹无虚发……他们的杰撒伊步枪或长枪在长射程内穿杨射柳,我方火枪在同等距离却不会对其造成任何伤害。阿富汗人能踪影全无地隐没在景致中,这本领也让英国人震恐”(12)威廉·达尔林普尔:《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 1839—1842》,何畅炜、李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18页。。阿富汗人以岩石为掩体,枪法百步穿杨,这种遭遇战打法,使得英军无还手之力。对阿富汗人而言,目标靶是穿着红色军服的高大的英军身体,对英军而言,目标靶是火绳枪在岩石间隙的一点闪光,显然,英军难以射中阿富汗士兵。“道路从伽拉花园中部穿过,两旁围墙林立,到处都有葡萄园。阿富汗人沿此排开泼弹如雨,密密稠稠枪枪致命”(13)威廉·达尔林普尔:《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1839—1842》,何畅炜、李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70页。。阿富汗人枪枪致命,表现出极高的射击技术与军事素养。
相较之下,英军在阿富汗完全未表现出专业军事素养,安营扎寨等方面都很业余。以英军在喀布尔扎寨为例,英军营地“位于靠近库希斯坦的大道的一块洼地上,四周被堡垒和小山环绕与控制着,但这些堡垒既未加以占领,也未加以拆毁。这个军营的低矮的胸墙,可以纵马一跃而过。除了这些缺点外,全部供应都贮藏在离军营边沿相当远的一个小堡垒内。从军营到那个堡垒之间有一些堡垒和有墙的园子,两者都不在英国人控制之下”(14)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第二卷上册,张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728页。。英军扎营于洼地,四面居高临下的制高点居然既没有派兵把守,也没有拆毁其军事设施。英军的军需居然放在了距离军营相当远的地方,一旦被敌人切断补给,后果不堪设想。阿富汗人反攻喀布尔时,果然利用了英军的一切漏洞,英军的安营扎寨与马谡在街亭的安营扎寨水准无二,最终自掘坟墓。
与阿富汗“枪枪致命”的军事素养相比,清军连瞄准都不会,魏源曾记载:“击八十丈以外,炮口加高,量高补坠。有量天尺插在炮口,以定远近,加高度数,折为尺寸以补坠数……皆中国营兵所不习。”(15)魏源:《海国图志》卷88,《魏源全集》,第7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2076页。命中率主要是5个部件的问题:矩度、铳规、铳尺、准星、照门。矩度用以精确测量目标和火炮之间距离,铳规用来测量火炮仰角,铳尺用于确定装药量,准星与表尺缺口相辅,构成瞄准基线,有的可以向各个方向移动,以便修正。照门的用法是让射手的视线透过它对准准星,准星再对准目标然后开火。清军的许多火炮没有准星、照门、铳规,5个部件缺3个。有的虽装有准星、照门,但缺乏铳规等辅助器具,结果只能大致确定射击方向,无论是确定高低夹角,还是火药装药量,都只能靠士兵的经验来完成。显然,这样的战术素养在面对英军时不堪一击。
英国人这样论述清军的炮台:“广州附近这些炮台……不过是处于幼稚阶段的堡垒建筑的样本,没有壕沟,也没有棱堡、斜堤或任何反击的防御工事……河岸上的炮台都是裸露的,没有一个能够抵挡得住一只大炮舰的火力,或可以抵御在岸上与炮舰配合的突击队的袭击。突击队总是从他们的炮火所不及的侧面和后方找到最佳的据点来袭击他们。值得注意的是炮台的门口常常开在旁边。正面的进路,如果不是全不设防,也只有一两门大炮控制着,没有壕沟,没有吊桥,没有吊闸或其他防御物,除了内外门那几寸厚的木板……据我们的判断,这些炮台的效能……一般是可能想象出那是再坏没有的。”(16)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69—70页。这样构筑防御工事充分体现了清军在战术素养上的业余水准。卡文迪斯说:“要是说在三亿中国人中找不出一支好军队,也许是对人类的莫大的侮辱。”(17)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华书局,2006年,第109页。这句话虽然过分,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清军战术素养之低下。
其三,武器射程。阿富汗抗英战争中,阿富汗人可以轻易地击中英军,英军却打不到阿富汗山地兵。英军中的印度兵悉达·罗摩说:“我们日夜遭受大炮炮击搅扰。敌军人数看似以千计增加,他们手中长长的火绳枪射程远过我们的火枪射程。虽然他们根本不可能抵挡正规冲锋,但只要能在墙后屋后等地找到隐蔽处,他们的射击就令人苦不堪言。”(18)威廉·达尔林普尔:《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1839—1842》,何畅炜、李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65页。汤因比也说:“1838年不列颠的滑膛枪的射程不如阿富汗的滑膛枪射程远。”(19)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晏可佳、张龙华译,《汤因比著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2页。阿富汗滑膛枪也叫杰撒伊(Jezail)火枪(也有的称为吉赛尔步枪),这是一种由阿富汗本土设计的前装燧发式武器。据说该枪的射程要超过同时期的滑膛火枪100码(91.4m)的距离,甚至更远。英国人对于阿富汗燧发长枪的评价极高,甚至直到1870年代,仍有一些英国军官认为该枪甚至可与现代化的马蒂尼·亨利步枪相媲美(20)方丽:《英国马蒂尼·亨利后装步枪VS阿富汗前装燧发长枪》,《轻兵器》,2012年第5(下)期。。
鸦片战争时中国的枪炮射程与阿富汗的情况截然相反。林则徐在1842年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彼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21)《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林则徐所言清军火炮打不到英军,英军火炮却能击中清军,是客观事实,但是英军“大炮远及十里内外”则是林则徐的想当然。晚清文人对于军事、数学等内容多昏聩无知,哪怕晚清最先进的中国人林则徐依然对于火炮射程没有基本的准确概念。其实此时英军射程最远的42磅弹岸炮也就是射程3100码(2850米)(22)张建雄,刘鸿亮:《鸦片战争中的中英船炮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0页。,何来“十里”(5000米)?
阿富汗的部分武器装备性能参数在英军之上,而清军武器在射程、射速方面则全面占下风。清军鸟枪铅丸重31.5克,装填火药10.5克,射程150米,射速0.3-0.5发/分钟;抬枪铅丸重18.9克,装填火药132克,射程480米,射速1发/分钟。英军伯克式前装线膛燧发枪铅弹重35克,射程220米,射速2-3发/分钟;布伦式威克前装滑膛击发枪弹丸重53克,射程330米,射速3-4发/分钟(23)张建雄,刘鸿亮:《鸦片战争中的中英船炮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页。。总体而言,清军在武器上占劣势,清军抬枪虽然射程远,但装备数量很少。此外,清军鸟枪、抬枪的制造工艺粗糙,枪身太长,弹药装填、射击均不便,且射速慢,因此清军武器在综合水准上远逊于英军。
久不闻兵戈的清军在军事素养上依旧停留在中世纪的状态,而阿富汗人通过与英国人的接触,已经掌握了许多现代武器和军事战术,如此,阿胜清败便不足为奇了。
二、国民性对比:彪悍善战与武德废弛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平定大小和卓木时,清军为捉拿大小和卓木,曾至阿富汗部落边境,阿富汗巴达克山部落将小和卓的人头送来,清军退兵,这是清朝人与阿富汗第一次打交道。此后,中国士大夫不断留下有关阿富汗的记载,在他们眼中,阿富汗人骁勇善战,勇武过人。乾隆四十年(1775),七十一所著《西域闻见录》中有“敖罕”的记载,“敖罕”就是阿富汗,他说阿富汗人“多力而横恣,遇有战阵,辄为前锋,无火枪弓矢,专用木矛,冲突于矢石之间,矫疾无伦……西域人皆畏之……侵凌相尚,劫掠成风,既大远于中国圣人之教,又不解佛教慈悲之说,嗜杀好利,篡夺相循”(24)七十一:《西域闻见录》,《中国边疆史志集成·新疆史志》,第一部第一册,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3年,第157页。。18世纪阿富汗人好勇斗狠、能征善战已经成为中国人对其国民性的认知。1795年至1798年,担任新疆镇迪道的福庆在《异域竹枝词》中写道:“红头子国少人伦,束腕缠头战斗身。”他在自注中解释“红头子国”就是阿富汗,阿富汗人“多强力,好杀,其名山大川之中有烟瘴”(25)福庆:《异域竹枝词》,《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33页。。在1849年成书的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中,阿富汗仍旧是崇尚武力的形象:“胜兵数万,军器用鸟枪、长矛、腰刀,不习弓矢……敖罕,西域之大国,亦西域之乱邦,诈力相尚,日日皆逐鹿之势,盖自古而然。”(26)徐继畬:《瀛寰志略》,《近代文献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3页。阿富汗群雄逐鹿,兵燹频仍,已经是清廷士大夫的共同认知。
晚清士人最早记载第一次阿富汗抗英战争的是魏源1852年扩充为100卷的《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对阿富汗国民性有比较客观的论述,阿富汗“民朴实,有仇必报,百年不忘。耻买卖,不肯家居,以持械争战为要务。山峡甚多,有外人入之,即绝其归路,故敌国不敢侵,而屡伐他国获胜……道光二十一年冬,土民乘冬攻击英兵,英兵乏衣食,多毙者。次年英兵攻之,仍令前王摄权,地始安静”(27)魏源:《海国图志》卷19,《魏源全集》,第5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721页。。在晚清士人笔下,阿富汗人彪悍善战,一言不合即兵戈相向。《阿富汗斯坦志》云:“阿富汗人最嗜畋猎,而纵鹰搏兽,尤其所好,常逐鹿于平原……彼辈素善骑射,而所用土制之枪,施放咸中准的,阿富汗人常团聚以行乐。其聚也,非以贸易哄斗,惟欢呼作乐而已。或较刺击,或竞射赛骑,或作各种无律之野乐以为乐。”(28)学部编译图书局:《阿富汗斯坦志附新志》,《历代地理外纪史籍丛刊》,第1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第149页。萧应椿《五洲述略》载阿富汗“户口甚稀,概崇回教,性犷悍,好战斗,一言不合,辄以干戈从事”(29)萧应椿:《五洲述略》,《历代地理外纪史籍丛刊》,第63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第338页。。精于骑射、弓马娴熟的阿富汗人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枪下,许多殖民者最终会成为活靶子。
至清末新政时期,晚清士人对阿富汗国民性已经有了比此前更多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并不一定绝对客观。《阿富汗斯坦志》云:“阿富汗人自幼时即使之习惯流血之事,故不以死为畏,而搏击极骁勇,然一遇败衅,则心亦易灰。性好扰乱,不善守国法,及军律,当有求于人时,外貌似颇坦白,且善交接。若所求不遂,则亦粗暴狠恶,绝无人理。善设伪誓,而奸诈虚骄,贪渎无厌,复仇必逾其分,且极残忍,务求快意。虽掷己之生命,亦所不惜。定律极严,虽小过亦获严谴,犯法之易,他处无可比者。然犯者亦不常治,设或科罚,则罚极严厉。在阿富汗斯坦诸民族中,以阿富汗人最好争斗,且诡诈无信,阴行离间。及与人斗殴,视若常事……至其天性之惨刻,殆如食乌之鹯……平日尝以世系与独立及其战绩,自豪于人,以彼阿富汗人,实为第一等国民,即不有所加上于人,然心目中常自以为阿富汗人也。”(30)学部编译图书局:《阿富汗斯坦志附新志》,《历代地理外纪史籍丛刊》,第1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第144至146页。说阿富汗人“一遇败衅,则心亦易灰”显然不妥,阿富汗人面对英国的三次侵略战争,皆不屈不挠,怎会心灰意冷?说阿富汗人“善设伪誓,而奸诈虚骄”,其实也是晚清士人参考英国等殖民者的记载,重述西方话语。
英国在与阿富汗打交道时,屡屡中计,自然会丑化阿富汗人。但深入了解阿富汗人以后,英国人对阿富汗民族这样评价:“阿富汗人是极其吃苦耐劳、果敢无畏、独立自主的民族,百伶百俐善谐谑,随时乐于天南海北娓娓而谈,这令他们成为非常讨人喜欢的同伴……阿富汗绅士克己复礼,人人举止优雅。”(31)威廉·达尔林普尔:《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 1839—1842》,何畅炜、李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52页。俄国人利亚霍夫斯基认为“阿富汗人素以尚武好斗著称,历代征战者都试图以剑与火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好在此地集结部队,所以阿富汗人自青少年起就开始从军”(32)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页。。生于阿富汗的美国人塔米姆·安萨利写道:“这里的人民向来悍勇不驯,还有着虔心宗教、仇视外族的名声。部落,是他们永恒的归宿。头巾、胡须、长袍、弯刀与马匹是部落习气的象征。每一个部落都必须拥有这些东西,否则,他就不属于这里。”(33)塔米姆·安萨利:《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钟鹰翔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页。可见,凡是与阿富汗人打过交道的各民族都普遍认为阿富汗国民骁勇善战、民风强悍。
阿富汗国民性尚武,勇敢善战的民族在面对侵略者时敢于亮剑,自然会让侵略者撞得头破血流,而鸦片战争时的晚清国人则军无斗志,毫无血性。军人地位低下,完全没有荣誉感。在晚清中国当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汉纳根说:“西国之将领由武备院肄业生考充,兵弁以次第升,必其学成而后致用。中国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用意本相吻合,乃偏视兵之流品为最卑,遂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鄙谚。而凡阀阅之子弟,博雅之生徒,尽以入伍为大耻。惟穷无聊赖、游手好闲之辈,始贪其月饷而趋之。”(34)林乐知译述:《德国汉纳根军门语录》,《万国公报》,第80卷,1895年9月,第18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最早出自宋人《新编五代史平话·汉史平话》卷上,原文为:“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汉唐时期的中国人还充满了尚武精神,对外作战屡战屡胜,自宋以来,尚武精神逐渐衰颓,到晚清,军队更是缺乏武德,自然在英军面前不堪一击。
在第一次阿富汗抗英战争时,阿富汗人以强宗大族为纽带,以宗族对抗英军,不像晚清中国军人“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对此,《续瀛寰志略初编》记载阿富汗“先王之世,以分族为分国,故君子有收族之礼。自汉迄唐,强宗大姓,率子弟以捍外侮者,屡见于史册。岂非宗法未废,族可得民,而先王治天下之迹,由分而之合,亦由合而之分,可知者固如此哉”(35)世增译,顾锡爵述:《续瀛寰志略初编》,《历代地理外纪史籍丛刊》,第78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第374页。。从国家角度言,阿富汗强宗大族的模式可能会削弱国家权利,但从社会角度言,却能提高社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
“民族国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欧美各国的标准模式,因为“民族国家”就是按照西欧的国家模式定义的。大清帝国可以看作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天下朝贡体系,民族国家是多国并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晚清前的大清帝国在原则上不承认任何与自己对等的国家(36)《中俄尼布楚条约》承认俄国与自己对等,是康熙基于现实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考量。,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清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与这两种模式不同,像阿富汗这样的伊斯兰国家则是亚于西方定义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政治实体,阿富汗始终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作为一个国家需要具备的因素至少要有:领土、清晰的边界、普遍遵守的法律、统一的货币。然而阿富汗除了有领土,国内人民有共同信仰——伊斯兰教外,在国家层面就再也没有共同点了。因此,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国王只能控制首都喀布尔,并接受几个大城市地方豪强的朝贡,而在这几座城市之外,都是由地方宗族长老控制,英国即便从国家层面战胜阿富汗,并不代表就能战胜各地方强宗大族,只有战胜实际控制国家政治生活的地方强宗大族才算取得战争胜利。“全民皆兵”的阿富汗使得英、苏、美等国军队防不胜防,最终有了“帝国的坟墓”这一称号。
《续瀛寰志略初编》云:阿富汗“分为二十四族,每族聚居一地,自理其事,其长之升降,亦听命于王,虽杂用回教,然实不相通,军额有马队一万三千人,步卒二千五百人,国有大战事则人人能兵,其人勇猛朴诚”(37)世增译,顾锡爵述:《续瀛寰志略初编》,《历代地理外纪史籍丛刊》,第78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第376页。。“人人能兵”的阿富汗以强宗大族为纽带,从地方角度而言,国民性有其共同体利益,故能团结一致,给英国人以极大打击。恩格斯说:“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消遣和摆脱单调的营生的休息。阿富汗人分为若干克兰,大大小小的首领对他们实行类似封建的统治。”(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7页。阿富汗虽然在国家层面不够强大,但地方上的强宗大族为了保护地方利益,在面对英国侵略军时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各地方部族长老都以抗英为己任。相反,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在面对侵略军时仍旧一盘散沙,我行我素,毫无国家观念,这样的国民性焉能战胜侵略军?
法国探险家古伯察记载,道光皇帝死后,他曾在茶馆里大声议论皇位继承问题,想刺激中国人发表意见,但无人作声,“这种冷淡的态度着实让我们生气。这时其中一个良民站起身,以长辈的姿态,把他的两只手放在我们的肩膀上,带着相当讽刺意味的微笑作答:听我说,朋友!你们何必用这些无济于事的推测来劳神费心?朝廷官员不得不管国事,他们吃俸禄就要管国事,那么就让他们赚钱得了。但是别让我们去烦这些与我们不相干的事,我们徒劳无益地去过问政事才是大傻瓜”(39)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在大清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险》,张子清等译,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55页。。国民性浑浑噩噩,对于国家大事视同儿戏,国民缺乏对国家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这样的国家在与英国军队交战时岂能胜利?
鸦片战争期间,以扬威将军身份在浙东抵抗英军的奕经在奏折中说,清朝百姓在围观清军在浙东与英军作战时,根本没有人支持清朝军队,“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竟不知是何肺腑?”(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5页。鸦片战争期间,此类事情不胜枚举。从国民性角度讲,大清百姓对清政府没有认同感,对侵略战争的价值判断缺乏是非感,把自己当成旁观者。梁启超斥责旁观者说:“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今吾观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41)汤志钧,汤仁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7页。梁启超此言俨然是阿富汗与晚清国民性对比之不刊之论。阿富汗人在面对英军侵略时,几乎没有旁观者,漫山遍野的游击队让英军闻风丧胆,而晚清国人大多数在面对英军侵略时持旁观态度,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战争只能惨败。
三、交通对比:千沟万壑与平畴千里
就交通条件而言,阿富汗千沟万壑,平原多为沙漠。在这样一个地理状况复杂的国家,英军的运输和补给都受到极大限制。英军何乌少校曾绘制有一张从喀布尔到白沙瓦的道路状况表格,阿富汗山地交通之艰险于此可见一斑:胡尔德·喀布尔河,海拔7466英尺,通过六里长的一个隘口,过这条河23次;德辛隘口,海拔8173英尺,这条路要过7个山口,在河谷宿营;阿拉伦特(巨人墓),道路是在一个多石的峡谷之上,水不好;卢德-依-库塔·宋,在岩石的道路上爬上爬下;苏菲德·宋,上坡下坡,进入冈达马克谷,最后3英里是坏路;苏丹普尔,路在一低平和多石的沙漠上;查尔底,头一段上坡,然后进入一宽广的山谷(42)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第二卷上册,张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724-725页。。
如果说这些描述还不够直观的话,英军的战地记录应该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阿富汗的交通状况。文逊特·艾尔爵士这样记载胡尔德·喀布尔关隘:“这个可怕的狭道全长有五里光景,它被两侧高峻的山脉封闭起来,在这个季节,太阳只能从隘道的险峻的峭壁中透入一线瞬时即逝的阳光。一股山涧急流冲向路中央……水边上结着厚厚的冰凌,冰凌上又积着泞滑不堪的雪堆……我们得在这条小河上过来过去二十八次之多……对方向先头部队猛烈开火。”(43)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第二卷上册,张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724-725页。1842年1月12日,英军向贾格达拉克关隘前进,“这个可怕的狭道约有两里长,窄极了,四面被险峻的高山所包围。这条路有一个相当大的上斜坡,在接近坡顶时,发现有完全遮盖着狭道的,由带刺的橡树的枝杈构成的两座坚固的障碍物,又挡住了去路。在这里,伤亡又是十分惨重”(44)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第二卷上册,张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742页。。仅一条小河就让英军来去28次,蜿蜒曲折的河流,岩石嶙峋的道路,使得英军根本无法充分展现自己的军事实力。“穿越山口难如登天。英格兰人早在两个月前就将两门大炮和用数千头驴驮载的火药送至山口,以便扫清道路,他们还不得不用绳索将这些物品逐一拖拽上来。运送其他补给同样艰辛,代价是损失了大批骆驼、马、犍牛”(45)威廉·达尔林普尔:《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 1839—1842》,何畅炜、李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83—184页。,战争补给相当艰难。阿富汗的山多是岩石山,寸草不生,英军根本不可能因粮于敌,拾取腐肉使得英军大量食物中毒,非战斗减员也为数不少。
与阿富汗抗英战争中英军遇到的艰难状况相比,英军在中国面临的自然环境俨如天堂,鸦片战争中英国与中国主要的12次战斗,分别发生在浙江舟山定海、广东东莞沙角和大角、广东广州乌涌炮台、广州、厦门、浙江宁波镇海、浙江嘉兴乍浦、上海吴淞、江苏镇江等地。这些地方除镇江外,皆位于中国沿海,英军战舰来去自如,如臂使指,战场全在膏腴之地,英军可随时补给,与阿富汗的地理环境有天壤之别。
相比之下,清军虽然本土作战,但交通远不如英军便利。被英国国会任命为全权代表的璞鼎查1841年6月5日离开伦敦,坐船到地中海后,由陆路过苏伊士运河(当时运河尚未开通),而后在红海乘船,7月7日抵达孟买,在孟买停留10天后,7月17日再出发,8月10日即抵达澳门。从伦敦到澳门仅用67天,如果刨去在孟买停留的10天,则只用57天(46)原文为“They left London on the 5th of June,and on the 7th of July reached Bombay,which they left on the 17th,arriving in China in 67 days after they left England”。《中国丛报》,第10卷,1841年,第476页。。与璞鼎查相比,林则徐的进度就要慢得多了。林则徐1839年1月8日从北京出发,“午刻开用钦差大臣关防……由正阳门出彰义门”,3月10日抵达广州(47)《林则徐全集》,第9册《日记》,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5、382页。,用时62天。英国人从伦敦至澳门的时间比中国人从北京至广州的时间还要短,这就是中英之间的交通差距。如果说钦差大臣仅带随从,速度还能快一些的话,身披甲胄、携带辎重的清军士兵的行进速度则更加缓慢。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1841年10月26日)道光帝下令“于四川建昌、松潘两镇属内,挑选精兵……共足二千名之数……前赴浙江军营,听候调遣”(48)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卷35,中华书局,1964年,第1317页。。十二月二十日(1842年1月30日)这2000人中的第一批380人才到达(49)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卷42,中华书局,1964年,第1611页。。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1842年2月21日)“四川末起兵三百人,尚未报到”(50)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卷43,中华书局,1964年,第1619页。。从四川到浙江,119天下来,还有六分之一的人没到,比起英国人62天即可从伦敦到澳门的速度,清军不疾不徐,如蜗行牛步,这样的交通差距使得清军根本无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只能被动挨打。
综上,从交通角度而言,在地形与交通工具的双重影响下,千沟万壑的阿富汗成为大英帝国陆军的坟墓,而平畴千里的中国沿海则成为英军的靶场。
结语
无论是战争能力、国民性,还是交通条件,阿富汗人都有巨大优势,于是赢得了抗英战争的胜利。与阿富汗过硬的战争能力,生而为战士的国民性相比,大清帝国则如同一个中世纪的地理名词,与英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作战,其结局可想而知。战争胜败不只取决于综合国力,也取决于单场战争的投送能力。英国最长于海战,海军无法在阿富汗内陆破碎的山地施展,阿富汗人因地制宜,本土作战,自然能取得胜利。清政府虽然总兵力有80万人,远大于英国远征军巅峰时的2万人,但是清军驻扎过于分散,其军队主要用于弹压各地可能出现的民变,而不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来抵御外侮,故而战斗能力远逊于英军。与此同时,英国在鸦片战争中以海军攻击沿海各地,即便是打到镇江,也是军舰溯长江而上,故而基本不存在阿富汗那样的陆路交通运输问题,这就是两场战争胜败判若霄壤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