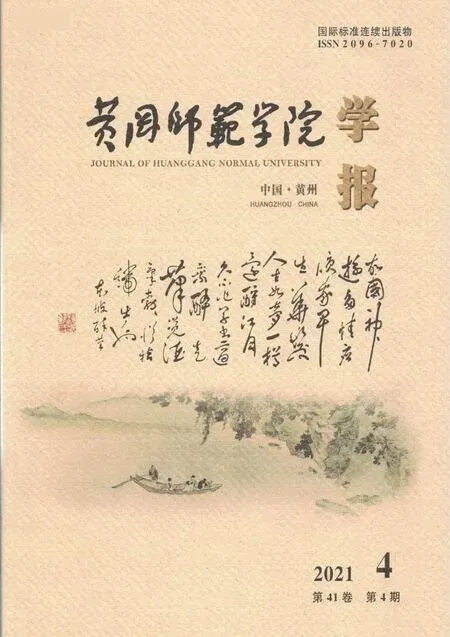鄂东本土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塑造策略
张才刚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0)
鄂东独特的地理与历史环境,造就了兼具保守与开放、独立与包容特性的地域文化,也赋予了本土人物鲜明的性格特质。从苏东坡到当代鄂东作家群,从李时珍、毕昇到李四光,从邢绣娘到历代黄梅戏表演者,从禅宗开创者到功勋卓著的鄂东革命者,在历史时空中交相辉映的“鄂东人物”不仅清晰地勾勒出鄂东文化的演进脉络,还为地域生活方式与人文精神做了最好的注解。已经被经典化、符号化的鄂东人物,已然成为本土物质生活与价值观念的综合载体,同时也为文学、戏曲以及现代影视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可以说,“自古光黄多异人”中的“异”,指的就是一种深植于鄂东乡土之中的性格养成。鄂东本土影视作品的审美意蕴与传播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者对这种“异”的艺术化发掘与影像化阐释。《铁血红安》《黄梅戏宗师传奇》《全城高考》等本土影视作品,表现的虽然是不同历史语境中的鄂东人物,但观影者依然能够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源于“大别山水”的个性气质,折射出创作主体相对一致的审美尺度和艺术手法。以“人物”为线索,能够窥见鄂东本土影视的叙事策略与价值追求。
一、在乡土情怀与革命理想的交融中再现“红色人物”
鄂东地域与历史语境中,“红色人物”具有尤为特殊的意义。他们既是特定历史时期民族大义与革命理想的践行者,也是地域生活方式及其生存理念的传承者——“乡土气息”与“革命情怀”的交互渗透,塑造出“鄂东革命者”这个特定的人物群体,也建构起“将军县”这一宏大意象。对于文学与影视艺术而言,“放牛娃团长”韩东山、“私塾先生党代表”王树声、“王疯子”王近山等鄂东革命者无疑是十分难得的表现对象:这些极富个性色彩的红色人物,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创作者的艺术灵感,还为其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故事与符号资源。在鄂东文学与影视艺术实践中,本土作家与影视创作者对红色人物塑造有着高度共识:他们往往不会高调宣扬革命人物的成就与功绩,而是将其置于鄂东自然地理与乡土生活场景之内,为个体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甚至命运走向的合理性提供成分的“证据”。这一人物塑造策略,摒弃了“高大全”的传统模式,由此催生出专属于鄂东地域的影视形象。对于观赏者来说,能够在自己熟悉场景中“遇见”的革命英雄,其性格、思想与行为更容易理解,整体形象也显得更加可亲、可信。这就印证了黑格尔的观点,“艺术作品之所以创作出来,不是为着一些渊博的学者,而是为一般的听众,他们须不用走寻求广博知识的弯路,就可以直接了解它、欣赏它。”[1]乡土鄂东代表的是一种世俗化力量,它既是艺术形象生成的本源,也为影视创作者与鉴赏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创造了空间。
鄂东本土革命题材电视剧《铁血红安》中“刘铜锣”的形象塑造,明显受到了《亮剑》中“李云龙”的启发。“李云龙”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世俗生活的质感融入到了人物身上,使得乡野之中生长出来的“痞气”与投身民族救亡时的“大义”结合起来,塑造出一个符合普通中国人审美认知的革命者,引起观影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刘铜锣”之所以被誉为“又一个李云龙”,正是因为其实现了鄂东乡土气质与宏大革命场景的有机统一,并在人物的语言行为与性格命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其成为了鄂东革命者群体的典型代表,迎合了现代观众多样化、个性化的审美趋向。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刘铜锣是红安地区的革命符号,被剧作家准确抓住了。”[2]面对这位“敲着铜锣打冲锋、光着膀子拼刺刀”,从占山为王到下山革命,最后成长为开国将军的人物,观影者(尤其本土民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他们与革命者有着同样的乡土生活经验。相较而言,在《夜袭》《旋风司令》《惊沙》《王树声征战豫西》《胡奇才痛歼千里驹》等以鄂东革命者为对象的影视作品中,表现的大多是主人公离开鄂东后的斗争经历,其地域性格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展现,观众甚至难以从作品中识别其真实的地域身份。
我们将《铁血红安》视为“黄冈出品”中本土革命题材的代表性作品,正是源于其在人物塑造中表现出来的独特个性,它使得“乡土鄂东”与“民族情怀”有了交互融合的鲜活载体——即主人公“刘铜锣”。《铁血红安》中,另一位人物“李坪山”既是老师又是红军师长,尽管他集满口“子曰”、喜欢引经据典的“夫子”与战场上的指挥者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于一身,在鄂东文化语境中却并不显得突兀。在这一人物身上,人们依稀看到了“木匠司令”“放牛娃团长”“私塾先生党代表”的影子。同样以黄麻起义为背景的电视剧《红槐花》,由本土作家何存中的文学作品《门前一棵槐》改编,故事地点设定在“麻安县”,男主人公“程牛儿”原本就是大别山中一个猎户,以“牛儿”为名的原因是山里人觉得“贱名好养活”。他爱恨分明,敢于挣脱民间习俗与宗族势力的束缚,唱着“高高山上一棵槐”的鄂东民歌抢亲,后参加革命并成长为一名有勇有谋的红军指挥员,及至成为开国将领。在何存中另一部长篇小说《太阳最红》中,主人公“王幼勇”的“敌人”就是自己的亲舅舅,使他不得不深陷于家族情感与革命理想的纠结,最终在取义成仁中获得升华。由此可见,鄂东地域影视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有其内在“惯性”,创作者始终力图在“乡土”与“革命”的冲突之中寻求调和之策,为观众(读者)展示一个独一无二的鄂东革命者形象,如“李云龙”一般鲜活。正如本土作家何存中所言,他笔下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个人都向往光明,只是信念不同”[3]。
在以往的革命题材作品中,创作者往往更加倾向于塑造宏大的历史场景与“高大全”式的人物,以满足观众寻找英雄、战胜敌人的心理期待。这一倾向,在文学创作中早就有所显现,“中国文学久来热衷于向历史邀宠,寄希望于历史的参与而使作品伟岸光亮流芳百世,特别是大历史,越大越好。这几乎已成一种病,一种追求向往的不病之病;也可说,这是一种自宫,是中国文学把‘历史’当切刀对自己的文学细胞、文学生长力进行的‘阉割’”[4]。正因为如此,磨灭了许多革命文艺作品应有的“人性”光芒,其人物难免千人一面。鄂东革命者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是因为他们身上天然交融的“乡土气质”与“革命情怀”,这两大性质完全不同元素一旦碰撞到了一起,就会催化出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的艺术形象。如同《铁血红安》与《红安兵谣》的编剧夏启发所说,刘铜锣除了是将军们的缩影,更是红安当地民风的缩影,“他代表了红安人的共同属性:执着、拼搏”[5]。在他们身上,鄂东生活的经验已然融入了其革命行为与精神之中,铜锣、布鞋乃至于红苕都不再只是“身外之物”,而变成了人物生存环境、成长历程以及革命意志的象征物,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显示出特有的符号价值。对于现代观众而言,这种立体化的人物塑造方法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也更能体现地域性格对个体所产生的“规约”——使得观众在影像空间中能够清晰地分辨出“鄂东人物”。
二、在文献史料与民间传奇的平衡中塑造“历史人物”
鄂东既是“红色圣地”,亦是“名人之都”。相对于鄂东革命者有史可循、较为清晰的形象,包括苏东坡、李时珍、毕昇、邢绣娘以及禅宗祖师在内的历史名人,大多并无确切的文献记载可供查询,其形象显得模糊而又飘忽。正是因为这一特质,使得鄂东历史人物在文学、戏曲乃至于民间传说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不同时代的“创作者”都可以将自己的情感植入其中,丰富甚至重构符号与故事系统,使经过“加工”与“再造”的人物更加符合特定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标准。这里所谓的“创作者”,既包括专业的文学作家与戏曲表演家,更包含无数生活在各个时代的本土民众,他们的创造活动赋予了鄂东历史人物以新的生命。沿着这一路径观察现代鄂东影视生产,其中大量历史人物题材作品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本土生活与艺术实践在新的媒体语境中的延续,其生成的内容产品更加适应“读图时代”文化消费的需求。审视鄂东历史人物题材影视作品,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多元化主体介入带来的影响:影像化呈现出来的“鄂东人物”,在其活动轨迹、主要贡献以及命运归宿等大体上遵循有限的文献记载,而在生活场景、社会关系、经典故事等层面,则更多地取材于民间传说。这一人物塑造策略,既展示出对历史事实尤其是人物历史定位的尊重,也获得了生动、鲜活的故事素材,符合大众的审美期待。
对于鄂东人物的文献记录,主要包括正史、地方志以及家族族谱等。囿于文献史料的体裁形式及表达方式,其内容大多是梗概式的,一般以纪年的形式呈现人物的生辰、经历与归宿,缺少故事与场景等细节。其中,与李时珍有关的记载,主要见于《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七》与《进〈本草纲目〉疏》之中,前者内容为概述其出生、治学、成书、去世,后者主要讲其子进献《本草纲目》的原因并颂扬父亲著述的艰辛过程,均十分简略。对于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的记载更为简略,仅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书中称毕昇为“布衣”,且只用了274字描述了活版印刷的流程,而对其籍贯、生平等并没有介绍;1990年英山县五桂村毕家坳发现一块刻有“毕昇神主”的宋代墓碑,经专家鉴定认定为毕昇墓,可为其籍贯、生平的佐证。至于黄梅戏“一代宗师”邢绣娘,目前所见除了地方志、家族族谱对其个人经历有一些记载之外,其他主要是流传下来的戏曲文本。禅宗开创者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其个人经历与思想主张则主要见于佛教典籍;基于宗教传播的需要,这些记载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并不都是史实。
相较于史料记载的单调与简略,民间传说的内容显得更为丰富:不同时代的民间讲述者将其情感、理想与期待投射到了特定鄂东人物身上,衍生出了结构完整且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系统,为职业作家与现代影视生产者提供了极佳的再创作资源。鉴于人物形象与故事线索的复杂性,鄂东历史人物题材多以长篇电视剧的形式价值呈现,其中包括已经播出的《黄梅戏宗师传奇》《大明医圣李时珍》和完成剧本创作的《禅宗》《毕昇传奇》,篇幅均较为宏大。《黄梅戏宗师传奇》中,邢绣娘经历爱情、逃荒、斗恶霸、告御状、收徒传戏直至被御赐“黄梅名伶”,成就一代宗师;《毕昇传奇》中,毕昇受到同门的刁难与陷害,被官府威胁、逼迫,却始终不忘初心与使命,最终被封为“大宋活字神”;《大明医圣李时珍》中,亦加入了情感纠葛、正邪斗争以及宫廷较量等内容,以塑造一个义勇双全的“大明医圣”形象;《禅宗》剧本以人物为主线分为《禅宗四祖》《禅宗五祖》《禅宗六祖》三部,分别讲述道信、弘忍、惠能三人的故事,其主要内容来自文史资料、佛教典籍以及民间传说。这些本土影视作品在故事建构以及人物形象塑造上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创作者在不违背宏观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明显引用与吸收了大量民间叙事的成果,塑造了一个可感知的影像化“鄂东人物”,更新了人们即有的认知。
对于文学、戏曲与现代影视创作来说,片段式或者纪年式的文献记载虽然不足以直接转化成为艺术产品,但其对鄂东人物本土身份及历史地位却产生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感,使得李时珍、毕昇、邢绣娘与禅宗祖师成了最为显著的地域符号,能够跨越时空的局限反复出现在不同时代的文艺产品之中,获得不断拓展、衍生与更新的机会。不论故事系统如何演绎,历史文献中呈现的内容依然是其源头与根本,在叙事系统中发挥着“稳定剂”的作用,民间传说的演绎同样必须遵循其所设定的历史语境,不至于产生大的偏离。与文献记载的客观性与粗线条相比,民间话语系统中的鄂东人物则显得丰满、生动得多,更加适合进行艺术化再创造。与文献记载赋予的确定性与权威性相比,民间传说中的鄂东人物则能够为大众带来一种独特的神秘感与亲近感,更加符合其心目之中的“理想状态”。在影视传播过程中,这种基于文献记载与民间演绎基础上的艺术形象再创造,既可以使观众在历史语境之中产生一种明确的真实感,又能够让其在民间视角与生活场景之中形成强烈的代入感;“真实感”与“代入感”的融合,无疑有利于鄂东人物的接受与认同。当然,艺术创作虽然强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对于地域身份与历史定位已经十分明确的人物而言,关键还在于掌握演绎的限度与边界;一旦为了追求娱乐化效果而出现“过度创作”的现象,将会损害历史人物的整体观感与社会认同。
三、在现实时空与人文传统的交汇中建构“现代人物”
鄂东本土影视作品中的现代人物形象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城高考》《梦行者》《守护童年》《不愿沉默的知了》《马兰花开》等作品中虚构的人物,另一类是《西河十八湾》《英雄无悔》中以当地先进个体为原型的写实性人物。前者虽然大多在鄂东地区各县市拍摄制作,但人物身上的时代标签十分明显:《全城高考》中面临人生抉择的青少年学生、《守护童年》中替罪犯子女寻亲的女志愿者、《梦行者》中三个回乡创业的本地青年、《不愿沉默的知了》中通过个人奋斗走出大山的男主人公、《马兰花开》中的共产党员选调生马兰等,无一不是当前时代中某个特定群体的缩影,其形象意涵显然已经超越了地域与个体的层面。在《全城高考》这部典型的“黄冈出品”中,创作者将“高考故事”设置在了有着“教育名城”之誉的黄冈,并将一系列鄂东经典景观符号呈现在影像空间中,试图借此强化观影者对“高考神话”发生地的感知印象。应该来说,将师生群体置于“黄冈”这个独特人文环境中,的确使其获得了较为鲜明的地域身份,同时也使“高考”主题具有了特定的意义指向,更易于被观众所理解与接受。在这一具体语境中,黄州古城、黄冈中学、东坡赤壁等本土经典景观所承载的鄂东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制度之间产生交汇碰撞,为解读师生群体提供了一个多维、立体的视角。由此建构的影视人物,其语言、行为、心理等已然超越了纯粹地域的局限,成为时代背景中某个群体的缩影。
基于主流价值传播的需要,《西河十八湾》《英雄无悔》等本土电影中的主人公均以现实人物为原型,具有一定的纪实色彩。《西河十八湾》以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为原型,《英雄无悔》则以浠水民警“扑爆哥”吴俊为原型,主要讲述他们的典型事迹。这种以先进典型为原型的人物塑造模式,符合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基本创作导向。由于这些人物先期已经通过媒体报道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其形象与故事相对确定,艺术化再创造的空间比较有限。在具体艺术实践中,创作者往往通过本土化的场景设置,尤其是经典景观、建筑以及器物的影像化再现来标识人物地域身份;与此同时,在不损害人物形象以及典型意义的基础上,围绕典型人物的行动轨迹创设必要的矛盾冲突,为其形象与精神的双重建构提供支撑,借此增强人物的可信度与感染力,使他们作为主流价值观践行者与弘扬者的功能得到强化。从宏观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些典型人物更多地被视为时代发展的产物,创作者更期待观众能够从他们身上看到特定社会群体的共同属性,以此实现价值引领目的。或者说,时代背景的强化使得这些鄂东典型人物具有了更为普遍的示范作用,其地域身份则附着于其上、融合于其间,为其真实性提供支撑。与《全城高考》中虚构的人物一样,经过艺术创造的典型人物同样获得了超越个体与地域界限的能力,成为特定时代的一面镜子。
影视作品对现代鄂东人物典型意义的强调,与地域生活的变迁不无关系。在媒体技术变革的推动下,人们的交往范围、交往对象以及交往方式发生显著变革,传统意义上以民族和地域为边界的文化认知亦随之迁移,全球化、大众化使不同民族与地域拥有了相对接近的审美标准,重塑了文化生产与消费格局。在这一宏观背景下,“鄂东”这个原本十分确定的生活空间概念逐渐被消解,其所指向的地域文化边界也日渐模糊,场域中心地位被具有极强扩散能力的大众文化所占据。地域文化的边缘化,使其在本土社会生活中的规约功能与导向价值大大降低,直接表现就是社会成员身份标签的淡化。正因为如此,较之于红色革命者与历史名人鲜明的地域身份,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中鄂东人物表现出来的“共性”明显强于“本土性”;即便许多作品在场景的设计上尽力突显“鄂东色调”,但其人物的“鄂东身份”仍然无法像“刘铜锣”“邢绣娘”那样鲜明。再者,基于主流价值导向的既定要求,创作者更多地关注主要人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典型价值和普遍性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其身上的本土化特质。理性而言,“鄂东人物”一旦无法承载地域性格,其身份辨识度将大为降低,文化传播价值必然受到限制。将鄂东文化的基因有效融入影视人物之上,是当前现实主义题材“黄冈出品”面临的核心挑战。
地域语境中的影视艺术生产,必须依托本土优势文化资源。鄂东文化系统中,最为显著与丰富的资源就是“人”——生活于各个时代的“鄂东人物”,构成本土影视创作的“原材料”与“原动力”。在鄂东历史时空中,虽然早期革命者、文化名人以及现代鄂东人物出场的背景各有不同,但创作者对他们本土身份突出与强调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这也使得人物身上具有了某些共通的元素,易于识别。与其说这是影视创作者的“审美惯性”所致,不如说是鄂东文化符号形式与精神内容内在建构的结果。对于观赏者而言,唯有回到鄂东生活场景之中才能真正与创作者进行“对话”,也才能确切地解读本土影视人物的性格、行为特征及其命运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