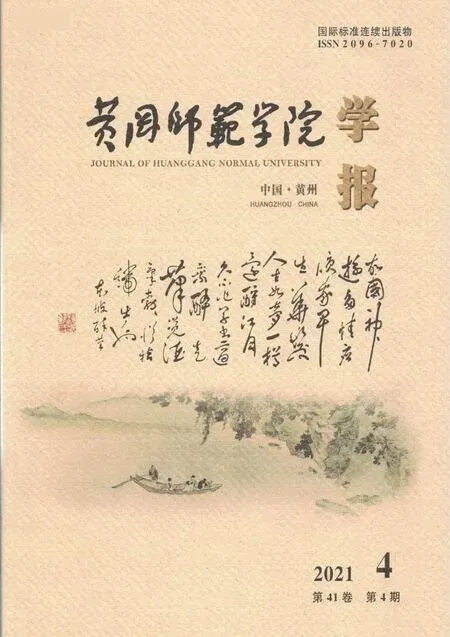李煜亡国哀思抒写策略
——兼论李后主词对词境开拓和词格提升的意义
潘志刚,张文华
(1.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0;2.武汉学院 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212)
李煜作为亡国之君,降宋后,他该如何排遣家破国亡之痛,甚至是夺妻之恨?①李煜是一位艺术天才,诗、书、画、律,无不精通,似乎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方式,但前提是,借助这些方式来抒发这种情感不会招致灾祸,因为在李煜进入汴京之前就有后蜀末帝孟昶这一前车之鉴。以李煜的聪明才智,他会选择一种稳妥、安全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怨恨,否则就会有性命之虞。从李煜所遗存的材料来看,他更青睐于用文字来表达,他选择了一种宋以来发展蔚为大观的文体:词。李煜好词,这是李煜的一个特点。不过吊诡的是,他竟然在词中赤裸裸地表达着亡国之哀和故国之思,情感非常饱满,几乎是在控诉着宋朝灭掉南唐国的悲痛②。李煜的这种行为让人非常疑惑:他为什么这么大胆,难道他没有考虑到因此而可能带来的文字之祸吗?又或者,李煜这样做是别有原因?有关李煜的研究论作繁多,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就这个问题所作的探讨并不能让人信服。笔者不揣谫陋,试通过考察词体在当时的文化生态环境来说明李煜这种“异常”行为,推进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词格卑微:词体在五代、北宋初期的文化生态环境
“诗言志”“文以载道”,在中国古代,诗、文一直都是正统文学样式,地位很高,受人重视,五代、北宋初期也不例外。在诗文中表达观点,稍微不慎就会落人以把柄。相较而言,词在五代、北宋初属于“小道”“艳科”,遭到人们的轻视和鄙弃,难登大雅之堂,可以让人轻松地表达私情和小感。
词体在当时如此低下的地位,与词这种文体所写的内容有很大关系。在五代、北宋初,词一般不写家国壮志、事业功绩等光明正大的题材,大多写生活琐事及具有私密性和低俗性的内容,一般也不会告诉他人。谢章铤《与黄子寿论词书》认为,“词之兴也,大抵由于尊前惜别、花底谈心,情事率多亵。”[1]词乃是宴饮嬉笑的产物,承载的内容与风花雪月有关,甚至有亵渎的意味。五代时期,后蜀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云:“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2]作为词集鼻祖,《花间集》收录的五百首词绝大多数描绘的是春风花月、宴会饮酒、男女欢爱情等一类的内容,传递的是人情中较为阴柔的一面,与《诗》的“诗无邪”形成对立面。彼时的词体作,难以和“言志”“载道”的诗文相比。由于词一开始就没有关涉宏大主旨的题材,导致词作在五代、北宋建国之初,难以进入大雅之堂。
词体地位的低下与词在当时所发挥的功能也有很大的关系。五代、北宋建国之初,人们多用词来娱乐助兴,作为酒席的催化剂,在正规场合并不适宜“露面”。北宋初陈世修的《阳春集序》有云:“公(冯延巳)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3]冯延巳是南唐宰相,他创作词的最大的目的是“娱宾遣兴”,以助宴会欢乐之情。而上面所举的《花间集序》,说的也是这种情况。人们一般在较为随意性或者私下场合作词,写完后基本也不在公共正式场合公开。如果这种小词一旦在正规场合公布于众,作词人的人格就会受到侮辱。据《南唐近事》记载:“(北宋)陶榖学士奉使,恃上国势,下视江左,辞色毅然不可犯。韩熙载命妓秦弱兰诈为驿卒女,每日蔽衣持帚扫地。陶悦之与狎,因赠一词名《风光好》云:‘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再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明日,后主(当为中主)设宴,陶辞色如前,乃命弱兰歌此词劝酒。陶大沮,即日北归。”③陶榖的这首《风光好》写的是儿女私情,展现的是陶氏的真情实意。其词和现在所见的“云雨词”相比,并没有表现出艳情和露骨的一面。这种含而不露的方式可以说是将私情演绎得恰到好处。尽管如此,这样的词仍然不能、也不好公之于众。《词林纪事》认为这是陶榖出使吴越时的事情,妓女名字为任杜娘,并非秦弱兰[4]。虽然记载的本事有出入,然而不论此事究竟发生在南唐国或是吴越国、歌妓到底是谁,都表明一个现实:词在当时的地位极其低下。正因为如此,南唐国主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来羞辱陶榖,从效果来看,南唐国主似乎顺利地达到了目的。
五代时期,不仅南唐人(南人)轻视词,将词作为调笑品,北方人也同样如此,整个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对词都持以轻贱的态度。和凝当上后晋宰相后,赶紧销毁他散布出去的词作。其目的在于消除之前的低俗形象,维护他当时正大光辉的人格。对于和凝这种亡羊补牢的措施,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依然严厉地批评道:“(和凝)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5]必须指出的是,和凝所作的词并非都是艳词。但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词因其出身,就等于是艳词。故作词绝不会增益作者的道德人品,相反,若与词发生关系,则非常有损于个人的品格和身份。五代时期,词体地位之卑微可想而知。
北宋初期,词体的地位与五代时期并无不同。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晏殊宴饮之后,“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6]。晏殊出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历经宋真宗、宋仁宗二朝,身居宰相之位,是北宋初期最具代表性的士大夫词人。然而在其眼中,词是宴会助兴的技艺,用来“娱宾遣兴”的,这一点和此体之兴一脉相承。又如稍后的文学大家欧阳修,在其《归田录》中记载了钱惟演(977年—1034年)的一则故事:钱惟演声称他自己“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欲阅小辞(词)”[7]。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的第七子,入宋后官至枢密使。钱惟演其他阅读时间看经史、看小说,而如厕的时候才看词,这说明他把词作放在污秽之地。而在这种绝对私人的环境下,也就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在看小词这种书。钱氏这种类似“见不得人”的行为令人莞尔。而透过钱惟演对经史、小说、词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北宋初期人们对文体的尊卑观念,即词的品格卑微低贱,居于末流小说的末流。纵观当时词体的文化生态环境,正如祁志祥所认为的那样,“婉约词以表现诗不屑表现的儿女艳情或羁旅之情为主,以娱宾遣兴为功能,与道德教化无关,因而,五代两宋时期多视词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卑下诗体,称之为‘小道’、‘诗余’。”[8]五代、北宋初,婉约词是主体,而豪放词,或者说境界转向豪放一派的词则是从李煜词作开始。
总之,五代、北宋初,词在当时的地位相当卑微低下,词作不可能成为大宋朝堂上构陷他人的罪证。如果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宋人要借李后主表达亡国哀思的词来作为杀害李煜的证据,对此,后果是得不偿失的。首先,词体品格实在太卑贱,正统人士避之而不及,一国之君又怎会把它当作正经之事,而且还是在朝堂上煞有其事、冠冕堂皇地用词作来作为证据④。其次,如果堂堂的大宋朝皇帝,用品格卑微的词来定一个俘虏的罪名,颇显得浮浪,只会有辱他的声誉与地位,贻笑大方。这不是想一统天下的宋人所愿的。最后,如果确实要借文字之口来杀人,赵宋皇帝的理由太多了。我们现在所见以及所闻的有关李煜之死与其词的关系是后人建构的,李煜之死与其词并无直接因果联系[9]。李煜用词来表达亡国哀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通过考察李煜的选择,我们认识到李煜有着自己的考量。
二、“暗渡陈仓”:李煜以词言“志”的抉择
李煜应该考虑过在诗或文中用含蓄、隐晦的手法来表达其心中的痛苦,然而当时人们对诗文、词持有的天壤之别的态度,怕死而且也不想死的李煜绝不会以身试险⑤。李煜对不同文学体裁的地位和功能有着深刻的认知,只有在词中,他知道才可以放心、大胆、自由地表达其心中的情感。
在五代、北宋初期,诗是一如既往地以正统地位示人耳目,在正式的场合中,人们通常用诗来进行交往。据《南唐书注》记载:“《宋史》曰:‘魏丕字齐物,相州人。南唐国后卒。谴丕充吊祭使,且使观其意趣,后主邀丕等昇元阁赋诗,有“朝宗海浪拱星辰”句以讽动之。’”[10]李煜偏好词,但李煜在这样的场合下并没有请魏丕赋词,这说明李煜清楚诗、词之别。诗体地位崇高,在两国正规交会的场合下,只有请魏丕赋诗才是符合礼仪规范的。
在当时,诗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入正式场合而词却不能;诗可以作为批评工具,这种功能也是词所没有的。据马令《南唐书》卷六《女宪传》记载:小周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后主乐府词有“钗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之类,多传于外。至纳后,乃成礼而已。翌日,大宴群臣,韩熙载以下皆为诗以讽焉[11]。李煜创作的有关小周后的词流出宫外,臣子们纷纷认为李煜这种行为与皇家身份不宜。等到李煜迎娶词作中的主角小周后入宫,臣子们便集体发难。不仅韩熙载赋诗批评李煜,作为文臣元老的徐铉甚至用一首律诗和三首绝句来讽谏李煜[12]。可见赋诗讽谏在当时是大臣们表达意见的一种认真而严肃的方式。当然,传闻有南唐有乐师杨飞花,曾在给中主李璟作乐时,趁机作词劝导李璟[13]。考虑到当时的场合充满娱乐性,以杨飞花伶人的身份,用小词来劝谏李璟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大家都不会去较真。而真正要显示批评的严肃性,则非诗莫属。毫无疑问,诗与词在地位和功能上天差地别。南唐群臣对诗、词的态度代表了南唐士大夫对诗、词的普遍认知,李煜对诗、词的认识也应当是这样的。
入宋后,宋帝对李煜在文学方面的试探加深了李煜对诗、词不同地位的认识。据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记载:“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尝因曲燕问‘闻卿在国中好作诗’,因使举其得意者一联。煜沉吟久之。诵其咏扇云:‘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上曰:‘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他日复燕(宴)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14]宋太祖对李煜说“闻卿能诗”,说明宋太祖对李煜及南唐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宋太祖在宴会中命李煜吟诗而非歌词,表明宋人对诗极为重视,究其原因,诗乃“言志”之体,赋诗是宴会正统的交流形式。以李煜之聪慧,他应该意识到这是宋太祖对自己的试探。他“沉吟久之”,用“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一联来搪塞过宋太祖。“他日(宋太祖)复燕(宴)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发明于南北朝。在唐代,翰林学士多为皇帝的御用文人,以诗文辞赋为务⑥,认为翰林学士就是皇帝的御用诗人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宋太祖再次举行宴会,称李煜为翰林学士,则是摸透了李煜之“志”。从宋太祖对李煜之称呼,我们不仅看到赵匡胤对李煜放松了警惕,也读出他对李煜的轻视:李煜只是一个不错的文学之士。宋太祖这看似无意却包含了诸多探视的一问突显了一个问题,即宋朝统治者对诗是极度看重的。如果不是词体地位卑微,难登大雅之堂,以宋太祖对李煜文学习惯的了解,他应当也要试探李煜作词的情况。宋太祖对诗的态度应当给李煜一个警醒,即他可以用词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绝对不可用诗或者文。
事实上,李煜在南唐国破之后曾用诗来抒发过内心的真实情感,只不过不像词那样大胆和直率,请看下面两首诗: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渡中江望石城泣下》)[15]69
残莺何事不知秋,横过幽林尚独游。
老舌百般倾耳听,深黄一点入烟流。
栖迟背世同悲鲁,浏亮如笙碎在缑。
莫更留连好归去,露华凄冷蓼花愁。
——(《秋莺》)[15]60
《渡中江望石城泣下》作于李煜绝别金陵故城之时,此时的李煜尚未体验到入宋后的俘虏待遇和八方笼罩的死亡,故他在诗中真切但又有所含蓄地哭诉亡国哀痛。而到汴梁之后,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使得李煜提心吊胆,李后主再也不能用诗这种文学样式率性地表达自己的心情,而《秋莺》一诗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创作的。这首诗抒发的是后主深沉的亡国哀愁,但他没有直接表达这种情感,而是借秋莺这种欢快的动物所处的自由自在的环境,暗示自己所处的环境危机四伏,含蓄、委婉地传达出内心的痛苦和悲哀。这样的兴比手法着实不易被人琢磨。将上面两首诗对比着看,不难感受到李煜的不自由。
此外我们注意到一则诗本事,说在汴梁的李煜曾偶然地写过表达亡国哀痛的诗句,《诗话总龟》卷三三《诗谶门》记载:
李煜暮岁乘醉书于牖曰:“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醒而见之大悔,不久谢世[16]。
李煜这两句诗赤裸裸地点出了死亡字眼。作者认为如此露骨的诗不是李煜正常状态下的作品,而是李煜醉酒后在放松警惕的情况下写的,而且作者指出李煜神志清醒过来之后就表示后悔不已,且作者又在末尾附上一句“不久谢世”。作者如此安排,颇有意味。我们认为,作者这是想告诉世人,李煜就是因为写了这样两句诗而遭到了不测。虽然无法证明这则本事的真伪,但这表明在五代、北宋初期,诗这种文体非常受人关注,一旦用诗“言志”就有可能触犯禁忌,后果不堪设想。而从李煜“醒而见之大悔”,侧面说明了李煜对诗与词的区别有着清醒的认识:诗是可以堂而皇之地作为构陷他人的罪证,而词或许还未能被人所“瞩目”。
在李煜看来,正因为词体的地位卑贱,用词这一文体来抒写在诗不能言且又不敢言的“志”不仅不为人所重视,反而更受人们的鄙弃,所以李后主才会暗渡陈仓,在词中自由地袒露亡国之恨和故国之思,而且是大胆地表达这种情感: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破阵子》)[17]63
这首词前面用对仗的手法铺陈李煜作为国主时所享有的荣耀和尊严,气势磅礴,大有英雄豪放的气概,显然,这是李煜在夸示他曾经的自豪和骄傲。然而后面一句“一旦归为臣虏”,即转入对现今处境的悲叹。前后对比的巨大落差,只有李后主才知,而读者也能从李煜的对比手法中体会到他满腹的亡国哀痛、愤恨以及无奈。
再如李后主的其它词作,赤裸裸地表达诗之“志”: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17]11
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子夜歌》)[17]17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17]24
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蝶恋花》)[17]28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17]117
上述词作与《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在气势、风格上迥然有别,一改为怨妇般的哀怜,但意旨浅显,且毫无避讳可言,简直就是在大胆、直白地控诉着亡国之恨和故国之思。
至此,我们认识到一个背负着亡国亡家、有着极大屈辱的李后主是如何在重重的死亡阴影下大胆、自由地表达着心中之志的。而李煜的聪慧也最终让他成为了“暗渡陈仓”的成功者。
此外,笔者还需要强调的是,北宋时期还没有李煜因写词而遭毒手的记述或故事,后来所传李煜因作《虞美人》一词而被毒死的本事,与南宋以来人们推尊词体有关。我们需要辨清历史的真相。其次,北宋一朝文字祸共有47例,由词而引起的文字之祸只有2例,且都发生在北宋晚期[18]。对比北宋诗、文、词各自所引发的文字灾祸可看出文体之间的尊卑差距。北宋初期的统治者鄙视词、排斥词,以致词无缘进入政治视域,柳永奉旨填词就是典型。再者,如果词的地位与诗等同,哪怕有诗一半的地位,词就会受到人们的重视,宋朝统治者就有可能将词作为构陷李煜的罪证,早早地除掉他。如果真是如此,李煜早在南唐国破之际创作《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时就应该被诛杀了,似乎没有理由允许他在入宋后的三年时间里,继续吟唱这些故国、亡国之思的作品。
三、李煜抒写策略的意义:开拓词境的典范
李煜借词这一文学体裁形式不仅抒发了其亡国之恨,也排遣了其心中的悲痛,最重要的是没有授人以把柄,可谓一举两得。这是李煜大胆、机智的表现。李煜的这种行为可以说为后来避免文字祸的宋代文人作了先导。如苏轼因乌台诗案(公元1079年)被贬黄州后,不再用诗来“言志”抒怀,而是开始大量作词,将其“好骂”的脾性从诗转移到词里⑦,这意味着,也将其真正意图从诗文中转移到词作中了。再如北宋南渡大臣李纲在《湖海集序》中说:“余旧喜赋诗,自靖康谪官以避谤,辄不复作。”[19]李纲此后果不写诗,且达两年之久,然而他并未停止作词。可见,北宋一朝文人为避免文学创作而带来的文字灾难,借词来表达心中之“志”,是一个极为不错的选择。而这一切可以追溯到北宋建国初期李后主的有意为之,这也使得李煜成为用词“言志”而开拓了词境的典范。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已有大家专论,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注释:
①宋人王铚《默记》卷下记载:“龙兖《江南录》,有一本删润稍有伦贯者,云:‘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又韩玉汝家有李国主归朝后与金陵旧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有人也指出这是将李煜族人的情况移作李煜,但李煜夫妻所受屈辱应该也不少。参见王铚.默记[M]//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564-4565.
②“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子夜歌》)“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破阵子》)“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参见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M].北京:中华书局,2007:11、17、63、117.
③郑文宝.南唐近事[M]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1.陶榖一事又见于文莹.玉壶清话:卷四[M]//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481.
④柳永因写“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宋仁宗在其卷中御批“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可见宋仁宗把填词看作是不务正业,认为填词贬低了读书人的身份。参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80.
⑤李煜在国破之日倘有死心,不会为俘虏。参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149.
⑥唐代每个时期的翰林学士地位和职责都不完全一样,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文为业,包括诗词创作、批答表疏、制诏,等等。参见杨友庭.唐代翰林学士略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5(3).宋太祖称呼李煜为翰林院学士是强调李煜在文学上的才华,认为其诗歌写得好。
⑦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三首》:“(苏轼)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参见黄庭坚撰,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第2册[M].南昌:江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