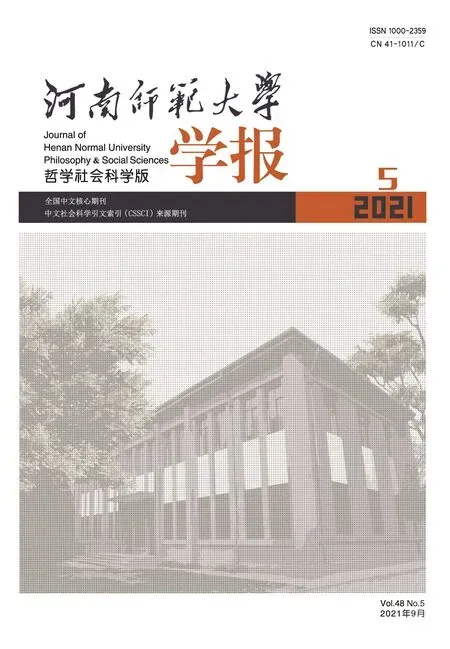东汉思想家赋学批评的文学史意义
——以桓谭、王充与王符为例
冷 卫 国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桓谭、王充、王符是东汉著名的思想家,与马、扬、张、蔡四大赋家不同,后者创立了辞赋文学的范式,前者则以思想家的敏锐发表了对辞赋的评论。桓谭生当西汉东汉之交,王充主要活动于光武、明、章、和四个朝代,王符的生卒年则在和、安之际到桓、灵之间。他们生活的时代基本贯穿了东汉王朝的始终,其思想观念亦彼此应和,有因有革。因此,分析三者的辞赋评论,有助于把握东汉赋学批评的主要脉络和发展轨迹。
一、桓谭:“乐高眇之志”的抒情指向
桓谭(公元前23—公元56年)的一生基本以49岁为界,此前主要活动于西汉成、哀、平及王莽新朝,以后活动于东汉光武时期。桓谭少时好赋,喜欢《离骚》,刘向、扬雄等人的赋。尝云:“谚曰:‘侏儒见一节而长短可知’,孔子言:‘举一隅足以三隅反。’观吾小时二赋,亦足以揆其能否。”(《太平御览》卷四九六)自矜之态,溢于言表。据《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记载“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可见当时尚有赋作传世。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也谈道:“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谕,不及丽文也。”虽然桓谭本人对自己的辞赋极为自负,但刘勰的评价并不高。桓谭赋现存《仙赋》一篇,见于《艺文类聚》卷七八。赋前有序:“余少时为中郎,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郊先置华阴集灵宫。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故名殿为存仙。端门南向山,署曰望仙门。窃有乐高妙之志,即书壁为小赋,以颂美曰。”(1)《北堂书钞》卷一○二文字有异,且较疏误:“余少时为郎,孝威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部先置华阴集灵宫,余户此焉。窃有乐高眇之志,即书壁为小赋。”序中谈到集灵宫,可见此处《仙赋》与刘勰所言《集灵赋》实为一赋。
据陆侃如先生考订,桓谭49岁以后事迹无考,估计已转入了《新论》的写作(2)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第80页。,据《后汉书·桓谭传》记载:“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其生前曾献《新论》一书于光武帝且得到了光武帝的称赞。《新论》反映的是桓谭对“当世行事”的深刻反思,也反映了两汉之际文化思想的新动向。关于此书的内容,据《桓谭传》唐章怀太子注“十二《道赋》”,可以看出桓谭对赋的关注,《道赋》的主要内容,应该是桓谭对辞赋的评论。不过与刘向、刘歆父子奉帝王之命对赋予以叙录与整理不同,桓谭是把赋当作社会文化现象加以考察,这显示了其特有的赋学批评视角。《新论》虽全书已佚,但刘勰《文心雕龙》、严可均所辑《新论》仍存零星材料,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于此可觇测其辞赋批评的意向。
第一,对骚体赋、散体赋的充分肯定。《新论·道赋》曰:“余少时好《离骚》,博观他书,辄欲反学。”(《全后汉文》卷一五)两汉时代虽然对屈原的人格毁誉不一,但对其作品艺术成就的肯定却众口一词。屈原的作品在东汉前期已上升为“经”,桓谭对屈原《离骚》高度认同。对司马相如的骚体赋也给予充分肯定,《文心雕龙·哀吊》引《新论》佚文:“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司马相如《吊二世赋》为骚体赋,桓谭认可其凄恻感人的效果。桓谭与扬雄不同,后者因散体赋“欲讽反劝”“劝而不止”而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反之,他将扬雄的四大赋视为“丽文高论”(《全后汉文》卷一四),承认从刘向、扬雄的辞赋中常常受到启发:“桓君山云:‘予观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文心雕龙·通变》)他认为刘、扬的辞赋兼综“美”“采”。“桓谭称:‘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文心雕龙·定势》)这两个概念与后来刘勰的“丽辞”“情采”两个范畴有着一定的连通性,《文心雕龙》中即有《丽辞》《情采》篇。桓谭认为,当时的辞赋作品只是词藻华美而缺乏情采,内容空疏。但刘、扬的作品不但文辞华美,而且内容充实且富有情采。桓谭对于辞赋的评价,坚持了“美”(丽辞)“采”(情采)统一的原则,与扬雄在重视讽谏这一大前提下评价辞赋的“丽以则”标准有所不同,“美”(丽辞)是对扬雄“丽”的继承,“采”(情采)是对扬雄“则”的突破和深化,在“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之间,扬雄更重前者,显示了复古的倾向,桓谭则对二者无所偏取,肯定了这两种赋的不同风格,相比而言比扬雄更为全面,其非功利的审美色彩亦有所加强。
第二,反对“暴思精苦”,强调“伏习象神”的辞赋创作论。《新论·祛蔽》曰:“予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而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动感发病,弥日瘳。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全后汉文》卷一四)(3)《文选》卷七《甘泉赋》李善注:“善曰:《汉书》曰: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雄少好学,年四十馀,自蜀来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馀,为郎中,给事黄门,卒。桓谭《新论》曰:雄作《甘泉赋》一首,始成,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按:李善注与史实不符,误。不少研究者认为桓谭意在藉此说明从事辞赋创作活动的艰辛。这样理解固无不可,但这段文字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赋需大才,非一般人所能为。桓谭自视甚高,扬雄才学淹博,在他看来,他们作赋尚且如此艰辛,至于其他人则可想而知。其二,隐含着对“暴思精苦”的创作方法的批判。在《祛蔽》这一标目之下凡所言说的事情,桓谭皆将之视为弊病,认为应当革除。这段话的重心在“尽思考,伤精神也”一句,“精神”一词又见于《新论·形神》,“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弘明集》卷五)(4)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弘明集》,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四将该段文字归于《新论·祛蔽》。,桓谭用形象的譬喻说明了形、神之间的关系,表现了其唯物主义见解,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类似道家的“葆真”思想,他认为“暴思精苦”的创作方法必然会伤及形体和精神。这一思想后来亦为刘勰《文心雕龙·养气》所继承。《新论·道赋》又曰:
扬子云攻于赋,王君大习兵器,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曰:‘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全后汉文》卷一五)
如果说,这段话仅仅限于对扬雄《答刘歆书》的征引,尚不足表明他对“伏习象神”的创作方法持肯定态度,联系以下两段文字,其意向已相当显豁:
成少伯工吹竽,见安昌侯、张子夏鼓琴,谓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为知音。”(《全后汉文》卷一五)
及博见多闻,书至万篇,为儒学教授数百千人,祗益不知大体焉。(《全后汉文》卷一三)
以上虽分别就音乐、著述而言,但二者与辞赋的创作方法一脉相通。从摹拟、沉潜开始,强调通过反复揣摹而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从批评史的传统来看,这种观点上承扬雄,中经桓谭的承接而下启刘勰——刘勰接受了桓谭的“知音”概念,“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与桓谭如出一辙。扬雄、桓谭皆谈到过“伏习象神”的问题,这反映出此种看法在汉代的普遍性,也可以解释汉赋何以多有模拟之作这一普遍性的文学现象。
第三,以赋言志。桓谭是无神论者,其《仙赋》却颂美了“出宇宙,与云浮”的神仙生活。不过,他对神仙生活的想象和描写仅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其目的只是为了表现他的“乐高眇之志”。但值得注意的是,赋与“志”在此第一次确立了联系。汉代人接受了“诗言志”(《尚书·尧典》)的观念,以“言志”解诗,但把“言志”限制在“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层面上。从《仙赋》本文可以看出,桓谭与一般汉儒不同,其“言志”带有更多的抒写性灵的倾向,诗以言志,赋亦言志,这从理论上昭示了东汉辞赋重视抒情写怀的主流倾向。班固作《幽通赋》,“以致命遂志”,冯衍径以《显志赋》名篇,都是东汉辞赋重视言志写怀的证明。
应用SPSS18.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实验数据均以 ±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比较t检验,方差齐,用LSD检验;方差不齐,用Dennett’s检验;以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第四,剖析了贾谊、扬雄创作的外因条件。《新论·求辅》云:“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淮南不贵盛富饶,则不能广聘骏士,使著文作书;太史公不掌典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全后汉文》卷一三)蒋凡认为桓谭这段话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环境对于创作主体的影响,桓谭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又有所补充和完善,良好的创作环境照样可以对创作有促进作用(5)蒋凡:《东汉桓谭文艺思想述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1989年第14辑。。但如果转换视角,也可以认为桓谭从个人遭际的角度说明了贾谊作赋、扬雄悔赋的外在因素,这对于今天我们解读二者的赋作仍不失启发意义。
桓谭与扬雄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在其人生历程的前半期,皆爱好并创作过辞赋,在其人生的后半期皆转向了子书的写作。扬雄作《太玄》《法言》,以孟子自命,意欲恢复正统儒学;桓谭作《新论》,以为“何异《春秋》褒贬”(《全后汉文》卷一三),究其实,复古的形式下包含着服务现实、兴利除弊的目的。与扬雄不同的是,桓谭的赋学批评包含着更多的新变因素。他生活在一个由乱趋治的社会,对世界的进化充满信心,不像扬雄对于世界的变化抱着悲观的态度。桓谭认为,“宓牺之制杵臼,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確,而利十倍。杵臼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全后汉文》卷一五),这种今胜于古的颇具进化论色彩的世界观,也是桓谭的文学观念趋向新变的思想基础。
扬雄五十岁以后主要精力投向《太玄》《法言》的撰述,桓谭四十九岁以后则投入《新论》的写作,很少甚至几乎不再作赋,而是“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汉书》卷八七下),扬雄视作赋“颇似俳优”(《汉书》卷八七),桓谭也把辞赋视作“应酬之文”,“茂陵周智、孙胡,不为赋颂酬应之文” (《全后汉文》卷一五),二人重视子书的写作甚于辞赋。在辞赋与子论之间,薄辞赋、厚子论的观念至建安时代依然赓续相传。从东汉初年到汉末建安,其二百年的历史发展说明了这种观念的延续性,预示着辞赋要赢得“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的崇高评价,尚需经历一段相当漫长的历程。
二、王充:“疾虚妄”“归实诚”的文学反思
王充(公元27—97年)一生经历了光武、明、章、和四世,彼时的社会充满着“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气氛。王充高扬 “疾虚妄”的旗帜,提出核“实”求“真”的“实诚”原则。他自言“《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论衡·须颂》)。其“平说”的对象,既包括当时“滑习章句”的学风,亦包括当时的文风。因深受谶纬经学的影响,当时的文章无不沾染上了“虚妄”气息,“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卿寤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天人合应,以发皇明”(《后汉书》卷四〇上)就是典型的例证。因此王充“疾虚妄”“归实诚”的原则存在着双重意义:既是哲学的也是文学的,或者说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文学反思,正因为如此,罗根泽先生评价王充说,“他开辟了‘文学批评’的新纪元”(6)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5页。,这也正是王充文学思想的重要意义。
汉赋是一代之文学,王充也曾创作辞赋,今传世者尚存《果赋》残句:“冬实之杏,春熟之甘(同‘柑’)”(《太平御览》卷九六八)。《论衡》的文本形态也充满着强烈的赋体文学色彩,例如《自纪篇》的问答形式、语言风格,与东方朔《答客难》、班固《答宾戏》、扬雄《解嘲》《解难》等完全是同一路数。
王充宣称: “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杨雄为双,吾荣之。”(《自纪篇》)(7)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205页。他认为孔子、扬雄是立身行世和为文著述的最高典范,其赋学批评亦表现出了依经立义的倾向。《论衡》直接涉及辞赋批评者有多处,且与扬雄的关系密切。
第一,马、扬大赋无补世用。王充认为“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佚文篇》)(8)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869页。,作文的目的乃是“为世用”(《自纪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9)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869页。。他从尚用的角度批判马、扬等人的散体大赋徒具“巨丽”之文、“眇深”之意而无补于世用:“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篇》)(10)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7页。
王充沿袭了扬雄“文丽用寡”的观点。但与扬雄不同的是,王充表现出了以文章品藻人物的倾向,对于散体大赋的“文丽用寡”,《谴告篇》也有一段阐述:“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子云之颂,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然即天之不为他气以谴告人君,反顺人心以非应之,犹二子为赋颂,令两帝惑而不悟也。”(《谴告篇》)(11)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641—642页。赋颂中过分的铺排夸张以及作者不明言自己的讽谏目的、正话反说的话语方式,这种文本结构的不平衡,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前者对后者的遮蔽。在这一点上,王充几乎全盘接受了扬雄的观点。从扬雄到王充,对散体大赋“劝百风一”“曲终奏雅”的批判,显示出汉代赋学批评对这一现象予以反思的普遍性与持久性,也表现出其依经立义的保守性。在今天看来,“文丽用寡”意味着汉赋突破经学的局限,文学完成了从抒情到体物的巨大转变,客观上促成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到来。
第二,对“文必艰深”的严厉批判。王充对以扬雄为代表的“文必艰深”说进行了批评。“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为自己的“文必艰深”说寻找依据。王充的时代,社会上依然流行着“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案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自纪篇》)(12)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5页的观点,实际上也在引导着当时的辞赋创作。王充痛斥“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自纪篇》)(13)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6页。。 “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自纪篇》)“言”“文”是一致的,“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意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自纪篇》)(14)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6—1197页。,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难以卒晓的原因在于时代的久远、空间的疏隔以及语言自身的发展变化,并非因贤圣材力超异而有意为之。他批判自枚、马以降深文周纳、好为艰深之词的辞赋创作风气,这无疑是正确的。而其“言”“文”一致的主张,指出了语言变化与文学创作变化的一致性,客观上成为南朝沈约 “三易说”的理论先导。
第三,要求提高“文”与“文人”的地位。在学术思想上汉代庶几是一个泥古的时代,尚“述”不尚“作”。王充却逆时代潮流而动,明确提出 “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15)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607页。,“文人”的地位仅次于“鸿儒”,而赋家是属于“文人”范围的,他热情称赞马、扬等赋家:“孝武善《子虚》之赋,征司马长卿。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使长卿、桓君山、子云作吏,书所不能盈牍,文所不能成句,则武帝何贪?成帝何欲?故曰:‘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佚文篇》)(16)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864页。“夫禀天地之文,发于胸臆,岂为间作不暇日哉?感伪起妄,源流气烝。管仲相桓公,致于九合;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然而二子之书,篇章数十。长卿、子云,二子之伦也。俱感,故才并;才同,故业钧。”(《书解篇》)(17)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3—1154页。显然,他把司马相如、扬雄抬高到了和管仲、商鞅等人同等的地位。汉代的官方政策,虽然以经学或辞赋为文人敞开了禄利之途,不少士人也由此跻身官场,但对士人来说,真正能够获取高官厚位的工具是经学而绝不是辞赋,赋家不过是皇帝的言语侍从之臣。因此枚皋、东方朔以及扬雄等皆有过自悔类倡的人生感慨。他高倡提升文人地位,“蹂蹈文锦于泥途之中,闻见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当尊,不通类也”(《佚文篇》)(18)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868页。,强调了文人的重要性:“龙无云雨,不能参天,鸿笔之人,国之云雨也。载圆德于传书之上,宣昭名于万世之后,厥高非徒参天也。”(《须颂篇》)(19)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854页。
第四,“臣子当颂”与“赋象屈原、贾生”。东汉光武、章、和时期,社会相对稳定,文化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这种现实背景赋予了王充“臣子当颂”的颂美意识。两汉胜于周的社会进化史观(20)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95页。,又使他热情地称扬了当代文人:
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哉?(《须颂篇》)(21)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855页。
今上至高祖,皆为圣帝矣。观杜抚、班固等所上《汉颂》,颂功德符瑞,汪濊深广,滂沛无量,逾唐、虞,入皇域。(《宣汉篇》)(22)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822页。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案书篇》)(23)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173—1174页。
上引文字说明,第一,王充称扬当代的赋颂誉得其实,认为汉代是超秩三代的盛世。第二,他认为屈原、贾谊的作品是光辉的典范。在其他篇章中,王充对屈原的“俊杰之材”与“香洁之辞”进行了全面肯定(24)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00页。。王充在此又重申了屈原赋及贾谊赋的典范意义。继刘安、司马迁对屈原作品予以“与日月争光可也”的评价之后,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应和着历史的进程,即将取代以描写为主的散体赋的地位而成为赋体文学发展的主流。
三、王符:“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的过渡特征
王符(约公元82—约167年)生卒年约在和、安之际到桓、灵之间。《潜夫论》的内容是“指讦时短,讨擿物情”(范晔《后汉书》卷四九),闪烁着思想家的光辉。《潜夫论》语言整齐,文气灌注,有不少段落就是典型的赋体,如《浮侈》揭露洛阳贵戚生活奢侈浮华的一段,亦具有浓厚的赋体特点。《潜夫论》论赋,虽是偶尔涉及,但他以思想家的敏锐深邃触及了辞赋创作存在的弊端,提出了“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的命题。
夫教训者,所以遂道术而崇德义也。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惑蒙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务本》)
两汉时代的辞赋创作沾染着灾异祥瑞的内容,尤以光武以来此种现象愈演愈烈,无论是大臣奏疏还是辞赋创作往往征引谶纬推阐因果,“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殆即指此。在他看来,这是“开乱危之原”,“乱道之渐来也”(《务本》)。王符的思想与王充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王充曾提出过“疾虚妄”的文学观,王符也反对“长不诚之言”的迷信虚妄,“高论而相欺,不若忠论而诚实”(《实贡》),在主张实诚这一点上完全沿袭了王充的看法。不仅如此,王符比王充更进一步,提出了“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的命题,要求辞赋发挥激浊扬清的社会作用。一个“泄”字,强调的正是创作情感的自发自在、自然自觉的真诚流露。
殇、安、桓、灵之世,社会黑暗,外戚、宦官交相擅权,汉家王朝倾危旦夕,一般士人处于生命的飘扬失落之中,以蔡邕、赵壹、崔琦为代表的文人辞赋创作反映的正是这种格调与倾向。蔡邕《述行赋》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不公,“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赵壹《刺世疾邪赋》指斥了统治阶级的无耻贪婪,“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崔琦则以赋讥刺权贵,据《后汉书·文苑传》记载:
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琦以言不从,失意,复作《白鹄赋》以为风。梁冀见之,呼琦问曰:“百官外内,各有司存,天下云云,岂独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过乎?”琦对曰:“昔管仲相齐,乐闻机谏之言;萧何佐汉,乃设书过之吏。今将军累世台辅,任齐伊公,而德政未闻,黎元涂炭;不能结纳贞良,以救祸败,反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将使玄黄改色,马鹿易形乎?”冀无以对,因遣琦归。
即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也要惩恶扬善,这正是敢于正视现实的人生情怀。“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赵壹《刺世疾邪赋》),也正是这一时期秉承传统礼义观念的辞赋作家的人生宣言。
毫无疑问,王符抨击的是“托之经义”的谶纬魔道,倾慕的乃是托之经典的先王圣道,这是《潜夫论》的核心。王符论赋围绕这一核心,所谓“善丑之德”“哀乐之情”,当然仍限制在风教的范围之内。他崇尚的依然是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这反映出其思想的局限性。不过,《潜夫论》毕竟不是石渠阁、白虎观里的经院学术,也不是充满经院气息的高头讲章,他以一个思想家的敏感准确把握到了辞赋发展的脉搏,“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既是对这一时期辞赋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暗示了关注现实人生的抒情传统再度确立。所以,王符论赋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且体现在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风教与性情。前者来源于儒家思想和王充的文学观念,后者则显示出了重视性情的文学指向。王符这一观念的重要意义正在于直接开启了建安文学慷慨通脱的时代精神。
东汉既是经学盛行也是谶纬张皇的时代,桓谭、王充与王符的思想具有儒、道、法杂糅并存的特征,他们的著作表达了对当世行事的关切以及对谶纬风气的激烈批判。在思想观念上,桓谭接受了扬雄的影响。而王充在《论衡》书中更是多次称颂桓谭:“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定贤》)甚至直接把桓谭称为“素丞相”,“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定贤》)。就写作的出发点和指向来说,《新论》《论衡》《潜夫论》一脉相承,批判谶纬的虚妄,意在论定是非,为世间立法,正是三者的共同特征。
如上所论,深受时代风气的熏染,桓谭、王充皆进行过辞赋创作;王符尽管无赋作传世,但《潜夫论》具有明显的赋体文学色彩,《新论》《论衡》在文体形态上亦无不如此。以上三部著作本为子书,以议论说理为主,但其文本形态上的赋体色彩,正说明辞赋对东汉文章发生的潜在影响。
综上所述,扬雄的赋学批评是桓谭、王充、王符的共同源头,而屈原、贾谊、刘向、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已经走上经典化的道路,并逐渐确立起垂范后世的文学谱系。“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纲领,与西汉相比,东汉的赋学批评已发生潜滋暗转,即“赋言志”的理论趋向已经确立,意味着辞赋从西汉的体物走向东汉的抒情,这反映了东汉赋学批评的基本脉络,也体现了东汉思想家赋学批评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