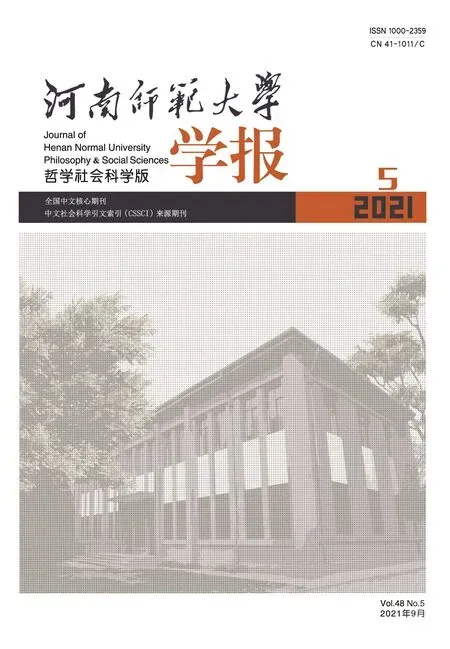戴震的训诂学思想对皖派朴学的引领
徐 玲 英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学报编辑部,安徽 合肥 230039)
清代考据学之鼎盛可与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提并论,梁启超称此四者“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清代考据学以其质朴的学风而被名为清代朴学。清代朴学分吴、皖两派而以皖派为盛。皖派朴学发轫于明末清初的黄生、江永。他们一改宋明空谈陋习,主张由音韵、训诂以求义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严以考据的治学方法的确立,标志着皖派朴学的形成。然而,真正使皖派朴学发扬光大的是戴震。戴震避仇入都,学者或信服而交友之,如王鸣盛、纪昀、朱筠等;或师侍之,如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等;或私淑之,如凌廷堪、焦循、阮元等。特别是在戴震弟子王念孙、段玉裁等的标杆性专著如《广雅疏证》《说文解字注》等的影响下,以校勘为训诂前提、因声以求义以及贯通群籍、择善而从的训诂思想成为皖派朴学的最大特色。皖派朴学突破了地域限制,终成有清一代显赫的学派。然而,戴震的草创之功被其弟子的辉煌成就所淹没,学界鲜有关注,本文以训诂学为例,结合戴震弟子的言论与专著,论析戴震训诂学思想对皖派朴学的引领。
一、以校勘为训诂前提的思想对皖派朴学的影响
戴震明确表示训诂当以校勘为前提,因为“自有书契以来,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隶,字画俯仰,浸失本真”(2)戴震:《与王内翰凤喈书》,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278页。。字体的屡次变化、传抄的颠倒讹脱,使得精准的训诂也难求经典原义。加上小学费失,即使如《说文》《尔雅》等字书、韵书亦不足为据。所以戴震指出,训诂之始应校订讹谬。由于戴震少年时期就精研《说文解字》,又取《尔雅》及汉儒传、注、笺之存者,参伍考究,打下了坚实的小学功底,加之戴震精通古音,故其能将文字、音韵知识运用于古籍校勘,发现典籍讹误。例如《诗经》:“维天之命,假以溢我。”《传》曰:“溢,慎。”《笺》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饶衍与我。”戴震于《毛郑诗考正》中指出,《春秋传》引诗作“何以恤我”,转写讹失耳。《毛传》本《尔雅》释“溢”为“慎”,但《尔雅》本误。戴震指出:“《说文》:‘谧,无声也。’《史记》‘惟刑之静哉’,徐广曰:‘今文云“惟刑之谧哉”。’”“谧”有静义。“溢”“恤”皆为“谧”字形体转写讹误。最后戴震总结道:“书之‘谧刑’谓‘慎刑’,伏生《今文尚书》足据。此诗承上文王之德之纯而言。嘉以慎我,我其取之,思取法文王嘉美之纯德,以敬慎也。”至此,戴震不禁感慨“古经难治类若是矣”(3)戴震:《毛郑诗考正》,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1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655-656页。。
段玉裁二十九岁便师从戴震,深得戴震训诂必先是正文字的思想,尝云:“东原师云:‘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辞生训也。其一,守讹传缪也。缘辞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缪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如孔氏‘虞痒在国西郊’,所谓所据之经非其本经也,而缘之立说,则所释之义非其本义矣。经文之不误者,尚惧缘辞生训,所释非其本义,况守讹传缪之经耶?”所释之经有误,释者守讹传谬,自然谬以千里,所以训诂的前提是校勘文本。段玉裁进一步将其师戴震的校勘实践理论化,将校勘分为订底本之是非和订立说之是非,云:“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4)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经韵楼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7、333-336页。
《说文解字注》是段玉裁的代表作。王念孙于书序中誉其为“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段玉裁于许氏之书,除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外,首先校订《说文》讹误,作《汲古阁说文订》。他于《序》中云:“今合始‘一’终‘亥’四宋本,及宋刊、明刊两《五音韵谱》,及《集韵》《类篇》称引铉本者,以校毛氏节次剜改之铉本,详记其驳异之处,所以存铉本之真面目,使学者家有真铉本而已矣。”(5)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序》,《经韵楼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73页。明末汲古阁本历经五次剜改,《说文》已大失原貌。为还许慎、徐铉《说文》原貌,扫除覆盖于《说文》上的历史尘埃,段玉裁利用形义互求、综贯群书和因声求义等方法,校订《说文》讹误。例如《说文解字》:“读,籀书也。”段注曰:“籀各本作‘诵’,此浅人改也,今正。《竹部》曰:‘籀,读书也。’读与籀叠韵而互训。《庸风》传曰:‘读,抽也。’《方言》曰:‘抽,读也。’盖籀、抽古通用。《史记》:‘纟由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字亦作纟由。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故卜筮之辞曰籀,谓抽绎《易》义而为之也。”(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62页。后人看来“读”和“籀”二者并非叠韵,所以浅识之人改“籀”为“诵”。段玉裁考证古音,指出“读”和“籀”二者叠韵而互训。他再从字义角度指出,“读”有抽绎、梳理意义以至无穷的意思。“籀”为卜筮之辞,作用就是理卜筮现象之端绪,由卜筮现象演绎出结论。段玉裁从字音、字义两个角度考证了“籀各本作诵”之误。此外,段玉裁还校订许慎立说之误,例如:“参,商星也。”段注曰:“商,当作‘晋’,许氏记忆之误也。《左传》:‘子产曰:后帝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叔虞,故参为晋星。’依此则商当为晋明矣。”(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548页。段氏以《左传》的记载订正许慎立说之非。校订《说文》传抄、妄改之误,还许慎、徐铉《说文》原貌,就是不诬古人;校订《说文》立说之误,就是不误今人。
除段玉裁以外,王念孙亦承戴震过庭之训。王念孙为吏部尚书王安国之子。王安国于1756年延请戴震馆于其家,令王念孙从其学。阮元曰:“戴东原先生当代硕儒也,文肃延为公师。……初从东原戴氏受声音、文字、训诂,遂通《尔雅》《说文》,皆有撰述矣。继而余姚邵学士晋涵为《尔雅疏》,金坛段进士玉裁为《说文注》,先生遂不再为之,综其经学,纳入《广雅》,撰《广雅疏证》二十三卷。”(8)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铭》,《研经室续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72页。王念孙《广雅疏证》在训诂学上的成就无与伦比,梁启超赞其曰:“《广雅》原书虽尚佳,还不算第一流作品。自《疏证》出,张稚让倒可以附王石臞的骥尾而不朽了。”(9)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页。
王念孙疏证《广雅》,首先校订张揖和先儒失误。《广雅疏证序》中称:“其或张君误采,博考以证其失;先儒误说,参酌以悟其非。……是书之讹脱久矣,今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以校此本。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辄复随条补正,详举所由。”例如《广雅》:“谲恑,美也。”王念孙指出:“恑与诡通。各本皆作‘谲恑,美也。’案二字诸书无训为美者。此因恑下脱去‘也’字,而下文傀美也又脱去‘傀’字遂误合为一条,今订正。”(10)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0页。
王念孙遵循其师戴震“训诂的前提为校勘文字”的治学之道,重视典籍的文字校勘。他所作《读书杂志》,郭沫若誉之为:“考证学中之白眉,博洽精审,至今尚无人能出其右者。”(11)郭沫若:《〈管子集校〉引用校释书目提要》,《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页。全书共校订了“史部如《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子部如《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子》《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集部如《楚辞》《文选》和部分汉碑”等十七部重要典籍,“校正各书传写讹误、衍夺、倒文等两千数百条,并与《淮南子杂志》后总结讹误之例六十二条,足为校勘古籍之范式”(12)虞万里:《高邮王氏著作集出版说明》,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6页。。例如《读书杂志·逸周书》:“不明开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王念孙指出:“‘不明’上有‘明开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十二字,而今本脱之。”文字讹脱,语义不完,达不到教化的目的。王念孙根据两“如化”上下相应、相对而言的句式,认为脱落“明开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十二字,并据文献《小称篇》《小明武篇》《吕氏春秋·怀宠篇》论证“如化”皆言其速,最后根据《群书治要》引文,补足脱文(13)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页。。王念孙以音考字、音义互求,而又经史互证,故多发明,故陈奂曰:“高邮王石臞先生渊源同出乎戴,故论学若合符节。”(14)陈奂:《王石臞先生遗文序》,王念孙、王引之:《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
王引之为王念孙之子,可谓戴震再传弟子。王引之幼承家学,小学根底坚实。他尝云:“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15)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47-148页。王引之继承了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之训诂学思想,“以小学说经,以小学校经”,并形成一定的校改原则,即写官误、椠工误、妄改者,则为之改正。至于异体字、假借字,则不改动。其所作《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为训诂、校勘学名作。例如《经义述闻》“威侮五行”条,王引之指出:“某氏传曰‘威虐侮慢五行’,正义曰‘无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曰‘威虐侮慢’。‘威侮’二字义不相属,威为暴虐,侮为轻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于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疑当作烕,烕者蔑之假借也。”并进一步证明烕、蔑音近假借,曰:“《小雅·正月篇》释文引《字林》‘烕,武劣反’,正与蔑音相近,故借烕为蔑,烕之为蔑,犹灭之为蔑也。”而且《逸周书》《史记》《说苑》有“蔑侮(侮灭)”词例,故而断定某传与正义释义之误。王引之不仅“以小学说经,以小学校经”,还于《经义述闻·通说下》分析、总结古籍用字行文规律、训诂原则以及致误原由,以指导后学。其总结的致误原由有“衍文”“形讹”“上下相因而误”和“后人改注疏释文”等。例如“后人改注疏释文”例,王引之指出:“经典讹误之文有注疏释文已误者,亦有注疏释文未误而后人据已误之正文改之者。……凡此者皆改不误之注疏释文以从已误之经文,其原本几不可复识矣,然参差不齐之迹终不可泯。善学者循其文义,证以他书,则可知经文虽误而注疏释文尚不误,且据注疏释文之不误以正经文之误可也。”(16)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87-789页。王引之总结的条例已具有高度的理论性,所以方东树认为:“近人说经,无过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也。”(17)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清道光十一年刻本,第117页。
二、“因声求义”之训诂方法对皖派朴学的影响
戴震已清楚认识到“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18)戴震:《六书论序》,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295页。。六书是文字的纲领,纲举则目张。戴震创造性地提出四体二用说,认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为字之体,转注、假借为字之用。由于假借字在文献中广泛存在,“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19)戴震:《转语二十章序》,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304页。。假借字字义需要因声求义。“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训诂音声相为表里”(20)戴震:《六书音均表序》,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384页。。为寻求通假的法则,戴震作《转语二十章》以发明古音通转的规律,方便学者推求假借字字义。
戴震深谙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他在传统训诂方法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使其系统化、理论化,成为清代训诂学一大钤键。例如《召南·鹊巢》“维鸠方之”,《传》:“方,有也。”戴震按:“诗中‘方’‘房’通用。《小雅》‘既方既皁’,《大雅》‘实方实苞’,《笺》云:‘方,房也,谓孚甲始生而未合时也。’是‘方’有‘房’义。《汉书·地理志》‘山阳郡方与’,晋灼云:‘音房豫。’是方有房音,‘方之’犹‘居之’也。”(21)戴震:《毛郑诗考正》,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1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597页。《传》训“方”为“有”很是突兀,戴震因声求义,指出“方”“房”音同假借,义为居有,并佐以郑笺、晋灼注,从而使人知其所以然。戴震还运用因声求义法训诂联绵词。联绵词的最大特点是由两个音节连缀成义而不能分割,且形体不固定,意义寄托于声。例如《方言》“佚婸,淫也”,戴震指出:“‘佚’‘婸’二字乃双声,即泆荡也。又‘跌踼’,《广雅》云:‘行失正。’踼音宕,唐与荡、宕虽有平上去之异,本属一声轻重。……皆淫逸之义。”(22)戴震:《方言疏证》,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3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114页。佚婸为联绵词,义寄于音,与“泆荡”“跌踼”义同,皆为淫逸之义。戴震利用文字声音揭示通假字的本字,系联同源词、联绵词的异体形式,并用语转表明方言的音变字异,使文字训诂走上科学的轨道。
段玉裁传承其师戴震的思想,摆脱传统训诂受文字形体限制的窠臼,以声音为纽带,贯通汉字形、声、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广雅疏证序》中曰:“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说文解字注》中形音义互求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说文解字》:“朕,我也。阙。”段注:“按,朕在舟部,其解当曰舟缝也。从舟,灷声。……《释诂》曰:朕,我也。此如卬、吾、台、余之为我,皆取其音,不取其义。”(2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707页。许慎因不明“舟部”的“朕”字何以表达第一人称的“我”,于是阙如。段玉裁指出,“朕”用作第一人称的“我”,为取其音不取义,乃文字之假借,这样就解决了此处的疑惑。段玉裁进一步指出,形、音、义三者,“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2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321页。,所以因声求义更具有理据。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因声求义的集大成者。《广雅疏证序》中曰:“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王念孙指出,声音之于训诂,就如领之在裘、纲之在网,抓住声音这一纲领,便可以至赜而不乱。王引之于《经义述闻》中多处阐释其父思想,曰:“夫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相远。”“夫古字通用,存乎声音。今之学者,不求诸声而但求诸形,固宜其说之多谬也。”“故凡字之相通,皆由于声之相近。不求诸声而求之字,则窒矣。”(25)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8、571、71页。“因声求义,不限形体”的理论贯穿于王氏父子《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四部著作之中。例如:《广雅》“昌,始也”,王念孙指出:“‘昌’读为‘倡和’之‘倡’。王逸注《九章》云:‘倡,始也。’《周官》:‘乐师教恺歌,遂倡之。’郑注云:‘故书“倡”为“昌”。’是‘昌’与‘倡’通。”(26)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页。周祖谟盛赞《广雅疏证》,曰:“最大的特点也就在于不泥于前人旧注,旁征博考,参互比证,即音以求字,因文以考义,所以解说精当,往往出人意表。”(27)周祖谟:《读王念孙〈广雅疏证〉简论》,《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
王氏父子也用因声求义法探求联绵词词义。王念孙于《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连语”条指出:“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28)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26页。连语即为联绵词。王念孙反复强调,训释联绵词只能“因声求义”,不能望文生训。例如他于“踌躇,犹豫也”条指出:“此双声之相近者也。踌犹躇豫,为叠韵,踌躇、犹豫为双声……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29)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又于“扬榷,都凡也”指出:“大氐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30)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所以段玉裁于《广雅疏证序》中称王念孙“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
正如许威汉所言:“戴震提到训诂音声相为表里,表明了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即现代说的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这就纠正了一千七百年来文字直接表达概念的错觉,成为现代训诂学的精论。”(31)许威汉:《序二》,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1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6页。马裕藻在研究了戴震转语理论后以为,戴震“在古音学上有这么大的成绩,所以对于六书训诂特见甚多。……段氏之《说文解字注》,王氏之《广雅疏证》,殆无不受其沾灌”(32)马裕藻:《戴东原对于古音学的贡献》,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7册,黄山书社,1997年,第576页。。戴震的因声求义之法影响了当时的整个学术界,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除段玉裁、王氏父子之外,程瑶田《果蠃转语记》、郝懿行《尔雅疏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钱绎《方言笺疏》、邵晋涵《尔雅正义》等都是对因声求义训诂法的实践运用,他们“就古音以求古义”,超越形体,揭示假借本字、系联大批同源词,训诂之学至乾嘉而臻于鼎盛。戴震对于清代训诂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三、参验群籍的训诂方法对皖派朴学的影响
梁启超于《清代学术概论》中将盛清学风概括为:“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孤证不为立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3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页。。梁启超指的正是清代朴学实事求是、言必有据的学风。作为皖派朴学的代表人物,戴震凭借其深厚的文字、音韵和文献功底,自觉地把小学和经史子集贯通起来,“以字考经,以经考字”。其《尔雅注疏笺补序》云:“《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为之旁摭百氏,下及汉代,凡载籍去古未遥者,咸资证实,亦势所必至。”(34)戴震:《尔雅注疏笺补序》,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276页。又曰:“广搜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35)戴震:《古经解钩沉序》,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377页。“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36)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371页。
戴震训诂实践便采用了这种字书、经传群籍互证之法。例如他疏证《方言》,便把《方言》写于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之上,实现《方言》与《说文》的互证,然后广泛参验群籍,引用书目多达101种,共采书证3268条。所引书目经部主要有:《周易》,晋王弼注,唐孔颖达疏;《诗经》,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古文尚书》,汉孔安国传,晋王肃注,唐孔颖达疏;《尚书大传》,汉伏胜撰;《周礼》,汉郑玄注;《礼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仪礼》,郑玄注;《大戴礼记》,汉戴德撰;《春秋左氏传》,东汉服虔注,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小学类主要有:《尔雅》,汉舍人注,汉魏间孙炎注,晋郭璞注,宋邢昺疏;《说文解字》,后汉许慎撰,南唐徐铉校订;《广雅》,魏张揖撰;《经典释文》,唐陆德明撰;《毛诗草木虫鱼疏》,晋陆机撰;《玉篇》,晋顾野王撰;《广韵》,宋陈彭年撰;《类篇》,宋司马光撰;《说文解字系传》,南唐徐锴撰。正史类主要有:《史记》,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汉书》,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后汉书》,宋范晔撰;《三国志》,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子类主要有:《荀子》,战国荀况撰,唐杨倞注;《老子》,春秋老聃撰;《列子》,列御寇撰,晋张湛注;《庄子》,战国庄周撰;《淮南鸿烈》,东汉刘安撰,高诱注。集类主要有:《楚辞》,汉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文选》,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乐府诗集》,宋郭茂倩辑;《艺文类聚》,唐欧阳询等撰;《初学记》,唐徐坚撰;《太平御览》,宋李昉等撰(37)徐玲英:《戴震〈方言疏证〉引书考》,《古籍研究》,2007年卷上。。 这些典籍或用于疏证词条,或校正传刻文字讹误,皆做到言而有据、孤证不立。
段玉裁继承其师“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训诂思想注《说文》。其尝云:“余之治《说文》也,以字考经,以经考字,大指本徽郡戴氏。”(38)王念孙、王引之:《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其《说文解字注》亦广征博引,遍及小学、经史子集,计50余种。小学类主要有:《方言》,西汉扬雄撰;《广雅》,曹魏张揖撰;《释名》,东汉刘熙撰;《玉篇》,南朝梁顾野王撰;《急就篇》,西汉史游撰;《三苍解诂》,晋郭璞撰;《埤雅》,宋陆佃撰;《匡谬正俗》,唐颜师古撰;《通俗文》,东汉服虔撰;《字林》,晋吕忱撰;《五经文字》,唐张参撰;《汗简》,宋郭忠恕撰;《九经字样》,唐唐玄度撰;《类篇》,宋司马光等撰;《佩觿》,宋郭忠恕撰;《说文解字篆韵谱》,宋徐锴撰;《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宋李焘撰;《六书故》,宋戴侗撰;《龙龛手鉴》,辽释行均撰;《声类》,曹魏李登撰;《唐韵》,唐孙愐撰;《经典释文》,唐陆德明撰;《一切经音义》,唐释玄应撰;《广韵》,宋陈彭年撰;《集韵》,宋丁度等撰;《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宋毛晃增补;《古今韵会举要》,元黄公绍、熊忠撰。经类主要有:《十三经注疏》,清阮元等撰;《尚书大传》,西汉伏胜撰。史类主要有:《史记》,西汉司马迁撰;《汉书》,东汉班固等撰;《后汉书》,刘宋范晔撰;《国语补音》,宋宋庠撰;《汉制考》,宋王应麟撰;《水经注》,北魏郦道元撰。子类主要有:《吕氏春秋》,秦吕不韦等撰;《风俗通义》,东汉应劭撰;《淮南子注》,东汉高诱撰;《颜氏家训》,南北朝颜之推撰;《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撰;《开元占经》,唐瞿昙悉达撰;《列子释文》,唐殷敬顺撰;《北堂书钞》,唐虞世南辑录;《初学记》,唐徐坚等辑录;《艺文类聚》,唐欧阳询等;《太平御览》,唐李昉等辑录;《事类赋》,宋吴淑撰;《小学绀珠》,宋王应麟撰。集部主要有:《文选注》,唐李善撰(39)李晓明:《〈说文解字注〉与段玉裁之校勘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8-41页。。《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辑录了大量散佚的资料,“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4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141页。。《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类书的运用为《说文》的注解和校勘提供了证据。

王引之称其父“校订之精,引证之切,触类引申之广,实上追两汉诸儒。训诂略其形迹,而取其精华,贯穿该洽,左右逢源”(44)王念孙、王引之:《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页。。受家风熏陶,王引之为学也旁征博引,毛、郑、贾、孔等传注皆为其所用,甚至援引师友观点予以佐证。他于《经传释词序》中云:“自《九经》、《三传》、秦汉之书,凡语助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为《经传释词》十卷,凡百六十字。”例如“谓”字条,王引之指出:“家大人曰‘谓’犹‘为’也。”为论证“谓”犹“为”,王引之引用了《周易》《诗经》《左传》《史记》《战国策》《国语》《大戴礼记》《晏子春秋》《淮南子》《汉书》《吕氏春秋》《盐铁论》等古籍辞例,特别是《庄二十二年左传》“是谓观国之光”,《史记·陈杞世家》作“为”;《说苑·君道篇》“则何为不具官乎”,《晏子春秋·问篇》作“谓”;《吕氏春秋·精谕篇》‘胡为不可’,《淮南·道应篇》作“谓”……这些别本异文最能说明“谓”“为”意同(45)王引之:《经传释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7页。。《经传释词》常引典籍主要还有:《尚书》《礼记》《仪礼》《中庸》《春秋》《后汉书》《韩诗外传》《竹书纪年》《公羊传》《谷梁传》《考工记》《论语》《孟子》《老子》《荀子》《庄子》《墨子》《管子》《列子》《韩非子》《淮南子》《晏子春秋》《春秋繁露》《山海经》《说苑》《新序》《楚辞》《文选》《论衡》,以及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著作(46)袁海林:《王引之〈经传释词〉的引据》,《语文研究》,1998年第4期。。
王念孙总结一生治学经验曰:“经之有说,触类旁通。不通全书,不能说一句;不通诸经,亦不能说一经。”(47)王念孙、王引之:《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3页。王氏父子紧步其师戴震之武,训诂一字必本六书,贯群经而后为定。所以皮锡瑞称“经学训诂,以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为最精”(48)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242页。。
四、结语
不同于吴派朴学以古为尚,皖派朴学求其是。戴震认为六经乃道义之府,为了探寻六经中的微言大义,必须走“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之路。“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49)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370页。;反之,“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50)戴震:《与段茂堂等十一札》,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541页。。为了探究六经中的道义,戴震重视文字训诂,然而文字训诂必以是正文字为前提。为求一字之“的”解,戴震不仅本之六书,分析形体,还运用古音知识,因声求义,实行音义互求;并且利用前人训诂成果,汇综群籍、择善而从,形成了鲜明的训诂学思想和特色。戴震的训诂学思想对皖派朴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尝曰:“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5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3页。在戴震训诂学思想的指引下,段玉裁和王氏父子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训诂学成就,皖派朴学也因之臻于鼎盛,戴震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