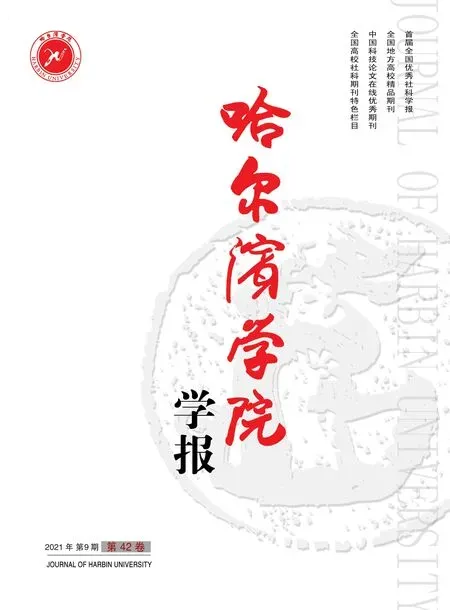故乡的迁移与回归
——论严歌苓的《寄居者》
汪礼霞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严歌苓的作品涉及话题众多,从部队军旅到校园生活,从文艺知青到农村寡妇,从中产阶级贵妇到绝命赌徒,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严歌苓借助这些人物形象命运的起伏跌宕来阐释东西方文化的不同魅力,表现其对特定时期社会边缘人物的深切关怀,同时,也是对人性复杂多元的思考和叩问。本文着意于《寄居者》在异域环境下的迁移与流放、对故乡的眷恋与回归、主人公精神困境的挣扎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异域文化下的迁移与流放
漂泊、流浪、迁移与流放,不是现当代文学才有的题材,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1]屈原在《离骚》中表达了自己被流放在外依然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积极上进的心态;唐代李白的出游诗、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以及李清照的词曲中都有迁移与流放、飘零与孤独的叙写。近现代作家艾芜、张爱玲、萧红等的作品中也书写着漂泊、飘零无依的意象。漂泊主题在新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如王德威在《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中说的那样:“去国与怀乡曾是现代中国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当代作家频繁的迁徙经验势必要为这一主题平添新的向度。”[2]严歌苓作为第五代移民作家中成就最高者,她的长篇小说《寄居者》以独到敏锐的眼光观察并书写了移民们在异域中的艰难跋涉与孤独的飘零。小说把人物置放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同一种族同一信仰的人不同价值观念的巨大反差,不仅给漂泊者本人带来精神上的迷茫和痛苦,也给他们的亲人带来精神上的犹疑和挣扎。迁移与漂泊给主人公命运带来的惊险与刺激使文本阅读的体验跌宕起伏,令人爱不释手。
寄居者们都是漂洋过海,在别人的国土上暂时寄居的人,像《寄居者》中的犹太人——彼得·寇恩、杰克布·艾德勒甚至没有自己的国土。在长达十几个世纪中,他们不断地迁移、被放逐,一代一代地迁徙、流浪,不同群体的文化传统、语言、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对他们也形成碰撞和挤压。犹太人信奉犹太教,对自己的宗教守护森严,喜欢建立自己的社区,崇尚种族内通婚等行为,这使得他们即使生活在别人的国土上,也不可能真正接纳别国的文化,并排斥当地的生活方式,因而产生诸如心理压力、好强出头又焦虑不堪等负面的情绪。《寄居者》中,作为寄居者的玫、彼得和杰克布,他们的形象和命运的铺排都与迁移、流放紧密相关,对故乡的眷恋、人性价值的回归都是作者想探讨的话题。他们在异域环境中所遭受的歧视与压迫、背叛与坚守,是所有寄居者的命运共性。同时,小说也充分展现出严歌苓对移民群体物质、精神方面的长期关注与探讨。
小说主人公玫是中国移民,祖父辈就举家迁徙。她出生于美国,接受地道的美式教育,但在这片远离国土的环境里,她痛苦压抑、孤独寂寞,被歧视和嘲笑,这一切都源于她的亚裔特征——黄皮肤、黑头发。但是她年轻、热情、真诚、叛逆、有个性,所以当知道能与父亲一起回国时,她欣喜若狂。回到上海,她又因不满父亲娶了年轻世故的继母而离家出走。为了彰显自己的自立能力,她去酒店应聘钢琴师,在此期间结识了犹太人彼得,并对彼得一见钟情。为了心爱的人,她甘愿冒险,陪彼得去参加聚会,被手包里的抗日传单连带进了日本人的牢房。被家人千辛万苦营救出来后,她面对日本人限期出境的威胁置之不理,偷偷跑去郊区教书,定期深夜去看望情人和父亲,又善良体贴地不让他们找到自己的藏身之所,以免给他们引来杀身之祸。所以,玫年少敏感、叛逆任性、玩世不恭,但她真诚善良、清醒有担当。玫认为:“我是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3]这既是玫的宣言,也是寄居者们的宿命。正如哈罗德·伊罗生在《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中说道:“在一个国家拥有公民身份,但却被剥夺了民族,也就无异于被抛掷到无家的荒漠,无异于处身猛兽出没的蛮荒。”[4](P232)玫从他的祖父那一代开始,就迁居于美国,虽持有护照,有自己的洗衣坊,不再贫穷卑贱,但在异域的环境下,仍然得不到认同和应有的尊重,虽然拥有美国国籍,但还是被歧视、被冷遇。
彼得和杰克布作为犹太人,寄居在二战时的中国,命运更为悲惨。一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中日战争的胶着时期,整个上海已沦陷;其次作为被纳粹驱逐追杀的犹太人,更是找不到一块立足之地。彼得能来到中国,得益于其母亲的活络和执著,以及遇到了善良的中国外交官。但歧视无处不在,即使是上海这样一个“全世界的给自己的道德放假的圣地”,也没有人把犹太难民当人看。难民所是他们的藏身之处,因为一般房屋不得对难民出租,工作招聘广告中明确写着“犹太人除外”。住在难民所里的他们遭遇瘟疫,每天有大量的人死去,所幸彼得一家躲过一劫。这就是寄居者的悲哀,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奔赴的地方不仅没有提供起码的安身立命之所,却是又一个想逃都逃不掉的绝境。彼得他们到来不久,就得知纳粹和日本高官密谋,要给在上海的所有犹太人“终极解决”。所以,没有自己的土地,流浪到哪里就被追杀到哪里,一如大海枯木,无根可依。
而杰克布来到上海一方面是因为避债逃难,另一方面是受到玫的有意哄骗。他与彼得长得很像,可性格完全不同。他一开始给人的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瘪三”“街头混混”,吃喝玩乐、赌博闹事、借钱耍赖样样与他相关,与他的两个精英哥哥形成强烈的反差,最后因为还不上赌债,被追打跟踪,想逃到上海淘金挣大钱。可是,事实上,杰克布骨子里是个有底线、有原则、真诚善良的人。下船到上海,他完全不理解还有种交通方式叫人力车,他拼死不坐人力车,认为那是践踏人权,把人当牲口使;在看到日军在中国的种种暴行后,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抗日革命中去,被殴打毁容且险些丧命也在所不惜。他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追随自己的革命信仰,用满腔热血投身抗日,消解了他流浪者的悲剧身份。
无枝可栖流放逃亡的犹太人也好,漂泊异乡踟蹰美国的中国人也罢,他们远离故乡,在异域的土地上无法真正接纳别国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和传统信仰的不同让他们始终无法找到认同感、归属感,使他们始终游离在社会之外。正如我们在阅读文本时所体会到的作者笔端的寄居者的心情,那种找不到落点的恐慌,走到哪里都感觉没有着落,无论在哪儿都是一个个体,一个不曾被融化的个体。玫到了美国想回到上海,没命地想念上海的小笼包和她常逛的小吃店;到了上海又想逃离,逃到亲情够不到的地方去,连自己很讨厌的旧金山洗衣坊似乎也透着可爱的光芒。因此,作者心里住着一份明白,提醒自己不属于这里,总有一个地方在等她。最后,没命地奔跑、寻找、求索,在重建与毁灭之间,仓皇四顾,疲于奔命。
二、对地域故土的眷恋与回归
无论是对于全世界飘零的犹太人而言,还是对华裔作家来说,移民改变的不只是时空,也不是倒倒时差一切就都能回归原位,按部就班。移民会让他们远离熟悉的语言文化环境,需要重新适应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文化和心理上的落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漂泊也意味着寻找。严歌苓作为移民作家,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敏锐情感为基础,讨论的不仅仅是因空间距离的改变而产生的孤独漂泊感,其本质是在关注人精神上的漂泊,而追寻、探索回归的过程就是寻找精神家园,想要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
灵魂不能一直游荡在漂泊的路上,必然要为心灵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漂泊的过程也是不断寻找精神归依的旅程,对地域故土的眷恋促使他们在漂泊中寻找,通过不断地自我认知、自我提高和自我审视来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精神信仰。对工作的执著、对伴侣的选择也属于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探索,归根结底,是想寻求心灵上的依托和心理上的安慰。
《寄居者》中的上海是一个汇集着“三教九流”的鱼龙混杂、肮脏失序的地方。在像战争这样的特殊时期,不同的寄居者有不一样的价值追求,有的追求暴利,有的追求活命,有的追求责任和信仰。玫作为一个任性不安分的人来说,对待爱情却专一认真,她对偶然遇见的犹太难民彼得一见钟情,看中他身上那种精英贵族般养育熏陶出来的贵气,所以在彼得遇到生命威胁的时候,她甚至想出牺牲别人来保全所爱之人的办法。为了帮助彼得逃离“终极解决”,她处心积虑、精心布局,从美国诱骗和彼得长得很像的杰克布来到上海,不惜以自身为代价,与杰克布日日周旋,以图拿到杰克布的护照,成功让彼得替换成杰克布逃往美国。但曾经的“犹太瘪三”杰克布在上海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秘密参入抗日活动,置自己的身家性命于不顾。而曾经被玫崇拜景仰的彼得却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倒卖粮食和药物,甚至在手握救命的手术刀时还在与自己的同胞讨价还价,且因为怕惹麻烦而见死不救,此时玫的天平开始倾斜。在船离开岸的刹那,“我头也不回地向着上海乌烟瘴气、臭烘烘的岸跑去。……最重要的是,那儿藏着杰克布·艾德勒。”[3]这里铺叙的不仅有玫对故乡的眷恋,还有那些有关故乡的零零散散的印象,那些小而窄的小吃店,那些能淘到更多心仪的漂亮裙子和俄罗斯皇室珠宝的寄卖店,那些啰嗦世故又有亲切感的邻居,都是玫割舍不下的。对故乡这些意象的书写是玫站在爱情的十字路口说服自己选择留下的托辞,也是玫在爱情里成长的见证。玫没心没肺,单纯简单,爱上彼得的时候,不在乎他的难民身份,不顾及他刚刚从瘟疫堆里逃出来的肮脏和狼狈。为了爱情,她愿抛弃父亲和亲人,准备一辈子隐姓埋名,甚至她出卖自己的身体,无视自己的道德和良知,沉迷在自己对爱情的想象里不顾一切。但当彼得倒卖粮食、药品和一心为己的自私冷漠的表现一再让她震惊、失望时,她也能毫不犹豫地放弃那段她付出了全部的爱情,选择了与杰克布一起去面对战争和死亡。从玫一开始对杰克布的有意利用,到最后与他倾心相守的转变与成长,不只是显示了这个中国女子在爱情中的盲目与坚持、成长与放弃,更是完成了她对故乡的眷恋与不舍、对心灵的探索与回归。这里,杰克布是正直、善良、自由、美好的化身,玫多年的飘零和寻找终于有了最后的依托,这也是玫从形体到精神世界的全面回归。
犹太人在两千多年的流浪和迁移过程中,他们的心灵深处积淀着深厚的集体意识和民族认同感。他们有群体观念,族群意识很强,有共同的信仰,遵循着同样的教义。可即便是这样的民族,个体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面对残酷的战争,人性的本来面目就更容易坦露。彼得得知玫计划偷杰克布的护照助自己逃往美国后,他不拒绝,没有震惊,甚至他根本没有想过这样做会对杰克布有怎样的影响,而是一再地确认和杰克布是不是长得像,能不能蒙混海关的检查。对玫而言,彼得是隐晦的,不透明的,她看不懂他。彼得对玫的爱情带有极大的功利主义色彩,他爱玫,因为玫是他在上海生存的救命稻草,可助其家人安然存活。迫不得已带玫回家,也完全不体谅玫的狼狈处境反而责怪玫表现不好,处处透着自私和冷漠。而杰克布坦荡热情,寄住在玫家,就承担了玫一家人的生活费用,在通货膨胀的战争年代,这可并不容易。自己参加抗日战争,不隐瞒玫,但绝不让她涉险参与,被逮捕了差点命丧黄泉,回家后也坚守秘密以保护玫和她的家人。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寻找人生价值,寻找精神的出路和心灵的归依。自从和玫一起来到上海,“此后他的自我发现,自我成全,似乎是这次来上海的偶然后果。但任何偶然都不会偶然得那么纯粹,都包含着必然。”[3]这是人性本善的必然,是生命追求价值体现的必然。杰克布以投身革命、坚持正义、追求自由的方式实现了他的精神探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人生价值的追寻,也是在追寻自己的精神家园,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也是精神回归和心灵回归的旅程。杰克布努力在漂泊的状态中寻得精神的归依,在战争的严酷中华丽转身,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
三、移民困境中的挣扎
严歌苓善于描绘女性形象,尤其是作为边缘人物的寄居者女性,书写她们的苦难。当然这也与她作为移民中的一员,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深厚的阅历有关。在对极端环境,比如战争进行描写时,揭示并彰显了最真实的人性,并将人性挖掘得更加透彻。但是,移民女性们虽然能承受生活的苦难,却很难走出精神困境。《寄居者》中的玫接受不了一直被她深爱、推崇甚至景仰的彼得变成一个贪得无厌、大发战争横财、精致纯粹的个人利己主义者;虽然一度追随杰克布的步伐,跟随他来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但最终也无法委屈自己,成为杰克布眼里的“有趣的姑娘”。她一生都在追寻、挣扎,最终,还是自己孤独的一个人。
在这样的精神困境中,婚姻找不到安全的港口,爱情结不成丰硕的果实,最终的原因可能是身份、种族,也可能是自尊,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高下差异。女性的敏感与自卑,自我保护与精神独立是底线,寄居者女性们承受得了生活的苦难,却难以找到心灵的出口,走出精神的困境。
严歌苓以她深厚的民族情结、丰厚的人文积淀和细腻的女性体验对寄居者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寄居者》不是一个单纯世俗的三角恋,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爱情故事,而是作者借助爱情这身华美的袍子,包裹了苦难民族的移民血泪史。小说通过对移民的文本书写和经典人物形象的塑造,让读者可以探源到幽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作品没有宏大的历史场景的叙述,没有从正面讨论移民的历史传承和历史渊源,也没有对移民制度和策略做过多的剖析和指责,而是将移民的血泪汗水铺陈在一个温情理性的爱情故事里,体察个体隐秘的内心感受。一如学者张栋辉所言:“作者没有从正面展开对移民历史的宏大叙述,而是将历史退隐幕后,成为小说主人公盛装出场的场景铺陈,但个体隐秘的内心感受从侧面传达了对历史的记忆与重构。”[5]对故乡的眷恋与回归,对精神苦难的挣扎与抗争,都是作者对历史的记忆与重构,使得在历史与文化的双重对接中,铺陈再现了浓烈的时代情愫和丰盈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