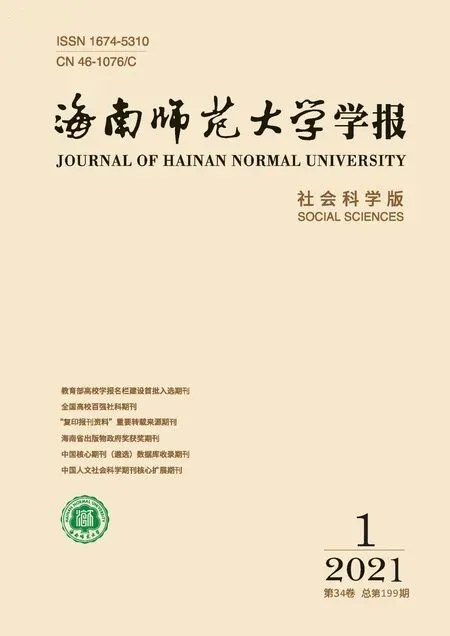仪式与游戏
——论麦克尤恩对“成长小说”的解构
蒋浩伟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关于麦克尤恩小说里的“成长”主题,已有很多论者进行过讨论研究。一般的研究模式是,先追溯传统成长小说中所谓“成长”的叙事模式,再描述现代以来小说中对“成长”这一叙事模式的突破和发展,然后以前两者为参照反观麦克尤恩对于“成长”的表现。在这一条主线索的叙述过程中,对于社会结构变迁和作者身世差异的因素也会相应考虑在内,最终完成对麦克尤恩“成长”书写的纵向和横向综合论述。而在这个论述视角下,主要讨论的对象是麦克尤恩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水泥花园》《时间中的孩子》,除此之外,可能会包含《赎罪》等其它小说在内。在这些论述中,麦克尤恩的“成长”叙事模式被描述为“反成长”小说,或者“非常态成长”小说。因为与传统成长小说讲究“走向成熟和和谐”不同,它们描述的更多的是“性心理走向迷误和畸变”。(1)张和龙:《成长的迷误——评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水泥花园〉》,《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4期。简而言之,是从成长走向拒绝成长,从理性走向非理性。以往的论述虽然在此方面用力颇多,但多数对麦克尤恩笔下“成长”的具体发展和演变过程缺乏深入的逻辑分析,这一“反成长”或“非常态成长”的模式往往落于浅层特征的归纳和整理,以区别于传统西方成长小说中的叙事模式,因而,也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这种归类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样的叙述就把麦克尤恩笔下的“成长”简单化了,没有洞察出其自我解构和重构的策略——麦克尤恩并不是旨在批判“反成长”,也不是旨在对传统成长小说的回归,而是对传统“成长”的概念作出新的阐释和理解。
一、“成长小说”中的仪式性
“成长小说”是西方文学传统中一种独特的小说类型,又被称之为“教育小说”,它“是以叙述人物成长过程为主题的小说,就是讲述人物成长经历的小说。它通过对一个人或几个人成长经历的叙事,反映出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因此,成长小说应该限制在主人公从对成人世界的无知状态进入知之状态的叙事。也就是说,主人公迈出了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才能够看作是成长小说。”(2)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
从历史发生的角度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大约起源于启蒙主义时期。直到18世纪前后,人们才开始关注儿童或青少年成长的问题,关于“儿童”的绘画、文学创作也才开始大量出现。(3)吕大年:《替人读书》,上海:上海书店,2007年,第31页。例如,17世纪的英国深受加尔文学说的影响,“由之引申出来的对儿童的看法,就是他们除了身形相貌还未臻成熟,本质上和大人并无二致,谈不上什么天真纯洁。以这种看法为基础的亲子关系和教育思想,自然不会承认儿童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会把儿童当作小大人来看待,来要求”,也因此“成年人没有感到儿童的生活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录、描写的地方”。(4)吕大年:《替人读书》,第34-36页。而到了乔治时代,社会开放宽松,富有的有闲阶级开始发觉自我童年的缺失,从而把这种注意力转移到对下一代儿童成长的重视上来,从而“发现”了童年。因而,英国成长小说传统的诞生主要离不开两个原因,一是工业化社会带来的生活富足,二是启蒙时代思想风气的影响。(5)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第37页。
与此相似的是,同样诞生于18世纪前后的德国成长小说,其诞生虽然有“内在塑造”和“外在经验”两个阶段,其产生也离不开上述两个原因,只是更倾向于启蒙思想的推动。这个原因想来简单,启蒙运动对“人”的重新审视,对如何进入成熟、理性的自我进行思辨,对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分模式自然会牵扯到青年和成年之间的关系,并对之进行二元区分。在这个成长模式里,儿童或青年自然被放入还未能完全掌控理性的一方,或者还未能进入社会的一方,探讨儿童或青年的成长问题实质上就是探讨如何掌控“理性”的问题。例如,英国乔治时代的“绘画里表现的是大人眼里的孩子世界——艺术里的童年总是由成年来限定,来描绘的。儿童对于自己被画成什么样子,恐怕是一词不能置。肖像的委托人一定赞同洛克的说法,儿童的价值标准都从见识模仿而来”。(6)吕大年:《替人读书》,第47页。这换到文学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以上这两种现象其实表明的是一回事,“成长小说”的兴起和“儿童”与“成人”的逐渐区分及认识有着密切联系,并伴随着启蒙时期特有的“理性”目的,这种理性的表现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塑造,二是外在对社会的改造实践。这个变化同样深刻反映在“教育小说”的德语名称Bildungsroman的内涵变化中,它由最初的宗教意义上的“按上帝的形象‘塑造’逐渐演变为强调人的德行和理性上的‘教育’‘修养’‘发展’的意义”。(7)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第39页。
因此,在“成长小说”中重要的关键在于其中的二元结构,也就是“天真”和“经验”的区分。“成长”本身意味着从“天真”涉入到“经验”的领域,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或领悟之前未曾接触的事物,这个逻辑的终点就是“成熟”。即使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成长书写有种种不同,这个模式几乎也是可以完全被应用其上的。现代小说中主人公在经历种种劫难和挫折,而最终好像并没有获得一个理性的、成熟的自我,反而更加迷茫,或者对世界充满了幻灭感。(8)孙胜忠:《美国成长小说艺术与文化表达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页。这当然是其与传统成长小说不同的地方,但其反对的是“理性”或者说“成熟”的目的,而并没有否定这一成长模式,即仍旧设立了一个“经验”的过程。主人公的迷茫和幻灭仍旧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是在其对社会或自我的深刻认识之后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仍涉及了“经验”的领域,只不过并不符合一般传统成长小说所设定的那个理性的、乐观的自我。这也就是其与传统成长小说殊途同归的一面,也是其依旧可以被纳入到成长小说予以讨论的依据。所以,那种所谓好像未曾“跨过门槛”但有所觉悟的主人公,仍然算不上是完全的“反成长”。
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标志在于变化,即从“天真”跨越到“经验”这一过程中所带来的变化。马科斯在《什么是成长小说?》中对成长小说有这样的定义:“以上这些概念综合起来将提供一个有效的定义。可以说,成长小说展示了年轻的主人公经历了重要的改变,这种改变要么是关于对外在世界或他自己的认识,要么是关于他自身的性格,或者两者皆有。这种变化必须指向或者引导他走向成人的世界。在其中,仪式可有可无,但是它必须给出证据显示这种变化能留下持久性的影响。”(9)Mordecai Marcus, 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 ,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19, No. 2, 1960.但换句话说,这种“证据”,这种对于特定“时刻”或“行为”的书写本身就是在营造一种仪式感。不能想象后来的人还会像古代的人一样行使特定的和隆重的“成人礼”来宣告自己进入成人世界。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以及文学世界里,仪式感在变弱,也更加多元,但并不是不存在。“成长小说中,常常通过某种象征性的仪式来表现阶段性的成长。”(10)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第190页。因而,在成长小说里,主人公的成长也好,顿悟也好,对于这种变化的象征和暗示就是仪式的过程。与古代成人礼相通的是,文学中的仪式也需要伴随着象征性“事件”的发生和表演,然后由主人公的选择和行动来宣告自己的变化。
不过,虽然“成长小说”中都有对“仪式性”的描写,并以此作为小说叙事的节点和结局,但却表现的并不相同。传统成长小说诸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大卫·科波菲尔》等中的主人公往往要通过外在旅程,应付诸如婚姻、战争等社会仪式来完成自我认识以步入成年,因此缺乏心理氛围和内在力量的描绘。(11)徐丹:《倾空的器皿: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9页。与此相对,像《简·爱》和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小说,其主人公则往往是在经历了外在世界的多重磨难后,从精神层面上走向自我成长的,对人物内心的力量描写更丰富。但无论是应付外在社会规则,还是战胜内在精神的困境;是着重女性的自我成长,还是突出新兴阶级力量的兴起,在从童年世界到成人世界这一过程中,也就是从“天真”跨越到“经验”的过程中,“仪式性”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往往在小说的结尾被点明,在主人公最终觉醒和成长的时刻都会作为突出书写的重点,给出提示,仿佛主人公经历一个特殊的时刻,从而跨越到完全不同的领域之内。这一时刻多以诀别式的宣言或者决定式的行动来展示,也往往是在成长小说情节的高潮部分。对此,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托马斯·曼的《魔山》结尾对主人公汉斯在山上遇到暴风雪陷入梦境的描绘。暴风雪中的沉寂就如同象征的仪式,给了七年里“浑浑噩噩”的汉斯一个顿悟的机会,使他醒来之后终于走出了种种争论和困惑,开始要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行动。而与传统成长小说不同的是,在现代成长小说中,这一时刻也会出现,但往往并不是向上提升,而是向下跌落,或者带有沉重的幻灭感,也就是无法对自我决定的力量抱有信心和希望。例如,在《麦田的守望者》中,霍尔顿并没有因为种种不堪的遭遇获得成长,而是产生了浓重的幻灭感。在故事的结尾,霍尔顿在突降的大雨中看着玩耍的妹妹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而放弃了自我出走的计划。这场象征着“成长仪式”的大雨本应导向一个乐观、积极的自我成长的结局,但实际上,回到家中的霍尔顿,仍旧对丑恶的现实无可奈何,只能是消极地抵抗和妥协。
因而,从另一角度而言,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成长小说虽然对传统成长小说乐观的、理性的自我和目的提出了质疑,或进行否定,但还是依然在二元区分的仪式中进行书写。这些小说依然是借由主人公在经验之后的体验和感觉来告诉读者何谓成熟的认识这一事实。如果借用后现代主义惯用的说法,传统成长小说所设定的理性认知过程和目的无疑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式的,而现代成长小说虽然否定这个理性的目的和结局,但仍然保有这种对立区分的模式,往往更加侧重于“天真”的领域。但在这里,孩子与成年,自然与启蒙仍然是二元的,只是其重心发生了变化而已。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要对麦克尤恩笔下的“成长”有所洞见,不能仅仅从文学的手法,或与其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层面作出解释,还要结合逻各斯的本体主义来看待,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麦克尤恩作品的特点。
二、对“成人”仪式的解构
在麦克尤恩的著作里,集中体现他对“成长”的关注的是《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水泥花园》《时间中的孩子》这几部小说。在这类被认为是“反成长”或“非常态成长”的小说里,它们与传统成长小说不同之处有两个方面,一是小说的人物“拒绝成长”或“难以成长”,二是所谓的“非常态成长”,也就是“畸形成长”。(12)杨燕:《伊恩·麦克尤恩小说中的“非常态成长”主题研究》,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9页。.前者如《与橱中人的对话》,后者如《家庭制造》《水泥花园》。但仅仅对两者情节上差异的对比和归类,并不能揭示出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差别。成长小说的二元模式必然要在“天真”与“经验”之间的仪式中建构起来,对以上几部小说而言,它们则在不同程度上否定、甚至消解了这个建构的原点,这才是根本性的因素。
在短篇小说《蝴蝶》中,故事的主人公“我”在奸杀了陌生的小女孩之后,应警察局的要求去接受其家长的谈话时,却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到同龄人中去了,“等他们再长大一点我们就一块去喝酒,而我也将学会爱上啤酒。我站起身开始缓缓地沿原路往回走。我明白我将不会参加任何足球比赛。机会渺茫,就像蝴蝶。你一伸手,它们就飞走了。”(13)[英] 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119页。在这个故事的核心里,死亡作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同样承担了微弱的仪式感,为读者提供了观察主人公从“天真”过渡到“经验”状态的契机。但与传统成长小说,甚至西方现代成长小说不同的是,主人公既没有跨越到成熟的自信与喜悦,也没有对未来感到失望的幻灭感,而是无动于衷的冷漠,仿佛这个跨越以及仪式并不存在。而在《与橱中人的对话》里,主人公“我”则因为父母的离异,以及被母亲抛弃导致了对家庭之外的世界感到恐慌和抗拒,在经历了社会的打击式仪式之后,只能躲在柜橱里期望能够永远停留在儿童时期。同样的,还有《家庭制造》里的汤姆,因为躲避同年人的追打,而情愿装作女孩,当一辈子的孩童。因而,在麦克尤恩的这些作品里,区分和微弱的仪式感仍然存在,但却失去了实质性的意义,它既不能够为故事的人物提供变化的契机,也不能指出转变的意义。
与以上几部作品不同,《家庭制造》《化装》《水泥花园》则对这种区分和仪式进一步进行重复性的表演,以致使它们沦为自我解构的游戏。在《家庭制造》里,“我”和朋友雷蒙德一直对成人的世界充满着向往和期待,对周围那些大人的言谈、举止等所有迷人的细节进行摹仿和学习,“就这样,到十四岁时,在雷蒙德的引领下,我已经熟知了一系列我恰当地归之为成人世界的享乐。我一天抽十支烟,有威士忌就喝,对暴力和淫秽颇有鉴赏力。我吸食过烈性的火麻脂,并明了自己的性早熟,但很奇怪的是,我从未意识到这有什么用,我的想象力尚未因渴望和隐秘的幻想而丰富。”(14)[英] 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第36页。对于“我”和雷蒙德而言,对这些社会成人规则和行为的摹仿并未能够像一般的成人仪式那样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或新的意义,而是没有什么用,也并不丰富。所有对成年的幻想和期望并没有因这一系列成人的举动而达到圆满。在“我”和雷蒙德看来,这种缺乏最为关键的是“那秘密中秘密核心,那肉欲的圣杯,漂亮露露的私处”。(15)[英] 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第43页。在与雷蒙德这个“舞台助理”商量好的实践这个秘密的计划之后,“晚饭吃的是面拖香肠,吞咽也仿佛一种无法言传的仪式”。(16)[英] 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第46页。但在“我”即将实践这个成人仪式前,“我”突然发现妹妹康妮也可以成为这秘密的补充和替代,从而提前实现它。于是,在“我”的诱导之下,这场仪式委托于“游戏”的名义来进行:
有一个游戏对像康妮这样既爱家又缺乏想象力的小姑娘来说是无法抗拒的,从牙牙学语开始,康妮就不断地烦我,要我陪她玩。因此我的少年时代经常被她这样的请求骚扰,而我总是以断然的拒绝将她赶走。总而言之,我宁可被绑在柱子上烧死,也不愿意被朋友们看见在玩那种游戏。现在,我们终于要玩“爸爸妈妈过家家”了。(17)[英] 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第50页。
“我”以前之所以不愿意玩这个游戏是因为它只是摹仿成年人的游戏,并不是“我”所期望拥有的成年生活,因而觉得幼稚和可笑。同样,现在“我”之所以提议玩这个游戏,也不过是借游戏的形式来完成自己的成年仪式,因而对“我”而言是严肃和重要的事情。但仪式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困难,“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每次康妮说‘我还没有任何感觉’,我觉得我自己的男子气就流失一点”。(18)[英] 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第54页。虽然最终我还是在妹妹的引导下完成了这个成人仪式,“我希望雷蒙德能看着我,我很高兴他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童真;我希望漂亮的露露能看着,事实上假如我的愿望能够实现,我会希望我所有的朋友,所有我认识的人,排着队走进卧室瞻仰我的光辉形象”,但这一切不过是“我”自己的感觉,事实上,“只用了几下就到了,可怜巴巴,草草了事,没什么快感”。(19)[英] 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第56页。
对这段情节的描写,完全把它归结为“我”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接受正常和有序的社会规则,就显得简单化了。这段叙事不仅仅是对这种畸形成长的否定,还是对传统成长小说那种“天真”和“经验”的仪式化进程的解构。在传统成长小说里,成长被建构为一个质变的过程,一个进入到理性世界的光辉瞬间。所有天真时期的不安和混乱都在进入理性的领域而消解,被理性这个目的辖制。而要保持这个目的,就是需要一定的仪式,并赋予这仪式以光环。但仪式作为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必须以想象建构起来,使其充满意义。所以,这就是“我”和雷蒙德成天成夜想象的事情,对成年那个领域的自我建构。正如有论者所言,这个领域充满着“男性气质”,是男性霸权的显现,也正是其导致主人公和雷蒙德误入歧途。(20)邱枫:《男性气质与性别政治———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家庭制造>》,《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传统成长小说正是与启蒙理性,以及男性中心主义结合在一起诞生的产物,而其背后所隐含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昭然若揭。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麦克尤恩用以揭露这个成人仪式虚幻的过程和方式,也就是以游戏来揭示。一般社会学的观点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在幼年期间的游戏都是对于成年规则的提前学习,因而相对于其目的而言,游戏也就意味着自身的缺乏和不足,意味着自身只是未来更加成熟和严肃规则的预备和补充。所以,游戏也被认为是不认真的,随意的。而作为成长小说的结构而言,游戏显然是“天真”时期的一个表征,成长也就意味着摆脱这种不认真的、随意的状态,进入到成熟和严肃的理性状态。但实际上,游戏并不是没有规则的和不严肃的,任何游戏都有规则和违反规则的处理方式。例如,故事里的捉迷藏游戏以及“过家家”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来判定输赢或者像与不像。但这一点也是游戏被贬低的原因,因为它被认为是摹仿的,而不是自足的。游戏不是实际现实的行为,不产生任何实际效用,它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假定一系列的规则,这些规则却不具备合法性。因此,游戏正是这样介于规则和无规则、合法和不合法、严肃和不严肃之间的行为。而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的可重复性——“有一种可能的游戏,它有规则性的差异和解释性的变化。但这种游戏没有可重复性将是不可能的,它既重复相同的事物,又通过重复自身引向我们在法语中称之为jeu(21)“游戏”“赠与”。的东西。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玩耍,而是在组织成分的间隔中运作和连接——就是为历史说话,无论好坏。”(22)J.Derrida, Acts ofLiterature,ed, Derek Attridge,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1992, p.64. 此译文中“游戏”一词的英文原文为“play”,这个词很重要,具体是指“符号的差异运作”,参见肖锦龙:《解构理论“自由游戏”论辨伪》,《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文中之所以译为“游戏”,一是为了契合文中论旨,二是有解构理论所谓“旧词新用”的意思。游戏即使输了,结束了,也可以重新开始。它对任何人、任何时间和地点开放,它可以无限地重复这一游戏的过程,在其中重复成人的行为,又重复自身,从而在规则的差异之间运作和引起变化。以上两点正是游戏的本质和它作为补充对于所谓严肃的成人世界危险的地方。
正如上文所言,成长小说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依靠仪式所划分的二元结构,在这个结构里,两者有着清楚的界限,并以成人的世界为主导。而成人的世界意味着它是严肃的,合法的,能够产生实际效用的。可以说,对于儿童的游戏世界,成人世界里任何行为都类似仪式。在这一点上,游戏和仪式之间的关系就像德里达的“文学行为”和奥斯汀以言做事的“施为句”之间的关系。游戏可以不断重复这一成人世界的“元话语”,重复成长小说里的成长仪式:“认真的‘行为句’的可能性依赖于表演行为的可能性,因为行为句所依赖的可重复性明显地显现在表演行为之中。诚如奥斯丁通过表明叙述句是行为句一个特殊例子,颠倒了他的前人的等级分明的二元对立,我们也可以通过表明他所谓的‘认真的’行为句只是表演行为的一个特殊例子,从而颠倒奥斯汀所设立的认真和寄生之间的二元对立。”(23)[美]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故事里自认为已经成熟并渴望成熟的主人公之所以害怕“游戏”,不仅是因为它幼稚,而且是因为“过家家”这种游戏采用的是与家庭成年关系同样的形式,它的不断重复性将使从他想象里建构起来的带着光环的成人仪式都耗尽自身的效力和严肃性,从而显现自身的虚构性。这才是渴望成熟,渴望“男子气”的主人公害怕的“过家家”的根本原因。因为,游戏混淆了认真与不认真,成长和幼稚,以及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既建构也解构了他心中渴望的赋予他“男子气”的成长仪式。
在小说最后,主人公“我”虽然借由游戏来进入成人世界,但也感受到游戏所暴露出的成人仪式的虚幻:“明天我会告诉雷蒙德忘掉和露露的约会,除非他想一个人去。我知道的是他根本不会想那么做。”(24)[英] 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第57页。如果不是仪式的光环感,实际上他们并不想那么去做,所以不是游戏给了“我”以动力和机会去“谎言,欺骗,羞辱,乱伦”,而是它揭开了这个“男子气”的、“理性”的仪式对儿童的不好影响。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我”在逃避游戏的同时,最终却不得不陷入到在游戏里开始自己的成人仪式,不过表明了仪式与游戏本身就不可分,它们既是促使,也是揭露;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所以,也不是说“我”误把游戏与成人的世界混淆在一起才导致“我”这种畸变的行为,而是在游戏里本来就含有成人的阴影,而成人的世界也有着游戏的一面。这种混淆不过是揭露出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像乱伦等禁忌本身具有双重性。
从“游戏”的角度来看,短篇小说《化装》和长篇小说《水泥花园》都从不同层次对这一解构行为进行了重复和表演。在《化装》里,正是“化装舞会”这一游戏的舞台揭开了亨利眼中成人世界虚伪、罪恶的面貌。而《水泥花园》则近乎是《家庭制造》这个短篇小说的扩充,在其中,“我”、朱莉和苏之间同样借由检查外星标本的名义来进行着乱伦的性行为,并在父母死亡之后扮演着现实版的“过家家”的游戏。对于他们而言,这些“过家家”的家庭游戏不再仅是游戏,而是成为他们互相行使和争夺权力的欲望领地。但如果仅仅把这些禁忌的故事当作没有成人指导的儿童时期的迷误,那就没有看到这些儿童身上暴露的恰恰是成人的影子,是成人世界种种道德问题留给他们的阴影。他们之所以产生这么畸形的行为和心理,不仅是因为他们是儿童,不守规矩,心智不成熟,还是因为他们太想早点成为大人了,以权力来辖制游戏,因而被那些带有光环的成人仪式和规则所迷惑,走上歧路。因而,这些关乎儿童成长的故事其本质则是关乎儿童与他们心中成人观念的故事,也是关乎成人的道德寓言,关乎那些成人世界里的种种规则和意识的反思。正如在《水泥花园》里想要假装成大人的杰克对德里克的车子质疑:“我不喜欢把车漆成红色,搞得它们就像是玩具。”对此,德里克则非常平静地回答:“等你再大一点你就会意识到它们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本来就是玩具,昂贵的玩具。”(25)[英] 伊恩·麦克尤恩:《水泥花园》,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这些成人的仪式本来也就是这么回事,本来就是游戏,昂贵的游戏。但这并不是说,儿童与成人毫无区别,因而不需要成人的指导而走向成长,而是说在成长中,儿童不应该把成人当作一个完全外在于自身的仪式,或者一个权力的象征,而是应该当做自身的一部分,当做自身内部自然而然发生的游戏事件。
三、对“儿童”游戏的解构
如果说在上述几部小说中,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成人仪式导致了儿童成为了成人的附属品,使儿童在从“天真”踏入“经验”的世界的过程中因为对仪式光环和权力的过分渴望,而产生了心理的扭曲和畸变,那么《时间中的孩子》所展示的则是从这种二元对立本身出发的成人把重心过分放在“儿童”身上所造成的迷误。因而,上面分析的是在儿童的成长中需要什么样的成人观念,而这里想要表达的则是成人该追寻什么样的儿童观念来使自身走向成长。
在《时间中的孩子》里,对“儿童”的看法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政府编写的《官方育儿手册》为代表,它意味着孩子的本性是自私的,童年和疾病相似,因而儿童需要接受成人社会的教育和规训,以使他们走向社会。这类观点正如上文所分析,它把儿童当作了成人世界的预备和补充,当作其有些累赘但却无法摆脱的附属品。这与启蒙时代出现的传统成长小说在理念上如出一辙。而与此针锋相对的是处在这场“育儿运动”中心的政治家查尔斯。查尔斯既对成人世界的权势和金钱充满欲望,又渴望回到自由、安全的童年时代。在查尔斯的儿童观里,儿童恰恰是自由自在的、完美无缺的象征,与《官方育儿手册》所表露的观点完全相悖。这种观点也是所谓浪漫主义时期所建立的儿童观,它恰恰是对启蒙运动时期所出现的成长小说中理念的一种反驳。(26)程心:《“时间中的孩子”和想象中的童年——兼谈伊恩·麦克尤恩的转型》,《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2期。正如华兹华斯的“孩子是成年的父亲”式的浪漫主义宣言,它不仅仅是对“自然”的复归,而且是对启蒙时代那种设定后天理性目的的反驳。而卢梭的《爱弥儿》也是异曲同工的道理,都是要对后天的理性约束和成人世界的种种仪式和规则进行批判。从这个角度而言,对纯真儿童的学习和模仿反倒成了文明社会里的成人需要再度历练和成熟的仪式。也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不可调节的处境里,查尔斯选择了以死亡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以保全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各自互不干扰。
以上两种“儿童”观念显然都是不合理的,它们都是成人对儿童的想象建构,各自以互相对抗和压制的方式来解决矛盾,而不能跳出二元对立的逻辑,最终只能走向更尖锐的困境,无法在儿童和成人之间找到真正和谐相处的出路。除此之外,在《时间中的孩子》里还存在第三种儿童观,它体现在儿童作家斯蒂芬的身上。早在斯蒂芬误打误撞写出并因此成名的儿童书《柠檬汽水》时,查尔斯就对此表达出“成人小说和儿童小说的区别本身就是虚假的……孩子心中早期的成人,和成人心中被遗忘的孩子”的观点。(27)[英] 伊恩·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何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5页。但这一点对于斯蒂芬而言是不自觉的,而对查尔斯而言是自知而不可调节的。因为在查尔斯的心中,孩子与成人事实上完全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他所谓的成人与儿童没有区别,要为成人找回遗忘的孩子,其实就是要成人再次成为孩子,而不是为了寻求两者间真正的相处方式。对于查尔斯的自觉而言,是女儿凯特的失踪才使斯蒂芬发现以往那些无知无觉的时间重新显露出其刻骨铭心,不可挽回的本质。最开始,斯蒂芬的做法是想方设法找寻关于女儿的一切,而当这一切都徒劳无果之后,他就开始逃避现实中的种种责任,沉溺于女儿生活的房间,企图靠着过往的生活细节和回忆来再现这一遗失的过去,但却只能以无望告终。事实上,不是凯特失踪才使时间发生变化,而是时间本身就是如此,遗失就是时间的显现和被感知的方式。因而,失踪这个事件的出现从一开始就喻示了“时间”是不可挽回的,那个纯真的凯特,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是根本不可能再现的。斯蒂芬的孩子失踪事件正是一个契机,一个重新思考孩子与成人之间关系的契机。也正是在这个角度,这本书并不是关于孩子的书,而是关于“成年人心中的孩子”的书。(28)PeterChild, ed, TheFictionofIanMcEwan, Basingstr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p.65.
事实上,以上几种“儿童”观念都离不开与“成人”观念的关系,它们正是为彼此各自的定义所定义。所以,“儿童”的观念反过来也喻示了相对的“成人”观念。在斯蒂芬企图寻回失去的凯特的同时,查尔斯已经为斯蒂芬作了反例,他在完全拒绝成人世界遁于游戏的孩童世界后,只能选择自杀。正如上述所言,游戏与仪式之间不是二元分离、毫无关系的事物,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如果以孤立的观点看待两者,要么屈服于成年仪式的光环下,要么为了消解这些束缚的仪式而逃避到儿童的游戏世界里。在查尔斯的隐居生活里,游戏正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也是他企图寻回儿童时光的最好仪式,使他体验到一个全新的自我。在这里,游戏也成了同样带有光环的仪式,它同样也就不可能达到查尔斯心目中理想化的纯真境界,因而查尔斯不可调节的死亡也喻示了他企图挽回的童年时光根本是不可能的。这种纯真的童年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追忆,它的源头只能是遗失和欠缺本身。
与此相对,斯蒂芬最终经由查尔斯的死亡逐渐洞察了这一道理——回到过去,以游戏代替仪式,以儿童代替成年的世界始终是件不可能的事。时间的缺失并不是面向过去,并不是企图再现过去就能够挽回的,这其实并不能改变时间仍然在逝去的事实,也无法填补时间在源头就已然缺乏的事实。在这里,时间本身,或者说童年本身就无疑是一种创伤的形式,它不是完全来自于对过去之事的恐惧,而是来自于对未来仍可能出现的恐惧。(29)Ilai Rowner, The Event: Literature and Theory,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5,p.115.简而言之,斯蒂芬不是无法面对过去,而是不敢正视现在以及未来凯特不在身边的事实。因此,面对创伤的最好办法,不是企图重现过去进行修改,而是承认过去欠缺这一事实,并积极地面对未来,从未来迎回丢失的孩子。丢失的儿童,或是丢失的时间,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未来,始终伴随着成人的世界,从未来迎向自身,是他需要不断面对的事物。因此,创伤的意义不在于故去的欠缺永远不可弥补,而在于这欠缺是镶嵌在现在和未来之中的事物,在于它始终预告着未来的可能性。在这里,仪式不再是仅此一次的事件,不再是一个决定性的、独一无二的宣告,而是不断重复的事件,不断重复的游戏。正因为其可不断重复,那丢失的时间和时间中的孩子才可能再次降临。只有承认其不可挽回的缺失,以开放的态度迎向未来,接受他者,才恰恰是弥合儿童与成年的可能性所在。正是如此,在故事的结尾,斯蒂芬和妻子终于正视了过去的不可再现,重新组成了家庭,并在再次孕育的孩子中找到了希望,找到了时间的意义——“童年似乎以一种永恒的现在时态而存在”。(30)Ian McEwan, Conversations with Ian McEwan, ed, Ryan Roberts,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0,p.81.
在此,《时间中的孩子》不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童年作为遗失之物永远不能被原初再现,但它却以这种欠缺的状态永远与人相伴,永远镶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人不应把童年当作与现在区分开来的过去之物,不应把它当作与现在毫无联系的完全逝去之物,这样人永远不可能走出迷途。相反,应该把欠缺的童年当作伴随着成人一生的事情,只有把童年纳入到自我之中,一个人才能成长。简而言之,成长不是向童年告别,也不是企图完全回到童年,而是在未来中对这依然欠缺的童年敞开自身的可能性。这两者实际并不是相悖的事物,而是要学会互相理解和沟通,才能够促使“成长”发生。
四、结语
“成长小说”的英文名称一般为Initiation Story,其中Initiation 有“起始”“进入”的意思。麦克尤恩的第一部作品《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其英文名称就为FirstLove,LastRites。在此,仪式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对于最初的爱情的最终结束,这两个词的并列不是对立的,也不是线性时间上的,而是互相重复的。在最初中就已经包含了最后的意思,而只有经历过了最后的仪式才能领悟最初的意义。麦克尤恩在其早期反映儿童和青少年成长的小说里同样展示了如此互相重叠的逻辑,不仅对隐含理性中心主义的成长模式提出质疑,也塑造了建立在互相理解和沟通基础上的成长故事。回顾以往的西方成长小说的叙事结构,麦克尤恩对于“成长”的理解不仅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路有相似之处,(31)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李杨,李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展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独特特征,也为当代社会的人们在面对“成长”的困惑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