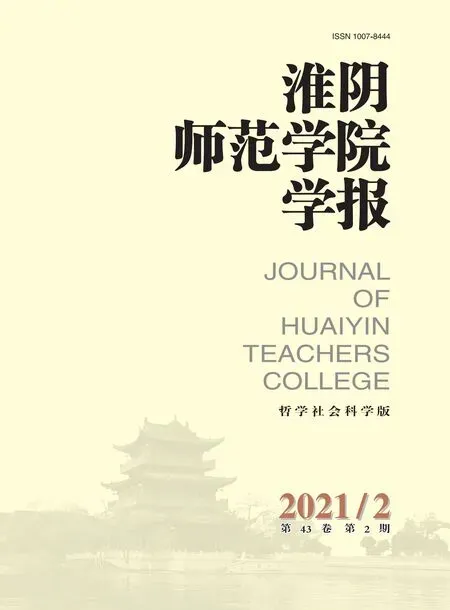重大疫情防控中披露涉疫人员信息的法治遵循
郭兴利, 孟 立
(淮阴师范学院 法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迫使中国卷入一场全民抗疫的斗争中。正是基于疫情信息的及时有效披露,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个人信息被随意披露曾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深担忧。超过7 000名的武汉返乡人员的个人姓名、手机号、详细家庭住址、车票航班信息,甚至他们的身份证号码、车牌号等信息被泄漏至网络广泛传播[1],使他们背负巨大的精神压力。
基于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既能保证涉疫信息及时有效披露以提升重大疫情的防控效率,又能防范个人信息被随意披露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我们指明了思考的方向,即“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2]。可见,重大疫情防控中的个人信息披露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才能解决疫情信息披露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内在矛盾,更好地促进重大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
一、重大疫情防控中披露涉疫人员信息的正当性
重大疫情防控关涉公众生命健康、关乎社会稳定、影响国家安全,需要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在重大疫情发生后,涉疫人员的个人信息披露对疫情的有效防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世界各国均对涉疫人员的部分个人信息予以强制披露,这尽管克减了涉疫人员的部分权利,但却具有正当性。
(一)披露涉疫人员信息符合权利无害行使原则
疫情信息的披露牵涉到个人信息权利的自由享有和自主行使。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3]。每个人在行使自身的个人信息权利时,应当以对他人无害为原则。我国《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重大疫情发生后,尽管法律最大限度保障社会成员的个人信息权,但这种保障是以无害为标准和限度的。其一,个人信息权的自由行使对其他社会成员应当具有无害性。当社会成员行使个人信息权损害到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其他合法权利时,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规定,政府部门有权披露包含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等人员的行踪信息在内的个人信息。其二,个人信息权的自由行使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应具有无害性。为了保护或促进某种重要的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可以对个人信息权的自由行使进行干预。重大疫情发生后,社会公共安全关系着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因而成了这一特殊时期最大的公共利益。政府披露涉疫人员的部分个人信息,是为了提升防控疫情的效率,促进社会公共安全,最大限度地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权。
(二)披露涉疫人员信息契合有效防控疫情的需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实践表明,正是由于疫情信息披露及时、精准,才使我们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即取得了这场大规模疫情防控的决定性胜利。首先,信息披露是控制疫情传播、排除潜在风险的必要环节。想要及时有效地控制疫情传播,就必须及时有效地进行信息披露。否则,社会公众难以及时发现周围的病例,这将会导致疫情蔓延,甚至失控。同时,信息披露有助于及时切断疫情传播途径,排除潜在风险。其次,信息披露是提升防控意识、消除恐慌情绪的重要途径。疫情信息的及时有效披露,有助于警示周围群众加强防范。如果不及时有效披露,社会公众就会陷入恐慌。最后,信息披露是减轻工作负担、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措施。疫情信息的及时有效披露,可以避免漫无目标、全方位、大面积的布控,避免浪费人力物力;有利于政府精准施策、重点防控,集中优势兵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还可以大幅提升行政效率,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披露涉疫人员信息利于公众知情权的实现
何谓“公众知情权”?学界一般认为,公众知情权是指公众对国家事务、社会信息有知悉的权利,可分为知政权与社会知情权[4]。本文所指公众知情权,是社会公众对疫情信息的了解权,属于社会知情权的范畴。与平常状态下的知情权相比,重大疫情时期的公众知情权应当获得更多关注和保护。这是因为,重大疫情发生后,公众基于自身生命健康安全的考虑,对其周围有无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症状感染者等信息产生了强烈诉求,希望能在第一时间了解自身所处环境的危险程度,以便采取针对性防范措施以避免自身被感染。因此,重大疫情时期的公众知情权不仅仅是一种民主权利诉求,而是升级为对公民生命健康权这种基本权利的诉求。在现代社会,政府存在的根本意义是维护公众利益,让公众拥有适合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重大疫情发生后,政府理应扛起疫情防控的责任,有义务让公众知晓自身所处环境的安全程度。这既是保障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也是动员广大公众加强自身防范和共同参与疫情防控的需要。
二、重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披露的乱象及其危害
(一)典型案例及其所揭示的乱象
如前所述,重大疫情防控中披露涉疫人员的个人信息是必要且正当的。但是,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个人信息被随意披露及其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也值得我们深思,试结合几则典型案例予以阐释。
案例1:据舟山公安机关2020年1月26日发布的《警情通报》,该市本地微信群传播的一份武汉返乡人员排查表系社区一工作人员将内部资料发给其丈夫张某,张某随后将该资料转发至其单位微信群,从而导致武汉返乡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详细家庭住址、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被泄露。最终,张某因侵犯他人隐私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其他涉事人员被移交纪检部门予以处理。[5]
案例2:2020年1月28日,湖南益阳一些小区的业主微信群中出现了一份《关于益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报告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调查报告》的电子版内容及其截图,其内容关涉到章某及其亲属共11人的姓名、具体家庭住址等个人隐私信息。相关部门调查后发现,这次信息泄露系该市赫山区的卫生健康局副局长舒某将信息通过微信转发给他人所致。舒某被予以党纪立案调查。[6]
案例3:2020年2月3日,文山州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文某、谢某、关某利用工作便利,将该医院电脑中记录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个人信息私自拍照后上传至微信群,致使这些患者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详细住址、行程轨迹、所接触的人员以及诊疗信息等在网络空间被公开传播,严重影响到患者家庭的生活安宁,也造成所在小区其他住户的高度恐慌。他们的行为因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被文山市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7]
上述三个典型案例集中反映了重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披露的乱象,体现在:其一,披露信息的主体违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披露;地方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由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披露。对照上述法律规定,无论是案例1中的社区工作人员,还是案例2中的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抑或是案例3中的医院工作人员,都不是合法的信息披露的主体。其二,披露信息所涉对象违法。在上述典型案例中,披露信息所涉对象有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患者所接触的人员、武汉返乡人员等。其中,武汉返乡人员和患者所接触的人员,并非《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规定的涉疫人员。其三,披露信息的内容违法。在上述典型案例中,披露内容涉及披露对象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详细住址、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行程轨迹,以及诊疗信息等,其中姓名、工作单位、家庭详细住址、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的披露,与新冠肺炎疫情并无直接关系,对重大疫情的防控也无实质性意义;相反,由于这些信息涉及个人隐私,这样的披露行为明显违背了《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有关保护公民隐私的规定,属于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
(二)违法信息披露所造成的危害
1.侵犯公民合法权利。上述疫情披露中的违法行为,极易侵犯被披露对象的合法权利,影响其本人和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第1034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第1039条和第1226条则规定,“国家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均不得违法披露相对人或者患者的个人信息。在疫情发生初期,如果说部分社会成员出于对疫情的极度恐惧,不当披露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个人信息,尚属“情有可原”。但是,对只是来自疫区人员信息的过度披露,则会给其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例如,2020年1月12日,在武汉上学的大学生琪琪回家之后,相关部门致电要求她提供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及与她密切接触的家人的全部详细信息。这些信息在小区微信群、楼栋微信群、众多微信公众号,乃至一些陌生人的朋友圈,被公开传播。同小区或同栋楼的许多邻居对她恶语相向、避犹不及,其全家人的生活都遭受严重影响。[8]在疫情防控已经常态化的情形下,如果仍然过度披露上述个人信息,则不仅侵害当事人的隐私权,还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例如,2020年12月9日上午,成都确诊患者赵某被迫多次发文,“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攻击我,我只是不小心感染了新冠,我也是一个受害者”。为此,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说:“要注意保护患者隐私,做好群众心理疏导,坚决制止网络暴力,营造良好的疫情防控氛围。”[9]
2.引起社会公众恐慌。首先,涉疫人员信息被违法披露,容易产生网络谣言,从而导致社会公众采取过度的防疫措施,如大量囤积食物和药品;或者产生心理压力,加剧焦虑情绪。其次,如果多个主体发布相互矛盾的信息,还可能导致信息混乱。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威胁性和不易控制性,本已使人们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混乱的信息发布,则使得民众更担心自己被感染,并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有的人过度服用药物,身心健康因此受损。第三,过度披露患者及其家属的信息,也可能导致社会恐慌。疫情期间,社会公众高度渴望获取周围信息,以便了解自身是否安全。而夸大的信息披露,则增加了人们心中的不安,进而导致社会恐慌。
3.妨碍政府依法行政。首先,不实信息披露会破坏政府公信力。不实信息的披露一旦形成“塔西佗效应”(1)“塔西佗效应”又称“塔西佗陷阱”,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而得名,一般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不论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那么,无论政府说什么,民众都将不再相信,从而破坏政府的公信力。其次,多头披露或者随意披露,会造成谣言盛行。此时,政府不得不站出来辟谣,无形之中增加了执法成本,进而影响疫情防控的效果。第三,可能导致公众不再配合政府的防控要求,影响疫情防控的效果,甚至阻碍应急管理和行政执法目标的实现。
三、重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披露的法治要求
为了避免上述乱象的发生,必须遵循法治的基本准则,以保证重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披露的有序进行。
(一)合法披露: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
合法披露是疫情信息披露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主体合法、权限合法、内容合法和程序合法。
主体合法是指实施疫情信息披露的机构必须是依法设立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常见的不符合这一要求的情形有以下几种:不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机构、非法设立的行政机构、已经撤销的行政机关、非公务员的人、身份终止的公务员、以自己名义行使职权的受委托组织、没有法律授权却以自己名义行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与派出机构等[10]。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为合法的疫情信息披露主体。除此之外,其他组织和个人均不得随意披露疫情信息。
权限合法是指行政主体必须在权限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实施行政行为,具体要求是行政主体职权的来源和范围符合法律的规定。[11]在疫情信息披露权限方面,依照法律规定,地方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披露信息须经授权且有范围限制。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地方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需要经过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授权才能披露疫情信息,并且只能披露本行政区域内的疫情信息,不能越权披露本行政区域外的疫情信息。跨行政区域的疫情信息应由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披露。
内容合法是指行政行为中相关的权利义务合法,具体指与行政行为相关的权利义务具体、可实现、可预测、受社会认同。[12]疫情信息披露内容合法的要求是:首先,披露的信息应当限定在法定的内容范围内。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第32条的规定,传染病疫情的发布内容包括传染病疫情性质、原因、发生地及范围、发病和伤亡及涉及的人员范围、疫情处理措施和控制情况、疫情发生地的解除等。其次,法定范围外的信息不得作为疫情信息随意披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部分有权主体向社会公布确诊病例的信息超出了法定授权范围。例如,部分地方的卫健委曾在披露患者信息时公布了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居住地、就诊医院、车牌号等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在法定授权范围内。最后,披露的信息应当有助于疫情防控和维护社会秩序。有些信息如果分开发布,风险相对可控,但同时发布这些可以关联到同一个病人的信息,就很容易让他人锁定到患者本人,其效果接近于实名发布[13],可能使患者及其家属遭受骚扰、歧视、谩骂甚至人身伤害,给其生活造成诸多不良影响。
程序合法是指行政行为须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即行政行为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顺序、期限、附款。[14]疫情信息披露须遵循法定程序,其要求包括:第一,疫情信息在披露前应当经过脱敏程序,即将涉及公民隐私权的个人信息进行去识别化处理,避免披露的个人信息中包含身份信息、详细家庭住址、手机号码等隐私信息;第二,疫情信息在披露前须经由有权披露部门的负责人审核签字,以确保所披露信息的准确合法;第三,疫情信息披露应当通过恰当的方式,如通过官方网站或报纸等予以披露;第四,疫情信息披露后应当加强监管,防范所披露的信息被随意更改,并对被披露对象或者社会公众所指出的披露错误予以纠正。
(二)合理披露:行政法治的必要补充
合理披露是一个涉及“合理行政”的问题。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规定,“合理行政”要求:政府部门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符合法律目的;所采取的措施与手段应具有必要性、适当性;在采取多种方式均可以实现行政目的时,应尽量避免采取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这一规定提出了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原则。重大疫情防控中涉疫人员有关信息的披露,也应遵循这三个原则。
适当性原则要求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实质的关联性,以充分保障人权,减少行政行为的恣意,促进行政者不断反思手段的合目的性。[15]重大疫情防控中披露涉疫人员有关信息也应基于疫情防控的目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披露信息前,应当进行合目的性判断,只有在不得不通过披露信息达成有效防控疫情的目的时,才能决定进行有关信息披露。
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损害原则,指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手段须具有必要性。它需要政府部门首先确定各个手段的损害大小,然后再对这些不同的、具有适当性的手段进行比较分析,以最终挑选出一个最小损害的手段。[16]在重大疫情防控中,政府部门收集到的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症状感染者的信息十分广泛。政府部门在披露有关信息前,必须作必要性审视。其要求是:既能达到防控疫情的目的,又要保障被披露的个人信息限制在最小范围内。深圳市在披露新冠肺炎患者的行踪信息时,只是披露患者曾经逗留过的小区、超市等公共场所,而将患者住所的具体门牌号码隐去。这就遵循了必要性原则,成为当时披露新冠肺炎患者个人信息的典范,随后被广东其他地市以及其他省份的政府部门借鉴[17]。
均衡性原则要求公权力行为增进的公共利益与其造成的损害成比例,要求公权力行为者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同时,认真对待公民权利,审慎权衡相关利益,以保护权利不被过度侵害。[18]政府部门在重大疫情防控中进行信息披露,必须遵循均衡性原则,只有在披露涉疫人员个人信息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大于给被披露对象的个人信息权利所造成的损害时,才能实施披露。例如,央视新闻在评论成都确诊女孩信息遭泄露时提到,不论她是否需要为疫情传播承担责任,这都不是曝光其个人信息的理由,“她的个人生活不该是公共话题,防疫才是”[9]。
(三)正当披露:行政法治的价值追求
重大疫情防控中的信息披露,还应当体现行政法治的价值取向,即正当披露。正当是一个复合概念,其衡量的标准是多方面的。结合重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披露的属性特征,我们认为,正当披露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平等及程序正当三原则。
信息披露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原则。首先,披露程度应与疫情严重程度相适应。不是所有疫情防控都需要具体细致的信息披露,只有在疫情特别重大的时候才需要详尽地披露信息。这是因为,信息披露是一种涉及私权利的公权力行使行为,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侵犯个人隐私。因此,只有在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不得不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时,才可以披露。即便如此,个人隐私仍然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其次,披露程度应与相对人的情况相适应。在疫情信息披露中,相对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等词汇频繁出现在疫情数据报告中。对于不同的相对人,如果都以同一个标准来披露信息,势必会导致对一部分人的信息的不合理披露。因此,信息披露程度应当与相对人情况相适应。最后,披露方式应与当地的情况相适应。疫情重点地区和非重点地区的风险程度不同,因此非重点地区的疫情信息披露方式不应与重点地区完全相同,而应当“温和”一些。例如,城市与乡村的情况不同,城市信息披露的方式不一定都适用于乡村地区。又如,少数民族地区的披露应适当考虑当地的风俗习惯,以便维护民族团结。
信息披露应当遵循平等原则。平等原则是指同等情况的行政相对人应该得到行政机关的同等对待,避免其遭受到歧视和不公[19]。在疫情信息披露中,披露机关应平等对待相对人。首先,不得对相对人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不能根据关系亲疏或地位高低选择是否披露或如何披露相对人的信息,不能因为亲戚朋友、上级领导等关系而少披露甚至不披露;也不能因为厌恶、仇恨等心理多披露。选择性披露行为背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严重损害了行政机关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应对其加以规制。其次,不得歧视信息披露中涉及疫情的相对人。在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披露中,发生了部分确诊患者及其家属因个人信息泄露遭到恶毒谩骂[20],一些与确诊患者同小区的居民外出办事时被当成“疫区”居民对待[21]等不公平现象。这些现象说明,如果在信息披露中歧视涉疫相对人,就可能引发一系列损害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因此,疫情披露有关工作人员应平等对待信息披露中涉及疫情的相对人。最后,对待涉及疫情的不同相对人的披露方式和后续措施应当一致。原则上,不应区别对待,更不能一个比一个严格。
信息披露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随着政府权力持续地剧烈增长,只有借助于程序公正,权力才有可能获得容忍。”[22]重大疫情防控中政府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披露相关个人信息是十分必要的,但公共利益的维护也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即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保障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首先,保障相对人的知情权。这主要体现在个人信息的收集阶段。行政机关应当向被收集对象说明收集的法律依据、使用目的、救济方式等,以避免被收集个人信息的对象担心自己个人信息去向不明或被不法利用所带来的恐惧。其次,保障相对人的参与权。被披露对象有权参与到信息披露中来,在个人信息被披露前,有权要求政府部门隐去自己的真实姓名、详细住址、身份证号码等识别性较强的敏感信息;在个人信息被披露后,相对人如果发现政府部门披露的个人信息有误或者涉及隐私,有权请求政府部门予以更正。最后,保障相对人的救济权。相对人在其个人信息被违法披露时,有权通过举报、投诉等方式获得救济,并要求政府部门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四、结语
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披露的得失,我们发现,“法治”是重大疫情防控中“各项工作的出发点与总基调”,只有遵循法治的精神和准则,才能保障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各级政府公务人员法治意识的提升,北京、上海等地的流调报告悄然发生了变化:新增确诊病例流调报告中隐去了病例的性别、年龄、籍贯等个人信息,而是以病例涉及区域和场所的信息披露为主。这种“只提轨迹不提人”的方式,不仅保障了公众知情权,更体现了对个人隐私的尊重[23]。我们相信,只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及普通公民都能遵循法治原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信息披露和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矛盾就能有效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