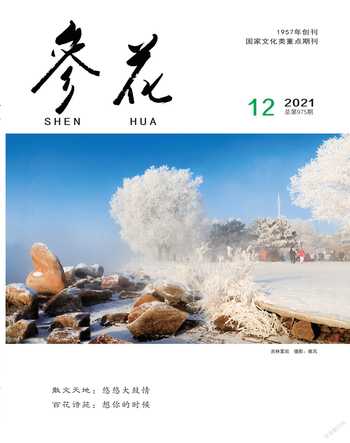人文与经济:乡土叙事的两个视角
摘要:当现代化进程不可阻挡地进入到乡土中国时,废名和茅盾没有像乡土写实派作家一样,去挖掘乡土世界中的精神创伤和文化专制。《竹林的故事》与《春蚕》一则从文化审美和文化建构的意义上抒写美好的乡风人情、原始遗风,一则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客观展示农村经济破产的全过程。人文与经济,两个乡土叙事的角度对于今天倡导乡村振兴仍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废名 茅盾 乡土叙事
无论从哪方面看,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与茅盾的《春蚕》都不具有可比较性,目前学界也鲜有这样的比较。从发表时间来看,二者前后相差七年;从立意到风格,两篇文章也是大相径庭。就拿作者与农村的联系来说,茅盾直言,“我不敢冒充是农家子”“我幼年的环境就是这样与农村无缘的”。据眉睫的考证,废名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部贯穿着家乡的消息,其早期小说具有很浓的自传色彩。眉睫曾走访废名老家冯家大宅的对门人家,有余氏老者,说护城河外以前有竹林,有坝,坝脚下是竹林。有一妇人在竹林边开垦菜园,以卖菜为生。她叫刘香桂,解放初去世。他认为此人即是《竹林的故事》三姑娘的原型。
一般认为,新文学的乡土抒情诗式小说发端于废名,大成于沈从文。“五四”文学倡导“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这种“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既“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又是孔孟“本来的礼与本来的中庸的复兴”。在文学取向上,追求远离十字街头,把艺术塔建在街头角楼上。
《春蚕》则是中国现代社会分析小说的先声,茅盾是较早将社会科学理论运用在农村题材的作家之一。在废名与茅盾之间,占据上世纪20年代乡村叙事的主流,是以王鲁彦、彭家煌、许杰等为代表的乡土写实派。杨义曾形象地比喻:“乡土写实派是家门的叛徒,愤愤地张扬着‘家丑’以图革故鼎新;乡土抒情派是家门的隐逸子孙,赏玩着家珍,以求得心灵的慰藉。”
一、启蒙主义立场的偏移
不同于鄉土写实派以启蒙主义立场,聚焦封建宗法制各种弊端,揭示人在宗法秩序下的生存状态,批判封建性的农村社会关系,《竹林的故事》与《春蚕》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家族专制的乡村叙事。一则从文化审美和文化建构的意义上抒写美好的乡风人情、原始遗风,一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客观展示了农村经济破产的全过程。这是两部作品最大的相通之处,也是二者具备可比较性的基本前提。
对于中国农村而言,“中国农民不是各自独居的,而是聚居在村落里。这种模式的形成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亲属的联系和互相保护的需要。在中国,兄弟平均继承父亲的土地,家庭就会开垦扩展土地,几代之后就可以发展成一个小的同姓村落。亲属的联系也使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显然,《竹林的故事》与《春蚕》中所描绘的乡村都呈现出某种异质性。
《竹林的故事》中,老程一家三口人独居在竹林里,他们并不从事春耕秋收的粮食生产活动,维持生计的手段是种菜、卖菜、打鱼、卖鱼。“种菜又打鱼”的老汉,洗衣喂鸡的少女,“绿团团的坡”和“一天一天的绿得可爱”的菜园……同样的一片乡土,传统乡村的宗族律法、地缘血缘被淡化,人文视野下“陶渊明”式的和谐田园被凸显,这正是废名审美情感的自然投射。
《春蚕》中老通宝一家“育蚕缫丝”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事活动,而属于“乡土工业”,并与经济全球化密切关联。老通宝祖辈的发家史正得益于国际生丝价格的上涨,其后出现“丰收成灾”的现象,根源就在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这是闭塞于杭嘉一隅的老通宝所未曾阅历的。也是因为“养蚕缫丝”这一活动,老通宝一户与“村里二三十人家”之间不再是错综复杂的宗法关系,而是在经济层面上实现了同质化。
二、人文主义的乡土想象与经济主题的全景呈现
当现代化进程不可阻挡地进入到乡土中国时,尽管废名和茅盾都没有像乡土写实派作家一样,去挖掘乡土世界中的精神创伤和文化专制,但两个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废名以人文主义为向度表达乡土作为精神家园的文学想象,茅盾则是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发直面乡土中国的现代命运。
写作《竹林的故事》时,废名还未表现出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清醒的反思,他曾在《莫须有先生传》中直陈:“我这回坐飞机以后,发生一个很大的感想,即机器与人类的幸福问题。”“机械发达的国家,机械未必是幸福。”早期创作中,废名更多是以一种亲切、柔情的目光对视传统、回望乡村,而憎恶人工文化对自然状态的人情美的干涉。《竹林的故事》里,小河、竹林、茅屋、菜园构成了一幅清幽古朴的山村图;老程一家的劳作、亲人间的互动、与邻里乡人的交往都渗透着东方情感所特有的温柔敦厚。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意境美、性灵美、天人合一、超脱功利的审美理想,它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逸情结。
废名也在小说中尽可能地规避任何可能打破这种古典情怀和审美理想的情节。全篇没有外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没有情感的激变与伪饰,只在乡土的一角平静地展示着乡村人物的生死苦乐,内蕴着道法自然的禅境。对于老程之死,废名没有大肆渲染悲情,仅以“绿团团的山坡上,从此也不见了老程的踪迹”“戒尺一般的土堆”,便将生者的悲痛与哀思隐去。“赛龙灯”的情节,母女俩因为彼此想着对方而轻微地争执着,把日常生活中的摩擦写得纯净自然。小说中唯一出现的经济活动,三姑娘卖菜,这场再普通不过的交易活动,却会让在祠堂读书的“我们”产生“简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觉得这太对不起三姑娘了”,整个场景不沾染一丝铜臭味和世俗气息。
茅盾的乡土叙事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一开始就对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抱有深刻的怀疑,对其对中国农村的威胁持批判态度。尽管《春蚕》中也出现了诸如荷花与六宝吵闹,多多头与六宝调情等富有情趣的乡野图景,但主要篇幅还是不出经济范畴。在老通宝的家庭内部,老通宝与四大娘、多多头之间的矛盾,关于蚕种的选择、借贷买桑叶、荷花偷蚕等,无一例外地都属于经济事务。老通宝一家人的情绪也在悬念迭起的养蚕之路中大起大落、焦灼不安:在最初“窝种”时,老通宝用蒜瓣占卜的结果并不吉利,担心蚁蚕不能顺利孵出;在养蚕过程中,老通宝家的蚕房又被“不吉利”的荷花村姑捣乱过,担心蚕宝宝不能顺利生长;在送蚕“上山”时,老通宝一家又担心蚕茧能不能顺利结出来。然而,真正把老通宝一家阻挡在丰收喜悦之外的,却是老通宝从一开始就忽略的细节——茧厂关门。
这里的“茧厂”是具有浓厚的经济意味的意象,茅盾在小说一开头就写到了“茧厂”:“离老通宝坐处不远,一所灰白的楼房蹲在‘塘路’边,那是茧厂。”整个村子都被卷入资本运作的流程之中,只有“育蚕缫丝”经验的农民对此还茫然无知,越是经验丰富越是要栽跟头。农民就这样在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跌入前所未有的困顿中。
三、时间维度的差异立场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
《竹林的故事》中,摒弃了线性进化的叙事时间,以一种自在天然、行至无定的方式安排情节,作者看重的是对每一个生活瞬间的兴味与体悟。这片竹林有的只是自然四季之更迭,而无生命“进化”之痕迹。主人公三姑娘的生命历程也化入周围的翠竹绿水之中,偶起微澜,又很快归于平静,无论是童年、少年,还是成年后,岁月的流逝都不曾改变她纯粹而聪慧的姿态。时间只作为一种背景存在于文本中。
同样,老通宝的时间观也不是直线式,老通宝生活在一个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信奉的是一套老祖宗的“阴历”,四季时令对他们的劳作至关重要。他的时间观如同四季一般周而复始。在老通宝看来,既然春天到了,就该养蚕,蚕结茧之后,茧厂就该收,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因此,他不会顾虑茧厂是否可能受战争影响而关闭,更不会知道经济危机对中国缫丝业的影响。
废名以“万物静观皆自得”守护古典主义审美理想,茅盾以“进化论”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天道轮回观。表面上看,是两人文化立场的不同,本质上也是中西文明的较量。
四、结语
在今天,一些农村依然存在因为乡民不了解市场行情,而造成“春蚕”式的“丰灾”。京派文学所表现的生死超然的宁静诗心,风花雪月的恬淡诗情在李子柒的视频中也隐约可见。如果以生态批评的视域凝视京派乡土文学,其对农耕文明的守望,以自然作为人的生命本源、精神家园以及关注人的自然天性的观念,如今看来,愈发显出前瞻性和生命力。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興过程中,如何让经济利益、人文关怀、村落景观取舍得当,不至于协调失衡,这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
参考文献:
[1]茅盾.我怎样写《春蚕》[J].作文之友,2010(010):31-35.
[2]周作人.生活之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3]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5]废名.莫须有先生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7]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朱小倩,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华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于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