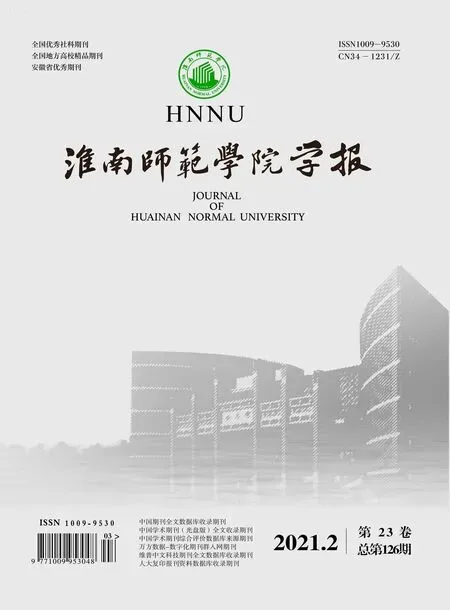“美术革命”与西画“再启蒙”
范本勤
(淮南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近年来,关于“美术革命”这一现代美术史研究命题,不时见诸学界。这一命题的来源,是吕澂与陈独秀1918 年1 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两篇互为通讯的文章——《美术革命》。 学界围绕二人的“美术革命”论之观点与论述的文本,以及其与民国美术(尤其是中国画)的发展走向之关联,展开了史学考据、理论批评、价值判断等多维度的研究。这些研究无疑对于探询民初知识分子的美术观、建构民国美术思想史都是有价值的,但其中有两种思维路径值得商榷:其一,基于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之身份,设想陈的《美术革命》一文(或“美术革命”论)在民初美术发展中的巨大影响力,并且淡化作为专业美术家的吕澂的“美术革命”论之历史作用;其二,基于陈的“革王画的命”“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1](P29)等论调,设想“美术革命”论与写实主义美术、尤其是中国画的写实主义改良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且忽略其与民初西画演进之间的联系。就《美术革命》文本而言,无论是陈独秀的还是吕澂的,都不可高估其在民初美术发展中的作用。但从宏观的文化语境考察,陈、吕两人的“美术革命”论是民初“美术革命”思潮的集中体现,而以“美术革命”论为代表的“美术革命”思潮与民初西画狂飙式的演进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一、《美术革命》与“美术革命”思潮
吕澂的《美术革命》与陈独秀的《美术革命》虽互为通讯,并且同时提出了“美术革命”口号,但通篇看来,两人关注的问题焦点和解决方案是有差异的。首先,从二人关注的主要问题来看:吕澂是以一个美术理论家、教育家的角色审视当时的美术发展现状,尤其是“西画东输”以来的美育问题,认为美术界十分衰败、恶俗,美术教育十分落后。他说:“近年西画东输,学校肄业;美育之说,渐渐流传,乃俗士骛利,无微不至,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似是而非之教授,一知半解之言论,贻害青年。 ”[2](P26-27)陈独秀是以文化批评家的角色,立足于其对“旧学”之“画学”的了解,审视的焦点主要在传统中国画的发展状况, 认为中国画以 “王画”为“画学正宗”,只会“临、摹、仿、橅”[1](P30),早已走进了死胡同。而后,从吕、陈二人对各自问题的解决方案看:吕澂认为,要让美术发展步入正途,首先要进行现代性的美学及美术理论启蒙,并大力实施中外美术史教育,“使此数事尽明, 则社会知美术正途所在, ……而后陋俗之徒不足辟, 美育之效不难期。 ”[2](P27)陈独秀认为,若要改良中国画,“首先要革王画的命”[1](P29),引进西方的“写实主义”。 吕的方案侧重于美育启蒙和艺术本体,而陈的方案侧重于“描写社会”的现实功用。
吕澂和陈独秀都痛感美术的衰败,都疾呼“美术革命”,这种呼喊,并非出于一时的灵感和情绪冲动,而是酝酿已久的心声,如陈所说,是“久欲详论”[1](P29)的。而将吕、陈二人的言论置于时代背景中看, 他们的观点则是时代思潮集中而激烈的体现,美术变革的呼声在知识界和美术界传播已久,只不过,由于《新青年》的媒体效应以及“美术革命”的鲜明口号,让人印象最为深刻而已。从清末到民初,学习西方美术、变革中国画、推行美育,是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诉求——虽然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不尽相同。
早在1905 年,王国维就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说:“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又最无与于当事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3](P1),将美术置于前所未有的位置。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美术一直没有独立的地位,这无疑阻碍了人的发展和文化的昌盛。 王国维所称的“美术”,其实是“艺术”“文艺”之概念,类同于西方的“art”一词所指之范畴,而今人所谓之“美术”,同“fine art”之义——即绘画、雕刻等“造型艺术”。这种混淆,或说使用习惯,在民初知识分子的表述中较常见,不过,确定无疑的是,王国维所谓“美术”是包含“fine art”的,他说,“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时之快乐,绝非南面王之所能易之也”[3](P2)。 康有为也较早注意到美术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1898 年,康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欧洲,在游历各大美术馆后,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绘画之学,为各学之本, 中国人视为无用之物。岂知一切工商之品,文明之具,皆赖画以发明之。 ……若画不精,则工品拙劣,难于销流,而理财无从治矣。”[4](P2)康有为的述说没有摆脱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思维路径,但他对西方绘画的科学性、独立性与工商业发展之融通,以及(现代)美术事业的重要性,却已有深切的感知。梁启超作为康有为门生,早年继承了康的改良主义思想, 但在1898 年流亡日本后,新环境为他的思想转变提供了契机,自此,他的思想逐渐倾向于“西体西用”,成为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性人物,其“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接连不断地提出一些新的观念、 新的思想”[5](P111-112),影响着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1899 年梁启超明确提出“文学革命”口号,早早发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其早年对美术的认知和改革诉求未见专门论著,但从其20 余年后发表的《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他的美术思想较康氏要更进一步,对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的关系,从心理学、哲学、自然科学等维度,曾进行过系统性的思考。
民国肇始,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遂着手制订现代性的美术教育计划。 1913 年,他在民国教育部编篡处月刊上发表了 《拟播布美术意见书》[6](P10-14),(鲁迅所谓“美术”,与王国维所谓“美术”同义,即“艺术”),在文中,鲁迅提出的艺术(art)发展方案是完全西式的、颠覆中国传统的,主张从建设、保存、研究等三个方面实施“播布”,在“美术”(fine art)方面,尤其强调美术馆、展览会等西方近代美术传播方式的作用。 蔡元培出身清廷科举,进士及第,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后投身反清的革命阵营,振兴民族是其毕生的自我使命,而教育,则是其选择的实现路径。 受两次赴欧洲留学、游历中考察美术所得启发,蔡元培认为,美术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不输宗教,宗教的社会功能可由美术(美育)取而代之,或部分取而代之——“文艺复兴以后,各种美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 ……鉴激刺情感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 ”[7](P15-20)所以,在 1917 年出席北京神舟学会讲演会时,蔡元培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这一革命性的主张, 期望在无西式宗教传统的中国社会以美术(美育)取代宗教“专尚陶养感情”的社会功能。
爬梳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群体的论述不难发现,从“第一代知识分子”[8](P172-173)中的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到“第二代知识分子”中的蔡元培、鲁迅、陈独秀等人,美术问题是他们共同的重要关切点。 不过20 余年间,知识界“美术革命”的准备业已显露峥嵘,从“中体西用”的美术改良路径逐渐演化为彻底的反传统、全面引进西方现代美术(及其教育模式)的革命性路径。 知识分子为何广泛思考美术问题、参与美术事业,其原因是复杂的,单就思想史层面而言,是知识分子面对外来思潮剧烈冲击时做出的被动或主动回应。在科学主义、实利主义、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各类新思潮引导下,“吾国之效法西洋文明,是为生存竞争上必不可免之事实”[9]。美术作为文化的一因子,被众多知识分子体察到其造福国民、改造社会的功用,并将其置于整体性社会改造方案的一部分, 提出各种西式变革的主张,实是时势的必然。美术变革(或革命)的思想能够快速有效地传导到大众,形成“美术革命”的社会思潮,无疑主要归功两个要素的成熟:其一是旧有社会体系尤其是科举体系的崩塌,导致知识分子的集体转型;其二是传播途径和方式的现代化。当然,这两个要素又是交互的,它们发生的共同前提是西方文明的强势输入。 清末民初的社会,“功名”已如浮萍,倒逼“新学术社会”[10](P174)快速形成。 新态势下,知识分子一方面受传统儒家道德使命感的引导,另一方面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启发,在仕途之外,努力通过其它途径推动社会变革, 他们变成职业性的“学术人”,借助新式学堂、现代报刊等多样化的途径,教授新知识,传播新思想。 此外,这些新的传播媒介也为知识分子群体与专业美术人士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更大便利,这无疑有利于各补其短、各取所长,达成更广泛的“革命”共识,而“美术革命”思潮就在这些因素的合力推动下逐渐形成。
二、“美术革命”思潮与西画“再启蒙”
在清末开埠之前, 有记录的西画传播史已近300 年。 明末,海禁废驰,西洋绘画渐渐流入中国。到了清代, 受以朗世宁为代表的传教士画家影响,“一般画人,多喜参用西法,相效成风”[11]。 康乾之间,中国画的西洋化风气至靡。 这一阶段的西画传播,主要在宫廷中和南粤、江南的市井中展开,用以满足皇家的猎奇和民间传教的需要。 其间,虽谓之有极盛时期,不过是有一些画家部分地采用了西洋画的技法而已,如冷枚、唐岱、曹重等人,作为主流的文人画,并未受到大的冲击。 由于禁教、禁海,随后的嘉庆时期,西画主要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民间流传,其中又以“十三行”的外销西画制作最有代表性,“十三行以及附近地区, 出现了三十家以上的画室,……从业的画家和画工超过百人以上。”[12](P256)这些西画的水准良莠不齐,总体而言,民俗化、风情化的倾向明显。
西画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时断时续,未能融入主流,更遑论取代传统文人画的精英地位。究其原因,除了中欧路途遥远、长期海禁等因素导致的空间上的疏离以外,文化上的抵牾是最主要的障碍。
洋务运动开始后,西画传播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商业性的西画样式逐渐流行起来,这主要得益于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和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尤其在西方人士最聚集、工商业最繁荣的上海,商业美术最为发达。 除了此前流行过的基督教绘画、西洋风的民间年画尚存以外,通俗画报、舞台布景画、广告仕女画(月份牌)、碳素容像画等,逐渐风靡沪上。一方面,“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13],商业化的通俗绘画丰富了人们的内在生活,促进了人们对外在世界的感知。 另一方面,商业化的绘画泛滥导致美术的庸俗化,知识分子群体和美术界的有识之士从中感受到了危机——如吕澂认为的那样——袭西画皮毛之学,以艳俗取悦大众,并不能滋养人的精神, 只能让人的思想徒增龌龊之念,于审美、于道德都无益。更让他们担心的是,由于西画“正统”未能开蒙,民众直将此类绘画视为舶来文化的正宗,以为受用着“新文艺”而自得。 遂有陈独秀说:“至于上海新流行的仕女画,他那幼稚和荒谬的地方,和男女拆白党演的新剧,……好像是一母所生的三个怪物。 要把这三个怪物当做新文艺,不禁为新文艺放声一哭。 ”[1](P30)
而放眼同时期的欧洲画坛——19 世纪中期以来——一些深刻的变化却悄然发生,传统自然主义绘画逐渐向“形式主义绘画”[14]演变,艺术赞助人机制逐渐让位于自由市场机制,世俗审美逐渐消弭了宗教精神,前卫艺术、庸俗绘画、商业美术逐渐分野,绘画的价值观、审美观、造型观趋于多元。 这些变化无疑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与工业化的市民社会相适应的。 换言之,西方绘画从其自身的传统逐渐演化到现代形态, 是与西方社会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整体上由近代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过程相一致的。 从康有为到梁启超,再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全盘性地反传统”[8](P172-173)的意识渐趋强烈, 他们认为,“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15](P43)。 以何“反传统”? 以何“重建”? 他们的答案就是近代以来的(或说是现代性的)西方思想和文化。美术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种,欲借之“重建”中国,那么,寻根祛魅,抛却“中体西用”的原有思维模式,来一次彻底的“再启蒙”,全面接受西方“画学正宗”[1](P30)的、“当下性”的美术(尤其是其中的主流——西画)是必由之路。于是,西画“再启蒙”,成为“美术革命”的题中之义,如德国学者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评价欧洲启蒙运动时所说,“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启蒙运动绝非一个纯粹的科学运动或主要是科学运动, 而是对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颠覆, 带来了世界关系的根本性移位和欧洲政治的完全更改。”[16](P175)换言之,“启蒙即革命。”[17]
当然,西画“再启蒙”的过程是润物无声的,并不是随着“美术革命”思潮的涌动而瞬间觉醒的。例如,清末的教会学校、(由政府开办的)“洋务”学校早已开设西式美术课程,“在这些学校里, 教授制图、几何画,出版了英国人John Fryer 的《器象显真》(1872)、《画形图说》(1885)、《画器须知》(1888),J.M.W.Farhlam 的《素描法》于1896 年改名为《论画浅说》 出版,1902 年又出版了 John Fryer 的 《西画初学》。 ”[18]从这些课程的名称即可看出,这类教育仍是重“器”轻“道”的,主要是出于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实用主义目的。其进步意义在于——不再附庸于本土的艺术传统而自成体系——为全面的“再启蒙”积蓄着能量。
到了民初,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美术专门学校、现代性的美术社团、美术刊物大量涌现,留洋习画成为风潮,“再启蒙”渐渐进入了全面发轫的阶段, 这一过程持续到1937 年全面抗战的爆发,才暂时落入低潮。 以“洋画运动”的中心——上海为例,1912 至1936 年间有上海图画美术院(1914 年)、上海美专西洋画科(1923 年)、东方绘画学校(1925 年)、私立新华艺术专科学校(1926 年)等11 间现代美术学校相继成立,成为“再起蒙”的主要实体。 有东方画会 (1915 年)、 天马会(1919年)、白鹅画会(1924 年)、决澜社(1932 年)等 40 余个美术社团相继成立, 这些现代性的社团以切磋、传播西画为主要的(或部分的)宗旨。 至少有50 余种西画类期刊杂志出版, 其中,《美术》(1918 年)、《艺术》(1923 年)、《艺专》(1926 年)、《艺苑朝花》(1929 年)、《美展》(1929 年)、《美术杂志》(1934年)等,质量上乘,发行时间较长,在西画“再起蒙”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 至少有陈抱一、汪亚尘、关良、林风眠、徐悲鸿、潘玉良等25 位知名西画家赴洋学画,这些西画家归国后,俱到上海从事西画艺术活动。 “油画人才的密集,造成了洋画运动在文化格局中多方位、多层次的深入和展开,主要是教学、研究和创作在各个层面继续得以深入。 ”[19](P56)
从启蒙活动的主体看,知识分子作为“美术革命”思潮的最初推动者,他们不仅为西画“再启蒙”提供了原初的、宏观的现代性思想来源,并且通过各类社会活动,持续支持着美术界的西画运动。 例如:蔡元培作为“美育”的积极推行者,对西画的“再启蒙”运动不遗余力,在他的大力斡旋下,杭州国立艺专(1928 年)得以成立,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1929 年)得以举办;陈独秀利用其媒体人、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在为“美术革命”呼喊之外,更用实际行动支持西画发展,促成潘玉良学习西画、留学欧洲,即是最生动的一例;鲁迅作为左翼文艺家,对现实主义的木刻情有独钟,民国中后期,木刻运动的快速发展,是离不开鲁迅的努力的,尤其是他亲自主持的《艺苑朝花》杂志,影响深远;傅雷作为翻译家、批评家,谙熟西方近代绘画和艺术理论,其对《艺术旬刊》的发行,乃至决澜社的成立,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而美术家群体必然是“再启蒙”的实践者,陈师曾、李叔同、黄宾虹、刘海粟、吕琴仲、汪亚尘等一大批民初的美术家,借助办学、结社、出版等途径,不遗余力地开展西画启蒙工作。 从启蒙的内容上看,西洋画史、造型、技法、绘画美学、艺术批评等西方绘画艺术的相关领域,是无所不包的。其中,吕澂的理论著述和教学工作是最有代表性的: 在1920 年担任了上海美专的教务长之后,“创了专校的规模,并开讲《美学概论》和《西洋美术史》两课(讲稿均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主编《美术》杂志,同时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师范美术史讲师。”[20]此后,吕兼任了南京美专的美术理论讲师一年,撰写讲稿《色彩学概论》,又应李石岑的邀约,撰写了《美学浅说》《近代美学说和美的原理》 两本介绍西方美学的书籍,俱交付商务印书馆印行。 对比洋务运动时期的学校,西画的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形而下的图画技法拓展到形而上的艺术史论、美学,这一情形体现了“再启蒙”运动与西画早期传播的根本性区别。
三、结语
民初的西画“再启蒙”开启了西画界的现代性转变,而艺术史是“非对称性”的,在20 世纪初的特殊年代,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建构有赖于西方美术的整体性移入,西方艺术史的线性叙事在民初文化语境中是扁平化的、 去历史化的。 在短短25 年间(1912 年——1936 年),西画传统的“写实主义”与当下性的“现代主义”在中国都被广泛传播,尤其是象征主义、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新兴流派,俱被引入,拥趸不绝。 并且,在 “写实派”与 “现代派”之间展开了激烈争鸣,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是1929 年第一届“全国美展”之后的“二徐之争”。徐悲鸿倡写实、贬表现,主张以西方的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而徐志摩则为“现代派”雄辩,认为中国接受“现代主义”的西画是时势的必然,“是他们强,是他们能干,有什么可说的? ……绘画当然就非得是表现派或是漩涡派或是大大主义或是立体主义……。”[21](P217)“二徐之争”投射出知识分子以及美术家群体中“美术革命”的两种态度——是要“写实”的“功利”还是要“表现”的审美创造? 换言之,绘画是要为人生,为社会,抑或为“艺术”自身?
事实上,以“二徐”为代表的两种观念,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功用。“写实派”着力点在于——以科学主义改造文人画的程式化、娱情化“写意传统”,使艺术摆脱陈独秀所贬斥之“虚文”,从而能够更好地书写现实,达到促进民族觉醒之目的。 “现代派”着力点在于——一方面,是要传播西方最新的绘画流派, 从而在文化上实现与现代西方的紧密接轨,迎头赶上;另一方面,是艺术家从西方现代艺术中窥见了“东方主义”要素,转而反刍,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 无论是“写实派”还是“现代派”,其艺术思想都离不开“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之引导,都是为了“美术革命”和民族振兴。“由此视角看艺术实践中的‘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探索,可以发现二者是现实性的‘两副面孔’,体现着艺术家回应现实的两种方式”[22]。也由此可见,西画全面启蒙的态势与民初知识分子的一整套社会变革的思想体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以西画为主的)西方美术的“再启蒙”开启了中国美术现代性转变的大门,并与诗歌、小说、戏剧等其它文艺一起,汇聚在“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大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