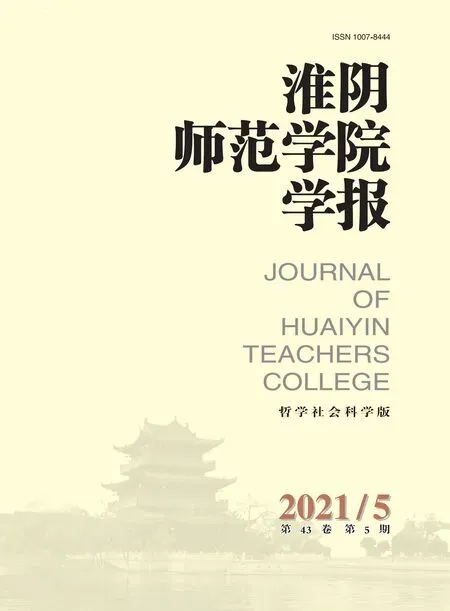论隐喻在李金发诗歌中的建构功能
叶琼琼,谷金雨
(武汉理工大学 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20世纪20年初,以“丑怪诗风”异军突起的李金发在诗坛濛濛“微雨”中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部分批评者对他持否定态度,如新诗肇始者胡适强调诗歌要“明白清楚”,批评象征诗晦涩难懂,说他的诗是一个使人难猜的“笨谜”。任钓也指责象征派诗歌的晦涩和暧昧,说读这些作品“好像在听外国人说中国话”,“读了也等于不曾读”[1]。然而这些所谓“读不懂、可读性差的诗歌”却得到朱自清的极力肯定和赞扬:“他(李金发)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2]。用李金发自己的话说就是“诗人因意欲而作诗,结果意欲就是诗。意欲在他四周升起一种情感及意想的交流”[3]。这种所谓不寻常的“章法”缘于隐喻结构在诗歌中的大量灵活运用:李金发通过隐喻串联起看似不相干的诸多意象,并建构诗歌结构、形成语言框架,而被李金发“藏起”的“那串儿”正是他的“意欲”——情感脉络和心理轨迹。
“诗人的大脑完全是一套隐喻的句法。”[4]隐喻在李金发诗歌建构过程中被广泛应用,并形成了具有浓郁现代主义文学风格的“意识流”和“双声部”两大结构特点。
一、意识流结构
“意识流”概念由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于1884年首倡,之后获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支撑,又被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等人发扬光大,后逐渐成为西方文学中一种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被视为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主要成就之一。而意识流小说也逐渐成为独立的风格流派影响至今。意识流小说以内心独白、自由联想为手段,淡化故事情节,围绕人的意识活动展开叙述,给读者以梦幻和陌生的阅读体验。随即诗歌也引入该手法,产生了一批具有意识流色彩的现代诗。意识流究竟囊括哪些技巧目前尚无定论,美国当代批评家梅·弗里德曼在《意识流:文学方法的研究》中认为,内心独白、内心分析和感官印象是意识流最主要、最常用的三种方法[5]。除此之外,中国学者刘庆雪还关注到意识流小说中的时空跳跃技巧,认为人物意识的流动可以跨越物理时间和现实空间的束缚,在心理时间和心理空间中频繁跳跃,使作者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表现出更加丰富的思想内容,呈现出人类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6]。从本质上来讲,内心独白、感官印象和时空转换(跳跃)这些意识流技巧展现出模糊、矛盾、自由的审美特征,形成了无序的片断化隐喻结构,是诗人用形式上的断裂和疏离来隐喻破碎、混乱、无序的现实和心理状况,让诗歌结构本身就形成一个绝妙的暗喻[7]。
所谓内心独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的,就是作者直接引述抒情主人公的心灵话语,将它毫无保留、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是非理性、无逻辑的;另一种则是理性的,抒情主体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心理世界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和推理,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意识流是灵动的,是思维在大脑中的自由体操,此时的诗人进入了意识混沌状态,时而迷幻时而清醒,迷幻时的诗句是自我独白,清醒时的诗句又成了审视之前呓语的理性分析。诗歌的基本功能是抒情,相比于叙事,用于抒情的意识流使作者能够更容易进入和把握自己的情绪,需要把情感加以宣泄的时候使用内心独白,需要将它加以节制、舒缓节奏的时候就成了内心分析。快与慢、狂野与理性、激昂与沉静在这里相互交织,这样一来,诗人自由奔放的思想情感就在泼洒到位与收束得当之间取得了平衡。李金发诗歌中有很多独白式的作品,如《题自写像》《希望与怜悯》《岩石之凹处的我》《自解》,等等。这些作品中,作者与自己对话、与虚无对话,把自己的心境排布在纸面上,把想法和盘托出。诗人在《题自写像》中这样与“另一个自己”对话:
即月眠江底,
还能与紫色之林微笑。
耶稣教徒之灵,
吁,太多情了。
感谢这手与足,
虽然尚少
但既觉够了。
昔日武士被着甲,
力能搏虎!
我么?害点羞。
热如皎日,
灰白如新月在云里。
我有革履,仅能走世界之一角,
生羽么,太多事了呵!(1)李金发:《李金发诗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2页。本文所引李金发诗歌皆来自此版本。
这首诗写于1923年李金发在德国柏林游学时,因为觉得立体派和先锋派的绘画艺术“不合自己的胃口”,于是“并无好感”,就自己在寓所练习雕刻和油画[8]65。画自画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习俗,在画中题诗写字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书画传统的典型表现。诗的第一节写的应是画中景物,月亮落入江底,紫色山林凝视着每一个观赏画像的人。在西方语境中,紫色具有噩梦、恐怖、死亡和幽灵等文化象征意义,与“微笑”并行出现生发出诡异之感。面对眼前这幅油墨未干的西式技法作品,这位中国诗人向自己发问:“我是耶稣教徒之灵吗?”随即自嘲,不过是自作多情罢了。第二节视角转到自己的手足上,作者将自己的身形与古代的猛士相比,虽然不能如冯妇搏虎,但也足用余生了。第三节又转回到画中景物上,此时恍惚于日月之间,凭借双脚只能走到世界的某一角。是否要生出一对翅膀飞上天空?他再次自嘲:太多事了!从画内到到画外,从心外到心内,生理视觉和心理视野的变换使写作视角不断变化,也预示着诗人向内向己寻求文化和解的倾向。三节诗歌,三次转折,节与节之间是场景的变换,句与句之间是语义的转折,自我肯定与否定的对立面不停地翻转、抵触。一个从中国南方乡村辗转到欧洲资本主义强国留学的年轻人看到以“耶稣基督”“西装革履”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不免产生民族性自卑,此时的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哺育自己二十余年的厚重传统,又该如何接纳新奇的现代文明,西式画作和他的东方人身份之间生成了一道文化鸿沟。随着视角的转换、语义转折的触发,主人公对传统信仰崩溃的茫然和对现代意识觉醒的错愕在字里行间和画作现实之间频繁流动,心理矛盾体也被推来推去,辗转在自我揶揄之间,从而使诗歌浑成一体。
弗里德曼指出,“头脑一般说来是消极被动,只受瞬息即逝的印象的约束”,感官印象“只是和一小部分意识有关,但它是距离注意力中心最远的一部分”。意即:感官印象,只是人物的感官于瞬间偶尔捕捉到的、稍纵即逝的客观存在物[9]。内心独白是诗人将自己的全部意识明白无疑地说给读者听,感官印象则不同,虽然它也可以通过内心独白的方式表现出来,但不是表现全部意识或者“有意识”,而只是“潜意识”或“下意识”,所以感官印象总是以片断、不连贯、朦胧模糊的形态出现。李金发刚到巴黎时,正是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风靡法国艺坛的时候,他“一度对雷诺阿等印象派画家颇为醉心,称赞马奈为‘人杰’”[8]41。或许是受印象派影响,他的诗作中多有刻画感官印象的痕迹。较典型的是《寒夜之幻觉》一诗:
窗外之夜色,染蓝了孤客之心,
更有不可拒之冷气,欲裂碎
一切空间之留存与心头之勇气。
我靠着两肘正欲执笔直写,
忽而心儿跳荡,两膝战栗,
耳后万众杂沓之声,
似商人曳货物而走,
又如猫犬争执在短墙下,
巴黎亦枯瘦了,可望见之寺塔
悉高插空际。
如死神之手,
Seine河之水,奔腾在门下,
泛着无数人尸与牲畜,
摆渡的人,
亦张皇失措。
我忽而站立在小道上,
两手为人兽引着,
亦自觉既得终身担保人,
毫不骇异。
随吾后的人,
悉望着我足迹而来。
将进园门,
可望见峗峨之宫室,
忽觉人兽之手如此其冷,
我遂骇倒在地板上,
眼儿闭着,
四肢僵冷如寒夜。
诗人调用了视觉、触觉、听觉、机体觉等多种感觉,写出了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自己出现诸多幻觉的经历,处处透露出可怖的气息。生理感觉产生感官印象是确定无疑的,除了描写自己不断变化的感觉特征,作者还积极地为自己的情感寻找“客观对应物”(2)“客观对应物”理论是T·S·艾略特提出的,可以概括为: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最终要做到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能立刻唤起那种情感。它是为处理诗人的个体经验,达到“非个人化”创作的目的而提出的。来强化它们,这正是现代派常见的写法。在这首诗中,作者想要表现的是客居异乡的孤独寂寥之感,夜晚的寒气加重了内心感受带来的实际痛苦。那他找的客观对应物都是什么呢?全是使人感到恐怖的意象:黑夜中的寺塔、死神之手、浮在水中的人尸和牲畜、人兽,这些并未真实出现,只存在于作者的幻觉中。这些隐喻场景在字面意义上没有明显的关联,体现出无意识下感官印象的随意性,但是它们所代表的心理意义和文化意义最终指向是同一的。另外,“忽而”“又如”“如”“忽”等连接词语在语言层面充当刚性衔接手段,保证了诗人的意识流没有成为痴人的呓语而是有诗味诗情的主题统一、意义连贯的文本。重视调动主体感觉器官和积极寻找情感客观对应物的创作技巧使李金发的诗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人产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代入感,再次印证了意识流的感性特质。尽管感官印象表面上显得天马行空、毫无关联,但是它们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和个体意义在创作目的上的指向是一致的,加之形式语言衔接手段的串联,这些隐喻性意象就能够保证全诗主题发展的一元线性趋势,使诗歌呈现出整一的形态。
时空转换(跳跃)类似于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剪辑手法,是诗人将存在于不同时间、空间的意象组合、拼接、粘贴在一起,产生联想、对比、悬念、暗示等效果。时空转换破坏了正常的时空顺序,时空跳跃的灵活性与多变性正符合了意识流飘忽不定的特点,这种手法的跳跃性和无序性让诗人有更充分的心理余地来表现琐细复杂的情感。如《小乡村》:
憩息的游人和枝头的暗影,无意地与池里的波光掩映了:野鸭的追逐,扰乱水底的清澈。
满望闲散的农田,普遍着深青的葡萄之叶,不休止工作的耕人,在阴处蠕动——几不能辨出。
吁!无味而空泛的钟声告诉我们“未免太可笑了。”无量数的感伤,在空间摆动,终于无休止亦无开始之期。
人类未生之前,她有多么的休息和暴怒:
狂风遍野,山泉泛生白雾,悠寂的长夜,豹虎在林间号叫而奔窜。
无尽的世纪,长存着沙石之迁动与万物之消长。
该诗前两节描写所见都是乡村悠闲惬意的景象:人们趁着空闲到乡村游览放松,景致优美,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这是当下的此时此地此景。第三节一阵“无味而空泛的钟声”引发了作者的联想,一丝与当下悠闲安逸的境界相抵触的自嘲、伤感之情蓦然涌上心头,诗人的思绪一转闪回到“人类未生之前”,所见的变成了原始狂暴的地球初年,由此他生发出沧海桑田、世事无常、万古无尽的感伤。人脑是一个很奇特的物件,小小的头颅竟能容下无限的宇宙和无尽的时间,任意地在其间跳转、变换。作者用这种无序化的叙述方式隐喻自己当下迷乱的心迹,以此时和彼时、此地和彼地的并置来隐喻时间空间的无限和人类自我有限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外在事物触发作者的头脑机能,联想和想象使作者产生创作的冲动,用时空转换的手法把想到的画面逐一呈现,作者的意识则随着时空翻转而不断流动并形成意识流。
前面说过,意识流没有固定的表现技巧,内心独白、感官印象和时空转换等手法相互之间联系紧密并且在实际应用上也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对意识流手法进行分类没有意义,之所以将它们分开叙述,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意识流和隐喻结构的关系。内心独白强调“作者—文本—物象—读者”之间的双双对位关系,外界客观存在触发作者内心情感和创作冲动,通过意识流的编织和隐喻的建构形成诗歌文本,读者面对已完成的、独立于作者的作品时,通过调动个体经验和隐喻解读能力来解构和重构诗行,最终完成对诗歌的理解和审美过程。而感官印象的重点在于凸显作者的个体感受(觉)力和寻找客观对应物的能力,提升读者阅读诗歌的体验感。时空转换则着眼于文本内部的条分缕析,把处于不同时空的意象、意念和场景打乱重建来形成和谐自洽的诗歌整体。
片断化的意识流创作技巧使李金发的诗歌呈现出鲜明的现代特色,由此形成的诗歌隐喻结构也显示出作者的智性特质。隐喻视角下的诗歌创作是这样一个过程:诗人受到外物的触动之后积极寻找“客观对应物”来具显情感进而启动隐喻机制,将自己的体验、感觉、经验等投射到“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等客观事物中,形成泥沙俱下、诸多片段杂糅拼贴的无序片断化隐喻结构。这正是所谓的“陌生化”手法,摒弃传统诗歌起承转合的结构模式和直抒胸臆的抒情习惯,甚至改变诗歌材料常见的生存语境,背离材料间常见的联系,通过大量不相关联的意识断片形成全新的结构,迫使读者从传统的阅读和感受方式中走出来,改变与作者沟通和交流的方式以及阅读诗歌的方式,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悟和审美感受[7]。
二、双声部:古典与现代的对话
有些学者对李金发诗歌中浓烈的“异域情调”表示质疑,认为他的诗歌“既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法国式的,它没有民族面目”[10],是移植的、甚至“冒牌”的象征主义,还有的说他作为一个汉语诗人,竟然连“中国话不大会说,不大会表达”[11]云云。然而这种“模糊的民族面目”恰恰是李金发初涉诗坛之际就确立的文学理想:“余每怪异何以数年来关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既无人过问,一意向外采辑,一唱百和,以为文学革命后,他们是荒唐极了的,但从无人着实批评过,其实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稍为留意,便不敢否认,余于他们的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12]可见,李金发不但没有忽视对古代文学文化的借鉴学习,也没有一味地嫁接移植西方文艺,反而有着调和中西、贯通古今的远大诗歌理想(虽然现实结果证明其并不成功)。所以在李金发的诗歌中能够读到的是厚重的古典味道和鲜明的现代异质的交融,既有深沉的中国性,也有前卫的西方性。古典与现代在他诗歌的立意选材、审美特征和文体语言等方面进行着跨时空的历史性对话。
李金发的诗歌以自然风物和城市风光等意象的描绘着力最多,其中既有异域的欧陆情调,也有故国的乡土气息。如午后倦懒的春光:
野榆的新枝如女郎般微笑,
斜阳在枝头留恋,
喷泉在池里呜咽,
一二阵不及数的游人,
统治在蔚蓝天之下。
——《下午》
有街头疲惫的工人:
他们将因劳作
而曲其膝骨,
得来之饮食
全为人之余剩;
他们踞坐远处,
嗤笑了。
——《街头之青年工人》
还有家乡的热带景观:
我的故乡,远出南海一百里,
有天末的热气和海里的凉风,
藤荆碍路,用落叶谐和,
一切静寂,松荫遮断溪流。
——《故乡》
乡土记忆和异国熏香在李金发的诗作中交织并存。在他公认的代表作《弃妇》中,传统美学和现代思维取得了更加密切的融合,他至少做到了立意选材层面的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全诗如下: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
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
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与蚁虫联步徐来,
越此短墙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
如荒野狂风怒号,
战栗了无数游牧。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
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
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
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
长染在游鸦之羽,
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
徜徉在丘墓之侧,
永无热泪,
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
首先,“弃妇”本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相当常见的母题,如《诗经》中的《卫风·氓》《邶风·谷风》,汉乐府的《孔雀东南飞》,魏晋曹植的《弃妇诗》,唐代张籍的《离妇》和顾况的《弃妇词》等等,流传久远。这些诗歌中多写的是被不义的男子抛弃的妇女诉说自己悲惨命运,控诉丈夫不忠。但是,也有一类表面上以弃妇作为抒情主人公,而实际上是被放逐的臣子斥责奸佞小人、标榜自己能德的“逐臣诗”。不达《弃妇》这首诗和被遗弃的妇女与被放逐的臣子都没有关系,李金发想表达的是苦闷抑郁而无人理解的心绪。李金发以“弃妇”为题只是“取其言而舍其义”,这样就在诗题和内容之间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用这样一种结构方式来隐喻作者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接受态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土壤有所取益,但是又不免有些自卑;另一方面用西方视角审视古典文明,却又不能完全接纳、消化。之所以说他的诗歌和古代文学密切关联,除了他借助文学母题进行改造和隐喻,还因为在这首诗中能找到很多被借用、化用的经典意象。比如,“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如荒野狂风怒号”的蚊虫对应“聚蚊成雷”的惯用语,“红叶”使人联系到古诗中很多时候作为闺怨愁思的象征,“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与山泉长泻在悬崖”与杜甫的《佳人》中“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也不无关联。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意象在古代诗人写作之时就已经成为固定的隐喻意象,经过千百年来反复袭用很多意象已经丧失隐喻活力,不能引起读者的联想,难以唤起原本的始源域而单一指向了概念域,成为了“死隐喻”[13]。但是,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有意使用这些“死隐喻”,把它们作为建构情感的客观对应物群的成员,比如“夕阳之火”“灰烬”“游鸦之羽”“游子之歌”等几个意象,看似毫无关联,读来也十分陌生,经过作者有机组合之后,形象地把弃妇的心境一层一层地暗示出来。同时,作者还运用现代隐喻思维进行隐喻书写的创新,例如“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莱考夫和特纳曾将人的一生视作一团火焰燃烧的整个过程,人的一生就是一段时间,我们逐渐衰老的过程对应生命之火燃烧的过程,死亡就是火焰末了的灰烬[14]。在这里,诗人把夕阳比作火焰,在比喻的基础上把时间的流逝、寿命的减少隐喻为火焰的燃烧、灰烬的留存,这种思维使诗歌具有了别样的智性内涵和现代意味。还有“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一句也值得玩味,古代的弃妇都像《祝福》里的祥林嫂一样不停诉说自己的遭遇,而在这里李金发将忧愁表现在动作上而不是语言上,说明他的忧愁不能以语言的宽慰来消除,只能通过身体的对抗来缓解,这是现代身体意识的表现。李金发就是这样,一方面袭用某些常见的古典文学母题(如《弃妇》《屈原》),挪用古诗的传统意象(如红叶、夕阳、钟声、古寺等);一方面又让它们一定程度跳出传统文化的语义场,进入到属于他个人的经验空间,表现出对文化传统的母孕性归依和现代性超越。
李金发诗歌的“审丑”意识和“恶美”趣味显然取法于西方象征主义诗派的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等人。波德莱尔让从丑中表现美的“恶之花”在20世纪的西方诗坛大放异彩,反对美即善、美即真的传统美学观念,要从丑恶的对象中挖掘出象征的、神秘的美来。李金发把波德莱尔认成是自己的“名誉老师”,并提出“世间任何美丑善恶皆是诗的对象”,并自称是一位“工愁善病”的骚人[15]。于是他的诗歌中就多有诸如死尸、腐烂、污血、枯骨、坟冢、残叶等一般认为是阴暗丑恶的意象:“青紫之血管,/永为人们之遗嘱。”(《死者》)“以你锋利之爪牙,/溅流绿色之血了!”(《呵……》)“或能以人骨建宫室,/报复世纪上之颓败,/我将化为黑夜之鸦,/攫取所有之腑脏,——”(《恸哭》)虽然李金发的诗歌和象征派颇有师承关系,但他并未完全摆脱中国诗歌的审美烙印。谈蓓芳精辟地总结:“没有一个作家是可以截然离开其本国的文学传统的;也可以说,没有一个作家是有割裂传统的能力的。在传统面前,没有一个作家是绝对自由的。”[16]尽管中国古代主流审美原则是“温柔敦厚”,但是不缺乏另辟蹊径的怪奇诗人。败落、恐怖、秽恶的情景在中唐时期“怪奇诗派”诗人们的诗中恣纵地陈列着:“老树无枝叶,风霜不复侵。腹穿人可过,皮剥蚁还寻。”(韩愈《枯树》)“久病床席尸,护丧童仆孱。”(孟郊《吊卢殿》)“岩峦叠万重,诡怪浩难测。人来不敢入,祠字白日黑。”(贾岛《北岳庙》)(3)“怪奇诗派”是中唐时期以孟郊、韩愈、卢仝、李贺、贾岛等为代表的一个诗人群。姜剑云:《审美的游离——论唐代怪奇诗派》,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58页。。从本质上来讲,李金发和与他相去一千多年的唐代诗人都是在“以丑写美”“以丑喻美”,想要以强烈的美丑对比来表达一种内在的、个体的生命意识。写丑不是为了表现丑、歌颂丑,也不是要批判和揭露丑恶的现实与社会,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是一种排解内心苦闷、抒发生命体验的新颖方式。
各种文体的相互交织是李金发诗歌的又一大特色。朱自清指出他的诗的语言整体特征是文言、欧化和新语言(入诗的白话)的纠结[17]。这种纠结是新诗发轫阶段诗人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在李金发这里转化为他诗歌中极具个人风格的闪光点。往往在同一首诗中,文言、白话和外语同时出现,作者用多种文体和语言的并置、杂糅来隐喻不同的心理状态和现实情境。如《一段纪念》:
Sport-woman之歌者,
以舞蹈之音,
战栗
我
残暴之同情。
并不是歌声之节奏。
你Lucette-Broguin之名,
在我是
极其可怕,
你眉端
之谄笑,
全为
狂喜之充满。
将永不出斯土也。
你,无情之歌女,
污浊了
无数神之忠告。
我,所谓诗人,
流尽了一切心泪,
终未溅湿你彩色之裳。
只感到
Dear friend,I am sorry!
这首诗中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英语相互交织缠绕,显示出独具风味的诗歌语言特色。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英语词句的使用,诗歌头尾两句皆是英语,末尾一句“Dear friend,I am sorry!”使人不禁联想到徐志摩的名作《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18]
同样的现代汉诗,同样的末句,同样的欧化用法,“我的朋友,对不起!(Dear friend,I am sorry!)”和“再会!(さよなら!)”是多么地相似!用朋友最熟悉的母语表达这个中国诗人最深切的情愫。除了外来词的使用,欧化文法的突入也很明显。如“你,无情之歌女”“我,所谓诗人”都是英语中的同位语结构,“你”“我”是主语,“无情之歌女”“所谓诗人”是补充说明前面成分的同位语,而汉语语法中是没有和印欧语系相对等的同位语用法的。尽管李金发诗歌中的欧化词汇和语法相当常见,但是他的语言习惯毕竟还是汉语的底子,白话的使用当然占了大部分,但是文言的入侵也是十分明显的。如诗人喜用“之”这种结构助词,前面有时是形容词(“残暴之同情”“彩色之裳”),有时是名词(“歌声之节奏”“神之忠告”)。又如“将永不出斯土也”是典型“……也”的判断句式,诗歌的节奏和韵律就是通过这些显性的词汇衔接手段建构起来的。
加拿大著名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在研究了《圣经》的意象之后认为“A:B”式意象的并置会形成“双重视域”,在这一“双重视域”的作用下我们会努力把所有并置的意象纳入一个整体之中,以便对诗歌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亦即所有的诗歌意象会形成一个“单一全体”[19]。例如,庞德的“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的显现;/湿黑枝条上花瓣片片”(《在一个地铁车站》))[20]这样纯粹由意象组成的诗歌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个观点对于诗歌结构隐喻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在诗歌中并置的两套体系可以形成“A:B”并置式的结构。李金发诗歌中的双声部对话就是这样,在意象的选择和使用上,诗人有时沿用古典诗歌典型意象和固定的象征意义,有时复活某些“死隐喻”并赋予它们新的内涵,古典意象和现代意象在诗歌中共存,通过文化背景的统摄归并产生新的隐喻意义。李金发诗歌“丑怪”的审美情趣也是从西方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怪奇诗派双向取益、各有继承的,这使得中国读者和西方读者能从中获得不同的阅读体验。在他的同一首诗中,文言、白话、欧化相互缠绕纠结,这些异质的成分在诗歌中并置,建构起诗歌新颖的外在形式语言架构。质性有别的古典与现代要素在诗人有意的交叉放置之下,在读者的心中迸发出极大的理解和审美张力。
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克罗齐在《美学》中谈到艺术作品的整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时说:“表现品总是直接地起于印象,构思一部悲剧者好像取大量的印象放在熔炉里,把从前所构思成的诸表现品和新起的诸表现品熔成一片,正犹如我们把无形式的铜块和最精彩的小铜像同丢在熔炉里一样。那些最精彩的小铜像和铜块一样被熔化,然后才能铸成一座新雕像。”[21]这段话对于解释诗歌的整体性建构也同样适用,结构隐喻就是那融化和粘合这些小铜像和铜块的潜在力量。隐喻与诗歌都是人类智性与审美的高度凝练,而诗歌结构隐喻则是二者的完美统一。诗人的伟大之处在于用语言将外物存在与内心感兴相联系,构建起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诗美境界。
李金发在20世纪20年代初崭露头角之时,中国诗界刚刚经历“文学革命”,正处于挣脱旧体诗词藩篱、进行现代化转换的稚弱初期。面对当时新诗过于平白、缺乏诗质的“无治状态”,李金发以开拓者的姿态独辟蹊径,重回古典文化传统,拉起象征主义的大旗,写出“以丑为美”的怪诗,给沉闷的诗坛带来新风,向彼时的创作者们展现了新诗进一步发展的多种可能:如融合东西传统的可能,新的审美原则和表现方法的确立,新的诗歌语言策略的探索,等等,推动中国新诗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