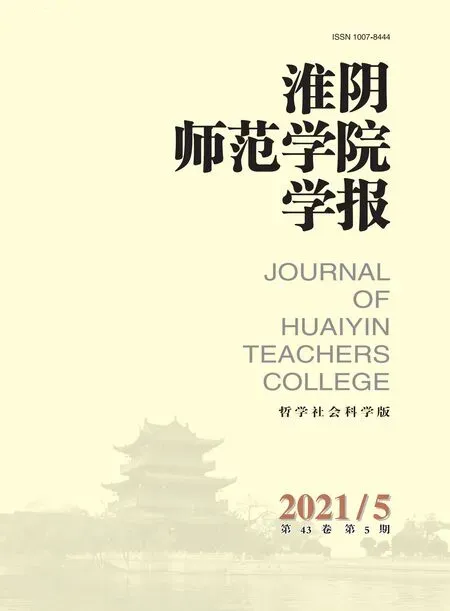无处倾诉的生命之痛
——论朱文颖的小说叙事
董 俊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语境背景下的“70后女作家”,历来为评论界所津津乐道。与卫慧、棉棉等人激越大胆、狂欢式的“身体写作”不同,朱文颖、戴来、魏微等以“相对冷面、理性的方式对女性生存、世事人心以及故事叙述作出个人的处理”[1]。其中,戴来的作品充斥着金属般的阳刚之气,魏微的文字蕴含着含蓄通透的美,而朱文颖则以对历史和现实的别样表达而独树一帜。小说“书写着生命的脆弱与寻常,世事的变幻与沧桑”,以饱含浓郁地域特色的古典情韵,被誉为“江南那古老绚烂精致纤细的文化气脉在她身上获得了新的延展”。[2]
朱文颖在张爱玲和杜拉斯的浸润下开始写作,以清醒冷静的态度和笔下人物保持着隔岸观火式的距离,情感表达隐忍、节制而有分寸感。“我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我认为它是一种东方的表达方式”,这“隐忍与节制”都是“蕴藏着力量的”,“也是一种激情表达”。[3]爱情和孤独是作品两个重要的叙事元素。小说以女性独特的细腻与敏感来展现都市男女的生存和情感困境,都市人欲望缠身、阻隔了彼此的温情传递,他们置身于钢筋水泥构筑的灰色牢笼,因而倍感压抑与寒冷,挥之不尽的是无处倾诉的孤独、焦虑、隔绝和恐惧;而气息的营造和意象的使用,使作品游移于传统与现代、幻想与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虚幻朦胧的叙事效果。
一、爱情:物质与精神的对峙
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面对诸多诱惑,由于出身、性格和成长环境等诸多复杂因素,朱文颖提出女性可能会出现的三种境遇:“第一种,优秀的具备生存质感的女人大量出现了。第二种,成为水,淹没在巨变的洪流里。第三种,成长于污泥,但并没有成为荷花。”[4]有趣的是,那种具有优秀生存质感的女性在朱文颖作品中鲜有出现,出现更多的是后两种,作品普遍诠释她们爱情的失落与破灭,结局多是悲剧性的。
“我写小说,在根源上是为了表达我的一种爱情观”。“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或者说,在所有的时代里,爱都是一件注定艰难的事情。”[5]如果说金钱象征物质、爱情代表精神的话,在朱文颖笔下,爱之艰难的主要症结就在于女性在面对物质和精神时究竟该如何取舍。朱文颖曾说:“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从生活经历和精神气质上当然更接近60后。还有一个地方觉得和60后亲近,那就是当年新生代作家出现时最鲜明的标签,就是‘精神的叩问、灵魂的探访和心灵的安妥’。我觉得我的小说气质里多少有点形而上的部分。”[6]正是文学气质造就的敏感天性和对人类灵魂的不断探索,使作家发现了两性情感生活中物质和精神的激烈碰撞,而来自江南的地域熏染和多元化时代以及自身性格等因素,也让她对笔下女性在面对二者艰难选择时,有了更多地理解和宽容。
朱文颖的小说文本多以女性为主人公、以女性为第一人称的方式展开叙述,以细致的笔触描摹都市女性的情感现状,女性在这座情爱迷幻花园中左奔右突,普遍流露出一种迷惘、困惑、焦虑与无奈的情绪。朱文颖笔下的女性爱情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不掺杂物质利益的纯粹爱情。女性以此来慰藉寂寞的心灵。《凝视玛丽娜》中的李天雨,母亲早逝、父亲又另外成家,自幼在姨母家长大。冷漠的家庭氛围使她极度渴求爱与温暖。明知来自香港的商先生只是将她作为打发寂寞时光的玩伴,他们之间只是露水情缘,她仍甘心情愿委身于他。也许是出于补偿,最终商先生离开时给她留下出租屋里的几件家具,她全部交给房东太太处理。“未必商先生不把她当成妓女,家具拖走了,权当付了嫖资”[7]55。在朱文颖的笔下,更有盲目的、只听从内心召唤的飞蛾扑火般的爱情,女性可以为爱情不管不顾、追随所爱之人浪迹天涯。《花窗里的余娜》中家境富裕的余娜喜欢有艺术气息的男人。她曾经眼睛眨也不眨地爱上对面楼房阳台上的那位不修边幅、穷困潦倒的作家;还有一次在太湖边游泳,便爱上了一位很有才华的画家。而《危楼》里,林容容的外婆从封建大家庭里逃出来,为了热血沸腾的理想与爱人私奔。“在一个大雪天的晚上,她狂奔了十多里路,身上只穿了一条蓝底白花的单裤。”[7]83这种狂热的激情、躁动不安分的基因在林容容身上得到完美复制。在夜校上美术课时,对“那个穿得土里土气、胡子拉碴”[7]82、气质忧郁的美术老师一见钟情,仅仅在认识了十几天后便与他私奔。朱文颖这类小说充满着传奇色彩,女主人公不约而同地都会爱上富有艺术气息的男人,对艺术家的偏爱或许是对人类崇高精神的向往,追求自由纯粹的爱情本身,便是对物质的摈弃与背离。
二是对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基本对等的爱情。女性在对物质追求的同时又不愿放弃情感,最后却往往两头扑空。她们不敢奢求爱情,所求的是情感,是一点点的“真心”。对此作最完美的演绎便是那篇带有寓言意味的小说《两个人的战争》,正如篇名所预示的,爱情是势均力敌的男女的心灵对搏,是缺乏信任与安全感的现代都市男女的“爱情游戏”,是一场考量双方智慧与耐力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瑞丽和郭安东才貌相当,同样精于算计。二人一见如故、互有好感,辗转于星级酒店、咖啡馆和西餐厅,表面般配,但终因缺少“真心”而分道扬镳。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是一座城的陷落最终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但对现实中的都市男女来说,更多的是因缺少这样的契机而分道扬镳。在富有古典情怀的《禁欲时代》中,两个门当户对的青年男女,彼此暗生情愫,但因那个旧时代对人欲望的压抑,爱情未能圆满。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女主人公隐秘、复杂的情感。她对情欲的压制、对景虎的猜疑、对丫头小红的嫉妒等,无不描写得淋漓尽致。“我觉得自己可能是疯了。没有人知道其实我有多么想念景虎。我有多少个夜晚夜不能寐。为了克制自己,我把全身的筋骨都迸得酸痛了。”[7]218《艺人》中的阿美,想借与丹麦人“蓝眼睛”的交往达到出国的目的。但对东方神秘文化颇感兴趣的“蓝眼睛”,钟爱茶道、京戏、老唱片等中国国粹,阿美只是他东方之旅的一次浪漫邂逅而已。即便能出国,阿美也是怅然若失。
三是物质至上的爱情。女性在追逐物欲的同时,在情感不可兼顾的情况下会断然舍弃一切精神羁绊。关于欲望化写作,其实卫慧、棉棉更有代表性,她们的小说中充斥着各种物质性因素:金钱、情欲、酒吧、蹦迪、时尚杂志,等等,主人公蔑视一切精神追求,只为发泄欲望而放纵尖叫。“与卫慧有所不同的是,朱文颖没有沉湎于个人的上海经验的过度表达,也没有一味地投入到对商业化上海的享受和赞美中,她试图在小说中保留与上海有关的冲突维度——个人的存在实现与上海冷漠的商业化之间的冲突,上海的今天与上海的历史之间的冲突,抽象的理想主义与物质的现实主义的冲突,等等。”[8]《高跟鞋》中,灯红酒绿的“十宝街”就是物欲的代名词,安第和王小蕊都不安于现状,她们用自己的青春美丽来换取物质上的享受。王小蕊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与男人的交往就是为了追逐物质,和情人之间的性,也从未有过灵魂的参与。安第比王小蕊单纯些,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不忘内心的理想与信念。“高跟鞋”隐喻着庸常的物质,虽然美丽,却使人精神堕落,而安第身上的玉则是具有精神特质的物质。然而对物质的追求并未能给她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心灵如同沙漠,虚无一片。《水姻缘》中,沈小红认为“婚姻就是一件大的物质,而结婚就是把这件大物质买回家。”在她看来,完美婚姻是建立在优越物质基础之上的,必须要有“很大的房子”,有崭新漂亮的“汽车”,有“包装精美的礼物”,还有“成功的西装革履的丈夫”。[9]9沈小红拒绝了真心爱她的技工男友,转而投入成功商人康远明的怀抱。两人各取所需,“终成眷属”。只不过他们的婚姻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空有美丽的外壳,却无爱情的内核。又如,《繁华》中王莲生的原配为了获得稳定的婚姻,只是把丈夫当成长期饭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年轻的女大学老师,为了得到各种升迁或出人头地的机会,不惜出卖肉体,与系主任搞暧昧,等等。
朱文颖小说关于都市女性爱情的描摹,让读者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种踩在“爱的碎片”上的疼痛感,作家对人的物化、女性情感无所附依的现状表示了担忧,她认为“文明的进步和人的物化,是一种两难,也是一种悖论,而知识分子的意义也许就是在参与某一方面时又揭呈此一对峙,并对每一方面都怀有警惕”[10]。
二、孤独:人类摆脱不掉的宿命
朱文颖与海派作家张爱玲、王安忆的都市小说一脉相承,其作品通过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状态的真实描摹,展示市井生活众生相,透露出了一种不确定性和诡异性;它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深处的卑鄙与丑陋。人物在欲海中浮沉,冷漠与自私是他们的性格标签,人性因欲望而扭曲变形,人与人之间产生隔膜,普遍陷于孤独苦闷之中。“孤独是叙述者赋予叙事唯一可以确定的方向感。这不仅是指对孤独的言说。更主要的是,叙述者力图将孤独作为一种激发的力量,激活情绪的种种体验,譬如恐惧、忧伤和绝望,以及至深至细的感受,对这类感受的传达构成了小说中最内在亦最生动的部分。”[11]
孤独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因性格命运和人生轨迹的不同,作家笔下人物对于孤独的外化形式表现各异:或因生活的压力无人分担而自我封闭;或因周遭人的冷漠自私而孤僻;又或因不被理解、与他人缺乏共同语言而无法沟通交流。孤独的现代人独自咀嚼人生五味,快乐无人分享、痛苦无人分担,形单影只是他们的宿命。
首先是生活重压下产生的孤独。《艺人》中,大雨滂沱中半路搭车的耍猴艺人,生活的重压使他过早衰老;他对待周遭人或物均表现出麻木的状态,这不禁令人产生疑问:他的生活究竟经历了什么?面对同车人的善意搭讪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偶尔的肢体语言就是点头或摇头,即便笑也是“满脸苦相”。他无家可归,心灵没有休憩的港湾,也没有方向,“去哪里都一样”。王伟等人半路下车入住旅店,“那瘸子就在冷得刺骨的冬雨里站着,茫然看着空荡荡的广场”,陪伴他的只有那只猴子。小说结尾,众人跟车离去时,“他们孤零零地出现在广场上,黄昏的广场上早已是空无一人,瘸子和猴子就这样坐在石阶上,漠无表情……他就那样坐在那儿,看不出他是快乐还是悲苦……他们漠然地看着那辆车,就像看一棵树,看一粒沙似的”。[12]115一人一猴何其悲凉!麻木冷漠的背后是对生活深深的绝望。小说《哑》通篇弥漫着一种阴郁冰冷、令人窒息的气息,4岁男孩罹患自闭症,对周遭一切充耳不闻,生活在自己幽闭的世界中,拒绝与他人沟通;母亲陆冬冬独自抚养照顾儿子,为儿子的病情和未来忧虑、恐惧而焦灼不安,承受着来自生活和心理的双重压力而心力交瘁;新来的保姆蔡小蛾,正是在打定主意结束生命和将之付诸实施的过渡期加入了这个破碎的家庭。朱文颖说:“每一种真正的写作都来源于一个伤口。”[13]在这里,她将“伤口”无情地撕扯、展现给读者。小说中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黑暗世界,没有阳光、只有死一般的孤寂。终于承受不了这份重压的母亲,在深夜敲开了蔡小蛾的房门,找她倾诉。单纯的倾诉并不能改变现实,但可让苦闷的情绪得以宣泄,让彼此在无情的社会中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小说结尾她们贴出了新的招聘广告,她俩都作为联系人出现在上面。我们相信必定会有新人加入,孤独者的队伍在壮大,但他们是否能成为彼此心灵的避风港?是否能真正从困境中解脱?自我救赎之路到底在哪儿?作品没有给我们答案。
其次是因冷漠自私的人性带来的隔膜与孤独。朱文颖说:“我觉得在情感世界里最能体现出人性的一些致命的弱点,比如说:自私、软弱和背叛。”[5]222其作品对人性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在小说《凝视玛丽娜》开篇,便提到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艺术,她为观众提供了72个物品,可以在她身上随意使用,有玫瑰花、蜂蜜……也有鞭子、剪刀和铁链。而最后竟然有人用上了膛的枪顶住了她的脑袋,这说明人性深处潜藏着邪恶和暴力的因子,一有机会便会伺机而动。作品中,戴灵灵在多年前曾给闺蜜李天雨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在说明一些基本情况后,又补充道:“这件事情还是应该要让你知道,他是个结过婚的男人。”于是接受抑或拒绝,选择权交给了李天雨。戴灵灵的所作所为其实是设置了一个不必负任何责任的圈套,和玛丽娜的那场行为艺术极其相似。“人们在不必负责的情况下会作出何等程度的事。这是一件阴险的作品,很像一个预谋,一次不知其终的逗引。”[7]65《无可替代的故事》中的外公是个浪荡子、败家精,出入高级妓院、酒楼,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败光了妻子的家产,对妻儿的生活不闻不问。外婆终生抑郁寡欢,在对丈夫彻底绝望后开煤气自杀。儿女们也因他的荒唐患有先天性疾病:女儿们对他有种“来自骨髓的畏惧”;天性敏感的儿子从小就“极为孤僻,脸上布满愁云,喜欢在家门前的林荫路上像幽灵般独自游荡”[12]129,对父亲极端仇视,最终因反抗他失足坠楼而死。《戴女士与蓝》通篇可用两个字概括:孤独。小说以男性视角进行叙述,在20世纪90年代出国潮中,“我”远赴日本打工,在冷漠的异国他乡苦苦挣扎,先是到海洋馆打捞鱼的粪便,之后竟然在老板的要求下穿上特制鱼皮,扮成鲸鱼供人观赏,失去了人的身份后,陷入了孤独苦闷之中。回国后,为忘记这段不堪的过去,“我”拒绝和鱼有关的一切事物。
第三是因不被理解、无法沟通交流引起的孤独。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的和睦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为保证社会稳定,很多“五好家庭”“模范夫妻”便应运而生。其实个中滋味,冷暖自知。朱文颖对此在作品中有诸多的描写,夫妻之间、母子和父子间表面平静,其实暗流涌动,充满着间隙与隔阂。《腼腆岁月》中的母女感情淡漠,形同陌路。《浮生》中,相敬如宾的芸娘和三白因“狐狸”而心生芥蒂。《倒影》里,母亲欲将青葱岁月留下的美好回忆与女儿分享,却得不到女儿的情感共鸣。女儿不断借故出差来躲避母亲过去亲朋好友的拜访。而将这种亲人间的隔膜写到极致的是《宝贝儿》,贝先生和上官雨燕是人们眼中“理智而美满婚姻的典范”。丈夫简单务实,妻子有点儿理想主义,喜欢神秘和未知事物。他们聊天的话题囿于城市、巷子、体检指标、晚饭和孩子等。“他很爱他的妻子,但她身体里的某一个部分是他永远无法了解的”;同样的,妻子也无法和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对话,“她不知道应该怎样接近他。他的世界,对于她,是整个关闭的”。[7]7无处倾诉的孤独使女人情感扭曲,竟然将全部情感寄托在一只蜥蜴身上,蜥蜴走丢后,她的精神彻底崩溃。
面对“孤独”这一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人们一直在寻找自我救赎的方法和出路,朱文颖也在作品中努力尝试与摸索。朱文颖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比较敏感的,还是文化。”并痛心地指出,“我们的传统正在割裂,我们的文化正在渐渐变得劣质,甚至堕落”[10]。因此作家呼唤传统文化的回归,并将它作为疗救人心灵创伤的一剂良药。于是便诞生了《老饭店》《贾老先生》等作品。这些作品中文本透露着一股伤感的文化怀旧的气息。《老饭店》中的那个百年老饭店便是老上海的象征,苏也青喜欢它“每一处墙角、每一个被锈色青铜壁灯照成昏黄的甬道拐弯处、前厅、缓缓上行的老式电梯、挂着厚重垂落丝绒窗帘的仿古客房里都弥漫着的气息”[12]14。舒先生温文尔雅,颇有绅士风度,抽着雪茄、喜欢翻看祖父时代的老照片和图片,爱听苏也青讲述老公园的故事和上海的旧式里弄。正是对老上海传统文化气息的共同迷恋,使二人彼此惺惺相惜。《贾老先生》中,作家以细腻温婉的笔触,营造了一个充满古典韵味的意境。贾老先生的文化怀旧因不合时宜,注定以失败而告终。除此之外,“在路上”的人生理想,或许是作家指出的逃避孤独的另一条出路。《危楼》中的林容容、《花窗里的余娜》里的余娜、《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里的“我”的外公,都是桀骜不驯、喜欢惹是生非的人,向往着奇特冒险的生活。他们是时代的局外人,都喜欢“在路上”的生活方式,不愿受任何形式的约束和羁绊。对他们来说,生活意味着对自由与快乐的追寻,累了便回家,倦了再离开,一路上奇遇不断,精彩不断。但他们因为不被人理解,依然会陷入孤独的困境中。无论是回归传统,还是在外漂泊,朱文颖笔下的人物始终没有摆脱孤独的精神困境,孤独已成为现代人逃脱不掉的宿命!
三、地域:回到野生以及原来的自己
朱文颖小说带有明显的地域化特征。她出生于上海,成长于苏州,被称为“上海往事中的女子”和“苏州文化的女儿”。她对这两座差别极大的城市有着特别的情感:“上海是我看世界的方式,苏州则是我的无底之底。上海就是你活着,就还得与生命打打仗,还得发生点这样那样的故事。而苏州就是不管打不打仗,打什么样的仗,我早就知道最终的结局是什么。”[14]197不同的作家对上海有不同的书写,张爱玲笔下的上海繁华而荒凉,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是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卫慧笔下的上海情欲泛滥,而朱文颖在《繁华》《高跟鞋》《哈瓦那》和《倒影》等作品中,凭借着“生命之仗”,“实现了上海话语运动的突围:消费社会与人性的冲突,精神与物质的较量”[15]。苏州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也有不同,陆文夫笔下的苏州清朗隽逸,苏州园林、小桥流水、美食文化,美不胜收;范小青的小说展现了苏州市井百姓的人生常态,见证了苏州的历史变迁;而朱文颖笔下的苏州则充满了诗意的阴柔之气。闲潭落花、小楼春风、评弹旗袍、芭蕉夜雨、巷陌情事是她叙事的主要背景,作品“如同江南苏州的园林一样,秀巧精致、移步换景、曲径通幽。加上她那天生的迷幻与忧郁的气质,纤细与感伤的诗性情怀,使这些作品具有了抒情诗一样的风韵和魅力”[2]。因此,朱文颖的笔下既有着上海所具有的现代感,也有着苏州的温婉和雅致,现代与古典在她的笔下融合贯通。
朱文颖小说“决不以情节的丰富与曲折见长,利用随意而空灵、隐忍而含蓄的意象化叙述,在大情境中凸现细节、剖析心性,才是朱文颖比较倾心的小说气质”[16]。《无可替代的故事》中有作家关于小说叙述方式的描述:“我发现自己对于故事的陈述,常常必须在某种时刻远离故事的情节,情节在我的头脑里是枯燥无味的……其实情节往往无关紧要。我感兴趣的倒是其中的一些气息。”[12]123例如:《浮生》通篇故事平淡无奇,只是讲述了三白辞别妻子芸娘、外出找新房子途中的见闻;《腼腆岁月》讲的是少女鲁桔对会弹钢琴的孔墙的迷恋。朱文颖的许多作品都没有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有的是大篇幅的情绪渲染,这给读者的阅读无疑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对作品诗性意境的形成却至关重要。
小说采用多样化的叙述手法,借助回忆、幻觉、梦境和现实相互交织等叙述手段,制造一种虚幻朦胧的艺术效果。小说《卑贱的血统》采用平行交叉的方式进行叙述,一部叫《卑贱的血统》的电影和一对孤独男女酒吧邂逅,这两件原本毫不相干的事物、作者将它们杂糅在一起,正常的叙事节奏被打乱,读来不免有晦涩之感。但人物身上都被孤独和绝望的情绪所笼罩,这种灰色阴郁的气息成为小说的主色调。《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回忆与现实的交叉叙述使文本具有了跳跃性特征,女性絮语的慢节拍相融合使作品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张力,女性化的叙述方式也使作品弥漫着阴柔、潮湿之气。《病人》《重瞳》《万历年间的无梁殿》等作品人物都是通过梦境逃避现实,进入到一个超越现实孤独和恐惧的世界中。
“女人天性近乎巫,她们使碎片飞舞,虫草说话,使错落的时间与嫁接的记忆天衣无缝,使无关的一切成为一个整体。”[2]朱文颖特别擅长捕捉某种细节或稍纵即逝的心绪或心情,来渲染小说的意境和氛围。如《禁欲时代》中以一场雨、一朵花来点缀一片心事,《重瞳》中以一首《虞美人》来渲泄一种心境等。
朱文颖的审美意象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除了月亮、旗袍、评弹、碧螺春茶等,评论家王彬彬说“花雨狐”也是其小说常用的意象。[17]这些意象酝酿出一种恍惚迷离、苍忧绵密的意境,人物若即若离、细致微妙的意绪与幻觉波动在文本中自然弥漫。如《重瞳》中的月亮是“白而发青”的,勾勒出南唐后主绝望软弱的复杂心绪。朱文颖酷爱旗袍,旗袍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代表,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表现出女性贤淑典雅与温柔清丽的气质。其中,有“紧身的织锦缎旗袍”(《腼腆岁月》),有“淡青色仿旗袍长裙”(《老饭店》),也有“开衩很高的旗袍”(《无可替代的故事》)。而《花杀》里用各色艳丽花朵烹制的有着浓郁香味的菜肴,在充斥着血、泪、刀、死亡的噩梦衬托下,是对痛苦无望爱情的祭奠。而“雨雾雪”等意象也是作家营造故事氛围、烘托人物情绪的主要手段。心境明朗时,“雨不大,反倒每一丝、每一滴都在竹叶上站稳了脚跟。空气里织着雨雾……连雨雾都是绿的”[7]201(《繁华》);心境恍惚时,“雪下大了,白的,让人觉得,白得空虚”[18]26(《绯闻》)。说到“狐狸”这个意象,自然的令人联想到《聊斋》或现代人所说的“狐狸精”。但朱文颖笔下的狐狸,有时是灵气逼人的惹人怜爱的小动物,如《绯闻》中,“银灰色的,很小巧,没有什么声音”,“狐狸跑得很快,飞快,又轻盈,像风一样”[18]30。而《浮生》里的“狐狸”,使芸娘和三白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代表着韶华失去的芸娘对未来的隐忧。江南的柔风细雨、风花雪月和飞禽走兽给小说带来了拂之不去的感伤情绪,神秘、凄美而哀婉的气息在作品中氤氲弥漫。
朱文颖在地域文化的传承方面成绩斐然,尤其苏州在她的小说中仿佛已具有符号地标的意义,但朱文颖不愿自缚手脚、将自己囿限其中。朱文颖曾说:“当一个词被长期使用的时候,它就获得了特定的含义。就像一头已经被驯化的动物,不再具有自身更大的内涵和野生的创造力。所以说,其实每个作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别样苏州的途径都只有一条:忘记苏州这个符号,回到野生的、原来的自己。”[19]归根结蒂,作家属于哪种地域文化,是否带有地域性标签,都必须踏实地面对人生和人性,“真实、勇敢、宽阔”地进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