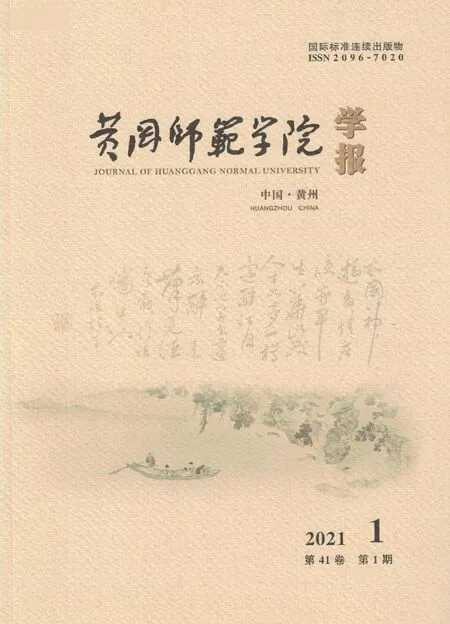现代文学副刊研究的历史回顾
段从学
(西南交通大学 中文系,四川 成都 611756)
自其诞生之日起,中国报纸所特有的副刊,就不仅仅是静态的作品容器,更是一种积极的生产机制,随着正张的出版节奏和发行渠道,在写作和消费之间建立了同步互动的共时性关联。作家心态、文学的社会位置、写作方式等,都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文学也从少数“骚人韵士”的古代文学,变成了和普通读者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现代文学”,进入了他们的日常消费。正是基于这种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副刊研究也一直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在文献整理、编目与研究等环节,都推出了大量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也积累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重要话题。
1949年之前的研究
创刊不久,不少副刊就从报纸正张中析出来,以合订本的形式开始了“书籍化”“杂志化”的文献汇集和自我保存。这项严格说来算不上整理,也没有什么研究的工作,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变成了副刊史料工作的“史前史”。《晨报副刊》《中央副刊》《〈创造日〉汇刊》《文学周报》等出版过合订本的副刊,也由此先行一步,受到了至今持久不衰的关注。那些至今仍然和报纸正张安安静静地躺在一起的副刊,则绝大多数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
同时期里,随着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和专门的新闻人才学校的创办,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等书,就开始了对中国报纸副刊史的溯源和梳理。1948年的《报学杂志》,更是连续发表了胡道静等人的《中国报纸副刊的起源和发展》等专题文字,对近代中国副刊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初步的总结。郑伯奇、陈纪滢、卜少夫、卢冀野等人,都曾对相关的报纸副刊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梳理和论述,既总结历史经验,也提出了各自的编刊理想。
现代文学领域,则从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晨报副刊》等重要副刊,就成了学科的基本史料。朱自清还据此划分流派,把《晨报副刊》变成了至今仍然有效的文学史关键时间节点。沈从文、苏雪林等人在大学课堂开设现代文学课程的时候,也大量采用了副刊史料,沿袭了副刊史料锁定的知识视野和历史划分,更是不必再说。
但严格意义上的副刊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却是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建立之后,为了给文学史教学提供参考资料,建立完整而规范的学科知识格局而在六十年代才正式展开的。
六十年代的草创与开拓
已故的樊骏,曾在《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中透露说,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迅速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曾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具有世界性意义,因而亟需总结和推广的宝贵历史经验。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这个开端中,实际上隐含了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历史前提”。第一、当然是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的“革命文学”因此而长期占据主流,左右和支配了“现代文学”主导叙事的问题。但正因为大家都已经注意到,所以这个问题反而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重要。不仅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持续不断地对这种将“现代文学”狭隘化和单一化的倾向展开了辩驳和修订,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相应的史料工作,当时就没有完全遵照这个标准,而是以不断修正和突破这个标准的形式持续展开的。第二、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中国”,实际上不是历史概念,而必然只能是“当代中国”。只有根据“当代中国”的要求和标准,从形成中的、充满了复杂性的“历史中国”拣选出相关的经验和事件,同时排除另外一部分事件和经验,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才能建立起来。旧体诗词之类时间上属于“现代”,但性质意义上被认为“非现代”的文学经验,因此当然也就毫不意外地被排除在了“现代文学”之外。主权意义上的“当代中国”之外的大量海外华文文艺,同样也未能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则是它奠定了一种至今仍然在隐秘而顽强地发挥着作用的支配性思路,那就是把“文学史”当作不言而喻的出发点,反过来从“文学的历史”中拣选相关史料的惯性轨辙。在这种情形之下,解放区和左翼“革命文学”副刊史料,顺理成章地率先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得到了调查、编目等初步的整理与研究。
署名“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1961年先后出版共3集的《山西文艺史料》,标题虽然是中性的“文艺史料”,内容却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文艺史料”。它明确把各解放区的“报刊杂志”列入了史料来源,对《新华日报》华北版的“新华文艺”、太岳版的“沁河文艺”、太行版的“太行文艺”等副刊做了简要的介绍,开创了至今仍然有效的“书、刊、报”三者并重的现代文学基础史料工作视野。
同时期的上海,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牵头,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创办了第一个以现代文学基础史料整理和研究为专门任务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丛书的乙种是广为人知的“革命文学刊物的影印本”。列入甲种的丛书出版,主要用于征求意见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却在“期刊”的名目之下,涉及到了报纸副刊。这个署名“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编著,实际由上海图书馆、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单位的刘华庭、江敦熙、周天、陈中朝、陈梦熊、翟同泰等人编制的“目录初稿”,在1919—1927年部分开辟了“主要报纸副刊”一栏,将《晨报副刊》《晨报增刊》《京报副刊》《觉悟》《学灯》等五种副刊列入了目录。此外,“主要社团刊物”栏里的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周报》《文学旬刊》、创造社的《创造日汇刊》,鲁迅主编的《京报·莽原》周刊等,实际上也是“报纸副刊”。衡阳《力报》馆的《半月文艺》,实际上也不是期刊,而是《力报·半月文艺》副刊的合订本。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里,上海古旧书店编写的《创造社期刊目录》,则把作为《中华日报》副刊出版,随后整理为合订本的《“创造日”汇刊》,也列入了“期刊目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辑以《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的意见——来信选登》为题,刊载了不少学者和文艺工作者的意见。何公超注意到“目录初稿”事实上“已经编入一部分报纸文学附刊”,但仍然局限于曾经有过合订本的少数几种,视野不够开阔的问题,提出了把包括《申报·自由谈》《民国日报·觉悟》等更多“报纸附刊”也纳入“期刊目录”的意见。臧克家提到了自己曾在1946—1947年的《侨声日报》编过每周出版一次的“诗刊”的事实——尽管报纸的准确名称是《侨声报》,副刊的名称是《学诗》。第3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继续刊发的《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的意见——来信选登(摘要)》中,杨瑾琤提出了将《新华副刊》等更多的“主要报纸副刊”也收入目录,潘梓年和蒋天佐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应该将抗战时期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团结》副刊、姚蓬子主编的《新蜀报·蜀道》副刊、《大公报·战国策》副刊、张恨水主编的《新民报》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申报·自由谈》副刊、《译报·大家谈》等收入目录的具体意见。
现代文学史之外,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等近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成果,也根据自己的收藏和访求结果,对部分近代小报的出版情况做了简略的勾勒。张静庐编的《中国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虽然没有将报纸和期刊区分开来,但也将清末民初部分重要报纸的出版情况,收入了其中。这些零散成果,从不同的侧面表明了时人对包括文艺副刊在内的报纸文献的高度重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原计划“每年出版四辑左右”,“每辑二十至三十万字”(《编辑说明》)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在1963年11月出版第3辑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已经拟定了具体书目的第三批“革命文学刊物”,也未能按照原定计划影印出版。尽管如此,已经展开的部分工作,还是在以书籍为中心的古典文献学之外,开辟了书籍、杂志和副刊三者并重的新视野,让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一开始就带上了有别于古典文献学的时代特色。
这个现代文学所特有的史料视野,不仅对当时和稍晚些时候的山东师范学院的作家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的《文教资料简报》等内部资料工作产生了影响,而且在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基础史料工作中保存和延续了下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从1980年恢复出版后,从第4辑开始连续计算,并在第7辑(1983年)和第8辑(1984年)分别刊发了张桂兴辑录的《〈京报·民众文艺周刊〉总目》和上海图书馆辑录的《〈中华日报·动向〉总目》——尤其是后者的署名“上海图书馆”,以及后来出版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收录的“报纸副刊编目”均出自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之手等事实,就是这种延续性的明证。
八十年代以后多元化时期的整理和研究
进入1980年代以后,报纸副刊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新闻史和出版史研究,以及地方史志研究等领域得到全面展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一)现代文学领域的整理与研究 基于刚刚结束的历史时期的惨痛教训,这个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明确提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坚实可靠的史料为基础重建学科的历史性和科学性品格的目标。发掘史料的“史学”品性,和与刚刚结束的历史展开对话,抒发“诗性”激情两种力量由此而不可重复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诗与史”亲密交融的学科发展源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组织、全国各地高校教师和社科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大型丛书中的丙种“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在《编辑说明》中提出了“书籍、期刊和报纸副刊”三者并重的编纂要求,也无形中把这个原则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基础史料工作的内在视野,和“以现代文学史上的运动、思潮、论争与社团资料为主”的甲种丛书,以“搜集和整理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资料”为内容的乙种丛书一起,奠定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和史料工作的基本格局。甲种丛书中的《创造社资料》和《文学研究会资料》,就分别对《创造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等重要副刊做了编目。
首先应该提到的,不用说当然是《新文学史料》。这份1978年底创刊,1980年改为季刊定期出版,一直坚持到今天的专业杂志,从创刊号发表袁省达的《申报〈自由谈〉源流》、第2辑发表萧乾的《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第3辑发表蹇先艾的《〈晨报诗刊〉的始终》开始,就一直把副刊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作为基本任务。如果把作家回忆录、各种访谈记录、作家年表、文献辑佚等史料文字中涉及的副刊也包括在内的话,这份专业刊物几乎涉及到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所有重要副刊,积累了大量不可替代的权威史料。
“内部发行”的《新文学史料》创刊号发表的《申报〈自由谈〉源流》,就是作者袁省达辑录1932—1935年间由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副刊目录的产物。文章特别添加了一条注释,说“此编目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因故辗转多时,才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内部印行”,未能公开出版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了一个今天看来似乎可以“过度阐释”的隐喻:文章既表明了《新文学史料》在副刊研究方面的开创和引领之功,也注定了副刊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将会是一条曲折艰难的不平坦道路。
随后陆续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抗战文艺研究》等专业刊物,也高度重视现代文学基础史料工作,发表了不少重要的副刊研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贡献和工作有目共睹,这里不再赘述。后者则因为八十年代后期停刊,相关论文未被中国知网收录等原因而淡出了学术视野。但事实上,《抗战文艺研究》曾专门开辟“报刊研究”专栏,发表了不少关于《新华日报》副刊、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文群》副刊等大后方副刊研究的史料和论文,对奠定和推动“书、刊、报”三者并重的现代文学基础史料工作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些相关研究成果,和同样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文天行、廖全京等人编纂的《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和《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续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除了编订《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文艺篇目分类索引之外,还收录了《新蜀报·蜀道》《大公报·战线》《大同报·夜哨》等16种副刊目录。
同时期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以上海“孤岛”文学史料为中心,开始了对“孤岛”时期出版的《文汇报·世纪风》《申报·自由谈》等副刊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相关成果虽然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才得以在包括24种报纸副刊目录在内的《上海“孤岛”时期文学报刊编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和《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面世,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却早在1979年开始编印的《资料与研究》这份内部刊物上就开始出现,对当时的现代文学基础史料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之类似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和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单位合作编印的《福建新文学史料集刊》。据笔者所见,这份从1982年5月开始,到1984年11月前后共出4集的内部出版物,先后刊载了《东南日报·笔垒》《中南日报·副刊》《福州小民报·新村副刊》《华侨日报·鹭风》等7种报纸副刊目录,发表了关于《福建民报·纸弹》副刊、南平版《南方日报·南方》副刊等多种副刊基本情况的回忆或介绍文字。除了一部分回忆文字后来曾收入《福州文坛回忆录(1930—1949)》(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之外,上述材料绝大部分未能公开出版,只在有限的范围得以保存和流传。同时期的东北,则有黑龙江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辽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作编印的内部资料《东北现代文学史料》,也曾对大连《泰东日报》副刊的作品作了编目(第3集),哈尔滨业余文学院编《东北文学研究丛刊》,对《大同报》《国际协报》副刊有相关整理及研究,发表了不少涉及到相关副刊基本情况的史料文字。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单位的“桂林抗战文化城”研究,也把报纸副刊之类的调查、整理和研究,纳入了基础史料工作的范围。
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从1976年开始先后由文物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等单位出版,前后共出24集的《鲁迅研究资料》,也因为研究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刊发过副刊史料和研究文字。李岫在第23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发表的《与鲁迅有关的社团资料选》,包含了浅草社、狂飙社等文学社团编辑《文学旬刊》等副刊史料。颜雄在第12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发表的《鲁迅的“万言长文”与〈社会日报〉》,以《社会日报》上污蔑攻击鲁迅和胡风“转变”的相关文字为根据,回击当时相关言论的文章,则至今仍然堪称史料与问题相结合的典范。
这个时期另一条同样重要的线索,就是上海书店、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单位,重新启动了196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工作,复刊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并以“乙种本”丛书的名义影印出版了《语丝》杂志、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等重要史料,随后又启动了第二个、第三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和出版工作。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分别收入了上海图书馆编写的447种和“近千种”以文艺和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报纸副刊编目”。此外,上海图书馆还编纂了《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副刊目录(1898—1949)》(1985年内部印行),收录7078种报纸副刊,初步完成了1898—1949年间出版的主要报纸副刊文献的调查和编目工作。上述编目与《北京图书馆馆藏报纸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1982年内部印行)等工具书一起,提供了查阅和检索的基本信息。由《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的另外一家重要参与单位“上海古旧书店”发展而来的上海书店,则在影印业界影响深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和《新月》《现代》《骆驼草》《鲁迅风》等现代文学重要期刊之外,影印了《社会日报》《申报》《新华日报》等重要报纸,对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整个现代中国文化研究,都产生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深远影响。其史料视野,也早已经超出了最早设定的“革命文学期刊”的限制。
因上海书店的影印工作而顺便在这里叙述,但在重要性上却一点也不“顺便”的,是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对1898—1949年间重要报纸的影印工作。这项从1954年影印《解放日报》、1960年影印《东北日报》和《大众日报》、1963年影印《新华日报》等规模浩大的“革命报刊”开始的工作,在八十年代以后,一方面坚持既有的方针和目标,继续影印出版了《华商报》《晋察冀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和太岳版等大量“革命报刊”,另一面也影印了《晨报副刊》《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益世报》《盛京时报》等普通报纸和副刊。后者实际上已经突破最初的史料视野,开启了今天正在进行的“民国文献保护工程”之先河。大量的硕博士论文等研究成果之所以集中在少数几种重要副刊上,就明显与这项全国性的影印出版工程密切相关。
(二)新闻出版等领域的研究 除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基础史料工作和出版界的文献影印工作之外,八十年代以降的新闻史、出版史和地方史志等领域,也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和史料。
1.新闻史研究。在随着新闻学的学科重建而兴起的新闻史研究领域,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先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新闻出版社、中国展望出版社等机构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该刊创刊于1979年,最初每年出版5—6辑不等,1987年改为季刊固定出版。1990年之前以史料为主研究为辅,1990年第1期,也就是总第50辑开始逐渐转向以研究性文章为主,史料为辅,1993年底停刊,前后一共出版了61辑。这份差不多和《新文学史料》同时创刊的新闻史料刊物,尤其是1990年之前的50辑,发表了大量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其中不少文字,都涉及到了报纸副刊的出版和编辑情况,足以和现代文学基础史料工作领域的相关材料相互发明和相互补充。比如诗人吴秾的《忆〈诗与木刻〉的编辑生活》(总第2辑),就是一份专门的,而且至今很少被现代文学研究者注意到的重要副刊史料。高天《对昆明〈扫荡报〉的回忆》(总第30集)称“吕剑同志主编的副刊,实际上成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一个阵地”,“给这个报纸撰写副刊稿件和评论文章的有华岗、田汉、闻一多、楚图南、周新民、光未然、刘思慕、李何林、李广田、孟超、尚钺、赵沨、周鸣钢、宋云彬、瞿白音、石凌鹤、谢加因等”,就提供了研究“文协”昆明分会后期活动的重要线索。王淮冰等人的《邵荃麟同志与汉口〈大刚报〉》(总第3辑)、左笑鸿的《〈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的副刊》(总第19辑)等文章,也比《新文学史料》上的同类文字要丰富和准确得多。1982年出版的总第13辑发表过徐光宵等人的“《新华日报》副刊研究”专辑、1984年出版的总第24辑,更是集中刊发了陈源理等人的“《新民报》副刊”专辑,对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新民报》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出版的主要副刊,做了全面而详实的勾勒。遗憾的是,由于学科条块分割带来的遮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很少注意吸收和消化《新闻研究资料》的相关内容,否则,副刊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至少不会像目前那样重复集中在少数几种大报大刊上。
此外,《新闻研究资料》还有几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是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立的“当代中国”视野束缚相对较少,对缅甸、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中文报纸及其副刊,均有梳理和介绍,从历史的“动态中国”的角度,把东南亚等地的部分副刊,也纳入了研究视野。第二、高度重视报刊史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者引用较多的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重要著作,最早都是以在《新闻研究资料》上连载的方式和读者见面的。
《新闻研究资料》的相关资料,还催生了重庆出版社从1982年开始陆续推出的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夏衍的《白头记者话当年》等报人回忆录,以及《世界日报兴衰史》《〈新民报〉春秋》等专题报史,为相关报纸的副刊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线索。直到2008年由中华书局推出的《邵飘萍与〈京报〉》《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张季鸾与〈大公报〉》等“报人时代”丛书,总体上的史料和线索,仍然没有超出《新闻研究资料》最初奠定的基础。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和承接重庆人民出版社1959年的《新华日报的回忆》及其“修订再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而来的《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几种专题报史资料,也有不少文章来自《新闻研究资料》。
值得单独提出来论述的,是曾长期在《大公报》工作的老报人王文彬的《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和《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两部编著。两部书都是作者因为遭逢历史冲击而未能完成的论著搜集的史料汇编,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著作,但仍然包含了完整的构思。《中国报纸的副刊》的第一编“名家论报纸副刊”,实际上就是理论性的“导论”,交代了中国报纸副刊的来龙去脉,总结近五十年的发展中形成的各种经验。以第三章《〈新华日报〉副刊的经验》做结,则交代了多元化的副刊最终的历史走向,表明了作者关于近代中国报纸副刊史的叙述框架。第二编“各地报纸的副刊”分地区展开,第三编“革命报纸和进步报纸的副刊”依据性质立论,对应的就是这个叙述框架。作者论述的范围不限于文艺副刊,而是广泛涉猎了青年生活、社会服务等曾对中国现代进步文化和革命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各种副刊。关于桂林《大公报·文艺》、成都《华西晚报·艺坛》等副刊的史实,也都要么不够全面,要么不够准确。但即便如此,作为同类著述的开创之作,《中国报纸的副刊》仍然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广泛的历史线索和完备的叙述框架,对以后的同类著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姚福申、管志华于2007年推出的《中国报纸副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仍然从中引述了不少史料列入“附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其中提到的文艺副刊,仍然有不少未能进入现代文学基础史料工作者的视野。晚出的《中国副刊史略》(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等书,虽然加强了论述,但史料线索的丰富性和视野的开阔性,也没有达到王氏这部“资料汇编”的高度。
《中国报纸的副刊》是“内”,是对浩如烟海的中国近代报海中一个特殊领域的专门钩沉。七十多万字的《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则是“外”,在更开阔的历史视野里勾勒了中国副刊这块专门领域周边的相关情况及其演化,为我们理解相关副刊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语境。尽管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初级形态的“资料集”,缺乏进一步的整理和论述,但这部除“绪论”和“附录”之外为七编,总数多达64章、306节的编著,仍然以视野的开阔和史料线索的丰富性,证实了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曾经搜集报刊史料“约七八百种”,为撰写中国现代报史做了长期的史料准备之说,也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线索。相对于普通读者比较偏爱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之类已经成形的研究论著来说,王文彬这种未完成的、初级形态的“资料集”,反而能为专业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线索,打开副刊研究的“金矿”。
2.出版史领域的研究。今天的出版史研究,已经随着出版学的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转向了以书籍和杂志出版为对象的专门领域,越来越明确地和以报纸为对象的新闻史研究拉开了距离。但在其草创时期,却没有这样明确,甚至有意识去追求的学科界限。最初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出版史料》,和出版史学科的重要创始人叶再生主编的《出版史研究》辑刊,都采用“广出版史”的视野,把报纸的编辑出版情况也纳入了研究范围。叶氏经过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以一己之力推出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就是这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三者并重的“广出版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正如其“内容提要”所说的那样,该书“为华文世界第一部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著作”,其“论述内容打破了通常的做法,从出版物方面来说,包括报纸、杂志和书籍三个方面,有利于人们全面地了解新闻出版历史和总结经验,汲取教益。同时一部书可以当作新闻和出版两部书用。”因为大量引用原始资料,所以“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又是一部涵盖面广泛的史料书。”对中国报纸副刊文献研究来说,该书虽然免不了因为种种限制而存在对新出现的史实重视不够,对部分回忆史料未做进一步核实或没有充分考虑与之相反的说法等失误,但仍然不失为出版史研究领域最有综合参考价值的权威著作,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涵盖面广的史料书”性质。
3.地方史志资料与研究。地方史志领域的资料与线索,严格说来也是新闻史和出版史的一部分,是分散在地方史志里的新闻史和出版史。这方面的材料和线索,最早出现在各地或者公开出版,或者内部印行的文字资料选集之中,但总的说来比较零散,也带着比较明显的时代烙印。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变化,第一是不少地方的文史资料工作者开始有意识地以专辑的形式对本地区的报史、出版史等进行专题总结和初步研究,出现了《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桂林文史资料》第38辑)《天津报海钩沉》(《天津文史资料选集》总第96期)等资料丰富、历史线索比较全面可靠的专题资料集。尤其是后者,对近代以来天津出版的65种报纸的来龙去脉和基本情况做了简明而准确的介绍,多达145人的《近代天津报人小志》中也有不少是现代文学研究者较少关注的通俗文学作家,是同类资料性著述中参考价值较高的一种。
第二个变化,是全国各地的新型地方志编纂工作中,出版了一批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合一的“出版志”,不少省市还将报纸单独析出,出版了一批值得注意的“报业志”。《云南省志·报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在第一章《近代报业》部分,曾专门以“副刊”为题,对1949年之前在云南出版的主要副刊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湖南省志·新闻出版·报业》(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对《力报》《大刚报》《中国晨报》等报纸出版情况的介绍,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边缘地带的湘西、湘南一带的文化和文学发展史实,丰富和补充了以重庆为中心“大后方文学”的历史视野。《湖北省报业志》(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人物”部分对七月派诗人伍禾解放战争时期在《新湖北日报》主编《长江》和《文艺》两个副刊,以及担任《正义报》主笔等情况的介绍,就不仅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线索,而且弥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界主要根据聂绀弩的回忆来了解颇有才华,也在抗战时期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七月派诗人伍禾的不足。对力扬、晏明等人“皖南事变”之后曾在南方局的安排之下疏散到湖北恩施,主编《新湖北日报·诗丛》副刊等史实的叙述,则不仅是了解诗人力扬生平史实的新材料,也从“地方史”的角度为我们了解“皖南事变”之后的国共两党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提供了新视野。以城市为单位的《成都市志·报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重庆市志·报业志》(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南京报业志》(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对相关报纸及副刊的介绍也详实而准确,不乏参考价值。相形之下,反倒是《北京志·报业·通讯社志》(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这样立足于“全国性”视野的著作,因为种种限制而多是粗线条的勾勒和叙述,未能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各地在编纂“出版志”“报业志”的过程中衍生的“副产品”。各地在启动编纂工程之后,都曾经广泛征集相关史料,多方征求意见,编印了大量出版史料、报史资料等内部交流资料。这些内部交流资料大多出自历史当事人之口,在准确性和正确性上虽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需要使用者认真辨析与核对,但依然为我们获取相关线索,拓展研究视野提供了大量不可替代的原始资料。《成都报史资料》《重庆报史资料》《浙江出版史料》《八桂新闻通讯》《北京出版史志》《广东出版史料》《河南新闻史志参考资料》等,都在公开出版的“出版志”“报业志”之外,保存了大量丰富生动的“原生态”史料。
事实上,不少地方史志工作者也注意到了这些多方征集而来的内部交流资料的重要价值,由此而衍生出了相关“史志丛书”等“副产品”。《江苏出版志》(后分为出版志和报业志分别出版)编写组,就曾深感如果把大量征集而来的出版史料“继续束诸高阁,弃之不传,那就太可惜了”,由此萌发了在编纂出版志的基础上“再编辑一套《出版史志丛书》”,以便“把已征集来的资料传之于世”的念头(《〈出版史志丛书〉前言》),推出了由《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江苏报刊编辑史》《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江苏艺文志》等专门著述构成的《出版史志丛书》。其中的《江苏报刊编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民国部分,根据当时的行政区划把上海出版《字林沪报》《苏报》《申报》《时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也纳入论述范围,从报刊编辑史的角度对《觉悟》《学灯》等副刊做了专门论述,对文学史的叙述和梳理构成了颇有参考价值的丰富和补充。《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同样也把《东方杂志》等著名的上海出版物纳入论述范围,与《编辑史》相互呼应,事实上变成了近代中国“东南文化圈”的报刊史。两书论及的重要报纸及其副刊,不仅在同类著作中数量最为丰富,而且不乏研究深度。比如《出版史》,就在第三章《现代江苏出版事业的建立与发展》中讨论了“副刊与地方性报刊的兴起”问题,还原了“副刊”与“正张”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副刊”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生产性功能提供了切实可靠的历史线索。纳入“出版史志丛书”,但规模和体系更为宏大的《江苏艺文志》从1995年初版15册,到2019年增订版的28册,虽然不再包含上海,但涉及的各种报纸副刊,尤其是近代“东南文化圈”的通俗文艺副刊基本史料和线索,也是同类著作中最为宏富,参考价值最高的一种。
同样的,广西新闻史志编写组也围绕着《广西通志·报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的编纂,刊行内部交流资料《八桂新闻通讯》,并以此为基础编辑出版了《〈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国际新闻社回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八桂报史文存》(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桂系报业史》(1998年内部印行)等“广西新闻史志丛书”。其中的《桂系报业史》,对艾青主编的《广西日报·南方》副刊、陈芦荻和韩北屏等人主编的《广西日报·漓水》副刊,以及《柳州日报》和《桂南日报》的几种重要副刊,均有详实而准确的介绍,在不少史实上修订了广西抗战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有关失误(如把《漓水》副刊中的专刊《文协》误认为艾青主编)。在各种“桂林抗战文化城”研究论著中,这是对相关副刊的梳理和叙述最为全面的一种。
4.其他材料与线索。由于出版环境的变化,不少作者不得不采取了自费印行个人著述,在小范围内相互交流的方式来保存自己的著述。这些著述中,也有不少涉及到了近代中国报纸副刊的编辑、出版和发表,保存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史料和线索。比如王进珊编著、署名“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和徐州师范学院科研处”编辑印行的《申报文艺副刊编校丛录》(1994年),就不仅完整地保存了王进珊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编辑《申报·春秋》和《文学》两个副刊的相关史实,而且由此旁及《上海新报》《申报》《新报》《沪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大公报》《新民晚报》《中央日报》等多种上海报纸及其副刊的来龙去脉,俨然具备了“上海近代报纸副刊史”的雏形。此外,以“水草平”“草坪”等笔名在抗战时期的成都等地报刊发表作品的钟绍锟晚年自费印行的《钟绍锟诗文集》(1995年)等,也提供了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史料线索。
新世纪以来的研究
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随着学科分化和发展,新闻史、出版史和近现代文学等领域的副刊文献研究,都出现了不少高水平的著述,推动了副刊史料整理和研究的繁荣。但相关研究,尤其是新闻史和文学史两个领域,也逐渐遭遇到了亟需在整体思路和框架上有所突破,而不是局部的修补所能解决的学科困境。
(一)新技术条件下的文献整理与保存之繁荣 作为相关研究得以展开的一个基础性前提,就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普及,保存近代中国副刊文献的手段,也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原本用于间谍活动的缩微胶片技术出现之前,影印是复制和保存包括副刊在内的近代报刊的唯一手段。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60年前后影印“革命文学”期刊,同时期的人民出版社影印《解放日报》《东北日报》等“革命文献”,就是在这种技术条件之下展开的。1980年代新增了缩微胶卷拍照保存的新技术,国家图书馆的所谓胶片阅览室,因此而成为了无数以副刊研究为对象的学位论文和著作“后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打卡圣地”——“而且没有之一”,用网络术语来说。
增添了数字文献技术手段之后,新世纪以来的民国报刊文献保存工作,形成了影印、缩微胶片和数据库建设三者并驾齐驱,而以影印和开放性数据库建设为主的新局面。与此同时,在刘福春等一批学人的呼吁之下,基于纸张的物理性质特殊性而迫在眉睫的“民国文献保护工程”,最终得以提升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文化工程,得到了包括社会资本在内的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支持而迅速展开,积累和推出了一大批重要报纸的数据库和副刊影印本。
除了众所周知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总库、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数据库之外,还有不少机构和平台,也开发了自己的特色数据库资源。比如四川大学图书馆的《新新新闻》数据库、天津图书馆的缩微文献影像数据库、广东中山图书馆的民国报刊与古籍全文数据库、上海师范大学的馆藏解放前报刊题录数据库等,都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
影印保存方面,除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终于将《京报副刊》列入“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影印出版(2016年版)之外,最值得称道的,是李扬2014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基础,经过多年的积累推出的《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汇编》(广陵书社2019年版)。目前的“第一编”,采取“以报系刊”的形式,汇集了民国时期北京、南京和重庆三地出版的15种重要报纸216种文艺副刊,煌煌80巨册,是目前文艺副刊文献整理的集大成之作。其中虽然也有将部分儿童、妇女、哲学等与文艺关系不大的副刊,以及少量临时性的纪念特刊也纳入了“文艺副刊”,因而略显过于宽泛的不足,但“宁滥无缺”的收录原则,却充分保证了史料的完整性。据作者说,天津、桂林、昆明等地重要报纸副刊的数据也已经采集完毕,“很快就会和读者见面”。相信即将推出的后续成果,必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数字资源的保存和传递的便捷性,不少尚未得到整理和公开出版的1898—1949年间的副刊文献,如完整或部分残缺的《华北日报副刊》《新川报副刊》、河北《民国日报》副刊、《新中华报》副刊等,事实上也早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成为了业内“准公共资源”。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准公共资源”,还将随着各自开放式数据库的建设和国家层面的民国文献保护工程的进展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空间里,成为我们的研究的重要数据资源。
(二)新闻史和出版史研究 因为内容的连续性和叙述的需要,前面已经提前谈到了新闻史和出版史等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如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二版)》(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等史料丰富详实的集大成之作。还应该进一步补充的是,专门的中国副刊史研究领域,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姚福申和管志华的《中国报纸副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影响较大的专门著述。前者是中国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专门的文艺副刊史,不在新闻史领域,反而是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后者则是新闻传播学领域影响最大,和下文将要提到的几种同类著作相比也是最为严谨的一种副刊学论著,——尽管在此之前就出现了不少以“副刊学”为题的论著。
此外,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和出版学研究的宋应离等人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2016年前后两次推出的12卷本《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对从近现代的张元济、梁启超、鲁迅、巴金,到当代的萧也牧、曹辛之等64位编辑家的编辑理念与相关实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主要研究对象虽然是书籍和杂志的编辑出版,但也有不少内容涉及到了副刊编辑和出版。大量的“存目”文献,也提供了进一步了解有关人物的编辑活动,从编辑出版工作的角度来拓展对副刊史料的理解和认识的丰富线索。
(三)近现代文学领域的新进展 从基础文献如何引领学科整体性变革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最值得重视的,有两个标志性的学术事件。
其一、古典文献学根据古代汉文献曾经在亚洲地区广泛传播的历史事实,打破了今天更多作为现代主权概念来使用的“中国”对大量“非中国”文献的遮蔽,以“域外汉文献”的崭新视域,用“从周边看中国”的方法,为古典文献学开辟了一个充满了活力的崭新领域,也为边疆学、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中国国家形成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和史料空间。
其二、此前曾经夹在辉煌的古代文学和同样辉煌的现代文学之间而位置尴尬,且因为新文学先驱们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但却未必公允的批判而遭受所谓的“压抑”,以至于八十年代还在要求“平反”,要求现代文学史予以接纳的近代通俗文学,在史料整理和研究范式的创新两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规模浩大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上海书店1998年版)就曾收录近80种已知,和40余种有间接线索,但有待进一步核查的中国近代“文艺报纸”,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较为完备的普查。郭骥、黄薇主编的《近代上海小报图录》(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收录了从1897年的《游戏报》到1952年的《亦报》在内的80种近代上海小报目录。刘永文的《晚清小说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和《民国小说目录(1912—19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两部该领域的重要目录学著作,也曾从当时出版的报纸中,辑录了大量小说,涉及大小报纸各50余种。其工作虽然是将小说从报纸和副刊中“抽出来”编目,但换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对当时刊载小说的各种报纸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学术普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史料线索。
孟兆臣主编的《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迄今为止已经出至第6辑,共700余册。从出版时间的持续性等情况来看,这个迄今为止最为浩大的民国文献汇刊工程,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还有可能持续推进下去,大有涸泽而渔,将中国近代小报一网打尽之势。出版与市场的成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近代通俗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研究,已经在新的研究视野和新史料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在新文化史研究、感情研究、市民生活史和区域史研究等新方向和新思路的引领之下,不仅摆脱了要求“平反”,希望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尴尬境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通行的“文学研究”之外,发展成为了一个充满了新兴活力的学术领域,为如何用“新史料”讲述“新故事”,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案例。
同时期现代文学领域的副刊文献整理与研究,虽然相对于方兴未艾的近代小报研究来说显得比较沉寂,但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进展。
第一、是延续八十年代以来的学术传统,继续从基础史料的调查和整理的角度,对相关副刊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和介绍。这方面的成果,除了发表在《新文学史料》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业内普遍比较熟悉的专业刊物上的论文,以及因为收入了中国知网数据库而广为人知,但水平参差不齐的大量学位论文之外,有必要特别一提的是:因为出版周期等原因而受到的关注相对不足的《史料与阐释》这份颇有特色的专业集刊,也发表过陈捷的《〈京报副刊〉综述》《〈京报副刊〉总目分类汇编》(总第2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沈杰飞的《我与八年抗日战争中的〈扫荡报〉》(总第4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颇有参考价值的文字,——尽管前者的内容,在同一作者的个人专著《〈京报副刊〉研究》(台北花木文兰出版社2016年版)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
此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上海“孤岛”时期文学报刊编目》等工具书开创的报纸副刊编目工作中断三十年之后,得到了复兴和延续。刘晓丽教授主持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中,日本学者大久保明男编著的《伪满洲国主要汉语报纸文艺副刊目录》,辑录了《满洲报》《盛京时报》《大同报》《滨江时报》《滨江日报》等五种伪满时期重要报纸的近40种文艺副刊目录,并对相关报纸副刊的情况做了简要而准确的“解说”。据笔者所见,这是自上海鲁迅纪念馆内部印行的《申报自由谈目录(1932.12-1935.10)》起,第一种不再是报刊混合,而是对报纸副刊进行编目的专门著述,有体例上的开创之功。
第二、出现了一批以副刊史料为依托,试图通过梳理副刊史料本身,或者借助于新理论,对相关问题做出新阐释的论文论著。除了大量无法一一列举的单篇论文之外,相关的专著有: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杜素娟《沈从文与〈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杨爱芹《〈益世报〉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雷世文《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以〈晨报副刊〉、三十年代〈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郭武群《打开历史的尘封——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员怒华《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李军《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田露《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1919~1927年北京报纸副刊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赵丽华《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日报〉副刊研究(1928—1949)》(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武军《〈中央日报〉副刊与民国文学的历史进程》(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
通常意义上的“近代文学”领域,也有不少性质相同或者接近,同时也提供了不少史实线索或值得借鉴的思路与方法的论著。如方晓红《报刊·市场·小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李九华《晚清报刊与小说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汪注《〈申报〉副刊〈自由谈〉初创十年散文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阙文文的《晚清报刊上的翻译小说》(齐鲁书社2013年版)等。
第三、在作家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大量从报纸副刊中发掘新作品和新材料的“史料学转向”,对此前以文集和杂志为中心的基础史料视野,构成了重要的丰富和补充。近十年来,业内各专业刊物的“佚文”和“集外文”,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大量以内容属性划分的“期刊集成”和报刊,尤其是报纸数据库。这些成果,虽然总体上属于将“副刊文献”理解为“副刊里的文献”,循着“因人究史”的思路,从中搜索和抽取各自所需要的部分纳入作家研究或者文学史专题研究,但换个角度,却也为研究者了解相关副刊的基本情况,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线索。
第四、从历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等规划项目立项情况来看,报纸副刊研究也一直未曾中断。前面提到的郭武群《打开历史的尘封——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研究》、员怒华《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研究》、李扬的“民国时期文艺副刊检索系统”,王巨川的《〈盛京时报〉副刊研究》,以及笔者的“抗战大后方重要报纸副刊研究”等项目,都得到了上述基金的支持。此外,大量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之中的专题文献数据库,也都明确把副刊文献纳入了研究范围。
主要的成就
综上所述,抛开1949年之前零星的“史前史”不算,严格从《山西文艺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等开始的调查与整理算起,现代文学的副刊研究已经断断续续走过了60年,在原始资料的保存、工具书的编纂、深入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一)大量的副刊史料得到了整理和保存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影印保存《解放日报》《东北日报》《新华日报》等重要“革命文献”开始,“仅次真迹一等”的影印再版,就成了我们保存包括文艺副刊在内的现代文献史料的重要手段。60年下来,积累了大量方便查阅和使用的原始资料。《申报·自由谈》《中央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副刊、《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新华副刊》等重要文艺副刊,或者因为单独影印,或者随报影印而成为了比较容易获取的资源,也成为了大量论著和学位论文反复取材的研究对象。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各地图书馆以各自的馆藏文献为基础,拍摄和保存了1898—1949年间出版的大部分影响较大、出版时间较长的主要报纸。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中心的收藏,以及后来以缩微文献中心为名出版的一系列重要副刊,就是这项工作的副产品。新世纪以来因为文献技术的创造性突破而迅速普及开来的数据库建设,则以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时期文献总库和上海图书馆的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49)为代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各大图书馆报刊数据库建设工程的陆续推进,必将还有大量的报纸副刊文献得到现代化的整理和保存。
影印、缩微文献和数据库建设,虽然不是专门的“副刊文献”整理和保存,但却极大地方便了对相关副刊的查阅和使用。可以想见的是,随着专门的文艺副刊文献工具书的完成,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会从目前的“已知引导型”检索,转向“未知阅读型”浏览,催生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二)积累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文学、新闻学、图书馆和编辑出版等学科领域,都积累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参考资料。《北京图书馆馆藏报纸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副刊目录(1898—1949)》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以及第二个、第三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还有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资料索引卷》等工具书一起,初步完成了1898—1949年中国报纸副刊总体情况的普查,为我们的的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出版、收藏等文献线索。只不过像《东北新文学大系·资料索引卷》这样将相关史料和线索“抽出来”,编为《东北现代文学篇目索引》这样的工具书,需要“倒过来看”,从中寻找和还原相关史实。
《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晚清报业史》《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20世纪中国编辑家研究资料》等新闻、编辑和出版史等领域的重要论著,以及部分编纂水平较高的地方新闻史志,等等,则为进一步了解“副刊周边”的人事变迁、政治纠纷等历史事实,提供了必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史实和线索。
此外,《鲁迅年谱》《郭沫若年谱长编》《叶圣陶年谱长编》《蔡元培年谱长编》等不胜枚举的近现代文人年谱,以及樽本照雄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刘永文的《晚清小说目录》《民国小说目录》等专业工具书,虽然都不是专门的副刊研究论著,但也为我们“倒过来”循着其中的史实或线索顺藤摸瓜,了解有关报纸副刊的基本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地方性的“报业志”“出版志”领域,也积累了一批诸如《桂系报业史》《湖北报业志》《江苏报刊编辑史》等一批水平较高或者史料线索丰富的论著。
(三)积累了丰富的编目成果与经验 撇开袁省达在1978年“内部发行”的《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上预告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却因故夭折的《申报·自由谈》编目不算,从1981年5月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申报自由谈目录(1932.12—1935.10)》开始,中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抗战文艺报刊编目》及其《续编》,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上海“孤岛”时期文学报刊编目》,再到大久保明男的《伪满洲国主要汉语报纸文艺副刊目录》,成果总字数将近200万,在报纸副刊的编目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的成果。这些成果,尤其是《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续编》等几种早期编著,虽然因为限于当时所能查阅的资料而存在不少空缺,但也为进一步的编目等整理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工作经验。
(四)“副刊文献”理念的初步浮现及相关研究 尽管目前的总体趋势仍然是把“副刊文献”理解为“副刊里的文献”,把报纸副刊当作存储作品和材料的容器,但在李欧梵提出的“公共空间”“生产机制”等理论的带动下,仍然有不少研究者开始自觉地把“副刊文献”和“副刊里的文献”区别开来,注意到了报纸副刊在制造话题和现象,规划现代文学新方向等方面的生产性功能。田露的《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1919—1927年北京报纸副刊研究》关于副刊功能的转变与文化人的转向、20年代副刊读者群之形成等问题的探讨,段美乔的《投岩麝退香——论1946—1948年间平津地区“新写作”文学思潮》(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对沈从文在抗战胜利后如何通过平津地区的报纸副刊引领“京派”的复兴,实践自己的“新文学”理想的分析,就是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著述。雷世文的《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以〈晨报副刊〉、三十年代〈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研究》一书,虽然总体上未能真正将“文学生产”的思路落实到研究之中,但也注意到了这个新思路。
主要的问题与不足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60年来的副刊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问题与不足,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关注。
(一)薄弱得近乎空白的副刊编目 尽管现代文学研究者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把文艺副刊纳入了现代文学基础史料工作的范畴,八十年代启动的大型史料工程“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更是明确提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书籍、期刊和报纸文艺副刊”,即我们的所谓“书、刊、报”三者并重的目标,但迄今为止,报纸副刊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却依然是三者之中最为薄弱——甚至可以说是近乎空白的环节。
撇开因为有传统的古典文献学经验和规范可以袭用的书籍文献工作不谈,以现代文学学科基本工具书的编纂而论,期刊领域先后出现了460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700余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和500万字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青岛出版社2015年版)等权威著作,圆满地完成了相关期刊的叙录和编目工作。如果考虑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从1965年开始,到1985年全部出齐,近1300万字的综合性《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以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以70余万字的篇幅,收录了从《瀛寰琐记》到《文学杂志》等44种近代“文艺杂志”,以及前面提到的《晚清小说目录》等几种工具书的话,甚至可以说这个领域的文献普查和编目等工作,甚至出现了拥挤和重复。
相形之下,包括《申报自由谈目录(1932.12—1935.10)》《福建新文学史料集刊》《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等内部资料在内,零星分散在各种工具书和研究著作(如《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解放日报·文艺〉研究》)“附录”中的副刊目录,总数不到200万字。迄今唯一的一部专门工具书《伪满洲国主要汉语报纸文艺副刊目录》,也只有29万字。这些成果,不仅数量少,而且零散,缺乏系统。大量报纸副刊的基本信息,分散在新闻史、文学史、图书情报学、出版史和地方史志资料等领域,没有得到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梳理与整合。也正因为缺乏全面的梳理和整合,目前已经有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一方面是大面积重复,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存在空白的情形。撇开大量学位论文不说,即便以目前公开出版的论著来看,对《大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申报》《解放日报》《华商报》《益世报》《晨报》等后来影印出版过,因而查阅和复制相对较为方便的报纸及其副刊,尤其是《晨报副刊》《申报·自由谈》副刊、《新华日报》副刊、《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研究,实际上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拥挤和重复。另一方面,则是数量庞大的既没有影印出版,也没有在上文提到的有限的几种工具书里得到编目的报纸副刊,仍鲜有人问津。
(二)“新材料”讲述“老故事”的学科困境 总体说来,研究者以报纸副刊为依托,发掘了不少“新材料”,也发现了不少“不应该忘记”的作家作品,在作家佚文考辨等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绩。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各大图书馆数据库的建设和陆续开放,“新材料”的发现更是突飞猛进,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持续不断的“学术增长点”。但就在以数据库为依托的报纸副刊“新材料”大量涌现,形成了所谓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以“现代文学史料学”“现代文学文献学”为题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同时,要求现代文学研究在基本格局和总体框架上有所突破的呼声,却也明显越来越高。“大文学”“民国文学”“磨合期文学”等近年来出现的宏大命题,虽然具体内涵和指向各有千秋,但在呼吁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和结构性创新,而不仅仅是局部的修补和完善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这也就是,现代文学史的总体格局和基本面貌,并没有随着所谓的“史料学转向”而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大量的“新材料”,总体上讲述的还是“老故事”。相反地,不少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新材料”,如伪满洲国文学史料的大规模整理和研究,却不能进入既有的文学史叙述框架,而只有在“东北学”“满洲学”等非学科概念里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回应。
这当然不是要否定发掘和运用“副刊里的史料”,对通行的文学史叙述进行局部和细节的完善,通过日积月累的进步来推进现代文学研究“问题化”与“再出发”的可能,更不是要否定“新材料”的学术意义,——甚至,也不是要否定讲述“老故事”的必要性。学科越成熟,研究也就会日趋精致化。而“老故事”也只有在不断的讲述中,才能成为一门学科稳定而不变的基础性前提。而是说,如何不仅仅停留在“新材料”讲述“老故事”这个基础性层面上,而是更进一步,在“新材料”与“新问题”的良性互动中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范式,也是我们必须予以考虑的现实问题。
没有这种总体格局和基本框架上的结构性突破,就很难摆脱“老故事”背后的“文献感觉”和知识视野的限制,发现更多的“新材料”。不挣脱以书籍和期刊为中心的“文献感觉”和知识视野的限制,也就很难真正把“副刊文献”当作文献类型意义上的“新材料”来对待。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史,也就会一直以其相应的叙述框架和知识视野,支配着我们对“新材料”的拣选和发现,把各种各样的“新材料”回收到“老故事”里面,变成仅只有局部和细节意义的“新发现的材料”。
不少看起来以“新材料”为基础,表面上是“史料推动型”的研究,最终变成了文学史的具体环节和特定问题掌控之下的“问题引导型”研究的根源,其实就在这里。材料和对象是副刊,结论却跟以文集、期刊为对象的研究没有什么区别,仍然是学界早已经熟悉的说法。
(三)纸质文献和数字资源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和交流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长期来看对学科发展的伤害或许更为致命的问题,则是大量的纸质文献和数字文献资源之间,目前还缺乏有效的交流和互动。这个问题的一方面,是不少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固守长期以来形成的以书籍、期刊等纸质文献为对象的“文献感觉”和知识视野,把近年陆续投入使用的大量数据库资源当作对前者的补充和丰富,由此而形成了以前者之“无”为标准,转而利用数字文献之“有”,从各种数据库中抓取文献,转化为纸质形态的“佚文”和“新材料”的趋势。
不能低估这种做法在维持学科生态系统中的基础地位,甚至也不能否认这些成果对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必须看到大量“新材料”背后隐含着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根深蒂固的“纸质文献中心主义”依然牢牢地控制着不少人的“文献感觉”和知识视野,大量还在不断迅速增长的数字文献则被推向后台,变成了传统纸质文献的补充和附庸。长此以往,“纸质文献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史料学工作,也就很难经得起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自我质疑。
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庸俗进化论思想的作用下,反过来认定既有的纸质文献可以彻底被新兴的数字文献所取代的“数字文献中心主义”。从可操作的,因而也是可以规范化和形式化的技术层面来看,这样的说法当然没有错。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数字文献也可以重新还原为纸质文献。但从主导文献类型的变迁和知识增长的角度来看,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以视觉为中心的书写文献及其相应的知识规则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以听觉为中心的口传文献及其知识规则的消亡或者失效,而是意味着我们由此而拥有了更多的文献类型,和更多的知识规则,我们的“文献感觉”和知识视野变得更丰富、更细腻了。同理,大量数字文献资源的出现,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可以压倒一切,取代一切的唯一有效的文献类型和知识规则的出现。这样的理解,反而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只是这个牢笼看起来更精致,更有迷惑性而已。
更重要的是,作为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基础性环节的文献工作,也不能大刀阔斧地简化为可以规范化和形式化的技术问题。不说口传文献,就拿我们相对比较熟悉书写文献来说,与书籍日夕相处中涵养出来的冷暖自知,但却很难形式化和规范化的“文献感觉”,显然就不能转化为数字文献工作领域的“文献感觉”。长期来看,这种身体化的“文献感觉”,或许才是学科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有之不必然,无之则必不然”,有这样长期涵养而成的“文献感觉”,不一定就会有第一流的成果;但没有,则一定很难有。
所以,如何从文献类型和知识类型的角度,既打破长期以来“纸质文献中心主义”,也反对同样简单的“数字文献中心主义”,充分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带来的新可能,在纸质文献和数字文献充分而有效的交互融合中重新塑造我们的“文献感觉”和知识视野,为现代文学的基础史料工作开辟“第三条道路”,不仅发现和运用新史料,同时也兼顾理论探讨和建设,也是目前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四、尽管我们在梳理相关成果的时候,指出了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副刊文献”不仅仅是“副刊里的文献”,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副刊文献”的事实,但仍然有必要加以强调的是:把“副刊文献”理解为“副刊里的文献”,从而将其“书刊化”的做法,仍然是目前的占主导地位的通行思路。如何立足于“副刊文献”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将其理解为虽然由具体的、个别的文献叠加和组合而成,但却在叠加和组合中生产出了无形的“溢出效应”,因而不能简单地倒过来分解和还原为个别文献的“副刊文献”来处理,以真正意义上的“副刊文献”整理与研究来推动现代文学基础史料工作的变革,也是必须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
未来的可能与挑战
基于上述情形,如何一方面“跟着做”,在既有学科格局和研究范式之内“跟着做”,一方面则把“副刊史料”从“保存在副刊里的现代文学新材料”,变成一种类型意义上的“新材料”,推动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化”与“再出发”,也就成了副刊研究未来的方向与目标。
第一、在基础文献工作这个层面,毫无疑问应该继续“跟着做”,填补现代文学基础史料工作的结构性空白。具体而言,就是循着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提出的“书、刊、报”三者并重的现代文学基础史料建设目标,以“丙种”丛书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和后来的《新编》《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等工具书为榜样,整合分散在出版史、新闻史、地方史志等不同领域的成果,补齐副刊史料编目工作长期以来严重落后于期刊的薄弱短板。
第二、研究上,则“跟着做”与“再出发”并重。所谓的“跟着做”,就是在通行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框架内部,以从“副刊里的文献”中发现的“新材料”,和作为一种类型意义上的“新材料”的“副刊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对现代文学史上的相关问题做出新的阐释和叙述,补充、完善或修订通行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当然也是用“新材料”讲述“新故事”,只不过这里的“新故事”是现代文学内部的“新”,而不是整体叙述框架或者只是视野意义上的“新”。
而“再出发”,则是借鉴“域外汉文献研究”“近代小报研究”等领域的学术经验,把通行的文学史叙述框架从拣选和定义“新材料”的默认前提,转化为一个可以,而且有必要给予检讨和反思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作为一种文献类型意义上的“新材料”的“副刊文献”为立足点,从整体上打开现代文学学科的“文献感觉”和知识视野,在通行的文学史叙述框架之外,打开另外一种进入和书写历史的可能,以此避开用“新材料”讲述“老故事”,材料和对象变了,但使用材料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却和书籍、期刊没有什么两样的困境。
第三、立足于数字人文研究的未来趋势,探索纸质文献和数字文献不仅在知识上,同时更在“文献感觉”的养成上能够彼此交融互补的可能性。放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中来看,只有这样的探索,才能最终实现口传文献、写本文献、印刷文献和数字文献之间不仅在资料上,更在“文献感觉”和相应的解释学理论方面的互补。文献不仅是方法,更是创造和拓展新理论的理想目标,也才能在这种较长时期的探索之中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