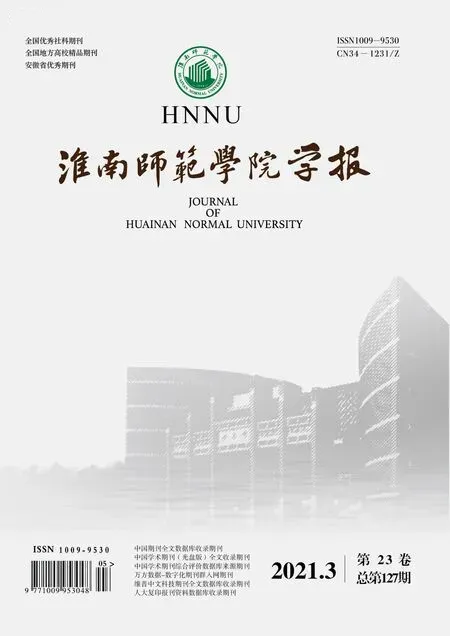晚清徽州地区禁烟问题探微
——以《陶甓公牍》为中心
邓高翔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陶甓公牍》一书收录了大量徽州知府刘汝骥任职期间的公文、信扎、告示、书函、社会调查等原始文献,其内容涉及晚清徽州地区的政治、经济、人文、风俗、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尤其集中记载了刘汝骥在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在徽州担任知府时所颁布的一系列施政方针,是研究清末新政在徽州地方具体实践的丰富而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陶甓公牍》又是刘汝骥对徽州进行社会调查的文献汇编,辑录晚清徽州社会的史料内容详实,例如晚清徽州地区弥漫的“烟赌”问题、底层社会的士绅冲突、封建宗法制度的瓦解与消散、衙役胥吏与地方势力的勾连等,这些丰富而又珍贵的文献是窥探晚清徽州地区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为徽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本文通过对《陶甓公牍》所载资料进行深度挖掘,以“禁烟”为切入点,探讨晚清徽州的社会秩序与内在矛盾,以期间接还原晚清徽州社会的真容实貌,为学界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禁烟背景
鸦片,原名罂粟、阿芙蓉,在诸多中医药方中可见,如缪希雍《先醒斋广笔记》“于中甫长郎,痘患血热兼气虚,先服解毒药后,毒尽作泄,日数次不止,痘平陷矣,仲淳以真鸦片五厘加炒莲肉末五分米饮调饮之,泄立止”[1](P62)。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治疗泻痢一病时也有记载“用白罂粟米三合人参末三大钱、生山芋五寸、细切研三物以水二升三合煮取六,合入生姜汁及盐花少许、和匀分服、不早晚亦不妨别服汤”[2](P1090)。可见罂粟一直是中医治疗泻痢的药材。
然于近世,西方列强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向中国倾销鸦片,诱使中国人患上鸦片烟的毒瘾。《壶天录》对吸食鸦片的情形进行了真实的描写:“一灯相对,短榻横陳,味傲煙雲自乐其乐,洎乎强仕之岁竟游泉下。病時无力呼吸,倩人吸烟喷之,无少间殁。”[3](P97)染上鸦片烟瘾以后“面皮顿縮,唇齿齞露,脱神欲毙”[4](P6),俗称“烟鬼”。
但清廷各级官员对于鸦片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弛禁派认为内地种植“土烟”可以冲击“洋烟”,扭转鸦片贸易的颓败趋势。不仅不严禁鸦片,反而在本土大力推广鸦片的种植,将鸦片生产贸易本土化,试图通过自产自销对抗“洋烟”在贸易经济中的冲击。严禁派认为“自此物一入中原,颓惰之人较往代当多十倍”[5](P20),使得吸食者“废时失业,病身败家”,“近见各省,贪种罂粟以其获利倍蓰,而不知其有妨饮食为害甚烈,若不及時禁止則日甚一日,而国将不堪矣。”[6](P22)。长此以往,地无可耕之农,国无可戍之兵,贻害无穷,可见鸦片问题于当时确属第一顽疾。
徽州地处峰峦掩翠、层峦叠嶂的万山之中,地理环境闭塞,其风最古,早就享誉内外。近世以来,鸦片内流,荼毒乡野,底层民众染上吸食鸦片罹患烟瘾者数不胜数,“程朱阙里,文献之邦”的徽州也难以幸免。
1840年以前徽州地区极少有鸦片的种植和生产贸易,风俗淳正的徽州地区也少有沾染烟瘾之人。鸦片战争的冲击和“驰禁派”错误的禁烟主张,导致安徽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范围进一步扩大,吸食鸦片的人员数量进一步激增。数年之后,安徽鸦片的种植遍布皖南皖北。“据日本外务省统计,1906年仅凤阳、颍州和徽州三府就出产约四五万担”[7]。如绩溪一县由于吸食鸦片人数陡增,沾染烟瘾之人不事生产,“生产者约十分之三,不生产者约十分之七,故生计日贫”[8](P270)。底层民众“渐趋于烟赌两途了”[8](P270)。刘汝骥在《徽州府禀地方情形文》中记载:“微俗不论贫富,吃烟者十人而六七,面黧骨削,举目皆是”[8](P157)。
对于吸食鸦片的管控时紧时驰,鸦片遂逐步流毒于中国。“鸦片烟迟禁以来,流毒几遍于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沈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9](P5570)。刘汝骥主政徽州期间恰好是清末新政推行之时,刘汝骥在颁布《劝禁缠足示》中明确指出“照得中国痼习为环球所诟病者有二:曰吸烟,曰缠足”[8](P4)。而在此时的徽州地区,吸食鸦片已经屡见不鲜,这些鸦片的吸食者,终日无所事事,成群吸食,“今四民皆困穷,孜孜谋利之不暇,其劣者又惟惟嗜赌嗜烟,终日群居,更无复雅人深至”[8](P248)。甚至是口诵佛经的宗教信徒,也沾染了吸食鸦片的恶习,“释教口诵牟尼而若辈多嗜烟癖赌”[8](P235)。徽州僻处山陬,生利单简,以农事为惮,沾染烟瘾的“烟鬼”一般都群居吸食,不事生产,更无心生计,民风逐渐恶化。徽州地区以刘汝骥为代表的一批开明官绅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认为吸食鸦片乃是“人人痛心疾首之事,地方官尚不能实力铲除,则一切新政皆属空言”[8](P202)。面对如此窘境,禁绝烟瘾,端正民风,恢复农业生产则势在必行,徽州知府刘汝骥认为试行新政“自当以痛除烟赌为第一要义”[8](P202)。
二、禁烟措施
(一)管控烟馆,遏制源头
刘汝骥在主政徽州期间,试图勒令所有烟馆在规定时间内“限律闭歇”,彻底禁绝。但徽州民众沾染烟瘾的痼习已久,很难在短暂的时间内铲除徽州境内的烟馆。短期内采取“一刀切”的高压政策不仅触动了烟贩、毒枭的最终利益,更容易激化官民矛盾,导致禁烟效果适得其反。为了缓和官民矛盾,减少禁烟的阻力,刘汝骥采取“宽旧染,严新吸”的原则,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逐步减少烟馆和烟民的数量来达到预期的禁烟效果。
实行禁烟,关键在于遏制源头,烟馆是烟民汇集之所,是烟瘾恶习所匿藏之地。烟馆多设于闹市之中,四壁皆是短榻,内设精致,一进烟馆便异香扑鼻,随处可见罹患烟瘾者“短榻横陈,吞云吐雾”之景。《烟草谱》有记曰:“置灯擎于床,持竹筒若洞箫者横卧而吸,其烟必两人并卧”[4](P6)。
烟馆为了招揽顾客,经常会运用特殊手段,以“减价促销”和“广而告之”的方式吸引鸦片吸食者。“欲推广销路,是以减价出售,零趸公道”[10]。甚至通过“免费吸食”的方式来吸引好奇者和贪图小利的底层群众,往往穷苦的底层民众最容易沾染烟。沾染烟瘾之后,终日精神恍惚,烟瘾发作之时“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萎顿不能举”[4](P6)。
烟馆的存在为鸦片的销售和烟瘾的弥漫打开方便之门。刘汝骥主政期间已经深刻认识到鸦片烟馆的弊端所在,是以他在《严禁烟馆示》中指出:
照得开灯烟馆勒限六月底一徘闭歇,历经颁示晓谕在案。近奉各大宪这谆谆告诫,至再至三。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埠凡以烟馆为生活者,无不幡然改计,舍其旧而新是谋……徽郡处万山之中,地瘠民贫,生利者少,分利者多,自当以痛除烟害为求治人手之办法。近据各县禀报,凡开灯烟馆遵限律闭歇。 本府何忍以不肖之心逆测我百姓,惟恐无知愚民得过且过,旦夕偷安,沉迷不返。其尤黠者,或勾结吏胥虎前作伥,或改换门面壁后置人,或昌言文诰不足畏,法律不足恃,招致无数惰民虱处于覆舟漏室之中,致有野蛮之举动,似此莠民岂容姑息?本府执法无私,除恶务尽。其悔过自新者,则是朝廷之好百姓,本府之好子民,本府当矜之恤之教育之;其仍有梗顽不化者,则是不有本府之言也……示仰阖属士绅人等一体查照,劝禁其以烟馆为生涯者速速改图他业,毋再存死灰复燃之梦想。经此次申示以后倘仍不知悛改,则是冥顽不灵,自甘化外,一经查明,定即饬拿到案,烟具销毁,房封入官,轻则量予科罚,重则发充苦工,其勿悔。切切!特示。
刘汝骥在给歙县候补县丞汪达增的禀批中批示“禁烟为现今第一要政,乡间私开烟馆尤为地方之害,长此漫漫 何以复日?”[8](P39)。对于禁食鸦片,禁闭烟馆的迫切性刘汝骥已经深有体悟。“披阅来牍,于徽属禁烟现象言之极中窽窍,所拟《现行办法》及《造册发照章程》亦极精核,均可见诸施行,嘉许何已!候即通饬各县切实照办。刊刷门牌册式所费无多,应由县捐廉给发,未便按户收取。请发委员封条一层,倘办理不得其人,或稍涉操切”[8](P39)。将禁烟《现行办法》刊印成册,按户分发,以儆效尤。
对“无知愚民”“狡黠之人”进行严厉的呵斥,对那些执迷不悟、偷偷吸食烟瘾患者和勾结胥吏的烟馆的老板必定依法究办,绝不姑息。他对以往开办烟馆之人不再追究,并劝诫以烟馆为生者早日改图他业。罹患烟瘾吸食者倘若能在限期之内,解除烟瘾,也既往不咎。以烟业为生却不知悔改,若敢于再犯,轻则“烟具销毁,封房入官”重则“饬拿到案,发充苦工”。刘汝骥认为禁闭烟馆即是扼住烟毒之源头,鸦片走私的数量会逐渐减少,与之相应吸食鸦片的人数也会逐渐减少,“少一吸烟之人,即多一有用之人”[8](P157)。 他认为戒烟并非难事,只要政策得当,循序渐进,引导有方,“有冻死饿死之人,断无瘾死之人”[8](P157)。刘汝骥严禁烟馆的告示一经发出“凡以烟馆为生活者始懔然不敢再犯,以此感悟者不少”[8](P15)。
(二)清点造册,领照吸食
清政府虽然明令禁止吸食鸦片,颁布了一系列吸食鸦片的惩治法案和条例,但是吸食鸦片的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鸦片烟瘾的戒除绝非一朝一夕,刘汝骥根据“严新吸,宽旧染”的原则,都率各地绅董将各地吸食鸦片的人数统计清楚,将鸦片吸食者全部登记造册,发给照牌。在给歙县乡绅蔡令世的信中写到“戒烟人数翔实调查,造册通报,是为至要”[8](P28)。在掌握和了解吸食人数的基础之上,严格控制新沾染烟瘾的人数,并发给照牌,吸户则按牌定额定点购买烟膏,并在牌照之上明确记录该吸户户主的籍贯、年岁、父母、妻妾、子女,包括兄弟子侄的人丁数量,并且将照牌悬挂门首,听候稽查。
对于暂时未禁闭的烟馆依旧严加控制,“仍须严为限制,以次递减,紧要关键义非将膏店凭照、吸户牌照办成不可,否则无从稽考,于事终无济也,仰即切实办理,并依限办竣,造册具报为要”[8](P39)。对于无照经营、私自开办的乡间烟馆给予坚决打击。在给休宁乡绅刘敬襄的禀批中明确写到对非法经营烟馆的处理办法“乡间私开烟馆,倚捕保为护符自所难免。应责成信实可靠之绅士查实,即行照章充公,以为房主贪图小利者警”[8](P39)。他认为,吸食鸦片的人固然可恨,但是兜售鸦片、诱使民众沾染烟瘾并从中牟利的烟馆更为可恶,正所谓“吸户可宽,烟馆断难曲贷”[8](P39)。
晚清徽州地区烟赌娼妓时常伴随一起,不少烟瘾之人躲在“娼寮”之中吸食鸦片,“娼寮”并无牌照,属于违令私贩烟土,对违反禁烟令的“伪君子”和娼妓,一律依法严办。绩溪有葛玉恒、程灶祚二人,躲进妓院吸食鸦片,当场被抓获,本应该详革例办,当地官员仅仅是通过“罚洋宽免”。刘汝骥认为此举未免有轻纵嫌犯之疑,遂特批绩溪县新任县令“立即发封变价,拨充巡警经费,一面勒拿该娼妇到案 提同葛玉恒等研讯明确,分别斥革详办,并移该代令知照”[8](P120)。足以可见他对禁烟的重视程度。
发放牌照,定点定量吸食既可以保证禁烟运动循序渐进地开展,减少鸦片的吸食和吸食者的数量,又可以将鸦片买卖的权利收归官有;而且通过颁发牌照收取税费和附加费用,不仅增加财政收入,也加强了对民间私贩烟膏的管控。
(三)宗族自治,乡贤共举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峰峦重叠,兵燹咸至,战火纷飞之年,北方不少大族举族迁居此地
“族大指繁。蕃衍绵亘,所居成聚,所聚成都。未有新安之盛者”[11]。徽州宗族均设有祠堂,祠堂之内又制定约束族人的族规家法。赵华富认为“族规家法是以族长为核心的房长、文人、乡绅等统治者们统治广大族众的主要工具”[12](P66)。
刘汝骥深刻认识到徽州地区宗族之间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自井田既废以来,其无常业无常居 者目皆是,或至比邻不相识。独我徽之民聚族而居,家有祠、宗有谱,其乡社目多沿袭晋唐宋之旧称,此海内所独也”[8](P28),并且十分赞同宗族社会,修建祠堂、续修族谱的行为,“今稍稍陵夷矣,强宗豪族或时结党纠论之事,然不数见也。乾隆中叶,江西巡抚铺德致有‘毁祠追谱’ 之疏,此可谓因噎而废食”[8](P29)。“就徽言徽,因势而利导之,此其时也。由一族而推之各族公举贵且贤者以为族正,由地方官照会札付以责成之……地方自治此其初哉首基,岂独戒烟一事哉?愿贤有司及各绅交勉之也。候录批札行所属各县一律推广,切实举行”[8](P29)。
徽州宗族是官府统治地方社会的得力助手,利用宗族社会进行地方管控,能弥补官府行政力量的不足,通过宗族力量将政府力量渗透到底层社会,可以加强政府对底层社会的管控。“独其联合各绅创文族柯戒烟社以辐官力之所不足,意美法良,此则为他县米有。鸣呼!”[8](P28)。利用宗族力量禁绝鸦片,是非常具有创见性的举措,刘汝骥正是认识到宗族势力在地方上的作用,才会大力鼓励各大宗族内部开办“族祠戒烟社”辅助官府戒烟力量的不足,通过宗族士绅之间商定,制定各族戒烟祠的具体章程,“族祠戒烟社事,弟已录批通饰各县年举行,将来未尽章程尚赖我公之手定”[8](P196)。他对宗族自办戒烟祠颇为赞赏,“黟县胡令所办族祠戒烟社甚为可法……并调查祠数报告为盼”[8](P199)。刘汝骥寄希望于宗族自办戒烟社能够肃清地方社会的鸦片烟患,以宗族为单位加强对底层社会的管控,同时依托宗族势力维护地方统治,以淳风俗。也正如唐力行所说“宗族不仅担当着教化、教育互济、公益建设等自治职能,而且担负起治安、司法、赋役等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13](P215)。
(四)加强官差、士绅的管控
严禁官员吸食鸦片,以端表率,有罹患烟瘾的官员,可以自行陈明,但需在一月之内,不论大小官员一律戒断,如有不按期戒律者、互相隐瞒者一律从严法办。“照得戒烟一事禁例甚严,‘十年限满’ 此系为六十以上老有废疾者而言。近奉朝廷严旨,凡大小官员一律戒除,皆须出具切结。尔书差等均系庶人,在官尤当谨遵法律,其有素染烟癖者,亦即自行陈明。本府并不苛求,限一月内实行戒断,照旧当差;其有互相隐瞒者,本府一经查出定即责革不贷”[8](P8)。
刘汝骥将林则徐戒除烟瘾的“忌酸”“补正”药方进行推广。他认为:“戒烟并非难事,林文忠公忌酸、补正二方最为有益无害,近日海上[上海]所售亚支奶戒烟药亦曾经化验无吗啡毒质,皆可购服。总之,无论何药皆可戒除,只在此心有恒。有饿死冻死之人,断无瘾死之人;有吸烟日瘦弱之人,断无戒烟后不强壮之人。此理至明,望而知。若因循不戒,再迟数年,试问腰缠十万将从何处购买乎?”[8](P8)。
对于罹患烟瘾且冥顽不灵的差役,将其送监关押,勒令限期戒烟,“着即勒令戒断,至看守夫役如有递给烟泡、互相隐朦情事,查明一律究办”[8](P112)。在禁烟问题上,刘汝骥对于基层士绅集团的管控明显加大。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祁门一县划成五区,各地都要公选议员。人口的多寡和地方广狭是议员分配匀当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为了选举出“德才配位”的选举人,各地区所选之人必须要“另册开呈”公布所选之人的名单,“必须将年岁、出身、官阶、品望、财产、吸烟已戒未戒,均一详细查明,不得含糊了事”[8](P139)。
刘汝骥对被选举人的德性相当重视,对其是否染浸烟瘾亦详加考察。如有吸食鸦片的陋习就与“选举资格”不符,继而不得被推选。“近日烟禁森严,绅士为齐民表率,不闻有具结一督责之条,有嗜好者帖然如故也。欲望澄清,必严加陶汰,而后可言资格”[8](P291)。“向章,都董无记功记过之举,洁身自爱、表率一乡者固有,世家相授、夤缘滥竽者亦在所不免,故公益多未振兴,私德又属缺憾。如某董之犯吸烟、某董之疲玩学务,拟自今始先行记过,以观后效,其如何记功,容拟另章”[8](P236),“凡有嗜好或未经断净之人,概不准充当各项董事”[8](P36)。黟县武生汪凤标在当地,暗售烟吸,私开烟馆,刘汝骥得知后勃然大怒,批道“借土店门面以为影射藏奸之计,致被查罚,实属孽由自作。乃任意牵砌,希图泄忿。须知本府疾烟更严,郡城迭饬拿办不知凡几,该武生岂无所闻? ”[8](P31)。
三、晚清徽州禁烟成效不足的原因
(一)社会的动荡不安
刘汝骥任徽州知府是光绪三十三年,即公元1907年,此时正是清政府推行预备立宪之时,清末预备立宪是清廷挽救风雨飘摇的封建政权的无奈之举,此时的清政府吏治腐败,官僚运转体系早已腐朽不堪,而地方性的禁烟问题,需要依靠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去推行。晚清封建社会的法制十分不健全,尽管光绪时新法令《会议政务处大臣筹拟禁烟章程折》等禁烟章程和法令都有明确的禁烟措施,但是自从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侵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手湖广总督张之洞起草《东南互保章程》之后,清廷各地方政府就已经分崩离析,各自为政,难以做到令行禁止、上行下效。
禁烟一事涉及太多既得利益者。首先封建官僚就无法禁吸,甚至不少的封建官僚私贩烟土,从中牟取暴利。对于烟瘾患者而说禁烟也绝非易事,烟瘾发作之时四肢无力,眼神空洞,涕泪交横,精神奔溃至几近疯狂。当时医疗条件设施都比较落后,辅助戒烟的治疗药物效果也十分有限,完全靠个人的意志力难以戒除。当时底层社会还有很多“黑市”私贩烟土,传播源头和烟瘾患者的数量都不能进行有效的控制。
(二)士绅阶层的堕落
为了有效地治理地方,刘汝骥尝试利用地方社会宗族绅士的力量,强调“用本邑人办本邑事”,他从本邑世职、乡宦、举贡、生员中,择其“老成公正”“学识兼优”“热心公益”者充当各局董事、管理员、调查员、统计员等职位。但是各地方的具体情况不一,所选择者也良莠不齐,最后导致“董事父故子袭,彼引此援,能孚物望者实少,更有勾通胥吏,于新令接代时汇缘填入名薄,目不识丁者亦滥竽充数”[8](P291)。可见这些地方社会的被推举之人,并不实心办事,往往最多只能做到廉洁自爱,徒有虚名。对于禁烟之事,只能“以保守名誉为方针”[8](P249)。
这样一来,政府倡导所设立推举的地方自治机构所能发挥的作用不仅大大削弱了,反而适得其反,滋生其他腐弊。“绅士近日烟禁森严,绅士为齐民表率,不闻有具结一督责之条,有嗜好者帖然如故也。欲望澄清,必严加陶汰,而后可言资格”[8](P291)。更有险陂贪狡之人假借义务为名,行其争权攘利之术。“办学堂目的只是在争公费,办邮政目的只在拆私函,办警务目的只在扣饷项、肥身家,办工艺、办戒烟目的只是在勒索捐款、布置私人。”“绅董其貌,奴隶其心,紫朵朱,郑乱雅”[8](P239)“若殷实董事之兼理众事者,如一村公产、一姓祠租、多无薪水,然以无薪水之故,遇事延宕不可究诘,甚至阳受美名,阴图厚利”[8](P250)。地方绅士政府对于差事敷衍了事,甚至还有“结党营私、抗玩官府者”[8](P251)的劣绅充当违法犯罪者的保护伞,政府之权责很难下浸到底层社会,底层社会禁烟治理的难度可想而知。
(三)吏治的腐败
清末新政时期官府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都需要各级官员的积极配合,尤其是底层衙役官吏。在宗族势力庞大的徽州地区往往“皇权不下乡”,真正管理地方必须依靠底层的官吏衙役。晚清徽州的吏治已经十分腐败,地方官吏非法干涉词讼、徇私舞弊,与赌徒烟民相互勾结。尤其是在遇到词讼之事,便开始大展敛财之手段,大现丑恶之嘴脸,“一涉讼事,则差役张牙舞爪以待,曲直未分,弱者废时失业,黠者转因以为利。惟恐其案之速结”[8](P108)。吏役在民间诉讼中贪得无厌,以狡猾奸诈之徒为首群体勾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其疲顽积习深厚,在处理其他政务时常会懒惰拖延、办事不力,甚至勾结不法分子,狼狈为奸,“至于倡优盗贼,所在多而为之隐匿、为之串通者,则亦莫非胥吏。阳取其利,阴蔽其辜”[14]。
除此之外,清末徽州的官吏“串谋诱拐,霸匿不放”[8](P105)。歙县四品封职吴永麟“控县三载,官经两任,迄未提集一讯,不过以一批了之”[8](P115)。这种害群之马只会把持贿蔽,鱼肉乡里。在刘汝骥推行禁烟期间,很多吏役都混差了事,阳奉阴违,将地方治理视为儿戏,将自己手中的权利作为敛财的利器。不少官吏对于赌棍、烟民也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烟民反过来“以衙役为爪牙”[8](P220),寻求保护伞。所以谋求地方自治的难度可见一斑。甚至吏役在履行禁烟职责之中,自己本身就是沾染烟瘾之人,例如一个叫孙金奎的吏役,在被拘押的前一天还念念不忘吞烟抵瘾,“至该革役被拘之夕,本府闻有吞烟自尽情事,讯供系吞烟泡以之抵瘾,实非欲图自尽,并将洋火盒、余存烟泡当堂呈验。诊革役身罹法网尚不思戒除烟瘾,实属冥顽不灵”[8](P112)。
四、结语
刘汝骥在“清末新政”的号角下,采取“宽旧染,严新吸”的方式控制鸦片毒瘾的弥漫,试图通过关闭传播烟瘾源头的烟馆来控制新吸者数量的增长,并采用医药辅助戒烟。同时,他通过颁发“吸户牌照”控制吸食鸦片的人数和鸦片贸易的数量,规范书差衙役、士商绅董的行为,加强士绅阶级的约束,而且寄希望于宗族势力配合政府参与社会底层的治理。但晚清徽州地区吏治腐败,帮办官吏对待政令阳奉阴违,与烟贩、烟瘾之人里外勾结,包庇纵容。甚至不少官吏自己就是罹患烟瘾的伪君子,抑或是与烟馆、烟贩沆瀣一气的幕后操纵者。底层社会民风衰坏,宗族势力开始逐步瓦解,士绅阶级矛盾冲突日益剧烈,宗族社会秩序紊乱,宗族势力对地方社会的管控力逐渐消散,治理能力愈发疲软。
尽管刘汝骥在徽州禁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效,徽民沾染烟瘾的数量得到有效遏制,徽州社会风气有所改善。但从整体禁烟成效而言,依旧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徽州地区绝大多数沾染烟瘾的烟民并没有彻底戒除,大量烟馆也并没有在限期内得到彻底禁闭,包庇纵容烟贩、烟馆的官员胥吏也并没有完全得到严厉惩治。而此时的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纵有开明的官员也很难将政令推行到基层社会。
刘汝骥的禁烟理念和禁烟举措对当今社会的治理仍有一些参考价值。例如刘汝骥首先考虑切断鸦片的传播源——烟馆。切断传播源,是降低烟瘾传播速度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宽旧染,严新吸”的措施也比较容易得到百姓的支持,减少了官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刘汝骥因地制宜,利用徽州宗族社会的特点,采取非常接地气的治理方式,将政府行政力量与宗族势力双重结合,逐步渗透进底层社会的治理当中,根据底层社会的实际情况,多管齐下,这些举措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