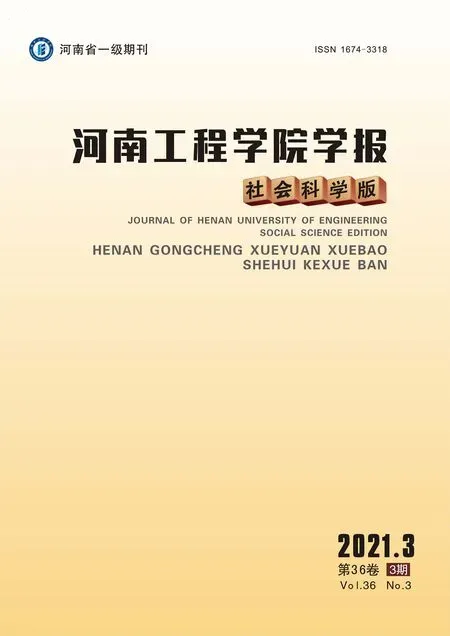钱锺书女性观的多面透视
张钰婧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钱锺书对女性形象的塑造集中体现在长篇小说《围城》与《人兽鬼》中的短篇小说《猫》和《纪念》中,对历史上女性的处境和地位的分析则散见于《管锥编》中。在小说中,钱锺书生动地描摹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女性的生活图景与婚恋心理。近年来,学者们大多以《围城》中的女性形象来分析钱锺书的女性观,普遍的观点是《围城》中的女性形象是残缺不全的,作者是用“男权主义女性价值观的规范来塑造自己作品中的女性”[1]的。《围城》作为讽刺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效果,以此推断钱锺书的女性观失之偏颇。本研究拟从文学作品与研究著作两方面探究钱锺书作为创作者与研究者的女性观,并以杨绛先生的《〈围城〉后记》与《我们仨》作为补充,分析钱锺书的女性观。
一、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女性
钱锺书在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在描写知识女性的婚恋生活时,长篇小说《围城》与《人兽鬼》中的短篇小说《猫》《纪念》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前者以戏谑讽刺的笔触揭示了她们的择偶观,后者则细致地描写了已婚女性的心理状态。
(一)《围城》中的两类女性
在《围城》中,钱锺书刻画了不同层次的知识女性形象。以往的学者多以方鸿渐为中心,将分析的重点集中在鲍小姐、唐晓芙和孙柔嘉三位女性身上,以她们与方鸿渐的爱情纠葛作为线索,而对于其余知识女性如苏文纨、范懿、汪太太等人的研究尚显不足。根据在文中首次出场时的婚姻状况,《围城》中的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未婚女性,如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和范懿,她们的择偶观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另一类是已订婚或已结婚的女性,如鲍小姐、汪太太,她们的行为反映了婚姻或家庭约束下女性的生活状态。
苏文纨是《围城》中学历最高的女性,作者用了两个绝妙的比喻描绘了她首次出场时的“孤芳自赏、落落难合”——“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2]3。在这种“崇高的孤独”的心态下,她将目光放在了方鸿渐身上,对他百般示好。作者细致地描绘了苏文纨这一时期的心理,“在大学同学的时候,她眼睛里未必有方鸿渐这小子。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见(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2]13。苏文纨选择方鸿渐,一方面是为弥补自己爱情上的遗憾,另一方面是认为方鸿渐的家世、钱财堪为良配。她在恋爱受挫之后,仓促地嫁给曹元朗,婚后不到一年的功夫就变得唯利是图、庸俗不堪。这正应了方鸿渐所想,“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2]44。与之相对,唐晓芙的爱情观恰如早年的苏文纨,她珍视自己的爱情,要求自己爱的人没有感情经历,留着空白等着她,这不正是苏文纨在大学时代的爱情观吗?如今的苏文纨或许是从唐晓芙走过来的,至于唐晓芙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苏文纨,则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孙柔嘉和范懿的婚恋结局虽然不同,但婚恋观念有几分相似。二人都对爱情与婚姻心存向往,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孙柔嘉的外表与家世十分平常,起初并未引起方鸿渐的注意,孙柔嘉却暗自布下“天罗地网”,借同事与父亲的压力迫使方鸿渐与其订婚。关于孙柔嘉的性格,夏志清先生曾指出:“柔嘉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刚上场她看起来羞缩沉默,日子久后就露出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这是中国妇女为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培养出来的特性。”[3]这一论断可谓精准。孙柔嘉的性格带有传统色彩,她在追求爱情时也借助了传统的手段。与她相比,范懿的遭遇便让人有几分同情。范懿在赴宴时努力地打扮自己以吸引赵辛楣的关注,这些举动被汪太太一语道破:“她不是来帮忙的,她今天来显显本领,让赵辛楣知道她不但学问好、相貌好,还会管家呢。”[2]239范懿力求在赵辛楣面前表现出传统女性贤惠、柔弱的特质,并且伪造了有许多人追求的假象。比起孙柔嘉的借机造势,范懿的示好与示弱显得不够聪明,看起来像是一场闹剧。范懿不聪明的举动正是基于主动追求婚姻爱情的心理,就这一点而言,一反在婚恋中被动接受的传统女性形象。
鲍小姐和汪太太在文中是十分独特的存在,虽然她们一个已经订婚一个已经结婚,但是她们仍在婚姻的围城之外寻求暂时的“爱情”。鲍小姐的订婚带有反抗旧式家庭的背景,“从小被父母差使惯了,心眼伶俐,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2]13。在利益的衡量之下,她选择与“半秃顶,戴大眼镜的黑胖子”医生订婚;出于对享乐的追求,她在邮轮上与方鸿渐做起了露水情人。汪太太嫁给了年长自己二十岁的丈夫,她有学识,却并不去学校做事,她认为“女人出来做事,无论地位怎么高,还是给男人利用,只有不出面躲在幕后,可以用太太或情妇的资格来指使和摆布男人”[2]229。她与汪处厚的婚姻存在着利用的成分,因而在寂寞的驱使下,她与高松年、赵辛楣产生了暧昧的关系。不同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与范懿追求爱情与婚姻,鲍小姐与汪太太可以说是现实的享乐主义者,她们利用男性达成自己的目的,用婚外情填补情感上的空虚,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反叛。
(二)《猫》与《纪念》
爱默与曼倩分别是《猫》与《纪念》中的女主角,她们的婚姻生活都空虚乏味,但具体表现各不相同。《猫》中,爱默以热爱交际、风流豪爽的形象出现,她与李建侯的关系一度呈现为“女尊男卑”,“建侯对太太的虚荣心不是普通男人占有美貌妻子、做主人翁的得意,而是一种被占有、做下人的得意,好比阔人家的婢仆、大人物的亲随或者殖民地行政机关里的土著雇员对外界的卖弄”[4]23。爱默热衷于举办知识分子参与的茶会,她并不卖弄才情,只是用灵活的外交手段操纵着他们,她的丈夫与宾客都是彰显自己美丽、机智与好客的陪衬品。在得知丈夫不忠后,诱使齐颐谷向自己表白,最终以悲剧收场。《纪念》中的曼倩在大学中没有恋爱经历,正当寂寞之时遇到了才叔,家庭的阻挠反倒促成了他们的婚姻。然而,曼倩在婚后发现才叔并不能在物质和情感上为自己提供依傍,生活与精神上的无聊使她将目光放在才叔的表弟天健身上,与之发展出了秘密的恋情。曼倩本想将天健作为弥补情感空虚的调味剂,最后却陷入自己所嫌恶的肉体关系中。在婚姻中,爱默与曼倩都存在着利用男性的心态:前者视男性为点缀,一旦失去了温驯的丈夫和示好的宾客,便感到“像塌下来似的老”[4]68;后者则想要通过微妙的婚外情弥补婚姻生活的空虚。
在《围城》《猫》与《纪念》中,钱锺书着力塑造了一群走出家门、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性,她们有学识、有能力,有别于旧社会“三从”“四德”的女性形象。“五四运动”后,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浪潮推动了知识女性群体的壮大,钱锺书在小说创作中对她们予以格外关注,不仅看到了女性的进步,而且指出了她们的困境。
如果将旧社会与传统家庭视为“围城”,那么这些女性正是从“围城”中走出去的人。例如:《围城》中苏文纨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足以在当时的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鲍小姐逃离了原生家庭,选择去英国学医;孙柔嘉在大学毕业后不辞路途艰辛,与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前往三闾大学就职。“走出去”的能力与勇气固然值得肯定,但在钱锺书笔下,她们不过是从一座“围城”走向了另一座“围城”。这些知识女性将丈夫视为“职业”,将婚姻视为毕生的归宿,苏文纨从主动示好方鸿渐到下嫁曹元朗,鲍小姐为了出国嫁给其貌不扬的医生,以及孙柔嘉处心积虑地抓紧方鸿渐,都显示出传统婚姻观念的根深蒂固。新式教育能够带给她们才能,却无法带她们走出旧式思想的“围城”。
钱锺书还用讽刺的笔法揭露了当时的社会,“围城”内外对知识女性的态度仍旧是轻视的,如方遁翁所说“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2]33,董斜川更是赤裸裸地指出“女人作诗,至多是第二流,鸟里面能唱的都是雄的,譬如鸡”[2]39。在传统思想中,女性的年龄与容貌、温顺的性情才是婚姻的砝码,“女孩子到二十岁就老了,过二十没嫁掉,只能进古物陈列所供人凭吊了”[2]87,就连赵辛楣也在追求苏文纨失败后表示要找一个老实、简单的乡下姑娘来侍候自己,做她的Lord and Master。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女性很难争取到真正的独立,因为她们在社会上的“一席之地”不过是男权社会的施舍。由此,一些女性走向了传统的对立面,她们一方面依附于男性,另一方面利用男性达成自己的目的或满足自己的欲望,例如汪太太与爱默对爱情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
二、学术著作中的女性观念
在《管锥编》中,有十多篇涉及女性及男尊女卑现象的论述,所占比例并不多。有学者[5]曾指出,钱锺书对女性问题的论述既是对社会与文化问题的重要见解,又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钱锺书在这些篇目里着眼于历史与文献中的“男女歧视不齐”现象,对男尊女卑的历史根源做了十分精彩的论述,并且在行文中流露出对女性处境的理解与同情,其深刻性与同理心在同时期学者之中是非常可贵的。
(一)“男女歧视不齐”现象
历史上的男女不平等已是常识,史学家多从宗法与婚制中指出女性被束缚、被压迫的史实。《管锥编》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选择了《周易》《左传》《史记》《太平广记》《全后汉文》等文献的一些篇目,从语言文字、社会风俗、文学创作等方面分析“男女歧视不齐”这一现象。
就语言文字而言,主要体现在用两性观念与自然界对应,以尊卑加以区别。《昭公十七年》篇中,引《左传正义》,阴阳之书的“五行嫁娶之法”认为,“火畏水,故以丁为壬妃,是水为火之雄”[6]384。这一观念基于阴阳五行,将两性与水、火对应,本无褒贬之义,在汉儒笔下,水与火的地位却产生了逆转。如《白虎通·五行》篇:“火者、阳也,尊,故上;水者、阴也,卑,故下。”[6]385已然将阴阳上下的性质与方位对应了尊卑。这一观点在宋代得以延续,并进一步地用于说明两性尊卑。如邵雍《击壤集》卷一六《治乱吟》之四:“火能胜水;火不胜水,其火遂灭。水能从火;水不从火,其水不热。夫能制妻;夫不制妻,其夫遂绝。妻能从夫;妻不从夫,其妻必孽。”[6]385这显然已经将水、火用来比喻夫妻人伦,以“水能从火”作为女性应当顺从丈夫的“天德”。至此,本无性别的水、火被赋予了两性尊卑特质。同理,“雌雄”体现出的男尊女卑就更加明显了,如宋玉《风赋》:“……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6]1394钱锺书先生指出,雌雄在此为贵贱之别,“王庶之判贵贱,正亦男女之别尊卑(sexism)也”[6]1394。钱锺书还指出,文字也能反映出对女性的轻视,如“义训之不美不善者,文多从‘女’傍,‘奸’、‘妒’、‘妄’、‘妖’之属”[6]1639。在这些字眼中,“妒”往往被视为女性的“恶德”,从字面到字义,无不显示出对女性的贬低。
在社会风俗中,男女不平等体现为双重的道德标准。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对女性向来不公,钱锺书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从新的角度予以阐释。例如,《大过》篇指出《周易》卦辞中的“老夫少妻”问题,“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6]43,到了“老妇得其士夫”却变成了“老妇士夫,亦可丑也”[6]43。钱锺书先生认为,“于老夫则奖之,于老妇则责之”[6]43。在婚姻中对男性和女性采取不同的评判标准,显然是违背平等之道的。另外,传统婚姻观念对女性的要求也更为严苛,如《无妄》篇一针见血地指出,“男高攀不得,尚可不娶,女高攀不得,辄须下嫁;盖世情患女之无家急于患男之无室也”[6]866。男子未婚,世俗尚能宽容,而对于女子则要求她们尽早成婚。结合《围城》中大龄未婚女性将“丈夫”视为职业,以及如今社会“剩女”一词的出现频率远高于“剩男”,足见这一观念的影响力。古代的女性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世俗强烈反对女性再嫁。在《全后汉文·卷八九》篇中,钱锺书梳理了笔记小说中“夫与妻盟不再娶,妻死而夫背信”[6]1639的情况,世俗反对女性再嫁,而视男性再娶为理所当然。钱锺书引白居易《妇人苦》进一步说明,妇人丧夫,如竹之折,男子丧妇,则如柳之折,因而夫死不可再嫁,妻亡理应再娶。“流俗视为当然”的背后,正是双重的两性道德标准。
在文学创作上,男性对女性歧视最为显著,集中体现在对“才德观”的评判上。钱锺书注意到前人研究中忽视的内容,如“吾国经籍中昌言愚为女德者,无过《大戴礼》,却鲜见征引”[6]1312。足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古来有之,在此影响下,历代不乏对女子识文断字的批评,李商隐《杂纂·不如不解》:“妇人解诗则犯物忌。”[6]1310-131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妇学》所论:“妇人文字非其职业”“妇女而骛声名则非阴类[6]1310-1312”。文人在编选诗集时也常将女性的作品列在诗僧之后,如“周亮工言女诗人羞伍诗僧,却不省诗僧且以伍女诗人为耻,方外闺中,相轻交贱”“选闺阃之诗,多列释子之后、娼妓之前,殊为失体”[6]1314。在男性作家的贬低下,“笔墨非女之事”的观念也成为女性创作的枷锁,如“孟昌期妻孙氏善诗,每代夫作,一日忽曰:‘才思非妇人事!’遂焚其集”。又如朱淑真《断肠诗集》卷一○《自责》:“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6]1310可见,在封建社会中女性作文赋诗已经被污名化。钱锺书列举古代对女性从事文学创作的压迫,并不为批判封建社会的腐朽,而是揭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他进一步指出,“男女不等,中外旧俗同陋”[6]1314,即便在女权主义最早出现的欧洲,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妇女戒‘诵读’”的观念仍旧普遍流行,如“十七世纪法国文家云:‘宁愿妇人须髯绕颊,不愿其诗书满腹。’”[6]1314-1315又如英国一小说家("Monk" Lewis)云:“女手当持针,不得把笔;妇人舍针外,无得心应手之物。”[6]1314-1315由此可见,文学创作中对女性的歧视历来有之,中西皆然,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知识女性都面临相似的性别歧视与生存困境。
(二)“男尊女卑”的历史根源
列举了“男女歧视不齐”在语言文字、社会风俗和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之后,钱锺书进一步点明了这一现象的历史成因,一是女性缺乏独立地位,二是男性掌握话语权。
造成男尊女卑的一个原因是女性缺乏独立地位。在《大过》篇中,有“学道修行,男期守身,而女须失身”[6]45的论述,这无疑是男女不平等的体现。究其原因,在封建社会,女性并不具备独立人格,只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盖视女人身为男子行欲而设:故女而守贞,反负色债,女而纵淫,便有舍身捐躯诸功德”[6]45。封建宗法要求女性守贞,是延续血脉的需求,而对学道修行的女性,则将失身看作是求取功德的牺牲,女性被视为生育子嗣、满足欲望的工具,她们的个人意志是不存在的。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女性并非独立的个体。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提出,“宗法社会中妇人非‘子’”的观点,即“妇人,不过伏于人罢了;夫人,不过扶人罢了;人就是第三者,是他人,所以妇人是伏于他人的;夫人是扶助他人的,自己没有独立性。虽然‘女子’也称作子,但其用意已和男子之‘子’不同”[7]。在封建社会,女性并无独立人格,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因而婚姻就成了女性的最高标准,女性在家庭中要唯父兄、丈夫是从,在社会上就更加没有地位可言了。
造成男尊女卑的另一原因是男性对话语权的掌握。这一点在《管锥编》中两次提及:“盖男尊女卑之世,口诛笔伐之权为丈夫所专也”[6]353;“男尊女卑之世,丈夫专口诛笔伐之权,故苛责女而恕论男”[6]1639。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低下,少有能接受教育者,无缘参与社会活动,对于涉及两性的礼法律令更是无从置喙。因此,在男权社会中产生了双重的两性道德标准,男性自然是其中受益者。于是就有了对“老夫少妻”“老妇士夫”截然相反的评价,钱锺书引谑语反对:“使撰诗、制礼、定律者为周姥而非周公,当不如是。”[6]43男性对话语权的掌握还体现在“女祸”之说上,朝代更迭之际,常有“美色误国”“美色亡国”之说。钱锺书驳斥了这一说法:“盖古之女宠多仅于帷中屏后,发踪指示,而男宠均得出入内外,深闱广廷,无适不可,是以宫邻金虎,为患更甚。”[6]206男性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一方面轻视女性,认为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另一方面则污名化女性,加以祸国殃民的罪名。相比之下,对男宠与佞臣的批评却少得多,且从未衍生出“男祸”一词。
《管锥编》中的女性问题论述体现了钱锺书打通古今中西的治学思路。历史上的男尊女卑现象已是公认的事实,钱锺书却通过文献梳理指出两性观念的历史变迁,由本无褒贬演变为尊卑有别,其原因是男性对话语权的掌握与女性独立地位的缺失。在这些篇目中,钱锺书关注的是历史上的女性面临的困境。与之相对,《围城》则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描述了近代女性的生活困境。将二者对照观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三、钱锺书本人的女性观
小说创作需要想象与虚构,学术著作则需要理性与思辨,两类作品中的女性观并不足以完全概括钱锺书本人的女性观。比如,有人就《围城》的讽刺笔法及正面女性形象的缺乏断言钱锺书对女性的看法存在偏见。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公允。探究钱锺书的女性观,不仅要分析他的作品,而且要从侧面去了解作为创作者与研究者的钱锺书,以及生活中的钱锺书。
(一)作为创作者与研究者的钱锺书
对于《围城》的创作目的,钱锺书已在序中说明:“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2]1“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指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社会与家庭生活,人物自然是虚构的,但与现实不无关联。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为书中的人物与情节做了注解,“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2]362。可见,《围城》以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反映了真实的社会阶层。杨绛指出,孙柔嘉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夫妇”[2]362。至于钱锺书本人的态度,小说结尾的一句话可作为说明,“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言语、一切啼笑”[2]352,“讽刺和感伤”是全书的基调,也是作者创作态度与情感的真实流露。作为讽刺小说,《围城》揭示了这样一部分现实——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女性有了追求平等独立的能力与诉求,但仍然不自知地屈从传统的婚姻观念,走入“围城”之中。在创作过程中,钱锺书“忧时伤世”的情绪营造了书中感伤的氛围,讽刺的笔法旨在揭示现实,而并非贬低知识女性。钱锺书注意到了知识女性的生存现状,从侧面点出了传统婚姻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同样是知识分子的男性对她们的轻视,这同样是对女性群体关怀的体现。
在《管锥编》中也能看出身为研究者的钱锺书对女性的理解与同情。如在论及《氓》时,他指出“士”“女”钟情之异:“夫情之所钟,古之‘士’则登山临水,恣其汗漫,争利求名,得以排遣;乱思移爱,事尚匪艰。古之‘女’闺房窈窕,不能游目骋怀,薪米丛脞,未足忘情摄志;心乎爱矣,独居深念,思蹇产而勿释,魂屏营若有亡,理丝愈纷,解带反结。”[6]163这是对“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的新解释,不是从男女的性格特质出发,主观地认为女性更多愁善感,而是从古代社会中“士”与“女”的活动范围着眼,客观地指出男性可寄情山水以排遣忧思,女性则被局限于闺阁之中,这是“不可脱也”的现实因素。若非以同情与关怀的眼光审视女性的处境,很难如此细致地体察女性的心理。
钱锺书曾戏作一组《当子夜歌》,三首诗如下:
一
妾心如关,守卫严甚。欢竟入来,如无人境。
二
妾心如室,欢来居中。键户藏钥,欢出无从。
三
妾为刀背,欢作刀口。欢情自薄,妾情常厚。[8]
在古乐府中,《子夜歌》属《吴声歌曲》,钱锺书借用古乐府形式写出女性的特殊心理,“欢情自薄,妾情常厚”两句堪称“点题”。有趣的是,据刘永翔先生的研究,此诗实为翻译德国十五、十六世纪的民歌,是钱锺书请夫人杨绛代为翻译成白话诗的:
谁道我监禁你?/还是你霸占我?/你闯进我的心,/关上门又扭上锁。/丢了锁上的钥匙,/是我,也许是你自己。/从此无法开门,/永远,你关在我心里。[9]
钱锺书借来写入《围城》中,成为他借以塑造苏小姐和曹元朗两人性格的一个小例子。钱锺书在此实际上是用古体重新翻译。比较起来,钱锺书的译文更为古朴。第三首化用袁枚《随园诗话》卷四:“刀背贵厚,刀锋贵薄。”[10]借用了中国古代的“刀喻”,喻男子感情淡薄,女子感情深厚。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竟然也是中西相通。
另外,在《太平广记·一八二》篇中,钱锺书用大量篇幅列举了历代关于“女子作诗”的议论。上自《大戴礼记》,下至《文史通义》,皆以愚为女子之德,认为“文字非女子事”[6]1310-1312,就连出现了女性诗人群体的明清两朝亦是如此。有趣的是,《围城》中说“女人作诗,至多是第二流”[2]39的董斜川也是一位善写旧体诗的文人,借他之口说出这句话,揭露了具有传统观念的文人对女性的轻视。在这一点上,可与《管锥编》所引议论齐观。
由此可见,作为创作者与研究者的钱锺书,在《围城》与《管锥编》中所体现的女性观是基本吻合的,二者均揭示了女性群体的处境。《围城》着眼于知识女性群体,《管锥编》选取历史文献作为佐证,指出男尊女卑这一古来有之的现象,并且对女性的境遇报以理解与同情。进一步说,《围城》中的女性之所以受制于传统婚姻观念,何尝不能在《管锥编》“男女歧视不齐”的论述中找到答案?
(二)生活中的钱锺书
众所周知,钱锺书与杨绛的婚姻十分美满,他对妻子的敬爱、对女儿的疼爱在杨绛的《记钱锺书与〈围城〉》和《我们仨》中多处体现。钱锺书从小生活在十分优渥的家庭环境中,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事不能自理,常自叹“拙手笨脚”。二人共赴牛津求学期间,“拙手笨脚”的钱锺书却在厨艺上大显身手,乔迁新居后的第一个早晨,为杨绛准备了丰盛的早餐。据杨绛回忆,“我们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锺书有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锺书做给我吃”[11]76。夫妻相濡以沫的温情,藏在这寻常的一粥一饭之中。他们一同分担家居琐事,钱锺书对时常下厨的杨绛更是十分怜惜,他曾在诗中写道:“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11]80杨绛怀孕之后,钱锺书细心地早早定下单人病房,让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在院长询问是否要女大夫接生时,钱锺书简短地回应:“要最好的。”女儿刚刚出生,钱锺书在这一天之中四次去医院探望,在终于见到女儿后,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11]86在女儿懂事之后,每逢生日,钱锺书总对她说:“这是母难之日。”对女儿的嘱咐又何尝不是对妻子的爱与尊重的体现?钱锺书对女儿也极为疼爱,他曾认真地对杨绛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2]375这种对孩子“用情专一”的“痴气”使他把爱倾注在女儿身上,成为女儿的玩伴与“哥们”、良师与益友。《我们仨》记录了一家三口生活中的不少趣事,在此不一一列举。
幸福而美满的婚姻与家庭使钱锺书得以将精力投入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中,这样的生活环境也影响了他以创作者和研究者的身份看待女性的心态。与同时期的作家相比,钱锺书对知识女性的关注尤为显著,这与他的妻子杨绛不无关系。可以说,钱锺书对杨绛的爱与尊重,使他能够推己及人,注意到和妻子同样身份的知识女性的生存处境,才能够以生动的笔触在《围城》中揭示当时女性欲寻求出路而不得的困境。《围城》中的女性之所以是残缺的,正是因为钱锺书以男女平等的观点看待她们,将她们视为平等的人。在这一点上,他比同时代作家的女性视野更为宽广。
文学作品、研究著作及作者本人的女性观是钱锺书女性观的一体三面,三者内容与角度各异,体现的立场与态度却是基本一致的。钱锺书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女性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深入她们择偶与婚姻生活的心理,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群刻薄善妒、心机十足的女性形象。钱锺书并非有意丑化女性,这些女性身上的缺陷并非先天具备,而是形成于封建观念的束缚之下,更何况,女性“丑陋”的一面正是小说中男性视角的体现,这同样是对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的讽刺。在《管锥编》中,钱锺书更是直指历史上的“男女歧视不齐”现象,以及男性对话语权的掌握。可见,钱锺书对现实和历史上女性处境的关注、对女性心理的洞察正是基于男女平等的立场,以及对女性理解和同情的态度。钱锺书的作品也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自“五四运动”提倡女性独立以来,女性要改变自身处境究竟面临着怎样的社会环境和传统思想,这并不是女性从自己身上就能够找到出路的。目前西方性别研究存在一种观点,即反对将古代女性的生活史视为遭受压迫无力反抗的历史,认为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出现的才女文化现象已是女性寻求独立的体现,社会对女性的态度也发生了改观[12]。这当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我们虽不否认江南才女文化现象在妇女生活史中的重要性,但区域性的文化现象并不能代表历史的主流,《管锥编》对女性才德观的论述已从明清文人的角度揭示了当时才女的处境。从这一方面而言,《管锥编》对女性的论述并非仅是史料的整理,对于我们从历史与文学角度审视女性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