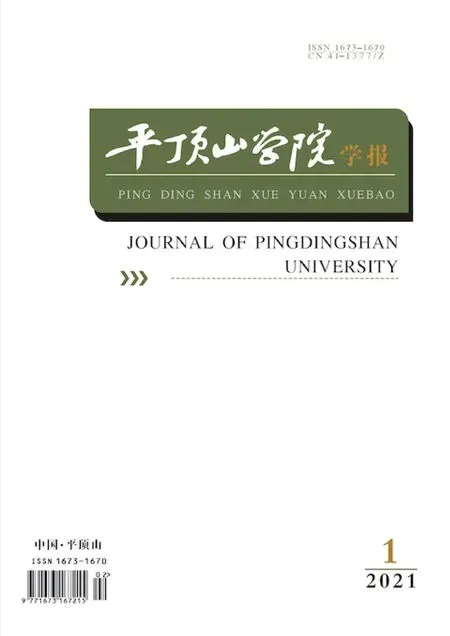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唐代墓志所见妻妾关系
焦 杰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一夫一妻多妾制是中国传统社会为礼法认可并保护的婚姻制度,主要流行在上层社会。它以男性为中心,既可满足父系“广嗣”的需求,又能满足男性喜新厌旧的心理。“唐代姬妾蓄养规模较之唐以前有增无减,多者数百,少者数十,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士人百姓,纳妾养姬成为普遍现象。”[1]基于情感的排外性,妻妾矛盾通常无法避免。为了维护尊卑等级秩序,唐代礼法倾向于保护嫡室的权益,严禁以妾为妻,但对丈夫冷遇妻子、厚待妾室的行为却无法约束,故妻妾矛盾常引发严重的家庭问题。然而,这样的情景在唐代墓志中却很难见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唐代墓志于妻妾关系的描述与传世文献颇不一样?墓志所载是否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本文即以墓志材料为主,辅之以传世文献,对墓志所载妻妾关系进行探讨,借以说明妇女史研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一、唐代墓志关于妻妾关系的描述
截至2016年,整理并出版发表的墓志有15 000方,涉及女性的墓志近10 000方。据统计(1)相关墓志著录图书主要有《唐代墓志汇编》《洛阳新获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新中国出土墓志》《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邙洛碑志三百种》《全唐文补编·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全唐文补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宁夏历代碑刻集》《洛阳新获墓志续编》《新出唐墓志百种》《江苏扬州唐五代墓志简介》《洛阳新见墓志》《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汇编》《越窑瓷墓志》《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辽宁碑志》《景州金石》《高平金石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上海唐宋元墓志》等近三十种。,妻子身份的志主墓志有4 323方,其中53方是继室;姬妾侍妓身份的志主墓志有39方,加上附载及合志有64方。虽然唐代纳姬娶妾风气盛行,而且“唐代妒妇堪称妇女生活史上的典型。中唐以前,是其妒性最盛的时期”[2],但无论是妻子墓志还是姬侍妾墓志,都极少言及妻妾的关系,偶有涉及便是正妻宽容、妾知进退的和谐描述。如《亡妻太原王夫人墓志铭》:
夫人姓王氏,字太真,太原郡人也。三世之上,皆历美宦……幼德敏慧,丽质天成,容止毕修,婉淑有裕……又有女奴,每许侍余之栉,以己之珍玩之物,俾自选以宠与之。其宽容柔顺恤下如此也。[3]1041
这方墓志的志主王氏为正妻,她的母亲是神策右军兵马使刘明之的养女,所以虽然她是太原郡人,但并不属于山东五姓。志文以丈夫口吻写成,赞美王氏聪慧美丽,知书达礼,为人宽厚,不仅不嫉妒女奴为夫侍寝,而且还经常送女奴礼物,让她更好地侍奉丈夫。墓志行文不仅对王氏的宽容不妒和大家闺秀风范表达了感激,也对她的早逝流露出无限的惋惜。
姬侍妾妓知进退、尊重嫡室、宠而不骄的记载,见于《大唐邠王故细人渤海郡高氏墓志之铭》:

志主渤海高氏出生于上层社会家庭,虽非显贵,父祖辈却也做过五品以上大员,所以能成为邠王孺人。她知书达礼,美貌出众,色艺冠绝王府,深受邠王宠爱,然而她懂尊卑、知进退,不但对王妃极为敬重,而且效法汉代的贤妃班姬,劝邠王勤于公事,不要冷落众位妻妾,竭力为邠王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因此当她去世之后,邠王“倍切安仁之思,弥伤奉蒨之神”。
《亡妻太原王夫人墓志铭》和《大唐邠王故细人渤海郡高氏墓志之铭》关于妻妾关系的描述显示了唐代社会对妻妾关系的理想诉求——妻妾有序,嫡室善待姬妾,姬妾敬重嫡室,双方和睦相处,家庭气氛和谐。
唐代描写妻妾关系的墓志虽然极少,但仔细梳理墓志的行文,仍然可以从个别墓志看出妻妾关系的确存在着比较和睦的事实。比如《唐故茂州刺史扶风窦君墓志铭》载道:
维唐大和七年岁次癸丑,冬十月廿二日乙巳,前茂州刺史兼监察御史扶风窦君终于成都府华阳县盐泉里之寄第……享年四十九。娶雅安守河间刘公渭中女,生二男,长曰郡郡,始五岁;次曰朗朗;并一女,犹未舍乳……厥有陇西李氏,五子二女,孟曰浑,仲曰裕,齿皆邻冠室矣,以积善之荫,咸有仕梯;次曰迦叶;次曰药师;次曰阿庆;女曰盻子;次曰顶师。以明年三月十九日庚午归葬于东都城北金谷乡之原,祔于先茔礼也。[4]2146-2147
该志文由高证述撰写,据其在志文中“证夙忝君欢,备详右事,且与刘氏昆弟早为名场游,承其请,敢辞荒陋”[4]2147的自述,则窦季余的丧事由其妻雅安太守刘渭中女刘氏主丧。除了刘氏外,窦季余还有一妾陇西李氏。刘氏生二男一女,最大者不过五岁,李氏生五子二女,年长者已成年并入仕,显然李氏乃是窦季余先纳的侧室,年长于刘氏不少,应该与窦季余年龄差不多。志文虽然没有谈及妻妾关系,但能将李氏写进墓志,又记载了她的生育情况,口气也比较尊重,说明刘氏和李氏相处得还不错。
妻妾关系比较和睦还可以体现在妻妾与夫合葬墓志里。根据礼法的规定,妾是无权与夫合葬的,更不用说与妻子共同与夫合葬,但唐代却有几个妻妾与夫合葬墓志。一是《大唐故海州司马赵郡李公墓志铭》。志主李君会开元九年(721)卒,年82岁;夫人太原王氏开元七年(719)卒,年78岁;夫人渤海南氏开元二十四年(736)卒,年74岁。同年,李君会的儿子将三人合葬[3]557。虽然志文并没有说南氏是妾,但王氏去世时她57岁,这个年纪不可能再被他人娶为继室,因此必是李君会婚后所纳妾室。二是《唐义昌军后院军头□彭城刘府君清河张氏鲁郡齐氏夫人墓志》。刘府君咸通八年(867)卒,年77岁;张氏大中十四年(860)卒,年71岁;齐氏咸通九年(868)卒,年69岁[3]1076。齐氏比刘公小9岁,比张氏小10岁,所以她不可能是继室,应该是侧室。李君会和刘府君的丧事是由其子主持办理,志文没有交代儿子为何人所生,他们能突破礼制,将嫡母庶母与父亲合葬到一起,说明她们生前相处还是比较和睦的。
另一例是《唐故郭府君二夫人墓志铭》,但此志所载主丧者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无法考察妻妾关系是否和谐。其曰:
有唐郭公字柳,讳柳,其先□原人也……以贞元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于还庆坊私舍也,春秋五十有九。夫人周氏。坤顺有□敬事舅姑,忽疾疗不差,兴元年初先殁也。次夫人赵氏,诗礼成德,规风有章……以宝历初年九月七日捐世安阳县郭氏之舍,享年六十九……有二女:长从陈氏,次归赵氏……天水夫人有弟法名灵素,内读佛经,去来□□耳;外披儒典,知礼之克行。乃与陈氏□□□□力为葬仪,以其年十一月廿五日祔府君共夫于望城东北角平原礼也。[4]2089-2090
志主郭柳世代以儒为业,应该是民间的教书先生。他卒于贞元十二年(796),59岁;次夫人赵氏卒于宝历(825—827)初年,69岁。宝历只有三年(825—827),则贞元十二年(796)时赵氏至少29岁。夫人周氏,兴元(784)年初先殁,年纪不详。志文既云赵氏为次夫人,则是侧室无疑,从年纪分析应该是周氏生前所纳。周氏似未生育,赵氏育有二女,丧事由赵氏之弟灵素僧人主持,将两人与夫合葬。在唐代夫妻合葬问题上,“除了主丧者于情于礼的选择外,原配与继室的后嗣情况很大程度左右着丧葬的最终结局”[5]。郭柳夫妻的丧事由赵氏之弟灵素僧人主持,所以尽管妻妾同葬,却无法判断妻妾关系是否和谐。
唐代以夫妻多人葬居绝大多数[6],本文所见妻妾与夫同葬唯此数方。个别只能说明一种存在,绝不代表普遍。另外,无论是妻子墓志还是男子墓志或夫妻合葬墓志,也极少有妻妾并提的,很多墓志往往从其有别出子女的记载才能推断出家有姬妾侍的现实。《唐代墓志汇编》大中138《唐故宣州宣城县府范阳卢府君并夫人博陵崔氏墓志铭》、会昌021《唐故京兆杜氏夫人墓志铭》、会昌015《唐故河南府河清县丞曲府君墓志铭》、咸通001《唐故宣州城县尉范阳卢府君并夫人博陵崔氏墓志铭》、咸通005《唐泗州下邳县尉郑君故夫人清河崔氏墓志铭》、咸通015《唐故怀州录事参军清河崔府君后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铭》等,加上夫妻合附墓志及附载妻子墓志,所见不过32例。这一情况其实很能说明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的妻妾关系并非如墓志中所载。
二、隐藏在墓志行文中的妻妾关系
尽管墓志很少对妻妾关系进行描写,即便描写也都是妻宽容不妒、妾知进退,家中一团和气,但细细品味墓志,还是可以从中感觉到妻妾不和、剑拔弩张,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与冲突。比如《郝氏女(闰)墓志铭》载道:
郝氏女名闰,字九华……九华聪敏柔懿,婉淑明秀。亭亭闲态,艳艳丽容。善吹笙,舞柘枝等十余曲,每至移指遣声,回眸应节,则闻者专听,睹者专视,而倾人城矣。年十有六,侍巾栉于柱史李君之门……诵习诗礼,不出帷房。时人思复见之,杳杳然,如隔云霄而望神仙矣。悲夫!怀孕八月而遘疾弥留,以建中四年八月七日终于河阳县花林里之私第,享年一有九……余之室尝谓人曰:姬人常妇所恶□,若九华复为所好,焉及其殁也。[7]
这位郝闰聪慧美丽,能歌善舞,才艺双绝,十六岁时被山东五姓的赵郡李柱史纳为侍妾。她的美貌和才艺令李柱史非常珍爱,金屋藏娇不欲令人所见。郝闰在十九岁那年“怀孕八月而遘疾弥留”,死后附葬在自己的外祖坟旁。郝闰孕八月而遘疾,死后返葬娘家,使她的死因透露出些许诡异。她的墓志为河阳怀卫节度掌书记大理评事清河崔倬所撰,他在文后借妻子之口很隐晦地表达了郝闰非正常死亡,害死郝闰的人是李柱史的正室。
又如陈子昂所著《馆陶郭公姬薛氏墓志铭》载道:
姬人姓薛氏,本东明国王金氏之允也……父永冲,有唐高宗时,与金仁问归国,帝畴厥庸,拜左武卫大将军。姬人幼有玉色,发于秾华,若彩云朝外,微月宵映也,故家人美之,少号仙子……年十五,大将军薨,遂翦发出家……遂返初服,而归我郭公。郭公豪荡而好奇者也,杂佩以迎之,宝瑟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鸟翡翠之婉娈矣。华繁艳歇,乐极悲来,以长寿二年太岁癸巳二月十七日,遇暴疾而卒于通泉县之官舍。呜呼哀哉!郭公恍然犹若未亡也。[8]
薛氏的死也颇令人生疑,她的暴疾比郝闰的遘疾来得突然凶猛。从志文的描述来看,郭公对薛氏的爱宠不下于李柱史对郝闰的宠爱,生前“其相得如青鸟翡翠之婉娈”,死后“恍然犹若未亡也”。以陈子昂之身份和薛氏的家世背景,馆陶郭公绝非一般的官僚。长寿二年(693)正是武后权力上升的时期,上层社会妇女的悍妒现象非常盛行,薛氏暴疾而死无疑与正室有关,也许正是郭公对薛氏的万千宠爱在一身刺激了正室的妒与恨。
同样令人生疑的是吕媛姐妹的死因。据《唐吕媛墓志铭》记载,乐妓吕媛和姐姐“以乐艺与姊俱进于祁公。明年,姊以疾殁。后一年,媛继终,年十七。父嘉荣其年仲冬月朔日葬于金鹅村祁公茔西北二百步,与其姊同茔别兆”[4]2164-2165。吕媛姐妹在同一年成为祁公的家妓,但两年之内二人相继而亡,显然背后也有故事。吕媛的后事由父亲操办,葬于祁公茔西北二百步左右的地方。根据志文推敲,吕媛死于祁公去世之后,她的姐姐应该死于祁公去世之前。因为后事由其父亲操办,所以她的墓志非常简单,既未叙述其相貌才艺,又未言及与祁公之关系,与郝闰和薛氏的墓志截然不同,隐藏在墓志行文背后的真实只可能是祁公正室对吕媛姐妹的迫害。

一些墓志虽然没有这般深情厚意,但也以平实的语言记载了妾室的生平,表达了对其离世的哀悼。比如《渤海严氏墓志》载道:
余时家于魏,女君少以乐艺方进余门,受性明博,惬适正礼,可重可愧。乃当处吾之室,先也育男二人,长曰名广,次曰名廙。已生女一人,成长而亡,即前年之祸……生无阻情,彼此和颜,补余之道,二十三祀。亡女在侧,幼子哀至,夏日赫照,新坟野次。我有血诚,君当知之,葬我葬所,永远望极![4]2148
严氏卒年41岁,18岁时被丈夫收为妾室,生育二男一女。从文中看,夫妻二人感情很好。《唐代墓志汇编》所收咸通060《孙君侧室杜氏墓志》、咸通076《申州刺史崔君侧室樊氏墓志》、咸通082《东海徐氏墓志》、咸通102《李公别室张氏墓志》和咸通107《清河张氏墓志》,以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061《华原县丞故美人李氏墓志》等都是此类。
既然正常死亡的姬侍妾墓志很多,是否意味着妻妾关系以和平相处的居多呢?当然不是,因为根据墓志的记载,与丈夫关系不错的姬侍妾大多是处于无主妻的情况。有的是男子金屋藏娇,未与正室生活在一起。如《李大使夫人曲氏墓志》载洛阳令某纳曲氏季女云卿,“宠以玉容,贮于金屋。期年果产一男,小字曰路人。及迁南阳郡太守,挈而随之,益加专房之宠”[4]2375-2376。有的是正室去世后所纳,其夫并未再娶。比如《唐杜陵韦氏侧室李氏墓志铭》载道:
秘书监分司东都韦澳之侧室李氏号越客……尔年十五,归于我,归我十二年,年廿六,咸通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于东都嘉庆坊之第。其年十二月廿五日葬于万年县洪固乡李尹村南,东北距我正室河东县君裴夫人之茔五百步已来……凡生二女四男,今其存者五人……吾老而被病,待汝而安。舍我长逝,痛可量哉![3]1064-1065
有的姬侍妾在世时她们的丈夫也未正式娶妻,妾是他们当时唯一主中馈、继后嗣的女人。比如《唐故颍川陈氏墓记》载道:
陈氏讳兰英,大和中,归于我。凡在柳氏十有七年,是非不言于口,喜怒不形于色,谦和处众,恭敬奉上,而又谙熟礼度,聪明干事。余以位卑禄薄,未及婚娶,家事细大,悉皆委之。尔能尽力,靡不躬亲,致使春秋祭祀,无所阙遗,微尔之助,翳不及此。无何,疾生于肺,缠绵不愈,以大中四年十二月三日终于升平里余之私第,年四十。[4]2285
此外,身份与曲氏女云卿一样的有《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96《唐张氏墓记》中的张三英;与韦澳妻李氏一样的有《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60《唐监察御史里行孙君侧室杜氏墓志》中的杜氏、咸通076《申州刺史崔君侧室樊氏墓志》中的樊氏、咸通082《东海徐氏墓志》中的徐氏、咸通102《李公别室张氏墓志》和咸通107《清河张氏墓志》中的张氏等;与陈兰英一样的有《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30《前邢州刺史李肱儿母太仪墓志》中的太仪和《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唐故谯郡曹氏墓志铭》中的曹氏。这些墓志并不能体现出唐代妻妾之间真实的关系,真正能反映唐代妻妾关系的是《郝氏女(闰)墓志铭》《馆陶郭公姬薛氏墓志铭》和《唐吕媛墓志铭》。
三、墓志行文隐恶扬善的原因
从前面两个部分的梳理来看,唐代墓志于妻妾关系要么避而不谈,要么隐恶扬善,竭力想给世人呈现出妻妾和睦、其乐融融的美好情景。作为出土文献,未经删改的墓志理应比传世文献更为真实,那么是否意味着传世文献于妻妾关系的记载有失偏颇呢?当然不是。李鸿宾指出:“墓志资料未经后人删改或整理,保持的相貌却是原初的,就此而言则较传世文献为真。即使是撰者有意识地回护和选择,也能反映出撰者和墓志家族成员的某种心态,具有‘通性之真实’。”[9]正如李鸿宾所指出的那样,唐人在撰写墓志的过程中,不论是故意回避妻妾关系,还是有意识地选择书写的内容,都从本质上反映了唐代男性关于家庭关系的文化心态。
自战国以来夫权得到加强以后,控制妇女的思想越来越得到儒家的重视。“在儒家学者的播弄下,婚礼的意义和‘三从’之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阳唱阴和、男主女从、夫死不嫁、从一而终取代‘成妇’成为婚礼的主题,女性的服丧原则——‘三从’成为女性的道德规范,而‘三从’中的‘从夫’则成为汉代礼学家重点强调的内容。”[10]至此,传统两性关系和夫妻伦理观念基本定型,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四德成为我国古代妇女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两性之间的男阳女阴、男主女从,夫妻之间的夫尊妻卑、夫强妻弱便成为古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两性关系和夫妻伦理”[11]。东汉时期,前有儒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而朝,君臣之道也。恻隐之恩,父子之道也。会计有无,兄弟之道焉。闺阃之内,衽席之上,朋友之道焉”[12]的“妇事夫”四礼。后有班昭《女诫》从义理角度对“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13]的“夫御妻事”原则的阐释。从此,儒家礼教对妻子的约束与管控更加严格,一方面是“出嫁从夫”“妇以夫为天”“夫御妻事”的洗脑教育与规训,一方面是“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妒忌、恶疾”等“七出”的惩罚,双管齐下之下,贤良淑德、宽容不妒便成为好女人的标准。
在唐代,尽管受南北朝遗风的影响,妇女悍妒之风较盛,但儒家思想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贤良淑德仍然是理想的妻子形象。“非礼教之法服,不敢服;非诗书之法言,不敢道;非信义之德行,不敢行。欲人不闻,勿若勿言;欲人不知,勿若勿为;欲人勿传,勿若勿行。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祭祀,盖邦君之孝也。”[14]这就是初唐时期成书的《女孝经》所规划的理想女性形象。所谓“邦君之孝”,就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的“有所兼之义”,也是班昭在《女诫》中提倡的“妻不事夫,义理堕缺”。在“非礼勿服”“非礼勿言”“非礼勿行”和“邦君之孝”的原则下,有条不紊地管理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家庭,为丈夫营造和谐家庭氛围的责任非妻子莫属,这就要求她们对待丈夫的姬侍妾一定要宽容。
《女孝经》为山东五姓的荥阳郑氏所著,其内容反映了以“诗礼”传家的世家大族对女性的要求,所以要求妻子宽容不妒、善待姬侍妾在世家大族中更为普遍。据《太平广记》记载,唐代大历年间(766—779),孤女陈氏自幼父母双亡,由舅舅赵盈抚养长大。赵盈与邛州刺史崔励的亲外甥太原王诸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便想将外甥女嫁给他。因为颍川陈氏与清河崔氏门不当户不对,故而赵盈不敢求明媒正娶,只说“可保岁寒,非求于伉俪,所贵得侍巾栉。如君他日礼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既某之望也”。后来崔励安排王诸礼娶自己的女儿,王诸将已纳陈氏为妾之事说出,崔励安慰他道:“吾小女宽柔,欲与汝重亲,必容汝旧纳者。”两人成亲之后,“崔氏之女便令取陈氏同居,相得,更无分毫失所”[15]。
《仪礼·丧服》曰:“妾之事女君,与妇之事舅姑等。”[16]从礼法而言,正室对家中的姬妾侍有绝对的权威,唐代法律亦对妻子的权利与地位给予保护。然而由于夫尊妻卑的缘故,大多数情况下妻子不得不服从于夫权,因此丈夫的权威与他们对妻妾的态度往往影响妻妾关系。姬侍妾年轻貌美、才情出众,更具性吸引力,往往会获得专房之宠。如果姬侍妾生育了子嗣,尤其是先于嫡妻产子,无疑会影响嫡妻的地位,使妻妾关系失序。《旧唐书·文苑传》中便有妾“凌其正室,专制家政”[17]的记载。因此唐代男子既希望嫡室能宽容姬侍妾,也希望后者能做到不恃宠而骄,对嫡室及其子女非常尊重,懂得尊卑上下之道。墓志行文中对这样的姬侍妾也是大加赞赏的。比如《大唐邠王故细人渤海郡高氏墓志之铭》以邠王口气称赞孺人高氏“以天伦至重,孝友情深,义虽爽于归宁,理或申于同气,企子之望,实获我心”[3]554。《大唐故范氏夫人墓志铭》也以丈夫的口吻称其“自谓桃根卑族,碧玉小家,每惊齐大非偶,能用鸣谦自牧,举事必承先意,服勤尝不告劳”[4]1562。《唐杜陵韦氏侧室李氏墓志铭》一再以韦澳的语气赞美李越客“柔顺明慧,承上接下”“承顺迎奉,尽卑敬之礼”,声称她的去世不仅使自己“痛可量哉”,也令全家感到“悲惜”[3]1064。
由于姬侍妾礼法地位的低下,嫡室宽容、妾知进退应该是妻妾共处家庭中最理想的相处模式,也是最不容易产生纠纷的模式。如果如男子所愿,嫡室皆如太原王氏宽容大度,姬侍妾皆像渤海高氏那样谦顺自持,一夫一妻多侍妾的父权大家庭当真可以和睦许多。可惜的是,人是感情的动物,追求情感、追求更好的生存是人的本能。相比于墓志中的蛛丝马迹,传世文献中悍妻妒妇的记载显然要靠谱得多。墓志与传世文献关于妻妾关系记载的不同,一方面在于墓志“为尊者讳”的特点及“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另一方面在于现实中的妻妾关系是极不容易处理的难题,避而不谈是最方便且容易的书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