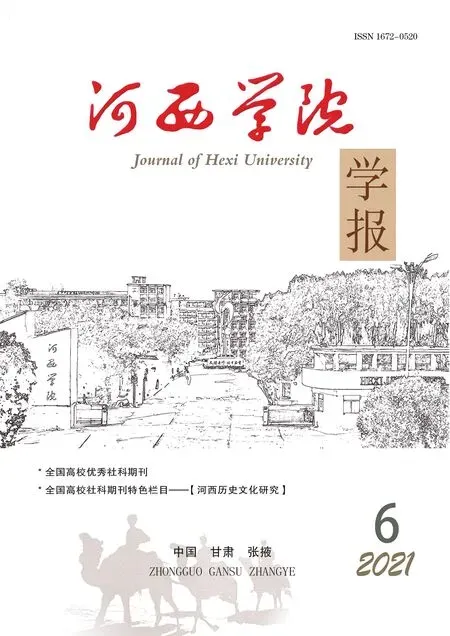上古汉语定语后置的适用语境
程 建 功
(河西学院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关于古代汉语定语后置问题,古汉语学界的探讨相对较少,并且对古代汉语中是否存在定语后置尚有争议,古代汉语教材一般也不涉及此问题。因中学文言教学常涉及定语后置问题,故中学语文教学界对此问题颇为关注,可惜从使用层面研讨的多,而从理论层面探讨的少。本着中学与大学学术一体的原则,我们试图换一种思路,不再探讨定语后置本身,而从定语后置的适用语境角度谈谈这一古代汉语的特殊语序。众所周知,语言选择和句式的运用往往取决于具体的语义和语境。从语言形式上看,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一样,定语置于中心词之前为常态,适用于正常的语言表达。定语后置作为一种非正常或特殊的语法现象,就一定有其存在的特殊语境和适用范围。那么从语用角度来看,古汉语定语后置究竟适用于怎样的语境呢?
据笔者初步考察,对此问题至今尚未见到专文探讨,学者们只是在探讨语序问题或句子结构移位(或易序)的语用功能时有所涉及。范晓先生认为“语序与句式的关系非常密切,语序的差异会影响句式的差异。……特定的语序对应特定的句式:原型语序、衍生语序、超常语序对应原型句式、衍生句式、超常句式。原型语序是本源语序、母体语序,变化原型语序(主要方法是成分的“移位”)就能生成各种衍生句式和超常句式。语义语序是句法语序和语用语序的基础,是生成句式的基底语序”,并强调说“语序影响句式是有理据的,这主要表现在:思维的定势和表达的需要”,同时指出“有些语序及其形成的句式受到语境因素的制约。比如在上下文语境里,为了保持话题或主题的衔接,就得适应语境需要选择某种特定的句式。”[1]李晋荃先生也指出句子结构的易序和变位,其语用功能一是“适应话题化的需要”,二是“适应突出主要信息的需要”,三是“适应句式和押韵的需要”[2]。范、李两位先生就语序的“移位”或“易序”问题从理论高度所作的概括可作为本文写作的基本理论依据。而王锳先生和赵世举先生关于古汉语定语后置的具体论述则是本文写作的语言事实依据。王锳先生通过对大量上古文献资料的考察,认为“定语后置的现象在古汉语中确实不多,但却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其存在形式至少有下面几种类型:一、名词及体词性成分作定语后置,二、形容词及谓词性成分作定语后置,三、‘者’字结构作定语后置,四、数量结构作定语后置。”[3]赵世举先生通过对《孟子》及相关语料的考察,认为“古汉语中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定语后置:一种是作为远古汉语遗留模式的定语后置——遗迹性定语后置,一种是出于表达需要的定语后置——语用性定语后置”,明确指出语用性定语后置“这类变异式与常规式是同义结构,结构形式上也只是语序不同,结构关系、语义关系都相同,主要的区别在于语用价值有异。”[4]我们完全赞同王、赵两位先生的观点。下面我们依据语用学的相关理论将古汉语定语后置的适用语境大体分为以下三类,并以学界常用的上古汉语定语后置例句作为基本语料对定语后置不同于常规句式的语用价值做一点初步探讨。
一、概括与具体表述语境下的定语后置
关于这种语言现象,清代学者称之为“大名冠小名”格式;学界一般称之为“名词及体词性成分的定语后置”;赵世举先生认为这是一种远古汉语遗留模式的定语后置,故将之称为“遗迹性定语后置”。孟蓬生先生曾对此进行过详细的语料整理和具体探讨,认为夏以前这种格式一统天下,商周时期“大名冠小名”与“小名冠大名”两种格式并存,秦汉时期“大名冠小名”格式逐渐消亡[5]。这一结论应当说基本符合古汉语发展演变的实际。这一类的例句上古汉语中较为常见。如:
(1)祖己圮于耿,作祖乙·。(《尚书·咸有一德》)
(2)肇牵车牛·,远服贾。(《尚书·酒诰》)
(3)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周易·泰》)
(4)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诗经·将仲子》)
(5)遂置姜氏于城颖·。(《左传·隐公元年》)
(6)畏其师旷·,告晋侯曰……(《左传·襄公十八年》)
(7)行夏令,则国乃大旱,煖气早来,虫螟·为害。(《吕氏春秋·仲春纪》)
(8)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孟子·离娄上》)
(9)大夫不得造车马·。(《礼记·玉藻》)
(10)若如臣者,犹兽鹿·也。(《韩非子·内储说》)
以上各例,前一名词为某一类事物的概括性名称,后一名词则为某一事物的具体名称。例(1)“祖乙”中的“祖”为先祖的通称,“乙”则指称特定的某一先祖,例(3)与此类似,只不过通称换作了“帝”,只是因为“乙”在商人称呼其为“祖”,而在周人称呼则为“帝”;例(2)的“车牛”即指牛车,例(9)的“车马”即指马车,其中“车”为通称,“牛”“马”则为限制车的类属的具体称谓;例(4)的“树桑”与例(8)的“草芥”用法相同,“树”与“草”为草木的通称,“桑”与“芥”则指称草木具体的类属;例(5)“城”为城池之通称,“颖”则指具体的地名,例(6)与此类似,“师”为乐师的通称,“旷”则为乐师之名;例(7)的“虫螟”为螟虫,例(10)的“兽鹿”即鹿兽,其中“虫”为动物通称,“螟”则为虫之一种,“兽”为野兽之通称,“鹿”则为野兽之一种。
通过以上分析,这一类定语后置是古人在属种概念并举语境下所采取的表述方式,是将属概念放在种概念之前加以表述的,这种属于原型语序的表述,应当与古人的思维习惯以及对事物的认识水平有关。或许古人一开始只有属概念一种认识,后来发现同一属概念之下还有种概念的区别,于是在属概念之下加上种概念以示区别,久而久之成为了一种用语习惯。这是文化语言学研究的问题,我们姑且不论,仅就一般语言理论而言,这种为区别事物属种概念的具体语境下产生的语序,客观上不是并列结构也不是后补结构,而只能是中定结构。既然是中定结构,那么将这种结构理解为定语后置也就顺理成章。尽管有学者认为“树桑”例为诗歌押韵而设,但也当承认正因“大名冠小名”为当时的习用表达,才不致出现因押韵改变词序而产生误读。同时正因这种“大名冠小名”的格式在商周以前为常用格式,商周时期“大名冠小名”与“小名冠大名”的格式才逐渐形成并举的局面,也正好说明了语序或语用习惯的改变与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紧密相关。有学者曾根据后世文献中尚存一定数量的“大名冠小名”格式,认为孟蓬生先生关于秦汉时期“大名冠小名”格式逐渐消亡的结论有误。我们认为这种情形应当是后世仿古造成的特殊现象,毕竟秦汉以后,在表述概括事物与具体事物关系时“小名冠大名”已成为通用格式。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后世之所以依然模仿上古“大名冠小名”格式,也恰恰说明这本就是上古汉语在概括与具体表述语境下的一种原型语序。
二、物量表述语境下的定语后置
一般情况下,上古汉语数量词连用时,名量式和动量式常常不用量词,直接用数词表示不仅如此,上古汉语名量式与动量式的用法基本与现代汉语相反。就是说,在上古汉语中,名词与数量词结合时,数量词往往放在名词后面。看起来这的确是上古汉语的习惯语序,当然实际情形要略为复杂一些。王力先生《汉语语法史》曾对这种语言现象做过细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上古汉语里,人、物数量的表示,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数词直接放在名词前,这是最常见的方式;二是数词直接放在名词后,这种方式较为少见;三是将数量词放在名词后,这种方式也比较少见;并强调如果是数词与度量衡单位词组合,就必须用第三种方式。[6]可见,上古汉语人和物的数量表示方式以第一种为常,即名词与数词的组合以数词放在名词前作定语为常式,这与现代汉语语序基本相同(因现代汉语数词后一般还要带量词),这显然是其原型语序;而以第二、第三种为变,即以数词或数量词放在名词后作定语为变式,这可视为衍生语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种语序下,王力先生所举的例证均为表人名词、表事名词、时间名词与数词的组合,没有一例是与表物名词组合的;二、三两种语序下的例证则多为数词或数量词与表物名词的组合,偶尔也与表人、表事名词相关。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的结论:上古汉语名量式语境下的数词或数量词与名词的组合一般与现代汉语语序相同;而物量式语境下的名词与数词或数量词(尤其是度量衡单位词)相组合时,数词特别是数量词常常放在名词后作后置定语。可见这是古人为区别不同事物的差别而在表述上所做的一种惯常处理。如:
(1)获虎一,豕十有六。(《殷墟文字乙编》)
(2)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城邑,牛一,羊一,豕一。(《尚书·召诰》)
(3)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诗经·伐檀》)
(4)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周易·睽》)
(5)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
(6)冉子与之粟五秉。(《论语·雍也》)
(7)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孟子·公孙丑下》)
(8)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战国策·齐策》)
(9)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庄子·秋水》)
(10)负服矢五十个。(《荀子·议兵》)
以上各例均为数词或数量词放在名词后作定语,特别是数词后带上度量衡单位时放在名词后作定语为其常态。可见这是先秦物量表示的一种惯常语序。这种情形在秦以后的典籍中也还常见,如“吏皆奉送钱三。”(《史记·萧相国世家》)“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汉书·王莽传下》)其实,不仅表物量的数量词或数词可放在名词后,即使表人名词的后面也可带上后置定语,如果例(6)“载鬼一车”里的“鬼”究竟指人指物尚难确认,那么“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周易·讼》)“吏二缚一人诣王。”(《晏子春秋·杂篇》)中的“邑人”“吏”指人则确然无疑。由此不难看出,先秦典籍在表示物量关系甚至名量关系的语境下,数词或数量词尤其是度量衡单位词常常放在名词后作定语。换句话说,秦以前的古人在表示名量关系和物量关系时,原本应当是有区别的:即表示名量关系时,数词直接放在名词前;表示物量关系时,则数词或数量词放在名词后,尤其是数词与度量衡单位结合时一定要放在名词后。只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示名量关系的数量词也可放在名词后了,但也仅限于数量词置于名词后,若是用单个数词表示名量关系时是不会置于名词后的(笔者曾考查过《周易》全文,无一例外)。从思维习惯来看,这应当是古人对人和物在数量关系上进行的有意区分,或许与古人的禁忌有关。从实际语用层面来看,数词直接置于名词后作定语表名量关系的用例很少,也恰恰说明了古人在具体使用数词时,究竟是指人还是指物其表述方式是明显有区别的。至于数量词组置于名词后作定语应当说是古人的一种习惯性表述,由于早期的古人使用量词较少,既然单个数词表示物量关系时可放在名词后,那么当数量词组合在一起表示物量关系时自然也要放在名词后作定语。对此,王力先生也曾明确指出:“就名词、数词、单位词三者的结合方式来说,有一种发展情况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那就是在先秦时代,数词在兼带单位词或度量衡单位词时,位置是在名词的后面。”[7]而大量的实际用例不仅证明王力先生的观点完全正确,也说明了这确实是古人的一种语用习惯。
三、特殊语境下的定语后置
我们这里所谓的特殊语境,是与习惯语境相对的概念。从语序来看,习惯语境的句式一般表现为常规的定中结构。而当定中结构不能准确表达语义时,就说明所处的语境已非习惯语境,而处于非常规的特殊语境。由于正常语序不能表达特殊语境的内容,所以只能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运用超常语序来解决问题。李晋荃先生关于句子结构的易序和变位,其语用功能一是“适应话题化的需要”,二是“适应突出主要信息的需要”,三是“适应句式和押韵的需要”。[2]将这一概括放在特殊语境下的定语后置上来考察同样适用。如:
(1)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荀子劝学》)
(2)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楚辞涉江》)
(3)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桃夭》)
(4)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者汶汶乎?(《楚辞渔父》)
(5)有一言而可乎以终?身行(之者《论语卫灵公》)
(6)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孟子梁惠王下》)
(7)齐人有,冯贫谖乏者不能自存。(《战国策齐策》)
(8)杞国人有。忧天地(崩坠身无《所寄废寝列食者子天瑞》)
(9)人之涂,其左体三被濡千衣人而,赴火右者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韩非子内储说上》)
(10)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
以上各例,从其外部形式上来看,中学语文教学界一般分为四类[8],许仰民先生分为六类[9]。分类标准不同所分类别自然不同,此乃通理。但由于分类不同,学界对此也有颇多争论,对前述原型语序和衍生语序所形成的定语后置学界一般是认可的,而对超常语序所形成的定语后置现象有些学者并不认可,甚至因此认为古汉语中不存在定语后置现象。这当然未免偏激,但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拿具有局限性的固定形式去套用和分析变动不居的超常句式是行不通的。以上例句,从其内容结构上来看,大致可分为形容词性定语后置和名词性定语后置两类,王锳先生将之分为“形容词及谓词性成分作定语后置”和“‘者’字结构作定语后置”两类。由于王先生将“者”字结构视为名词,所以同我们的分类实质上并无区别,只是表述略有不同而已。从语言理论上讲,可作定语的词类无非名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等几类,前述习惯语境下的定语后置涉及到名词和数量词,而特殊语境下的定语后置涉及形容词以及名词或名词性结构符合语言规律,因古汉语中代词作宾语常常后置,而代词作定语则不后置,故不涉及代词定语后置问题。可见,分析以上例句是否为定语后置还得从其语义、语境入手,方能得到准确的结论。
例(1)为形容词作定语后置,从上下文语境看,“利”“强”两个后置定语分别起强调作用,目的在于突出“蚓”缺乏必要的可用于劳作的器官以及自身弱小的程度,其中“之”为结构助词起联结作用(下三例“之”用法与此同)。例(2)“陆离”“崔嵬”两个形容词作后置定语,不仅起强调作用,以突出宝剑之长之美和帽子之高之美;从诗歌语用角度分析,还有上下呼应、音韵和谐之作用。例(3)形容词“夭夭”作后置定语同样具有强调和使音韵和谐的作用。例(4)形容词“察察”“汶汶”作后置定语,基本作用与例(3)相同,此外二者还有对举作用。以上四例均为形容词作后置定语,从语用层面讲,都不属形容词置于名词前作定语的原型语序(或常规语序),均属超常语序,而这种超常语序只适用于突出强调或呼应、对举、音韵和谐等特殊语境。例(5)“可以终身行之者”为名词性“者”字结构作后置定语,起特意说明作用,“而”为连词起联结作用。例(6)结构与例(5)相同,后置定语作用也同于例(5)。例(7)“有冯谖者”名词结构直接置于中心语后作定语具有特意说明作用,这种句式上古汉语中较为常见。若与“冯谖者,齐人也”的判断句相比,明显可以看出前者为特殊叙述,后者为一般叙述;前者似有“在某地有这么一号人”之义,在上下文语境中往往略带戏谑意味,后者则为比较正式的人物介绍,在上下文语境中一般具有郑重意味。例(8)结构同于例(7),“有忧天地崩坠身无所寄废寝食者”这个后置定语的特意说明作用更加明显,从语境分析戏谑意味也更浓。例(9)(10)结构相同,均为“者”字结构作后置定语,并用结构助词“之”与中心词相联结。从上下文语境来看,例(9)“涂其体被濡衣而赴火者”特指为了领赏而作出非常举动的人,例(10)“清者”“任者”“和者”“时者”则指某一方面的才能非常突出的圣人,均有褒扬意味。当然,也有学者将例(9)(10)的“者字结构”内容视为复指,不无道理。我们认为作为超常语序的定语后置起突出强调作用或许更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古汉语定语后置现象,均有其适用的语境,其中既有表述概括事物与具体事物的鲜明区别之语境的,又有用于名量与物量区分之语境的,还有或用于强调、或用于特意说明、或因音韵和谐等特殊语境的。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以上所述的那种情形,它都与正常的定中结构语序不同,表达的内容也往往是与定中结构不易表达或与之有所区别的内容,这其实正是古汉语存在定语后置现象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