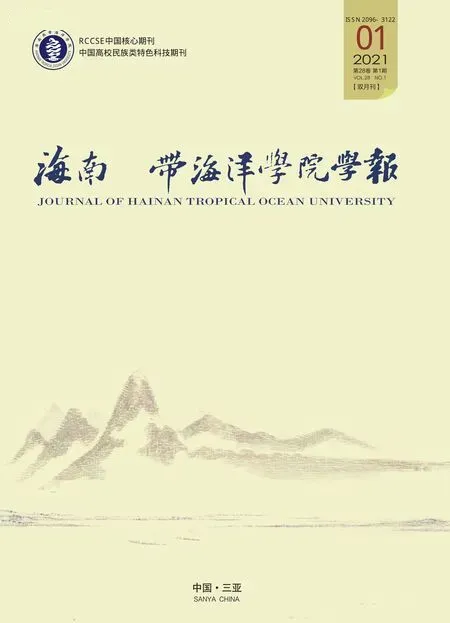古典诗词英译中的情感效度
谢艳明,范 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073)
情感是诗歌的灵魂。诗歌之所以能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魅力,就是因为其中饱含浓重的感情色彩。尽管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是“诗言志”,但它并没有将中国的诗词引向纯粹的理性说教,而是侧重于情感的书写。《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63中国的诗词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情”是其中重要的元素。魏晋文论家陆机在《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1]171的观点。钟嵘的《诗品》开篇就强调“情”:“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2]15在中国诗词中,“志”是情感的仪式化和仪式表达,“诗言志”论也是关于情感问题的理论[3]。“诗歌由于用语言来建立情感的秩序和情境,就有了某种固定情感的力量——能再现诗人依附在感性事物和清晰观念上的情感。感情不仅作为一种动力,存在于诗的孕育和创造过程,它还是诗的直接表现对象。”[4]中国古代是没有写诗这个职业的,诗人们写诗也并不是为了谋生。他们为什么要写诗呢?很多时候诗人们有感于情,有结于心,以至于不得不抒发出来。清代学者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之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5]10况周颐的“万不得已者”就是华兹华斯所说的“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6]。既然情感是诗词的生命,在翻译时就必须突出情感的表达,要使得译文像原文一样在读者的心灵中产生情感的共鸣。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的检索,有关诗歌情感研究的论文超过52篇,有关诗歌翻译的论文多达637篇,然而研究诗歌情感翻译的论文为零。不仅这方面的研究存在严重不足的现象,而且许多诗词译者过于注重语言形式,忽视了情感传达。诗歌翻译讲究“传神达意”,“传神”的核心就是“传情”,情感传达到位了,“神”就出来了。也就是说,译文要达到原文的“情感效度”。
一、 情感效度及其判定
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7](functional equivalence)强调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要求译者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语言形式。“功能对等”理论在我国翻译界引起了很大反响,金隄认为它对“直译和自由译之争,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8]15。根据这一理论,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的死译,而是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对原作的一种解释和再创造。因此,金隄指出:“翻译中需要的对等是一种综合性的关系,不是机械地综合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等方面的对等,而是依靠艺术的眼光和文化语言素养,全面细致地考虑各方面因素。效果上的对等就是这样一种综合性的对等关系。”[8]22“效果上的对等关系”就是“等效”,其主要原则是原文和译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信息,但要产生基本相同的效果[8]27。中国古典诗词很讲究运用简洁的词语表达深重的情感,力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将“人生意趣”与“物外意象”深刻交融起来。诗歌的译文要让读者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在原文中就存在,而且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对这一情感冲击的反应应该是基本一致的、等效的。诗歌翻译也是一种移情的过程,将情感从一种语言移进另一种语言,而且要求是等效的,即“情感等效”(affective equivalence),也就是译文实现了与原文基本对等的效度(validity)。
所谓“效度”就是有效性,它本是一个测试学的概念,其意为“使用测量工具或手段准确测量出某一事物的程度”,即“所测量到的结果反映所想要考察内容的程度”[9]。本文提出的情感效度是指诗歌译文的情感反映原文情感的程度,也就是原文的情感传达到译文中的程度,译文的情感越接近原文的情感,其情感效度就越高。当然,没有一种科学仪器能够精确地测量译文的情感效度。情感是纯感性的东西,虽然译者可以通过问卷的形式调查读者对原文和译文的感觉是否相同,是否最大限度地达到情感等效,但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边做问卷调查边翻译实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译者往往通过假想的读者去感知译文的情感。要判定译文的情感效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译文的情感表达是否做到了“真”。这里的“真”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情感之“真”,译文要让读者感觉是“真情流露”,而非虚情假意的无病呻吟;其二是叙述的自然流畅,而不是故作矜持、曲笔跌宕,即情感的表达要显得自然,不露人工雕琢的痕迹,否则就会让译文中的情感显得不真实,因而也达不到译者所需的效度。《蕙风词话》论词的创作中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意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5]6“真”也诗歌译文之“骨”,无“骨”而不立。《惠风词话》也说:“诗笔固不宜直率,犹切忌刻意为曲折。”[5]5译诗也是这样,诗句固然不能像日常语言那样直率,但不可因为诗歌的形式因素(如押韵和节奏)刻意将句子颠来倒去,使得情感表达不自然顺畅。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很多翻译家们十分认“真”地注重情感的锤炼。比如,汉代苏武写过一首《别妻》诗(一说是假托苏武写的),描写了一位刚烈节义的男子,在出使临行前,告别自己深爱的妻子。这首诗最后六句为:“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将夫妻离别的无限悲怆、难以自持的情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催人泪下,震撼人心,表现了男子对爱情忠贞不渝的赤诚和生死相依的决心。对这六句诗,Henry H.Hart的译文是:
How tight you held my hand!
I can see yet
The tear that fell upon it,
And those words you whispered last
I treasure still:
“Do not forget the hours of life and love
That we have shared.
If I live,
I shall surely come back to you.
If I die,
Remember
That all my thoughts have always been of you.”[10]88
Arthur Waley的译文是:
I hold your hand with only a deep sigh;
Afterwards,tears-in the days when we are parted.
With all your might enjoy the spring flowers,
But do not forget the time of our love and pride.
Know that if I live,I will come back again,
And if I die,we will go on thinking of each other.[10]88
两位译者对原诗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Hart将妻子作为叙述的主体(第一人称是“妻子”),用直接引语的方式引述了丈夫临行前的爱情誓言;Waley的第一人称是“丈夫”,也有临行前的嘱咐和誓言。在Hart的译文中,妻子感受到了“你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看见了你的眼泪流下来”。通过观察者的内心感受和观察,描写了“丈夫”难舍难分的情感。“丈夫”的述说生动地再现了他临行前向“妻子”表示出的生死相依的情感。Waley的译文直接描述了“我握着你的手,深深地悲叹,然后泪流满面”,通过叙述者的内心悲恸表现临别前的凄惨景象,接下来的四行像戏剧独白一样,是“丈夫”向“妻子”的爱情宣誓。两个译文都十分注重情感的渲染,读起来情真意切,自然流畅,毫不矫揉造作。
第二,译文的情感表达是否恰到好处。《蕙风词话》说创作词要“恰到好处,恰够消息,毋不及,毋太过”[5]6。这句话也适合翻译诗歌,译者在用词和情感渲染方面要把握好一个度,不能表达不到位,也不能表达太过,能做到“恰到好处”便是取得了最佳的效度。例如,有人将李清照的《一剪梅》的第一节英译如下: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From lotus to bed,aroma does blow.
My silk robe’s lightly doffed.
The lone canoe I row.
Who would send me a letter from the clouds?
When the wild geese come back,
The rail’s moonlit to glow.[11]
李清照写这首词时,她和赵明诚结婚不久,赵明诚便负笈远游,她不忍离别,便写下这首词以倾诉相思、别愁之苦。第一句是说秋天到了,天气转凉,荷花的香气变得残败微弱了。而译文却说“荷花的香气吹进到了床上”,译者使用了blow一词,力度很大,可见荷花的香气不但没有残败,反而依旧浓烈。此词用在这里就不是“恰到好处”,而是“太过”。“玉簟”是精美的竹席,枕席生凉,既是肌肤间触觉,也是凄凉独处的内心感受。译文没有渲染这一情感,因而有传情“不及”之嫌。“月满西楼”不仅仅是一幅“月亮照在房屋西面”的静态画面,而是在叙述词人思念丈夫,辗转反侧,直到月亮偏西的后半夜仍然无法入眠。译文却将“西楼”隐去,因而无法传达词人的相思之愁苦。
当抒情述怀恰到好处,译文一定是耐人寻味的。许渊冲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十分注重情感的锤炼,他的许多译文“用情”之深,动人心弦,感染了许许多多的读者。比如,他的杜甫《春望》的译文不仅做到了“音美、形美、意美”,而且在遣词造句上凸显了情感的美,且看前四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On war-torn land streams flow and mountains stand;
In towns unquiet grass and weeds run riot.
Grieved o’er the years,flowers are moved to tears;
Seeing us part,birds cry with broken heart.[12]
许渊冲将这首诗每行译成十个音节,构成五步抑扬格,并精心设计了行内韵,译文的音韵极美。在传达原诗的“意美”时,译者运用了情感冲击力很强的词语,十分扣人心弦。他将“国破”译成“被战争撕裂的国家”,将“草木深”译成“杂草长得狂乱”,具体化的处理,画面感增强了,情感也加深了。接下来的伤感在译文中处理成“多年的痛苦,花都感动得流泪”,虽然没有原文“溅”的力度,但在前两句慷慨激昂之后,稍稍抒情一下,更好地引导读者的情感波动。最后一句译成“鸟都苦得心碎了”,将情感的书写推向高潮。在翻译诗词时,译者除了在遣词时要考虑诗歌形式上的适应性,如押韵、音节数量、构成诗歌节奏的重音位置外,还要在词义方面仔细比对两种语言相关表达方式的词汇含义和联想含义,找到最为贴近的表达方式,以取得对等的情感效果。“情感对等”要求译者做到和原作者心灵相通,要全面而又细微地感受和领悟原作的情感,“调动译入语中最适宜的手段,用恰如其分的译文,使读者也获得同样全面而细致的理解和感受”[8]8。
第三,译文的情感表达是否合乎原文的文化规约。诗歌的情感即为“审美情感”,而“审美情感”又来源于“有意味的形式”[13]27,体现着特定文化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情感是主观感性的,看起来是个人的心理表征,实际上“积淀了人的理性”,也“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13]10。可以说,情感虽然是诗人的“生命冲动”,它具有文化的符号性质,受文化的规约,体现着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例如,《关雎》的第一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诗以关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君子对淑女的思恋。
汪榕培英译为:
The waterfowl would coo
Upon an islet in the brook.
A lad would like to woo
A lass with nice and pretty look.[14]
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译文为:
Hark! From the islet in the stream the voice
Of fish hawks that o’er their nest rejoice!
From them our thoughts to that young lady go,
Modest and virtuous,loth herself to show.
Where could be found,to share our prince’s state
So fair,so virtuous,and so fit a mate?[10]3
从抒情层面上看,理雅各的译文比汪译情感充盈得多,呼语“Hark!”一下子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情感距离,读起来更加生动亲切。从意义层面上看,汪译要简洁明了,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而理雅各的译文则阐释过多,略显啰唆。从文化层面上看,汪译不如理雅各译文接近原作的情感效度。这首诗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汪译将它们分别译为“lad”和“lass”,在文化上显得贵气不足,有些轻佻。第一节没有叙述“君子”如何追求他心仪的“淑女”,而是说“君子好逑”,即这个美丽善良的“淑女”是“君子”好的伴侣。这里为什么不能理解为“君子喜好追求该女子”呢?《毛诗序》在解释这首诗时,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1]63。这实际上给出中国传统男女关系的一个文化规约:普通民众都是有情感生发的,但有德行修养的人会控制情欲,不让它僭越礼义。因此,“君子”对“淑女”产生爱慕之情,但不会一开始就展开追求(woo),他纵然思念若渴,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也要在礼义规约的范围内,用“礼乐”去取悦心仪之人。理雅各将“君子好逑”译成“该女子美丽、有美德,是君子的适合的伴侣(So fair,so virtuous,and so fit a mate)”更合乎中国文化的情感效度。
二、 情感效度的翻译策略
既然情感效度关乎诗歌翻译的是否“传神”,关乎翻译的成败,那么怎样在翻译实践中达到或捕捉到理想的“情感效度”呢?
第一,尽力缩小叙事距离,将叙述者和主要人物尽量融合起来,让叙述者“亲临”故事场中,这样的译文会给人一种真切感,能取得良好的情感效度。叙述距离是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来的重要概念,指故事叙述主体(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中国古典诗词的故事叙述主体和人物通常比较模糊,叙述视角呈多样性。例如,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像绝大多数中国古典诗词一样,此诗没有明确的叙述视角,尽管读者一般都解读为第一人称视角,“今夜里鄜州上空那轮圆月高照,我不在你身边,你只能在闺房中独自欣赏了;我远在他乡怜惜起幼小的儿女,还不懂得为何思念长安”,但是此诗也可以解读为第三人称。不过,当叙述者和诗中人物融合一体时,读者会感到情真意切些;若叙述者和人物分离,距离产生了,感染力就随之减弱。王宏印在翻译此诗时,采取了缩减叙述距离的策略:
This night,at Fuzhou,my wife,my dear,
Do you alone come out and look at the moon?
And does our daughter,so young,so little,
Remember and mention her father in Chang’an?
Take care.Your hair should be wet with the fog,
And your arm,so cold—so deep in the night.
When shall we meet and sit together by the bed,
And our tears be dried by the same moonlight?[15]
王宏印的译文读起来就像在聆听叙述者兼人物“我”对妻子说着情意绵绵的悄悄话,三个问句表达了对妻子及儿女的深切牵挂。译者十分注重情景和情感的锤炼,一开头就充满情感,“my wife,my dear”,亲切的呼语让人感到一股暖流。在问到小儿女时,译者似乎重复了“so young,so little”,但充满了情感和关切。原诗虽未着一个“我”字,但抒发的全是“我”的愁苦和思念。译文将第一人称突出出来了,情感距离拉近了,更显得真情实感。
第二,由静态表达转译为动态叙述,让“情感”动起来。中国古典诗词倾向于使用静态的意象来展示一幅意境深远的图画,常常呈现一种状态(state)。比如柳宗元的《江雪》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将读者带到一个幽静寒冷的境地,是一个静态的、“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16]的景象。这样的诗句在中国诗词中比比皆是。很多的诗句是静态的情感描述,表现一个人内心的情感状态。英语诗歌比较倾向于使用动词来表达一种动态的事件(event),通过事件来体现人的情感。因此,在翻译古典诗词时,译者可以使用动态的描述来再现静态的情感。
例如,五代时期词人牛希济(生卒年不详,913年前后在世)写有《生查子·春山烟欲收》,用清峻委婉的语言,生动形象而又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对情人分别时难舍难分的场面。这对有情人在离别前倾诉了一夜的恋情,直到天明仍然依依不舍,总有诉不完的情:
语已多,情未了,
回首犹重道:
记得绿罗裙,
处处怜芳草。
They’ve talked too much,but with more love to pour,
Turning her head back,she urged him once more:
Keep in mind the green satin skirt I wear,
And feel tender to green grass everywhere.[17]158
纵然诉说了一整夜,但心中的恋情仍然滔滔不绝。“情未了”是对恋情的情态描写,译文使用一个动感很强的“pour”,叙述了恋人之间诉说了一整夜的情感,依然很浓烈,犹如“倾盆大雨”在心中泛滥。
宋代女诗人朱淑真在《秋夜闻雨·其二》中写道:“独宿广寒多少恨,一时分付我心头。”她在一个下着雨的秋夜想起了独自守着广寒宫的嫦娥,嫦娥的处境和心境实际上是诗人自己当时的情感状态,诗人同样感受到了广阔无边的孤寂和幽恨。这两句诗可以翻译成:
How many rues She’s paid for staying in the Cold Palace?
She has hurled all those rues upon my mind,so strong.[18]84
“分付”到“心头”是一个相对静态的描写,动作感不是很强烈。译文运用了“hurl”(投掷)一词,动感极强,让读者感受到原文中的“孤独”和“幽恨”很有力度地冲击着内心的情感。
第三,动态的情感转译为静态的表达。虽然中国诗词倾向于静态的抒情,但这并不是说动态的事件完全被拒之门外。实际上,很多诗句像“僧敲月下门”运用“敲”字一样将动态的事件描写得出神入化。在多数情况下,动态的事件仍然译为动态的。但在一些诗句中,动态转译成静态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情感效果。例如,南唐中主李璟(916-961)写的《摊破浣溪沙》第一节: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Gone is the lotus’ fragrance,and withered its leaves;
Among green waves,the west wind brings sad heaves.
Our life is on the wane,as time goes by.
A cruel sight to our eye.[17]161
荷香消散,荷叶凋零,深秋的西风拂动绿水,使人愁绪满怀,美好的年华也在凋谢,。与韶光一同憔悴的人,自然不忍去看到这一景象。“不堪看”译成“a cruel sight to our eye”(残酷的景象),将动态的动作“看”转译为静态的“看”的对象,并且运用“cruel”一词进行情感渲染。
再看看朱淑真的(《恨春五首 其二》):
泪眼谢他花缴抱,愁怀惟赖酒扶持。
莺莺燕燕休相笑,试与单栖各自知。
Thank Heaven in tears for flowers’ cheerful embrace,
And when in sorrow,wine becomes my sole soul mate.
Orioles and swallows do not laugh at my poor case;
You will know how you suffer if you’re separate.[18]15
尽管时令是花繁锦簇的春天,但因心上人的离开,诗人感到无限的惆怅,她内心的愁怀只有酒才能消解。“扶持”一词具有动感,显示她已悲凄得支撑不起自己的身体。若译成“My sorrow is only counteracted by wine”或“supported by wine”,不仅诗意没传达出来,情感效果更没到位。译成“when in sorrow,wine becomes my sole soul mate”,把“酒”比作“心灵伴侣”,从身体的依赖到内心的寄托,由外而内,诗人忧戚的情感跃然纸上。在孤独无助、人生不如意、忧伤悲凄的时候,中国古代诗人往往借酒浇愁,酒成了他们的心灵伴侣和情感慰藉。所以,在这首诗里,朱淑真的“酒扶持”不就是“心灵伴侣”吗?由此可见,静态的表达虽然不如动态那样给人以栩栩如生的感觉,但其定性式的描述同样能达到情感效度。
第四,将原文中情感话语具象化。具象化(concrete)翻译就是将原文中总结性、评价性、抽象化的话语由面到点地转译成具体的意象或事件,使宏大的、概括性的叙述变成细节性的话语,通过细节来再现原文的情感功能。具象化的翻译可以使译文的情感表达更为细腻、丰满、有力度。例如,《诗经·邶风·击鼓》的第一节:“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战鼓擂得隆隆响,校场上士兵踊跃练兵。有的在修路筑城墙,我独自从军往南行。“战鼓雷动”和“士兵操练”在这里都是笼统的状态描写,是“总结性、评价性、抽象化的话语”。笔者将这一节翻译如下:
Beat! Beat! Beat! Bong the drums out.
Charge! Charge! Charge! We’re busy about.
They are building walls far and near,
But I go to the south frontier.[17]9
回译过来就是“敲啊敲啊敲啊,战鼓隆隆响;冲啊冲啊冲啊,我们忙操练。他们到处修城筑墙,我独自去南方的边疆。”三次重复“Beat!”和“Charge!”将士兵紧张训练的情景具体展现出来了,表现有力度,读起来很有节奏,似有雷霆万钧之势,让读者感受到士兵们斗志昂扬的样子。再如朱淑真的《牡丹》一诗:“娇娆万态逞殊芳,花品名中占得王。莫把倾城比颜色,从来家国为伊亡。”
Unique scents it shows with many a fetching pose,
And wins among others flowers a fair from fairs.
Don’t compare it to beauties who can e’en ruin cities;
For them,many kingdoms have met their nightmares.[18]171
此诗歌颂牡丹花的美丽、独特、妖娆,具有高贵的品质,是“花中之王”。将“占得王”译成“a fair from fairs”,巧妙地借用了莎士比亚的Sonnet 18中的具体意象。在许多诗词中,诗人们一般将美女比作花,而在此诗中,朱淑真将牡丹与倾城倾国的美女相比拟,并说不要将牡丹比作这些美女,因为美女会引起国家灭亡。将“为伊亡”译为“met their nightmares”虽然改变了原作的内容,但其意象更为具象化,起到了对等的情感效果。
第五,走进诗人的情感世界,围绕原文创设语境,以达到情感效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和原作者达到了一种心灵上的契合,这种契合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打破了种族上和文化上的樊笼,在译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种创造上的满足;在读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种新奇的美感经验”[8]34。朱淑真的《清平乐·夏日游湖》一词记述了她与情人在湖上约会的情景。上片写他们俩相约游湖,先是“携手藕花湖上路”,不料遇上“一霎黄梅细雨”。游湖赏花而遇雨,却给他们造成了一个幽清的环境和难得亲近的机会。接着下片写道: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
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在他们小驻的地方,应当没有第三者在场。于是他们便搂搂抱抱,未免轻狂起来。词人不管许多,“不怕人猜”,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一类清规戒律,遂有了相恋以来第一次甜蜜的体验。正因为是第一次,感觉也就特别强烈而持久。“最是分携时候”,多么依依不舍:“归来懒傍妆台”,何等心荡神迷!两笔就把一个初欢后的女子情态写活了。这两笔要想翻译得像原文一样情感充盈是具有相当挑战性的。
I didn’t care I was thought to be girlish and silly;
With my dress on,I slept in your arms straightway.
But the time when I parted you was really chilly;
Back home,at my dressing table I was lost in idle gaze.[18]199
此译文围绕原文创设了一个情感语境,两情相悦的人相约游湖,他们陶醉在二人世界里,相依相偎。可是,相聚越是甜蜜,分别越是难舍。所以,分别的时候一定是冰冷的(chilly)。独自回到家里,她坐在妆台前,怅然若失,她什么都不想做,只是痴痴地坐在那里,眼睛一定在凝望着。虽是凝望,其实什么都没有看,所以是“lost in idle gaze”,这不就是活脱脱的、约会归来的、心荡神迷的女子情态吗?
结 语
诗词是以情动人的文学形式,情感是诗词翻译中重要的参数。如果译者不注重于情感锤炼,即使言辞精美,其译文就像钟嵘批评玄言诗那样:“理过其辞,淡乎寡味。”[2]17“情感效度”强调“真实性”,读起来像是蓄积在诗人内心的一种不可抑制的情绪冲动,而非矫情、伪饰,或无病呻吟。只有“情投意合”的译文才能真正地让读者“知之,乐之,好之”。翻译诗歌除了要求译者具备很高的智商外,还需要很高的“情商”,译文要努力做到“情不动人誓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