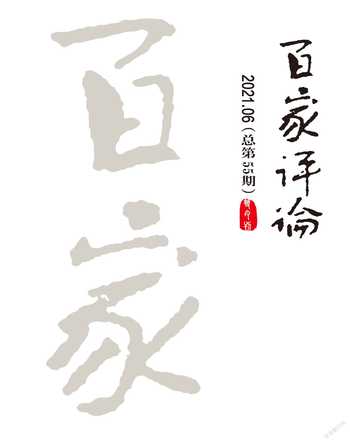建党百年乡土小说乡贤形象书写简论
田振华
内容提要:建党百年以来,传统乡土中国的存在样态和内在结构正在或者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贤在中国乡村变迁、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环节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推动乡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等领域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乡土作家塑造了一批批鲜活、生动的乡贤形象,乡土作家既把乡贤作为乡土文学重要的审美对象,又通过乡贤形象的行为事迹展现或透视百年中国乡村波澜壮阔而又摧枯拉朽的现代化进程。当下,在大力倡导乡村振兴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要通过乡贤形象再现乡土的真实魅力,重新认识乡土,进而为树立中华文化自信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美好未来奠定基础和动力。
关键词:建党百年 乡土小说 乡贤 乡村建设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既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进入改革开放和今天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富起来和强起来的胜利。建党百年的沧桑巨变,中国经历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再到城市中国的不断现代化之路。百年来,传统乡土中国的存在样态和内在结构正在或者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作为传统乡土中国的重要存在样态之一,百年来中国乡村日益现代化的变迁史就是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最好见证。乡贤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引领者,作为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政策的重要传递者,在中国乡村变迁、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环节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推动乡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等领域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钱念孙指出:“乡贤,旧时又称乡绅,是指在本乡本土知书达理、才能出众、办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在传统中国,乡村的基层建设、社会秩序和民风教化等,主要由每个村落和地方的乡贤担纲。这些乡贤或以学问文章、或以清明善政、或以道德品行等赢得乡邑百姓的高度认同和效仿,从而形成植根乡野、兴盛基层的乡贤文化。”①建党百年以来,乡土小说记录、反映和表现了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迁,在这一书写过程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乡土作家塑造了一批批鲜活、生动的乡贤形象,而不同历史时期的乡贤所面临的时代环境和个体命运也有所不同,乡土作家既把乡贤作为乡土文学重要的审美对象,又通過乡贤形象的行为事迹展现或透视百年中国乡村波澜壮阔而又摧枯拉朽的现代化进程。
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人”的发现与新乡贤形象的出现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同步的,它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代表着两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路径。”②建党之初,“五四”文学对人的发现,到1920年代乡土文学对“农民”的发现,展现的是中国文学对底层的关怀和日益凸显的人道主义情怀。乡贤作为农民的代表或代言人,从这一时期开始,就日渐成为乡土文学最为重要的表现对象之一。鲁迅、茅盾、沈从文、王统照、台静农、萧军、艾芜、沙汀、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周立波、赵树理等一批优秀的乡土文学创作者,不仅描述了封建文化旧乡贤的没落,而且塑造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新乡贤形象,呈现出从古老的乡土中国到现代新中国的艰难蜕变过程。
王统照的《山雨》中,就塑造了一个具有介于下层乡绅和村庄耆老之间的村庄领袖形象——陈庄长。他既是传统农民形象的代言人和领导者,又在动荡年代成为被压迫、被损毁的对象。面对时代不可逆转的洪流,虽然他们的努力最终无法扭转失败的颓势,但他们积极为乡村发展谋划出路、奔走呼号的精神,已经成为早期乡土文学书写的乡贤形象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这一时期,虽然共产党的队伍还不是十分壮大,但是作者从作品中塑造的新乡贤形象,特别是他们的行为事迹,背后所呈现的价值诉求与中国共产党服务人民、热爱人民的追求是不谋而合的。
大革命失败后到30年代,乡土文学中的乡贤形象表现出不同样态。在左翼作家群体中,乡贤或乡绅成为政治体制变革中的重要打击对象。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里的赵守义,叶圣陶《倪焕之》里的蒋士镳等受打击和破坏的乡绅形象,成为左翼乡土作家传递或表现左翼思想和时代洪流的重要手段。在国民党统治区,乡绅成为国民党对农村统治的代言人,成为乡村的实际控制者,如蹇先艾《四川士绅与湖南女伶》中道貌岸然的堕落士绅和《初秋之夜》中阿谀奉承、丑态百出的前清举人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和解放区范围的扩大,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在乡贤乡绅身上得到了体现。特别是以土地改革为代表的政策的实施,大大削弱了部分乡贤和乡绅的财力、权力和物力。乡土文学中的乡贤形象,要么是传统的作为富农代表的乡绅乡贤形象受到打击和迫害,要么是新的时代的新乡贤形象。这一时期现实乡村社会中乡贤形象呈现的是:传统的乡贤形象的集体大撤退和新乡贤形象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当然,这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和乡贤的政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态度和应对方式,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乡贤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特别是解放区文学在批判旧乡贤的同时,也塑造了一批新乡贤形象。
“十七年”乡土文学:社会主义改造视域下的新乡贤形象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反”“五反”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新乡贤形象层出不穷而又颇具时代风貌。这一时期赵树理、柳青、梁斌、郭澄清等乡土作家塑造了一个个富有时代感的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新乡贤形象。他们成为新中国农村社会中具有权力、威望而又富有集体意识、奉献精神的崭新形象,对推动中国农村建设运动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建设运动的代言人和践行者。这一时期的新乡贤与旧中国以地主为代表的旧乡贤形成鲜明对比,旧社会的地主合法地大量占有土地,而新中国土地公有背景下的新乡贤,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背景下的,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同样呈现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中的新乡贤形象。
柳青到陕北深入生活多年,实际上他本身就是一位具有时代使命的知识分子新乡贤形象。《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是研究“十七年”文学不可绕过的人物形象,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体现的正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新乡贤形象。梁生宝以其巨大的公心和面对困境所展现的魄力,成为践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建设运动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和捍卫者。梁生宝带领村名不懈努力,从扩大借贷到买稻种,从进山割毛竹到密植水稻,再到依据国家政策进行统购统销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建设运动相关政策的直接或间接体现。
山东作家郭澄清《公社书记》中的“公社书记”形象,是一位兼具地方权力、知识文化和勤劳双手的干部型新乡贤形象。首先他是一位地方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传递者。其次他还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可以拿起笔杆子谋划乡村建设的前景和未来。再次他还是一位农民,他可以和农民打成一片,拿得起“锄杆子”。他的“笔杆子练好了,锄杆子、枪杆子还都没撂下”。他是一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又自觉学习文化理论的新中国公社书记形象,洋溢的是一种理想主义气息。
可以看出,“十七年”时期乡土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新乡贤形象,大多都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乡村建设有着直接的关联,他们身上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正是新的时代新乡贤形象所需要的。当然,这一时期的历史题材小说中,对旧乡贤、旧乡绅形象也有所书写,如丁玲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恶霸地主钱文贵、梁斌《红旗谱》中砸碎共产凭证的冯兰池等。作者大多站在批判性的视角,对旧社会的旧乡贤乡绅形象予以批判和否定。
新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背景下的乡贤
形象建构
进入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乡村外在样貌和内在肌理都在发生着变化,乡土文学也因为创作环境的改变走向了深入。中国共产党与时代潮流同步,积极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稳步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新时代的新乡贤们有了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政策基础;统购包销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得农民大军也加入了商业化的潮流,以新乡贤为代表的农村能人的伦理观念也开始发生变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城乡之间的交流日益加快,新乡贤有了接触城市新思维和新理念的机会,从而可以更好地服務于农村建设;乡村文化建设运动的兴起,使得本就有着一定文化基础的乡贤们,有了加快发展乡村文化的动力。这一时期,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炜、赵本夫、刘醒龙、谈歌、和申、关仁山等为代表的乡土作家,通过新时期新乡贤形象的塑造,展现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迁。
1980年代,乡土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新乡贤形象要属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了。虽然孙少安是一个平民形象,不是一位有文化和知识的乡贤,但是他依托自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致富的精神,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积极开拓自我和村民的生存渠道,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等一系列行径,足以使他成为新时代新乡贤的代表。他身上既保留了传统社会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具有强烈的公心和奉献精神,又能顺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势,积极带领村民分地种地,还能兴办村级企业,给村民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摆脱贫困的同时为国家创造财富。孙少安作为这一时代的新乡贤形象,他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实际上都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他很好地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运动的政策和要求,成为新时代新农民形象的重要代表。
1990年代,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实施,乡村变迁背景下乡村的活力日益减退,乡村衰败甚至乡村消失成为一个无法逆转的潮流。而乡村衰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乡贤为代表的乡村能人的纷纷出走,他们远离故土,纷纷走向生存环境更好的城市或它地。李静就指出:“从梁生宝、李月辉、刘雨生到萧长春,再到郭存先、呼天成、权桑麻,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乡贤的形象是怎样一步一步蜕变,传统乡贤的文化道德精神是怎样一步一步沦丧,并最终埋下了1990年代之后中国乡村文化溃败的内在危机。”③这一时期的乡土作家们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新历史乡土小说中,呈现历史中的乡贤形象,挖掘乡贤的内在价值,同时表达对当下乡贤出走或缺失的反思。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白嘉轩身上汇聚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和文化的核心元素,他的身上既完整地保留着仁义礼智信的一面,又有阴险狡诈和顺势而为的一面。当触及村民公众利益时,他仍能够坚守自我初心,同时他身上还具有责任担当意识。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作者还塑造了一个近乎圣者的乡贤形象——朱先生。王斯福指出,当代中国乡村领导制度“其中一种类型的制度只是基层政府的行政,另一种是由下而上的‘传统’权威以及他们在文化知识与地位上的声望等级。”④朱先生是乡间大儒,他熟知天下大势而守其一隅,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声望。当日本人的残暴行径入侵当地时,他愤慨之下舍弃小我,以年迈之身奔赴战争一线。这一时期,作者之所以塑造了这样一个传统乡贤形象,与1990年代乡村衰败特别是乡村文化的衰败有关。白嘉轩和朱先生身上所具备的优良传统文化品质,在这一时期日渐走出大众视野,成为这一时期所稀缺的存在。这一时期的乡村能人大多将经历集中于自我欲望、权力和财富的满足中,这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代表作家刘醒龙、谈歌、和申、关仁山等的作品中有着直接体现。现实的乡村社会,再也难以看到如朱先生和白嘉轩这样的乡贤存在,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当然也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事情。
新世纪:“加速社会”视域下乡土作家的新乡贤想象
进入21世纪,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速度日益加快,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的标签,中国真正进入了德国加速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所指称的“加速社会”。社会加速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乡村消失的速度加快,传统意义上的乡贤几乎彻底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这一时期的乡贤更多地停留在作家对历史的想象中。作家们或者通过对乡村变迁的书写,展现乡村的衰败特别是乡村文化的凋零,或者通过书写传统乡贤形象在新的时代日益呈现唯利是图的样态。
贾平凹的《秦腔》中,作者塑造了夏家五兄弟“仁”“义”“礼”“智”“信”,但在新的时代,他們失去了各自名字中内含的元素,即使是尚有所保留的那些人,也都早早离开了人世。这里明显可以看出作者隐喻的表达:传统乡贤所具有的那些美好品质,在加速社会到来之时,就已经荡然无存了。此外,关仁山的“农民命运三部曲”,付秀莹的《陌上》、叶炜的《福地》等多篇作品中,都有着这样的表达。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乡村日益凋零甚至快速消亡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通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和全面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等措施,开始了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新的乡村建设运动。在这一运动的号召下,许多作家开始以虚构或非虚构的方式,书写中国乡村振兴的过程,塑造或想象适应社会现实的新乡贤形象。
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中,就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新乡贤形象——范少山。范少山被称为新时代的“梁生宝”,他本可以在北京做点小生意,但当生意有了起色后,他却选择回到大山里的农村中,带领当地人克服重重困难,因地制宜发展本村经济。很快本村的生存环境得以好转,收入来源日益多样化,逐渐走出贫困的深渊。值得一提的是,作品末尾提到了范少山带领村里儿童背诵村训的情节,这展现的是作者对复兴乡村传统文化的一种探索和渴望,同时这也与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对实现乡村振兴和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诉求一致。
此外,21世纪乡土小说中的乡贤形象众多,其性格类型也日趋多样。主要包括历史强人型、知识分子型、乡村能人型、忍辱负重型、改革先锋型、哲理反思型、城市返回型、道德复杂型等。莫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贾平凹《带灯》、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张炜《你在高原》《独药师》、李佩甫《生命册》、周大新《湖光山色》、王方晨《公敌》、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张继《乡村爱情》系列、阿来《空山》《格萨尔王》《瞻对》《蘑菇圈》、刘震云《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阎连科《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毕飞宇《玉米》《平原》、格非《人面桃花》《望春风》等作品都塑造了众多各具特色的乡贤形象。在艺术特征上,英雄化的塑造手法依然是主流,但是多样化的性格特征也越来越多。对比、反讽、隐喻、互文、解构等手法被大量应用于塑造乡贤形象。乡贤形象所面临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也日趋复杂。在结构形式方面,新世纪的乡贤书写也多种多样,出现了乡村志、人物志、传奇史、心灵史等多种写法,乡贤与乡土生活之间的关系被多样化重构。
乡贤是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运动政策的传递者,也是乡村建设运动实际的见证者和践行者。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是乡村建设持续现代化的进程离不开乡贤的努力和参与。乡贤也成为乡土作家发现乡土、建构乡土和想象乡土的途径之一,乡贤形象更成为乡土作家挖掘乡土历史、乡土文化和乡土情感的寄托。百年来,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乡贤形象为我们重新认识乡土、重新发现乡土乃至展望乡土未来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坐标。当下,在大力倡导乡村振兴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要通过乡贤形象再现乡土的真实魅力,重新认识乡土,进而为树立中华文化自信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美好未来奠定基础和动力。
注释:
①钱念孙:《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学术界》2016年第3期。
②陈思和:《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③李静:《当代乡村叙事中乡贤形象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④[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当代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021SJA1045”);2021年江苏师范大学职业生涯教育精品重点项目“成就‘新乡贤’型乡村教师,助力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