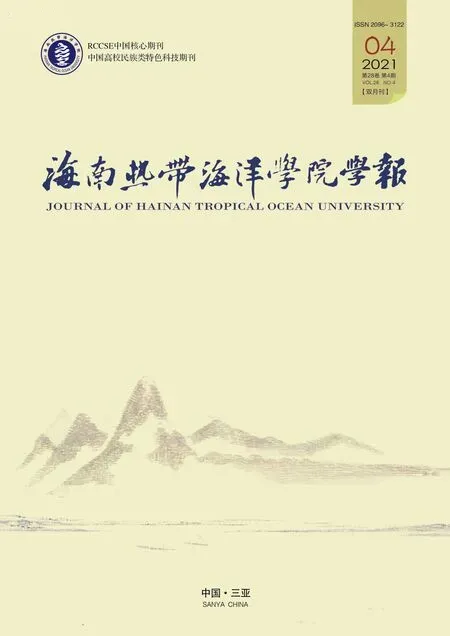张载的道德理想及其建构路径
——以“横渠四句”为中心
郭敏科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100089)
大同社会一直以来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张载秉承前人的美好愿望,在《西铭》中进一步描绘了这一蓝图,其志向也通过“横渠四句”[1]加以总结。但无论是《西铭》所绘的亲亲社会,还是“三代之礼”的协和有序,抑或是“横渠四句”的崇高旨趣,都隐隐含有理想化的色彩。在其具体实践措施上,冯友兰指出:“王安石的措施是现实主义的,张载所计划的措施是理想的,或者说简直是幻想的。”[2]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张载的理想对于政治家来说近乎遥不可及。但是他辟佛造道,重建儒学思想体系,有力地回应了绝大部分的现实问题,这一影响又是为历史所不能否认的。以此,他的道德理想又与现实的国计民生紧密相连。事实上,张载是从不同维度来回应和建构其道德理想的,“横渠四句”无疑最为集中地表达了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结合。《西铭》是其“理想国”的基本蓝图,而“横渠四句”既可看作是其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完整的表达,也可看作是达致这种理想蓝图的建构路径。“为天地立心”是以“仁”为心,为人确立价值根基;“为生民立命”是以“义”为命,为人确立应当之路;“为往圣继绝学”是以“智”相继,为人传承文化命脉;“为万世开太平”是以“礼”相合,使人人均平。“信”者实之,四者皆践履不懈,则理想可期。这种“理想”,并非是一朝一夕之理想,而是万世之“理想”。与其说它是一种难以实施的具体政治实践,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实践背后的正义价值,即他所思考的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将建基在什么价值之上?如何实现这种价值?“横渠四句”正是基于这些问题对此进行回应的。
一、 立人心——仁为天地之心
余英时教授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指出,与古文运动和改革运动一样,重建理想的人间秩序也是北宋道学的政治关怀的中心所在。有所不同的是,“面对着新学的挑战,他们为自己规定了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为宋初以来儒学所共同追求的理想秩序奠定一个永恒的精神基础”[3]。对张载而言,永恒的精神就是在天人之间确立人道价值的基石。在他看来,人为天地之心,而为天地立心,就是以天道为根基确立人心的价值依据,这种价值依据来自天地的生生之德,即“仁”。
人为天地之心,这一论断历来为儒家所公认。早在《礼记·礼运》篇就有言:“人者,天地之心也。”[4]277后世南宋哲学家王应麟也说:“人者,天地之心也。”[5]王夫之说:“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6]清朝学者也认为:“天地无心,人者天地之心也。”[7]人何以是“天地之心”?总体而言,是以人之贵与万物之灵为主要缘由。《礼记》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4]276朱熹似乎秉承了这一观点:“惟人也得其形气之正,是以其心最灵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体,于并生之中又为同类,而最贵焉……而物则得夫形气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与我不同类而不若人之贵。”[8]立天地之心,实为立人之心,“故人心即天心,立天之道,所以定人”[9]。
在张载看来,立人心又必须依据天地之心而立,其价值依据来自天。他在发挥《彖传》时说:“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10]以生物为本就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就是不断地创生、生生。但是从存在论上而言,生生本身就是天地的特性,心却不同于生物本身的特性而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词语,这二者之间又需要可以联系起来的桥梁。从传统儒家一贯的传统以及他的哲学理路来看,以宇宙观作为其道德观的价值来源,是他必然的选择,“与天地不相似,则违道也远矣”[11]35。可见,张载之道是来自于天地本身,其价值根基从天地之特性演化而来。他认为天地所行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教法,可以作为“至教”,“天道四时行,百物生,无非至教”[11]35。
因此,对于天地而言,其德为生生;对于人而言,其德为生生之德,为善。从存在论上说,恶并不促进人之生,恰恰是善促进人之生,所以,依据天心的生生之德,人也应该展现出与天地不断创生一样的向上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人道所立的基础,即生生之善——“仁”。“生”与“仁”的这种联系也为诸多思想家承认,如“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则天地之心不立矣。为天地立心,仁也”[5]。戴震在《原善》中说:“生生者仁乎!”[12]马一浮也认为“天地之心于何见之? 于人心一念之善见之”[13]。
为天地立心,就是使人持“仁”而立,择善道而从。这种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善行,而是使人依据天地之生所选择使人能够真正发展自己正确价值的善,为人道奠定价值根基。“夫人心至是,几不立矣,知人心便知天地心。自先生斯言出,举凡人心皆有以自持,其不至于高卑易位,东西易面者,胥由之矣。是天地之心无能自立,先生为之立之也。”[14]在张载看来,“儒者应该肩负起为社会确立以善为核心的道德文化价值的历史使命,心中始终想着如何能弘道于天下,而不是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安危”[15],立定人道价值基石,方能开拓人之社会理想,此所以为天地立心。
二、 正人路——义立生民之命
人道已立,则人所向何方、所行何处便是张载构建“理想国”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这也是基于对当时现实问题的回应。佛教尚空,无礼无义,人们行无所据,难以真正的安身立命。他从气一元论出发,分人性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从宇宙论上说明人们把握命运的可能——气之变动不居顺理而不妄,因此人于后天可以穷理尽性、变化气质。与生生之德的人道相对应,仁之所处当义以行之。为生民立命实为以义立生民之命,确立人之当行之路,使万千生民皆有安身立命之本。
“生民”与“立命”都出于传统儒家典籍,但张载赋予了其新的哲学含义。“生民”是人民的意思,《尚书·毕命》载:“道洽政治,泽润生民。”[16]《诗经·生民》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嫄。”[17]“命”在传统儒家文献里也不少出现,但较早完整论述的应属孟子。孟子将命分为正命与非正命。在孟子看来,人之不能为者为天,不能致者为命。他说:“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18]所以,命无能为不能为,而有正与不正。正其命,就是顺承天之所命,正道行之。非正命,就是自己招致祸端。朱熹解道:“人物之生,吉凶祸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顺受乎此也。”[19]冯友兰对这一句也解释说:“此整个的环境中,有绝大的部分,不是他的才及力所能创造,亦非他的才及力所能改变……是就其非才及力所能创造及改变说。”[20]正其命,就是孟子的“立命”。所谓立命,就是把握命运的方向,这种把握,是指人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以当下的作为来为未知命运定向。孟子言桎梏、言非正命都与存心养性、尽其道对举而言,其实存心养性即修身以俟,二者并列同一,所谓事天就是立命。换句话说,对孟子而言,存心养性、集义尽道都是“立命”的工夫。而立命,实质就是尽其所性的德性之命,张载正是在此基础上阐释自己的“立命”说的。
他继承了孟子的德性之命说,但二者人性论的出发点不同,孟子从四善端出发谈德性之命,而张载依据天人之性与气质之性,将命分为“气命”与“德命”[21]。张载说:“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故论死生则曰有命,以其言气也;语富贵则曰在天,以其言理也。”[11]23意思是“以天或天道为根源的命运属于‘德命’,以生理和恶俗等因素为根源的命运则属于‘气命’或‘德命’”[22]。人要尽力穷理尽性,以德胜气。而这种变化的依据又是来自气的变动不居,“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11]7。所以,人就可以顺气之理来“变化气质”。
“德命”是为人可以把握的,也是人所当行的。张载说:“富贵贫贱皆命也。今有人,均为勤苦,有富贵者,有终身穷饿者,其富贵者只是幸会也。求而有不得,则是求无益于得也。道义则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11]311“求在我者”的道义,就是“德命”,而这种“德命”正是通过“义”来体认和证成的。对张载来说也是如此,人应当之路正是在以“仁”为根底的人的价值根据上作出来的,“义,仁之动也,流于义者于仁或伤;仁,体之常也,过于仁者于义或害”[11]34。生民之命就是所说的大义,“义公天下之利”[11]72。富贵福泽之所以能厚吾之生,就在于此生为德性之善,所以为厚;贫贱忧戚之所以能庸玉汝于成,就在于此等患难更能砥砺德行而以德胜气。所以存吾顺事,存义而顺性命之正;没吾宁也,是尽义而心有所安。张载提出为生民立命,正是要万千生民在祸福难测、人世无常的命运中,以“义”确立道德价值方向,以“义”来安身立命,以“义”来确立人之应当之路,从而掌控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
三、 开人智——智继往圣绝学
继立人心、正人路之后,张载构建“理想国”的第三步是开人智,这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辟佛破妄,使人自信自足;二是复兴儒学道统,开启人的生命智慧;三是开发智识,使人勇于为学。如此则人们能够担负起道统复兴和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弘扬和光大人道,为往圣继绝学。
当时诸多思想家都认为,儒学失落,道丧已久。张载认为,既然能够使人所知,那么道就有存在和重新唤起的合理性。而往圣绝学之所以不得传,正在于佛氏之盛而此学者鲜少。所以培育学者,昌明此学便是其使命。但是昌明此学并不容易,因为当时佛氏之说遍布大江南北,“至今薄海内外,宗古立社,念佛之声洋洋乎盈耳”[23]。这使得社会人伦无序无礼,“瓯越之民,僧俗相半,溺于信奉,忘序尊卑”[24],迷信泛滥,“宋代统治阶级极力推进儒、佛、道三教的合流,从而促使了封建迷信的泛滥”[25]。溺于信奉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现实生活苦难的关注,从而缺乏了改造现实的动力,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痛苦,于国民生计无益。人伦无序、迷信盛行,加之民生艰难,佛氏无力于此现实生活的改善,无法振奋人之改造精神,都使得张载决意辟佛破妄。
辟佛当以儒学为基,张载从哲学理论高度上来批佛。一是批评佛氏以空论性使人无所立。他意识到,佛氏不立天而以心法起灭天地,是本末倒置。如此,现世虚妄则人无所自立。不难看出,在崇尚性空的背后,是人的现实生活与主体性的退场,“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与!夏虫疑冰,以其不识”[11]26。只有立天与性,从现实的人出发,才能使人实际的认识自身之性,从而拓开内在的生命智慧。“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11]63牟宗三对此解道:“清通太虚落实于个体生命即为性,此谓张横渠之天地之性,也即吾人性体之根源,故万物一源、寂然不动、感而遂通。”[26]二是批评佛氏不明人伦无序无礼使人无所据,不察庶物空谈自误,使人无所学,“因谓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故未识圣人心,已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11]64。他在气一元论的宇宙论基础上阐发了人们认识的可能性以及为学的路径,把人性结构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指出人们的恶来源于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是可以通过学习改变的。这种对人性的解释批判了佛家的轮回说,使命定理论逐渐瓦解。人们的注意力开始专注在力所能及的现实改变中,“性犹有气之恶者为病,气又有习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于齐,强学以胜其气习”[11]329-330。
张载所以基于儒学辟佛破妄正在于佛氏之学不仅有违儒家传统的刚健有为精神亦使人无法担负起人世的责任与义务,而他昌明此学就是要使人能够自立自足,以此拓开人内在的生命智慧,启发人的智识,以此现世之“实”来破来世之“虚”,以此奋发变化气质来克生活之艰难困苦,使人能够在现实的社会中挺立起来——于社会责任中提升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智继往圣绝学既是张载对自己一生奋斗的写照,也是对人们担负道统复兴与文化传承的殷切期望,更使人的本质得以还原先秦儒学的原生血脉——人必定的处在一系列的人伦秩序之中,因此,对于家国责任,我们责无旁贷,而这也是他在第四句话中所要展现的。
四、 理想国——为万世开太平
“为万世开太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秩序以及如何重建这个社会的秩序问题。《西铭》描绘了这样一副社会蓝图,其具体的实践措施则在张载“复三代之礼”的思想中得以体现。对张载而言,“礼”就是秩序的象征,“何谓礼?条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12]。道德教育之礼在重建人们内心和行为的道德秩序,而“三代之礼”则是为了重建社会纲常与道德规范的秩序。但是“三代之礼”远离张载的时代千年之久,为何张载一定要效仿“三代之礼”呢?他所效仿的“三代之礼”到底在哪些地方可以作为他的政治实践方案?
张载所要恢复的“三代之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一个朝代制度的完全重复与复制,而是价值理念意义上的因时损益。“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事业者,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但非时中者皆是也。……时中之义甚大,须是精义入神以致用,始得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此则真义理也;行其典礼而不达会通,则有非时中者矣。”[11]262这种因时损益的特质与他的气之变动不居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时损益就是体会其“精义入神”,得其“真义理”。这种“真义理”则是通过对“礼”的本质的认识而把握的。“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变!……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11]293对他来说,天地之礼是“天叙天秩”,自然而不假于人,其表现便是“尊卑大小之象”。这种天然的秩序是出自其事物本质的内在规定。当我们把握其“真义理”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它外在的这种变化,更要把握其中不变的东西。《西铭》中描绘的相亲相爱的道德和谐画卷,正是在张载天地之礼的本质规定下的应然的社会状态,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万世太平”。合内外之道就是既要有理想的应然图景,更要有为之能“开”的可行之策。
“渐复三代之治”的治理之策便是“开万世太平”之路,即恢复井田、重建封建、恢复肉刑。前两条措施许多学者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张载之策没多少可行性。不仅王安石对此不置可否,就连朱熹在与弟子们讨论时也说:“讲学时,且恁讲。若欲行之,须有机会。经大乱之后,天下无人,田尽归官,方可给予民。如唐口分、世业,是从魏、晋积乱之极,至元魏及北齐、后周,乘此机方做得。荀悦《汉纪》一段正说此意,甚好。若平世,则诚为难行。”[27]通过张载自身的实践看来,此法确实很难实行,吕大临在张载行状中也说“此皆有志未就”[11]384。但是很明显,张载并不是凭空杜撰出这样令人难以理解的政策来,实质上,他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状而提出这样的对策的。
当时人民贫苦,国家积弱。北宋不立田制,允许土地自由交易,《宋史》记载:“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刬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甽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28]因此,土地兼并严重,从而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如马端临说:“自汉以来,民得以自买卖田土矣。盖自秦开阡陌之后,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于富贵者也。”[29]民因此流离失所,生计艰难。“恰则炎炎未百年,今看枯柳着疏蝉。庄田置后频移主,书画残来亦卖钱。春日有花开废圃,岁时无酒滴荒阡。朱门从古多如此,想见魂归也怆然”[30]。
抑制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使人民生计自足,便成为当政者的首要任务,也被众多思想家所关注。如庆历新政时范仲淹就在《答手诏条陈十事》建议“均公田”。他认为,建国之初,民生凋敝,士人之家依靠国家俸禄可以自给自足,等到安定多年物价上涨,俸禄不继,士人家生存问题便日益显现,于是便有人行侵民占田之举。土地私相交易,而徭役不均,受损害最大者无疑是贫弱百姓。“在天下物贵之后,而俸禄不继,士人家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复于守选、待缺之日,衣食不足,贷债以苟朝夕。得官之后,必来见逼,至有冒法受赃,赊贷度日;或不耻贾贩,与民争利。”[31]
因此,均平田地,缩小贫富差距,从根源上为百姓解决生存问题,使其自足,为国家开源节流、振奋武备,便是张载提出治理之策的出发点,而“恢复井田”自然首当其冲,“治天下之术,必自此始”[11]212。基本的民生与民计才是张载井田之策的出发点,贫富不均是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所谓‘井田’,就是改变土地占有方式,并非改变原来土地占有制度,只是在封建土地制度下,抑制土地兼并,为土地占有不均做些调整”[32]152。张载认为田地上的均平需要政治制度的支撑,这种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上的,“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11]259。保证朝廷有世臣,在于确立“宗子之法”,但是宗子之法不是一个家族所宗,而是以国为家之宗,作为家庭的“宗子之法”仅仅是一种个人德性,而作为国家的“宗子之法”则上升为保家卫国,“在张载看来,仅仅依靠个人内在德性的忠义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国运与家世联系起来”[33]150。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张载之所以提出恢复井田与封建的真正缘由:一般意义上的家与国并没有在人们的情感中建立起一种于家一样的亲密联系,而以国为家,在宗法意义上来建构的家国一体才能真正唤起人们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这也正如学者李蕉[34]指出的,张载是在人民之利的层面来思考问题,其意在“公天下”。张载之所以将封建制视作治国政体的最佳选择,是因为他认同“封建制度”中所内蕴的“公天下”价值追求。张载意识到“公天下”才能充分调动政体中各个阶层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治国效率。兼顾“公”“私”利益平衡,尤其注重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新的时势下封建制有可能复兴。
结 语
“横渠四句”是张载在面对时代之问时做出的积极的、正面的、强力的儒者式回应,正如张立文指出的,“宋明理学家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职志;以建构伦理价值本体,给出安身立命、精神家园为标的;以格物致知、修养心性、自利自律、存理去欲为工夫。他们是当时的社会脊梁和社会良知的担当者,是时代精神和价值理想的创造者”[32]3。它不仅涵盖了张载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同时也内蕴着对理想国度的追求。所谓“理想”之意味是在应然状态而言的,而前置的每一个动词,又将这种理想转变为一代儒者的艰苦实践和不懈努力:责任之在我也,当仁不让于师!
时值儒学式微与文明危机,现有的儒学自此无法解决人们安身立命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人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佛学以其形而上的信仰构建的报应说、轮回说虽然吸引着人们,但是佛学尚空,在乱世之中逃避社会责任,这一点与自古以来儒家士大夫的担当精神格格不入,也无法真切的有力的解决人们的苦痛和迷惘。先秦儒家的学说缺乏形上理论性深度的说明,董仲舒的神学伦理学在封建王朝的更迭中也完全被淹没,玄学儒学则趋向顺其自然,这一切的学说,都无法对现实问题给予非常有力的回应,并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
在此情形下,张载意识到必须建立和恢复正常的秩序,重建人们的价值信仰,使人们行有所据。《西铭》实质上是其道德理想的政治实践表达,是他道德理想的基本蓝图。他将家和国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宗法关系由旧有的血缘政治结构变作了哲学本体论,观念上的宗法想象变成了维系社会秩序的一条纽带,从而使人们开始觉醒一种家国意识和担当意识,这使得天下在理论意义上成为一家,各个阶层拥有了理论上的血缘关系,从而给了家国另一种意义上的联系。“这表明张载巧妙地弥合了经学与时政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因此而大得士人的欢心,传统的修齐治平获得了新的社会格局的支持,本属于先秦社会的亲亲与尊尊的社会秩序也因此而获得了新的落脚点,毫无皇族血缘的士大夫阶层也由此而重续了血统,和皇族攀上了亲戚,变成了孟子所谓的‘贵戚之卿’,自然也承担起‘贵戚之卿’而非‘异性之卿’所当承担的责任,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便自然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便是宋代知识分子对时政之担当精神的一个出处。”[35]
而“横渠四句”则是“理想国”具体的建构路径。重建人在天地的地位,立定人道的价值根基,此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对纲常无序、道德规范失调做出的回应,义以立命,是使人有所立,正路有所行。为往圣继绝学,是他意识到儒学式微危机做出的回应,智继往圣绝学,是使人能够安顿身心与精神信仰。为万世开太平是他的天下大同道德理想的政治实践。我们不必苛求一个哲学家能如一个政治家抑或王安石、张居正一样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政治改革措施,但我们却可从其中管窥其宏大无私的政治价值指向:他重视民生,力求使民自足而不为盗;力求均平,使耕者有其田不为贫不为乱;他教人变化气质,使民自信,天下可治,仁德可昌。
张载的道德理想是一个哲学家对一种完美社会的理想和向往的认真思考,同时也反映着他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北宋道学虽然关注北宋王朝具体的政治实践和操作,但更为核心的关切仍在于理想人间秩序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建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达成理想人间秩序的根本途径上,道学家更强调的是礼乐和风俗的重建,而非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尝试的政治制度的变革。”[33]142在这一意义上,他的道德理想更多的指向的不是具体的政治实践,而是政治实践背后的正义性质。他以崭新的理论形态重新阐释了人和天地、人和社会的关系。此心安处是吾乡,于中国人的心中所安,正是“横渠四句”所唤起的在“公天下”理念之下的一个民族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为其传人吕大钧等“坚持用儒家治世理念求得国家的稳定”,“将礼学思想融入社会实践中去”[36]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