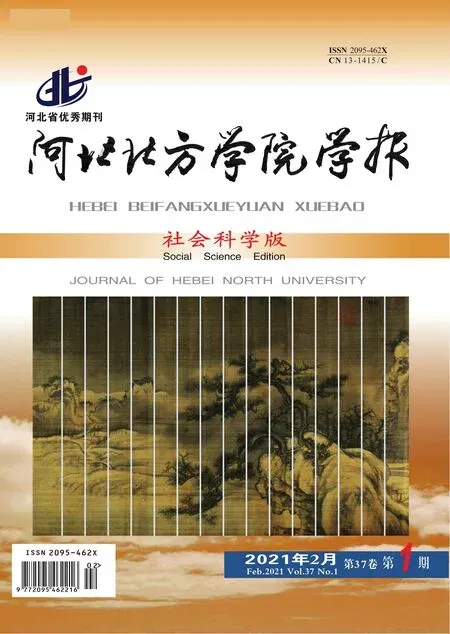文化翻译视域下的《牡丹亭》英译
——以汪榕培英译《牡丹亭》为例
魏 梦 溪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中国的翻译历史从晚清算起,距今已有百余年。众多翻译方法和翻译理念层出不穷,而翻译中最难的莫过于对不同文化所渗透的知识和理念进行转化。因此,文化翻译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汪榕培是中国著名的经典文化典籍翻译家,他提出的“传神达意”的翻译理念也正是文化翻译中所讲的文化层次,对其《牡丹亭》译本翻译策略进行研究可为古籍翻译提供借鉴。
一、文化翻译的内涵、原则及方法
语言本身带有民族性的社会文化特征。文化决定了人们的生存和思维方式。作为最能深刻反映文化的语言,其中包含着本民族的情感、思想和信仰。因此,文化背景相异的人会存在理解障碍。为了克服此种障碍,文化翻译应运而生。文化翻译的核心其实还是对语言的翻译,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表现。
文化翻译的原则是文化对等,要使译入语与源语言的读者能产生相近的文学体验。翻译中不仅强调文化的再现,同时也需要对文体风格、人物语言风格和作家的写作风格等进行整体把握。翻译也是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过程,需要兼顾以内容为主导的创作原则[1]。换而言之,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准确传递内容,当源语言文本形式与内容相冲突时,应当以内容为主导。
通过文化翻译的内涵以及原则可知,文化翻译最终还要落脚于对语言的翻译。翻译方法包括直译法、意译法、替换法以及加注法等。直译法尽可能保留了源语的文化特征。意译法是在文化差异无法翻译的情况下侧重于对源语言的内涵意义进行翻译。替换法是当源语言中某些语言形式的文化属性在目的语中缺失或与目的语文化体现形式相异时,用目的语中具有同等功能的指称来代替源语言的相关表达。加注法是当源语文本中出现具有特定文化色彩的人物、事件和典故时,通过增词和加注释来进行翻译[2]。
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符号形式的转化,而且也是一种文化间的交际行为。因此,处理源语文本中的语言形式有归化和异化两种方式。归化翻译是从目的语出发,清除文化理解障碍,使译文符合目的语语言习惯的对等翻译。其代表人物奈达认为,翻译应该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就是“以读者反应为中心”,无论是表达方式还是文体风格,都归属于读者文化范畴。而异化翻译则是从源语言出发,帮助读者了解陌生的异国文化。解构主义学者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应当“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差异”。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两者是辩证统一的[3]。
文化间性翻译走出了传统的归化与异化、意译与直译的二元对立论,其目的是在考虑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促使处于两种文化中的人进行交流,改善文化间的关系。间性一词最初使用在生物学中,表示雌雄同体之意,后来被用在社会学和文学当中。主体间性是指主体在对象化活动中与他者的关联性,其本质是主体间的平等与开放的对话关系。文化间性强调主体间性在文化中的体现,其核心在于文化的差异和共存。如果说文化间性是平衡两种文化主体的翻译策略的话,那么文化调停则是省略文化意义的妥协策略,也就是将源语文本的文化因素省略不译,只翻译其中的深层含义[4]。
二、汪榕培英译《牡丹亭》概述
《牡丹亭》原名《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是明代著名戏剧作家汤显祖的作品。其文辞华丽,人物形象生动,通过歌颂生命与欲望鞭挞了腐朽的封建礼教。虽然已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但其艺术价值却历久弥新。21世纪初,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牡丹亭》作为中国戏曲史上最重要的戏曲作品之一,其翻译与传播就显得更为重要。目前,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英译本当属以徐朔方和杨笑梅的校注本《牡丹亭》为底本的汪榕培译本。汪榕培在翻译《牡丹亭》时注意到了戏剧中韵文与散文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如果把唱词和诗体都当作散文来翻译的话,诗句优美的形式就不复存在。因此,他采用英国传统的格律诗的形式,不仅在形式上与原文接近,同时也能产生间离效果,使西方读者更好地领略原著的风貌。同时他还指出,诗体比散体更能表现忧郁的情绪[5]。汪榕培在译文与源文本之间形式和内容的转换与统一中运用了文化翻译的原则和方法,对文化翻译的灵活运用是汪榕培英译《牡丹亭》成功的关键。
三、汪译《牡丹亭》中的文化翻译方式
汪榕培英译《牡丹亭》中主要采用了4种文化翻译方式,分别是归化、异化、文化间性以及文化调停。
(一)归化
在汪译本《牡丹亭》中,第十出“惊梦”被翻译成“An Amazing Dream”。因为“惊梦”二字内涵丰富,汪译本将其翻译为偏正结构,淡化了杜丽娘从进入庭院到入梦过程的心理变化。这是归化的翻译方式,目的是方便外国读者理解。再如【步步娇】的唱词中,杜丽娘娇羞照镜这一段也堪称经典。“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雲偏。”汪榕培将其译为:
In the courtyard drifts the willow-threads,
Torn by spring breeze into flimsy shreds.
I pause awhile
To do my hairstyle.
When all at once
The mirror glances at my face,
I tremble and my hair slips out of lace.
“闲庭院”被翻译成“courtyard”,杜丽娘“闲”的心理感受在翻译中被译成了对“院”的单纯描述,“景”与“情”的交融变成了只有“景”的描述。“丝”音同“思”,“线”是“思”在形式上的体现,但因为在英语中没有文化对等词,所以“摇漾春如线”省略了“线”的意象,被翻译成“被春风撕成碎片”,这些都是为方便外国读者理解而采取的归化翻译方式。“停半晌、整花钿”中“停”的主语是缺省的,从上下文可知“停”这一动作的发出者是杜丽娘。考虑到英语中主语必须存在的句法特征,汪译本将主语补充完整,且选择了第一人称代词“I”和”my”而非第三人称,这是因为第一人称更能体现杜丽娘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反对封建礼教的坚定,这样处理也符合大部分外国读者对于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个人理想的文化心理。此外,为了降低读者的理解难度,“花钿”被简化为“hairstyle”,“菱花”被译为“mirror”。由于“偷人半面”一句表现了杜丽娘在偷照镜子时灵动又娇羞的样子,因此译文中除了用“glance”表达“偷”的概念以外,还添加了“tremble”来表现其心惊的样子。
(二)异化
汪榕培对《牡丹亭》中大部分曲牌名采用了拼音形式,但对少数可以阐释意义的曲牌也进行了解释。如《惊梦》【绕池游】直译成“To the Tune of Raochiyou”;【隔尾】被翻译为“To the Tune of Quasi-coda”,【尾声】被翻译为“To the Tune of Coda ”。不管哪种方式都属于异化处理,保留了中国文化中曲牌名的特色,目的是为了促进源语言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交流。
杜丽娘入梦前有一段宾白:“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汪榕培将其译为:
In the past,Lady Han met a scholar named Yu,and Scholar Zhang came across Miss Cui.Their love stories have been recorded in the books.The Story of the Maple Leaves and The Life of Cui Hui.These lovely ladies and talented scholars started with furtive dating but ended in happy reunion.
此段宾白主要写杜丽娘感慨春色虽好却无人爱怜的心情,其中提到了两段古人的爱情故事,表达杜丽娘对于爱情的向往。《题红记》讲述了宫女韩翠屏与书生于祜通过红叶题诗寄情并最终喜结良缘的故事[6],译文中“lady”直接对应韩夫人中的“夫人”一词。《崔徽传》讲述了娼妓崔徽爱慕裴敬中却不得善终的故事[7],汪榕培将“崔氏”直译为“Miss Cui”,“氏”直接对应“miss”,表示未婚女子或者年轻女子。“lady”与“miss”都是基于源文本的异化译法。汪译本对于复杂典故的人物关系并没有随文添加词语或加注说明,而是采用异化的翻译方式,将《题红记》和《崔徽传》翻译为“The Story of the Maple Leaves”和“The Life of Cui Hui”。
(三)文化间性
《牡丹亭》下场诗中采用集唐诗的形式,不仅使其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同时也最具中华美学的传统形式。《惊梦》一出中的集唐诗为:春望逍遥出画堂,间梅遮柳不胜芳。可知刘阮逢人处?回首东风一断肠。汪榕培将其译为:
A springtime tour from painted halls,
Brings near the scent of bloom that falls.
If you should ask where lovers meet,
I say that hearts break where they greet.
在集唐诗的翻译中,汪译本的特点是韵律整齐,体现了通过形式“传神”的翻译标准。《牡丹亭》原著辞藻华丽,讲求平仄押韵,汪译本《惊梦》一出中则采取了抑扬格的形式,注重句式、节奏和韵脚[8]。《惊梦》中的4句诗各有出处,第一句出自张说的《奉和圣制春日出苑应制》,讲杜丽娘怀春所看到的庭院之景,“春望”一词被译作“A springtime tour”,“画堂”翻译为“painted halls”,描绘杜丽娘闲情的“逍遥”一词缺省。第二句出自罗隐的《桃花》,本写桃花的香气,这里借用“梅”和“柳”二字暗示男主人公柳梦梅的名字。译文中虽然将“柳”与“梅”的意象进行了省略,但用“scent”对应“芳”,隐喻万物生发的春之香气正是杜丽娘的爱情。第三句出自许浑的《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岭》,这里借许浑之诗暗示了杜丽娘与柳梦梅是在梦境中相遇。第四句出自罗隐的《桃花》,表现杜丽娘梦醒之后的怅惘心碎之情,译文中用“hearts break”来对应“断肠”,且为了与上句“遇仙”连接,用“where”引导状语从句表示“lovers”相见的地点。汪译本在保留诗句基本含义的同时也翻译出了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原文情景交融。形式上,则使用四音步抑扬格搭配aabb韵律,节奏明快、形式隽永,以英语诗歌形式展现了中国诗的韵味。
(四)文化调停
汪译本对生、旦、净、末、丑、外、贴等类型化的角色采取了直接以名字代替的翻译方法,如“生”译为“Liu Mengmei”,“旦”译为“Du Liniang”。中国戏曲中的角色是人物社会身份的象征,其性别、年龄及地位等均在角色名称中得以体现。清代李渔认为,生和旦所扮人物一般品性高洁,而净和丑所扮人物则以诙谐为主[9]。这些内涵丰富的角色类型在英语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概念,自然无法采用归化的方式,若采取拼音加注又会繁琐。因此,汪译本采用了文化调停的翻译策略。如第二出《言怀》中柳梦梅的宾白:“小生姓柳,名梦梅,表字春卿。原系唐朝柳州司马柳宗元之后。”汪榕培将其译为:
My name is Liu Mengmei,also called Chunqing.A descendant of Liu Zongyuan,poet and Prefect of Liu-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源文本中姓名分开介绍的形式是中国讲唱文学的特点,除此以外,“表字”是汉族男子在20岁冠礼之后起的表示德行或者与本名意义相同的名字。“名”是一个人的称谓代号,而“字”是对“名”的解释与补充,两者互为表里。柳梦梅在开场白中就通过改名这一行为暗示了之后牡丹亭要发生的事情,“春卿”中的“春”字更是对杜丽娘入梦时节的谶语。英译则忽略这些文化因素,直接用“also called Chunqing”来翻译。“原系唐朝柳州司马柳宗元之后”一句表明柳梦梅的出身,“poet”是译者添加的对于柳宗元的解释,而用“Prefect”即“地方行政长官”来表示“司马”一职,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因素的省略。
文化翻译是对不同层次文化的翻译,但其核心还是对于语言的翻译。《牡丹亭》作为明人汤显祖最著名的戏曲作品,其英译本众多。上文将汪译本《牡丹亭》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各种翻译方式的交叉运用进行了分析,以期能为其他学者的文化翻译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