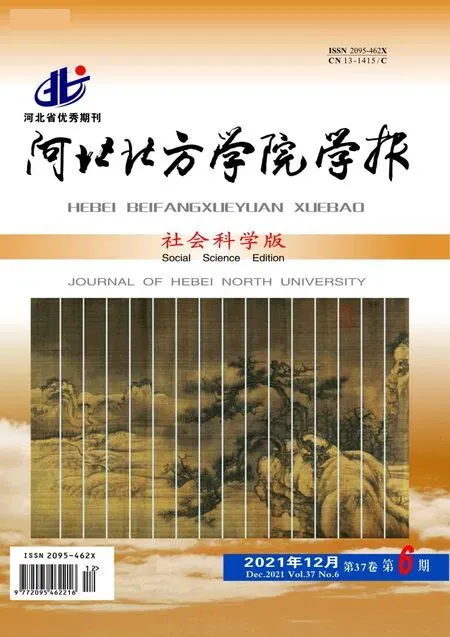论《扶桑》与《小姨多鹤》中异国生存的女性形象书写
姚 津 津
(喀什大学 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在严歌苓塑造的一系列异国生存的女性形象中,扶桑和多鹤是两个特殊的存在。扶桑是走出去的中国人,多鹤是走进来的日本人。《扶桑》讲述了中国少女扶桑被拐卖到旧金山唐人街的妓院里邂逅了美国少年克里斯的故事,《小姨多鹤》则讲述了流落中国的日本孤女被卖到张家替人生孩子的故事。对比分析两部作品中异国生存的女性形象,可为解读严歌苓的小说提供新的视角。
一、扶桑与多鹤的身份象征
扶桑被作家置于19世纪华人劳工到美国旧金山务工的时代浪潮中,多鹤则身处抗日战争结束后反日情绪强烈的中国,她们都处在19-20世纪这段充满变革与冲突的动荡岁月中,且都深陷两个民族的历史性交锋中。扶桑是流落在美国的中国人,多鹤是流落在中国的日本人,她们都是异国生存的女性,且在异国都遭遇了不幸:扶桑被以“六元一磅”的价格拐到旧金山的唐人街当妓女;多鹤被以“一角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张家当作生孩子的工具。扶桑与多鹤的身份使其都陷入了民族的歧视与仇恨之中,前者是被美国人歧视的黄种人,后者是被中国人仇恨的“日本鬼子”后代。作为第一批华人劳工,扶桑和她的中国同胞在异国被视作“东亚病夫”,被当作“比人便宜的游过太平洋的人形老鼠”,被用作“驴一样的苦力”。他们处于种族歧视的漩涡中,被认为是一个该被灭绝的低劣人种。扶桑因为自己民族的弱小而备受歧视与欺凌,多鹤则成为自己民族犯罪后的替罪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种种残暴行径激发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日情绪,当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因抗战而死去的亲人,张家也不例外。张俭的哥哥死于抗日战争,张俭的媳妇小环也因躲避日本兵的追杀而流产最终无法再生育,战后的中国人痛恨日本人。所以,当日本孤女多鹤来到张家后,“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家仇国恨情绪的发泄口。可以讲,扶桑的身上背负着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歧视,多鹤的身上交织着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仇恨,她们的命运都在两个民族的拉扯下被撕裂。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扶桑与多鹤都爱上了异国的男子,扶桑爱上了美国少年克里斯,多鹤爱上了中国男人张俭,却不被所爱男人的民族所接纳。
扶桑与多鹤站在历史的交叉口上,身上都有鲜明的历史印迹与时代色彩,即资本主义发展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冲突。《扶桑》揭露了资本主义奴隶贸易对中国劳工的残酷压迫,《小姨多鹤》表现了侵华战争对战后中国的深刻影响。19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导致劳动力紧缺,美国资本家从大洋彼岸的中国运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廉价劳动力供自己所用。以扶桑为代表的第一代华人劳工事实上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奴隶贸易的畸形产物。扶桑最初是一个乡下的种茶女子,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的代表,她被人贩子漂洋过海地卖到美国,成为华人劳工共享的妓女也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9世纪3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滋生殖民主义思想与侵略扩张野心的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侵华战争,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混乱动荡中。在中国的日本眷属村是日本殖民主义的象征。抗日战争胜利后,包括多鹤在内的日本眷属的流亡则象征着日本殖民主义的失败。多鹤在与张家人一起生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三大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中日建交等中国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缩影。严歌苓赋予扶桑与多鹤相似的身份与经历,将她们置于异国环境中,用她们的生命轨迹展现了不同民族的历史荣辱与兴衰。
二、扶桑与多鹤的民族象征
生死观是一个民族价值观的最直接体现。中国人认为“生”是崇高的,而日本人认为“死”是崇高的。中国人讲究“忍”,认为忍耐是人的生存法则。《扶桑》中,当第一代华人移民遭到美国人不加掩饰的厌恶与光明正大的驱赶时,他们谨遵祖先教诲中的“忍”字并将其当作至宝与精神信仰,丝毫不敢懈怠。中国劳工们总是安静地忍耐,默默地做事,被白种工人称作“黄色工蚁”。“他们天不亮就一个个赤足走到工地上干活,却拿着最低廉的工资,靠着一小罐米饭一撮盐活下去。”[1]47“中国文化‘重生’,这种‘重生’的观念,是务本求实的,是悲天悯人的。而日本文化更‘重死’。日本是一个崇尚自杀的国家,认为死亡是无所畏惧的,同时也是备受尊崇的,是超脱一切的。”[2]《小姨多鹤》中多次出现了自杀这一情节。日本侵华战争失败后,在中国的几个眷属村的村长带领村民集体自杀殉国,多鹤见证了这场惨烈的聚众自杀,她和部分村民出于求生本能逃跑了,但在逃生路上见证了更可怕的死亡:无法支撑的老人默默跳进河里,母亲们仿佛屠夫一般了结自己婴孩的生命,一觉醒来少了好多人的队伍……多鹤也深受这种自杀情结的影响,她曾有3次想要自杀:被张俭抛弃后、同张俭幽会被捉后以及张俭被捕后。每当多鹤深感无望时,她的脑海中总是闪现自杀的想法,“她想着一了百了,想去另一个世界里找自己的日本代浪村”。与多鹤相反,中国人小环提倡“凑合文化”,“事实上,这种‘凑合’也是一种韧性,是民间固有的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实用性极强的生存智慧。也就是小环这种对生活的热爱与柔韧的态度改变了多鹤,把多鹤从自杀的边缘拉了回来”[3]。
小说中,严歌苓赋予扶桑与多鹤鲜明的民族本色。扶桑代表的中国是暗红色的,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色彩,它神秘而昏暗。扶桑身上有着鲜明的中国特征,她有一双残颓而俏丽的“三寸金莲”,总穿着红绸衫和黑长裙,戴着两条长长的耳坠;她用花汁染红指甲,半倚在雕有花纹的圆木桌上;她有时品茶,有时嗑像被血浸了的西瓜子,有时吸田螺。她的房里常年熏着檀香,房外挂着红灯笼,走廊上是来往的嫖客,乱哄哄的妓院外是脏乱不堪的唐人街。而多鹤代表的日本是白色的,这是中国人眼中看到的日本色彩,是过分干净的。多鹤是一个十分讲究的日本女子,她总是把张家人的衣服熨得平平整整,老是跪在地上认认真真地把水泥地面擦得发亮,她要求大家脱鞋进家门,遇见谁都要鞠躬问好。“对她而言,日本就是小火车运来的一包包紫菜,一捆捆印花布,是母亲做的酱鱼、红豆团,是母亲擦地、洗衣、熨衣、拜神、拜长辈丈夫儿子时弓下的背。”[4]多鹤虽然生活在中国,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日本人。
扶桑与多鹤虽然深受各自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熏陶与浸染,但生活在异国的她们势必会受到异族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同样,她们的存在也自然会影响身边的异国人。美国白人少年克里斯与扶桑的爱情象征着东西方文化的交织与纠缠。起初,克里斯在扶桑身上感到了“鸦片般的魔力”。但他在为扶桑着迷的同时,也开始憎恶带给扶桑身心痛苦的中国男人和影响扶桑“忍”的中国文化。他渴望带扶桑逃离唐人街这一“迷你”的东方世界,想凭一己之力帮助扶桑摆脱原生民族对她的种种影响。所幸他最后觉醒了,他意识到是东方文化塑造了扶桑。克里斯因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而爱上扶桑,又因为扶桑重新接纳了东方文化。成年后的克里斯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反对迫害华人以及华人间的互相残害。“他已不再囿于单纯肤浅的爱情,而是在追求一种人性的理想”[5],扶桑使克里斯接纳了东方文化。多鹤则是用真心付出得到了张俭一家的尊重与接纳。起初,张俭一家只把多鹤当作延续香火的工具,并打算在多鹤生完孩子以后就赶走她。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张家人都无法离开多鹤。他们都习惯了熨得平整的衣服、刷得发亮的水泥地面以及一尘不染的家。多鹤也学会了张家人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当多鹤学着“美死了”“哎呀妈呀”与“吃了没”这些中国话时,她开始努力适应中国;当她生下几个孩子并随着张家四处搬迁时,她开始接受中国;当她爱上张俭时,她开始爱上中国。可以讲,多鹤与张家的平淡生活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习惯的碰撞与融合。
三、扶桑与多鹤的情感象征
严歌苓赋予扶桑与多鹤相同的情感意蕴,使她们凭借顽强与隐忍的高贵品质在强者世界倔强地生存。扶桑作为妓女遭到了无数的凌辱与折磨,但她是从中国来的3 000名妓女中活得最长的一个,她也是极少数奇迹般活过20岁的幸存者。扶桑在异国求得生存的原因在于她用自己的“痴”与“温吞”软化了苦难的痛,她如凤凰一般具有超越和重生的能力。“扶桑在创伤性事件中的未创伤化姿态反转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沉默坦然的接受来言说底层女性的抵抗。”[6]扶桑用沉默来软化苦难,多鹤则用倔强来抵抗苦难。面对抗日战争后中国人强烈的仇日情绪,多鹤作为日本孤女在中国顽强地生存下来。日本同胞死后,她靠着给张家当生育工具活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生完孩子被张俭丢弃后,她倔强得“没个人样儿”地走了几十天找到了张家;文革中多鹤身份暴露,她一个人毫无怨言地打扫十几个厕所……可以讲,她是被歧视、被嫌弃与被抛弃的弱者,却倔强地活了下来。
扶桑的沉默与多鹤的倔强都是女性顽强生命韧性的体现,扶桑像水一般柔韧,多鹤像山一般坚韧。她们外表柔弱,身份低微,是整个社会歧视与霸凌的对象,如果没有强大的生命韧性与坚忍的意志,她们早已被社会的洪流冲刷得面目模糊甚至尸骨难存。严歌苓曾这样形容扶桑,“她跪着,却宽恕了所有站着的人们”[1]236。扶桑的一生受尽欺侮,作为人却被当作牲口一样买卖,作为女人被男人侮辱,作为中国人被西方人歧视,但她的脸上至始至终带着温吞的笑容。“跪”同样贯穿了多鹤的一生,她跪着擦地洗衣,同时也“跪着”原谅了伤害过自己的丈夫、儿女和友人。她们的姿态是跪着的,但她们从未向任何人屈服,反而以一种更高的姿态宽恕他人。她们跪着的卑微姿态与其高贵的精神品质毫不矛盾,她们是生活的弱者,却都是生命的强者。
扶桑与多鹤所遭遇的异国生活困难与文化冲突困境正是严歌苓自身情感的投影。作为第五代华人移民,严歌苓在美国求学与生活,并嫁给了白人丈夫,这使她面临着语言交流的障碍、行为习惯的差异与强势文化的压迫。移民者的身份使严歌苓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也引发了她心灵上的漂泊感与文化上的无归属感。严歌苓的超越之处在于她并没有囿于这种无归属感,而是将其转化成一种文学创作的自由感,“由于游离在两种文化背景之间,使她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中穿梭,从而获得比一般人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视野”[7]。她用双重的文化心理投入到“移民文学”的创作中,《扶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小姨多鹤》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移民文学,但也着重关注女性在异域生存的困境。严歌苓在两部作品中都有意识地表现了异国生存的女性身上深厚的民族文化和不可磨灭的民族色彩,体现了她们对本民族深沉的爱,也展现了严歌苓自身浓重的的民族文化意识。换言之,《扶桑》与《小姨多鹤》是严歌苓在思想情感、民族观念与文化视野等方面的自我映射。
扶桑与多鹤是严歌苓塑造的两个异国生存的女性形象,她们在身份背景、生活遭遇以及情感态度等方面有很强的相似性。她们在异国的生存状态展现了时代造就的坎坷命运与民族矛盾带来的悲惨遭遇,也展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扶桑》与《小姨多鹤》都展现了女子在苦难中的坚忍顽强与宽容高贵的生命姿态,也传达了严歌苓的思想感情倾向与民族文化观念。扶桑与多鹤身上的重重印迹是时代、民族与作家共同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