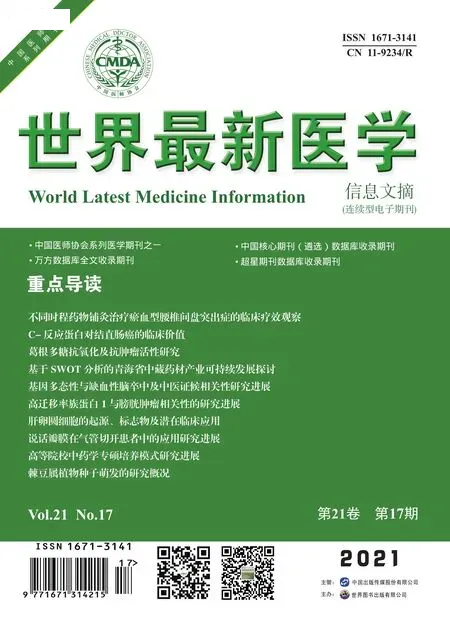从经络讨论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的发病关系与治疗前景
方正逸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 成都 610000)
0 引言
过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 AR)又称变态反应性鼻炎,是指特应性个体接触致敏原后,由IgE 介导的介质(主要为组胺)释放、并由多种免疫活性细胞和细胞因子等参与的鼻黏膜慢性炎症反应性疾病[1]。哮喘是支气管哮喘的简称,是一种以慢性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为特征的异质性疾病[2]。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过敏性鼻炎和哮喘都被认为是毫无关联的两种疾病,这两种疾病虽常相伴而行,但由于现代医学临床分科不同的缘故,患者常常经年在耳鼻喉科以及呼吸科间辗转治疗,极大增加了患者的就诊难度与就诊压力。近年来,国内外诸多研究发现,全球过敏性鼻炎患者中有20%-40%合并哮喘,而哮喘人群中有40%-80%合并过敏性鼻炎[3],这一调查结果显示鼻部疾病与支气管哮喘间关系密切,有学者提出二者发病机制均是基于临床或亚临床的呼吸道Ⅰ型变态反应的认识。ARIA指南也详细阐述过敏性鼻炎与哮喘的关系,提出“一个气道,一种疾病”的新概念,“慢性变应性全气道疾病综合征”的概念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将二者视为同一种疾病进行深入研究。
1 中医对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的认识
中医古籍对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未有专门的论述,但查阅古籍和近现代文献可知过敏性鼻炎类似于中医耳鼻喉科学中的常见病“鼻鼽”,而支气管哮喘类似于中医内科学中的“哮病”。
1.1 中医对过敏性鼻炎的认识
过敏性鼻炎类似于中医耳鼻喉科中常见病“鼻鼽”,是以突然或反复发作的鼻痒,喷嚏频频,清涕如水,鼻塞等症为主要表现的鼻病。鼻鼽首见于《内经》[4],《素问·脉解篇》曰:“所谓客孙脉则头痛,鼻鼽,腹肿者,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其孙络太阴也,故头痛,鼻鼽,腹肿也。”[5]明代王肯堂在《证治准绳》中对其注释:“鼽,鼻窒也”,解释为闭塞不通,此时的“鼻鼽”还尚未单独作为病名出现。遂至唐代,《素问吴注》中提到:“鼽,音求,鼻出水谓之鼽“,出现鼽嚏,鼽水,鼻流清涕等别称,至此鼻鼽指鼻流清涕的认识逐渐被各医家认可和广为流传。从金元时期开始,有鼻鼽作为单独病名的专节记载出现,各医家开始对其病因病机及治疗做出深入研究与探讨,成果斐然。
1.2 中医对支气管哮喘的认识
支气管哮喘类似于中医内科学中的哮病,是一种以反复发作的痰鸣气喘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患,临床症状因人而异,程度轻重不一,多在夜间及凌晨发作或加重。中医早在几千年前便对此病有了相关的论述,但病名尚未统一,有 “喘鸣”“喘喝”“上气”等不同称谓。直至金元时期,朱丹溪在《症因脉治》中首次提出了“哮喘”的病名,病名逐渐统一。东汉时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设专篇论述“上气”,其辨证已分虚实,出现用射干麻黄汤、越婢汤等方治疗该病的记载。至明代,《医学正传》中记载:“喘促喉间如水鸡声者谓之哮,气促而连续不能以息者谓之喘”,将哮和喘分为两种症状,并做出明确区分。至此,中医哮喘理论趋于完善,对指导哮喘的临床实践治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 鼻鼽与哮病的发病关系
2.1 中医对鼻鼽、哮病发病机制的认识
中医学认为,鼻鼽多由禀质特异,脏腑虚损,兼感外邪,或感受花粉,灰尘及不洁之气所致[6]。《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提到,鼻鼽的病因主要包括原发病因和诱发因素。其中原发病因为肺脾肾三脏虚损和(或)痰饮水湿内停;诱发因素多为外感邪气(以寒邪为主)、饮食所伤、情志变化及气候变化等。哮病的发生内责之于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津液凝聚成痰,伏藏于肺,留为夙根;外责之于外感六淫,气候突变,加之素体饮食不调、情志不畅、劳倦体虚等诱因引发水液代谢失常,聚而成痰,阻碍气机,致使痰阻气道,肺气上逆,气道挛急,发为哮喘。其中,气候突变是哮病发作的主要诱因。
2.2 鼻与支气管生理联系
鼻,又称明堂,位于面部正中,为肺之官窍[7]。《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记载:“肺主鼻,在窍为鼻”[8]。《灵枢·五阅五使篇》有云:“鼻者,肺之官也。”[9]这些论述阐述了鼻与肺间的络属关系。从中医角度看,肺开窍于鼻,鼻与喉相通而连于肺,鼻作为肺之门户辅助肺行使其主气,司呼吸的功能[10]。若肺气调达,鼻窍通畅,呼吸平和,鼻能辨识香臭,控制气体进出功能正常,肺鼻协调,人体生理功能活动正常[11]。若肺气亏虚,肺宣发肃降功能失调,气机上逆,鼻窍壅塞,嗅觉亦受影响。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鼻与支气管及肺间的关系密切,上下呼吸道黏膜间有解剖上的连续性。鼻鼽与哮病分别作为鼻,肺支气管的常见病变,均属于肺系疾病,两者间也常互相影响,相兼为患。
2.3 从经络论治鼻鼽与哮病联合发病的病因病机
鼻鼽与哮病联合发病,患者常出现反复发作的鼻痒,喷嚏频作,流清涕,鼻塞,咳嗽和喘息等整个肺部系统的病理证候表现,与近几年现代医学提到的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Combined Allergic Rhinitis and Asthma Syndrome,CARAS)症状表现类似[12]。CARAS 发病的始动因素为感受外邪(以风邪为主),“风善行而数变”,故CARAS 患者常伴有皮肤湿疹或耳、鼻、眼等官窍瘙痒的症状。笔者从中医经络理论系统为出发点,详述CARAS 的发病机制与过程,旨在为诊治该类疾病的临床医生提供理论指导方向与思路。
体质是疾病生成的土壤,相同体质的人群常罹患同种或类似疾病,现代中医学家认为,CARAS 以“阳虚体质”和 “过敏体质”最为常见。“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在此笔者以“阳虚体质”的患者为例分别论述手太阴肺经、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阴肾经与CARAS 发病之间的关系。
2.3.1 手太阴肺经
《灵枢· 经脉》曰:“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13]手太阴肺经循行经过肺及其相联系的组织器官,与肺部疾病的发病息息相关[14]。
“阳虚体质”患者大多由于先天禀赋不足或疾病长期反复发作而致气血虚弱,正气不足,阳气虚衰,蒸腾气化失司,素有伏痰。恰逢邪气外袭,正气亏虚,卫外不足,邪气由表及里侵袭肺脏,与体内伏痰两邪相合,痰随气升,壅阻气道则发为哮喘;外感之邪循经上扰鼻窍,气机循行受阻,气不行津,津液停聚鼻窍发为鼻鼽。
2.3.2 足太阴脾经
《灵枢·经脉》中有记载:“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可知手太阴肺经经脉循行与气血流注均经过中焦脾胃[15],且足太阴脾与手太阴肺作为同名经同属于太阴,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位处中焦,是一身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脾气亏虚则肺脏失于濡养,气机升降失调进而发为哮喘及鼻鼽,若脾气得健,肺气有所养[16],则气机升降得调,哮喘及鼻鼽自愈,故《石室秘录》曰:“治肺之法,正治甚难,当转治脾,脾气有养,则土自生金。”[17]且脾主一身津液的运行,脾气得健,津液运化有常,不得聚而成痰,则哮喘及鼻鼽的夙根自除,故足太阴脾经在哮喘及鼻鼽的治疗中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18]。
2.3.3 足阳明胃经
《灵枢·经脉》:“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旁约太阳之脉,下循鼻外。”足阳明胃经起于鼻旁,上行鼻根[19],可见阳明经气血流注经过鼻部[20]。胃经素为多气多血之脉,气血翻涌,胃病则鼻部气血流注不足,鼻窍失于濡养,卫外不固,则邪气易从鼻窍侵犯人体,导致人体气机运行失常,津液输布失司,可发为哮喘及鼻鼽。
2.3.4 足少阴肾经
鼻鼽、哮病共同发病日久,久病伤肾,足少阴肾经受损,《灵枢·经脉》云:“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可知肾经有一旁支经脉走行过肺,上循喉咙。肾阳为一身元阳之根本,肾阳亏虚,蒸腾气化功能失司,水液输布异常,痰浊内生,留于体内,成为哮喘及鼻鼽发病之夙根,与外邪相合乘虚发为哮喘及鼻鼽。且肾主纳气,与肺共同调节全身气机的升降出入,肾气亏虚,纳摄无权,气机升降失司,引动伏痰上扰可发为哮喘及鼻鼽。
3 小结
受现代医疗体系影响,哮喘和鼻鼽常分而论之,但两者在发病机理上存在许多共通之处,两者都有宿痰伏于体内的诱发因素,且两者在治疗上都可以从肺、脾、胃、肾等脏腑来论治,现代研究也证实全球过敏性鼻炎患者中有20%-40%合并哮喘,而哮喘人群中有40%-80%合并过敏性鼻炎[21],故将两者合而论之,既可减少患者的就医负担,也可提高医生的临床疗效,又合中医“治未病”思想,一举三得。两者在发病后期,手太阴肺经、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与足少阴肾经均可全部受邪,肺脾肾三脏皆虚,病情严重。“过敏体质”的患者则多是素体禀赋不足而致免疫力低下,不能抵抗外邪的侵袭故致病,在此不做详述。过敏性鼻炎与哮喘均属于现代医学中常见慢性病的范畴,治疗周期长,容易复发,完全治愈有一定难度,且具有一定的遗传性,患者受众面积广,波及率高,故治疗前景较优,研究潜力大。祖国医学理论以阴阳为本,阴阳调和为基,重在宏观调和人一身之气血,兼以经络循行理论为辅,疏通各经脉,微观调整局部气血阴阳,两相合之,为治疗过敏性鼻炎与哮喘提供了安全可行、潜力巨大的诊疗思路与研究方向。笔者略呈拙见,意在抛砖引玉,望吾辈之同僚楷模发而扬之,为过敏性鼻炎及哮喘患者早日减轻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