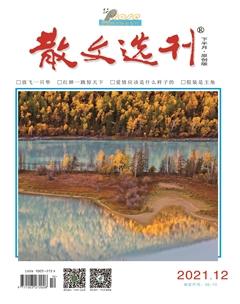一碗苦菜汤
温秀清

苦菜是餐桌上的美味。如果把它和猪大肠一起煮,吃起来又是一种特殊的香味。然而,苦菜易得,猪大肠难求。
那年仲夏,乡里圩日,父亲特意买回一副新鲜肥厚的猪大肠。然后,母亲就忙碌起来了,焯苦菜、洗大肠、劈柴火、炖高汤,像过节似的忙着。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像一群饥肠辘辘的“饿鬼”,围着母亲团团转。母亲不紧不慢,烧开大铁锅里的水,把苦菜干扔进锅里焯,再用冷水清洗,过滤。苦菜汤苦味的浓淡,全靠焯水时间的长短,短了苦味浓,長了苦味淡。
洗净的新鲜猪大肠和焯过水的苦菜干在锅里相遇后,经历着一场炽热的相恋。灶里的柴火在熊熊燃烧,大铁锅里发出“噗噜、噗噜”的声响,那股特别的香气,从屋里飘到屋外,再从屋前飘向远方,邻居不出门,就可知道哪户人家炖苦菜了。苦菜汤想做得好吃,也需要下一番功夫。它的味道和火候有很大关系,熬的时间不够,苦菜又硬又涩,汤色黑,味道苦。熬得太久,苦菜太烂,没嚼劲,不香。三到四小时后,熬好的苦菜汤被母亲装在一个大铝锅里,我们姐弟拿着碗争先恐后去盛,母亲看了在旁边呵斥着:“你们这些妖荒,三年没吃过东西啦,把锅打翻了看你们还吃个啥?”我们顾不上那些,迫不及待地装上一碗狼吞虎咽起来。用大火熬出的汤,苦中带着清甜,吸上一口,立马征服味蕾。苦菜叶不苦不涩,大肠肥嫩爽口,细细嚼之,唇齿间回荡着一股大自然原始的清香。
苦菜在农村还能用来做杀猪菜。通常,母亲把猪大骨扔进大铁锅里,用柴火灶先熬出汤汁,再把焯好的苦菜加进锅里和猪骨头一起炖上两三个小时,然后装在一个大木桶里。不用打招呼,左邻右舍们听到猪嚎声,闻到苦菜味,就会各自从家里走来,聚在一起看热闹,唠嗑。当母亲从厨房往大厅端出一木桶热气腾腾的大骨苦菜汤时,邻里们顾不上谈话,拿着大碗自己动手盛。谁也不用拘束,撑开肚皮,想吃几碗就几碗。炖制多时的苦菜香气扑鼻,大骨肉美味鲜,抓上一块,越啃越有味。黑色的汤,苦中带甘,滑入喉根,舒爽温润。如此美味,让人吃到快撑破肚皮,还舍不得放下碗筷。
苦菜不仅仅是菜,还是一味药。
那一晚,我牙疼得厉害,母亲就做了一碗我爱吃的荷包鸭蛋。那碗苦菜汤很苦,我是知道的。但我是醉翁之意不在汤,而全在那两枚荷包蛋上。为了能尝到诱人的蛋,我手掌捂着腮,表情装得很难受的样子,用微弱的声音对母亲说:“妈,我这几天牙齿时疼时好,现在感觉又疼了。”声音很小,但母亲却听得很清楚。她没说什么,只是笑笑,然后拿起勺子,拨开碗中的苦菜,切下一块蛋白,塞进我的嘴里,然后再切,一块一块地分给姐姐、弟弟。最后,鸭蛋几乎被我们瓜分完了,她才“吧唧、吧唧”地把苦菜和汤一起吃完。
慢慢地,大肠苦菜汤成了德化街头一道受人青睐的小吃。那些夜归的人们在一块小方桌前坐下,叫上一碗拌面,再来一碗大肠苦菜汤,最能慰藉心灵呀。
——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