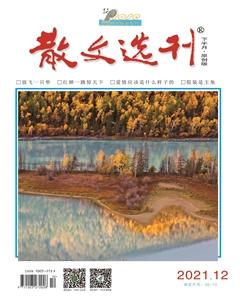一张发黄的粮票
2021-01-11 02:32吴仲尧
散文选刊·下半月 2021年12期
吴仲尧
日前,整理读高中时用过的那只旧书箱,从一本破损的《新华字典》里,抖落一张皱巴巴、面额半斤的浙江粮票。睹物思情,不由想起那个艰难的票证年代。
记得我12岁那年的腊月,跟父亲去上海走亲戚。临行前,父亲想方设法托熟人帮忙,想调换一些全国粮票备用,结果到处碰壁,一无所获。父亲愁得团团转,唉声叹气地对我说:“你可要好好念书,争取将来成为一个‘吃粮票’的公家人,赚些全国粮票回来。”最后,还是在供销社上班的邻居,忍痛割爱,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父亲感激涕零,就差没给邻居下跪。
1982年秋,我考入离家约15公里的章镇中学读高中,吃住在学校,生活十分清苦。每当看到镇上几位有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着雪白的馒头、飘香的油条,我眼馋得要命,但囊中羞涩,只好望食兴叹。有次周末回家,与父亲闲聊,无意中提及在外读书,没有粮票的無奈处境,老实厚道的父亲面露难色,感觉怪对不住我似的,硬让母亲凑了几两粮票,叫我带上。周日留校,清晨我兴冲冲地走进早餐店,买了一根油条,两个肉馒头,吃完,一打嗝儿,满嘴油香味,浑身舒坦。回到教室,我端正地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吃上令人羡慕的供应粮。”
1985年夏天,上天眷顾,圆了我的大学梦,捧上了梦寐已久的“铁饭碗”。毕业参加工作时,农村早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粮票宣布作废。
我将那张发黄了的粮票重新收藏起来,当作是我一段苦涩的岁月的一份见证。
猜你喜欢
作文周刊·小学二年级版(2022年28期)2022-07-19
汉语世界(2021年5期)2021-11-24
共产党员(辽宁)(2019年3期)2019-11-18
共产党员·上(2019年2期)2019-03-29
散文选刊·下半月(2018年7期)2018-09-26
金秋(2018年22期)2018-03-25
商周刊(2017年17期)2017-09-08
金融理财(2016年5期)2016-12-15
创新作文(小学版)(2016年17期)2016-11-11
学苑创造·C版(2016年6期)2016-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