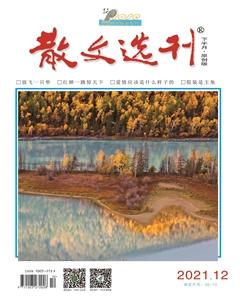我的哑巴学生
汪道波

偶遇老同事他告诉我:“罗浩没了。”“谁?”他说:“你班的罗浩——哑巴。”
我一怔,傻傻地站在小店门口,一下子想起7年前在山里支教的日子,哑巴好像站在面前,咧着嘴,怯怯地笑。一双黑粗节巴的手,不知所措地插在破旧的蓝衫兜里,一半伸不进去。
2013年9月,我到罗山县彭新镇前锋小学支教,担任三年级班主任,当我点名点到叫罗浩的学生时,最后一排的一个男孩站起来,点了两遍也不答应。班长陈思雅举手告诉我,他是哑巴。
我让罗浩坐下。然后自我介绍,我讲了山外的城市,城市的公园,公园里的树,树下的草,草丛的花。引用了十几首唐诗宋词。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我问他们山外好不好?第一排叫罗昭阳的女孩举手说好。我问他们想不想到山外的城市去,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想。我告诉他们,从今天开始好好学习,你们的高中,你们的大学,你们的生活,一定在山外的城市。
下了课,学生们围着我,问东问西。只有罗浩站在角落,我过去,梳理了他乱草似的头发,笑着问:“罗浩,想不想到山外去?”他惊慌地后退,差点撞了墙。几个学生哄堂大笑。我说你们笑什么?许多说不出话的人都在其他方面特别聪明。我打开手机,找到《千手观音》让学生们看,说这些大姐姐都说不出话,可是,她们的表演特别棒。
罗浩也可能有特别聪明的地方,你们谁能说一说他聪明在什么地方。陈思雅说,他心肠好,常帮助我们扫地。罗昭阳说,放学回家,过小桥,他牵我们的手,一个个送过桥。叫罗长江的学生说,我家羊跑山上,他帮忙赶,身上扎了狗尾巴刺也不叫疼。
想不到学生们竟然说了这么多。叫刘创的男孩说罗浩不写字不交作业。一听这话,罗浩低下了头。
我上完语文课,布置默写词语任务。我特意关注罗浩,他正埋头写呢。当我发现他拿着铅笔,在作业上画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注意到我在身边,忙放下笔,直直地看我,好像沉思什么。
下了课,我把他叫到教室外说,你画的老师没看懂,你想让老师看懂,得学会写字,把你想告诉我的写出来,他用力点头。
每天进班,总是看见罗浩要么摆放桌椅,要么打扫卫生。他扫地不洒水,灰尘大。我到井台打水,洒了,重新扫。他后来到厨房外蓄水池提小桶水,先洒水,再扫地。
罗浩平时总穿墨绿的上衣,黑裤子,露脚的秋鞋。衣服脏,还破了许多地方。放学后,我把他留下来,用热水给他洗头洗澡。
一个周末,下小雨,我送罗浩回家。弯弯曲曲的路坎坎坷坷,他怕我摔倒,总在险处牵我的手。到了他家,我吃了一惊,破旧的灰瓦土墙房,两间,小院堆了杂乱木柴。
一个中年妇女灰头灰脸,抬头看我,忧郁的神情,抿紧的厚唇。罗浩拉着她衣角,指着我,比画。
女人站起来,拍打身上的灰尘。问,你是老师?才来的?罗浩又做坏事了?我,唉,打也没用。没爹管,我一个女人也顾不了他。
我问罗浩父亲在哪里。她说跑了,好多年前到山外打工,一直没回来。要不是这不会说话的孩子,我也跑了。
我说不出话,也不知怎么安慰这个女人。我不知道是怎么离开她家的。月光如水,我心却似火。一路想着怎么帮助这孩子上完学。
罗浩不受所有老师待见,学校也当没这个人。每次统考评比,把他排斥在外。平时,也没人过问他。有的同事说,他就是废人,长大了也没法独自生活。我也这样想过。我甚至担忧他妈妈真跑了,他该怎么办。
我早晚自己做饭,中午在学校食堂吃。每次吃饭都给他留一大碗饭菜。周六不回城的话,就领着他和几个孩子在山里走。我背唐诗,为他们讲解诗意。他们饿了,我就分给他们饼干,渴了,每人一瓶矿泉水。学生们也讲山里的奇闻轶事。
我常常让罗浩洗完澡,光着身子躺在我的床上看连环画,我用电风扇吹干他的衣服。我带了很多连环画让他看,又给了他学习用品。联系县中医院专家为他和学生们体检。
时间久了,罗浩也写字,也交作业了。数学老师陈民惊奇地说,太阳真从西面出来了,哑巴交作业——对错没啥,只要学习就行。罗浩各科成绩再也不是零分了。
他就像缠人的孩子,只要我单独坐着看书写作,他总搬个小凳坐在后面,有时用书当扇子,有时捏捏肩、捶捶背。我也给他讲故事,他聚精会神地听。
就这样,我在那所小学支教一年。光阴迫,寒假最后一天,我告诉学生们以后不在这里教书了。孩子们哭了。放学时,罗浩跟着我,天都黑了也不走。我告诉他以后一定来看他。他才依依不舍地走了,一步一回头,我抑制不住自己失声哭了许久。
回城以后,太多的杂事分散了思念之情。我在博客上写了许多追忆文章,文中插上我與学生们的合影。
我想闲下来,到山里看看学生们,但一直抽不出时间。直到在大街上遇见老同事,才知道罗浩死了,死在大雨滂沱的桥下。我忍不住自责:为什么不去看一下学生们?忙是理由吗?
我那几天总失眠,一个人在公园夜行。有时,好像看见罗浩走来,那笑容多么可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