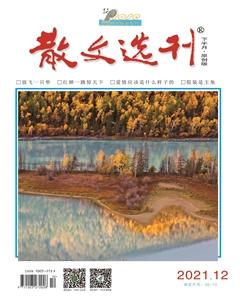草原的旗帜
北方

草原的黎明,被一声马嘶唤醒。这声长嘶,听起来清脆、稚嫩,令人振奋。
我瞬间没了睡意,顿生去寻找这匹马的冲动。
露水浓重。一出门,湿气便裹挟了全身。东山上,有耀眼的光,我想跑上山去截住光、截住红日,可仅转身工夫,它就跳到了山巅,光芒四射,像无数根笔直而柔软的针,刺向苍穹与大地。
脚踩在草地上,竟有浅浅的水渗出来,濡湿了鞋帮。被光叫醒的各色小花舒展身姿,红色、黄色、蓝色、白色……几乎囊括了所有颜色。这些类别各异的野花,在同一时段竞相绽放,它们以四季为轮回,以一种野性之美共赴一场绚丽而朴素的大地之约。
那些群石林立的山,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海退山成的巨变,战栗而出,蓦然寂静。站在巨石脚下,唯有敬畏大自然的无穷之力和不可预知性,慨叹人类的渺小。
在草原,所有的生命似乎尚在鴻蒙里,朴拙,任性。
在草原,花儿尽可烂漫,尽可妖娆;草木不修边幅地生长,尽可狂放不羁。
云也会开花,它们成群结队,一团团、一簇簇,聚在天边恣意怒放。
脚步漫无目的,随性、自由,掠过风,掠过花草,掠过无边的绿。这样的清晨,让我心无挂碍,心生欢喜。
草原的酒猛烈。昨夜,微醺的我从毡包逃出来,一抬头,天幕如洗,星月璀璨,心底那一泓清澈倏忽荡漾开来。远处,高亢的蒙古长调,恍若一叶小舟,悠悠扬扬载我回前世。前世,我是否有着深邃的眼神、紫红色的面庞、宽阔的臂膀,在马背上,于风吹草低处驰骋?于这片辽阔里,有过叛逆、思念与离愁……
歌声,在草原,有别样的动人之处,草原的宏阔赋予了歌手宏阔的歌喉和宏阔的胸襟,否则,如何唱得出那样拨人心弦的曲调?
阳光开始炽烈,风却是凉爽的。
山坡上,一匹小马与另一匹马如影随形,想来它们该是母子。
很快,母马被牧马人牵着离开了,一群游客要骑上它和其他几匹去观光。小马在一旁先是仰头长嘶,用一只前蹄捣着泥土,复又焦躁地来回踱着步。我无法辨认黎明的那一声嘶鸣是不是它,但它的憨态吸引着我,也引来了几位摄影师,对着它兴奋地拍。它竟也不避人,转动着身体配合着他们。
一个小时过去了,小马突然长嘶一声,撒欢儿向远处奔去。远处,母马被牧马人牵着在回来的路上。
莫非小马熟稔母马的蹄音,或是通过嗅觉来辨认母马的体味。母子相逢处,小马欢快跳跃,须臾不离母马左右,母马用头拱着小马,一派亲昵。亲情,以及母性,动物与人是相似的。
当轮到我们这拨游客开始骑马观光时,母马又一次被牵走了。分配给我的,恰巧是这匹母马。我骑在它的背上,任由牧马人牵着缰绳在草原上慢悠悠地溜。牧马人不肯放开缰绳任由马自由奔跑,这于我们定然是安全的,可时间久了,这些马会不会丧失驰骋草原的能力?
除了自然的力量,人类极其强悍,强悍到几乎可以征服一切。我们让狗直立行走,让猴子模仿我们,让老虎、狮子、熊表演,无论它们曾经如何凶猛,人类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去驯服它们。即便那些被豢养的宠物也只能按人的意愿生存,人认为它们冷,便在它们的皮毛上加一层衣;人怕尘土和泥垢,便给它们穿上鞋,无论它们能否适应人有时都感觉蹩脚的鞋。
很久以前,马是可以在草原上自由徜徉的,它们逐水草而迁移,骨骼强壮,肌肉坚实,草原是它们的天堂。可它们遇到了人,被强制驯化,骨子里的奔放和不羁逐渐消失,就成了失去本能意义的马。而另一群马,将它们人为聚集起来,在长鞭的驱赶下,仍可以呈现万马奔腾状,看似壮观,却难掩被动奔跑的纷乱。
我不能够确定草原与马有着怎样更密切的联系,草原因马而存在的吗?抑或马因草原而生生不息?倘若没了栖息的草原,它们将失去归宿;而没了可以驰骋的马,草原的风景将不再完美与生动,失去了某种摄人魂魄的力量。
飞奔的马,是草原的旗帜。它们身上流淌着草原的血脉,而草原是它们不离不弃的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