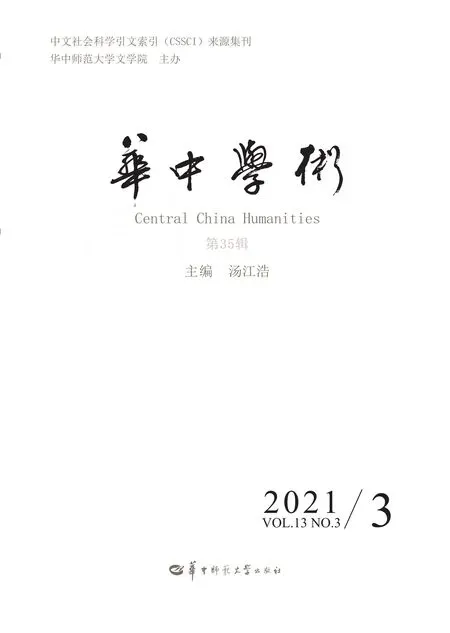生产视觉共同体:“图像治愈”的诞生、散布与使命
刘文军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广西南宁,530022)
图像是发动观念战争和心理战争的武器。W.J.T.米歇尔(W.J.T.Mitchell)将由图像引起并打击图像的“反恐战争”称之为“图像战争”[1]。“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利用第一架撞向双子塔的飞机吸引媒体,目的是让媒体将第二架飞机毁灭双子塔的场景呈现在全球观众面前,从而制造“媒体景观”[2]。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认为“‘9·11’以前,曾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恐怖奇观”,而这种媒体文化奇观是攻击敌人的方式[3];攻击被震慑所替代和执行,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认为“震慑行动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需要让那些未被直接袭击的人看到这个行动”[4]。因此,图像在其直观性和批量复制等特性的加持下成为战争的同谋与手段:大量制造并快速散播恐慌,虽然不能扼杀身体,但却造成心理创伤。
众多视觉文化和媒介文化学者以“9·11”事件为例,论述了图像和战争及恐怖之间的联姻,特别是提出“图像战争”概念的米歇尔,他在论著和演讲中多次兜售这个概念,导致诸如米尔佐夫等其他重要学者都论及此概念。诚然,“图像战争”概念恰当地描述和解释了在视觉社会中图像对个人心理的破坏力量及对整个社会的撕裂能力;但图像难道不是一枚“硬币”?“图像战争”只是这枚硬币的一面?换言之,图像可以被用来制造心理创伤,是否也可以被用来治愈受伤的心灵?是为选题的理论困惑。
2020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国。在这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中,全国民众运用传统媒体、社交媒介和直播平台等技术与媒介生产和传播了大量“看得见”的图像:逆行的医护工作者、执勤的警察和志愿者、出征的驰援部队等,除了奋战在一线的英雄,还有更多自我隔离在家的民众。众多陌生的面孔呈现在我们面前,借助视觉社会中技术的发达和网络社会中传输的方便,海量图像被生产、复制与散播。在非常态环境下,我们缘何创造和传播图像?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图像并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创造,除非我们将新冠病毒拟人化,认为这些图像是向病毒宣战;因此,这些图像的生产并非指向外部敌人,而是指向内部战友;并不是用以发动战争,而是用来消灭战争。是否诚如此言?其生成机制和运作逻辑如何?是为选题的现实思考。
基于上述理论困惑和现实思考,本文尝试提出“图像治愈”概念来阐释这类图像的诞生、散布与使命。既然真实战争和被隐喻为战争的事件中,图像能被挪用为战争的手段;而图像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谁挪用以及为何挪用;那么图像也可以被征用为治愈的手段:战争中不仅有制造伤亡的敌人/图像,也应该有治愈伤病的医护/图像。诚然,缺乏心理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很难建立民众生产和传播图像与心理治愈之间的关联,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必然也不能用审美、经济和政治等目的来搪塞;或许它是一种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谓的“自我呈现”,但其解释力有限,而且没有抓准最深层、最根本的原因。因此,作为一种阐释的尝试,本文聚焦疫情期间民众和媒体对钟南山相关图像的生产与传播,借用人类学中仪式研究和传播学中媒介仪式研究的相关思想,论述“图像治愈”的可能性、生成机制及运作逻辑。
一、“图像治愈”的诞生:治愈性图像的意义生产
“图像治愈”的诞生是反拨图像战争的起点。治愈性图像的生产是一个系统过程,其发生于有意识的创作和无意识的生成之中。诞生过程的系统性强调了治愈性图像生产的背景和过程:前者为图像的诞生确立意义,而后者为图像的诞生灌注意义。人类创造的图像是意义的载体,意义为图像赐予生命,更为治愈性图像赋予治愈和抚慰功能。
(一)战争隐喻:为治愈性图像确立意义
“图像治愈”的诞生是时事孕育的结果。洪涝干旱、战争饥荒等灾难导致的非常态环境是孕育图像治愈的土壤,同时也凸显治愈性图像的意义和价值。当然,并不否认“图像治愈”存在于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中,而是强调在社会秩序和组织结构受到威胁时,“图像治愈”现象更为明显。换言之,治愈性图像在社会中始终存在,它是“长效药”,例如逝去亲人的照片对生者的抚慰;但同时它在非常态环境中被强调,成为“救命药”,正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不断出现的钟南山图像。
钟南山相关图像的生产与传播是时事召唤和隐喻设定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按下武汉的暂停键之后,恐慌向全国蔓延。2003年SARS病毒肆虐的集体记忆被激活,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社会停摆。媒体通过大量报道激活“战争隐喻”,将民众拽入恐慌的深渊之中。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引导方式被媒体熟练使用,它们将防疫工作称为“战争”:作为疫情重灾区的武汉是“一线”,武汉市发布“封城令”,火神山和雷神山是生命的“堡垒”,医护工作者开展“疫情阻击战”,各地驰援“部队”挥别亲人、写下“请战书”、举办“誓师大会”、“出征”武汉等一系列相关概念组成概念的系统,并构成隐喻的基础。而隐喻反过来建构人类的感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用隐喻来界定现实,进而在隐喻基础上采取行动”[5]。因此,在媒体设定的“战争隐喻”框架下,具有隐喻思维的全国民众才能共同抗疫,这是制造“战争隐喻”的结果;但同时,将武汉人和病毒混淆在一起、并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同泼掉”的拒斥思维则是“战争隐喻”的副产品;而钟南山相关图像的生产和传播则是“战争隐喻”的必需品:“时势造英雄”,“英雄”概念是“战争隐喻”概念中的核心概念之一,防疫“战争”需要英雄,因此“战争隐喻”是召唤钟南山出场的号角,也是钟南山相关图像诞生的催产素。
钟南山相关图像的生产与传播同时也是“图像战争”激发的结果。疫情防控不仅是隐喻性的战争,同样也是“图像战争”。病毒不会生产作为战争工具的图像,但迎战病毒的人类却替代病毒完成武器的生产。和恐怖分子利用斩首视频和摧毁大楼等恐怖镜头制造恐慌一样,病毒通过制造和撒播恐惧来摧毁人类的意志,因此,反恐战争是一场情绪战争,防疫战争同样要消除民众的恐慌:对物资生活资料的囤积、对医疗急救资源的挤兑等现象都显示出恐慌的破坏性力量。这种破坏性的力量通过大量图像的生产和复制呈现出来:医院大厅里突然倒下的老人、挤满医院走道的就诊者、街道上飞奔的救护车、送别亲人时悲痛欲绝的脸庞、确诊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的图表……在病毒的“胁迫”下,恐慌的民众生产和传播大量会复制和散播恐慌的图像,图像和病毒相互裹挟,图像传播心理的病毒,病毒加速图像传播的效率。甚至图像本身就是病毒,其大量复制的自我生产机制和撒播恐慌的作用机制如出一辙。因此,生产和传播图像的民众无意中成为病毒的“同谋”。替代病毒发动“图像战争”,生产敌人,激发内心恐慌;同时,民众也需要“图像治愈”,塑造英雄,抚慰内心伤痛。用图像反制图像,即用治愈和安定反抗战争和恐慌,而钟南山的相关图像则成为治愈的良药。
“战争隐喻”和“图像战争”形成召唤结构,虽然它们召唤的不是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所谓的“意识形态的主体”,但却是对英雄的召唤机制,因为众多历史记忆和影像经验为民众设定了逻辑关联:有战争,必然有英雄。“战争”为钟南山相关图像的生产和传播铺垫意义。
(二)英雄神化:为治愈性图像灌注意义
“战争”敦促媒体和民众进行治愈性图像的生产,英雄及其图像的生产构成治愈性图像的内在意义,使它区别于审美性、政治性和经济性图像,而执着于治愈和抚慰功能。治愈性图像的生产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为英雄及其神化图像的生产,其内涵相互勾连、不断深化,充塞图像的内里并赋予其生命与灵性。
治愈性图像的生产由英雄及其图像的生产所孕育。在渴求英雄的背景下,媒体为民众塑造英雄成为当务之急。与再造英雄相比,召唤英雄的再次出场显然更为高效。因在2003年爆发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时期勇担大任,钟南山已然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17年后,《广州日报》官方微博于2020年1月21日下午发布主题为“84岁钟南山再战防疫最前线”的微博,并配图两张:一张是钟南山在开往武汉的高铁餐车一角闭目养神,另一张是钟南山走进武汉金银潭医院大厅。这条微博的转发量、评论量和点击量构成其微博近期关注度的首次波峰。由此可见,《广州日报》对“英雄出场”的聚焦成功引起民众“夹道欢迎”,网民用“致敬钟院士”“挂帅出征,国士无双”等众多评论替代身体,汇入欢迎英雄的虚拟“街道”和“广场”。
图像通过叙事和修辞完成英雄形象的塑造,构成治愈性图像的意义内核。《广州日报》微博发布的上述两张钟南山的图像在微信朋友圈被众多网友转发,图像的复制和传播相互交织,成为这两张图像生命力的注脚。其生命力蕴藏在叙事力量之中,因为它们完整讲述了英雄沉睡、苏醒和出场的转折故事:第一张钟南山在高铁餐车闭目养神所展现的静态,与第二张钟南山在金银潭医院疾步行走的动势形成鲜明对比。前者用“沉睡”勾连起17年前的战“疫”,后者用“出场”指向17年后的战“疫”。两者都具有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所谓“过渡礼仪”的性质[6],特别是后者展现钟南山疾步走进大厅内,通过对背景中极具过渡意义的门的形象的挪用,强调其出场的仪式感;同时他周围的其他人相互交谈,站立的位置大致构成半圆形,环绕着钟南山;更为画龙点睛的是,右侧摄影机的镜头指向钟南山:目光坚定的终南山被摄影机凝望,作为观众的网友凝望他和摄影机,通过双重凝望,其英雄身份被再次强调。
图像叙事通过两张图像共同讲述。钟南山在高铁餐车和医院大厅的两张图像被《广州日报》官方微博并置在一起,进而凸显了其叙事意义:很显然,两张图像并不是同一时刻拍摄的,但记者和编辑用同一条微博将两张不同时刻、不同场景的图像勾连起来,构成完整的叙事。蛰伏和沉睡与苏醒和出场被勾连起来,两张图像似两张电影的剧照,运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的书写中使用的蒙太奇手法,将两张背景不同的图像“剪接”在一起,进而生发出新的意义。类似于爱森斯坦(Sergei M.Eisenstein)在熟练运用蒙太奇手法的电影《战舰波将军号》中所拼接使用的三个不同姿态的石狮图像:沉睡、苏醒和咆哮,三者相互衔接,被用以表现人民的觉醒和力量。相对于多张图像发挥叙事力量而言,单个图像倾向于动用修辞手法。在英雄出场之后,钟南山另一张健身的图像也被大量转发:穿着运动背心的钟南山咬紧牙关,结实的右臂举起哑铃,面容坚毅。这张“秀肌肉”图像的引申意义大于其实质意义:曲臂举手握拳的姿势表达了“战斗”和“加油”,前者指向外部敌人病毒,后者指向内部战友民众。“运动员”和“战士”的双重形象在这张图像中巧妙融合,“运动员”的毅力和“战士”的勇气等意义被灌注到这张图像的内里,并孕育后者的生命力。
英雄及其图像的生产为英雄的神化埋下伏笔,而英雄的神化宣告治愈性图像的诞生。官方媒体通过图像塑造钟南山的英雄形象,民间个人则通过图像将其神化:一张漫画将穿白大褂的钟南山置于图像的正中央,火神山和雷神山分置左右上角,并配上“百毒不侵 诸邪莫近”的“符咒”。和图像的并置一样,在“火神山雷神山钟南山三山镇邪妖”的对联中,共同拥有的“山”字也将钟南山、火神山和雷神山串联在一起,“神”被让渡出来,成为“披”在钟南山身上并将其神化的“天衣”。另一张同样基于“接触律”而创造的钟南山的图像则巧妙地将其和钟馗融合在一起:中国画中的钟南山右手指地,着红袍配利剑,正气凛然。左侧配文:“当代钟馗造像。古今二尊皆姓钟,辟邪消灾有神功……”除了姓氏一致,钟南山和钟馗在精神层面也获得相通:忠诚勇敢、驱邪解难。同时,作为古老治愈手段的巫术和现代治疗工具的医学在钟馗和钟南山两者融合的形象中被勾连起来,英雄钟南山形象的神化反映了民众被治愈的渴望。
英雄及其神化构成治愈性图像的内在价值,赋予其不同于其他图像的灵性。英雄的出场及神仙的拯救能够抚慰人心,这是众多宗教形成的起点。和宗教图像一样,治愈功能的最大化必须依赖于图像的大量复制与散布。
二、“图像治愈”的散布:治愈性图像的仪式传播
散布是图像治愈发挥药效的关键性药引,被灌注意义的图像在散布中确认和展现自身作为治愈性图像的价值。治愈性图像的仪式传播使得具有意义的图像进入公共空间,后者被散播、复制和增殖;同时,在仪式传播的过程中,治愈性图像施行仪式功能,激发想象与情感,塑造群体与认同。
(一)张贴与传播:“图像治愈”的仪式形式
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而言,传播钟南山相关图像和张贴门神是一致的。除上文论述过的精神价值以外,钟南山和作为门神的钟馗同样经历了从凡人到英雄、从英雄到仙人的过程,虽然前者只是在漫画中被塑造成具有驱疫能力的仙人形象。同样的过程重复出现在同样作为门神的秦琼和尉迟恭的神化经历故事中[7],因此治愈性图像的意义生产为钟南山的形象赋予门神特性。
与此同时,张贴形式也是钟南山和门神之间相似性的佐证:《广州日报》官方微博对钟南山英雄形象的呈现、《人民日报》对钟南山神化形象的转发、新华社对钟南山眼睛湿润镜头的发布、微博和微信对钟南山“秀肌肉”场景的展现……媒体和个人对钟南山相关图像的刊载都具备张贴的性质。事实上,钟南山和火神山、雷神山并置的漫画形象被众多网友设置为屏幕保护,锁屏和锁门、护屏和护家的相似性强化了钟南山相关图像和门神之间的关联;如果说漫画上“诸邪莫近”的“符咒”还不足以佐证,那么钟南山和钟馗形象的融合则是这种一致性的铁证,毕竟“当代钟馗造像”的配文直陈两者的一致性。张贴就是传播,传播存在于张贴之中。门作为张贴的载体,承担了信息传播的功能。因此,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都具备门的性质:从过渡仪式的维度来看,它们是划分客观现实和拟态环境的“门楣”;从信息交往的维度来看,它们又是对外展示和言说的“门厅”。与其证明“媒体具备门的性质”,不如求证“门具有媒体的性质”。
从古至今,门都具备传播功能和媒体性质。虽然在门祭和过渡仪式等民俗学及人类学研究中,门都被认为具有区隔和划分作用,它划定了内与外、生与死、神圣与世俗等二元地理,“鬼门关”“过门槛”等说法可为佐证;也正是因为门具有区隔的原始文化意义,能够将“瘟鬼”阻挡在门外,因此才生成了“门祭”和“门神崇拜”传统。但门不仅仅是区隔的屏障,同样也是沟通的渠道。门的意象的含混性和复杂性使其具备相互冲撞的两种性质,但并不意味着“关门是区隔”“开门是沟通”,而是指向“门”自身的性质:或开或关,门都具有传播的意义。在古代政治生活中,门的意义和作用的含混性表现得尤为明显。古代皇城通过宫门将皇室和民众区隔开来,营造宫廷的威严感;与此同时,城门也完成宫廷和民众的沟通,成为政治传播的工具和载体:“奏凯于门”和“献俘于门”成为皇帝炫耀武功的方式,“午门斩首”和“张榜于门”则是政治权力让奖惩的威力弥漫开去的方式。因此,“宣政于门阙”中的门绝不是信息流通的屏障,反而是信息的放大镜和扩音器。现代生活中,门依然延续了传播属性,只需要看看“城市门户形象”和“政府门户网站”等词汇的使用就一目了然。
同样,在政治生活之外,门也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传播作用。张贴门神在抵挡门外“瘟鬼”的功能之外,也发挥着沟通左邻右舍的功能:他也贴了门神,和我一样。没有哪户人家将门神压在箱底或贴在门背后,门神始终通过张贴于门面而具有天然的敞开性和言说性。换言之,无论是古代政治生活,还是现代日常生活,它们都是群体生活和组织生活的表现形式;因此,政治传播和日常沟通都是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具体表征。而在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中,门成为重要的传播工具和联结纽带,它是竖立的广场和实在的公共领域。
总而言之,传播钟南山相关图像和张贴门神都是一种群体性仪式行为,传播和张贴自身具有仪式性,而媒体和门的统一性与传播和张贴的同一性让两者重叠在一起。媒体、门、传播和张贴共同指向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而后者是治愈性图像发挥药效的药引。从这个意义来看,门神可能是最早的治愈性图像之一,钟南山相关图像的生产与传播只是这一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是袪魅之后的再施魅。
(二)情感与想象:“图像治愈”的仪式功能
作为仪式的张贴和传播使得图像进入公共空间,传统媒体对钟南山英雄形象的传播、民间个人对钟南山神圣形象的散播,以及两者在社交媒体的交汇使得基于钟南山形象的治愈性图像快速渗透与弥漫,开辟和填充公共空间。但并非止于公共空间,治愈性图像最终直抵病灶、释放药效、抚慰人心还得有赖于仪式功能的发挥。
治愈性图像的传播是不同层次的传播仪式的交织现象。在电子复制时代,钟南山相关图像被大批量、同一化、无差别地复制。和病毒一样,图像在传播中复制,也在复制中传播。复制和传播成为图像繁衍的方式,治愈性图像尤其如此。因此,钟南山相关图像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以及人际传播等不同传播领域流动,以图像为纽带和中介,奏响不同层次的互动仪式“交响曲”。
治愈性图像的仪式传播是共同情感的确认,同时也是共同体想象的确证。在“战争隐喻”框架下,社会失序和组织涣散让原本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被抛洒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因此,被恐慌俘获的头脑必须重整社会秩序,后者的关键和前提在于重建社会关联,而“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8],因此治愈性图像的诊疗方案就是通过自身将分散的个人重新编织到社会之网中。重建关联是一系列社会心理活动的结果。治愈性图像生产阶段所灌注的意义激发民众内心的情感,而治愈性图像的仪式传播则将激发的情感再生产、再扩大和再凝缩。图像蕴含的内容及其传播的形式巧妙融合,共同发力。图像及其情感的再传播将分散的、匿名的个人从四野八荒的屏幕背后打捞起来,和点赞、转发以及评论一样,这是个体浮现的方式:他们在作为身体延伸的符号中表明身份;与此同时,这也是社会重现的过程:你、我、他共同体验了图像所附载的情感,共同的经历和体验确认集体身份。换言之,治愈性图像的仪式传播构成群体的互动仪式,被图像传播所“再发现”的个人“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与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活动”[9]。
同样的过程和机制发生在张贴门神的经验中。作为门神代表的秦琼和尉迟恭的传说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三也说到唐太宗以秦琼,尉迟恭守门而邪祟平息的故事:‘帝有疾,梦寐不宁,如有祟近寝殿,命秦琼、尉迟恭侍卫,祟不复作。帝念其劳,命图像介胄执戈,悬于宫门’”[10]。染疾的唐太宗因为宠臣秦琼和尉迟恭的守卫而痊愈,因此召集巧手丹青绘制秦琼和尉迟恭的画像,赐给众臣贴在自家门上。后来,此二公由忠臣而被神化,从朝堂之上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近代门神的主要形象。在原始思维作用下,张贴二公图像能够阻挡鬼祟,臣子向皇帝效仿、民间向朝堂看齐的连锁反应让张贴门神成为同一性行为。特别是左邻与右舍贴出同样的门神,不仅不会造成审美疲劳,反而因为一致性而形成情感纽带,构成共同体想象的基础。
因此,被“战争隐喻”所支配的个人在治愈性图像的传播中获得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所谓的“情感能量”,共同体情感驱散内心恐惧,最终在重返社会的旅途中完成创伤的治愈。当然,传播属性内涵于治愈性图像之中,构成图像治愈的关键,因为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发现个人与重整社会,而“任何心灵的共融状态无论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都会增强社会的生命力”[11]。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杜威(John Dewey)所言:“社会,不只是通过传递、交流而得以持续存在;说它存在于传递、交流之中,也不为过。‘共同的’、‘共同体’和‘交流’这些词不只是在字面上有关联。人们基于共同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而交流则是他们拥有这些共同事物的方式。”[12]更不难理解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经由杜威的思想,创立“传播的仪式观”思想,并发现传播和文化的内在一致性[13]。而传播中的图像就是杜威所说的“共同的事物”,也是凯瑞所说的“文化”的具体表征,图像在分散且独立的个体心灵间不断迁跃,像电流一样串联个体,点亮共同体意识,最终其传播价值取代和超越其展示价值。因此,在传播中联合人与人、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实践中,图像获得治愈属性,成为治愈性图像,最终完成“图像治愈”。
三、结语
“图像治愈”通过内在意义的生产和外在仪式的传播而完成其使命:制造同一、激发情感、唤醒想象、生产及维系视觉共同体,而个体在共同体的安全感中被抚慰和治愈。“图像治愈”的生成机制和运作逻辑无法被查验,毕竟在除夕夜燃放鞭炮的娱乐喧嚣中,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鞭炮声深深地卷入共同体想象中。声色犬马掩盖了钟响磬鸣,图像亦如是。因此,“图像治愈”是流淌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潜意识里的暗河,悄无声息,却完成勾连与交流。难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激发想象的共同体的群体仪式“是在沉默的秘密中,在头盖骨下的巢穴中进行的”[14]。因此,虽然我们被事物表面功能所迷惑而不愿承认其内在意义,但隐藏的维度始终存在,并行使喋喋不休的“腹语术”。
诚然,图像并不是唯一具有治愈功能的良药。正如前文所言,声音也同样如此,无论是鞭炮声还是防控警报声。虽然两者都基于共同体想象,但相对于声音所唤起的“可听见的共同体”而言,图像所描绘的“可看见的共同体”有其独特性和亲近性。在确立视觉中心主义的视觉社会中,“图像想要被吻,当然,我们也想要被回吻”[15],像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笔下处于哀悼期的瓦拉蒙加人一样,相互间的仪式性亲吻让他们满足彼此接近的需要;而且“正如马丁·路德所言:‘相较于文或字教义而言,图片和图像更容易打动他们,让他们回忆宗教的历史’”[16]。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言及的是宗教圣像,它和门神都属于宗教巫术领域,也都是治愈性图像。随着文明的马车滚滚向前,人类的原始思维却并没有被碾落成泥,图像的治愈和抚慰功能依然被保留;因此“图像治愈”在宗教巫术领域之外描绘世俗的图像,用以抵抗敌人(病毒和恐怖分子等)用图像发动的“战争”。
注释:
[1]W.J.Mitchell,CloningTerror:TheWarofImages,9/11toThePres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2] [美]W.J.T.米歇尔:《图像何求:形象的生命与爱》,陈永国、高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3]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
[4] [英]尼古拉斯·米尔佐夫:《如何观看世界》,徐达艳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97页。
[5] [美]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4页。
[6] [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90页。
[7]殷伟、程建强:《图说民间门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9~54页。
[8]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
[9] [美]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1~72页。
[10]王子今:《门祭与门神崇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17页。
[11] [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53页。
[12] [美]约翰·杜威:《杜威全集》第9卷,俞吾金、孔慧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13] [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页,第23页。
[14]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页。
[15] [美]W.J.T.米歇尔:《图像何求:形象的生命与爱》,陈永国、高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序言。
[16] [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第2版,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