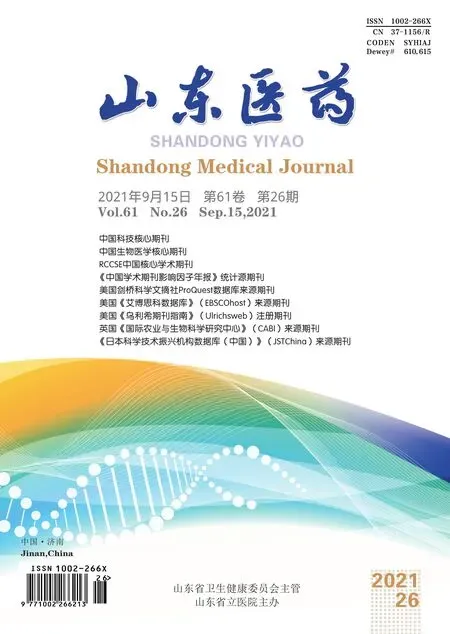左半结肠癌与右半结肠癌差异性的研究进展
杨柳,游柳平,于佳永,赵翰铮,黄跃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科,哈尔滨150081
结肠癌是一种异质性疾病,具有独特的解剖、病理生理和临床特征。结肠肿瘤位置被认为是影响结肠癌病情进展、治疗方式选择和生存预后的重要因素。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NCCN)指南近期已将结肠原发肿瘤位置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导指南中[1]。研究显示,香烟烟雾中的致癌物质如亚硝胺、杂环胺、苯和多环芳烃等,可通过直接摄入或血液循环途径到达结肠黏膜,对结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致癌作用。GRAM等[2]发现,与吸烟相关的结肠癌发病风险在总体上男女性患者是相似的;与从不吸烟的人群相比,男性吸烟者患左半结肠癌的风险增加,而女性吸烟者患右半结肠癌的风险更高;在绝经后女性中,无论是否接受绝经激素治疗,与吸烟有关的右半结肠癌患病风险均显著增加。因此推测,香烟可能通过对不同性别人群的表观遗传差异修饰促进结肠肿瘤偏侧性的发生。本文就结肠癌在解剖生理、能量代谢、组织病理学、肠道菌群构成、分子生物学的偏侧性差异进行综述,旨在为左、右半结肠癌的精准化诊疗提供新的思路。
1 左半结肠与右半结肠的解剖生理学差异
左半结肠与右半结肠在胚胎来源及解剖生理方面存在差异。右半结肠在解剖上包括盲肠、升结肠以及横结肠的近三分之二,胚胎期起源于中肠,与空肠和回肠同源;左半结肠在解剖上包括横结肠远端的三分之一、降结肠以及乙状结肠,胚胎期起源于后肠。结肠两侧不同的胚胎起源同时也表现在结肠的双重血供上。肠系膜上动脉的分支血管主要负责右半结肠的血液供应,而位于结肠脾曲及其远端的左半结肠血液供应由肠系膜下动脉负责。支配结肠的副交感神经在左半结肠与右半结肠也各不相同,迷走神经随动脉的分布支配大部分右半结肠,而支配左半结肠和直肠的神经来自骶2、骶3和骶4神经。
在生理状态下,结肠主要负责吸收水、钠离子和氯离子,同时分泌钾离子和碳酸氢盐;参与阴离子交换的主要催化酶为碳酸酐酶,其浓度在靠近回盲部的右半结肠较高,但在左半结肠浓度较低[3]。由于短链脂肪酸是结肠上皮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故结肠可以被动吸收短链脂肪酸。脾曲近端的结肠上皮细胞代谢活动主要依靠乙酸盐,而脾曲远端的结肠上皮细胞代谢活动主要依靠丁酸盐。此外,左半结肠与右半结肠的胆盐浓度也存在较大差异。由于靠近回盲部的右半结肠肠腔内胆盐浓度显著高于左半结肠,一些影响胆盐分泌的因素会选择性地增加右半结肠肿瘤的发生风险。荟萃研究显示,胆囊切除术是右半结肠癌发生的危险因素,而与左半结肠癌的发生无明显关联[4]。
2 左半结肠癌与右半结肠癌的能量代谢差异
代谢异常是结肠肿瘤细胞的一个显著特征,肿瘤细胞能通过改变代谢途径来增加其增殖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和能量。目前已知肿瘤细胞的代谢途径包括糖酵解途径、谷氨酰胺代谢途径、一碳代谢途径以及脂肪酸合成途径等[5]。CAI等[6]发现,女性右半结肠癌组织能够增加天冬酰胺的合成及包括丝氨酸在内的相关氨基酸的摄取,从而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女性右半结肠癌患者天冬酰胺合成酶的高表达与更差的生存预后相关。目前天冬酰胺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治疗靶点之一,药物天冬酰胺酶可用于降低血液循环中天冬酰胺的水平。天门冬酰胺酶能够使肿瘤细胞丧失天冬酰胺,从而导致肿瘤细胞死亡,提示天冬酰胺可能作为女性右半结肠癌的潜在治疗靶点。
肿瘤细胞优先利用有氧糖酵解分解葡萄糖,而不是通过线粒体氧化磷酸化来获取能量。MUKU⁃ND等[7]研究表明,靠近回盲部的右半结肠肿瘤比左半结肠肿瘤在能量代谢方面产生更重要的改变。葡萄糖转运蛋白1是葡萄糖转运和吸收的关键限速酶,其在右半结肠癌细胞中选择性上调,而参与脂肪酸降解和氧化磷酸化的几种线粒体代谢标志物选择性下调(包括G6PC、FABP1、CPT1A、CPT2、ACAT1、ACAA2、ACOX1、EPHX2和EHADH),这就进一步支持了由于右半结肠肿瘤的能量代谢是以葡萄糖的有氧糖酵解为主,从而使其更具有侵袭性的观点。因此,可以根据左、右半结肠肿瘤的能量代谢差异来寻求结肠癌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肝脏是生物转化(化学解毒和新陈代谢)的主要器官。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肝脏以外,特别是胃肠道的生物转化与胃肠道肿瘤存在关联。细胞色素P450超家族(CYP)、谷胱甘肽S-转移酶超家族(GST)和UDP-葡萄糖醛酸基转移酶超家族(UGT)与人体致癌物质分解的不同阶段有关[8]。MUKUND等[7]报道,CYP家族在右半结肠癌的抑制基因集中富集,特别是来自CYP2C和CYP4F亚家族(包括CYP2C8、CYP2C18、CYP4F12等)的相应酶会受到抑制。其中CYP2C亚家族的酶能够将花生四烯酸(AA)转化为活性的环氧二十碳三烯酸(EETs),而CYP4F亚家族的酶能够将AA转化为羟基EETs[9]。此外,在右半结肠癌中还出现UGT1A的肝脏异构体UGT1A3和UGT1A9的调节异常;几种与药物相关的溶质运载体(SLC25A42、SLC44A4A、SLC46A1)和抗坏血酸转运体(SLC23A1/A3)在右半结肠癌中也相应受到抑制[7]。总之,与左半结肠癌不同,来自CYP2C和UGT1A家族的蛋白在靠近回盲部的右半结肠癌中存在调节异常,特别是在肿瘤的早期阶段如T1、T2期,因此导致右半结肠癌患者对致癌物的解毒能力降低,从而相应出现了遗传毒性的肿瘤环境,产生了比左半结肠肿瘤更具侵袭性的表型。
3 左半结肠癌与右半结肠癌的组织病理学差异
右半结肠癌与左半结肠癌组织在肉眼形态上存在较大差异。右半结肠癌肿属于典型肿块型、外生型及息肉样病变,通常突出于肠腔呈隆起型生长,可导致明显的贫血症状;左半结肠癌肿通常是环绕结肠管腔的浸润型或缩窄型病变,常引起肠梗阻的发生[10]。
在组织病理学上,相较于右半结肠癌,左半结肠癌腺癌所占比例更高,右半结肠癌以黏液癌、未分化癌及印戒细胞癌更多见[11];在肿瘤细胞分化方面,左半结肠癌比右半结肠癌有更高比例的中、高分化程度[12]。此外,左半结肠癌患者以肝、肺转移更常见,而右半结肠癌患者以腹膜转移更常见[11]。
结肠癌主要沿淋巴路径扩散,淋巴扩散的解剖模式不同可能导致患者预后差异,有研究表明,右半结肠癌淋巴结转移率较左半结肠癌显著升高[13]。鉴于结肠癌患者的预后与清扫淋巴结的数量有关,因而外科学领域存在关于扩大淋巴结切除术价值的讨论。由于结肠癌淋巴扩散的分子机制和解剖途径还未完全揭秘,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理论一是最初在乳腺癌中描述的Halsted模型,癌细胞的淋巴扩散遵循的是以可预测和循序渐进的转移过程:原发肿瘤细胞首先扩散到结肠旁淋巴结(L1),然后扩散到中间(L2)和中央淋巴结(L3),最后扩散到其他器官,如肝脏[14]。这一模型给出了一种治疗思路,即肿瘤细胞若没有侵犯L1淋巴结,那它将不会侵犯L2及L3淋巴结,切除所有受侵袭的淋巴结即可达到外科学治愈。理论二是Fisher模型,该理论认为肿瘤细胞通过淋巴结扩散的方式是随机的,其远处转移与所侵袭的淋巴结位置无关联。若遵循Fisher模型,那么扩大手术切除所有局部淋巴结对患者预后影响不大[15]。KATAOKA等[16]发现,右半结肠癌侵犯L3淋巴结的比例是左半结肠癌的两倍多(8.5%vs3.7%),而L3淋巴结阳性的预后价值受结肠肿瘤位置不同影响:在多变量回归模型分析中,右半结肠癌L2、L3淋巴结侵犯对其总体生存率没有影响;而左半结肠癌出现L3淋巴结阳性患者的总体生存率明显更差;此外,左半结肠癌淋巴结跳跃转移率低于右半结肠癌。因此认为,左半结肠癌淋巴结的序贯转移是结肠癌患者预后不佳的因素之一,而右半结肠癌普遍不遵循淋巴结序贯转移规律。
4 左半结肠癌与右半结肠癌的肠道菌群构成差异
研究显示,肠道不同部位菌群构成存在差异,而肠道微生物失调可以通过包括引发慢性炎症疾病及免疫反应的诱导、对有毒代谢产物及基因毒性致癌物质的生物合成、影响宿主代谢等多种方式促进结肠癌的发生发展[17]。
大肠埃希菌来自系统发育群的B2群,含有一个名为聚酮合酶(PKS)的基因组岛,能够编码合成基因毒性物质大肠杆菌蛋白,在真核细胞中可导致DNA损伤、细胞周期阻滞、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的不稳定。LYADORAI等[18]报道,与健康人相比,大肠癌患者肠黏膜组织中可分离出更多的PKS+大肠杆菌;在8例分离出PKS+大肠杆菌的结肠癌患者中,6例原发肿瘤位于远端结肠(左半结肠)。这可能是由于结肠不同位置的菌群构成及不同部位结肠黏膜的生物学特征存在差异所致,这种差异同时可能会影响结肠上皮细胞对某些致癌物质的易感性。
梭杆菌是一类厌氧、无芽孢形成的革兰阴性杆菌,具有一个黏液帽,能过度表达如MUC6、MUC5aC、MUC17和MUC2等黏蛋白基因,这种特性有助于结肠癌细胞的转移[19]。此外,梭杆菌已被证实能够表达高水平的毒力因子,例如FadA、Fap2和MORN2蛋白等,在促进大肠癌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20]。ITO等[21]比较了梭杆菌在结肠癌前病变和结肠癌中的分布情况,发现从癌前病变状态到肿瘤状态,从乙状结肠到盲肠,梭杆菌含量逐渐升高。但梭杆菌在左半结肠与右半结肠中含量的差异是否会影响结肠肿瘤的偏侧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SAFFARIAN等[22]报道,左半结肠和右半结肠的肠隐窝及黏膜相关的菌群组成存在显著差异:梭杆菌和脆弱拟杆菌在右半结肠肿瘤中更丰富,而微小微单胞菌在左半结肠肿瘤中更常见。进一步研究发现,右半结肠肿瘤标本肠隐窝中的牙周梭杆菌含量明显高于肿瘤临近区域正常结肠的肠隐窝,但左半结肠肿瘤标本中并未出现上述差异。未来对这些差异菌落和结肠隐窝上皮(特别是其中存在的肠道干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将有助于探明两者之间潜在的致癌机制。
DEJEA等[23]研究发现,在结肠腺瘤和结肠肿瘤上存在一层生物膜,该生物膜由一系列相互黏附的肠道细菌和由细菌产生的细胞外基质组成。生物膜可能会创造一种局部致癌环境,这种环境对结肠肿瘤的促进作用与肠道特定致癌菌群同样重要。生物膜所覆盖的肠上皮细胞主要表现为E钙黏蛋白减少,从而导致肠黏膜通透性增加;IL-6及STAT-3活化增加,从而导致肠上皮细胞异常增殖。研究发现,生物膜主要存在于靠近回盲部的右半结肠腺瘤和右半结肠癌的肠腔中,这提示生物膜与右半结肠肿瘤之间具有潜在的联系。
5 左半结肠癌与右半结肠癌的分子生物学差异
左半结肠癌与右半结肠癌在遗传学、表观遗传学、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等方面也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征。虽然例如APC基因的突变及WNT信号通路的异常表达等一些改变在大多数结肠癌中普遍存在,但至少有1 300个基因已经被证实在左半结肠癌和右半结肠癌中存在差异性表达。左半结肠肿瘤常富含KRAS基因突变,HGFR/HER2的扩增,以及双调蛋白、上皮调节蛋白的高度表达;相反,右半结肠肿瘤常存在BRAF、PI3KCA以及TGFBR2基因的突变[24]。此外,在右半结肠癌中,热休克蛋白HSP70编码基因表达上调,而热休克蛋白HSP105编码基因表达下调。由于这些蛋白参与机体的免疫反应,HSP70基因表达上调已被证实可促进细胞增殖和肿瘤生长,并与结肠癌较差的预后有关;而HSP105能增强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应答。SUN等[25]研究表明,上述热休克蛋白的调节紊乱可能是右半结肠癌比左半结肠癌更具侵袭性、预后更差的原因之一。HOXB13是一种已知的致癌基因,目前研究已证实HOXB13基因在左半结肠癌中处于抑制状态,而在右半结肠癌中处于上调状态[26]。
目前有关左半结肠癌与右半结肠癌的DNA甲基化差异已引起了医学界重视,其中CpG岛甲基化表型(CIMP)在右半结肠癌中更普遍。此外,共识分子亚型(CMS)与结肠癌的偏侧性紧密相关。CMS1(高免疫活性)和CMS3(代谢性)类型的肿瘤在右半结肠癌中占比较高,而CMS2(典型性)和CMS4(间叶组织性)类型的肿瘤在左半结肠癌中占比较高[27]。
转钴胺素蛋白1(TCN1)是一种维生素B12(钴胺素)结合蛋白,能够将钴胺素从胃运输到肠道。TCN1在维持细胞增殖、修复与新陈代谢等功能上发挥重要作用。新近研究发现,TCN1在肿瘤组织的高表达与肿瘤的侵袭性和不良预后有关。LIU等[28]通过高通量测序结果证实,TCN1基因是结肠癌中表达水平最高的5个基因片段之一;进一步比较TCN1基因在右半和左半结肠癌中的表达,发现右半结肠癌中TCN1表达水平较左半结肠癌明显升高,患者生存时间缩短。这表明TCN1表达水平与结肠癌偏侧性及生存预后存在关联。
综上所述,左半结肠癌与右半结肠癌在解剖生理、能量代谢、组织病理学、肠道菌群构成、分子生物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鉴于目前结肠肿瘤所在位置影响着临床的一线及二线治疗方案,未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揭示右半和左半结肠癌是如何对细胞毒药物、靶向药物以及免疫治疗药物(如PD-1抗体等)的疗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不断寻找左半结肠癌与右半结肠癌各自特征性分子标志物,来制造新的有效靶向药物以及作为临床预后的生物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