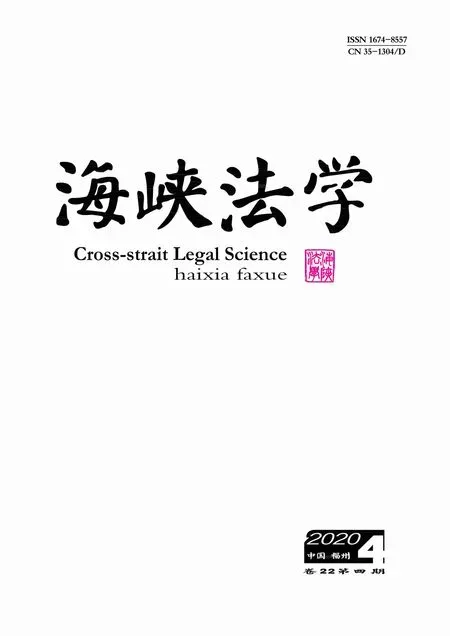短视频的著作权法保护:依据、定位及救济
齐立文 ,宋晓亭
近两年来,短视频凭借其“短、平、快”的特色成为全民新宠。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到8.50亿人次。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20-04/27/c_1589535470378587.htm,下载日期:2020年6月12日。大流量催生了新行业,而新行业则带来了新问题。在著作权法领域,每个新兴行业或者商业模式发展初期都面临着其客体能否被著作权法保护,以及侵权发生后如何救济的问题。短视频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使公众在碎片化时间完成碎片化表达,正是因为其制作简易、传播速度快、交互性强,才使得大家对热门内容转发分享甚至效仿制作,由此便产生了短视频的版权侵权问题。针对侵权现象,国家版权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剑网2018”专项整治行动,其中就关涉短视频领域的著作权问题。2019年1月9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对短视频进行规范。由此,短视频的著作权问题成为知识产权学界讨论的热点。虽是热点,短视频著作权问题并未掀起著作权法的改革浪潮,也未对现有著作权法产生冲击。仔细分析与短视频有关的纠纷内容,可以发现问题的根源并非是著作权法制度层面的缺漏,而是因短视频自身特色导致的司法保护层面存在分歧。在厘清短视频领域相关侵权纠纷后,可以通过现有著作权法的基本理论对其规范,不必掺杂新的规则更不必改变现有制度。
一、短视频著作权法保护的依据
(一)短视频著作权法保护的现有研究状况
在CNKI平台中输入主题“短视频”并含关键词“著作权法”后,检索到截至2019年11月份,平台发文量共158篇,在将全部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后发现短视频的著作权问题自2010年就开始出现,至2016年呈现大幅增长趋势。而这158篇文献在“短视频”这一总主题下,涉及著作权法、网络平台、侵权及APP等主题,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涉及短视频的著作权问题时,所发表文献的主题围绕“著作权”“独创性”“合理使用”等著作权法主题展开。由此可见,知识产权法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始终聚集于著作权法范畴,并且在近几年呈现逐年增强的研究趋势。
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作品经过作者的创作行为,成为其某种情感或思想的外在表达。大多数的作品类型是大众所熟知的,比如摄影作品、文字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等,但近几年来出现了很多新的作品类型,比如音乐喷泉、有声读物、游戏直播以及短视频等。新事物总会带来新问题,又兼之立法总会不可避免的落后于技术发展,因此初期的争议不可避免。以音乐喷泉为例,在最初发生侵权纠纷时,备受争议之处在于其喷射效果能否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若是给予音乐喷泉以著作权法上的保护,那么应当将其归入哪一种作品类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音乐喷泉的保护对象是在特定音乐背景下形成的喷射表演效果,因此应当给予其著作权法的保护,即便《著作权法》中不存在“音乐喷泉作品”这一类型,但由于该作品本身具备独创性而应受保护,法院最终认定被告著作权侵权成立。无独有偶,对于短视频的著作权法保护问题在发生一系列侵权纠纷后,学界对此也展开了激烈的探讨。
(二)著作权法设立初衷:保护独创性表达
针对短视频的著作权问题,有观点主张其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原因在于著作权法设立的初衷是激励更多“优秀”的作品产生,而当下大多数的短视频由于其短时、易作,从而难免质量良莠不齐,并不能称得上“优秀”,对短视频作品著作权的认定其实与著作权法的设立初衷相背离。有学者将短视频分为可构成作品的短视频和不构成作品的短视频。①丛立先:《论短视频作品的权属与利用》,载《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4期,第9页。此种观点大多是因为短视频的镜头切换较少、缺乏人工主观因素从而显失独创性,不符合著作权的客体要件。
笔者认为,短视频是作者情感的外在表达,具备独创性,应当为著作权法所保护。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大部分短视频不论其场景切换的多少以及主观因素的有无,都是短视频制作者的独创性表达,是其思想的外在体现。不能因为短视频制作的时间较短、内容较为单一而否定其作品的属性,究竟是否需要著作权法予以保护应当交由市场来判定,而非仅仅考量以上因素就对其不予保护。从现有的市场行情来看,短视频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司法实践中短视频侵权纠纷的泛滥恰恰说明了其市场价值的巨大,因此给予其著作权法的保护十分必要。在承认给予其著作权法保护后,可以参照现有的立法规则对其著作权归属做出梳理。实践中,短视频按照内容产生方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用户生成内容,即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第二种是专业生成内容,即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第三种则是专业性用户生成内容,即PUGC(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Content)。在UGC方式下,短视频一般为普通用户所创作,若其未与第三方达成著作权转让的约定,则该短视频的著作权归属方大多是该用户;在PGC方式下,大部分短视频具备较高的专业性,一般由专门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委托、联合某自然人甚至某专业性团队创作完成,其著作权一般归属于专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而在PUGC方式下,短视频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则需结合以上两种方式分不同情况讨论,如果该专业性用户与第三方达成著作权转让的约定则按约定进行转让,若没有与第三方形成著作权归属的约定,则权利归短视频的创作者即该专业性用户所有;如果该专业性用户为了完成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任务抑或是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主持、体现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志、并由该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责任,则该短视频则应归属于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有。
二、短视频在著作权法中的定位
(一)理论界的认定
将短视频划归“作品”还是“制品”,争议的焦点在于短视频独创性的高低。著作权法中的独创性是指表达的独创性,而非作者思想或者感情的独创性。对于作品的独创性认定,是否真的像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所言,只有独创性的高低,而不论独创性的有无?我们知道,德国法在对作品进行独创性判断时要求作品达到了一定的创作水准,产生某种特别的、具备想象力的东西,在自己作品类型领域中带来比人们所期待的普通的智力劳动更多的成果。①[德]M·雷炳德著:《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而我国《著作权法》中并未对独创性给出明确的界定标准。从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的规定来看,作品是指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够以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因此,短视频是否具备独创性成为判断其作品适格性的核心因素。而独创性的判断又分为独创性的有无及独创性的高低,前者是衡量作者“创作物”的性质能否满足作品要件;后者则是在具备独创性的前提下衡量其创造性的高低,下文对此分述之。
1. 独创性的有无
在对短视频进行独创性的认定时,需要考虑独创性要求中的“独”和“创”两个方面。首先,“独”是指作品的完成依赖于创作主体的“独立行为”,这是从主体的独立性出发以保证作品的形成是独立的;其次,“创”则是指作品在时空上要求是“首创”的,这是从作品的时空性出发以保证作品的创造性。衡量一部作品独创性的有无,就是判定其是否满足上述两方面的要素。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是作者独立完成,一般不会引发太多争议,但对于作品创造性的判定就比较复杂,需要借助著作权法中的“思想——表达二分法”原理。众所周知,著作权法只保护具备创造性的表达,而不保护具备创造性的思想。也就是说,需要根据作品与既有的表达在符号组合上的差异度,确定独创性的有无。①孙山:《短视频的独创性与著作权法保护的路径》,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4期,第46页。新产生的作品与既有作品在符号表达方面的差异,标志着新作品创造性的产生,著作权法会给予其应有的保护;然而,当一部作品由某个人或者两个及以上的独立个体单独完成,但鉴于作品表达中符号选择的有限性,著作权法会否定其创造性,从而无法给予其著作权法的保护。在这一点上,考虑到短视频表达的多样性,其著作权法保护显然不会遇到此类问题。笔者认为,大部分短视频的创作并非局限于特定思想的表达,其表现形式多样,不囿于固有的形式,是创作者利用不同形式来展现自己思想的表达方式。在独创性的有无方面,短视频具备作品的创造性,在作者独立创作的基础上,应当给予短视频以著作权法的保护。
2. 独创性的高低
在论述了短视频独创性的有无之后,应当分析其独创性的高低。作品独创性高低的认定标准,会影响一国著作权法的整体制度构架。而谈及独创性的高低,必须提到版权体系与作者权体系的分野。以英国法和美国法为代表的版权体系主张最低的创造性标准,认为作品作为智力劳动成果与体力劳动成果一样具备财产权属性,其注重作品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认为只要某作品是独立创作且具备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就可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也就是说,只要一部作品能够带来些许经济价值,哪怕其只有很低的独创性,也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与版权体系相反,以法国法和德国法为代表的作者权体系则主张较高的创造性标准,认为作品是作者人格属性的外现,注重作品上负载的精神价值,在作品的认定中加入“作者人格”等精神要素,主张作品的独创性要达到“一定的创作高度”才能受著作权法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兼采版权体系与作者权体系,在规定了著作财产权的同时,也规定了著作人身权。但在我国著作权法律规范体系中,并未详细规定作品独创性高低的认定标准,只是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2条中对作品的定义做了如下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短视频领域,为了保障市场的繁荣,维护权利人的创造积极性,应当采取较低的独创性标准。也就是说,在短视频的独创性认定方面,只要短视频符合独创性最低标准即可承认其具备独创性,从而给予其著作权法保护。
(二)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在司法实务界,大部分观点主张某些具备独创性的短视频可以认定为作品,而那些没有过多的镜头切换,仅仅是简单事实的客观记录类视频不能够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可以将其定义为录音录像制品。持此观点者认为,对于同属视听类表达的短视频和电影作品,在对其定性时要根据各自的独创性高低来断定其是作品还是制品:独创性高的可以将其认定为作品,独创性低的则可以将其划归到录音录像制品来保护。比如在“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对电影作品独创性高度的要求受著作权法的逻辑结构影响。在存在与电影作品相对应的录像制品这一邻接权客体,而独创性有无并非我国著作权法中著作权客体与邻接权客体区分标准的情况下,电影作品与录像制品的区别显然应为独创性程度的高低,而非有无。”②陈锦川、芮松艳、周丽婷、周文君等:《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176b7def-5828-4b1e-8901-a8c900108061&KeyWord=2015,京知民终字第1818号,下载日期:2019年6月21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把体育赛事的直播同电影作品做了对比后,认为体育赛事的直播无法达到电影作品的独创性高度,不能给予其“作品”层面的保护。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短视频的独创性判断需要根据个案来衡量,在短视频不构成作品的情况下,可以将其认定为制品。③张璇:《议涉短视频知识产权民事侵权纠纷的若干法律问题》,载《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4期,第17页。对于那些仅仅是对他人讲话的录制,没有加入其他创作性元素的短视频,可以将其认定为录像制品。同理,那些对生活场景的录制以及对日常所见所闻的随手拍摄,由于未体现拍摄者的取舍或者安排,通常情况下很难认定其构成作品。对此,笔者认为,对短视频根据创造性的高低划分成作品与制品的观点不予认可。事实上的创作都是自然人主观生成的内容,思想或者情感的高低无法评判,也不好界定。另外,那些被认为“不属于作品的短视频”一经创作者发出,其侵权可能性以及被复制、转载的可能性相较于那些内容独特、十分具备独创性的短视频而言是很低的,这也是只有少部分的网络短视频红极一时的原因。但凡创作,都或多或少倾注了创作者的主观任意性。因此,对于短视频而言,应当给予其稍微宽松的认定标准。对此,司法判例中也是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认定规则,例如在“快手公司诉华多公司”一案中,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在短视频已渐成规模的当下,法律规范应当对市场及其中的商业逻辑有所回应,尤其不应为‘作品’设限,人为提高作品构成要件的门槛”。①“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案”,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49079号民事判决书。由此可见,司法判决中对作品的独创性认定遵循了较低的标准,这就为承认、尊重和保护大多数人的著作权提供了保障。当前网络环境下的短视频大部分都是较为具体的表达,且具备可复制性,在遵循较低独创性标准的前提下,大都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应当给予短视频以著作权法保护。
三、短视频侵权的救济路径
短视频由于制作门槛较低,传播途径较广,从而使其在现实中被侵权的概率加大。从目前已发生的司法案例来看,常见的侵权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以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年审理的“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诉百度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一案为例,两被告未经原告允许,擅自使用原告短视频,从而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②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诉百度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一案,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0491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又如,以“搜狐视频诉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一案为例,被告以短视频方式将当时热播的影视剧、综艺节目及体育赛事等内容切割成部分片段进行传播,从而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③“搜狐视频诉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案”,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5民初331号民事判决书。在类似案例中,涉案短视频的价值存续因素值得关注。侵权行为发生后,法院在考虑损害赔偿的计算方面,应当注意到短视频的短时性而带来的“价值时效性”。短视频同普通时长的视频相比,其时间短暂、内容单薄的特性使得其存续价值以及存续时间也相应缩短,市场对其接纳迅速遗忘也迅速,这与当下盛行的网红现象如出一辙。因此,其市场存续价值就会相应的缩短,而市场存续价值的缩短势必会表现在侵权赔偿的减少,这一点在法院侵权损害赔偿的判决中值得考虑。另外,常见的侵权行为还有利用短视频的形式,未经允许将他人的音乐作品或者文字作品进行翻唱、演绎。除此之外,短视频中标明的水印问题也需要作出说明。在观看过程中我们会注意到有些视频会通过标注上浮水印来标明视频的制作者或者出处,为的是该短视频在后续转发或者宣传时能够表明作品的原始来源。在“抖音诉火拍小视频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中,司法实践的观点是该上浮水印并不属于短视频制作者为防止他人侵权所采取的技术措施,而是单纯在自己的作品中标明创作者来源或身份的象征,如果没有相反证据,可据此判断出该水印上的用户名即是短视频的作者;平台水印表明了是该视频发布平台的信息,根据其与用户签订的协议,平台享有相应传播者的权利,如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是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④刘佳:《网络短视频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初探》,载《出版广角》2019年第3期,第73页。从短视频侵权纠纷的根源来看,创作者文化水平的差异导致短视频内容的良莠不齐。面对他人的侵权,创作者的防范意识较弱,不认为其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从而纵容了侵权作品的传播。并且,短视频侵权纠纷发生后,对相关侵权者分散追究责任使得权利人维权难度变大,侵权救济成本增加。由此可见,解决短视频著作权问题的主要路径不是事后的司法救济,而是事先的侵权防范。①李琛:《短视频产业著作权问题的制度回应》,载《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4期,第8页。面对短视频的侵权问题,一方面需要提高短视频用户的法律防范意识;另一方面,考虑到短视频传播平台的功能以及分散追究侵权者的难度,可以在合理范围内认定短视频传播平台的过错责任。具体而言,短视频传播平台应当围绕以下三方面履行相应的义务。
(一)短视频上传前的提醒义务
在大部分的短视频用户看来,积极传播某短视频既可以表达自己对视频内容的喜爱,也可以体现对该短视频上传者或者制作者的认可。此类群体主观上并无侵权恶意,可以通过合理的教育或引导预防侵权。对此,传播平台可以将短视频领域常见的侵权行为类型化并列明相应的法律后果,在用户于平台注册时以及每次传播视频时对其加以提醒,引导其自查是否已经构成侵权。这样一来,侵权行为会在低成本范围内大幅减少,传播平台的后续审查任务也会相应的减轻。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侵权纠纷后可以将平台是否履行必要的提醒义务作为考量因素。
(二)技术层面的法定义务
现实中,大部分文化产业都会设置相应岗位或配备相关人员审查内容的合法性,比如小说行业通常会设置“内容审核组”来检查文字内容是否涉黄涉暴,短视频领域不妨借鉴此种模式,在行业内推行版权检测技术。众所周知,短视频传播迅速因而侵权风险很大,而大风险会带来大收益,履行相应的技术审查义务是传播者理应承担的商业成本。由此,在短视频领域,有必要敦促国家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在互联网行业设置相应的技术审核标准,进一步推广近几年面世的“短视频版权检测技术”,这样视频传播平台将用户上传的短视频与先前的视频库进行对比后可以判定短视频侵权与否,从而有效减少短视频侵权纠纷。
(三)过错责任下的审查义务
大多数情况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面临侵权控诉时,只需按照避风港规则履行“通知——删除”义务,即在接到控诉者的侵权通知时,视频传播平台将涉案短视频及时删除,从而免除自己的义务,否则将会与视频上传者承担连带责任。然而传播平台在特殊情况下不能因此就摆脱“红旗规则”②红旗规则:是指当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事实像红旗一样明显时,即便权利人没有发出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即本文所述的视频平台)在不及时采取删除、切断链接等合理措施的情况下应当与侵权者一同承担侵权责任。的束缚。尽管视频库中存在海量视频给审查带来难度,但现实中的短视频侵权案例大多是对热门影视剧的剪切,其制作者都会以影视剧的剧名作为标题。此种情形下,侵权行为十分明显,应当认定短视频传播平台对此具备审查能力,侵权发生后应当对其适用“红旗规则”。
三、结语
短视频虽然时长较短,但相对于长视频来说,同样是作者思想和情感的独特表达,肯定该短视频的作品地位即是对其创作行为的认可,对于繁荣文化市场具有积极意义。从现有的著作权法理念出发,一件作品的形成不会计较时间的长短,而艺术创作也不会在意独创性的高低。从创作高低的主观角度对短视频的作品适格性作出界定并不可取,司法裁判中的作品认定标准也应当予以放开。短视频是技术发展浪潮中的新兴行业,对短视频的定义并不能因其“新”就断然质疑现有的《著作权法》,应当回归著作权立法的初衷和原理,从现有著作权法中寻求原则性规定,在既有立法的基础上完成对短视频的著作权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