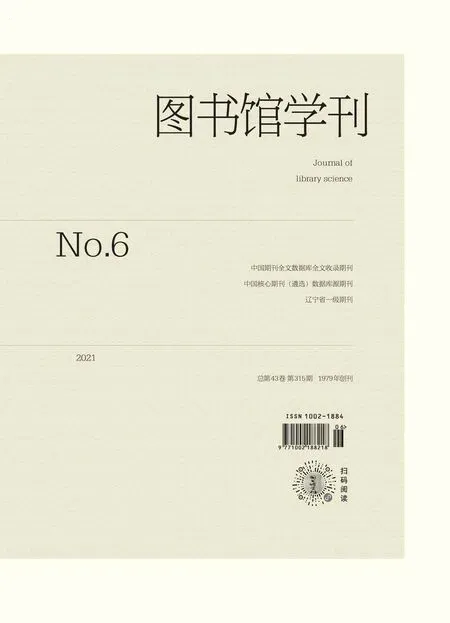康骈《剧谈录》的版本和性质及其文献价值
韩 婷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 合肥230039)
康骈,又作康軿,字驾言,池州(今安徽贵池)人。咸通中曾应进士试,乾符五年(878)登进士第,次年举博学宏词[1]。历官崇文馆校书郎[2]。僖宗广明之乱后,退居乡里,后入宣州田頵幕府,荐授中书舍人。“頵善为治,资宽厚,通利商贾,民爱之。善遇士,若杨夔、康軿、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为上客”[3]。《剧谈录》是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康骈著作,其中包含大量的历史事实、社会民情、名宦轶事、典故纪闻、灾异怪谈等,这些资料不仅可以佐史、补史之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对文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也颇具价值。
1 《剧谈录》的版本与属性
《剧谈录》在唐以后诸家书目中多有著录,其版本有两卷与三卷之异。《旧唐书·经籍志》未见收录。《新唐书·艺文志》载:“康軿《剧谈录》三卷。字驾言,乾符进士第”[3],并将其列入小说家类。《郡斋读书志》言:“《剧谈录》三卷。右唐康軿字驾言撰。乾符中登第。书载唐世故事”,亦纳入小说类[4]。郑樵在《通志》小说类载:“《剧谈录》三卷,康軿撰”[5]。《直斋书录解题》未收录。《文献通考》小说家类有言:“《剧谈录》三卷。晁氏曰‘康骈,字驾言撰。乾符中登进士第。书咸载唐世故事’”[6]。《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收录:“康骈《剧谈录》二卷”[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载有“《剧谈录》二卷,唐康骈撰……凡四十条。今以《太平广记》勘之,一一相合。非当时全部收入,即后人从《广记》抄合也”[8]。由上收录情况可见,《剧谈录》版本存疑,有两卷与三卷之争。据《剧谈录》作者自序,称为其书分为二编,而宋代所修史志目录与私修目录等皆收录《剧谈录》为三卷本,或因传抄过程中误将“二卷”作“三卷”,后人传抄因袭,疑有三卷。但多家著录多有考证,不至错误如此。或曰康骈此书本为两卷,并在其后附录若干条目,实际上便成为三卷,故此史志目录视为三卷。至元代修《宋史》时又言两卷本,当是此书几经辗转,有亡佚,后人从类书《太平广记》中辑佚而成。据作者自序两编之说,辑佚之后编为两卷已合著者序中所言,其后清修四库本因袭其说收录为两卷。
目前国内一些图书馆藏书存有明清刻本或抄本《剧谈录》古籍。其版本众多,亦不乏版式精美,雕刻优良的善本。较为精良的为明代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国家图书馆、慕湘藏书馆、福建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等皆收藏有以其为底版的1册、2册或与他书合刻1册等多种版本。另有无从考订具体刻印年限的明刻本8册,明抄本1册藏于国家图书馆。清代版本众多,品相各异,主要有新疆大学图书馆所藏无从考证具体年限的抄本1册,吉林省图书馆藏清嘉庆照旷阁刻本2册,收藏较广的清光绪四年(1878)葛氏啸园刻本(扬州市邗江区图书馆藏有2册、天津图书馆藏3册、保定图书馆藏2册、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1册),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氏唐石簃刻贵池先哲遗书本1册,以及清光绪三十年(1904)刻贵池先哲遗书本1册(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金陵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皆有收藏)。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旧小说》收有《剧谈录》,该本《剧谈录》所录条目较少,每个条目题以人物之名,共16条,多与其他诸版本有异;《丛书集成初编》以影印津逮秘书本的形式收录《剧谈录》两卷本;中华数字古籍库将《剧谈录》古籍进行了数字化,共涉版本8种,版式各异,内容上多为两卷本。
《剧谈录》古籍版本的收藏、辑录、保存、影印和数字化,以多元方式延长和拓展了古籍的寿命,其功用和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为古籍文献的研究提供了资源支持,为出版、印刻等相关研究提供了实物支撑,其收录内容亦为史学、语言学、文学研究提供了文献证据。今本有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刘世珩刻《贵池唐人集》增校本断句排印,出版《剧谈录》两卷附逸文4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收录校点本《剧谈录》,上卷收录20条,下卷22条,附逸文4条,合计46条。
在该书性质所属类别上,目录书目较为统一,皆归入小说家类。一方面是由于该书内容多杂以神仙鬼怪荒诞不经之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该书涉及到唐代名人,如元稹与李贺的故事被考证为不实,弱化了其史料价值的真实可靠性。颇为重要的是,康骈本人在自序中亦自目为小说家言,更是使其性质归类成为定论。即便如此,史家对其功用价值仍做出了肯定,诸家目录多见收入即是明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稗官所述,半出传闻。真伪互陈,其风自古。未可全以为据,亦未可全以为诬,在读者考证其得失耳。不以是废此一家也”[8]。此又是《剧谈录》实的部分。
《剧谈录》书名著录无异,著者同为一人即康骈,亦写作康軿,“骈”与“軿”两字书写不同,已有学者考证,或言传抄有误所致,然未得统一。现存明清古籍刻本与抄本,作者名字多用“骈”,当可视为一个旁证。史书言“軿”者,因时隔久远无从考证缘由,而两字又是通假字,互用亦无不可,相互借用而非误抄亦存可能。据《说文解字》:“骈,驾二马也,从马,并声”[9],“軿,辎车也,从车,并声”[9]。从古人名与字同义来看,“字驾言”,“驾”亦从马,“骈”当是作者本名正字。故,从康骈一说则更为恰当。
康骈生活于唐后期,其经历见闻较为丰富,康骈在自序中言其未中第有功名之时,退黜羁寓,游历于秦洛之间,“新见异闻,常思纪述。或得史官残事,聚于竹素之间,进趋不遑,未暇编缀”[2]。后因唐末兵祸起义不断,关中政治动乱、社会不安定,于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过程中书稿亡逸颇多。家乡亦离乱动荡,自己闭关云林,身边更是缺乏坟典,想要“叙他日之游谈,迹先王之轨范,不可得矣。”想来自己于国无功,又怎能吝惜笔墨?鉴于“时经丧乱,代隔中兴,人事变更,邈同千载,寂寥埋没,知者渐稀;是以耘耨之余,粗成前志。”最后,康骈笔锋一转又言“所记亦多遗漏,非详悉者不复叙焉。分为二编,目之曰《剧谈录》。文义既拙,复无雕丽之词,亦观小说家流,聊以传诸好事者。”此句既有康骈对于因种种原因书作内容多有遗漏的真实表述,能力有限不能达到史家、名家的水平,也有康骈的自谦之词。也正是康骈自己将《剧谈录》目为小说,成为后世目录著作多将其收录入小说家的重要原因。然,康骈作为晚唐时期的文化名人,其游历经历,涉入官场、文坛,更是深入民间,隐居池州黄老山等都为他广搜见闻提供了可能。无论从康骈个人的主观著述目的和缘由看,还是从其著述内容为后世流传的既有事实看,康骈的《剧谈录》均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其存史与史论并重的历史记述观,更是值得关注与探讨。
2 《剧谈录》为政治和人物研究提供史料
《剧谈录》其内容在文字量上并不多,却广泛涉及了唐末多个领域,最为突出者为名宦轶事、典故纪闻、灾异怪谈之类。《剧谈录》现存本收录条目最多、校勘精良者为两卷附逸文4条本,其内容为后世展示了唐末社会的多角度图景。
对唐末政治和人物的关注是此书的突出侧重点,为研究唐末政治和人物相关课题提供了多样化的史料。
首先,在政治史方面,“宣宗夜召翰林学士”记唐宣宗夜召令狐绹论事问政,令狐绹对答颇佳,得宣宗赏识,不久便拜其为相。唐宣宗是晚唐中兴之主,性格较为强势,令狐绹是太尉令狐楚之子。据《旧唐书》所言令狐绹性儒缓[10],这也是其能以宰相之身执政长达十年的原因之一。《新唐书》与《资治通鉴》除进一步表明宣宗重用令狐绹得益于感念其父令狐楚对宪宗忠诚,也收录了宣宗夜召翰林学士令狐楚之事。《新唐书》载:“大中初,宣宗谓宰相白敏中曰:‘宪宗葬,道遇风雨,六宫百官皆避,独见颀而髯者奉梓宫不去,果谁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对曰:‘绪少风痹,不胜用。綯今守湖州。’因曰:‘其为人,宰相器也。’即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入翰林为学士。它夜,召与论人间疾苦,帝出《金镜》书曰:‘太宗所著也,卿为我举其要。’綯擿语曰:‘至治未尝任不肖,至乱未尝任贤。任贤,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祸。’帝曰:‘善,朕读此尝三复乃已’”[3]。《资治通鉴》记载类同[11],宣宗与白敏中谈及令狐楚,问其子弟,白敏中言令狐楚次子令狐绹有才器,宣宗感念令狐楚对宪宗的忠诚,擢升其子令狐绹,“上即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綯入谢,上问以元和故事,綯条对甚悉,上悦,遂有大用之意”[11]。可见欧阳修与司马光等后世史家对令狐绹得以仕途有进乃至宰辅十年与其父及夜召事件密不可分是采取认可态度的。康骈在此条中对宣宗中兴之势多有描述,虽不乏溢美之词,同时也显示了宣宗中兴唐室的愿望和尝试。宣宗夜召值守学士令狐绹,讨论治国理政之事,提及文宗所著理国理身之书《金镜》,令狐绹除了对此书一番赞颂,说自己“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之外,更是提及其父亦盛赞其书乃万古格言,对宣宗观书夙夜,择贤举善,庶绩咸熙,功冠百王做了一番肯定。由此,史书所言令狐绹性格谨慎,多依其父美名可见一二;康骈的史料选取与记录也为后世保留了史料,成为佐史的证据之一。
“刘相国宅”条,康骈交代了通义坊刘相国宅的渊源,本是文宗朝朔方节度使李进贤旧宅,描述李进贤居住时极尽奢华之事,“豪奢奉身,雅好宾客。”后刘瞻相国居住此处,康骈以刘瞻相国之“人以甲第为献,竟无所受”“清风俭德”对比前者之奢华无度,最后议论道:“君子曰:‘仁义之感物也大哉!刘公知帝道钦明,欲贤人尽举,四海之内,翕然向风。虽谪居累年,再升鼎饪,奸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誉一时,流芳千载,岂不伟欤!其有冒官爵,叨货贿,怙宠专权,身存名灭者,一何谬哉!’”[2]康骈借助他人之口,评论刘相国之忠君仁义,批判卖官鬻爵、贿货纵横、脏污狼藉、侍宠专权之官是多么谬误无知的行为!
“凤翔府举兵讨贼”条对凤翔府举兵讨贼之事的来龙去脉及细节记录颇为细致。夹叙夹议,交代了唐末王、黄之乱下各地或投降归附或闭关自保的状况,致使巢寇攻陷宫阙。凤翔郑相国有勤王之念,在艰难中举兵讨贼。康骈借用先秦的《崧高》诗所言“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2],赞扬郑相国起兵勤王、力挽狂澜的行为。此条裨益于对唐末王仙芝、黄巢民变的了解与研究。
“曲江”条展现了曲江胜景之美,中和、上巳节都人游玩,热闹非凡。然“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2]。裴休相国廉察宣城,“朝谢后,未离京国,时曲江荷花盛发,与省阁名士数人同游。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领小仆,步至紫云楼下,见五六人坐于水际。裴公与名士憩于旁。中有黄衣饮酒半酣,轩昂颇甚,指顾笑语轻脱”[2]。裴休意稍不平,因问其所任何官,乃新授宣州广德县令。裴公效曰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狼狈而走,同坐亦皆奔散。赐宴曲江亭是唐代帝王在重大节日时与群官百僚同乐的重要庆祝形式,尤以德宗至武宗时期最为常例。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九月,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癸丑,赐百僚宴于曲江亭,仍作《重阳赐宴诗》六韵赐之”[10]。后又于贞元五年春正月以岁时有碍,诏:“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10]。此后,德宗多次于曲江亭赐中和宴、上巳宴、重九宴以享群臣百僚。贞元六年(790年),“二月戊辰朔,百僚会宴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群臣赐宴》七韵……三月庚子,百僚宴于曲江亭,上赋《上巳诗》一篇赐之”[10]。贞元九年(793年)二月,德宗始从所请,诸司分宴,“先是宰相以三节赐宴,府县有供帐之弊,请以宴钱分给,各令诸司选胜宴会,从之。是日中和节宰相宴于曲江亭,诸司随便,自是分宴焉”[10]。自此,曲江亭赐宴渐渐成为宰臣、两省供奉官于三节之时受帝王宠渥的专有特权。贞元十三年(797年),德宗“二月丁巳,赐宰臣、两省供奉官宴于曲江亭”[10]。此后所载之赐宴宰臣群僚于曲江亭,当也是对宰臣两省供奉官的变异记叙。由此可见,唐代官员既好宴游,朝廷也鼓励官员选胜赏游,既给假又赐钱赐宴,同时至德宗之后,曲江亭赐宴开始具有一定的官品等级色彩,相约宴游之人多同级同好者,不可丝毫僭越,同时也反映裴休个人对轻率高傲之官的蔑视。
“元相国谒李贺”条被后世史家论证为不实,但从该条的内容反映出唐世对由科举进士及第从官之人另眼相看,对于明经擢第及非科第出身的官员则不齿于人。
其次,在民族关系方面,“李朱崖知白令公”条谈及大中初年,“边鄙不宁,土蕃尤甚,恣其倔强。宣宗欲致讨伐,遂于延英殿先问宰臣,公首奏兴师,请为统帅,沿边藩镇兵士数万,鼓行而前。时犬戎列阵平川,以生骑数千,伏藏山谷”[2]。白敏中凯旋,“所获驼马辎重,不可胜计,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为内地”[2]。同列皆进诗盛赞白公功绩。为我们展现了唐末中央与地方民族之间关系的张力。
此外,“宰相布施”“洛中豪士”在反映当时社会的国乱民乏和政治腐败的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上的奢靡之风,即使在国家濒临颠覆之际,仍未有所改。尤其是“洛中豪士”条,在洛阳面临被巢寇陷落之际,豪门士族弟子们宴席间仍因烹饪方法不合己意而拒绝食用上等食材所制佳肴,其铺张浪费、穷奢极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慈恩寺牡丹”条,给后世提供了牡丹品种培育发展的线索,揭露权要子弟与亲友的飞扬跋扈,追求名物之丰奇瑰丽。
在法制制度方面,“袁相雪换金县令”条,康骈在表达官员不应以私利作为自己仕途上升的手段这一劝诫之意外,袁相通过黄金与土在同一容器即体积相同的情况下,其重量不同,实际上利用了黄金和土密度不同的知识为县令洗清冤屈。可知唐人在运用科学知识方面亦颇有章法。宋代郑克撰著的法学著作《折狱龟鉴》释冤门有“袁滋称金”即是收录引用《剧谈录》“袁相雪换金县令”条,可见此事对唐代法制史的研究亦颇具价值。《新唐书》中对袁滋善断亦有记载,“部官以盗金下狱,滋直其冤”[3];《旧唐书》同载其事“部有邑长,下吏诬以盗金,滋察其冤,竟出之”[10],两史对此事记载颇简,《剧谈录》恰可补充细节。
《剧谈录》以上条目,围绕人物,以对国家政治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为依托,关注政治时局,对唐代社会实况进行了多角度呈现。
3 《剧谈录》展示唐代文化和社会风貌
除注重于政治生活以外,《剧谈录》收取材料广泛,为研究唐末宗教、经济文化状况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线索和宝贵史料。
第一,在经济史方面,“宰相布施”“真身”等条都提到当时物价情况及经济状况。“乾符中,有宰相自中书还第,使人以布囊盛钱数千,沿路以施丐者。于是贫乏相率罗路隅,所分既微,渐不能普”[2],可见百姓多有以乞讨为生而不以为侮,宰相亦深知此情,经济状况不佳而以救济式的惠施方式救世是不可能取得效果的。“自开成之后,讫于咸通,计其资积无限。于是广为费用。时物之价高,茶米载以大车,往往至于百两。他物丰盈,悉皆称是……妖妄之辈互陈感应……因此获利者甚众”[2],集中反映了唐末物价飞涨,但宗教狂热者却挥金如土,投机分子仍借宗教聚敛财富,经济乱象丛生。“潘将军失珠”讲到一女子与母同居,以纫针为业,提及吴中初进洞庭橘子,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民众生存的经济来源和物产流通的细节。这些史料都为研究经济史提供了一个侧面。
第二,在宗教史方面,康骈在《剧谈录》中除爱好选取高官权贵作为记录对象外,最为着力的当属宗教方面的内容。在整本札记中占有大量篇幅,其中包括中国社会弥漫性的民间宗教,也不乏丰富以佛、道为代表的制度性宗教。“老君庙画”条,康骈还指出政平坊安国观,因玉真公主所建,受其影响,女冠多是上阳退宫嫔御。卢尚书有诗“君看白首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2]对这一现象有所印证。《全唐诗》卷二七九收录有卢纶《过玉真公主影殿》与之同[12],卷七八三收录《题安国寺》诗亦相同,署名卢尚书,具体姓名不知[12]。康骈通过此条内容进一步论证了唐代上层贵族的公主信仰道教对宫廷女性的影响。
第三,医疗史方面,在宗教的佛、道传教手段和巫术方士之技中,较多涉及到医病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民众治疗疾病通常采用中医和巫医共用的现象,甚至有些时候巫医和中医身兼两职,有医巫同体的趋向。这为后世研究医疗史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
第四,在社会史方面,唐代郊游、宴饮、蓄门客颇为风尚。“李相国宅”条在对相国府内名物极尽奢华铺陈、设计精巧有序进行了不吝笔墨的描述,反映了唐末虽政治纷乱,然而高门士族仍奢靡有费。“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尝因暇日休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语”[2]。同时也反映了唐人的宴饮之风。“曲江”条极言曲江胜景,唐代官僚士子多有宴游、郊游之好,曲江更是佳选,每至中和、上巳节,游人如织。上巳更是“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敎坊声乐”[2]。“白傅乘舟”条亦言白尚书好游历,高逸之情莫能有及。
另有“含元殿”条对含元殿的描述有益于建筑史,更是可与史家所言含元殿参照比较,对了解唐代建筑规模和格局具有积极意义。
4 《剧谈录》大量内容为其他文献所转录
剧谈录以其广泛的史料收录视角为后世提供丰富的资料,其内容亦多有被他书转录或辑佚。
“元相国谒李贺条”附唐咸通之后章句有名之文士,列举以文章著美者9人,以词赋标名者7人,以律诗流传者9人,以古风擅价者4人。“广谪仙怨词台州刺史窦弘馀撰”条考证了《谪仙怨》曲词之本事,言窦弘馀为《谪仙怨》作序以为随州刺史刘长卿所言为误也。康骈为严谨起见两存其事,以为理或可观。为研究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全唐诗》收录有康骈所作诗词《广谪仙怨》一首[12],可知康骈虽进士及第,颇有文才,但留世作品有限,《全唐诗》所搜罗之词亦疑从其存世之《剧谈录》中摘录。案:《全唐诗》所录刘长卿《谪仙怨》与窦弘馀《广谪仙怨》[12],二人更无他诗收录,此两首亦当自康骈《剧谈录》此条析出。可见,在保留大量资料上,《剧谈录》作为札记的作用不应被忽视,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太平广记》对《剧谈录》中的大量资料进行了分类吸收,神仙、女仙、道术、方士、异僧、征应、知人、精察、豪侠、文章、画、相、奢侈、诙谐、轻薄、鬼门、雷门、雨(风虹附)、宝(钱、奇物附)、龙等门类下皆有自《剧谈录》析出之文献。神仙门类下“严士则”条源自《剧谈录》“严使君遇终南山隐者”条;女仙门类下“玉蕊院女仙”条源出“玉蕊院真人降”条;道术门类下“唐武宗朝术士”条源出“说方士”条;方士门类下“桑道茂”条出自《剧谈录》逸文“桑道茂”条,实则《剧谈录》逸文本即从《天平广记》辑出;异僧门类下“永那跋摩”条源出“真身”条康骈议论所引用《名僧传》;征应门类下“裴度”条源出“裴晋公天津桥遇老人”和逸文“裴度”2条,逸文“裴度”条原本即自《太平广记》辑出;知人门类下“李德裕”条源出“李朱崖知白令公”条;精察门类下“袁滋”条出自“袁相雪换金县令”条;豪侠门类下“田膨郎”“潘将军”2条分别源出“田膨郎偷玉枕”“潘将军失珠”2条;文章门类下“王智兴”条源出“王侍中题诗”条;画门类下“老君庙”“杂编”2条源于“老君庙画”条;相门类下“丁重”“殷九霞”“龙复本”3条源出“龙待诏相笏丁重相于驸马附”“道流相夏侯谯公”2条;奢侈门类下“李使君”条出自“洛中豪士”条;诙谐门类下“裴休”条出自“曲江”条;轻薄门类下“李贺”条出自“元相国谒李贺”条;鬼门类下“刘平”“郭鄩”“李浔”“王鲔”4条源出“刘平见安禄山魑魅”“郭鄩见穷鬼”“李生见神物遗酒”“王鲔活崔相公歌妓”4条;雷门类下“元稹”条出自《剧谈录》逸文“元稹”条,此条本是据《太平广记》辑录;雨(风虹附)门类下“狄惟谦”条出自“狄惟谦请雨”条;宝(钱、奇物附)门类下“李德裕”条自“李相国宅”和逸文“李德裕”2条合成,其中逸文“李德裕”条本是从《太平广记》辑出;龙门类下“华阴湫”条源出“华山龙移湫”条。所涉多达20个门类,涉及面颇广,其中既有虚无缥缈令人神往的虚构之事,又充斥着大量的社会真实生活状态,可见《剧谈录》正是在这种游离于虚构与史实之间的构思框架下为后世类书提供了丰沛的事类、物类资料和广阔的社会史料。
《剧谈录》所记材料,有些为史书所不载,尤其是大量社会生活实态是正史缺乏关注的,可补史书之阙;有些史书见载者则可与史书互补互佐。当然,其不足之处,如故事本身的可信度问题,记载史实偶见张冠李戴,鬼神灵异等迷信色彩,也是不容忽视的。《剧谈录》也正是在这种虚实之间为研究唐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后世文学增加色彩,于史于文都是唐代笔记小说中不容忽视的书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