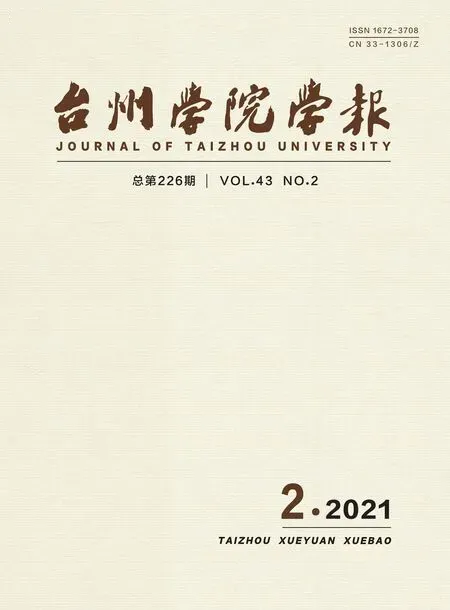传承、革新与反思
——宋代遵式大师的忏悔理念与方法
孙桂彬
(1.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000;2.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遵式,北宋台州人。20岁受具,曾在普贤像前燃一指誓弘天台教法。后师从义通,与知礼同门,皆成为山家派核心人物。他力推净土,奏请天台教部入藏。重视忏讲,撰述许多忏仪,被称为百部忏主。忏悔是修持天台止观的重要前行,随着忏法的制作与实践,忏悔逐渐与理观结合,一定程度承载起天台观心的功能。遵式承继前代祖师重视忏悔的传统,大力推行忏法并躬身实践,成为宋代天台中兴的代表性人物。学界之前对其忏悔思想的研究,多侧重考据其忏法源流及行忏史实,欠缺对其理念与方法的宏观梳理,本文力图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尝试对遵式忏悔思想的特质作出整体把握。
一、忏悔文本的传承与新意
遵式非常重视忏文,他一方面尊重权威,致力保持古忏仪的本真,但又常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新主张,同时撰写新的忏仪,来满足当时社会民众的拜忏需求。
(一)对忏本文献的勘定与维护。忏本为忏法所行之依,是忏悔活动的行为规范,其文本的正确且无错漏是忏法如法进行的保证。遵式具有明显的维护忏本正统的自觉意识,投入较多心力去搜集各种忏本,并加以比对校勘,力求契合原忏旨趣,修正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舛误。他在《法华三昧忏仪勘定元本序》中说到如果不校对讹误,明其得失,则忏本极易失真[1]949。这种对忏仪“真味”的追求,一方面是对道场纲纪废弛和忏本失真的现实状况的呼应,另一方面也是遵式弘传天台教观强烈使命感的自然流露。他结合先贤著作,凭借其敏锐的观察指出当时流通本存在的种种错误。
《法华三昧》以十科组织,理观是其重点,故其保持原旨,尤为关键。遵式对当时流行版本理观部分着重进行了考察,发现其观空时,提到了五句观心,而据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只有前四句,“因心故心,为不因心故心,为亦因心亦不因心故心,为非因心非不因心故心。”没有第五句“非非因心非非不因心故心”,故遵式推断多出此句原文本无而为新本所加[1]949。圣凯法师根据《金泽文库》本指出第五句在当时流行本中确实存在[2]355。遵式进一步批评当时流通本卷末乱引经文,随便加注,诸多过失难以详举,故发心勘定以改其误。现行《法华三昧忏仪》正是遵式当时的勘定本。
《方等三昧行法》文本唐后佚失,宋时日本僧人带回汉地,遵式为其作序,并高度肯定这一行法面世的价值,认为其为方等三昧的行持提供正确规范,纠正长期以来随便臆裁行法的局面。行法共六篇,其中后两篇“方等秘法修行第五”和“方等秘法受戒第六”缺失,遵式指出此两部分可参考《国清百录》《摩诃止观》及相关律典,而之所以仍保留篇目,是为了使行法有始有终。
遵式在《金光明忏法补助仪》中以《国清百录》所录忏文为基础,依据昙无谶和义净两个译本内容及《法华三昧忏仪》对《金光明忏》进行了订补。其在正修前添加了缘起、按文开章以定铨次、别明礼请洒散二法、略明能请及所求离过、总示事理观慧所依等五部分内容,并强调如果没有这五部分内容则并非正本[3]957。说起撰述的缘起,遵式指出智者大师《金光明忏仪》是依据昙无谶译本,某些行法如散洒供食之事存模糊之处,而义净本所译内容更丰富,可补此阙。他还提出百录本初日以后就废请三宝并不合适,他认为此忏与《请观音忏》类似,皆非常注重对三宝护法的恭请,应七日之中多番礼请[2]957。
他参照义净新译本在补助仪中新添五悔和赞叹内容,又尊重佛经原典,没有仿照《方等三昧》《法华三昧》提出坐禅,而是以诵经取代[3]957。虽然遵式指出依据《金光明经》经文,禅坐亦可开,但他明显有意推崇诵经在拜忏中的功用。他认为法华经修持中有相安乐行正是依靠诵持经文而见上妙色像的。诵经不是泛泛而读,依据《国清百录》,诵经时要正念分明,音声条理,且观其性空,并将其供养三宝[3]961。这样诵经掺进了理观因素,具有了有相安乐行的特征。《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三昧仪》中,遵式将百录本《请观音忏》中的第四系念数息改为禅坐,第十坐禅改为诵经,实际使忏本增加了诵念经典的环节,再次体现他对诵经法门的注重。
对于为何要在《金光明忏补助仪》中增设五悔,他解释说经文中含有五悔要求,只是相对简略。如只是念诵经文忏悔品,并不能充分表达出五悔意涵。而且隋朝宝贵所合的《合部金光明经》明确提到五悔:“有四种对治灭业障法。何者为四?一者,于十方世界一切如来至心亲近,忏悔一切罪;二者,为十方一切众生劝请诸佛说诸妙法;三者,随喜十方一切众生所有成就功德;四者,所有一切功德善根悉以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4]369而且展开时皆有“日夜六时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一心一意口自说言”[4]368等敬仪,因此有必要特别列出五悔。
遵式以经典为据,努力挖掘忏法原旨,痛心当时忏文被肆意改动,呼吁忏文传写不可随便添加或删削,以保持文献的完整和准确。《金光明忏法补助仪》中他要求后学传写时要保持文本完整与正确,不能有所脱漏与错误。他见当时一些抄本多随意删削原文,深感痛心[3]958-959。又《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三昧仪》中,他提到有的抄写者任意在抄本上加注,有的则随便删减要文,不尊重经典原貌[5]968。还有的改换题目,或只抄对自己有用的内容,让遵式痛心疾首。他奋力投身到忏本文献的传承保护中,也正是仰仗遵式在世时对诸多忏本的维护整理,我们今日才得见诸多忏本的原容。
(二)忏仪制作的出新与务实。遵式重视依据先有忏本及所依经典对不同忏文的主旨和特色进行挖掘,其中既有传承亦有创新。传承体现在其对忏文原旨的把握和对文献的整理上,他害怕忏本流传中被篡改,因此多次嘱咐后学抄写时切莫以私意改写文本。又如百录本《金光明忏》中无有禅观而只有诵经,他认为此正合经典,故所作忏仪保留了这一特征。创新体现在遵式并没有因此墨守成规,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行忏体悟及对经典的熟练把握勇于对某些忏仪的细节加以调整。如上文所述,他在《金光明忏法补助仪》中添加了五悔内容。又如《请观音忏》属于四种三昧中的觉自意三昧,相比常坐、常行和半坐半行三昧有劝修法,其并无劝修法。智者大师认为觉自意三昧不仅观善,亦观恶。障重者本已沉溺恶业,再劝修就与佛法意旨相违[6]18。而遵式大师则从其他视角给出新的见解。“然随自意凡约四法论修,何妨劝善乎?……今别约依经方法,经中佛自劝修,岂关人情?”[4]972遵式认为虽然不能劝恶,但无妨劝修善法。他进一步引用《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经文,证实佛在经中宣扬陀罗尼的功德利益,正是劝修行为。“呜呼诸佛慈音如此,称赞诚实不虚,愿再读再思勇发道意。”[5]972他慨叹佛陀如此称扬,行者自应发大心广修此经法咒语,因此忏仪中加入劝修。
又《金光明忏法补助仪》中,遵式发明洒散食物的具体做法,指出应在道场外另置净地用于洒食,或者作一个小坛盛香汁,要求其保证严洁,行者向四周洒散直到食尽。有人问此法所依,遵式坦诚回复说虽然在《国清百录》和经文中皆无明确作法,上述所行是其构想出来以成善法,想必也无任何过咎,最后他谦虚地表示如果以后见到更好的合适作法再改也来得及。如此遵式并不简单的是忏法的守成者,他在忏仪撰述中也加入一些自身合理的创思,使忏法内容更具完善,同时也烙上他个人的思想印记。
由于丰富的亲身践行,他对行忏流程及大众参与实效有着个人的真切体验。这种现场觉受提升了其撰写忏仪时对细节的把控能力,体现出可贵的务实精神。《炽盛光道场念诵仪》中,对清净道场的要求他就采取了灵活态度。一方面,他考虑到底层人民生活的困顿,故允许他们只要在居处相对殊胜的净地就可以安置坛场,以扫除他们修忏之障碍;另一方面,对于国王大臣及富豪,则需选取远离喧嚣的上处或未被染污之地,甚或财力具足则可专造道场。如此弹性的设置使得贫富二者皆可参与到忏法修习中来。
他要求参与者不能只走过场,仅泛泛而行,而要对忏本的内容及要求提前消化理解,以使行有所本,切实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如修金光明忏,需要参考百录及新旧两个译本,参照法华三昧事仪、《摩诃止观》及其他忏法,并阅览忏悔品及注解,了解忏悔下手处[3]958。
遵式制作忏仪,有通盘的天台整体教观作为指导,其中以法华三昧和摩诃止观精神为核心,其他忏仪则以此为依据。在行忏前,需提前充分做好功课,对诸多事理及行法次第熟稔于心,行法时自然得心应手、易入佳境。这是遵式对当时形式主义之风的拨乱反正。正是基于这种务实的精神,遵式在实践层面才能将忏法修习真正推广开来。
二、忏悔观念的革新
宋时,忏悔活动逐渐民间化,遵式推广忏悔实践,其忏悔思想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一)对忏仪中施食进行理论阐释。一般提起施食,多指向对鬼神的饮食供养,但其最初亦包括对三宝的供养。忏仪中有时用散洒一词指代,遵式指出施食对象也含摄三宝,如若只言散洒,容易让人误解对象仅限鬼神,因此他建议改用奉供一词[3]959。后世流通的三种施食主要是瑜伽焰口、蒙山施食与水陆法会,除去蒙山施食,其余两种与遵式皆有密切关系[7]527。施食被认为可以感召延寿的果报。其所依经典主要是实叉难陀译《佛说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后不空又译作《佛说救拔熖口饿鬼陀罗尼经》。后者内容更加丰富,添加四如来圣号及其他陀罗尼咒语。遵式曾作《施食法式》讲解简单的施食方法步骤。“祇是以左手擎食,右手按器,咒之七遍,弹指七下,以食泻置净地即足也,但起施心,想此水食由咒力故无穷无尽。”[8]108他认为依据实叉难陀译本已然足够,只变食真言念至七遍再弹指七下就可以,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加上四如来圣号及其他咒语。在交代《施食法式》的缘起时,遵式特别提到遵依古式[8]108。可知他主张依经而行,反对别出心裁。古式先是称念三宝和观世音菩萨名号,唱诵祝愿偈词,持咒语,念诵四如来名号,功德回向,最后弹指散洒。
遵式推崇施食中的密咒作用和观想力量。他认为正是依靠密咒作用,一抟之食可化无穷[8]103,“故大慈诲以密教诅少令多而博济之至”[8]107。因此行者在施食中自应具足信心仰仗神咒神奇力量。至于观想,遵式引入天台教观,认为所施饮食之色味即陀罗尼体,而由一食变无量则即陀罗尼用。施食中的变食真言名为无量威德自在光明胜妙力陀罗尼,遵式以法身三德对其进行阐释,无量威德自在是解脱德,光明是般若德,胜妙是法身德,力是总结力用也,正是法身妙用方可一食变多。有人对此存有疑惑,问既然我与陀罗尼体皆为法身,为何还要借助咒语?这是因为圣人证得法性,因此可称性而用,但众生仍迷惑于事理,未得自在。而圣人应机施教宣说陀罗尼方便,凡夫可借诵持陀罗尼发挥法身妙用。有人问鬼能变食为何不直接施食于它而要借助咒语?遵式回复说鬼有多种,只有少数鬼具有自己变食的能力且其只能自用而无法广济他类,绝大多数鬼要依赖人利用咒力变出饮食才可享用[8]108-109。
那施食时如何作观呢?要先起慈悲心怜悯众生饥渴故欲施食,观想有一广博严净之处作施食之地[8]109。再观想容器,器内美食无量,而容器亦有无数,无数鬼前皆有我身施食于它,同得饱足。“据余咒部,印契观想,随咒句句而作,不可一念差舛,此咒亦令以手按器,咒之七反,咒已弹指七下,非全不作法,今加观想弥益其功。”[8]109施食时要口持咒、手结印、意观想,三密相应,遵式指出其是吸纳密宗修持作法。整个过程中加入观想增强了施食效果。
他明确指出观想次第依据来自天台教观中的历事作观。天台忏仪中供养三宝香花是常有内容,遵式正是参照其观想要求而设置施食运思方式。既然变食是由咒力而为,为何还要用观呢?遵式认为观想可增强咒力,其是自力,而咒为他力,两者相辅相成[8]109。如所观与法界相称,微小善行皆可成就佛果。由此可知遵式所提倡施食未受经文所限,而杂糅进密教和天台教观的色彩,其对施食理论与方法的阐释无疑推动了这一法门在天台忏法中的运用。施食法门在密教衰落后经过天台化改造而得到可贵的发展契机,其进入天台忏仪亦彰显台宗忏法广大的包容力。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改祭为斋的现象,即革祭祀的旧习而换用斋戒形式祈福,由此断肉止杀而行斋戒。遵式对这种改变深为赞许,但由此而来也出现种种质疑,他为此专门作《改祭修斋决疑颂》来回应世俗中的种种疑虑,其中亦提到施食。有人问家眷死后祭祀能否得食,遵式解释说要看亡者现在处于何种轮回状态,如果堕为饿鬼,还要看其具体是何身。他提到饿鬼有三类:无财鬼、少财鬼和多财鬼,其中无财鬼无饮食可得,而平时施食对象主要就是无财鬼中的炬口鬼、针咽鬼和臭口鬼[8]109。而世俗的祭祀中它们是接收不到食物的。因此要想利益它们,需借助施食供其饮食或者依靠斋戒的力量超度祈福。
(二)推崇斋忌,反对世俗祭祀。遵式极力倡导斋忌文化,反对世俗祭祀。传统祭祀要求杀生,并以供品飨鬼神,儒家提倡尊师重道,祭拜先祖,以祈求得先灵护佑,是祖先鬼神信仰的体现。而佛教辞亲出家,视一切众生为父母,虽不再像世俗社会承欢膝下但亦有行孝的伦理规范,这主要体现在师承之间,徒弟需承侍师长,并由此扩展到缅怀并举行仪式纪念先代祖师恩德。遵式曾作《天台智者大师斋忌礼赞文》,称扬智者大师一世修行及传法功绩。他用修斋并忏悔的方式来追思智者大师,并创作此礼赞文。该文先是奉请天台历代祖师,接着用十二偈颂赞叹不同时期的智者大师,之后运顺逆十心在三宝诸祖前发露悔过并行五悔。这种斋忌从佛教教义出发抛却世俗祭祀杀生的弊端,用行斋三宝的方式表达内心对传承祖师的感恩之情,并将忏悔纳入其中,祈求祖师加被,与一般忏悔文相比多了孝道色彩。
佛教行斋与世间祭祀体现了佛教与世俗不同的祈福方式。遵式站在佛教护教的立场,在提倡行斋的同时,也对民间祭祀渗入佛教法会的现象保持强烈的警惕。盂兰盆会本是每年七月十五日佛教通过供僧超荐亡亲的传统仪式,当天会将珍馐美味置于盆中以供养僧众而借三宝之力超拔先人。当时吴越地区虽举行盂兰盆法会但却变质失味,当地有些民众不供三宝而备办供品祭祀先祖甚至烧化纸钱以求祖先佑护而全然失去供僧祈福的意味。目犍连母堕在饿鬼,佛陀让目犍连供养十方僧借僧众神力超度其母,这是盂兰盆会的本义,而此时却沦为民间的鬼神信仰。遵式严厉批判这种现象,指出祖先去世后不管是否堕入饿鬼,如斋僧供僧皆能蒙福解脱,大可不必举行民间祭祀[9]7。总结来说,盂兰盆会与施食同为佛观机逗教救度先亡而所开法门,奉盆供僧自可使鬼众得脱而不必另外祭祀,而且先人死后不一定为鬼,即使堕鬼其也不一定能受食,而供僧则可利益各道众生,不管其是否堕在鬼道。
(三)对天台净土忏的推广。宋时,天台与净土合流趋势明显,许多台宗祖师在宣扬本宗教观的同时也极力弘扬净土思想。遵式曾作《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阐述自己的净土理论。他将修习净土的行愿分为四门:礼忏门、十念门、系缘门和众福门。通过其中礼忏门可为往生净土清净业障净化身心[10]146。而四门各有行愿内容,皆是往生正因。前两门可选择斋日集中修持,后两门则可在日常生活中随力而行[10]146。针对礼忏门,遵式还撰述了一个简单的修持仪轨,先烧香供养、赞佛礼佛、顶礼净土圣众,再忏悔发愿、三自皈依、诵经念佛等,这一仪轨又称小净土忏。据大睿法师观察,台湾许多道场现行净土忏仪轨正来自此[11]323。
遵式还专门作《往生净土忏愿仪》,被称为大净土忏,而《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则为小净土忏,藕益大师将此两忏编入其所集《净土十要》中[12]659。大净土忏是遵式采集无量寿经及其他称赞净土的大乘经典而成,他指出此忏不仅可以有助求生安养,也可速破无明,永灭五逆十恶,清除犯戒罪障。由此,这一净土忏不但适用于净土法门,也可便利日常忏罪修法。此忏共分十科:严净道场、明方便法、明正修意、烧香散华、礼请法、赞叹法、礼佛法、忏愿法、旋诵法、坐禅法。第三部分中,遵式提到“故全用论文为今正意”[13]491。此处论文是指天亲菩萨所作《往生论》。此一部分以这一论典教义为指导,但同时添加忏悔内容,目的是能除灭往生障碍,顺应佛之慈愿速速往生。忏愿法实际正是五悔法门,其中忏悔则运用天台顺逆十心等理论。坐禅法部分,遵式提供了两种观法,让行法者选择:一者扶普观意,要求观想自己所修福慧已然圆满成功往生净土,莲花中化生并听闻佛菩萨讲法,如此观想要求如同亲身经历,并心散不乱;二者则直接定心观想阿弥陀佛形象。无论运用哪种方式,又观所想皆为空性,唯心所现,是一念三观的中道实相。遵式鼓励大家勿生疑怖,勇猛修习久久必成念佛三昧。
三、对不如法现象进行反思与整治
遵式作为忏法实践的推动者,对正法的维持和僧众秩序的维护有着深重的使命感,努力纠正所目睹僧团和普通信众中存在的不如法现象,其纠错对象既有行忏的僧众亦有檀越。《金光明忏法补助仪》中,他批评某些出家人行忏目的不纯,贪着财利。《金光明经》中功德天曾保证为说法者提供所需种种资具,以使他们心能安住在法义上[4]388。而有些出家人则以此为求财途径而舍弃行忏的本义。遵式批判道:“且出家之子,尚不应求事戒世禅,及二乘智慧,岂容全不资道,专为养躯?谄附行仪,窃规财利。设遂多畜,自犯严科,不净八财招苦三恶。”[3]958他认为出家本为求道却贪财物,唯招苦趣,修法自然也就难有感应,如此毁戒护法自然远离,功德天本为护持真修之人,怎会保护那些专注养护色身之人?他指出经中提到持诵可获财主要是为了满足世俗中人,以凸显经典殊胜功用,而要想求财成功也不是全无要求,需要乐善好施,深信三宝[3]958,未见沉溺世俗甘当凡夫而能得人天拥护者。
《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三昧仪》中,他指出行忏者缺乏诚敬精神,置办道场如同俗务,如此反招罪累灭障实难。而正修中,需提前做好功课通达事理,如有疑惑则要提前询问知晓者。《炽盛光道场念诵仪》中,他列举当时僧众行持忏法时的一些不合理举止[14]979。他们肆意而为,全无恭谨,不守规矩,如此不仅自己无法办道也虚消信施得罪不少。而这与他们不信因果有关。遵式叹息这不是个别情形而是普遍现象,扭转起来难度甚大,呼吁有识之士深切改正。
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忏法实践也融入进商业因素,原本神圣的宗教活动有沦为商业交易之忧。佛教僧众原本享有尊贵地位,作为檀越则应恭敬礼待,僧众通过法事祈福行使服务大众的责任,檀越则以钱财供养表达感恩之心。而随着忏法俗化,这种供养关系在某些场合演化为交易买卖。檀越俨然买主,而僧众则成为提供服务的卖主,如此佛教传统僧俗伦理被严重破坏。遵式曾揭示当时所见情形,一方面,檀越慢心滋长,不知礼敬,自认以钱财庇护僧众有功而未晓僧众实为福田之义,因此越礼失节,造下轻慢之罪;另一方面,僧众则过度依赖檀越并失去原则地设法攀附,逐渐失去话语权[14]982。这种僧俗之间的失序导致忏法等宗教活动的法则无法被很好地遵守,宗教的神圣性被破坏殆尽,比如对僧众和三宝敬重之心的丧失,有的道场未整理清净便行法事,不避荤腥就请三宝,延请佛像敬心不够等。遵式睹此痛心不已,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他提出了檀越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要以僧众为师,态度恭敬,如有法事提前问询并安置妥当,僧众临家则诚惶诚恐。他总结出五条原则:陈请法会要尽心,保持身心清净,并每日随僧发露忏悔;斋僧应坐于僧下,恭谨守序;供佛应多于供僧,细心料理佛事;尽己能力布施佛僧,不贪财吝啬;不能仆役僧人[14]982。这五条原则致力于维护僧众的地位,强调施主行法需有恭敬心而不能流于形式,并应舍弃对财产的执着等。也许是见到不如法行为太多,并认识到难以扭转,遵式无奈地表示僧俗可能不会全力执行,“吾知此文将被烧灭,愿十方三宝及有识者用力护持”[14]982。当商业的利益关系切入到神圣的宗教行为中,宗教仪式的本质难免会被侵蚀。这一无奈在各大宗教的发展史上不断上演,但同时又有许多有识之士认清并致力于改正。这种破坏与维护教旨的斗争一直在持续,遵式身处忏法逐渐世俗化的社会潮流,其也难以力挽狂澜,故只能发出惋惜的慨叹。
结 语
宋时忏法极为流行,无论知礼还是遵式皆非常注重忏法,他们对天台忏悔理念与方法的贡献可用“发展创新”四个字来总结概括。他们一方面在与山外派的论争中维护了天台宗的正宗教义,抵制了湛然以来华严宗思想因素的入侵,坚持忏悔的妄心观;另一方面,无论是忏仪制作还是忏悔理念的阐发又颇有革新意识。遵式注重恢复和保护已有天台忏仪的原貌,又自己撰写多部新的忏仪,其忏法轨式与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他还批评当时僧人主持行忏贪财而无诚心,忏法的意旨严重变质,这已是近代以来广受质疑的经忏佛事弊端的滥觞。这种批判的积极意义在于,正确的忏法规范并未因为当时不如法现象的出现而被埋没,正确标准的不断被设立对负面行为起到对冲作用,保障了忏法秩序的顺利传承。当然这种不同时代的不断呼吁也折射出忏法弊端屡禁不止的尴尬,因为忏法不如法行为的出现不仅仅是个人原因,更有社会深层因素。正如近现代大家对经忏佛事的反思,其问题解决仅靠佛教内部远远不够,还应从社会多个层面通盘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