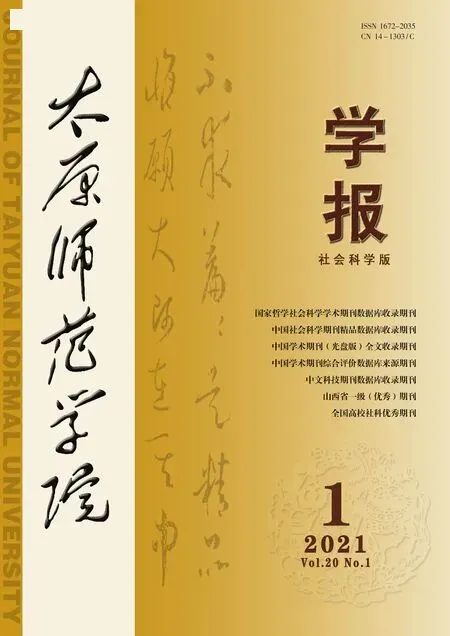尉迟恭记忆形象的建构
林 玲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尉迟恭作为唐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以骁勇善战著称。《新唐书》《宋史》等典籍中对他的生平记载颇多,褒贬各异;民间传说中,既有对尉迟恭未征战前传奇事迹的讲述,也有对他战场上大显神威之事的渲染,重在突出尉迟恭的神性色彩;元代戏曲、明清小说更是将尉迟恭作为创作素材,对其事迹进行二次创作、演绎,意在突出他的忠勇之义。目前学界对尉迟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门神信仰,二是戏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演变。这两类研究选取不同角度对尉迟恭进行梳理解读:前者将尉迟恭放置于门神信仰中,对其形成背景、缘由进行分析考察;后者则着重比较了元明清戏曲、小说中尉迟恭形象的整体流变过程。这些研究通过史料钩沉,对厘清尉迟恭形象演变脉络起到了奠基作用,是学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相关研究未能注意到尉迟恭作为历史人物、民间神灵、文学典型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相关讨论多注重对典籍(正史和戏曲小说)的梳理,忽略了碑刻、图像、口承文本等文献资料,且对尉迟恭记忆形象的演变多停留在人物性格、事迹的梳理描绘上,缺少对其记忆形象建构动因的探讨。
笔者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记忆理论,试图对尉迟恭记忆形象的建构过程进行辨析。扬·阿斯曼认为人的思维是抽象的,但回忆的过程是具体可感的。“真理如果要被保留在群体的记忆中,那么它必须具有一个具体的形式,这种形式或是具体的人,或是具体的事或具体的地点。”[1]30即只有把思想变成具体可感的人或物,它才能转变为记忆,进而成为记忆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扬·阿斯曼提出“回忆形象”(Erinnerungsfigur)这一概念,与哈布瓦赫使用的“回忆图像”(Erinnerungsbild)概念不同,“回忆形象”是指受文化影响、具有社会约束力的“回忆图像”,“形象”(figur)的概念不仅可以指涉图像性的,同时也可以指涉例如叙事性的形式。[1]30“形象”(figur)相较于“图像”(bild),其指涉范围更大,将回忆的视域从庙宇、雕塑等图像性实体转向了叙事性文本(口头的或文字的)形式。在德语中,“回忆”与“记忆”的含义都可用“Erinnerung”一词表示,笔者依据目前国内学界固有的表达习惯,暂将“回忆形象”等同于“记忆形象”。历史上,尉迟恭被记忆的过程,也就是其由人成神象征意义的生成过程。尉迟恭记忆形象的生成,与特定的时空、群体相关联,同时也在当下框架内被不断重构。历史人物由人成神是一个常见的文化现象,背后既有官方推动,也有文人加工和民间助力,这个过程绝非阶段性、层次性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尉迟恭由历史人物成为小说戏曲主角、民间神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漫长历史过程中多方共同建构、人为选择的结果,其记忆形象的复杂性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
一、置庙祭祀:官方加封成神
尉迟恭(585—658),山西朔州人。公元7世纪初,隋炀帝大兴土木,徭役繁重,农民起义不断。隋大业末,尉迟恭从军高阳(今属河北省保定市),讨伐乱贼,官至朝散大夫,后投靠刘武周,任为偏将。武德二年(619),秦王败刘武周,宋金刚败奔突厥,留尉迟恭独守介休(今属山西省介休市)。秦王惜才,召至麾下,引尉迟恭为右一府统军。从此,尉迟恭破郑灭夏、忠心拒金,经玄武门兵变后封吴国公,击破突厥后又改封鄂国公。贞观十七年(643)二月戊申,唐太宗“召图画司徒、赵国公无忌等勋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旧唐书》卷三《太宗下》)[2],尉迟恭亦“图形于凌烟阁” (《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2]。显庆三年(658),尉迟恭卒,年七十四,唐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册赠司徒、并州都督,谥曰忠武。赐东园秘器陪葬于昭陵”(《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2]国家权力介入尉迟恭祭祀是在唐代,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诏令于两京置太公尚父庙,以汉留侯张良配。……至肃宗上元元年闰四月,又追封为武成王,移座南,而选古代良将为十哲,令有司祭。德宗在位建中四年,又诏令选范蠡等名将六十四,图形于壁,每因释奠,皆从祭焉”[3]。鄂国公尉迟敬德画像位于庙内东壁,配享祭祀。北宋宣和五年(1123),宋徽宗从礼部言,沿袭唐代武成王庙祭祀旧制,“释奠日以张良配享殿上,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绩并西向,……尉迟敬徳、裴行俭……并东向。凡七十二人”[4]。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唐鄂国公尉迟敬徳以二公于徐州皆□遗□。建金牙庙于梧州府,祀唐尉迟敬徳。”[5]尉迟恭在统治者的推动下,由一代名将进入宗庙,正式列入官方祀典,逐渐被推上神坛。
明清时期,各地以尉迟恭为主神的庙宇日益兴盛。从现存碑文来看,尉迟恭庙宇得以修建或重修的缘由有二:一是老百姓感其治水有功,故自发修庙祭祀。《明一统志》云巩昌府(1)巩昌府辖境范围:东至凤翔府陇州界五百五十里,西至临洮府渭源县界七十五里,南至汉中府凤县界一千三百里,北至平凉府固原州界六百里。有尉迟敬德庙,“在马跑泉侧,其水有灌田之利,民德之,故立为庙”[6]。相传“尉迟敬德与蕃将金牙战,士卒罢,敬德马忽跑出泉,三军饮足”[6]。此泉故称“马跑泉”,颇具神性色彩。康熙本《马邑县志》也记载了他为民治水之举,卷三《官师志》云“公曾为徐州牧,水患方殷,公因势利导,民免陷溺,徐人建祠,至今犹祀之。其他州邑所在,祀公者亦多”[7]。由此可见,民立庙与徐人建祠之举,都属于民众的自发行为,目的在于纪念尉迟恭的治水功劳,对尉迟恭寺庙的日常祭祀也主要是由民众完成。历史上尉迟恭除了有治水之功外,还监修了多处佛寺,“山西邠县西二十里明咀山麓,崖壁间有唐代所建大佛寺,寺系尉迟敬德监修,名庆寿寺……为西陲著名古迹之一”[8]。在华北地区,尉迟恭所建佛寺比比皆是,如天津的独乐寺、双峰寺,日照的卧佛寺等。尉迟恭修寺之举无疑扩大了他在民间的影响力,也是日后尉迟恭配享祭祀的重要缘由。二是官方为弘扬尉迟恭忠勇之义,树立政治伦理典范,也曾多次修葺鄂国公祠。《(成化)山西通志》载:“鄂国公祠,在马邑县西北一十里金龙池南。唐将尉迟敬德曾于此获神马,故庙存焉。国朝岁以二月十七日、六月十七日,有司致祭。”[9]与“民德之,故立为庙”不同,鄂国公祠为国朝祭祀之地,是经过官方认证的正统祠庙。因此,在马邑县(今朔州市朔城区)当地,尉迟恭信仰愈发兴盛,庙宇也几经修葺。明隆庆元年(1567)《新建唐鄂国尉迟公庙记》载:
嘉靖丙寅岁,予奉命按治宣、云、夏四月,巡历至马邑。一夕,梦金甲神英姿环侍,直立马上。马蹀躞若龙,金戈翠旗导从前后,谒予若有所诉者。予觉,大伟异其事。翌日,出至龙泉寺,见唐鄂国公遗像在焉。叩其所自,邑尹吴子进曰:“鄂国旧有祠,去此仅二里许,爇於燹火有年矣,栋宇灰烬,惟神与马岿然独存。居民不狎於栖神之无所,权奉於此,以存尸祝。”遂即其遗址观焉,草莽丘墟,睠言怀感。予曰:“异哉!向夕予梦金甲之神,非与?”祠前有金龙池,即桑乾河源也,清涟澄澈,严冬不凝。邑尹复进曰:“旧池有龙,时化为马,一骊一黄,人莫敢御,唯鄂国骁勇绝伦,能跨而制之。”[10]1225
碑文记载了御史蒙近野夜梦尉迟恭英灵而重建公祠之事,并称尉迟恭为“真豪杰士,非特将略之雄也”[10]1225。从现存碑刻来看,尉迟恭征战沙场,擒世充、平黑达、降建德、坠雄信之举广为流传,堪称英雄豪杰;他赤心事公、不容奸邪,建元贿之不睬,又为精忠大节。唐朝建立初,太子李建成曾想用一车金器收买尉迟敬德,被其断然拒绝:“秦王实生之,放以身徇恩。今于殿下无功,岂敢当赐?若私许,则怀二心,徇利弃忠,殿下亦焉用之哉?”[11]3034这样一个集忠、勇于一身的臣子,自然也就成为了统治者推崇、后世敬仰的典范。故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鄂国公庙再次得以修葺。《新增重修鄂国公庙记》曰:“余今岁春,欲捐俸庀材,鼎新庙貌,而守戎郑君怂恿之,议遂决。诸簪绅与四民向义者,亦各乐于轮资,以襄兹举,因属仪宾李宦董其事。甫三越月,堂宇门庑焕然改观,又于正殿之东侧禅房一区,命僧元锦居之,以旦晚供奉香火。”[10]1228-1229重修鄂国公庙由马邑县县令王日新发起,乡绅与老百姓共同集资完成。至于重修原因,大抵是因仰慕尉迟恭慷慨沉毅之姿、叱咤风云之态。可见,各地尉迟恭祠庙,或官致祀,或民立庙,都将其奉作神灵加以祭祀。以上文献碑刻中所记庙宇建立、重修之事,意在凸显鄂国公的英勇气概和忠义形象。官方加封和置庙祭祀,是尉迟恭由人而神的第一步,有关尉迟恭的记忆,也借助庙宇碑刻这一物化载体被保存了下来。在这个阶段,尉迟恭的形象与正史记载相似,重在强调他的忠君与英勇,其记忆的核心在于“忠勇”二字。碑文中也多次将尉迟恭与关公相提并论,称二者“性情不相远也”“雄武不相远也”[10]1274。
祠庙碑刻作为尉迟恭忠勇形象的空间框架,它所体现的是集体的共同记忆,尤其是官方的意志表达。尉迟恭作为忠勇伦理精神的化身,其形象在碑刻中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在特定的庙宇场域中被唤醒,又在重复的祭祀仪式中被不断强调、记忆。“回忆形象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使其被现时化,所以回忆形象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总是具体的。”[1]31也就是说,尉迟恭记忆形象根植于特定的时间(祭祀)与空间(庙宇),而不断“被经历的时间”(erlebte Zeit)与“被唤醒的空间”(belebter Raum)就成为记忆尉迟恭忠勇形象的重要方式和场域。
二、民间话语:门神信仰的建构
尉迟恭作为初唐大将,民间广泛流传着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这些传说经文人辑录,主要保存在《说苑》《三教搜神大全》《历代神仙通鉴》《新搜神记》等神仙列传和小说中。民间话语中的尉迟恭从一出生就颇具传奇性,他“生来黑壮胖大,加之其母称怀上他时夜梦黑虎入怀,所以就有尉迟恭乃‘黑虎下界’之传说”[12]357。与典籍记载的忠勇之士不同,民众记忆中尉迟恭摇身一变成为了驱灾辟邪的民间神灵。实际上,历史人物“由人成神”是较为常见的现象,黄景春教授指出“民间神灵与小说人物经常相互转换,二者可以说是互为源流,互为宾主”[13]480,并进一步将这种互动归纳为四个模式,即西王母模式、老子模式、龙王模式、柳毅模式。尉迟恭“由人成神”属于老子模式,即“著名历史人物转化为传说人物,被神化以后成为民间信仰的神灵,相关口头传说经过文人记录、加工而成为小说,这些小说被视作宗教经籍,人物也得到帝王加封,从而不断扩大影响力”[13]481。从内容上来看,尉迟恭传说主要集中在对其生平传奇性的讲述上,《逸史》载:
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抵官府,因穴而入,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神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恭贴来,此尉迟敬德钱也。”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断铁尉迟敬德者,方坦露蓬首。锻炼之次,书生侍其歇,乃前拜之。尉迟公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尉迟公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贴,他日自知。”尉迟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书生拜谢辞去。尉迟公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铁,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遣书生取钱,止于五百贯。后敬德佐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敕赐钱,并一库物未曾开者,遂得此钱。阅簿,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贴子。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贴。累日惊叹,使人密求书生,得之,具陈所见。公厚遣之,乃以库物分惠故旧。[14]1048
《逸史》中对尉迟恭从军前铁匠身份的讲述,弥补了正史典籍的空白。在民间,人们关注的不再是尉迟恭如何忠君、英勇,而是将话题转移到他的传奇经历上。在朔州地区,至今仍流传着大量关于尉迟恭的传说,如“敬德吃饭坐正面”“敬德钢鞭破碌碡”“敬德龙池擒海马”[15]77-104等。这些传说多将尉迟恭塑造为天赋异禀、异于常人的神人形象,重在凸显他的传奇色彩。“传说作为民众口传的历史,在增衍的过程中不仅改变某些情节,也注入很多细节,民众以此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因而传说总是打上老百姓的情感烙印,能够比较朴素地表现出民众的爱憎好恶之感”[13]325。关于尉迟恭的各类传说中,他总是以正面人物形象出现,也始终是受到神人帮助、获取胜利的那一方。经过民众的想象和附会,尉迟恭的神性不断增强,逐渐演变为民间神灵,主要包括门神、黑虎神、财神等神格。
其中,门神是尉迟恭影响最为广泛的神灵身份。门神即古代传说中的司门之神。《礼记正义》卷十四记:“门神阴气之神,是阴阳别气在门户者,与人作神也。”[16]283《文献通考》卷八十六将“五祀”解释为:“行是道路之神,门是门神,户是户神,与中二、灶凡五。”[17]782自先秦以来,中国民间便流传着贴门神这一习俗,门神也通常分为三类,即文门神、武门神、祈福门神,尉迟恭属武门神类。《三教搜神大全》卷七明确记载了尉迟敬德成为门神的缘由:
门神乃是唐朝秦叔宝、胡敬德二将军也。按:传唐太宗不豫,寝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呼号,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夜无宁静。太宗惧之,以告群臣。秦叔宝出班奏曰:“臣平生杀人如剖瓜,积尸如聚蚁,何惧魍魉乎!愿同胡恭戎装立门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无警,太宗嘉之,谓二人守夜无眠。太宗命画工图二人之形象全装,手执玉斧,腰带鞭铜弓箭,怒发一如平时,悬于宫掖之左右门,邪祟以息。后世沿袭,遂永为门神。[18]87
尉迟恭字敬德,属于鲜卑族,故民间俗称胡敬德,文献中的胡恭即尉迟恭。《历代神仙演义》对此事也有记载:“帝有疾,梦寐不宁,如有祟近殿寝,命秦琼、尉迟恭侍卫,祟不复作。帝念其劳,命图像介胄执戈悬于宫门。”[19]762清代李调元《新搜神记·神考》曰:“今世惜相相沿,正月元旦,或画文臣,或书神荼郁垒,或画武将,以为唐太宗寝疾,令尉迟恭秦琼守门,疾连愈。”[20]民国时期贴门神的习俗仍在延续:“大门三道,门上漆着的‘秦叔宝和尉迟恭’都斑斑剥剥,不成整个的形体,有一扇门只剩‘尉迟恭’的眼睛和‘秦叔宝’的鼻子了。”[21]但在广东等地,门神角色略有改动:“住宅之两扇大门之上恒分贴‘文丞’、‘武尉’,或‘神荼’、‘郁垒’,盖信其能治鬼辟邪也。‘文丞’是魏徵,‘武尉’指尉迟恭。此出于传说故事,谓唐太宗曾患病为鬼魔所扰,得此文武二臣侍立,鬼魔尽退。”[22]神荼、郁垒是最初的门神形态,早在《山海经》《风俗通义》等典籍中就有记载;元代以后,门神逐渐转变为秦叔宝、尉迟恭,特别是在明清小说《西游记》《隋唐演义》的推动下,秦叔宝、尉迟恭门神信仰已经十分普遍。如果说唐宋之际是尉迟恭入庙成神的萌芽期,那么明清时期是尉迟恭由人成神的高潮期,大量尉迟恭显灵事迹在这个时期被记录、保存。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祀鄂国公碑文》载:“鄂国公故鄯阳人,专祠马邑。府议入祠,尚持……端,余谓:‘世民虽有惭德,鄂国委身尽忠,且有保障功,祀之可。’此八月……事也。晋闱分校杨宪幕阅卷时,恍见尉迟公入簾内,问其意,欲中大……人已揭榜,获隽者二,咸诧以为奇,高太守谓余追崇乡哲,作兴人材……甚奉切神之格,所以报也,余乌敢当!□□显灵,□□时□事,会亦足神□□□,吾人一动念,靡不降陟,不可不慎,□为祭之,□复记其事……”[23]233康熙本《马邑县志》也记载了类似的事件:“先边烽多警之秋,公屡示神威,以捍牧园。”[24]126尉迟恭生前征战沙场,英勇无敌,死后依然可以屡显神威,颇具传奇色彩。考场、沙场显灵之事,无疑增强了尉迟恭的传奇性与神秘性。
“从传说到信仰的过程,是口头叙事影响人们行为、口承文学积淀为民俗心理的过程。”[25]首先,民间对尉迟恭的想象与建构,是基于正史记载的构拟。民众认为尉迟恭久经沙场、威武勇猛,“开门安卧,酣然而睡,杀手震恐而退”[12]356,自然他也可以辟邪攘祸、驱除鬼祟。“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1]35因此,民众对尉迟恭成神的想象,是基于他作战勇猛的史实,是民众对典籍中尉迟恭忠勇记忆的重构。其次,民众在此框架内不断附会、增衍出新的传奇叙事,注入民众的情感与信仰观念,形成独立于官方的民间话语体系,重构了对尉迟恭的文化记忆。至此,尉迟恭由唐朝名将进入百姓家,成为民间信奉的重要神灵。
三、文学演绎:艺术典型的生成
与其他英雄将相传说相似,尉迟恭传说也经历了一个由史实记载、民间流传到文学演绎的过程。从唐代开始,《隋唐佳话》《谭宾录》《大唐传载》《逸史》等笔记小说中就记录了尉迟恭比武夺槊、擒琬夺马之事;宋代话本《薛仁贵征辽事略》中,也有不少关于尉迟恭的文学描述。唐宋时期经由文人记录而文本化的志怪小说、平话,与严格意义上的文人创作不同,多是对民间传说的辑录与剪裁,因此文本原貌与民间流传形态尚未发生太大的变动。到了元代,则产生了大量文人创作的尉迟戏,分别为“尚仲贤《尉迟恭三夺槊》杂剧(简称《三夺槊》)、《尉迟恭单鞭夺槊》杂剧(简称《单鞭夺槊》)、杨梓《功臣宴敬德不伏老》杂剧 (简称《不伏老》)、无名氏《小尉迟将斗将认父归朝》杂剧(简称《认父归朝》)”,另仅存目有“关汉卿《介休县敬德降唐》杂剧、郑廷玉《尉迟恭鞭打李道焕》杂剧、于伯渊《尉迟恭病立小秦王》杂剧、屈子敬《敬德扑马》杂剧、无名氏 《老敬德挝怨鼓》”。[26]这些杂剧以正史中的尉迟恭生平为基础,进行加工附会,创造出大量征战传说,以凸显其勇猛的大将风范,这也为明清小说中的尉迟恭人物形象奠定了基调。明清时期,尉迟恭频频出现于《隋唐两朝志传》《大唐秦王词话》《说唐全传》等小说中,人物故事愈加繁复,性格也逐渐多元化。
与正史碑刻中的尉迟恭形象稍有不同,话本、戏曲、小说不仅仅将其视为君臣之义的人臣典范,而且将笔墨用在尉迟恭生平的描述上,重在突出他的义气与传奇性。在各类文学体裁中,尉迟恭的相关叙述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与齐王元吉比武夺槊之事,见于唐代笔记《隋唐佳话》《大唐传载》、元代戏曲《单鞭夺槊》《三夺槊》、明清小说《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大唐秦王词话》《隋唐演义》《说唐全传》等文本中。其二,勇擒王琬、夺其良马之事,见于唐代笔记《隋唐佳话》《谭宾录》《大唐传载》、元代戏曲《单鞭夺槊》《三夺槊》《敬德扑马》、明清小说《大唐秦王词话》《隋唐演义》等文本中。其三,大战单雄、单鞭救主之事,见于元代戏曲《单鞭夺槊》《三夺槊》《单鞭救主》、元明之际无名氏所作杂剧《鞭打单雄信》、明清小说《隋唐演义》《说唐全传》以及戏曲《麒麟阁》《御果园》等文本中。其四,大闹功臣宴、出征高丽,见于宋代话本《薛仁贵征辽事略》、元代杂剧《功臣宴敬德不伏老》、明清小说《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隋唐演义》以及明代戏曲《金貂记》等文本中。上述四个情节皆有史可溯,是在史实的框架内进行的文学演绎。有一些情节则多半是文人的虚构,如唐代文言小说《逸史》中对尉迟恭天命富贵的描述,元代杂剧《认父归朝》中关于尉迟恭与其子(尉迟保林)战场相认的叙事,清代传奇无名氏《紫金门》中尉迟恭之死的神异讲述等。在征引史实与创作虚构间,文人群体将尉迟恭塑造成一个出身贫苦而天命不凡、勇猛善战而义薄云天、率直自负而赤胆忠心的英雄形象。可以说,尉迟恭艺术典型——英雄形象的生成背后有着一定的文化叙事逻辑,关涉到文人群体对他的记忆建构。“集体记忆是站在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群体立场上的。”[1]32因此,尉迟恭记忆形象的建构,不仅代表了个体的单独回忆,更是与之相对应的群体的情感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形象表达了这个群体的一般态度,并且重构了集体的历史。[27]103那么,文人群体在对尉迟恭进行文学演绎时又出于怎样的目的和情感选择呢?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记:“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28]194可见,早在宋代,勾栏瓦舍间就有讲述唐代开国故事的传统。尉迟恭作为唐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自然成为了说书艺人的讲述对象。《旧唐书》中有关尉迟恭的记载颇具传奇性,又有诸多不明晰之处,虚构空间大,文人群体便以此为契机进行虚构、演绎。在尉迟恭的诸多事迹中,文人群体侧重于对其忠义精神的刻画、渲染。这是因为“忠”“义”思想在中国道德伦理体系中一直占居着重要位置。《国语·晋语二》云:“夫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29]105《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30]12尉迟恭身上所具备的忠义精神,恰好符合传统儒家伦理范畴。中国古代社会固有的价值评价体系,使得文人群体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他们渴望获得体制认同但又追求独立人格,最终陷入了对自我身份认知的焦虑中,这种焦虑是“当时社会体制与儒学价值谱系下正常的心理反应与必然的价值选择”[31]。为了获得体制认同,文人群体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社会政治道德层面,并将这种价值倾向带到了文学创作中,因此“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形往往都有较为明确的伦理用意”[32]。尉迟恭作为统治者所推崇的政治伦理典范,自然也就成为了文人群体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对象,关于他的忠义事迹在各类文体中被不断凸显和演绎。《单鞭夺槊》中尉迟恭介休被围,却不肯背弃旧主刘武周,后不得已为刘武周守孝三日才转投李世民麾下。《大唐秦王词话》第三十四回中,该情节更加丰富。尉迟恭见到刘武周首级时“两眼掉泪”,感叹“夺利图名翻做梦,苦争恶战化为尘”,遂要拔剑自刎以死报恩。此类文本与史书记载“金刚战败,奔于突厥;敬德收其余众,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谕之。敬德与寻相举城来降” (《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2]之语大有不同,多侧重于对尉迟恭忠义形象的刻画。他的义行还体现在其富贵不易妻上。玄武门之变后,太宗欲以女妻敬德,敬德对曰:“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其妻,此非臣所愿也”[33]6144。尉迟恭富贵不忘糟糠之妻,符合儒家伦理规范,故在戏曲小说中也曾多次出现此类情节。近代有人称之为“义夫”:“今人言义夫,动称汉大司马宋公,而不及唐鄂公尉迟敬德。”[34]文人群体有意对尉迟恭降唐之事、拒婚之举进行想象改编,进而将他塑造成一个仁厚、忠义的完美英雄。
尉迟恭“被不同的记忆主体‘记录’和‘想象’,被不同的记忆载体‘承载’并‘延传’”[35],其记忆形象愈加复杂、多面化,但“忠义”内核从未发生改变。这是因为文人群体“在选取回忆内容及选择以何种角度对这些内容进行回忆时,其根据往往是(与集体的自我认识)是否相符、是否相似、是否构成连续性。”[1]33从唐代笔记到宋代话本,从元代杂剧到明清小说,尉迟恭的忠义精神经由文人书写后不断被重复、强化。
正史、民间、文人话语中的尉迟恭记忆形象在不断发生变化,其原有形象虽不能被完全保留,但始终以尉迟恭的“忠勇、仁义”为叙事核心。尉迟恭从历史人物转变为民间传说中的重要神灵和文人笔下的典型英雄人物,其中既有国家话语权力下的政治动因,也是民众、文人群体共同推动的结果。其转变过程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互动过程:首先,国家权力的介入,为尉迟恭的记忆形象奠定了基础,民众和文人群体在此框架内对其形象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重构,前者侧重于对尉迟恭神性的想象,后者则侧重于对尉迟恭大义的刻画。其次,文人群体通过对民间口承文本的辑录、增饰,塑造出具有文学色彩的典型艺术人物。最后,文人创作的杂剧、小说流行后,也会对民间传说、信仰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官方、民间、文人在对尉迟恭进行记忆、重述的时候,既相互影响又相互渗透,多方合力共同完成了对尉迟恭记忆形象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