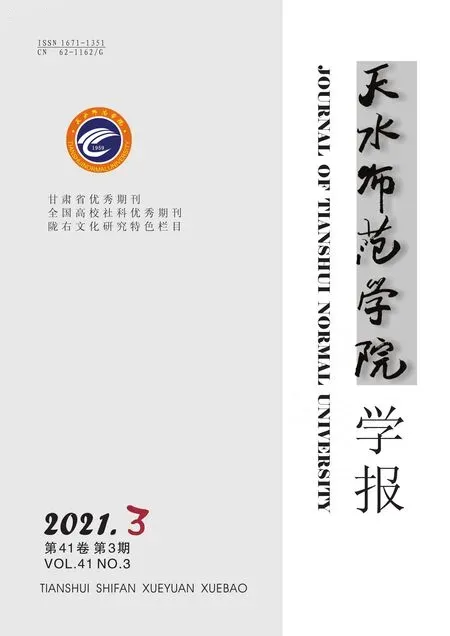从七子派格调论到沈德潜格调论的嬗变
——以叶燮诗学为视角
曾贤兆
(河西学院 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以前后七子为核心的明代诗学复古思潮贯穿了明代诗学史的始终,即使站在七子派对立面的公安派也承认前后七子倡言复古,对于扫荡“近代固陋繁芜之习”[1]452起到了重要作用。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序》中,直接将明代诗歌的特点归纳为“复古”,可见明代诗学复古思想深入人心。其诗学复古论的核心主张即古诗宗汉魏,近体法盛唐。初衷是通过对汉魏盛唐诗歌格调的摹仿,以达到振拔时代诗风的目的。格调与摹拟复古如影随形,他们在追慕汉魏盛唐的同时,将“格调”作为诗歌形式美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来反对明初以来的性气诗、理学诗、台阁诗风,重树诗歌尊体意识,尊崇先秦汉魏以至于盛唐的古代文学典范。这一轰轰烈烈的诗文复古运动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其所复之“古”,也绝非一种刻板和倒退,相反,却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追求,为明代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显示了勃勃生机。整个明诗都处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之下,抑或与反复古思潮进行着激烈的论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世移时迁,随着诗学史的发展,到了清代初期,复古派的格调诗论遭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是由于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和领袖人物提出的理论主张存在先天的缺陷,第二则是众多的末流参与其中,不仅没有对他的领袖人物的观点给予必要的修正,更是片面理解、拘泥陈说,导致诗坛剽袭成风,丧失创造,徒有模仿,不见意蕴。叶燮针对诗坛流弊,从七子派的理论偏失与七子末流的泥古剿袭入手,对其复古与格调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进而将其抽象为一般的诗歌史理论,是为其具有精湛理论体系的诗学著作《原诗》。沈德潜是乾隆时期的诗坛盟主,曾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至四十二年(1703),约五年时间,问诗法于横山叶燮之门。其论诗承明代七子派而以格调为主,同时融通乃师之论,以其远见卓识修正和改造了格调诗说,既继承了七子派格调论在树立古代诗歌典范等方面的优点以及以格调为手段振拔时代风气的有益尝试,又规避了七子派及其末流格调优先、以形式规范诗歌意蕴和内容、本末倒置等偏失,从而形成了以“格调说”为核心的诗美理想。本文从叶燮对七子派的批评与沈德潜格调说形成的角度立论,以彰显叶燮于清中期格调说形成的重要作用。
一、从七子派的形式至上到沈德潜对诗人主体地位的重视
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认为:“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2]卷48,潜虬山人记其中“格古”“调逸”成为格调论诗学最根本的主张和论诗的基础,相形之下,“气”“思”“情”等内容要素反而成为体、格、调等形式的附属。这是李梦阳格调论的致命缺陷,尽管在当时运用于诗歌批评,对扭转时代诗风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诗学理论指导诗人们的创作,却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尤其是七子末流将之奉为圭臬,大量创作所谓“格古调逸”的作品,徒有形式的模仿而无意蕴的创造。后七子领袖李攀龙“于本朝独推李梦阳”,[3]卷287他的一些乐府诗和五言拟古之作,以摹拟古人为能事,甚至“易一二字,便居为己作”,[4]10这几乎是整个时代的风气。[5]88-89此后,胡应麟认为:“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6]100以“体正格高,声雄调鬯”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和法门,试图通过对诗歌体格、声调等形式方面的努力,来达到兴象风神等内容方面的提升。可见,胡应麟与李梦阳一样,在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本末倒置。
身处清朝前期的叶燮,有感于“有明末造,诸称诗者专以依傍临摹为事,不能得古人之兴会神理,句剽字窃,依样葫芦”[4]10的现实,指出:“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4]17在叶燮这里,胸襟是作为性情、智慧、聪明、才辨等内容要素的载体出现的,即指诗人的理想、信念、情操、志趣等,是创作冲动得以发生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叶燮针对七子派以格调统领诗歌创作诸要素的偏失而提出的。他还以杜诗为例,指出杜甫遭逢时代的苦难,而以宽广的胸襟作为其情感、志趣与理想信念的载体,发而为不朽的篇章,就是最有力的例证。叶燮反对的是七子派以格调统领诗歌其他要素的诗学方法,并非反对格调本身和诗歌的形式美。相反,他很重视格调,他只是反对以格调为诗之旨归,认为格调只是构成诗歌形式美的要素之一,而不是诗歌最本质的特征。对于李梦阳、胡应麟等格调优先的主张,在叶燮看来仅仅触及诗歌的皮毛和表面,而非骨骼和本质,体格、声调“皆诗之文也,非诗之质也”。[4]45
沈德潜承明七子派而以格调论诗,但并不单纯以格调为旨归,而是赋予格调以新的内涵,既重视思想的雅正,又强调诗法、韵律、气格,也兼顾性情及其他,以此作为批评原则,编选《唐诗别裁集》《古诗源》《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诗歌选本。他发挥叶燮关于“胸襟”的观点,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7]187将“襟抱”与“学识”作为优秀作品的基础。也就是说,要写出上乘的作品,必须以阔大的胸襟与广博的学识作为基础,这就很自然地将诗歌创作与人格修养联系起来了,突出了诗人作为创作主体的决定性地位。体格、声调、音韵、字句等形式的东西是处在第二位的。他认为:
世之专以诗名者,谈格律,整对仗,校量字句,拟议声病,以求言语之工。言语亦既工矣,而幺弦孤韵,终难夫当作者。惟先有不可磨灭之概,与挹注不尽之源,蕴于胸中,即不必求工于诗,而纵心一往,浩浩洋洋,自有不得不工之势。无他,功夫在诗外也。[8]缪少司寇诗序,1318
对于当代徒有形式美而无胸襟、性情的作品,他严厉批评“言语非不工,性情何有焉”[8]古风,52“镂刻非不工,性情渐乖隔”,[8]答曹谦斋见赠并题诗稿,103他还将作为诗歌内容的性情与作为诗歌形式的体格、声调、音韵提升到源流正变的高度来论述:“夫《诗》三百篇为韵语之祖,韩子云:‘《诗》正而葩’则知正其诗之旨也,葩其韵之流也。未有舍正而言葩者。”[8]曹剑亭诗序,1566“正”就是包含了性情等要素的内容,“葩”则指构成诗歌形式美的格调。
与格调等形式因素在诗歌创作中地位下降相适应的是内容要素以及诗人主体地位的上升。叶燮认为诗歌所表现的对象是“天地万物之情状”,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就是理、事、情:
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4]21
沈德潜则进一步发挥,认为理、事、情当通过比兴的方法来表现:
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7]186
对学诗者来讲,沈德潜站在诗人主体的角度,通过对诗歌表现对象“比兴互陈、反复唱叹”的方法来抒情言志,比七子派首先模仿古人格调的做法更加辩证,也更具有操作性。
二、从七子派的格调优先到沈德潜对诗歌伦理价值的强调
在七子派确立的格调优先的诗学规范中,伦理价值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而在叶燮的诗论体系当中,特别强调了其学说根柢经学的正统性。他在《答沈昭子翰林书》中以自己幼年未能及早“从事于六经而根原于于古昔圣贤之旨”而抱憾,壮年以来,则“思从事于古昔圣贤之经学,才有其志而自顾年已老矣”“无已,则于诗文一道稍为究论,而上下之,然又不敢以诗文为小技,即已厌弃雕虫饾饤之学,则此亦必折衷于理道而后可”。[9]卷13所谓“理道”,即是圣贤之理,六经之道。也就是说,叶燮是自觉地以经学为基础来专治诗学的。很多地方可以看出他以经学或儒家的观点作为自己诗论体系的理论基础。[10]153比如,关于诗歌创作的动机,叶燮强调“风人之旨”,即“情偶至而感,有所感而鸣,斯以为风人之旨,遂适合于圣人之旨,而删之为经以垂教。”[4]35在这一点上,沈德潜吸收叶燮的观点对七子派诗学进行了改造,赋予“格调说”以新的内涵。在他看来,诗歌的温柔敦厚与否乃诗人人格修养高下的表现,正如诗歌的意蕴是诗人胸襟开阔与否的表现一样。他在《古诗源序》中说:
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8]卷三,1301
可以看出,他编辑诗选、提倡格调的目的与七子派有着很大的不同,是希望通过盛唐格调上窥风雅遗意,下明诗史源流,发挥诗教功能,强化儒学规范。在他的格调论诗学体系当中,“格调”只是手段,而“诗教”才是真正的目的。《说诗晬语》开宗明义:“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7]186沈德潜的选诗原则是“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未尝立异,不求苟同,大约去淫滥以归雅正,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庄者,庶几一合焉。”[8]唐诗别裁集序,1302这就是以传统诗教立场作为其格调诗说的伦理基础,来规范诗歌的思想内容,其次才是体裁、音节等属于格调范畴的形式要素。他漫长的一生几乎都贯穿着这样的宗旨,《七子诗选序》说:“予惟诗之为道,古今作者不一,然揽其大端,始则审宗旨,继则标风格,终则辨神韵。”[8]七子诗选序,1360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又重申:“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8]重订唐诗别裁集序,1998“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11]卷首沈德潜坚持儒家正统的诗教观,首先强调“审宗旨”,那么“宗旨”具体指向什么呢?《七子诗选序》说:“宗旨者,原乎性情者也。”[8]七子诗选序,1360也就是诗歌批评首先要考察的是作为“性情”载体的“人伦日用”“古今成败”“兴坏之故”等等,可见其伦理指向相当明确。这也是诗歌思想内容的主体,要发挥诗歌有补于世道人心的积极作用,而坚决摒弃嘲风雪弄花草的无为之作。可见沈德潜论诗深受乃师影响而强调诗教立场,更进一步将其伦理价值强化,以作为清代中期格调诗学的思想基础。
三、从七子派独宗盛唐到沈德潜对诗史源流的追溯
七子派将诗歌发展的高峰聚焦于汉魏盛唐。李梦阳认为“三代而下,汉、魏最近古。”[2]卷62,与徐氏论文书其他时代成就不大。何景明古诗“必从汉、魏求之”。[12]卷34康海倡言“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13]卷中可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诗史观念,仅仅将数千年诗歌史视为僵化而不连续的片段。后七子领袖李攀龙更胜一筹:“文自西汉以来,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豪素污者,辄不忍为,故所作一字一句摹拟古人。”[14]卷172这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诗学主张,对数千年诗歌史上其他时代优秀的作家作品视而不见,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就是模拟剽窃、千篇一律,汩没性情,了无生气。叶燮将这种僵化的观念比拟为今日之人模仿远古初民穴居巢处,唱击壤之歌,以兽皮为礼一样可笑荒唐。他指出:
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不可谓后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4]6
叶燮充满自信地断言“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也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七子派宗汉魏盛唐以为圭臬的做法。强调“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自然包括诗歌在内,其艺术技巧有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针对七子派僵化的诗史观,叶燮指出诗人应当熟悉诗史发展的盛衰、源流、沿革、因创,出入于不同时代优秀的作家作品之中,融汇多种风格而自成一家,不当拘泥于特定时代的特定作家,而对其他时代众多诗人的精华视而不见。叶燮在《原诗》中开宗明义:
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共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4]3
叶燮推源溯流,认为《诗经》时代是诗史创辟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诗歌的规模、体制、格律、声调等形式特征于汉代初具,此后历经魏晋六朝以至于三唐,宋、元、明数千年之发展,形制渐趋完备。这期间,诗歌诸要素虽有不同和高下之别,但总体上却在不断地踵事增华,“以渐而进”。相形之下,七子派独宗汉魏盛唐,鄙薄中晚唐、宋、元诗的做法就愈益凸显出其短视与偏狭。这就从理论层面否定了七子派独宗汉魏盛唐的合理性。
数十年之后,沈德潜通过编辑诗选的方法也对诗史源流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他在编订了《唐诗别裁集》之后,进而溯唐诗之源,梳理唐诗与前代诗歌的关系,编选了《古诗源》。他在《古诗源序》中说:“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又说“唐诗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诗,又唐人之初祖也。”[8]卷三,1300-1301指出宋元诗由唐诗发展而来,而唐诗又由汉魏六朝诗歌发展而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自七子派以来格调诗学强烈的门户习气,从而开辟了清代中期格调诗学阔大的视野。此后,他又编选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在其晚年又编选苏轼、陆游、元好问诗为《宋金三家诗选》。由此而完成了对数千年诗歌史的梳理和诗史源流的追溯。这样阔大的气象远非七子派格调论所能仿佛,其根本原因在于沈德潜承师说而推源溯流,摒弃了七子派“古诗宗汉魏、近体法盛唐”等狭隘的观念。
四、从七子派固守古法到沈德潜“以意运法”
“法”是诗歌创作的“规矩”和“法式”,可理解为学诗者入门的捷径。李梦阳说:“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2]卷62,答周子书可以看出他对古人作诗的方法推崇备至,是“物之自则”,当恪守之。他还将作诗比喻为书法,“作文如作字,欧、虞、颜、柳,字不同而同笔,笔不同非字矣。”[2]卷62,驳何氏论文书“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摸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耶?自立一门户,必如陶之不冶,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杨耶?”[2]卷62,再与何氏书李梦阳遵循古法,反对自出机杼,于诗人主体的创造性弃置不顾,甚至“守古而尺尺寸寸之”,[2]卷62,驳何氏论文书这就很容易流于剽窃因袭,千篇一律。
叶燮在《原诗》中不仅用较多的篇幅探讨了五古、七古、七律、七绝的字法、句法、章法以及用韵的问题,还提出了诗歌创作中,“法”处在一个很次要的位置,因为今人同古人一样作诗,而不是“述诗”,所有的创作,都该有创新:
若夫诗,古人作之,我亦作之。自我作诗,而非述诗也。故凡有诗,谓之新诗。若有法,如教条政令而遵之,必如李攀龙之拟古乐府然后可,诗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若徒以效颦效步为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诗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后法,非废法也,正所以存法也。夫古今时会不同,即政令尚有因时而变通之。若胶固不变,则新莽之行周礼矣。奈何风雅一道,而踵其谬戾哉![4]23
可见,叶燮虽然也重视“法”,但对“法”在诗歌创作中究竟能起到多么大的作用却持保留态度。他并不是无视“法”的存在,而是将“法”尽量地淡化,也就是“后法”,以至于到了不存在的地步。这样,就能很好地消解李梦阳“尺寸古法”的弊病,也不至于会出现于有明一代独推李梦阳的后七子领袖李攀龙视“法”如教条政令,而写出效颦效步的摹拟剽袭之作。叶燮对“法”的辩证地解释与运用的原则,是符合实际的。“中国古代诗论家对技法的根本态度是反对执著于固定的法,追求对法的超越,最终达到‘无法’的境地。所谓无法’,并不是随心所欲,混乱无章,而是与自然之道合,达到通神的境界。”[5]149叶燮关于“法”的辩证解释与运用原则,无疑是由“法”通向“无法”的极具可行性的策略之一。叶燮批评李攀龙模拟乐府之作,改窜个别字句而以为己作,自以为得法,全然失却了诗歌创新的本质,是诗之末技。钱谦益、冯班等诗论家对此也多有批评。沈德潜强调,“古乐府声律,唐人已失。试看李太白所拟篇幅之短长,音节之高下,无一与古人合者,然自是乐府神理,非古诗也。明李于麟句摹字仿,并其不可句读者追从之,那得不受人讥弹?”[7]199不仅如此,沈德潜在诗歌韵律的认识上亦多发挥师说,于“法”的观点更与其师如出一辙。沈德潜认为,“法”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往见有明中叶,一二巨公倡导天下,谓作文当师先秦汉京,句取其拗,字取其僻,而先秦汉京之精神不存焉:其病在袭。于是诋諆其后者,救之以唐宋八家,以平坦矫其拗,显易矫其僻,而唐宋八家之精神不存焉:其病在庸。而诋諆者,又随其后。嗟乎!根本之不求,而面目形体之是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吾知相訾无已时也。夫文章之根本在弗畔乎道。根本既立,次言体、法。”[8]答滑苑祥书,1376沈德潜所谓“根本既立,次言体、法”,就是叶燮所说的“余之后法”,都是将“法”从七子派“守古而尺尺寸寸之”的位置上拉了下来,鼓励学诗者,从复古摹拟最终走向创新,从有法通向无法的境界。在此基础上,沈德潜还提出了“以意运法”的原则:
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如碛沙僧解《三体唐诗》之类。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着得死法?[7]188
沈德潜并不反对“法”,他认为诗歌当遵循一定的法度,也就是说,要汲取古人成功的经验,但又不可拘泥于古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以意运法”,这即是“活法”;若过分拘泥于古人的经验,以至于使自己的创作严格服从于法的规范和束缚,“以意从法”,这就窒息了创作的活力,就是“死法”。
五、结 语
明代七子派格调论的初衷是复兴古典审美理想,振拔时代风气,企图通过摹拟古人格调,从而上窥古人之意蕴。他们主张形式优先,使诗歌的意蕴处于字句、格律、章法、体格、声调等凝固的范式的规范之下,束缚了意蕴的创造和情感的自由表达,导致了诗歌创作的僵化和千篇一律,徒有对古人的摹仿,而不见古人之神理与精神,更遑论自己的性情、面目了。因此,这一派的诗学理论,并未深入诗歌的本质。至晚明受到了公安派的猛烈攻击,继而受到以钱谦益为首的虞山派诗论家的非难和指斥。叶燮则以精湛的理论建构,对以前后七子为核心的格调诗学进行了严厉批评,既针对当代诗坛复古模拟丧失性情与创造的现状,也具有站在文学史高度探索诗歌源流正变以及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自觉。叶燮将作为诗人性情、智慧、聪明、才辨等内容要素的载体的胸襟置于优先的地位,这为他的学生沈德潜继承发扬,并将其作为改造格调说的重要内容,使格调论诗学尊崇的重心逐渐转向了性情、意蕴与诗人主体;诗歌的思想内容是叶燮与沈德潜共同关注的话题,沈德潜力倡诗教,与叶燮宗经的立场如出一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充实了格调论的内容。针对七子派狭窄的师法取径,叶燮站在诗史发展观的立场上,对诗史源流作了高度的抽象和梳理,从理论高度消解了七子派“古体宗汉魏,近体法盛唐”等偏失。沈德潜则通过编辑诗选的方法推源溯流,将叶燮的理论吸收到新的格调诗说当中,极大地开拓了学诗者的眼界和师法取径的范围。对法的固守与变通也显示出七子派格调论与沈德潜格调论的区别,七子派固守古法窒息了诗人的创造力;叶燮虽然也重视“法”,但是同时主张将“法”尽量淡化,也就是“后法”;沈德潜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意从法”,契合了古人由“法”走向“无法”的诗学路径。此外,叶燮反对复古,针对诗坛模拟流弊,着眼于诗歌创新。沈德潜主张复古,针对诗坛萎弱诗风,强调继承优秀的传统。在根本上,这两种主张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一种优秀的诗作应当同时具备的质素:既能继承优秀的传统,又有生新独创的活力。他们的出发点是美学的和艺术的,尽管在具体的方法和取径上相背离甚至截然相反。沈德潜是格调说的集大成者,他的格调理论从晚明以来众多诗论家尤其是他的老师叶燮对七子派格调论的批评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而叶燮对七子派的批评,也在诸多方面为他的学生沈德潜推衍和发挥,成了清代中期格调诗论重要的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