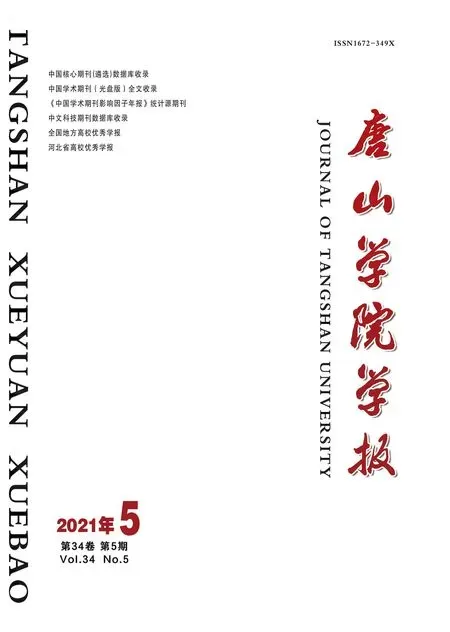论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
何琪琦
(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
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是审美主体基于对外物的感悟和体验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活动过程。在审美活动中,人首先通过感知审美对象获得最初的审美感受,然后在想象和情感的内在驱动下形成独特的审美体验。“观物取象”中的感知、比兴思维中的想象体验和情变所孕中的审美超越共同组成审美心理活动的一般过程。审美意象就是基于主体的审美经验和物我关系等从无到有而生成的,是“物我双向交流的产物”[1],会随着审美活动中物我双方的境遇不同而不断变化。因此,审美意象是动态生成的,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中包含着发展和变化。审美意象作为中国古典美学意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过程的突出特点是动态变化。从审美心理活动的动态性入手,分析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对于进一步揭示审美活动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一、观物取象:意象创构的基础
“观物取象”是从《周易》中演化而来的命题,最初并不是审美的概念。但是,随着对审美活动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观物取象”作为审美意象创构的基础,被赋予了重要的美学意义。古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402。其中,“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就点明了仰观俯察的观物之道,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则说明了主体基于物我关系的取象之道。在审美活动中,主体“观”物的特征、“取”物的精华,在“观”“取”之中将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象转化为符合主体内在审美需要的“象”,体现了“观物取象”在意象生成中的基础性作用。
“观物”是主体进行审美活动的前提,“观物”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心理过程。“观”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也是我们感知审美对象的主要方式。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观”不仅与视觉有关,也与听觉有关。在通过视觉感知审美对象的过程中,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关注方式和注意重心会受到来自物我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视觉审美对象自身的颜色、形状、大小及其与环境的对比度等物理属性;其二是审美主体自身的性别、审美经验及不同社会文化和成长背景下产生的审美追求等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因素。“视觉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它是有高度选择性的”[3],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视觉注意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调节机制,是以审美主体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审美经验与判断为基础的,会因为主体本身的心理调节和反馈的不同而不同。除了视觉,听觉也是审美活动中的一种重要感知方式。在先秦音乐史中,“观乐”的概念具有丰富的礼乐文化内涵。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观乐”逐渐涵盖了对音乐的感知和欣赏,具有了更加明晰的审美意味。“观乐”的过程也是动态的。音乐作为一种听觉审美对象,是一种流动的时间性艺术。声音在被截取的瞬间里只是没有意义的音节。在中国古代乐论中,乐有五声、六律,分别表示音程的长短和音调的高低。不同的音在一定的时间顺序中有序展开,不同的序列搭配表现出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内容。主体在听觉审美的过程中,通过连贯而又沉醉其中的欣赏获得整体的审美体验。总之,无论主体通过哪一种或哪几种感官进行审美感知活动,都遵循“观物”的基本规律。审美主体在“观物”中调动自身的注意力,耳听目遇,在仰观俯察的流动中直接感知审美对象,从而为创构出独具特色的审美意象提供基础。
审美主体由“观”而“取”。“取象”的过程是一个由客观物象生成符合内在审美需要的“象”的过程。“象”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作动词或名词使用。作动词使用的“象”,通常是指主体依靠一定的技巧手段创造特定的形象来模拟自然万物。就认识活动而言,求真是首要任务,即主体创造的“象”要符合自然物象的真实状态和形式。如《淮南子·原道训》中“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4],表达的就是民众通过“文身”模仿虫兽的形象,使自己被误认为是虫兽的同类,从而避免受到伤害的愿望。在这里,“象”的实用功能占据主要地位,具有明确的功利性和现实性,体现了人在面对现实挑战时的能动作用。这也体现了一种积极的天命观,其审美属性还处于潜在的不自觉状态。作名词使用的“象”,其含义比较丰富,既可以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所显示出来的现象,也可以指人类基于外在事物进行意识加工或创造的成果。在审美活动中所取之“象”,是主体基于对外物的“观”而进行选择性提取的结果。在审美活动中,处于审美状态下的主体在面对审美对象,尤其是未经艺术家精心创作的形象时,往往会忽略其中有碍审美的属性。比如人们在欣赏雪景时所感受到的,往往是世界一片银装素裹、粉妆玉砌的直观形象,而忽略道旁被泥浆染污又将化未化的残雪。“取象”就是主体基于内在的审美需要,忽略雪景里无益于审美的属性,在“观”中获得“银装素裹”的眼中之“象”。在这个过程中,审美主体接受并改造了客观物象,在形成眼中之“象”的同时,获得愉悦的审美感受和体验。
“取象”建立在“观物”的基础上,审美主体所取之“象”是具有感性意味的“象”。宗炳在绘画意象的创构原理中提出“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5],“应目会心”的内在逻辑关系与“观物取象”是一致的。“应目”指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通过感官直接把握生动具体的自然物象,“会心”则指由这些感性形象所引起的审美主体内在的心理反应,物象与内心相契,目遇而神合。此时,头脑中出现的“象”已经被审美主体自身的审美经验和偏好赋予了不一样的审美情感和趣味,已不再是客观物象的原貌了,而是具有感性形态的审美的形象。《乐记》中也有“乐象”的说法:“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6]30心动就是主体内在的思想活动。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心动就是情动。“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6]1外物作用于心,心应物而动,于是“情动于中,故形于声”[6]3。所以,“声”作为情感的外在表现,在时间的流动中同时呈现为“乐”,而审美主体在“观乐”的基础上,体察“声”所内蕴的思想情感,形成具有不同情感特征的乐象。
“取象”蕴含着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基于物、又不滞于物的超越意识。阿恩海姆提出“视觉思维”理论,将感知与思维联系起来,强调“积极的选择是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7]。主体通过“观”物的基本特征,从而“取”物的审美属性,获得物的直观形象,形成符合内在审美需要的眼中之“象”。《周易·系辞上》记载:“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384主体面对纷繁错杂的事物时,能够通过对自然物象的观察模拟和抽象总结,突破繁杂的表象,激发内在的审美体验,并用“象”来形容和表达。这反映出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基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考和体悟,而产生独特审美体验的心理过程。
总之,主体在“观物取象”中所取之“象”,是基于内在审美需要而对自然物象进行选择性提取的结果,是审美活动展开的前提。主体在“观物”中的心理调节体现了意象动态生成的过程性特征。主体基于“观物”所取之“象”,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创造的审美的“象”。“取象”是主体基于自身的审美经验和判断,选择和提取审美对象中有益于审美的属性。“取象”的过程体现了审美主体在意象生成中对于物的超越意识。“观物取象”作为意象创构的基础,与审美主体的心理活动息息相关,具有动态性和过程性特征。
二、比兴思维:物我交融的方式
中国古人讨论诗歌时常提及的“比”“兴”不仅是诗歌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审美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述。比兴思维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物感观念。《周礼注疏》中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8]。“比”是一种比拟,主体通过“比”将此物与彼物联系起来,用物来打比方。“兴”是一种隐喻,借物起兴,目的在于寄托主体的思想和情感。比兴思维在审美想象的作用下实现物我交互,四时万物在激发人的情感的同时,又成为情感的寄托,物我相照,贯通交融。在审美意象生成的过程中,物我相照而情动于中的现象,就源自感物而发、比兴起情的内在思维过程。
比兴思维不同于理性判断,比兴是遵循“类”的规律和原则,实现物与物、情与物的联结。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都可起兴,任何一物都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联系到他物,起兴之物象和所咏之物象两者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类”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比兴思维中有两方面的体现。其一,主体基于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感知,将此物与彼物联系在一起,此为以物喻物的基础。孔颖达在对“兴”的解释中就提到:“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9]强调“兴”作为一种比喻的手法,将物与物、情与物联系起来以实现主体情意的表达。其二,两个事物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巨大,但是都具有能够与主体的某种情意产生共鸣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将物与情联系起来的关键,也是“取譬引类”与以类比逻辑为特征的理性思维之间的重要区别。如作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形貌上相去甚远,并没有相似性特征。但是,由于松树岁寒不凋、翠竹经冬不衰、梅花凌寒独放,三者共同拥有的耐寒属性与主体高洁坚韧的情志产生共鸣,因此使其成为人们联类讴歌、表情达意的对象。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基于比兴思维展开的类比联想,是审美意象动态生成的一种表现。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认识传统,在这个浑然为一的系统之中,物与物、物与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强调彼此间的互相感应、转换与影响。如人的身体可以作为外在的形象产生隐喻,内在的自我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精神和理想联类无穷。事物在这种浑然的相互关系中变化流转、生生不息,从而促进了审美活动中的物我交融。
比兴思维是审美主体实现物我贯通的方式,与审美意象生成息息相关。“圣人立象以尽意”[2]396,“立象尽意”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象来更好地表达难以被言语穷尽的情意,“立象”是实现“尽意”的手段与方法。在审美活动中,“立象尽意”与比兴思维密切相关。“立象”是一个以客观现实为基础的创构过程,先有“意”,后有“象”,“意”决定着“象”的选择。审美主体在选择“象”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的审美经验和判断,对众多的“象”进行比较挑选,通过比兴思维找出适宜于“尽意”的形象。这个过程包含了联想、想象、象征和隐喻。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也着重阐释了比兴对意象生成的意义:“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10]主体面对感性直观的自然物象,因为由物所感发的情意难以被言语穷尽,于是以物拟心,通过比兴思维选择具有类似特征的具体物象,取象比类,起兴寓情,从而表达自身的情意,达到“尽意”的效果。客观具体的自然物象在表达主观情意的同时,也由于主体赋予的情意而成为审美的感性形态。这也意味着物我双方在审美活动中超越了自身的限制,在有限的时空当中,实现了以少总多、以有限呈现无限。
想象力作为比兴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使审美意象的创构和生成更加充满生机。审美意象的生成伴随着主体的审美想象而展开,审美主体借助想象将自己的情思融入物象中。在审美活动中,想象可以基于比兴思维“类”的特性,依据当下的审美情景和主体的审美经验充分调动不在眼前的形象。只有在各种具有相似特征、又各不相同的形象的协助下,既有的物象才有可能契合于审美主体复杂而又多变的情思。主体内在的审美心理活动是通过各种感性的、直觉的思维来完成的。萧子显提出“感召无象,变化不穷”[11],也体现了审美活动中想象力的积极作用。事物变化流转,在审美主体感性的想象之中转化为生动、鲜活的图画,呈现在脑海里,“象”无定式,联类无穷。联想、想象是主体保持心灵与外物相契合的思维手段。审美主体只有在想象力的作用下充分调动自身丰富的审美经验,才有可能做到物我之间的充分交流。为了强调想象力在意象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刘勰将其简约概括为审美心理的首要因素:“神思”[12]493。
“神思”是审美主体的艺术想象,是带有创造性特点的审美心理活动。“神思”的心理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总是带有主体丰富多样的心理记忆和经验积累等因素。“神思”中的形象往往是伴随着情感体验而出现的,并且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13]36。事物的形象在审美想象的思绪中翻涌变换,彼时彼地的经验汇聚于此刻,在主体的审美心理中交融激荡,往来神通。刘勰强调“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12]493,就是审美过程中的思维状态,审美主体通过想象与外物相接,心由外物感发,而外物随心游动。这是一种共同突破时空桎梏、往来无极的心理活动。在“神思”中,审美主体与现实生活物象进入一种物我交融的状态,兴会、神到,由神到而意到[14]。审美意象是主体审美心理活动过程中的产物。主体想象和联想的心理活动体现了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会随着物我关系的变动而变动,从而形成审美意象的无限丰富性。
总之,主体在审美意象生成的过程中,遵循比兴思维下“类”的原则,将物与物、情与物联系在一起。审美主体的情意在外物的感召下涌动而出,但又难以言传,于是反照于物,以物为情感的寄托。在审美活动中,比兴思维将物我相联,同时焕发主体情意,以推动物我交融的审美体验的产生。在审美意象生成的过程中,比兴思维需要借助想象力的作用。“神思”作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特点的艺术想象,是审美意象生成中促进物我联结贯通的方式。
三、情变所孕:意象创构的动力
情感为审美意象创构提供内在的驱动力。艺术在于激发美感、表达情意,正如克罗齐所说“诗是情感的语言”[15]。情感是审美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尤其是在写景抒情的作品创作和赏析过程中,往往带有鲜明的以己度物的情感特征。刘勰高度重视情感在“神思”中的作用,认为“情”是“神思”产生的动因。“神用象通,情变所孕”[12]495,在强调“神思”需要在“象”的作用下才能得到贯通的同时,也点明了“神思”是在情感的发展变化中产生的。所谓“孕”,是指意象随着审美主体的心理活动变化而动态生成。
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涌动焕发的情感,为物我双方交互往来提供内在动力。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里提出“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12]136。其中,“情以物兴”就是指审美主体在具体审美对象的感发中,通过比兴思维产生联想,进而触发情感并激活内在的审美体验。“物以情观”则指静态而客观的自然物象感染了具有主体审美理想和情感态度的个性化色彩,成为主体情意的寄托。主体感于物而动于情,在由外物感发情意的同时,也在审美主体的实践活动中赋予外物情感寄托,从而实现对外物的改造和提升。如同童庆炳在对“物以情观”进行阐释分析时所强调的那样,物我双方齐驱争锋,既避免了仅仅以心为主而流于荒诞,也避免了仅仅以物为主而陷入简单复制,缺乏突破和创新的现象[16]。在比兴思维下焕发的主体情意,在为外物赋情的同时,也为主体在审美活动中进入物我交融的状态提供驱动力。
在审美活动中,强调审美意象以情为本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物象的重要性。在审美领域里,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万物会以自身的感性形态,与主体丰富多变的情感相呼应。陆机在《文赋》中谈到“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13]36,说明情与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主体的情思随着审美的心理活动而逐渐鲜明,联类无穷的形象也在与情感的相互作用下逐渐清晰。对于物象在审美活动中重要意义的分析,钱钟书强调:“否则先入为主,吾心一执,不见物态万殊。……我既有障,物遂失真,同感沦于幻觉。”[17]也就是说,如果执成见而强物,物反而会离我而去,物的多样性也会被单一性所取代。这同时也暗示了审美意象结构的生成与变动须以主体情感的构造能力来实现,而主体情感构造能力的差异、发展及变化将进一步推动审美意象的动态生成。情感体验要借助于“象”才能够更好地显现出审美主体自我生命的价值,而客观物象也会因为主体的认识、体验、欣赏和创造呈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审美意象就是物我双方在审美活动中物我交融、情景合一的结晶,是“神与物游”的产物。
审美意象的动态生成中,“意”与“情”联系密切。在审美活动中,“意”不仅能影响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情感倾向,而且也能为意象生成注入具有主体情感特征的审美内涵。朱熹说:“如爱那物是情,所以去爱那物是意。”[18]这就鲜明地指出了情感是审美活动的内在驱动力,而“意”则为审美活动提供了方向性指引。此外王夫之也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19]“寓意则灵”是在强调审美活动中“意”的重要地位。审美活动中,四时万物与主体交互往来的生命力量,源于蕴含主体情感特征的“意”。自然物象感发主体情意,审美主体在耳听目遇的静观感悟中,以“情”为动力,以“意”为指引,架构起物我之间良好的情感交流结构。同时,在意象生成的过程中,具有主体情感特征的审美内涵赋予自然物象以灵动的生命力,寓情于物、感物动人,为物我神合交融提供可能。
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是动态的,但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看,意象一旦生成就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审美活动中审美对象对主体情意的感发不仅与自身属性有关,更与关于审美对象的描写、创造和表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蕴涵与隐喻作用有关。陈植锷在《诗歌意象论》一书中说:“从符号美学的角度看,像这类在特定的生活场景中反复出现并因此引发出某种固定情绪和习惯性联想的程式化意象,乃是一种人类情感诉诸艺术形象而形成的‘客观关系’或‘现成用语’。”[20]也就是说审美意象虽然是在不断地变动而丰富着的,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主体的生命情感体验与时代环境及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由此形成了一些具有特定情感内涵的审美意象群。这些意象群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时代中流转,生生不息,在人们的审美意识中积淀下来,并且能够激起大多数人底色一致的情怀和感受。如松林明月、青竹红梅、落花流水等审美对象,经过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最终演化为具有相对稳定意象底蕴的文化因子,并鲜明地体现出不同时期的审美观照,具有稳定的历史延续性。意象作为无数同类经验心理的凝聚物,在人类心理历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淀在人类意识深处,附着于大脑的组织结构中,成为人们用于表达审美情感与体验、建构主体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
四、结语
审美意象的创构,从“观物取象”到比兴思维下的物我交融,直至主体在审美活动中获得情感的愉悦和满足,都体现了意象生成的动态性。“观物取象”作为意象创构的前提,为审美活动的开展提供基础。物我在“观”和“取”中发生联系,而比兴思维和想象力则是物我交融贯通的关键。主体的审美情感在外物的感召之下得到焕发,同时又以外物为寄托。审美活动中的物我关系在情感的驱动下,突破时空的限制,并最终激发主体神与物游的审美体验。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是一种审美主体基于自身审美经验,在具体审美情景下涌动的内在的心理活动过程。随着历史文化的演进,意象的内涵被不断深化,随着个体生命体验和历史文化的发展而演化,并保持相对的完整性和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