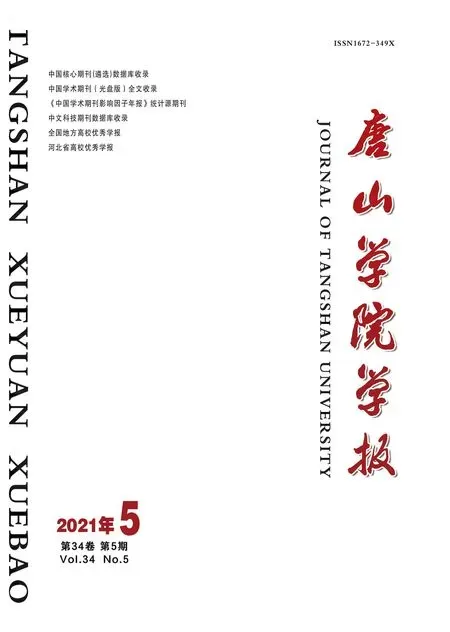论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
赵书昭
(天津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57)
鸦片战争之后,进入工业时代的西方文化与仍然停留在农耕时代的东方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冲突,并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着交流与融合。两个具有明显“代差”的文明孰优孰劣、谁才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爆发的“东西文化论战”的争论焦点。这场论战几乎贯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体现了中国文化精英在民族和文化双重危机之下的寻路与彷徨、理性与焦虑、自信与自卑。论战各方包括: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蔡元培和吴虞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以辜鸿铭、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为代表的“学衡派”,以章炳麟、邓实和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派”等。五四后期的“科玄论战”发生之后,又分为以胡适、丁文江、吴稚晖为首的“科学派”和以梁启超、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玄学派”,以及以陈独秀、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在论战立场和观点上,有的学者立场笃定,有的则摇摆不定,有的主张全盘西化,有的主张复兴儒学,亦有人主张东西调和,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李大钊是五四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也曾参与了早期的文化论战,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西文化观。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人思想发展阶段的局限,其早期文化观当中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然而,当李大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之后,其东西文化观逐渐克服了早期的缺陷和不足,实现了质的发展变化。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东西文化论战首先从陈独秀和杜亚泉之间爆发,也引发了思想界持续而广泛的争鸣。与此同时,李大钊也悄然加入了这场著名的文化论战。虽然他并没有像陈独秀那样采用公开论战的方式,但也相继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新的!旧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和《新旧思潮之激战》等文章,展现了他颇具特色的早期东西文化观。
(一)承认“西强东弱”的现实,提出“以西济东”之策,但不盲从全盘西化思潮
首先,作为“新文化派”的重要成员,李大钊不仅承认“西强东弱”的事实,而且也指出了“以西济东”的必要性。李大钊一直对中国的封建礼教、官场积弊和社会风气痛心疾首。“文化不如人”而导致国家民族衰败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共识,即所谓“东洋文明之地位,已处于屈败之势”。李大钊认为,西洋文明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相比于东洋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1]216。所以,他提出“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的观点。这说明李大钊对“西强东弱”事实的认识是清醒的。他认识到了西洋文明在物质、科技和创新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并且意识到中国必须弥补这一差距。他虽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绝不孤芳自赏,而是以积极的姿态对待外来优秀文化。
其次,李大钊并未盲从于全盘西化思潮。虽然均身处“新文化派”阵营,但李大钊并未盲从于陈独秀、胡适等人所提倡的全盘西化思潮。陈独秀认为东西文化本质迥异,势如冰火,不可调和。他认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2]175同时,陈独秀认为中国文化太过落伍,与西方文化相比已经处于“望尘莫及”的地位,中国已经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股强劲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于涤荡纲常礼教等腐朽文化无疑具有重大进步意义,但也容易导致文化自卑和文化虚无主义,甚至丧失精神家园。相比之下,李大钊则显得更加客观和理性。他也曾推崇过英美的民主宪政制度,但却留有余地,指出“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3]158。同时,他也看到了西洋文明存在“创造发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深问题者”的缺点。事实上,这种认识与杜亚泉、梁启超等人颇为相似,大家认为西洋文明是物质文明,西方人都在拼命地追求物质财富,而忽略了人的心灵建设。
再次,李大钊在东西文化评价上持谨慎的态度,并不妄论高下。他指出:“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1]213他认为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好似“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1]214。可见,李大钊既认识到了东西文化存在差距的现实,主张学习西洋文明的优点,但又能看到东西文化互有长短,这种不偏不倚、理性冷静的态度在当时实为难能可贵。
(二)在集体文化自卑的大氛围下坚持文化自信,但不赞同复兴儒学的复古路线
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酣畅淋漓地批判旧文化和旧道德,极力推崇以法兰西文明为代表的新文化和新道德,一时间拥趸众多,风光无两,成为当时的主流性思潮。然而,热烈高扬西方文化、猛烈贬低中国固有文化的全盘西化思潮,也使整个中国文化界陷入一种集体性文化自卑之中,易使国人丧失精神家园和民族认同感,沦为精神上的流浪者。相反,“东方文化派”的成员大多学贯中西,他们并不排斥西学,但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在文化自卑的大氛围下保持着一份可贵的文化自信。在此方面,身处“新文化派”阵营的李大钊却与“东方文化派”心有灵犀。他在称赞辜鸿铭先生时指出:“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1]219这种惺惺相惜应是源于李、辜二人对中国文化的深深眷恋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当然,李大钊的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建立在强烈的民族情感之上,更源于对中华文化精髓的深刻认知。他指出中国文化具备“容人并存的雅量”和“自信独守的坚操”两种优秀品质,并认为中国文化必然能够走向复兴。事实上,这种文化自信并不是李大钊的一厢情愿,而是中华文化从来就是一种极具开放性和创新性的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和开拓未来的磅礴力量。五千年来,中华文化不断吸收优秀外来文化因子,使自身不断得到滋养和发展,又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核”,恰恰体现了“容人并存的雅量”和“自信独守的坚操”的高度统一。正是基于这种深刻认识,李大钊才有底气发出“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的强烈呼声[1]215。当然,在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上,李大钊既不盲目跟风全盘西化思潮,也不赞同复兴儒学的复古路线。针对北洋政府《天坛草案》中写入“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倒行逆施之举,李大钊愤然撰文进行批判。他指出:“苟有匿身于偶像之下,以圣人之虚声劫持吾人之思想自由者,吾人当知其祸视以皇帝之权威侵害吾人身体为尤烈,吾人对之与以其反抗之决心与实力,亦当视征伐皇帝之役为尤勇也。”[3]229虽然,李大钊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以及儒学的内在价值,但他并不赞同“东方文化派”寄希望于儒学的复兴来拯救国家的观点。此时,他已经将目光投向了融合东西文化优秀因子的“第三种文明”。
(三)强调东西文明的调和性,认为中华民族应承担起开拓世界文化格局的重任
陈独秀认为东西文明严重对立并且不可调和,主张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固有文化,颇有一种“文化替代论”的味道。李大钊则以“文化融通论”取代了“文化替代论”,强调东西文明的调和性,认为代表东西文明的新旧思潮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另外,杜亚泉、梁启超和章士钊等人也持调和论的态度,并主张以中华文化的精髓救济西方文化之弊。但是,无论是“替代论”还是“调和论”,都忽略了创新的因素,而李大钊恰恰弥补了这一点。他指出东西文明需要“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1]214。所谓“第三种文明”是经过东西文明取长补短之后创造出来的崭新文明,这自然比杜亚泉所认为的“文明之发生,常由于因袭而不由于创作”[4]346的观点要进步很多。同时,李大钊指明了中华民族在开拓世界文化新局面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说:“作为亚洲文化中心的中华民族对于此等世界的责任,有所觉悟,有所努力”[1]223,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亚洲文化的中心,应该担负起东西文化融通和开拓世界文化新局面的重任。
(四)视“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将目光从欧洲转移到了俄罗斯,从民主主义转移到了马克思主义。巴黎和会以及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使李大钊愈发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的虚伪本质。在东西文化论战之初,李大钊就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文明优越于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从而提出了“第三种文明”的独特观点。同时,他明确地将俄罗斯文明视为“第三种文明”。在他看来,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在文化上兼具东西文明之长,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已经建立了苏维埃人民政权,已经打破了宗教神权和封建专制,将权力归于人民,实现了真正的人道和自由,具备了社会主义文明的雏形。所以,李大钊高度评价俄罗斯文明。他高呼:“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1]227当然,我们不能将李大钊简单地视为一个俄罗斯文明的崇拜者,他坚信社会主义文明同样能够降临中国大地并结出繁花硕果。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与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之间爆发了“社会主义论战”。李大钊也撰写了大量文章来证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他说:“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5]255可见,李大钊绝不是一个仰慕他国文明的临渊羡鱼者,而是一位始终抱有坚定文化自信为中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懈奋斗的实干家。同时,在论战各派为“东西文明孰优孰劣”争论不休的时候,李大钊能够跳出文化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束缚,将社会主义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其远见卓识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所罕见。
二
如前所述,李大钊早期的东西文化观确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受时代和个人思想发展阶段的局限,亦存在某些不足。发现这些不足,不是为了在先驱者身上吹毛求疵,而是为了将李大钊东西文化观发展的前后变化进行整体性研究,以使其更加全面、立体、饱满地呈现出来,让我们从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
(一)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存在固有缺陷
进化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当时在中国较为流行的两大学说,也是李大钊认识东西文化的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然而,这两种理论都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将地理环境因素视为文化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是不科学的。从根本上讲,地理环境因素只属于社会生产力的部分内容,无法用它解释思想文化产生的全部机制。其次,一种文化的发展还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比如,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交流与融合早已成为文化发展的常态,世界上的许多文明都是不同文明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果,但这种现象却很难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说明。再次,地理环境决定论容易导致“种族优越论”的产生。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认为希腊的地理环境因素决定了希腊人的优秀品质,使其具备了统治其他民族的资格。可见,这种论调很容易为殖民侵略张目。李大钊批评说:“欧美人对于东洋民族多以为劣等国民,偶或见其长处则直惊以为黄祸,其真倾耳于东洋人之言论者极少。”[1]218同时,李大钊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很深。他曾运用进化论分析道德的起源,并认为道德是社会的本能,这种本能不是人类所特有的,乃是动物界所共有的。很显然,进化论容易把人类道德与动物本能混为一谈,模糊二者的边界,无视二者的本质区别。或者说,从生物学和遗传学去解释文化现象势必造成缘木求鱼的后果,不可能获得科学的结论。当然,随着李大钊成为一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便不再奉这些学说为圭臬了。
(二)对文化差异和文化差距的区分不够
所谓文化差异是由文化自身特色产生的,体现的是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不反映文化的优劣高下。所谓文化差距是指文化发达程度的差别,体现的是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一般而言,文化差异与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紧密相关,而文化差距与文化的时代性紧密相关。当然,文化差异和文化差距之间也存在紧密的联系。但是,东西文化论战时期,思想界并未能对此进行严格区分,因而造成了一定的混淆。陈独秀曾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实利、感情和虚文为本位”[2]35-37。这样的对比,表面上看是在讲文化差异,但实质是在讲文化差距。李大钊则指出东西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这些是在讲文化差异,突出的是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但是,“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1]211-212,这些则是在讲文化差距,突出的是文化的时代性特征。遗憾的是,李大钊、陈独秀并未将文化差异和文化差距进行严格区分,而是混在一起讲的。在同样的问题上,“东方文化派”并没有比“新文化派”更高明。杜亚泉认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4]338显然,这种只承认东西文化差异而完全无视两种文化巨大差距的观点是不客观的。
(三)未能摆脱“东静西动论”的窠臼
中国哲学上的“动静之辩”始于先秦诸子时代。儒释道三教合流之后,“动与静”便不再呈现出明显的学派之争,而是作为文化的基因传承下来。但是,“动静之辩”却成为东西文化论战时的重要观点。1916年,杜亚泉发表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拉开了东西文化论战的大幕。1917年4月,李大钊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中亦指出:“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1]961918年夏,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继续以“东静西动”作为比较东西文明的总观点。当时,“东静西动论”非常流行,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也反映了一定的客观事实。但是,受时代的局限,当时的知识精英无法从社会制度和阶级性质上来认识东西文明的本质性差异,更多的是在两种文明的外在表象上徘徊。事实上,“东静西动”只是在具体条件下有限地成立,不是亘古不变的常理。东方文明中也包含丰富的“动”的思想,比如儒家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等。西方文明中也包含丰富的“静”的因素。因此,笼统地认为“东静西动”是不够严谨的。客观地讲,“东静西动论”给人一种直观性和生动性,缺点就是容易让人陷入一种刻板印象,造成对东西文明认识的固化。
(四)缺少对东西文化融通的有力论证
在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寻找东西文化融通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路径,旨在使两种文化达成一种和解。当时,东西文化融通论在中日学者当中颇有市场。日本学者北聆吉、金子马治和茅山原华,中国学者杜亚泉、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和李大钊,都曾提出过东西文化调和融通的观点。但就当时而言,东西文化的冲突和对抗是主流,也最具现实性,而文化融通则显得有些曲高和寡。大家对东西文化融通的态度多是一种心理期待,缺乏有力的论证。梁漱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大家的意思要将东西方文化调和融通,另开一种局面作为世界的新文化,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确切的论断。像这样糊涂、疲缓、不真切的态度全然不对。”他又说:“如要调和融通总须说出可以调和融通之道。”[6]当然,我们不能对李大钊等知识精英过于苛刻,遍看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也没有哪位学者对文化融通能否实现给予有力的回答。因为,纸上谈兵终究不能代替实践检验。然而,暂时缺乏对文化融通的有力论证,并不代表它是一个伪命题。文化融通必须要经历文化间的冲突和碰撞,特别是长期的交流与融合才能实现。文化融通的过程既有文化间取长补短的现实需求,更离不开具有高度文化自觉自信的行为主体的积极推动。总之,文化融通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也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实践过程。
三
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开始将目光转向俄罗斯和马克思主义。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后,他基本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当时最具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知识精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李大钊逐步克服了其早期东西文化观的缺陷和不足,实现了质的发展与飞跃。
(一)科学分析了东西文明产生“古今之别”的真正原因,逐渐摆脱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
历史证明,东西文明的交锋更多体现在时代性上,也就是封建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抗衡。陈独秀就明确地将中国、印度等东方文明称为“古代文明”,而将西方文明称为“近世文明”[2]136。这就是“新文化派”所指出的东西文明的“古今之别”。但是,对于东西文明巨大“代差”的成因,论战各派却各执其辞。李大钊最早坚持地理环境决定论,根据地理位置和太阳光照的不同将世界分为“南道文明”和“北道文明”。东方各国为“南道文明”,自然禀赋优越,故而成为以农业为主的定居民族。相比之下,西方各国为“北道文明”,“自然之赐予甚乏,不能不转徙移动,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1]212,属于非定居的迁徙性民族。这种分析与杜亚泉所说的“西洋社会发达于地中海岸之河口及半岛间,交通便利,宜于商业……吾国社会,发达于大陆内地之黄河沿岸,土地沃衍,宜于农业”[4]339的观点颇为相近。运用地理环境学说进行解释,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终究不得要领。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李大钊找到了答案。他指出:“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升华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5]146可见,李大钊认识到了儒学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已经不能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更无法指望依靠复兴儒学来实现民族复兴。同时,他也认识到了东方文明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就在于东西文明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差距。他认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5]147由此可见,李大钊已经能够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来科学地解释东西文明的“古今之别”了。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日臻成熟,李大钊逐渐摆脱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
(二)准确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因,彻底走出“东静西动论”的泥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空前,西方文明几乎在大战中自毁,人们也开始对这场战争的爆发原因进行反思。但是,大多数人依然是从“东静西动论”的陈词滥调中去寻找答案。杜亚泉是“东静西动论”的倡导者,他认为西洋社会“无时不在战争之中,其间之和平时期,乃为战争后之修养时期……战争为常态,和平为变态也”[4]340。李大钊也曾经深受“东静西动论”的影响。他看到了西洋文明“在物质的机械的生活之中,纷忙竞争,创作发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又言“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1]216。此时,李大钊强调了西洋文明的优势,却也看到了其弊端。然而,这种脱胎于“东静西动论”的观点终归不能深入问题的本质。除从文明属性进行分析外,学者们也没有放弃从社会现实来分析大战的成因。杜亚泉就指出这场大战实际受各国资产阶级所操纵。他说:“经济界中,已形成一种阶级,经济上势力,全操纵于少数阶级之手,国家民族间之经济竞争,实不过少数阶级间之阶级竞争。”“多数民众为少数阶级所驱策,投身于炮火兵刃之地,创巨痛深。”[4]348应该说,杜亚泉的认识颇有见地,遗憾的是浅尝辄止,未能再进一步。面对战后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杜氏不以为然,不仅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各取所需”和“均贫富”,更是将之与王安石变法混为一谈。相比之下,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则明显高人一筹。他鲜明地指出:“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为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1]255这说明李大钊已经成功地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来分析大战成因了。除此之外,他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大战中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素,并高呼大战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认为不应该为哪一国或者哪一国里的哪些人庆祝,而“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1]259。这说明,他不仅超越了当时“公理战胜强权”的庸俗性论调,更是彻底走出了“东静西动论”的泥淖,并公开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全世界劳苦大众、为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鼓与呼。
(三)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秘密,深化了对西方文明现代性的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意志、俄罗斯、土耳其、奥匈帝国四大帝国解体,英法等国亦深受重创,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高涨。为了应对尖锐的社会矛盾,西方各国纷纷调整政策。英国学者罗素开始大力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战后欧洲的工人运动迫使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一定的妥协,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欧洲思想界开始了对西方文明现代性的集体反思。他们开始批评“科学主义”,曾经盛极一时的“科学万能论”失去了市场。正如梁启超所言:“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7]18受此影响,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东西文明的反思,大有西方文明繁华落幕之后转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势头。而且,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并非仅仅停留在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上,也触及了社会制度层面。面对战后欧洲的凄凉状况和人民大众的悲惨境遇,梁启超看到了这是剥削的罪恶。他指出,欧洲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工人所得的工钱,彀吃不彀穿,彀穿不彀住”。除此之外,他也控诉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赤裸裸的剥削,并以工人的口吻控诉道:“你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绞着我的汗,添你的油,挖我的疮,长你的肉。”[7]12面对西方文明的弊端,“东方文化派”的主张就是“以东济西”。梁启超信誓旦旦地说:“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7]52但是,他对资本主义剥削现象的认识却未能深入本质,除了基于正义感的道德控诉之外,一不能揭示剥削的秘密,二不能拿出彻底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李大钊则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秘密。他指出:“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5]38。同时,李大钊认识的深刻之处在于不纠缠于对资本家的道德控诉,而是上升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认识。基于此,他更加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
总之,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不是简单依靠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提升道德水准就能解决的。学者们以东方文明这剂“药方”来救治西方文明“痼疾”的企图,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也是对西方文明现代性反思的局限所在。事实证明,只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才能真正破解西方文明的“死结”,才能彻底地实现对西方文明现代性的反思,才是人类对自身前途命运的最大觉悟。
(四)纠正了文化救国的片面路线,坚持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为中国文化复兴开辟道路
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企图通过文化救国的路子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进而实现民族振兴,“文化兴则民族兴”是他们的思想逻辑。但是,东西文化论战最大的弊端就在于空谈者多、实干者少。文化救国说到底依然是社会改良的路线,大家总是企图在成本最小的前提下,在不触动旧中国社会根基的前提下,通过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来实现国家自强和民族振兴。但是,事实是残酷的!李大钊相比于其他文化精英从来不满足于坐而论道。“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是他的真实写照。他不屑纠结于口水战,而是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进步团体,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运动,促成国共合作,不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最终,他认定中国人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曲折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他彻底抛弃了文化救国的片面路线,在与胡适的论战中提出了“根本解决”的路子,也就是要彻底地进行社会革命。他认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5]6也就是说,只有完全彻底地对旧中国进行改造,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才能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开辟道路。因为,社会改良必须以良性社会制度为前提,如果宏观社会制度和环境是好的,就必须维护和坚持,在微观上进行优化和调整,实现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相反,如果社会制度根本上是腐朽的、黑暗的,阻碍一切进步力量的成长,就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来推翻它,创造一片新天地,才能为后续的社会改良提供可能。正如李大钊所说:“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1]266纵观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来、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历史,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四个伟大成就”就是先进行社会革命,谋求一个“根本解决”,然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无数革命先驱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
回首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历史,我们早已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然而,目前西方国家在经济、金融、军事、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仍然占据较大优势。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依然拥有一定市场,并不断干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回望李大钊同志东西文化观的发展和演进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以及它扎根中国大地后迸发出来的历史伟力。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始终不忘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才不会失去前行的动力。只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才不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和方向。只有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才能最终获得事业的成功。唯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才能确保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让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同向共进,梦想成真。届时,我们足可以告慰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回答他们的百年之问,为东西文化论战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诚然,李大钊同志所期盼的“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的历史夙愿也必然能够实现。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朱文通研究员曾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