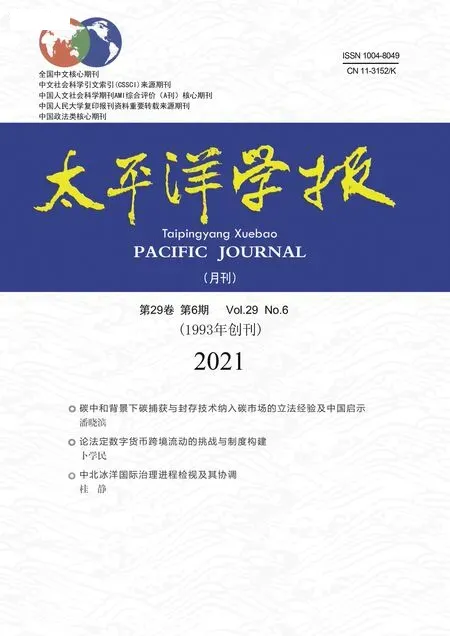“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研究
游启明
(1.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316002)
21世纪正见证“一个更加注重和依赖海上合作与发展的时代”①“‘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新华网,2021年4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6/20/c_1121176798.htm。的到来,各国积极面向海洋寻找发展机遇。在占地球面积近71%的海洋中,有约64%的部分属于公域。鉴于全球海洋公域所占面积之广,合理评估其治理态势,明确设定治理原则,理性出台治理政策,既应该成为各国善用全球海洋公域的题中之义,也是学者需要密切关注的研究课题。下文在对全球海洋公域进行理论解析后,将分析全球海洋公域在治理需求、治理供给以及治理价值导向等方面的发展态势,探讨治理全球海洋公域应遵循的规范原则,并给出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政策建议。
一、理论视野下的全球海洋公域
作为人类所涉猎的第一个公域,全球海洋公域既是全球公域的组成部分之一,具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产权归属和利用方面存在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鲜明特征,还在生态、经济以及安全等方面发挥着正向作用。
1.1 全球海洋公域的内涵与外延
全球海洋公域是全球公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全球公域指“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由人类共享的地球区域”,①韩雪晴、王义桅:“全球公域:思想渊源、概念谱系与学术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88页。王明锁:“论无主物与其所有权归属——所有权原始取得方法之先占”,《学习论坛》,2014年第5期,第74-76页。或指“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外为全人类利益所系的公共空间”。②杨昊:“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公域治理”,《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3期,第56页。
学者对全球公域的具体构成存有争论。巴里·波森(Barry R.Posen)认为,全球公域由相关海域、国际领空和太空组成;③Barry R.Posen,“Command of the Commons:The Foundation of U.S.Hegemon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1,2003,pp.5-8.任琳则将相关海域、网络、太空、极地视作全球公域的组成要素;④任琳:“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第114-128页。郑英琴认为相关海域、太空、极地构成了全球公域;⑤郑英琴:“全球公域的内涵、伦理困境与行为逻辑”,《国际展望》,2017年第3期,第99-115页。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存在战略性与环境性两大不同类型的全球公域:前者包括网络、相关海域、太空、极地,后者包含水资源和气候变化。⑥[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洪漫译:《战略远见与美国全球权力危机》,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第144页。
总结上述论述可以发现,不管对全球公域的具体外延存有何种分歧,学者都将相关海域无可争议的纳入其中。具体言之,全球海洋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而为全人类所有的海域及其所包含的资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指出,全球海洋公域包括公海与海底两部分:前者包含“专属经济区、领海或群岛国群岛水域之外的水体”;海底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⑦Theodore Okonkwo,谢红月:“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公域管理”,《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51页。
1.2 全球海洋公域的特征
全球海洋公域在产权归属和使用方面存在鲜明特点,使其区别于私有物、无主物和纯粹公共产品,成为一种“公共池塘资源”。
首先,产权的无主权归属性。全球海洋公域是人类共有物,任何实体都不能独占其所有权。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指出,任何国家都不能声称对公海享有独占权,它是人类共有物。⑧[荷]雨果·格劳秀斯著,马忠发译:《论海洋自由或荷兰 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9页。联合国大会颁布的《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与下层土壤之原则宣言》规定,国际海底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任何国家都不对其享有主权。⑨“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与下层土壤之原则宣言”, 载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海洋法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6-119页。这种产权的无归属性使全球海洋公域区别于私有物,因为后者具有明确的产权归属。
其次,利用的非排他性。“全球海洋公域向所有人开放,所有人都能利用它所蕴含的资源”,⑩Carlar P.Freeman,“The Fragile Global Commons in a World in Transition,”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6,No.1,2016,p.17.任何国家都不得被排斥在外。该特性加上产权的无归属性使全球海洋公域区别于无主物。无主物也具有无主权归属性,强调产权不为任何个人与组织所有,但对它的实际利用则遵循“谁占领谁拥有”原则,允许通过占有来对其进行产权分割,而一旦分割后占有者就能排他地利用无主物,使其成为私有物。⑪韩雪晴、王义桅:“全球公域:思想渊源、概念谱系与学术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88页。王明锁:“论无主物与其所有权归属——所有权原始取得方法之先占”,《学习论坛》,2014年第5期,第74-76页。尽管所有国家在理论上都享有全球海洋公域的使用权,但现实中对它的利用则存在“进入门槛”,只有掌握了相关能力的国家才能有效利用全球海洋公域,如只有具备了深海探测技术才能进入与开发国际海底,只有拥有了远航能力才能使用国际航道,只有具备了远洋捕捞能力才能汲取公海鱼类资源等。
再次,使用的竞争性与拥挤性。尽管全球海洋公域由人类共有、共享,但它的边界是限定的,其含有的大部分资源也是不可再生的,这意味着各国对全球海洋公域的使用存在潜在的竞争性与拥挤性,即一国对全球海洋公域内资源或空间的使用,可能会减少他国的使用量并造成拥挤。比如,全球海洋公域内的鱼类资源是有限的,一国的捕捞会减少他国的捕捞量,而各国对国际航道的同时使用,也可能会造成海上拥挤。此特性加上利用的非排他性使全球海洋公域成为一种“公共池塘资源”,区别于具有使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纯粹公共产品”。①John Vogler,“Global Commons Revisited,”Global Policy,Vol.3,No.1,2012,pp.61-71.
最后,使用的规范性。该特征主要体现在相关国际法对各国利用全球海洋公域的目的、方式等做出的应然规定上。在使用目的上,要求各国和平利用全球海洋公域,避免发生冲突和对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指出:“公海应只用于和平目的”;②刘振民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与下层土壤之原则宣言》规定,各国在对国际海底进行科考时,“促进国际合作,进行专为和平用途之科学研究”。③“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与下层土壤之原则宣言”, 载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海洋法资料汇编》,第117页。在使用方式上,要求各国负责任、可持续地利用全球海洋公域,防止发生环境损害、资源破坏等情况。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指出:“各国应在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地采取一切符合本公约的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④刘振民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3 全球海洋公域的价值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3页。全球海洋公域也为人类发展贡献着生态、经济以及安全等方面的价值。
(1)全球海洋公域是一个巨大的生态调节系统,具有气候气体调节、水调节、生物控制以及废弃物处理等多种生态功能,⑥刘曙光,郭越:“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经济学探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6月5日,第4版。如全球海洋公域在吸收人类生产生活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同时还能产生氧气,有助于降低温室效应、稳定全球气候;此外全球海洋公域还能吸收太阳辐射,稳定地球温度等。
(2)全球海洋公域既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所需的资源和能源,也为便利世界贸易提供了空间通道。在资源供给层面,全球海洋公域蕴含丰富的生物资源,不仅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所需的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还为国家发展创造了海洋经济产业。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目前人类六分之一的动物蛋白来自鱼类消费,2018年有将近五千一百万的人口就职于渔业和水产养殖产业。⑦“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联合国粮农组 织 官 网,2021年4月2日,http://www.fao.org/3/ca9231en/CA9231EN.pdf。除生物资源外,全球海洋公域还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稀土、多金属结核矿物等自然资源。据估计,有高达3万亿吨的多金属结核矿物埋藏在国际海底,有多达880亿吨的稀土深藏在太平洋国际海底。⑧“聚焦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开发规章的研究和建立”,新华 网,2021年4月2日,http://www.xinhuanet.com/expo/2017-05/19/c_129607654.htm。在便利交通上,全球海洋公域被视为“全球经济的结缔组织”,为各国货物、人员往来提供了交通便利,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发展,如2018年国际公海承担了全球90%的海运货物量。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发布<2019全球海 运发展评述报告>》,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2021年4月2日,http://aoc.ouc.edu.cn/2019/1203/c9829a277742/page.htm。
(3)全球海洋公域具备重要的战略潜能。广阔的海洋公域既能作为军力投送通道,增强国家影响和塑造陆上事务的能力,如美国利用全球海洋公域充当所谓的“全球警察”;也能在战时作为海上封锁战略的实施场域以施压敌国,如一战、二战英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还能作为防御屏障,拒敌于千里之外,防止国家本土受到干扰。鉴于全球海洋公域所具备的潜在战略价值,巴里·波森将控制包括全球海洋公域在内的全球公域视作建立和维持全球霸权的基础;⑩Barry R.Posen,“Command of the Commons:The Foundation of U.S.Hegemon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1,2003,pp.5-46.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直言:“利用和控制海洋现在是并且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①[美]阿尔弗雷德·赛那·马汉著,安常容等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二、全球海洋公域治理面临的挑战
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是指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网络、个体等多元行为主体,利用多种手段,协商解决海洋公域相关事务的过程。当前,全球海洋公域在治理需求、治理供给以及治理价值导向上面临着挑战。
2.1 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态势的权力政治化
伴随人类认识、接近和利用全球海洋公域进程的是作为治理客体的全球海洋公域也逐渐涌现出多样的治理需求,需要进行综合性的合作治理。然而,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正从权力政治的狭隘视角出发,窄化治理议题,破坏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政治环境。
(1)全球海洋公域正面临多种非传统安全治理挑战。首先,治理区域覆盖面不足。尽管海洋公域占全球海洋64%的面积,但囿于知识、科技发展等方面的不足,人类并未完全对其进行探索、利用和治理,留下了较大的治理空白区域。据估计,只有1%的公海得到了开发与治理,而只有0.01%的国际海底区域被纳入了人类治理视域。②张茗:“全球公域:从‘部分’治理到‘全球’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67页。此种治理区域覆盖面的不足,既容易导致各国因在相对有限的海洋公域内活动而产生拥挤与摩擦,也使人类不能全面享用海洋公域所提供的广泛价值。
其次,资源不可持续发展挑战。全球海洋公域在使用上的非排他性与竞争性意味着,如果各国不能负责任地勘探、利用公域内的资源,就很容易在短视利益驱动下,过度开发和利用公域资源,造成“公地悲剧”。比如,据世界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从1974到2017年,全球处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的鱼类捕捞量已从10%上升至34.2%,其中最不可持续地区为地中海和黑海(过度捕捞种群占62.5%)、东南太平洋(过度捕捞种群占54.5%)、西南大西洋(过度捕捞种群占53.3%)。③“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联合国粮农组织官 网,2021年4月3日,http://www.fao.org/3/ca9229en/ca9229en.pdf。
再次,生态污染与破坏问题严重。人类从陆上给海洋公域制造了垃圾倾泻、放射性污染、工业和农业废物排放等破坏;从船上给海洋公域造成了垃圾倾倒、外来生物入侵、海上溢油以及货物泄露等损害;在海上钻探过程中给海洋公域带来了油气泄露等难题。据估计,每年大约有八百万吨的塑料垃圾由人类倾倒至海洋,致死约十万头海洋哺乳动物和百万只海鸟,“海洋塑料垃圾正成为一种新的、真正的全球挑战。”④Lisa M.Campbell,“Global Oceans Governance:New and E- merging Issues,”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2016,p.534.此外,对比工业革命前,由于人类活动全球海洋公域的平均酸碱度减少了0.1个单位,海洋公域酸度则上升了30%。⑤吴士存:“全球海洋治理的未来及中国的选择”,《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5期,第15页。
最后,治安问题突出。全球海洋公域所具备的联通价值以及处在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的特性,使相关犯罪团体将其视为逃避追责的“犯罪天堂”,开展海盗、恐怖主义、贩毒、人口走私等犯罪活动,给全球海洋公域带来了严重的治安问题,如2019年发生了162起海盗袭击和武装劫船事件,给全球航运事业制造了安全隐患。⑥“2019年全球海盗活动总结与分析”,搜狐网,2021年4月3日,https://www.sohu.com/a/370960474_100080233。
(2)全球海洋公域治理出现权力政治化趋势。一方面,面对全球海洋公域非传统安全治理需求的上升,美欧等西方国家表现出冷淡的治理意愿。特朗普执政的美国秉持“美国优先”治国理念,明确否认多边主义与全球化的价值,表现出单边主义作风,相继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定》,损害了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多边机制。欧盟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意愿也在下降。据2019年的一份调查显示,荷兰、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国内部反对参与包括海洋公域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问题的人数在增加。英国脱欧则进一步影响了欧盟的参与能力,如2019年3月英国将在地中海区域打击海上人口走私活动的指挥权移交给西班牙,影响了欧盟维持海上治安的能力。此外,在2019年12月,由于波兰的反对,欧盟未对包括全球海洋公域气候治理在内的“气候中立”协议达成一致意见。①吴士存:“全球海洋治理的未来及中国的选择”,《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5期,第10页。
另一方面,在弱化非传统安全治理意愿的同时,美欧等正从主导与控制视角出发,将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议题权力政治化。美国倾向于从霸权护持视角对待全球海洋公域相关治理议题,认为“进入并主导包括公海在内的全球海洋公域,是美国国家战略的根基”。②Colonel Philip J.Ridderhof,“Organizing to Control the Global Maritime Commons,”U.S.Army War College,2011,p.1.特朗普政府提出和推进了“印太战略”,将美国60%的海外兵力部署至“印太”地区,提升了地区军事部署密度,恶化了地区海洋安全环境;拜登政府则继续强调参与“印太”事务对美国的战略作用,意图通过军事部署、政治接触以及经济竞争等手段强化美国对“印太”海洋事务的控制与塑造能力;③刘国柱:“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针与发展方向”,《当代世界》,2021年第5期,第50-57页。此外美国不顾国际法规范,随意实施所谓的公海“航行自由”行动,宣示自身对全球海洋公域的控制力,破坏了全球海洋公域的公有属性。脱欧后,英国将“全球英国”作为国家身份定位,力争在全球海域扩展影响力,并追随美国在南海相关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④叶圣萱:“英国介入印太地区的新动向与中国的应对论析”,《区域与全球发展》,2021年第5期,第30-46页。日本则在努力寻求放宽宪法对自身军事活动的限制,积极谋求军事与政治大国地位,并将海权作为自身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⑤宋德星、黄钊:“‘印太’视域下日本的安全威胁认知与安 全防卫理念重构”,《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6页。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也扩大了在“印太”海域的军事活动,搅乱了地区安全形势。⑥宋芳:“欧盟在中美之间的艰难选择——基于‘蛋糕主义’视角的分析”,《国际展望》,2021年第3期,第76-95页。在权力政治心态的影响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从相对收益视角出发,消极看待和应对地区国家提出的海洋公域治理倡议。比如,面对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倡议,美国不但污名化中国在借该倡议修正地区秩序,追求地区霸权,而且还采取行动阻挠倡议实施,如借“印太战略”加强对中国的海上前沿侦察与挑衅活动,破坏倡议实施的安全环境。
另外,美欧等西方国家还从战略竞争视角出发,有意纵容盟友和伙伴国的“海洋单边主义”行为,进一步恶化了全球海洋公域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当日本未做合理的风险评估并同地区国家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协商,就从自身狭隘的国家私利出发,计划将福岛核污水倾倒至海中,从而将治理成本不负责任地转移至他国时,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为了拉拢日本在“印太”地区共同制衡中国,既不顾及国内民意对日本此举的反对,也不考量此举可能对海洋生态环境以及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发声支持日本的行为,恶化了“印太”地区海洋生态治理的政治环境。⑦李嘉伟等:“大数据分析:国际社会对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放的反应”,FT中文网,2021年4月5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2287?Archive。
2.2 全球海洋公域治理供给的赤字化
联合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成了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主体架构,该架构目前在治理主体、治理机制上面临不足,无法回应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所产生的新需求。
(1)治理主体偏倚。科技进步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激发了各类行为体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兴趣,还为其创造了参与机会和能力。然而,既有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架构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突出国家的主导治理地位,弱化、忽视甚至排斥跨国公司、个体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如非国家行为体的身影基本未出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过程中;在对国际海底资源勘探与保护等治理议题进行谈判期间,非国家行为体也只能作为咨询的“旁观者”,无法对议题设置、机制建设等问题产生实质性影响。①王发龙:“全球公域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3期,第134页。
即使在国家主导下,现有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框架也存在“大国主导”现象。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公海以及国际海底等相关治理议题上积极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贡献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和“人类共同关切事项”等倡议,②韩雪晴、王义桅:“全球公域:思想渊源、概念谱系与学术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97-198页。但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科技、军事等实力优势,从自身利益出发,主导了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议题设置、规制设立与运用等事务,将发展中国家“边缘化”。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主导了国际海底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谈判进程,忽视了沿海小国与陆地国家的权利。再比如,即使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美国从自身霸权利益出发,随意阐释和运用公约中的“航行自由原则”,搅乱地区局势。而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加速,新兴国家正逐渐走近国际舞台中央,这要求建立在既往实力对比格局上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机制进行相应调整以反映新的国际格局,但以美国为首的守成国却不愿做出改革,甚至还打压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热情,如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对中国正当海权发展的压制。③叶泉:“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角色与实现路径”,《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第77-78页。
(2)治理机制的“充裕悖论”。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机制指围绕海洋公域有关治理议题所形成的原则、规范、规制与程序。目前,各国以联合国为中心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机制,不仅在渔业资源、生物多样性、海洋污染、海上运输等功能性领域建立了相关治理机制,而且还组建了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海底管理局等为中心的治理组织,但这些治理机制在应对全球海洋公域所出现的治理需求时依然存在三点主要不足。
首先,治理机制的“碎片化”问题。横向上,既有治理机制以功能领域为基础进行切割式治理,忽视了全球海洋公域的整体性,使治理机制间的协调不足,容易引发“各自为政”的条块式治理问题。现有全球海洋公域的治理过程还存在同一领域由多种机制治理的“事出多门”现象,如联合国框架下的多数组织都具有治理公海鱼类资源的职责,从而使有效的治理资源无法得到精准、高效的利用,影响了机制的治理效率与效能。④Dotoca.Pyc,“Global Governance,”TransNay: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arine Navigation and Safety of Sea Transportation,Vol.10,No.2,2016,p.160.纵向上,全球海洋公域治理需要统筹全球、地区与国家等多个治理层级以实现治理规模的最优化。但现有治理机制在各层级间出现了错配,要么存在治理规制标准不一的现象,要么在各治理层级间缺乏规则对接。比如,欧盟对大西洋部分海洋公域的治理规则标准高于联合国规则,引发了规则间的适用冲突问题;而有些国家由于发展不足等原因,还无法建立同联合国规则相匹配的国内治理规制。⑤Carlar P.Freeman,“The Fragile Global Commons in a World in Transition,”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6,No.1,2016,pp.21-22.
其次,存在缺乏治理机制的空白领域。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是个动态的过程,在国家与非国家治理主体认知、能力以及利益变化的推动下,在治理客体本身演进的作用下,既有治理机制应该做出适应性调适,可其并未充分跟进动态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环境。比如,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对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BBNJ)的治理,目前就该问题谈判相关治理规则的进度依然比较缓慢;对深海塑料的治理也还未建立明确的机制;对国际海底矿产开发与利用的治理也缺乏明晰的规则与共识。⑥王发龙:“全球深海治理:发展态势、现实困境及中国战略选择”,《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61页。
最后,治理规则的执行力赤字。由于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不存在拥有强制执行力的“世界政府”,因此对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规则的执行主要取决于各国自愿,所以时常会出现国家对治理规则的选择性和机会主义遵守行为,如日本枉顾国际法执意计划将核污水倾入海洋、美国滥用“航行自由”原则等。①王义桅:“全球公域与美国巧霸权”,《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52-53页。
2.3 全球海洋公域治理价值导向的私有化
全球海洋公域在使用上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以及各国在利用能力上的差异性预示着,如果不能合理规制各国的行为,则可能会导致有开发和利用能力的国家抢夺先发优势,对全球海洋公域采取“先占先得”的利用态度,侵蚀海洋公域的公有物属性,将其变质为无主物,不幸的是这种倾向正呈凸显之势。
一方面,有关国家正凭借技术优势,意图将海洋公域“私有化”,以满足国家私利。比如,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握着成熟的深海探测与开发技术,它们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对国际海底资源的探测与开发利用,并形成了排他性的“精英俱乐部”,使国际海底正逐渐退化为发达国家的私有物,违背了由人类共有国际海底的国际法原则。再比如,有些国家将本国的专属捕捞权延伸至专属经济区之外的公海,并抵制其他国家的捕捞活动,试图将特定公海“封闭化”。②丘君:“悄然兴起的‘新海洋圈地运动’”,《中国海洋报》,2012年3月2日,第4版。
另一方面,有些国家正试图利用先进的科技与军事优势,掌控全球海洋公域的治理权,意图达到“以治权行主权”的目的。比如,美英等国提出的“公海保护区”倡议,名义上想通过产权切割以更好地治理海洋公域,但鉴于各国在全球海洋公域治理中存在的能力差距,此种倡议最终可能会将“公海保护区”沦陷为发达国家的私有物。③王勇,孟令浩:“论BBNJ协定中公海保护区宜采取全球管理模式”,《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5期,第1-15页。此外据估计,目前只有美英法加等少数西方国家掌握着开发海洋遗传资源的技术,而它们也提议对属于人类共有的海洋遗传资源采取“自由开发”原则,并对相关技术与产品进行有偿转让。这种治理提议不仅反映出这些国家想借先进技术先行占用海洋公域资源的意图,还暴露出它们想将开发出的公有资源产品售至不具备开发能力的国家以赚取利润的贪婪。④张士洋:“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ABNJ海洋遗传资源的 国际治理与中国实践”,《海洋开发与管理》,2020年第6期,第1-9页。
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完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原则
全球海洋公域治理面临的上述挑战,要求各国更新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方式,以维护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海洋公域。不管采用何种治理手段,首先都需要明确应该坚持的治理原则,从而为海洋公域治理设定规范基础。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为完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提供了指导原则。
(1)坚持治理主体的包容与协商原则。“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视“国家不论强弱、国际组织不论大小,有关各方都能够在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平等地表达关切。”⑤朱璇、贾宇:“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期,第57页。如果在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过程中,个体、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都是利益攸关方,那就应该摒弃既有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国家或大国中心”现象,“让有权使用海洋公域的每个个体都参与海洋公域事务管理,让他们享有发言权”。⑥Theodore Okonkwo,谢红月:“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公域管理”,《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31页。这不仅体现了治理一词所蕴含的“多主体协商共治”的价值理念,也能发挥各类行为体在全球海洋公域治理中的比较优势。当然,在广泛包容各类治理主体的同时,也要注意主体间的统筹问题,防止出现因治理主体规模增加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上升问题。一般而言,存在各自为政的“无协调式”、家长制的“统制式”以及平等协商的“伙伴式”三种治理主体的协调模式。鉴于“无协调式”只会加剧治理的交易成本、降低治理效率,而“统制式”模式则表现出高压强权色彩,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不符且不利于调动各类行为体的积极性,因此在包容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进程的同时,还应秉持“蓝色伙伴关系”原则,在各类主体间构建平等的“共同治理”伙伴关系,做到“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44、464页。
(2)秉持治理方式的多元与规范原则。市场、政府以及制度是治理全球海洋公域这类“公共池塘资源”的三种主要方式。市场方式借产权分割明确使用者的权利与义务来提升全球海洋公域的利用效率;政府模式突出大国作用,强调借此类国家的较强实力来规范各类主体对全球海洋公域的利用;制度模式则重视通过构建涉及多个层次和领域的国际机制来治理全球海洋公域。②Stephen C Nemeth,“Ruling the sea,”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Vol.40,No.5,2014,pp.2-4.鉴于全球海洋公域是一个复杂的治理系统,存在丰富的治理需求,因此在分析每种治理模式的适用条件以及具体的治理环境的基础上,需要综合采用多种治理方式。比如,对鱼群这类流动性强、不易进行产权分割的公海资源,需要创建国际机制进行协调治理;而对二氧化碳(蓝碳)排放这类问题,则可以借鉴全球气候治理中以产权分割为治理手段的碳排放交易机制。不管采用何种治理方式,都应该坚持效率、公平、合作、和平相统一的治理规范,既不能为了提高治理效率而忽视全球海洋公域的公有属性,也要防止和反对借保护之名行“私有化”全球海洋公域之实的治理倡议和行为,更不应该从“控制”与“争霸”视角对待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而是要坚定维护全球海洋公域的共有属性,排除和放弃对它的“权力政治”幻想。此外,不论采取何种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方式,都需要综合囊括不同区域、各类治理议题,防止出现治理遗留问题,并注重协调同一层级以及不同层级间的治理规制,避免出现“部分”和“碎片化”治理现象。③Lucia Fanning and Robin Mahon,“Governance of the Global Ocean Commons:Hopelessly Fragmented or Fixable?”Coastal Management,Vol.18,No.3,2020,pp.4-6.
(3)贯持治理收益共享原则。海洋公域的公有性意味着,它所创造的收益应该由人类和海洋共享。首先,要摒弃人定胜海理念,坚持人海和谐原则。人类与全球海洋公域是命运与共的关系,对海洋公域的利用、保护质量会直接反作用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各国应该“像对待生命一样爱护海洋”,“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44、464页。具体言之,在利用全球海洋公域时,既要坚持预防性原则,以不对全球海洋公域造成损害为基本要求,也要秉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不采取“涸泽而渔”的短视做法,还要贯持跨代平等原则,不能为满足本代人的利益而忽视后代人利用全球海洋公域的权益。⑤Vito De Lucia,“Ocean Commons,Law of the Sea and Rights for the Sea,”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Vol.32,No.1,2019,pp.1-12.其次,坚持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共同体”原则。尽管实力不均衡是国家间常态,大国也因具备较强的实力而需承担特殊治理责任并享有特殊激励,但这不意味着应该忽视小国和发展中国家权益。相反,治理海洋公域时,不仅要正视大国的作用与优势,也要“特别倾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的声音”,⑥朱璇、贾宇:“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期,第57页。并反对任何形式的“仗势欺人”和“以权谋私”行为。此外,鉴于国际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的提升,既有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机制也应该进行调整,以反映他们的呼声和关切。最后,秉持治理主体间的“责任共同体”原则。既然各类利益相关者都拥有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进程、享用治理收益的权利,那么它们也应该主动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以匹配所获得的治理权益。而鉴于各类行为体在治理能力和治理权利上存在着现实差距,因此其承担的责任应该是“共同但有区别”的。①陈秋丰:“全球公域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国际论坛》,2021年第3期,第57-58页。
四、中国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路径选择
中国的复兴需要善用来自海洋的发展机遇。习总书记在2013年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②习近平:“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中 国政府网,2021年4月6日,http://www.gov.cn/ldhd/2013-07/31/content_2459009.htm。这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进程,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
4.1 加强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能力建设
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具备了坚实的治理能力,才能为持续参与海洋公域治理议题的设置、治理机制的创设、治理规则的设定提供支撑,为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努力。为此,中国“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新 华网,2021年4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6/26/c_137281151.htm。
首先,深化海洋科技强国建设。前文述及利用与开发全球海洋公域需要一定的“技术门槛”,只有具备了进入与利用实力,才能在全球海洋公域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使自己成为不可忽视的治理攸关方。尽管中国目前在远洋测量、深海勘探、海洋新能源开发等方面已具备世界先进的科技能力,但同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还存有差距,对此中国需要从加大科研投入、创新管理机制、培养科技人才、强化国际交流等方面着手,不断提升海洋科技水平,努力将自己建设成海洋科技强国,为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打造坚实的技术支撑。
其次,加强海洋科学研究。对全球海洋公域具备科学、全面的认知,既有利于中国提出令人信服的倡议,也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国不仅需要持续加大对海洋科学研究的投入,繁荣发展涉海研究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如可考虑设立专门的“海洋学”,④张景全:“为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人民论坛》,2020年第7期,第101-105页。以为自身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提供坚强的智力支撑;还应该坚持同外国政府、学者、智库以及国际组织等的交流互鉴,使自身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前沿科学研究保持同步。
再次,完善涉海法律储备。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⑤“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为何如此重要?”,新华网, 2021年4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17/c_1126752206.htm。目前中国已制定了《领海及毗连区法》《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涉海法律,但对公海遗传资源等治理议题的立法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一方面,中国可以加快国内立法进程,缩短同既有国际法规存在的衔接差,显示自身深度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决心与担当;另一方面,对有关法律不存在或不完善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领域,如跨区域鱼类资源管理、国际海底资源勘探等,中国可以考虑率先在国内制定相关法规,既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也为自身后续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创造先发优势。⑥唐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思考”,《南海学刊》,2021年第3期,第65-66页。
接着,夯实海洋国防基础。强大的海洋硬实力既有益于中国维护正当的海洋发展权益,也有利于提升海洋公域治理话语权,还有助于提供海洋公共安全产品。中国应该坚持强军目标,从合理提升国防投入、加强海军装备建设与更新、强化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出发,持续推进“蓝色海军”建设,努力打造一支维护和平的海上“正义之师”,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提供国防支撑。
最后,科学谋划参与进程。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所涉地域之广、涵盖事务之多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掌控和参与全部议程。中国需要在统筹国家利益、国际利益以及国家能力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方向、重点与方式,避免出现战略透支陷阱。
4.2 积极推动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机制改革
一方面,强化国内涉海机制建设。在参照自身涉海事务的治理现实、能力和正当利益诉求的基础上,中国可以对照现有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机制,完善国内涉海机制建设,以实现国内国际治理机制对接。这不仅能向外界显示中国参与海洋公域治理的包容与开放心态,也有利于动员国际有利经验促进国内海洋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中国也可以就海洋公域新出现的治理议题进行内部机制创新,如探索建立规范深海勘探、海洋遗传资源开发与保护、深海塑料治理等方面的国内制度与机制,为自身更好地参与相关国际机制建设的谈判提供经验与能力储备,反向为创设国际机制贡献“中国经验”。①刘惠荣:“海洋战略新疆域的法治思考”,《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4期,第17页。中国还可以在国内就中央和地方涉海治理机制的协调问题做出尝试与创新,为全球海洋公域治理中层级间机制协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②姜秀敏:“探索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行动方案”,《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15日,第005版。
另一方面,改革与完善既有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机制。中国需要积极推动现有机制改革,使其切实关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善意倾听个体、跨国公司以及社会运动网络等多元主体的正当关切。中国也可以协调各方就全球海洋公域新出现的治理议题创设国际机制,弥补既有治理空白,如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身份,就创建新的海洋公域治理机制发出声音和倡议,动员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中国还可以借承担国际会议的机会,并通过自己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等多边会议,就创设新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机制发出“中国倡议”。
4.3 主动宣扬和践行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中国话语”
(1)打造一套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中国话语”。在吸收传统价值观和新时代治国理政新理念的基础上,中国可从目标维度、路径维度以及行动维度出发,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中国话语”,为世界提供理念引领。③季思:“积极为全球公域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当代世界》,2019年第2期,第1页。目标维度上,中国可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导引,传扬“和平之海”、“安全之海”、“发展之海”以及“绿色之海”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理念,以此明确反对海上霸权和单边理念;中国也可以将“开放包容、具体务实、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作为全球海洋公域治理“中国话语”的路径内容,高举规范利用全球海洋公域的“道义旗帜”;中国还可以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作为全球海洋公域治理“中国话语”的实践内容,彰显中国务实作风。
(2)从传播主体、客体、平台、方式等全要素过程出发,主动宣扬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中国话语”。首先,中国可借助政府、智库、媒体、学界等多元主体向外界传播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中国话语”。其次,在进行受众分析的基础上,中国需要细化传播客体类型,把握不同传播对象的心理与诉求,从而找到传播全球海洋公域治理“中国话语”的最佳方式。接着,中国可以利用联合国大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多种平台宣扬“中国话语”,提升话语的受众面和影响力。最后,在传播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中国话语”时,中国需要加强对整个传播过程的监测,及时调整传播策略,形成正传播反馈环。
(3)以实际行动提升全球海洋公域治理“中国话语”的战略信誉。除上文提出的两大建议措施外,中国可以通过加强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对接、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积极构建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等方式,先在局部范围显现全球海洋公域治理“中国话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以此逐步提升话语效力的覆盖范围与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