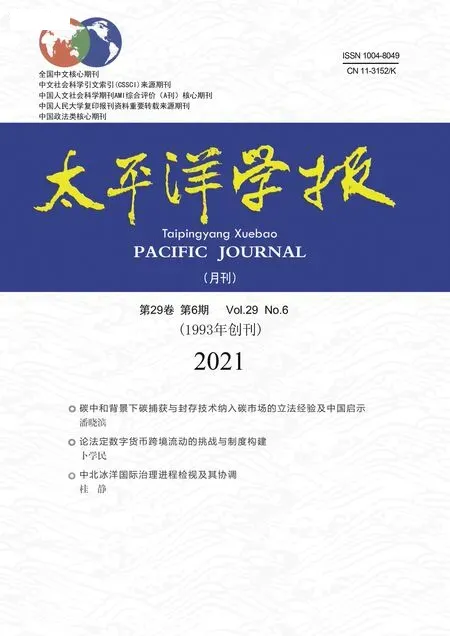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策略研究
杨振姣 牛解放
(1.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266100)
全球气候变暖使北极可通达性提高,逐渐频繁的资源开发和海上运输等加剧了北冰洋海洋环境的污染,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环境使全球治理赤字加剧,如何更好地维护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重要议题。然而北极现行的地缘政治理念、治理机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功能不足,无法有效应对环境保护与资源分配等新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①丁煌、朱宝林:“基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北极治理机制创新”,《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3期,第94页。秉承协作共赢、责任共担、环境共治原则的协同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方式,将成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首要而必然的选择。
生态安全的概念源自环境安全,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Lester R.Brown)最早将环境问题引入安全研究,在其《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明确提出“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力图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安全的定义必须扩展,超出对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而要包括环境恶化和发展条件遭到的破坏。”①付宝荣、惠秀娟著:《生态环境安全与管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一般来说,生态安全概念可以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根据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在1989年提出的定义,广义的生态安全是人的各项权利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由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狭义的生态安全则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主要反映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状况的整体水平。②陈星、周成虎:“生态安全:国内外研究综述”,《地理科学进展》,2005年第6期,第9页。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角度解读,海洋作为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生态安全都是最重要的生态安全类型。海洋生态安全作为一种具有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安全,其特点与非传统安全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战略性、全球性、复杂性和滞后性等自身特点。③杨振姣、姜自福:“海洋生态安全的若干问题——兼论海 洋生态安全的涵义及其特征”,《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6期,第93-94页。海洋生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是指与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活动相关的海洋生态处于良好的状态或不遭受不可恢复的破坏,④丁德文、徐惠民、丁永生等:“关于‘国家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10期,第64页。具体包括海洋环境、海洋生物和海洋生态系统三个方面的安全。本文认为海洋生态安全是指海洋生物、海水质量等处于良好状态,海洋生态系统保持可持续发展,人类用海活动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动态协调、人海和谐的一种状态。
通过概念梳理,可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两方面对北极海洋生态安全面临的问题作简要分析,一方面是气候变暖引发的北极冰层、积雪的融化影响生态环境稳定,⑤“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Climate Change 2013: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IPCC),Cambridge,United Kingdom and New York,NY,US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1.表现为北极生物生存空间萎缩、多样性受损,海平面上升导致海岸侵蚀加剧;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 策》白皮书”,中国政府网,2018年1月26日,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18203/1618203.htm。另一方面是北极开发引发的生态环境污染,船舶通航北极产生的噪音、压舱水、废水油污和重型燃油产生的黑碳会破坏北极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加剧北极温室效应,离岸油气开发和近岸船舶维修产生的废油、重金属等会长久留存在北冰洋,对北极海洋生态环境产生长远影响。北极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船舶通航造成的污染等问题是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应着重关注的领域,上述领域呈现明显的跨区域性特征,需要域内外国家、国际组织等共同合力应对,以更加协同的治理策略实现北极海洋生态安全。
一、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态势与机制分析
北极国家及其主导的北极理事会一直以来都掌握着北极治理的绝对权力,对北极治理工作影响显著。但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北极重新成为被广泛关注的“新疆域”,越来越多的域外国家、组织想参与北极治理过程,并通过建立论坛、缔结条约等方式形成新的北极治理机制,以期重塑北极治理框架格局,改变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态势。
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是北极治理的重要一环,分析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态势必然要对北极治理态势做分析。北极治理态势可从两方面进行解读:一方面是北极治理的“门罗主义”趋势愈发明显,其实质是一种排他性思维,⑦潘敏、徐理灵:“超越‘门罗主义’: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与北极治理机制革新”,《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期,第93页。体现为北极治理的排外性、治理实践的局限性,以及治理主体的固定性,凸显“北极是北极国家的北极”这一理念。北极理事会通过构建“等级差序结构”,使北极理事会成为北极国家实行北极“域内自理化”的有力工具。⑧王晨光:“中国推进‘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法律风险及应对建议”,《兰州学刊》,2021年第3期,第98页。总之,北极国家通过“制度化集体垄断”的方式主导北极治理格局的意图明显,①肖洋:“北极经济治理的政治化:权威生成与制度歧视——以北极经济理事会为例”,《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7期,第99页。趋向固化的“等级格局”将制约域外国家有效参与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工作,对协同治理进程形成掣肘。
另一方面是北极治理的全球性与国际合作趋势加强,表现之一是北极治理国际合作平台的拓展,北极圈论坛、国际北极论坛能够为非北极国家提供协商合作的平台,以广泛参与北极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航道开发利用等事务,尽管论坛内容难以对北极海洋生态治理产生主导作用,但作为一种国际社会广泛参与北极海洋生态治理的实践方式,论坛相关决议和报告内容将为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定北极治理策略提供有效参考,是对当前治理机制的完善。而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能够为各类主体参与北极科学合作提供平等交流的平台,实现北极决策者和科学界的“直接沟通”,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超越北极治理“门罗主义”特征的潜力,将有效削弱北极理事会主导下的《加强国际北极科学合作协定》对非北极国家北极科学研究的制度性歧视,借助会议平台宣传对北极生态气候变化的关注和国际合作的重视,强调非北极国家对北极科学研究的贡献,拓展北极合作的领域。另一表现是协议或条约制定组织的国际化,《极地水域船舶作业国际规则》(以下简称“《极地规则》”)、《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是两部由非北极理事会主导制定的专项规则,在北极环境保护、船舶安全和渔业保护方面,为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生态环境与航运治理和渔业保护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②陈奕彤、高晓:“北极海洋资源利用的国际机制及中国应对”,《资源科学》,2020年第11期,第2066页。形成了不同于北极理事会运作模式的北极治理机制。
具体来看,《协定》提出的背景是保障中北冰洋海域完整的科研生态环境,使其能够为未来的科研工作提供完整数据,防止因商业捕鱼活动对区域环境造成破坏,美国首先提出制定中北冰洋治理的法律方法并将其提交至北极理事会讨论,但理事会未接纳相关提议,而后北冰洋沿岸五国(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挪威、丹麦)先后举行了四次高官会议,并与远洋渔业五方(中国、欧盟、韩国、日本、冰岛)先后举行六次十方会谈,2018年10月3日,上述十方缔结《协定》。从《协定》对缔约各方所规定的责任义务和相关权利来看,其不同于北极理事会“内外有别”的国家地位界定,《协定》对于域内外国家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总体是一致的,国家之间地位相互平等。此外,《协定》着重强调科学技术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北极科研能力的发展在《协定》生效后或许会成为新的主导方向,《协定》体现了平等性、科学的主导性等特点,这对于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是一种进步,未来或许会形成一种新的北极区域合作治理路径。而《极地规则》的起草源于在极地海域发生的原油泄漏、船只沉没等灾难性事件,为有效保障在极地航行的船只安全、规范通航船只的行为、保护极地海域生态环境,国际海事组织经过多年协商修改,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的《极地规则》于2017年1月1日正式生效。《极地规则》是面向极地水域船舶航行安全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国际规则,具有明显的全球属性。从北极区域来看,《极地规则》的出台能够更好地整合分散化的北极航道航行规范,强化对北极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极地规则》将改变北极地区强制性法律缺失的问题,将强制性法律规范与建议性航行指南相结合是《极地规则》的一大特点,对于过多依靠“软法”开展治理的北极地区来说,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和重要意义的法律规范。此外,《极地规则》同样充分考虑到了缔约国之间的不同状况,对于缺少极地航行经验的国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及科学的技术性指导,对不同缔约国的意见均给予了尊重和重视,是国际合作和国家平等参与的一次成功案例。上述种种尝试,将为国际社会更好地参与北极治理奠定良好基础,提升北极海洋生态安全的治理水平。
北极治理态势的发展决定了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总体上也体现为治理的“门罗主义”与治理全球化趋势加强的特征,但相较于高政治敏感度的传统安全治理领域,北极海洋生态安全作为低政治敏感度的非传统安全治理领域,推进领域内的协同治理工作所受阻力相对较小,且北极域内外国家大都意识到北极海洋生态环境变化会给国家的生存发展带来挑战,更加倾向于寻求国际合作,通过协商签署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极地治理规则、条约,探索新的北极治理机制和运行模式,以共同应对北极海洋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综合来看,北极治理正在朝着多元化、国际化方向缓慢推进,北极理事会主导的北极治理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但基于北极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影响的广泛性,包括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开始寻求更加广泛和有效的合作方式与平台,打造国际协同的北极治理机制或将成为未来北极治理的目标所在。
二、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政策解析
从根源上看,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态势的变化受到国家政策和战略的影响,北极与非北极国家通过制定北极发展战略,以各种形式参与北极海洋生态治理事务,表达国家对协同治理与海洋生态保护的立场(参见表1)。

表1 主要国家的北极政策分析
美国2013年颁布了《北极地区国家战略》,保护北极生态环境成为五大核心利益之一,并将提升国际合作水平作为主要实施目标之一,①“北极地区国家战略”,美国白宫网站: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nat_artic_strategy.pdf,访问时间:2021年4月30日。树立美国对北极事务特别是气候治理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时期相继颁布《北极战略》《北极战略展望》,旨在强化北极地区军事管控,并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签署北极资源开发政策,弱化了对北极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关注,突出军事优先级,这与北极治理遵循的和平与国际合作的主基调背道而驰。②刘惠荣、陈奕彤、孙凯著:《北极蓝皮书——北极地区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拜登执政后,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由签署禁令,关闭了北极保护区内的资源开发项目,③Tegan Hanlon,“Biden Immediately Slams the Brakes on Oil Drilling in Arctic Refuge,”Alaska Public Media,https://www.alaskapublic.org/2021/01/20/biden-to-immediately-slam-the-brakes-onoil-leasing-in-arctic-refuge/,访问时间:2021年3月14日。此举可视为新政府对北极政策的转变,但最终美国北极政策会如何发展尚无定论。
加拿大在其《北极与北方政策框架》中提出,优先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共同应对北极生态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支持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寻求与其他北极与非北极国家有效合作的方法,探索新的国际规则与管理机构。④加拿大原住民—皇家关系和北方事务部,“加拿大北极与 北方政策框架”,加拿大政府网,https://www.rcaanc-cirnac.gc.ca/eng/1560523306861/1560523330587,访问时间:2021年2月26日。
俄罗斯在《2035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国家基本政策》中提出要坚持国际法基础下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强化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北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在北极实施特殊的环境管理和保护制度,积极推动北极和非北极国家参与俄北极地区的经济合作项目。⑤“2035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国家基本政策”,俄罗斯联邦 法律、法规和条例网,https://www.legalacts.ru/doc/ukaz-prezidentarf-ot-05032020-n-164-ob-osnovakh/,访问时间:2021年2月28日。
挪威在《挪威的北极政策:挪威在北极的人口、机遇和利益》中强调要积极开展双、多边合作,切实加强与欧盟、中国、俄罗斯等在北极生态环境和全球气候问题方面的合作,并着重提出要有效治理北极海洋垃圾和微塑料问题,构建北极保护区和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合作网络。⑥挪威外交事务部:“挪威的北极政策:挪威在北极的人口、机遇和利益”,挪威政府网,https://www.regjeringen.no/globalassets/departementene/ud/vedlegg/nord/whitepaper_abstract2020.pdf,访问时间:2021年2月20日。
芬兰现在执行的北极政策是其2013年颁布的《芬兰2013年北极地区战略》,该政策的核心是认识并把握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北极生态环境的影响,支持北极域内外国家之间开展广泛合作,共同构建北极自然保护区网络,加强北极生态环境保护。①芬兰总理办公室:“芬兰2013年北极地区战略”,芬兰政府网,https://vnk.fi/documents/10616/334509/Arktinen+strategia+2013+en.pdf/6b6fb723-40ec-4c17-b286-5b5910fbecf4,访问时间:2021年2月22日。
瑞典政府在《瑞典北极地区战略》中将国际合作、气候和环境、安全与稳定,以及环境监测与研究等作为优先事项,强调在北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尊重国际法的重要性,通过加强与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和各类主体在环境和气候领域的合作,致力于在北极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各项目标。②瑞典外交事务部:“瑞典的北极战略”,瑞典政府网,https://www.government.se/country-and-regional-strategies/2011/10/swedensstrategy-for-the-arctic-region/,访问时间:2021年4月10日。
冰岛在《关于冰岛北极政策的议会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提出包括加强国际合作、支持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开展北极合作与治理等在内的12项原则。③“关于冰岛北极政策的议会决议”,北极门户网,http://library.arcticportal.org/1889/1/A-Parliamentary-Resolution-on-ICEArctic-Policy-approved-by-Althingi.pdf,访问时间:2021年4月10日。而在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2019—2021年)颁布《共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北极》工作政策,强调北极海洋环境、北极气候和绿色能源解决方案等优先事项。①冰岛外交事务部:“共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北极”,冰岛政府网,https://www.government.is/library/01-Ministries/Ministry-for-Foreign-Affairs/PDF-skjol/Arctic%20Council%20-%20Iceland’s%20Chairmanship%202019-2021.pdf,访问时间:2021年4月10日。显然,《决议》的核心原则在工作政策中得到了延续,开展国际合作、保护北极生态环境仍是冰岛的核心目标之一,冰岛致力于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北极、安全北极。
2018年以来,中国、英国、德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组织相继发布了北极政策,相较于北极国家,非北极国家更加关注多边合作,注重借助多边合作机制共同应对北极治理问题,强调维护北极秩序稳定的重要性。中国、日本、韩国等“北极利益攸关国”希望通过政策内容展现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目标与行动,特别是参与北极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决心和措施,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国政府网,2018年1月26日,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18203/1618203.htm;韩立新、蔡爽、朱渴:“中日韩北极最新政策评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58-67页。以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拓展北极事务参与范围。
无论是环北极国家还是域外国家,对于北极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气候变化的应对都表现出要强化国际协同合作,扩大国际合作平台与范围的意愿,集全球之力共同应对日益恶化的北极生态环境和不断变暖的全球气候问题,这从政策层面为构建北极生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不能忽视北极域内大国对国家北极利益的维护,协同治理需要各方政策的支持,北极大国未来的政策走向或是一个重要的变数。
三、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困境分析
面对北极海洋生态安全问题,各国通过不同治理机制和国家政策开展治理行动,治理机制的运行与国家北极政策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工作的开展,但也要看到整体向好的治理趋势中仍然存在需要应对的治理困境。
3.1 “逆全球化”使协同治理面临形势困境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全球化浪潮,同时也见证了三次逆全球化思潮,③盛斌、黎峰:“逆全球化:思潮、原因与反思”,《中国经济 问题》,2020年第2期,第5页。“逆全球化”可以看作是全球化进程的反转,是一种与全球化进程相抵制和冲突的趋势,具有明显的排外主义,拒绝参与广泛的国际合作。“逆全球化”出现的根本诱因源于全球化红利在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分配不均,④万广华、朱美华:“‘逆全球化’:特征、起因与前瞻”,《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第38页。导致参与方利益受损,引发民粹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潮,部分国家和地区开始对全球化这种“高度依存”的全球治理模式提出质疑。特别是受全球公共卫生形势影响,国家经济复苏与治理能力提升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锐减,国际合作发展受挫,导致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凸显,“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并不断冲击和解构全球化时代形成的合作共赢、协商共治等既有价值观,使国际合作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国际社会的治理变革在疫情冲击下显得尤为迫切,亟需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北极地区治理赤字更加凸显。例如,特朗普政府时期一直拒绝将气候变化列为北极理事会的议事内容,并强调中国和俄罗斯的“北极威胁论”,提出“权力和竞争的新时代”在北极的到来;对于中国“近北极国家”的定位和建设“冰上丝绸之路”的计划,特朗普政府以多种方式对上述内容进行恶意揣测甚至诋毁,试图将中国打造成北极的“威胁制造者”;挪威颁布《新奥尔松科考战略》,旨在强化对斯瓦尔巴群岛的控制与对《斯瓦尔巴条约》各缔约国的约束,收缩缔约国既有的权利,并将斯瓦尔巴机场由“国际级”降为“国内级”,不仅有违《斯瓦尔巴条约》规定的“无歧视原则”和“公平原则”,而且含有配合美国战略、防范中国在北极发展之意。①郭培清:“挪威斯瓦尔巴机场降级事件探讨”,《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2018年第11期,第40-42页。这些都在削弱北极地区全球治理的合作基础,不利于北极治理公共产品的多渠道供给,加剧北极竞争态势。
3.2 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国际合作困境
国际合作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或价值追求进行的一种政策、措施的协同。从根本上讲,国际合作是国际社会对公共区域进行协同治理的重要前提和抓手,因此,对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国际合作困境的讨论集中在以北冰洋核心区公海为主的北极公域。
国际合作多体现为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困境便成为制约国际合作的主要因素,集体行动困境理论把集体的共同利益看作是一种公共产品,每个人都有权利使用,而集体行动中存在“搭便车”现象,理性个人只想获取利益而不付出代价,从而导致“集体不行动”,最终每个人都没有获利。②陈潭:“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非合 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9期,第140页。集体行动困境说明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集体行动未必能导致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国际合作就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每个国家都能认识到北极资源环境及海洋生态安全的重要性,但基于北极海洋生态安全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国际合作中“搭便车”现象同样存在,导致在此过程中责任分担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以北极资源开发为例,俄罗斯、挪威、加拿大和美国等北极国家纷纷在其管辖的北极范围内开采油气和矿产资源,此类举措必然会对北极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但不同的是俄罗斯、挪威和加拿大同时也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北极生态环境的影响,支持共同应对北极变暖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实现北极可持续发展。而特朗普政府一直拒绝承认气候变化,并在2019年举行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拒绝将气候变化写入会议文本,拒绝谈论气候变化对北极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不再履行相关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尽管拜登政府宣布将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并关停了相关区域资源开发项目,但这种“治理责任转嫁”行为对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是一种阻碍。每个国家都是理性的,在治理成本与收益呈现出不对等关系且缺少足够措施加以纠正时,会反过来削弱相关治理主体的积极性,造成逐利避责的局面,最终导致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低效化。
3.3 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面临技术困境
北极处于地球最北端,恶劣的条件决定了在北极地区开展活动困难重重,必须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才能实现有效的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但现实是匮乏的科技使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面临多重技术困境:第一,高纬度地区工业生产排污技术缺乏,源头污染难以有效防治。北极地区资源丰富,尤其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资源,以及金刚石、铜和铀等矿产资源。但由于相关国家在高纬度的资源开采作业技术水平限制,导致资源开采的同时无法有效处理工业生产中造成的原油、固体废弃物等污染,匮乏的污染源防治技术使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形势变得严峻。第二,严寒地区船舶航行技术不高。一方面,破冰船技术水平较低。全球范围内掌握破冰船技术的国家较少,破冰船总体数量有限,从某种程度上说,进入北极成为少数掌握破冰船技术国家的“特权”,同时普遍存在船体结构强度不够、动力系统续航能力不强、船舶配套设备抗低温能力较差、船舶燃料环保性较低的问题。③郎舒妍:“极地船舶发展动态及展望”,《船舶物资与市场》,2018年第5期,第34页。另一方面,掌握高水平航海技术的人才较少。北极气候环境恶劣,突发极端天气较多,在船舶航行过程中遇到突发状况需要具有专业航海技术的人员及时正确的反应,确保航行安全。第三,北极海洋空间规划综合能力缺失。海洋空间规划是一项重要的海洋综合管理工具,以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安全为基本原则,解决各类用海矛盾,是治理海洋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但北极海洋空间规划面临着规划体系不成熟、规划主体不明确和规划技术支撑不足的问题,①杨振姣:“海洋生态安全视域下北极海洋空间规划研究”,《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期,第83-84页。导致北极地区海洋空间规划发展缓慢,技术水平相较于一般海洋空间规划也较低。第四,北极生态监测预警技术不足。生态环境监测与生态灾害预警是治理生态问题的重要依据,但北极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许多精密监测仪器无法运行,难以依靠现有技术搭建北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3.4 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面临法律困境
相较于南极治理已经形成的“南极条约体系”,北极治理一直未能形成统一的类“南极条约体系”,各项条约之间独立运行,缺少统筹整合,在规则适用领域、适用要求、遵循原则等方面难免会出现相互掣肘或“管理真空”的问题。分散化的条约、尚不明确的北极法律地位,为北极准确适用国际法律蒙上了一层阴影。一方面,国际法对于北极的适用具有模糊性,②卢静:“北极治理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探析”,《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5期,第68-69页。《公约》中关于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问题是北极大陆架划界问题中难度最大、最为复杂、处理结果溢出效应最大的问题,③章成:“北极海域的大陆架划界问题——法律争议与中国对策”,《国际展望》,2017年第3期,第117页。北极国家纷纷对200海里外大陆架提出管辖权声明,但受北极恶劣的气候、极地勘探技术等限制,北极国家至今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200海里外大陆架的范围,而大陆架主张范围相冲突会进一步引发北极国家在大陆架划界中的纠纷,继而动摇国家间的合作基础。与此同时,《公约》第234条在“冰封区域”的界定中赋予了北冰洋沿岸国开展单边环境管辖的法律权利,沿岸国是否能够真正依据《条约》开展北极航道生态环境防治工作,抑或是借环境保护之名实行航道控制尚不明确,国际“硬法”在北极治理中难以发挥应有效果,法律的模糊性可能会导致有关国家钻法律漏洞,极力拓展本国的北极权益范围,恶化北极治理态势,影响协同治理的合作基础。另一方面,历史悠久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以下简称《斯约》),虽为国际社会共同研究治理北极提供了合作样板,但因其仅适用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且并未涉及北极其他区域的相关事务,故无法发挥作用。④杨华:“中国参与极地全球治理的法治构建”,《中国法学》,2020年第6期,第208页。更因挪威与各缔约国对《斯约》中关于挪威对群岛管辖权范围的划定存在争议,双方各执一词,⑤TorbjØrn Pedersen,“The Svalbard Continental Shelf Contro- versy:Legal Disputes and Political Rivalries,”Ocean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Law,Vol.37,No.339,2006,pp.339-358.可以预见,这种争议将会持续存在,为后续国家间的协同合作埋下隐患。此外,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更多是依靠呈现“软法”性质的规则对治理行为加以规定,对于各参与方来说缺乏强制性,难以形成有效的行为规范,而且《极地规则》等相关强制性规范只能在北极海洋生态治理的部分领域产生效力,治理效果间的差异会影响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能力的提升。
四、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策略
随着北极竞争的“白热化”和安全形势的日趋严峻,协同治理成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实现善治的首要且必然的选择。通过政治、法律和技术等多层面、多维度的协同,以及北极事务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不同子系统间的协同和共同规则的制定,在开放的北极系统中实现共赢和实现整体利益,⑥朱宝林、刘胜湘:“协同治理视阈下的北极治理模式创新——论中国的政策选择”,《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5期,第43页。并借鉴现有治理机制体现出的主体地位平等、相互尊重和共同参与等特点,进一步提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策略(参见图1)。

图1 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策略关系简图
4.1 以“共赢共享”为导向,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在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中,各国应该充分认识到北极关乎人类共同命运,建立共同利益观与责任观,以海洋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共赢共享”为导向,引导各国跳出国家主义的思维困境,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角度审视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倡导域内外国家公平分配北极治理中的权利与责任,建立互信、互尊、互助的合作共生关系,以承认和尊重彼此权利为合作的法律基础,以相互理解和信任为合作的政治保障,以共同研究和解决跨区域问题为合作的主要方向,以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合作的共同目标。①丁煌、朱宝林:“基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北极治理机制 创新”,《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3期,第99页各治理主体在北极治理的不同领域中实现资源共享,加强交流合作,以解决共同问题为导向,治理方式上互商互谅、利益诉求上兼容并包,②白佳玉:“中国积极参与北极公域治理的路径与方法——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23期,第93-94页。在灾害预警、事故救援、信息共享、主体合作和法律完善等方面协同推进,探索理念指导下的国际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合作平台建设的可行性措施,共同弥合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现实缺陷,打造健康的北极海洋生态系统,实现从“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共同体”到“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
4.2 明确治理主体,构建多元治理主体网络
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关系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每个国家、每个组织都有义务和责任参与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工作。总的来说,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主体主要包括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和跨国公司等,每个主体各尽其职,构成系统化的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主体网络。第一,主权国家发挥治理主导作用。主权国家是全球问题,特别是全球环境治理问题的主体,在政策制定、机制构建方面是重要的主导力量。就北极问题而言,北极国家是处理北极事务的核心主体,然而随着北极问题的不断“外溢”,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域外北极利益攸关国在北极治理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共同构成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主体网络。在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中,特别是环北极国家,应该积极展开多边谈判、磋商,制定相应的制度规则来防治北极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此外,还应充分尊重域外国家的北极参与权,将其纳入北极治理多元主体网络体系,集各国之力共同应对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难题。第二,政府间国际组织发挥综合协调作用。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在条约和宗旨规定的范围内,由国家或政府基于某个特定目标而创设的常设机构。它不受国家权力的管辖,依据国际法与相关条约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拥有参与国际事务活动的独立地位。在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中,应充分发挥北极理事会、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等组织的作用,以有效处理好北极生态、环境保护等综合性国际议题。第三,民间组织发挥专业支持作用。一方面要发挥国际环境民间组织的作用,该类组织是由不同国家的人员组织起来,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国际自治组织,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世界自然保护基金、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国际环境民间组织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使其能够致力于全人类的环境保护事业,加之其在环境保护领域专业性比较强,能够有效弥补其他组织的不足,进而更好地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另一方面,要有效保障北极原住民组织(如萨米人理事会、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在北极治理中的参与权与利益诉求,发挥其专业性强、参与意愿强和立场中立等优势,提升其在北极事务中的影响力。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应发挥多元协同共治的主体优势,借助既有合作平台构建国际协同治理机构,给予各主体更多参与权、决策权,逐步拓展北极事务参与范围,充分利用各方力量推进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消解北极治理的“制度困境”。
4.3 加强多边谈判,明确生态治理目标
北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条件以及明显的“政治化”趋势,使得北极事务敏感复杂,北极地区国家博弈日益复杂激烈。各主体间应强化国际多边谈判,制定具体可行的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目标,引导治理机制协同发力。第一,强化谈判合作,积极提供生态治理公共产品。一方面以制度供给为切入点,在尊重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前提下,实现积极推进制度框架由“区域性”向“国际性”转变,从多层面提出改进方案;另一方面提供文化供给,以提升北极居民海洋生态安全意识为核心,结合北极国家相关文化建设措施,共同打造文化传播体系,向域内外国家和国际组织输出北极海洋生态保护的知识内容,提升国际认同度。第二,明确资源开发利用边界和底线。域内外国家应依据底线思维,借助资源评估数据和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以保障北极可持续发展为前提,谈判商定北极公域资源开发的最大范围与资源最大开采量,以生态保护为目的,设立北极海洋生态保护的“国际红线”,平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第三,发挥治理主体的海洋生态监督作用。倡导各国遵循相互制衡原则,发挥各参与主体的监督功能,搭建起多元主体参与的立体监督网络,共同监督北极海洋生态安全状况,每一主体既是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在切实履行海洋生态保护治理职责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生态监督作用,避免相关责任方“投机取巧”、推卸责任,形成涉及准入约束、开发限制、监督制约的标准体系,推动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
4.4 强化法律制定,完善生态治理法律体系
完善北极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全人类共有财产已经刻不容缓,应从国际与国内两个角度开展多方面、全方位的立法工作,以推动和完善北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构建。一方面,着力完善现有国际性海洋法律体系。其一,国际海洋生态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应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根本,《生物多样性公约》《极地水域船舶航行安全规则》《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偏僻海域营运客船航行计划导则》等普适性国际权威规范,《北极海洋油污防治与应对合作协定》《北极冰封水域船舶操作指南》《北极海空搜救合作协定》《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以及即将实施的北极黑碳治理协定等具有针对性的国际权威规范为框架,同时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下文简称BBNJ)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谈判进程中,商讨制定北极BBNJ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规定,①袁雪、廖宇程:“基于海洋保护区的北极地区BBNJ治理 机制探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2期,第83页。在明晰北极海域权属规定,减少用海争端的基础上,从生物保护、航道管控和环境污染防控等方面加强北极海洋生态保护工作。其二,针对目前北极海域开发与航道利用所引发的新问题,在原有法律体系框架下补充并完善北极海上油气开发、北极核污染治理,以及综合性环境保护协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其三,为保证生态保护法律实施效力,还应完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相关习惯法理性、公正的解释程序,提高国际海洋法律体系的现实适用性与规范效率。另一方面,应加强国家层面的北极生态环境政策战略制定。参与北极海域活动的各国应依据国家发展实际与北极生态环境现状,以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协议、法规为基础,具体制定本国北极海洋生态环境研究政策战略,保持国内政策战略对国际协议的灵活适用性,使两者保持同步。构建起层次鲜明、功能一致的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法律框架。
4.5 开展多领域合作,提升协同治理科技水平
北极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决定了防治北极海洋生态环境污染需要较高的科技水平。相比中、低纬度地区的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所需的各项技术尚不成熟。因此,世界各国应该加强沟通交流,开展包括科技、经济等多领域的合作,大力提高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所需的科学技术水平。首先,遵循“科技无国界”,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推进治理大数据共享数字化、智能化。各国政府应该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国内专家、学者参与国际性科研工作;同时吸引国外专家学者来本国进行相关科研工作,强化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合作,不断创新技术方法、突破原有的技术难题,实现国际间共同的科技进步。其次,各国应携手共建北极生态动态监测体系,共同提升北极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水平,建立生态灾害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实现各国救援互联互通,增强北极综合适应能力。最后,各国应保持足够的资金投入,推进北极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科研工作者与原住民的基本生活条件,缓解北极治理赤字现状,增加北极公共产品供给,同时要给予北极科研团队充足的科研资金以保障极地科考工作的顺利开展。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责任,各国都应该摒弃争端、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以开放友好的姿态积极参与到北极海洋生态安全的协同治理进程中。
五、结 语
全球气候变暖与各国日渐增多的北极活动,使北极海洋生态安全面临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的双重压力。北极是全人类的北极,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是北极治理的重要一环,更是推进“冰上丝绸之路”的安全基石。中国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参与北极务实合作,建设“北极冰上丝绸之路”,强化在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保护等领域的合作,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中国政府网,2021年3月13日,http://www.gov.cn/zhuanti/shisiwu/chrome/index.html#! /section/content_9。积极拓展与北极国家、原住民组织和非北极国家在国际组织框架下的协同合作,共同治理北极生态环境、维护北极稳定。可以预见,中国将在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北极冰上丝路”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国际合作,并借此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其中,共同打造“北极蓝色伙伴关系”,构建开放包容、具体务实、互利共赢的国家关系,形成更加稳定的北极治理新秩序。中国积极参与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议题既是出于对国家生存环境的考量也包含着对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追求,是中国为维护本国合理的北极利益、提升国际话语权而做出的必要努力。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不仅对非传统安全治理意义重大,而且是对复杂国际环境下北极治理赤字的重要补充,切实发挥“协同式参与”的作用,推动国际社会达成以“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为基础的一系列策略正当其时。以此引导各国搁置争议,消除疑虑,克服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进程中诸多困境,加强科技合作、开展多边谈判、完善相关法律、条约内容,构建北极协同治理主体网络,鼓励多主体多渠道提供公共产品,缓解全球治理赤字对北极治理的负面影响,保障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的有效开展,继而实现北极海洋生态环境的安全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推动北极良性治理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