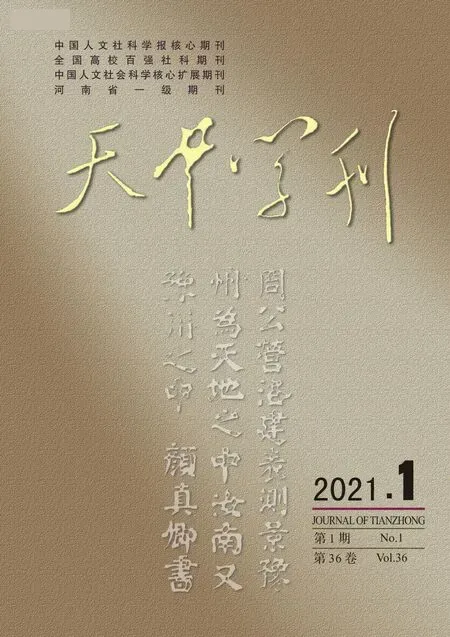问题、方法与视野:谢思炜教授杜诗研究述评
刘晓亮
问题、方法与视野:谢思炜教授杜诗研究述评
刘晓亮
(广东开放大学 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91)
谢思炜教授坚持杜诗研究30余年,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2016年出版的《杜甫集校注》,是谢思炜杜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杜诗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绩。梳理谢思炜的杜诗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他在问题的发掘与辩证、方法的传承与变通、视野的开阔与多元三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特点,值得后学认真总结和借鉴。
谢思炜;杜诗研究;问题;方法;视野
自宋人纷纷研究杜诗以来,杜诗学研究逐渐成了一门显学,历经千年而不衰。评价个中得失,亦可做出有关学术思想、学术潮流等有价值的判断。杜诗学史上取得卓著成就的宋代及明末清初两个高峰至今为人瞩目,学术研究转型后的20世纪杜诗学,所谓“第三个高峰”,其研究成果亦得到了“平议与反思”[1],这些为今后的继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众多默默耕耘的杜诗学研究者中,谢思炜教授的研究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与借鉴。
谢思炜是新中国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学习,师从启功先生。从硕士阶段的江西诗派研究到博士阶段的白居易诗文研究,从1984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到2001年转至清华大学任教至今,谢思炜一直在唐宋诗学领域默默耕耘,其中尤以白居易诗文研究和杜诗研究成绩显著。笔者据中国知网统计,其自1985年发表《〈宋本杜工部集〉注文考辨》[2]至今,已发表相关杜诗研究论文20篇,同时在其专著《禅学与中国文学》中亦有关于杜诗的论述。尤其是2016年出版的其独自校注的《杜甫集校注》,不仅是其个人研究杜诗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杜诗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朱熹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山东历城周永年亦云:“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3]这些做学术和写文章的良言都指示后学要对前贤之成就有所总结,并加以继承和转化,学术与文章方得“能”与“大”。对谢教授杜诗研究之总结,亦复如是。
一、30多年耕耘:杜诗研究概述
谢教授在其《杜甫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前言中回忆道:“笔者三十年前初次通读仇注杜诗,当时曾据《续古逸丛书》本和几种宋本进行校勘①,由此初步尝试文献工作基本方法,稍窥治学门径。其后一直将杜诗作为研究课题。”[4]古代注杜之人,动辄几易其稿②、耗费十几年③,谢教授之杜诗研究,亦继承了前人这种坚持不懈的可贵精神。为清晰了解谢教授之杜诗研究,现将其研究大致分为四类:
(一)杜诗的语词笺释
对杜诗的注释始于北宋,即所谓“二王本”上已有部分注文。后又有吴若本、九家注,至所谓“千家注”。后世杜诗研究大家,如钱谦益、朱鹤龄、卢元昌、仇兆鳌等,皆以注杜为业。因所见材料不同、学识不等,故后世注家对前注加以辩驳在所难免。近现代杜诗研究大家如闻一多、冯至、萧涤非等,皆对杜诗进行过注释。可以说,研究杜诗的第一步工作必须从注释开始。不明语词所指,很难做出基于注释基础之上的其他阐释。谢教授的杜诗研究亦以语词笺释起步。
其《〈宋本杜工部集〉注文考辨》首先将“二王本”注文与其他各本(《九家集注》《分门集注》和《草堂诗笺》)进行对照,进而比较分析“甫自注”“公自注”,并介绍了吴若本注文的特点;其次对“二王本”注文的内容进行分类,分析注文中的典故;最后对影宋本吴若本部分注文进行了鉴别。总的来说,此文是对杜甫自注的整理与研究,也是对杜诗语词笺释的深入研究。清人吴梯《读杜姑妄》对杜甫自注多有申论,谢教授对我们今天重新梳理杜甫自注、对吴梯的申论加以检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谢教授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的《杜诗人物考补》一文乃延续古人如黄鹤、钱谦益、朱鹤龄等,近人陶敏、陈冠明等对杜诗所涉人物之考辨研究,共考补22人。此文之特色在于“旧材料”之“新用”,如对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陈冠明《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以及《唐会要》《大正藏·历代法宝记》《册府元龟》等文献资料的使用。
在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2期的《杜甫的数学知识》一文中,谢教授结合《大衍历》来考杜甫《唐兴县客馆记》所谓“秋分大余小余”;结合唐代流行的六甲八卦冢葬法分析《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所记葬法。其中有关历法问题部分,已先于2012年发表于《傅璇琮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杜甫诗文中的历法问题》;而关于唐代的冢葬法,2014年又扩深一步,有《唐代葬法与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一文,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此等研究乃基于杜甫诗文中某一两个语词之考释,进而做出有关文化背景方面的研究,所谓“小中见大”的典范。
有关杜诗与六朝文学尤其是《文选》的关系向为杜诗学研究者所注意。早在民国时,已有李详《杜诗证选》。谢教授发表于《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的《杜诗与〈文选〉注》一文可谓李详之仿作,但又有所扩深。一般人研究杜诗受《文选》之影响,主要秉持“无一字无来历”之说,从《文选》中寻绎杜诗之典源。谢文则主要讨论了杜诗与《文选》李善注、五臣注的关系。“杜甫在写作中应是首先参照李善注,同时也参考五臣注。”因《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的流行,唐人写诗除了熟读《文选》,对注释亦了然于胸,故受其影响在所难免。
语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某些词语会表现出“由俗到雅”或“由雅到俗”的转化。杜诗中有好多唐代流行的俗语,时至今日则有可能因不明其意而致诗意误解。研究杜诗中的俗语先有蒋绍愚《杜诗词语札记》、曹慕樊《杜诗杂说全编》等。谢教授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1期的《杜诗俗语词补释》一文乃绍继前贤之作。此文分动词、形容词、名词、副词、连词五类分别对杜诗中的57个俗语词进行了考释,对杜诗的诗意理解裨益甚大。
谢教授在《校注》“前言”中谓:“注书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由于受整体研究水平所限,旧注在官制、科举、军事等唐代专门史方面有较多知识局限,在涉及天文历算等专门之学时也往往力不从心……对《唐兴县客馆记》所记秋分‘大余小余’,杨伦则直言‘即观朱释亦未明’。又如《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铭》,杜甫实为说明继祖母不能与祖父合葬,旧注不知是否有所避讳,亦不予深究。”[4]由此可见谢教授之《校注》乃其多年对杜诗语词笺释的集大成之作。
(二)诗艺阐释研究
杜诗之文学成就除了其蕴蓄的道德关怀,便是其艺术特色。近体诗发源于六朝,至唐初经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实践,最终定型。但真正成为后人宗尚,却得力于杜甫的全力创作及其艺术感召。故自白居易始,后人总能从杜甫这里找到其想要学习的技巧。因此,历来杜诗学研究者,皆对杜诗之艺术予以深刻阐释。
谢教授对杜诗诗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杜诗的“叙事艺术”。《〈丽人行〉与〈羽林郎〉——一个改造传统的示例》(《名作欣赏》,1988年第4期)一文虽为个案研究,但所讨论问题却异常丰富。首先,对《丽人行》之“讽刺说”主旨进行了纵向梳理;其次,重点分析了该诗之叙述方法;再次,对比分析了《丽人行》与《羽林郎》的相似性及《丽人行》对传统妇女描写的改造。该文注重学术史的梳理,同时亦注重横向比较,纵横结合恰到好处。此外,该文还顺带讨论了传统诗歌妇女形象的演变;在分析具体问题时,注重引用国外理论,如苏联巴赫金学派关于文学、文学体裁的观点,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蒂娃关于诗学语言的观点,结构主义文论家罗朗·巴赫特的叙述学理论,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观点等。
谢教授发表于《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的《论自传诗人杜甫——兼论中国和西方的自传诗传统》一文属于比较文学研究,对杜诗的自传性书写具有开创意义。该文指出:“与西方诗歌比较,中国(文人)诗歌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不在于它的意象性、神韵、格调等等,而是它进入社会、进入历史的一种特殊方式,即自传方式。”文章首先梳理了杜甫之前中国自传诗的发展,接着从三个方面对杜甫自传诗的特征加以论述,最后通过分析西方自传诗人代表英国的华兹华斯和美国的惠特曼,将杜甫诗歌的自传性与西方自传诗进行了对比。
通过对《丽人行》的个案研究及杜诗自传性书写的透视,谢教授于《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推出了其杜诗叙事艺术研究的总结之作——《杜诗叙事艺术探微》。该文首先对民间叙事传统与文人记事传统进行了辨析与梳理,然后指出杜甫在面对“民间叙事传统、文人抒情记事传统和文人仿作叙事诗传统”所要做的两件事:“一是发展提高文人仿作的叙事诗,开拓更多的题材,注入更鲜明的社会意识,使之成为真正的文人叙事诗”;“一是改进充实原有的文人抒情记事诗,扩大体制,加强批判精神”。这两件事并非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再然后便详细分析了杜甫所做的文学“改造”:结合《兵车行》和《丽人行》谈杜诗“记事对叙事的改造”;结合“三吏”“三别”谈杜诗叙事和记事的拼合;结合风俗诗(如《负薪行》《最能行》)和寓言诗(如《客从》)谈杜诗“叙事的替代”。最后加以总结:“这两种形式(叙事诗和抒情记事诗)的结合,才使得杜诗具有‘诗史’的性质,具有可与社会历史本身相媲美的完整性和深厚性。”从叙事艺术来探讨杜诗的“诗史”性质,视角非常独特。
谢教授发表于《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的《杜诗的自我审视与表现》一文是继续杜诗的自传性研究,并开宗明义道:“自传性是杜诗的一个基本特点。”然后该文依次讨论了下列问题:杜诗的自我审视,一方面是情感发现和道德自觉的过程,另一方面则伴着反省自嘲和对自觉主题的拆解。由此引出杜诗在内容和修辞、风格上的一系列变化:穷愁生活的描写、修辞上的用拙以及具有反讽意味的戏谑风格。在文章结尾谢教授总结道:“戏谑态度后来在韩愈诗文中又有所发展,在苏轼身上发挥得尤为淋漓尽致,那是由于他们在追求思想目标或表达个性自由时遇到了更多的挫折和限制,但在基本格调上显然与杜甫有一脉相承之处。”
长期以来,谢教授对杜诗叙事艺术的研究与阐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道德阐释研究
杜甫被称为“诗圣”,主要因其博大的儒家情怀。故历来论杜诗者,多发掘其诗所蕴寓的儒家伦理道德。谢教授对杜诗的道德阐释也主要基于其道德关怀,并对杜甫之精神探索和思想界限予以深入探析。
谢教授发表于《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的《杜诗的伦理内涵与现代阐释》一文主要论述了“杜甫在中国传统道德性文学中的典型意义”。该文指出:“杜甫成为一个道德诗人,与那个道德意识低落而正趋于复苏的历史转变时期紧密相关,他自己在其中也经历了由道德的不自觉逐步走向自觉的转变过程。”并以“三吏”“三别”和《北征》等诗为例,分析了杜甫“在文学中深刻展现了道德意识背后复杂而深厚的社会内容和历史内容”。文章最后,呼应了标题的“现代阐释”,指出“杜甫的以伦理意义为支持的文学实践,又确实是九至十六世纪新儒学思想革新运动的先导和有力支持”,并指出该文的所谓“现代阐释”,是将杜诗之伦理内涵放到儒学发展的背景上阐释,来见出杜诗中所体现的“儒家伦理的诸种困境,体验到在纯思想论述中无法看到的儒者个人的道德发现、完善乃至动摇、失落的真实思想过程”。该文不仅从文学角度研究了杜诗,且不乏深切的现实关怀。
谢教授发表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的《杜甫的精神探索与思想界限》一文梳理了杜甫的精神成长之路——从理想破灭到社会批判——再到最后自我人性的发现。通过分析杜甫的人性关怀,作者指出了杜甫的思想界限,即杜甫最终无法逃脱中国专制社会传统政治格局和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思想格局的限制。杜甫的思想遗产尽管包含了道德自觉、社会批判、人性关怀等内容,但在整体上或许正属于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权威平民化”的有效组成部分。该文可以说是《杜诗的伦理内涵与现代阐释》和《杜诗的自我审视与表现》两文的总结与深化,体现了谢教授杜诗研究的一贯性特点——谢教授对杜诗某个问题的关注,并非点到为止,而是形成一种持续性关注。
(四)文化学视角下的杜诗研究
文学研究引入文化学视角,不仅丰富了文学的阐释,而且增加了文学阐释的厚实之感,但这无疑给研究者增加了难度。所谓“打通文史哲”并非每一个文学研究者都能做到,多数仍停留在一种“口号”或“设想”阶段。谢教授的杜诗研究,有一部分是基于杜诗的基本阐释,从而做出有关诗学、史学等方面的研究,本文统称之为“文化学视角”。
谢教授发表于《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的《杜诗解释史概述》一文将诸多杜诗解释按照线性发展分为七类:白居易的伦理解释,从道德层面解释杜诗;李商隐和黄庭坚的诗艺解释,对杜诗从技巧层面加以分析和模仿;引述伽达默尔的“体验美学”理论来分析宋人关于杜甫年谱的编订;由对杜诗的阐释来观照杜诗阐释者所处的时代;运用传统以意逆志的诗学阐释方法对杜诗创作意图的解释;断章取义式的解释,把解释当作创作,阐发解释者自己的学说或思想;诗史说的历史价值。此文不仅对杜诗解释史提出了自己的分类,还指出了各种分类存在的不足及其价值所在,如关于“诗史说”,文章指出这种阐释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将本文与历史统一起来,在历史框架内理解本文的新的可能”。此外,作者在文章开头也总结出杜诗解释应该持有的一种“共性”追求:“杜诗解释史也体现了解释的双向性特征,不但逐步揭示出杜诗本身的丰富内涵,同时也在不同时代以多种方式反映了解释者对他们的处境和他们自己的理解。因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追寻对杜诗的某种最终的、绝对的、唯一的解释,也并不是单纯推翻或驳正前人的种种解释,而是发现这些解释和它们的历史条件的关联,说明这些解释如何成为可能的,从而显示杜诗解释曾有的和还会有的丰富的历史可能。”此外,该文亦引用了国外诸多理论,如心理重建解释学、结构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等。
杜甫作为儒家伦理的代表,长期以来研究者多关注其儒家思想,其诗歌所体现出的佛教教义,尤其是禅宗思想,也得到了诸如钱谦益、郭沫若、吕澂、陈允吉等学者的考证,但究竟其信仰南宗还是北宗,学界一时论争难分。谢教授发表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的《净众、保唐禅与杜甫晚年的禅宗信仰》一文则撇开南北宗的争执,根据《历代法宝记》的材料,从禅宗支派净众宗和保唐宗来探讨杜甫晚年漂泊四川时所受的影响。该文对杜诗《望牛头寺》“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一联进行了分析,认为“不住心”即杜甫受净众“无念”法门影响的体现。此外,“杜甫如何在主体伦理实践中遵循儒家思想,以及这种理想如何遭遇困境,以致他晚年如何转向宗教思想寻求出路”,谢教授在其《禅宗与中国文学》中亦有专门论述。该文属于旧材料的新利用,然在未经人使用的情况下,亦可谓“新材料”的发现与利用。该文还提示了一个事实:“恰恰从杜甫开始,儒家思想的认真信奉者和实践者们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对禅宗思想的影响做出回应。”
自唐元和年间开始,“李杜优劣论”成了一桩诗学公案,久讼不息。谢教授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的《李杜优劣论争的背后》一文亦从这一公案入手剖析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在诗坛影响和诗学观念上的区别、变化和竞争。
谢教授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的《唐代葬法与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一文属于对唐代葬法的研究。文章首先考证了《墓志》所载卢氏;继而考实《墓志》为杜甫作。文章主要根据唐代六甲八卦冢葬法分析杜甫祖父杜审言所葬系乾冢壬穴,卢氏取甲穴。这种葬法合乎唐代五姓葬法中杜姓属商之说,而卢氏不与夫合葬,合于唐代士族的通行做法。该文特色在于多种材料的运用,如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续补》、洛阳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李献奇和郭引强编《洛阳新获墓志》、魏津《偃师县志》、李岗等《西安南郊唐贞观十七年王怜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等文献,为该文之考证论述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谢教授在其《唐宋诗学论集》的“后记”中曾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特点和成就进行过一次总结:
文学史研究一方面以文献工作和史实考察为基础,另一方面又与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密不可分。前一方面依靠材料说话,有事实管着;后一方面需要思想的理解能力,有思维逻辑管着。但正像弗罗斯特(Frost)的诗里说的,未选择的路总给人留下遗憾。我所从事的文学史研究,让我在向这两个方向努力的同时感觉遗憾的是:既缺少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也缺少哲学的专业训练,在两个方向上都走不了太远。走到目前这一步,就人生而言大概已基本“定型”,不大可能返回去重新开始了。回头看一下勉强可算是“学术”的这些文字,就事实考察而言,只有几个分散的点,始终未能连成一片,因为没有读那么多的书,被“分段”、专题研究方式限制住了;就对文学现象的理解而言,只反映了自己在那一时期的观察视野,所能达到的度,其中某些刻意求取之处,浅深得当与否,不仅自知,读者亦知。[5]
这段话是谢教授于2002年2月说的,十几年过去了,以杜诗研究来说,他所谓的两个努力的方向相对于以前均得到了进一步推进;而他曾经的“遗憾”和所谓的“只有几个分散的点,始终未能连成一片”,通过十几年的积淀,亦得到了部分“偿愿”。
二、杜诗研究特点分析
1400多首杜诗犹如一座宝库,凝结着时代印记和思想履痕,故为各个时代的研究者提供了挖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并总结谢教授的杜诗研究特点,只是现阶段的一步工作。即使像《校注》这样集大成之作的出版,也并不能使我们断言谢教授之杜诗研究不会再出现新的成果,相反,其可能在《校注》的基础上做出更大的成就。分析谢教授的杜诗研究特点,也可为更多的杜诗研究者以及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一种“方法论”参照。
(一)问题的发掘与辨证:杜诗阐释的必要性
杜诗虽经千年阐释,但其所蕴寓的问题还有很多,即使已被发掘的问题有些亦存在争议,故需要辨析,这些都提示出杜诗阐释的必要性。
一是对杜诗所蕴寓问题的发掘。对杜诗所蕴寓问题的发掘和解决,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杜诗。比如杜诗中所涉及的典章制度、名物、职官、杜甫的诗学思想等。纵观谢教授之杜诗研究,其抓住了杜诗的“自传性书写”“叙事艺术”“伦理内涵”等几个关键问题进而做了多角度研究,层层深入。尤其关于“叙事艺术”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杜诗及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对“叙事学”研究、现当代诗歌的叙事艺术研究亦有所帮助。
二是对杜诗研究诸多问题的考辨。杜诗研究积累下众多成果,当然也存在诸多未解的问题。谢教授在研究杜诗时,亦注重对这些未解问题的梳理与考辨。比如“二王本”上之“甫自注”“公自注”这些注文、杜甫之“忠君”思想、杜甫的禅宗信仰、《卢氏墓志》是否杜甫代作、李杜优劣论等问题,谢教授通过排比材料或观点,加以辨析,不仅对这些争论未解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找到了部分问题的答案。如谢教授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的《唐代葬法与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一文围绕《卢氏墓志》的作者问题,梳理各种不同观点:黄鹤疑此《卢氏墓志》为杜甫代其叔父杜登作;钱谦益驳黄鹤,认为乃代杜闲作;朱鹤龄“弥缝”钱谦益之失,亦以为代杜闲作;今人闻一多采朱鹤龄之说;洪业始辩驳“代杜闲作”之说。然后,谢教授综合诸家观点指出此志确为杜甫作,对文中存在争议的“某”字,谢教授指出:“‘某’字并不是作者自称,而是杜甫避父讳不书,所指即是其父杜闲。大概前人皆习惯于以‘某’字自称,因此对本文‘某’字出现误会。”
(二)方法的传承与变通:杜诗阐释的可能性
学术研究不仅需要“才、学、识、德”④,亦需要“术”,即所谓方法。谢教授之杜诗研究,在方法上继承前人,又有自己的变通。
一是细读文本。谢教授在《校注》“前言”中提示了一条治学的“重要经验”:“注书是细读原著的最好方式,当研究进展到一定程度,势必要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很多被忽视的问题,在注释工作中得以发现。一些问题看似已有成说,但在注释中发现还有待推敲。”这既是“注书”的经验,亦是其细读文本的心得总结。他的杜诗研究,可以说皆基于细读文本。对“影宋本吴若本部分注文”的鉴别,若非细读,恐难以鉴定;对《丽人行》与《羽林郎》的叙述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通过对杜诗中“自我审视”所涵盖的“双重焦点”的分析,得出其“个人阅读经验”:“正是这种多面性和内在矛盾张力为杜诗赢得众多观众,而并非单纯道德意义上的‘诗圣’使他名压众人。”[6]等等。
二是无征不信。谢教授在一篇总结其师启功先生治学特点的文章中提到一点——“无征不信”[7]。谢教授之杜诗研究亦复如是。如谢教授发表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的《净众、保唐禅与杜甫晚年的禅宗信仰》一文,谢教授详细征引并分析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所载宝应、永泰年间“无相传法”“无住出山”之事,又据唐史所载严武、高适、杜鸿渐、崔旰等都深深介入无相门下继法之争,而杜甫与这些人皆有交接,故对净众在成都的活动及法争应有耳闻,最终吸引其对禅宗的注意,这亦可从其成都以后的诗作中找到印迹。从佛书、史书记载来推测杜诗之禅宗信仰,进而从其诗歌所写来印证这一事实,征引材料翔实可靠,故其结论亦较为准确。
三是纵横比较。自唐韩愈始以“李杜”并称,后人逐渐开始讨论“李杜优劣”,或者从杜甫身后寻找受其沾溉者,如白居易、李商隐、黄庭坚等,加以比较论述;或者将杜甫与其同时代之高适、岑参、王维等加以比较。这些研究仅限于中国传统诗歌范围之内。冯至曾将杜甫与歌德进行比较,从“两个诗人的同和异”“诗与政治”“诗与自然”等方面展开论述⑤。谢教授之杜诗研究,不仅将杜甫置于中国传统诗人的对比之中,如讨论杜甫记事诗的感情表现方式,提及嵇康、阮籍、陶渊明、庾信等(《论自传诗人杜甫》);而且将杜甫置于中外诗人对比之中,由杜甫之自传诗来比较西方的自传诗,如华兹华斯、惠特曼等。其对中外自传诗传统的梳理与比较,亦十分见功力。
比较诗学的研究虽有其限制性,但若运用得当,确能收到“比较”之效。谢教授将杜诗置于中外、古今的纵横比较之中展开论述,拓展了杜诗阐释的可能性。
(三)视野的开阔与多元:杜诗阐释的丰富性
视野的广狭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成果的厚重与否。因此开展文学研究伊始,就应有开阔的视野作为“先导”。谢教授之杜诗研究,体现了其视野的开阔与多元,也正因为这种视野,从而丰富了杜诗的阐释。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材料的“旧与新”及其利用。“新材料”之于学术的推进至关重要,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贤早有论述。但光占有“新材料”而不懂利用,则无异于买椟还珠。另外,除去出土材料的发现,材料的“旧与新”又是辩证的,过去的旧材料久置不用,而一旦被人发现其可用的部分,“旧”的便变成了“新”的。谢教授之杜诗研究,除了对近代以来“唐史各领域研究”“唐语言研究”成果的利用,还将诸多“旧材料”转换成了新材料,如《册府元龟》等大型文献,旧注家极少有人利用;此外便是对新材料的利用,如新见唐人墓志、敦煌文献(《历代法宝记》等)。诚如其《校注》前言所谓:“本书尽可能利用这些材料和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对杜诗所涉及的背景、编年、地理、人物及语言运用等各方面问题加以探讨。对杜诗语言运用,除核查各种书面成语出处外,还要根据见于敦煌文献和其他材料的各种语言用例,说明大量俗语口语词及社会流行语的用法;除对前人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加以查证外,还有必要对杜诗中的自造语和一些特殊用法加以鉴识。这样才能全面了解杜诗的语言追求。”这虽是仅就其《校注》而言,但其实是对其杜诗研究心得的总结。谢教授懂得如何将“旧”材料变成“新”材料,又懂得如何用新材料来证实或辩驳旧说。总之,材料的利用为阐释杜诗提供了确切的帮助。
二是理论的引用与化用。材料是研究的基础,而理论对于研究是一种指导。谢教授之杜诗研究,对于理论的引用,并非仅仅局限于文学理论(上文已经述及,此不复述)。这种多学科理论的引用,并转化为自己研究的支撑,使其研究显得十分厚实。比如引入结构主义文论家罗朗·巴赫特的叙述学理论来分析《丽人行》的叙述方式,让我们清晰地明白了《丽人行》这种“取消了自己作为作者、作为诗人的自我形象,采取了非己性的单纯叙述者的语言”的特殊性。
三是打通文史哲的界域。中国古代文学所体现出的“文史哲不分”的现象在先秦文学中表现尤为明显,后世文史分途,术业专攻。尤其现当代学术研究工作者,限于专业,故往往多“专家”,而鲜有“通才”。也因此,“打通文史哲”基本停留于一种口号或一种理想,与实际研究不符。谢教授作为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深受老一辈学者治学特点与人格情怀之熏染,故将文学与史学、哲学融合,从而收获经得起推敲的成果,如谢教授从对历史的梳理来辨析钱谦益、卢元昌等所秉持的讽刺比兴说,从儒家思想的发展来透视杜诗的伦理内涵,从前人不够重视的释道农医卜算之类的文献中发现杜诗的语言真意,又从杜诗中来见出制度、伦理、诗学思想、学术、风俗等内容。总之,文史哲等多个领域的融会贯通,极大地丰富了杜诗的阐释。
以上对谢教授30多年的杜诗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对其研究特点予以总结,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若想全面了解谢思炜教授的杜诗研究成就,最好的凭借无疑是其新近出版的《校注》。近几年杜诗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日渐繁盛,为开展杜诗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而对如谢教授这些杜诗学者研究成就的总结,亦是构建“杜诗学史”的必备工作。
① 此处“校勘”的结果即其撰写的《〈宋本杜工部集〉注文考辨》。
② 如浦起龙在《读杜心解》“发凡”中称:“事始辛丑夏五,期而稿削,又八月而稿一易,又十一月稿再易。”
③ 如卢元昌在其《杜诗阐》“自序”中称据其注杜始于“乙巳(1665)秋”,“何朝夕,何寒暑,不手是编”,梓于“壬戌(1682)夏”,积十八年。
④ 按,“才、学、识”为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的治史者应具备的能力,“德”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治史者能力的一种扩充。
⑤ 详参赵睿才《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1] 赵睿才.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5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5:136–143.
[3]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M]//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4.
[4] 谢思炜.杜甫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5] 谢思炜.唐宋诗学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29–330.
[6] 谢思炜.杜诗的自我审视与表现[J].文学遗产,2001(3):40–48.
[7] 谢思炜.启功先生的治学与育人之道[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3):50–55.
Problems,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Review on Professor XIE Siwei's Research on DU Fu's Poetry
LIU Xiaoliang
(Guangdong Op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91, China)
Professor XIE Siwei has been studying DU fu's poetr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has published a lot of research papers. His masterpiecewas published in 2016. Combing his researches, one can find thre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in problems-digging history, methodology-inheriting and vision-broadening, which is worth studying by the followers.
XIE Siwei; DU fu's poetry research; problems; methods; perspective
I206
A
1006–5261(2021)01–0048–08
2020-08-07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杜甫研究中心”资助项目(DFY20188);2019年度《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专项课题(2019GZY20)
刘晓亮(1985―),男,河北迁西人,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