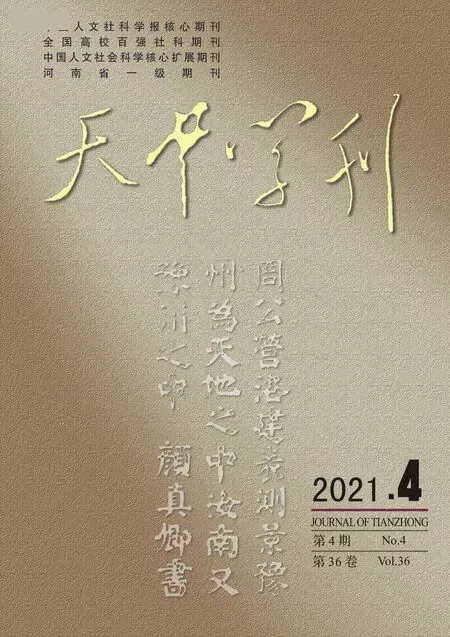论元末文人“崇杜”与“学杜”
武君
论元末文人“崇杜”与“学杜”
武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元末文人对杜甫流离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将杜甫作为忧国忧君、忠君爱国的精神偶像是其“崇杜”的主要表现。故此,他们从老杜的襟怀中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从杜诗中提取感动人心的精神力量。此外,元末文人“崇杜”还表现在他们对杜甫放怀自适、安其所遇的人格魅力的激赏。在“崇杜”的同时他们也“学杜”,杜诗被作为元代诗歌启蒙教育的典范教材,“仿杜”与“注杜”成为一时风尚,并且以杜诗为评裁标准选编、评点当代诗作。当然,元末文人“学杜”更注重对杜诗的取法,在对杜诗的取法与练择中,形成了他们独具个性的诗学内容。
元末;杜甫;精神偶像;诗学取法
傅若金《和宋子与病中》诗云:“去国休题王粲赋,忧时苦爱杜陵诗。”[1]元末天下离乱,杜甫其人、其诗受到文人再次关注。元末文人“崇杜”,首先表现在对杜甫流离愁苦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与杜甫产生的心灵共鸣,他们从老杜的襟怀中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其次,他们将杜甫作为忧国忧民、忠君爱国的精神偶像,从杜诗的忧思深广中提取感动人心的精神力量。此外,元末文人“崇杜”还表现在他们对杜甫放怀自适、安其所遇的人格魅力的激赏。在“崇杜”的影响下,他们也“学杜”,杜诗被作为诗歌启蒙教育的典范教材,“仿杜”与“注杜”成为一时风尚,并且以杜诗为评裁标准评点当代诗作,又以杜诗注释时人诗作。当然,元末文人“学杜”更注重对杜诗的取法,在对杜诗的练择与取法中,形成他们独具个性的诗学内容。现有的杜诗元代接受史研究已有可观成果,然尚未见系统探讨元末“学杜”方式及对杜诗取法问题的研究①。
一、元末文人“崇杜”的表现
元顺帝后至元三年(1337年)夏四月,杜甫被元朝追谥为“文贞”,褒誉这位前代诗人经天纬地、道德博闻之“文”和慈惠爱民、恒德从一之“贞”。张雨《赠纽怜大监》诗后注曰:“请以蜀文翁之石室,扬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学宫。又为甫得谥曰文贞。以私财作三书院。遍行东南,收书卅万卷及铸礼器以归。虞奎章记其事,邀予赋诗如上。”[2]可见,追谥杜甫对时人来说是一件文化盛事,而就在这个月,大元王朝恶兆频现,天灾人祸此起彼伏:“甲戌,有星孛于王良”“辛卯,合州大足县民韩法师反”“庚子,太白昼见”“龙兴路南昌新建县饥”[3]。在多事之际,树一尊道德文章典型,再次强调“忠孝节义”的价值观,对于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元朝来说,本不足为怪,而就在此后的战争乱离之中,“文贞”成了元末文人的一剂安慰之方,在漂泊困顿中,他们重新体会了老杜的精神实质。
元末文人尊崇杜甫,首先表现在他们对杜甫流离愁苦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与杜甫产生的心灵共鸣。在他们眼中,杜甫的诗、诗中的杜甫,总是一幅飘零、流离的形象,贡师泰《忆侄景》云:“干戈连数岁,书问动经时。寂寞扬雄赋,飘零杜甫诗。”[4]549在干戈不息的岁月中,文人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杜甫飘零之苦,亲友的挂念只能是梦中的相会,朋友间论交、邂逅也往往染上了生死契阔的悲苦:“湖海论交伯仲知,死生契阔每攒眉。别来岁月如长夜,相见衣冠异昔时。有酒阮公浑得醉,无家杜甫不胜悲。”[5]94此时此际,杜诗似乎成为他们诠释、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人生良会和尽情抒发依恋不舍之情的最佳载体,倪瓒说:“余与宗普道兄别十有六年矣。忽邂逅吴下,杯酒陈情,不能相舍,老杜所谓‘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者,讽咏斯语,相与怆然,人生良会不易而况艰虞契阔若此者乎?”[6]在飘零之中,他们认识到此身只是客,希望通过金卮杯盏来安慰这失去凭依、漂泊无定的愁苦。然而时事多忧,岂是一醉可以消除?别离的泪水,又岂能抵得过世事纷扰在他们心灵中留下的创伤?在兵戈扰攘之际,杜甫哀时、忧天下的精神再次被他们提出,且有了更加深刻且感同身受的体会,钱惟善《题杜甫麻鞋见天子图》诗云:“四郊多垒未还乡,又别潼关谒凤翔。九庙君臣同辟难,十年弟妹各殊方。中兴百战洗兵甲,万里一身愁虎狼。寂寞当时穷独叟,按图怀古恨茫茫。”[7]一位寂寞穷困的老翁,四方漂泊求索,杜甫的形象仿佛穿越时空,成了元末文人的缩影。
元末文人“崇杜”更多表现在对杜甫忠节精神的肯定。他们将杜甫当作忧国忧民、忠君爱国的精神偶像,从杜诗的忧思深广中提取感动人心的精神力量。宋人即体认到杜甫“一饭未忘君”的精神价值,到元末这种“一饭不忘君”的精神得到时人更多赞许,李存《杂说》云:“杜甫诗令人浑然,端且厚,慨然有忠节,舍是吾未见其多益于人也。”进而他列举张翥居钱塘时为人传慈孝、节义之事,而“长幼无不慷慨长叹至流涕,或恸哭不能终观”[8]。出于对杜甫忠节之事的赞扬,元末文人每将杜甫与屈原、诸葛亮等前代忠义之士并举,沈梦麟《绿静为邱通政赋》诗云:“漱渴每思唐杜甫,浊清独美楚灵均。老夫屡有凭阑兴,只恐衰年咳唾频。”[5]102陈旅《明美堂记》曰:“三代以降,世之豪杰,孰有如诸葛孔明者乎……其所为盖三代之王佐也……自寿(陈寿)以来,世之真知孔明者,孰有如唐之杜子美者乎?观其流落成都,数谒故祠,锦亭之东而抚其遗树,感慨悲歌,诗凡数篇,皆足以发千载之忠愤,而直以伊吕与武侯相伯仲。”[9]他们认为杜甫与屈原、诸葛亮虽出处不同,但忠君爱国的思想是相通的。杜甫的忠义之气、一寸丹心形于歌诗,后人“颂其诗,读其书”,忠君爱国之心、缱绻恻怛之意油然而生,为千秋万古称颂。
当然,元末文人“崇杜”还表现在对杜甫人格精神的另一个维度——放怀自适、安其所遇之人格魅力的激赏。贡师泰《草堂诗序》云:“及唐安史之乱,而杜子美又筑草堂于浣花溪上……然而间关寥落之际,即其所处,未尝不长吟醉饮,放怀自适,以安其所遇焉。”[10]189元末文人对杜甫这一人格魅力的崇仰,一方面充分表现于元人以杜甫诗语命名其所居庭院;另一方面表现为采杜甫诗韵以资燕集唱和。顾瑛“玉山草堂”取自杜甫《崔氏东山草堂》诗句“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玉山佳处之“浣花馆”取老杜“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之意;“金粟影”取自杜诗“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句。关于玉山佳处场馆得名,刘季《玉山雅集诗歌创作中的崇杜倾向》一文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而据该文统计,玉山雅集分韵赋诗31次,引杜诗一家即有14次[11]。所引杜诗如《夜宴左氏庄》“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风林纤月落,衣露净琴张”,《八月十五夜月》“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羌村三首》“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月》“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携妓纳凉晚际遇雨》“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等都是杜诗清逸、流美之句,表现为一种清净适居、赏心悦目的审美取向。此外以杜诗用作燕集唱和的韵料也并非仅局限于玉山草堂的唱和之中,引杜诗起韵在元末成为一种时尚,钱惟善有《久旱酷热以杜诗“林热鸟张口”为韵分得口字》诗,陈镒有《次韵孀妇叹(用杜工部诗韵)》《夏日周子符过访用杜工部严公仲夏枉驾草堂诗韵二首》,贡师泰《春日玄沙寺小集序》载至正二十一年(1361)春正月廿六日,其与廉公亮、李景仪、答禄道夫、海清溪等人游玄沙寺,以杜甫“心清闻妙香”句分韵,各赋五言诗一首,“示闲暇于抢攘之际,寓逸豫于艰难之时”[4]595,无论如何,在兵乱中,元末文人总能从杜甫那里找到心灵安放之地。
二、元末文人学杜的方式
在“崇杜”的推动与影响下,元末文人也不断尝试“学杜”,那么他们如何“学杜”?他们每每认为“学杜”重在学习杜甫的襟怀,而襟怀蕴含在诗歌文本中,因此,他们“学杜”,依旧是从杜诗文本出发,首先将杜诗作为儿童诗歌启蒙教育的典范教材。贡奎《岁晚写呈大人》诗云:“堂前双亲袖梨栗,调笑吾儿读杜诗。”[12]又欧阳玄《题子美寻芳图》云:“吾年三岁声吾伊,慈亲膝下教杜诗。”[13]由此可见,在元代,杜诗成为儿童必读读物。李祁《刘申斋先生文集序》载刘申斋以杜诗作为教学内容及杜诗对他本人诗学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予尝侍教于先生,先生极知爱予,宜不可辞,因念予之生也。后数十年,又远隔江湘数百里,不及见庐陵先辈诸老,而犹以得见先生为幸。先生每见予,辄举老杜‘好心事’‘真颜色’之句,为予诵之,予亦每念不忘今也。”[14]655
将杜诗作为童蒙训读的范本也表现在元代以杜诗为范例撰成的诗法、诗格类著作。旧题杨载注《诗解》又名《杨仲弘注杜少陵诗法》《杜律心法》,该著以杜甫诗篇为纲目,下注具体格法,如《秋兴》篇下有“接项格”“交股格”“纤腰格”“双蹄格”“续腰格”“首尾交换格”“首尾相间格”“单蹄格”详致阐释杜诗诗法。佚名撰《杜陵诗律五十一格》与《杜律心法》略同,其他如《诗法源流》《诗法正宗》《诗家一指》等均标举杜诗或援引杜诗为证,甚至如《联新事备诗学大成》《诗学大成押韵渊海》《群书通要》《韵府群玉》等启蒙工具书亦大量摘引杜甫诗句,以指引、垂示初学者入门。以杜诗训蒙,在元代往往还表现在抄写杜诗,在书法学习过程中加入对杜诗的研习,许有壬《题龙处厚所藏子昂画马并书杜工部诗》云:“世知公书画,不知诗更雅。时还写杜诗,千金莫酬价。”[15]李祁《孙氏遗金集序》载新安孙氏以抄写杜诗为训蒙家学:“新安孙彦能从军永新,畏事如畏虎,恒闭门读书。时伸纸信笔作汉隶,亹亹逼近古人,予意其当得师法,决非苟焉者。其后因抽其架上书,乃见其先君子叔弥所书杜诗一帙,然后知其师法乃得家传,诚有非苟焉者。初叔弥善蒙古书,入京师,书宣敕,积劳调官湖广,又善书汉隶,尝取老杜五、七言律,书之计七百七十四首,通作一帙,将以遗其子若孙焉。壬辰兵兴事变,携至山中无恙。”[14]657
元末文人“学杜”的方式还表现为“仿杜”与“注杜”。“仿杜”主要集中于集杜诗的创作及对杜甫诗句的化用。集杜诗在元末风行一时,如郑允端集杜诗《桃花集句》。而化用杜甫诗语在元末人诗作中亦俯首可拾,如谢应芳《题杜拾遗像》有“国破家何在,穷途更暮年”句,明显有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痕迹;袁凯《客中除夕》有“戎马无休歇,关山正渺茫”句,化用杜诗《登岳阳楼》“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王冕《过江南》有“何时卜邻住,会老细论文”句,显然是拟自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清人楼卜瀍《铁崖乐府注》,常以杜诗为杨维桢诗出注,如《丽人行题玉山所藏周昉画卷》“杨白花飞愁杀人,美人如华不胜春。锦鞯驮起双凤缕,黄门挟飞五花云”,注曰:“按杜甫《丽人行》,为诸杨赋也。词云:‘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又云:‘黄门飞鞚不动尘。’”又如《邯郸美人为赵娘赋也》“邯郸市上美人家,美人小袜青月牙”,注曰:“杜甫诗:‘细马时鸣金腰袅,佳人屡出董娇娆。’”[16]在《铁崖乐府注》中,以杜诗为注者共出现34次,可以想见杜诗对杨维桢诗作的影响程度。翁方纲《石洲诗话》载杨维桢“自命学杜,正如老旦扮外,上场道白,时露情态”,又以其所作“嬉春体”佐证其“去杜不远”的自负之言,以此批评当时学杜者专注于模仿杜诗语言外在特征的弊习[17]。足见,元末文人学习杜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能否达到置于杜集、孰能辨之为标准,寻求与杜诗字拟句模的相似度。“注杜”也是元人学杜的一个重要方式,王逢有《日本进上人将还乡国,为录予所注〈杜诗本义〉,留旬日,赠以八句,藤其国中著姓》诗,可判断他曾著有《杜诗本义注》一部,此书今不存。现存元末杜诗注本主要有张性《杜律演义》、赵仿《杜工部五言赵注》、董养性《杜工部诗选注》等,在“注杜”的过程中融会了他们学杜的经验。张性《杜律演义》选杜诗七律151首,分为21类,以其细密的分类见称,又征引史料及注释,语言明白通畅,方便初学者了解杜诗内容,掌握学杜的途径。赵仿《杜工部五言赵注》取杜甫五言诗261首,分16类,注释多附于句下,简洁明了,在列引原注中尤推崇刘辰翁注,重在杜诗的格调句法、渊源所自及后世影响,颇有精到之解,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多有征引赵注之处。董养性《杜工部诗选注》收杜诗916首,包括五古、五律、七律、七古、五排、七排、五绝,先分体,后分类,有天文、地理、人物等10类。董氏注杜强调杜诗情性之正、补益教化的特点,对宋人穿凿附会、不见性情的观点予以纠正。董氏注杜也侧重于对杜甫本意的探究,力求揣摩杜本之心,挖掘其忠君爱国的思想。
元末文人“学杜”也表现在以杜诗为评裁标准选编、评点当代诗作,以及以杜诗来注释时人诗作方面。杨维桢《大雅集序》云:“客有赖良氏,来谒余七者寮,致其请曰:昔山谷老人在戎州,叹曰:‘安得一奇士有力者,尽刻杜公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复盈三巴之耳?’有杨生素者任之,刻石作堂,因以‘大雅’名之。先生铁雅虽已遍传海内,而兵变后诸作,人未识者有之,请其诗付有力者刻之,亦使大雅之音盈于三吴之耳,不亦可乎?余曰:‘东南诗人隐而未白者不少也,吾诗不必传,请传隐而未白者。’……盖良以待我,而我以待诸公,庶入是集者皆可以续杜之后,而或有慊焉者不入也。”[18]在杨维桢看来,《大雅集》即是以杜甫入夔州后的成熟诗作为标准选诗的,因此以“大雅”命名此集,且杨维桢秉此标准亲自参与选编工作。而在吴复所编的《铁崖先生古乐府》中,亦以杜诗之余绪来评价杨维桢的诗作,《铁崖先生古乐府》卷四收《古愤》《贸丝词》《吴城怨》《七哀诗》《梁父吟》等40首,卷末总评曰:“已上凡四十首,多古乐府之续题。或写风情,或述风土,或吊古悯时及游方外之作也。以古风人之兴象,带太史氏之评裁,诗家自老杜以来之所稀有也。”[19]
当然,元末文人“学杜”重在对杜诗的取法,戴良《申屠先生墓志铭并序》认为申屠某“为诗,勾章棘句,洒然有杜甫之遗音”[20]。杜诗及杜甫诗论对元末文人诗学观念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对杜诗的取法又经过他们的认真练择,从而由对杜诗的不同取法表现出不同的诗学主张。
三、元末文人对杜诗的取法与练择
元人黄至道曾说:“范德机得杜工部之骨,杨仲弘得杜工部之皮,虞伯生得杜工部之肉。”[21]370元人认为范梈诗学侧重学习杜诗的骨骼构架,杨载诗学强调杜诗的诗法锤炼,而虞集诗学则看重杜诗的精神内涵。范梈、杨载、虞集在“元诗四家”之列,代表元代中期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三家诗学均源自对杜诗的学习,然取法不同,而成自家风格。元末文人亦将杜诗作为诗学取法的模本,杨维桢《李仲虞诗序》云:“删后求诗者,尚家数,家数之大,无上乎杜。”杨维桢认同杜诗“集大成”的特征,并且认为学杜者有不同的侧重点:“观杜者不唯见其律,而有见其骚者焉;不唯见其骚,而有见其雅者焉;不唯见其骚与雅也,而有见其史者焉。此杜诗之全也。”[22]240以此,元末文人从对杜诗的不同取法与练择中构建起自己的诗学内容。
首先就杜诗的“声律”而言,元末文人对“诗律”多持反对意见,认为律诗在格式上的限制阻碍了音韵的自然抒发,李祁《周德清乐府韵序》云:“天地有自然之音,非安排布置所可为也。以安排布置为之者,人也,非天也。天地既判,而人与之并立焉,草木生焉,禽兽居焉,凡具形色肖貌于天地之间者,莫不有声焉,有声则音随之矣。清浊高下,抑扬徐疾,何莫而非自然之音哉。声音具,而歌咏兴,虞廷载赓,《三百篇》之权舆也。商颂、周雅,汉魏以来,乐府之根柢也。当是时也,韵书未作而作者之音调谐婉,俯仰畅达,随其所取自中,节奏亦何莫而非自然之音哉?韵书作而拘忌多,拘忌多而作者始不如古矣。”[14]671李祁以自然之音为最高准则,认为古诗之“音调谐婉”“俯仰畅达”即出于对自然声韵的客观遵循,进而他认为即便精深于诗律的杜诗,其意趣风格亦不能与古诗相并举,“古之诗未有律也,而律诗自唐始,精于律者固已有之。至杜工部而雄杰浑厚掩绝今古,然以比之汉魏诸作,则意趣风格盖亦有不然者矣”[14]671。
李祁的观念似乎落入尖刻与绝对,而杨维桢的观点则较为折中,他也赞成“诗至律”是“诗家之一厄”的观点,然而他认为杜诗之律是“虽律而不为律缚”,他在《蕉囱律选序》中说:“东坡尝举杜少陵句曰:‘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动影摇。’‘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是后寂寥无闻。吾亦有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报甘泉宫。’‘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为近之耳。余尝奇其识而韪其论,然犹以为未也。余在淞,凡诗家来请诗法无休日,《骚》《选》外谈律者十九。余每就律举崔颢《黄鹤》、少陵《夜归》等篇,先作其气而后论其格也。”[22]250杨维桢反对律诗,其出发点是反对律诗格式阻碍诗歌“气”的发挥。因而他主张“先作气”而后“论其格”,诗歌创作如果没有“排海突岳,万物飞走”之气力,便落入了四声八病的拘泥之中。因此他对“杜律”的取法,多重视其“拗律”,学其“奇对”,“其在钱唐时,为诸生讲律体始,始作二十首,多奇对,其起兴如杜少陵”[23]447。这种拗律体在当时被称为“放体”,即学习杜诗拗律而得到“乖龙震虎”的诗歌张力,所谓“水犀硬弩,朱屠铁槌,人见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其中自有翕张妙法”[23]448。
元末文人认为杜诗源自《骚》《雅》,为“志之所之”,因此他们也强调杜诗“本乎性情”的特征。吴复《辑录铁崖先生古乐府序》云:“君子论诗先情性,而后体格。老杜以五言为律体,七言为古风,而论者谓有《三百篇》之余旨,盖以情性而得之也。”[24]而他们对杜诗“性情”的看法亦有不同意见。
一方面他们认为杜诗之“性情”是“本乎人心,契乎天理”,万世不变的“风雅”之情。因而,由此性情而发的诗歌可以“观时政,论治道”,使儒家风雅之教得以倡行。旧题“傅与砺述范德机意”的《诗法源流》云:“唐海宇一而文运兴,于是李、杜出焉。太白曰:‘大雅久不作’,子美曰:‘恐与齐梁作后尘’,其感慨之意深矣。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瞻,故其诗兼备众体,而述纲常、系风教之作为多。”[21]235故而元末诗人对杜诗的学习也多强调杜诗“述纲常、系风教”,表现出对时事、政事的深切关注。至正五年(1345年),旅途中的迺贤亲睹了河南、河北饥荒灾害,效杜甫“三吏”“三别”作《颍州老翁歌》:“颍州老翁病且羸,萧萧短发秋霜垂。手扶枯筇行复却,操瓢丐食河之湄。我哀其贫为顾问,欲语哽咽吞声悲。”诗后有李黼跋曰:“状物写景之工,固诗家之极致。而系于风化,补于政治,尤作者之至言。易之此诗,兼得之矣。”[25]陈镒《次韵孀妇叹用杜工部诗韵》云:“城东孀妇发未华,半生苦乐随夫家。前年夫戍死锋镝,姑老子幼长吁嗟……此身抱节誓不改,甘守寂寞黄茅材。”[26]而在杯酒交觞的雅集聚会中,元人也没有全然忘却世道之多艰,郭翼《漫兴一首呈上》诗云:“前月海寇入郡郭,病里移家愁杀人。桃花野屋苦多雨,杨柳清江无好春。谁似庞公居陇亩,自惭杜老在风尘。草堂梦寐惊相见,把酒论诗月色新。”[27]元末文人甚至直引杜诗关注现实的诗句用作酬唱之韵,如至正二十年(1360年)缪思恭等人于嘉兴南湖分韵唱和,以杜甫“不可久留豺虎地,南方犹有未招魂”②为韵,人得一字,即席而成,并以之记录世事治乱的情况。
另一方面元末文人也认为性情所发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李继本《傅子敬纪行诗序》云:“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诗非本乎志,而规规守绳墨以学,为声律之细,诗则陋矣。虞之歌,周之雅,十五国之风,虽所感异趣,所发异情,所出异时,本乎志也。”[28]737因而此“情”是个人之“情”,“情”之不同表现为不同的风格,故而有“雅诗情纯”“风诗情杂”“屈诗情骚”“陶诗情靖”“李诗情逸”“杜诗情厚”的区别。杨维桢认为“宗杜者,要随其人之资所得”,所谓“资”就是由个人性情而来的个性:“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天台李仲虞,执诗为贽,见予于姑苏城南,且云学诗于乡先生丁仲容氏。明旦则复谒,出诗一编,求予言以序。予夜读其诗,知其法得于少陵矣,如五言有云:‘湛露仙盘白,朝阳虎殿红。诏起西河上,旌随斗柄东。西北干戈定,东南杼轴空。’置诸少陵集中,猝未能辨也。盖仲虞纯明笃茂,博极文史,而多识当朝典故,虽在布衣,忧君爱国之识,时见于咏歌之次,其资甚似杜者,故其为诗,不似之者或寡矣。”[22]240李仲虞“纯明笃茂”之“资”表现为其虽在布衣而有“忧君爱国之识”,因此其“资”与杜甫相似,发言为诗则可与杜诗伯仲其间。然而以“资”论诗,总归将“资之拙者”一笔抹杀,杨维桢以为可用“师”(后天学习)来补“资”,而所谓“师”者仍旧要从师事性情开始,杨维桢《漫兴七首》有注曰:“学杜者必先得其情性语言而后可。得其情性语言,必自其《漫兴》始,钱塘诸子喜诵予唐风,取其去杜不远也。故兴《漫兴》之作,将与学杜者言也。”[29]从杜诗性情出发,便可以避免“拘之则卑”和“袭之则陋”的流弊。而无论是忧国忧民的“沉郁顿挫”,还是“性情盎然”“与物而为春”的“萧散清新”,都可从杜诗中取法一点而成自家之言。
元末文人对杜诗“诗史”的性质也有较为全面且独到的看法,杜诗反映民生疾苦和记录时事政治的诗歌在他们看来不仅有“史”的“叙事核实”,也有“讽喻深远”的诗教意义。苏天爵《书吴子高诗稿后》云:“夫诗莫盛于唐,莫逾于杜甫氏,其序事核实,风谕深远,后世号称诗史,《传》曰:‘诗可以观’,岂空言云乎哉!”[30]杨维桢进而认为杜诗之谓“诗史”,有《春秋》之法:“世称老杜为诗史,以其所著备见时事。予谓老杜非直纪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其旨直而婉,其辞隐而见,如《东灵湫》、《陈陶》、《花门》、《杜鹃》、《东狩》、《石壕》、《花卿》、《前后出塞》等作是也,故知杜诗者,《春秋》之诗也,岂徒史也哉?虽然,老杜岂有志于《春秋》者?《诗》亡然后《春秋》作,圣人值其时,有不容己者,杜亦然。”[22]251
所谓“《春秋》之法”,即《春秋》中所表现的“微言大义”,旨意蕴含于委婉的语言之中。他认为杜诗是《春秋》之诗,意在指杜诗不仅有“纪实”的特点,而且也在叙事之中陈古讽今,表达讽喻之见,因此杜诗的“诗史”性质在他看来还是诗教的内容,对杜诗的取法不仅取其叙事的手法,也要在叙事之中达到“《春秋》属辞比事之教”的目的。
元末文人认为,在诗学发展史中杜诗有崇高地位,可以揽千载既坠之绪,又祖雅颂之作,有《三百篇》遗意。李继本《傅子敬纪行诗序》云:“唐之兴也,以神武翦积世之乱,三光五岳之气复混。士之生也,钟乎天地之英,其为志,岸然而不淆于俗;其为诗,炳然上丽乎古。其擅名于后,先者若陈子昂、孟浩然、崔颢、李白辈是已,至杜甫氏起,大振绝响,志则咎、夔、稷、契之志,诗则虞、周、楚、汉之诗,藻发乎天趣,声系乎风教,诗与志混然不凿也。”[28]737–738杨维桢《诗史宗要序》云:“及李唐之盛,士以诗命世者,殆百数家,尚有袭六代之敝者,唯老杜氏慨然起揽千载既坠之绪,陈古讽今,言诗者宗为一代诗史。下洗哇媱,上薄风雅,使海内靡然复知有《三百篇》之旨。议论杜氏之功者,谓不在骚人之下。”[22]254然而就如何达到杜诗成就,或学杜的具体途径是什么他们却有不同看法。
元人认为诗学“家数之大,无止乎杜”,因而以杜诗作为“专门之学”来取法学习,李继本在《邓伯言玉笥诗集序》中说:“西江邓伯言先生(邓雅)以能诗鸣东南,其名《玉笥集》者,予因其北来,得而读之,大抵本之于骚、雅,支叶魏、晋,而于杜甫氏则其专门也。”[28]732而杨维桢、贡师泰等人则认为学杜需求其本源,杨维桢说:“魏晋而下,其教遂熄矣。求诗者类求端序于声病之末,而本诸三纲、达之五常者,遂弃弗寻,国史所资,又何采焉?……噫,比世末学咸知诵少陵之诗矣,而弗求其旨义之所从出,则又徇末失本,与六代之弊同。”[22]254杨维桢认为徒诵杜诗而不求其旨义所出是“徇末失本”,学杜首先要从“三纲五常”的儒家经义出发。贡师泰进一步指出,学诗的方圆规矩在《三百篇》而不在“杜”:“世之学诗者必曰杜少陵,学诗而不学少陵,犹为方圆而不以规矩也。予独以为不然。少陵诗固高出一代,然学之者句求其似,字拟其工,其不类于习书之模仿,度曲之填腔者几希。夫诗之原,创见于赓歌,删定于《三百篇》。汉、魏以来,虽有作者,不能去此而他求。今近舍汉、魏,远弃《三百篇》,惟杜之宗,是犹读经者舍正文而事传注也。”[10]171贡师泰认为杜诗一振六朝以来“气象萎苶,辞语靡丽”的弊习,是因为杜诗得《三百篇》遗意,因而舍弃杜诗本源,惟杜是宗,犹如读经者专力于传注。故而在他们看来,学杜的正确途径是由古而今,从《三百篇》等儒家经典出发,进而理解并求诸杜诗之法。
综上,元末文人在杜甫的精神世界中重新体会了老杜的一片“如血之心”,而在杜诗的滋养中通过不同的取法练择也培育了属于他们的诗学内容。
① 如赵海菱《杜诗在元代的研究与整理》(《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2期)着重探讨元人对杜诗的学习以及杜诗在元代的编撰整理情况。赫兰国《辽金元时期的杜诗学》(四川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讨论了几种元代杜诗选集。刘季《玉山雅集诗歌创作中的崇杜倾向》(《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集中讨论玉山文人群体的崇杜倾向)。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宗法与超越: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一章专有“崇杜诗论”一节,比较了宋人与元人学杜的异同,对方回论杜有精彩阐述。诸种成果详于考察元代前、中期而略于后期,详于元人崇杜的表现而略于考察他们学习杜诗的方式和诗学取法。
② 此为杜甫《返照》中诗句,原句为“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按清人沈季友《槜李诗系》卷六、陈衍《元诗纪事》卷二三“缪思恭”条所载南湖集会所用分韵诗句,“乱”“实”分别为“地”“犹”二字。本文依此引用。
[1] 傅若金.傅与砺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0.
[2] 顾瑛.草堂雅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615–616.
[3]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839.
[4] 贡师泰.玩斋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沈梦麟.花溪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 倪瓒.清闭阁全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02.
[7] 钱惟善.江月松风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00.
[8] 李存.俟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63.
[9] 陈旅.安雅堂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6.
[10] 李修生.全元文:第45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1] 刘季.玉山雅集诗歌创作中的崇杜倾向[J].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3):40–45.
[12] 贡奎.云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25.
[13] 欧阳玄.圭斋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7.
[14] 李祁.云阳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 许有壬.至正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
[16] 楼卜瀍.铁崖乐府注[M].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刻本:卷2.
[17] 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0.
[18] 李修生.全元文:第42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494.
[19] 杨维桢.铁崖先生古乐府[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8.
[20] 李修生.全元文:第53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503.
[21] 张健.元代诗法校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2] 李修生.全元文:第41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23] 杨维桢.东维子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4] 李修生.全元文:第39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650.
[25] 迺贤.金台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84.
[26] 陈镒.午溪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5.
[27] 顾瑛.玉山名胜外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453.
[28] 李继本.一山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9] 杨维桢.杨维桢诗集[M].邹志方,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138.
[30] 苏天爵.滋溪文稿[M].陈高华,孟繁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495.
Worship and Learning of DU Fu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WU Ju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The literati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had a personal feeling for DU Fu's displaced life and regarded DU Fu as a spiritual idol who was worried about the country and the king, loyal and patriotic, which was the main expression of their “admiration for DU”. They seek the spiritual pillar for their lives from him, and extract the spiritual power that moves people's hearts from his poems. The literati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also showed their appreciation for DU Fu's charismatic personality as a self-effacing man who was comfortable in his own skin and at peace with what he encountere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learn from DU”, and DU poetry was used as a model textbook for poetry enlightenment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imitating DU” and “noting DU” became a fashion.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the literati formed their unique poetic content by taking and practicing DU poems.
Late Yuan Dynasty; DU Fu; spiritual idol; poetics
I207.227
A
1006–5261(2021)04–0105–08
2020-10-28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CZW023)
武君(1988―),男,河北张北人,助理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 杨宁〕
——评王新芳、孙微《杜诗文献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