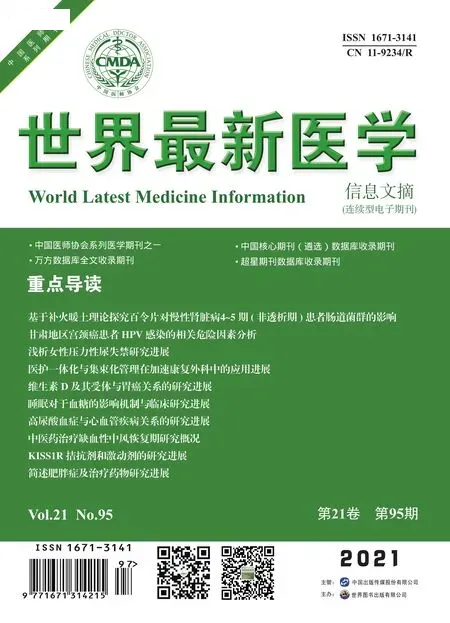从湿浅析便秘及泄泻
覃瑶,许阳慧,姚佳敏,夏琳超,李春林,唐梅文
(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0)
0 引言
湿之理论为中医重要的诊治原理,从古论治至今,为诸多疾病之病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早有提出“湿胜则濡泻”。湿为一种病理变化,六淫中风、寒、暑、湿、燥、火,表述的为外来之邪,为外湿,在这里我们谈及的是内湿。内湿多为水液代谢输布障碍所致,其性郁滞重浊,可隐匿起病,并能与多种病理产物结合成新的病理因素,性质复杂多变[1]。由于两广地区地理环境、气候影响及饮食所伤等,脾胃受累,外邪之湿长年累月侵蚀人体,脏腑功能失调,内湿孕育而生。通过对于临床病例观察及文献医籍的阅读所见,湿邪所致的胃肠道疾病十分常见,文章欲通过对湿性便秘及湿性泄泻的探讨,目的为抛砖引玉,对中医药的临床诊疗提出浅薄的见解。
1 便秘及泄泻的病因病机
便秘是指粪质干硬团块,排便时间或排便间隔时间延长,或大便排出困难但粪质不干[2]。对于便秘之症的记载,追溯历代古籍,其首见《黄帝内经》的“大便难”“后不利”,而便秘之命名首次出现于清代沈金鳌的《杂病源流犀烛》,除此外也见有“大便难”“脾约”“秘结”等名。经过多年的不断深入探究,目前对于中医对便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便秘发病原因可归总为感受外邪、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及年老体虚,基本病机为大肠传导失常,主要病位在大肠,与肝、肾、脾、胃、肺等脏腑也密切相关,其病性概括为虚、实两方面,其辨证分型,根据临床常见类型及经验总结,目前多分为热积秘、气滞秘、寒积秘、气虚秘、血虚秘、阴虚秘、阳虚秘等[3]。
泄泻是以大便次数增多,粪质稀薄,甚则泻出如水样为主症。古时称大便溏薄而势缓者称为泄,清稀如水而势急者称为泻,现一般统称为泄泻[2]。《内经》时期称“泄”,如“濡泄”“洞泄”“飱泄”等,汉唐时期把“下利”混称,隋代巢元方才把“泻与痢”分论,唐宋以后才统称“泄泻”。泄泻的致病原因有感受外邪、饮食所伤、情志失调、劳倦伤脾及久病年老等,主要病变在脾、胃、大肠、小肠,主脏责脾,与肝、肾密切相关,目前证治分类有寒湿困脾、肠道湿热、食滞胃肠、脾气亏虚、肾阳亏虚、肝气乘脾等[4]。
2 从湿辨证
湿是形成泄泻的主要病理因素之一,湿邪易趋于下,大肠小肠受盛化物、泌别清浊的功能受到影响,则见大便溏之临床表现。朱丹溪提出:“泄泻者,水湿所为也。”李中梓《医宗必读·泄泻》有云:“无湿则不泻。”可见在泄泻发病过程中湿邪为重要因素。然湿不独存,当进一步辨其证候。若为寒湿泄泻多见泻下清稀甚如水样,伴肠鸣腹痛,或兼畏寒,舌苔薄白或白腻,脉濡缓;湿邪夹热可见泻下急迫,粪黄而臭,烦热口渴,舌质红,苔黄腻,脉濡数或滑数等,《内经》有云:“暴注下迫,皆属于热”;若病发于盛夏之际,身热烦渴,呕吐下利,舌苔黄,脉滑数等,则为暑湿泄泻。
湿秘近代少有论及,但早在《重订严氏济生方·秘结论治》中就有说到,“夫五秘者,风秘、气秘、湿秘、寒秘、热秘是也。”这也是首次提出湿秘,文中简述“槟榔散”对肠胃有湿所致的大便秘涩的治疗方法。《温病条辨》中说到:“湿凝气阻三焦具闭,二便不通。”《读医随笔》中亦有提及:“燥湿同形者,燥极似湿,湿极似燥也。故湿之证,有筋急,口渴,大便秘结”等,这些有形邪气阻滞肠道气机而造成便秘。近代教科书上少有提及湿秘,但其于临床并不少见,且由于现代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多食肥甘厚腻之味,脾失健运,脾胃负担加重导致水谷运化失司,因湿所致便秘应当引起重视,如功能性便秘就可从湿邪辨证论治[5]。而因湿邪重浊黏滞的特性,湿秘的表现应是大便黏滞不爽、排出不畅,或兼有身体困重,胸闷痞满,舌苔厚腻,脉滑等症状。
3 中医的病治异同
辨证论治被视为中医学理论研究的精髓,其过程为分析、认识疾病的过程。仲景为论证大家,其《伤寒论》就有说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涉及到“证”的概念。中医的证是人体处于某一个状态的病理概括,包括了当下的病位,病因,病机等[6]。一个病可出现不同的证候,而不同的病又能出现相同的症状。如胃脘痛的病人,若出现疼痛拒按,嗳腐吞酸,不思饮食等症,多为饮食积滞所致,而见胸闷嗳气,脘痛连胁等,则考虑肝气犯胃之证。我们在进行望闻问切的过程,便是辨证的过程,而中医又讲究整体观念,不能将病症割裂开来治病。如上所述,胃脘痛的基本治疗原则是理气和胃止痛,但又分别有两种证型表现,其治则也不尽相同,病因为饮食积滞的则需以消食导滞为法以达理气和胃止痛的治疗目的,肝气犯胃则治以疏肝理气。这也体现了“同病异治”的中医理念。早在《内经》时期就有提及同病异治的治疗方法,《素问·病能论》曰:“有病颈痈者……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此所谓同病异治也”,其在《素问》中有两种含义:一为同一疾病采用的治疗手段的不同,一为同一疾病采用的治疗原则不同[7]。
异病同治与同病异治有异曲同工之妙。异病同治见于清代陈士铎的《石室秘录》中:“同治者,同是一方而同治数病也……又可治痰气之疾”。在此之前虽无明确提及,但如仲景所著《伤寒论》,全书便充满了“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的思想[8]。异病同治的中医思想,指的是不同的疾病,在各自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病因病机同源,发病机理相同,便可用相同的治法甚至同一主方来治疗。如临床上常见的“郁病”“痞满”“乳癖”等病,都可由气滞而致病,虽可有多种不同症状,但三者病因病机均与气关系密切,气滞为其共同病机,抓住这一首要因素,探求核心病机,达到异病同治的效果[9]。
4 治则治法
湿为有形之邪,多为相合起病,易与风、寒、暑、热等邪气同载,若独治以化湿之法,往往收效甚微,需分证论治才能对症下药。
湿性泄泻以运脾化湿为基本治法,若起于寒湿,则与藿香正气散加减芳香化湿,疏表散寒,起于湿热,则与葛根芩连汤清热利湿,起于脾虚湿盛,可与参苓白术散健脾益气,渗湿止泻[4]。熊继柏认为,对于内有湿邪的寒湿泄而言,应以《金贵要略》中:“下利气者,当利其小便”为重,治方以五苓散;若为外感寒湿则以藿香正气散散寒祛湿;若暑热夹有湿邪,当以仲景《伤寒论》:“太阳病……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所言,以葛根芩连汤清热祛湿[10]。朱子文认为“湿不单见,脾不独虚”,虽其关键在于湿盛脾虚,但多呈“寒热交织,正虚邪恋”的证候,其治疗泄泻以扶正袪邪为法度,以祛湿、温脾为要,不胡乱投以补涩之剂,若因湿热,则以生薏仁、车前子、茯苓清化湿热;若因暑湿,则清暑化湿,惯用滑石;若因寒湿,则行温化之法,焦白术、炮姜炭颇为适宜[11]。杜晓泉强调辨证祛湿,要兼顾兼证,整体调理,兼表邪较重者增强疏散风寒之效,湿邪较重而致腹胀尿少、小便不利者,予利水渗湿药以达淡渗分利之功,暑湿见身热烦渴、胸闷脘痞者不忘清解暑热,其治疗湿泻多用藿香正气散加减及葛根芩连汤加减[12]。吴文尧在治疗泄泻时强调在治法上应以健脾为主、祛湿为辅,应注重顾护脾胃,善用参苓白术散化裁治疗脾虚湿盛之泄泻[13]。黄明河则采用调补脾肾、祛湿化浊为治疗之大法,以健脾化湿汤与温阳化湿汤为主治疗脾虚湿困型慢性泄泻[14]。张天文根据明朝李中梓《医宗必读》中的“治泄九法”加上“平肝法”,总结出治泄十法,分别为淡渗法、升提法、清凉法、疏利法、甘缓法、酸收法、固涩法、燥脾法、温肾法、平肝法;在治疗上,寒湿泄适用升提法,外感风寒致泄宜葛根汤,外感夹湿用荆防败毒散,外感而又内伤湿滞,则用藿香正气散,脾虚湿盛宜升阳除湿汤,暑湿伤脾用缩脾饮;湿热泻适用清凉法,外感湿热宜三仁汤,湿热伤中用葛根芩连汤,脾虚心热宜甘草泻心汤、黄连汤;水湿泄适用渗利法,湿困于脾治以五苓散,湿夹热邪宜六一散、车前子散、猪苓汤[15]。
湿秘同样治以化湿为主,虽有关湿秘的系统认识和诊疗规范尚未完善,但各家均有经验之方。朱凌云认为湿秘以脾胃虚弱、湿浊内停、气滞不行三端为核心病机,三者互为因果,如环无端,以健脾益气、除湿化浊、行气导滞为法,药选生白术、枳实、皂荚子、蚕沙拟成和中化浊导滞汤[16]。张庆东等考虑阴虚湿秘之证,须滋阴除湿,行气通便,可选用沙参甘苦微寒善补五脏之阴,怀山药、扁豆、苡仁、茯苓以滋脾阴袪湿,化湿不伤阴,白术健脾益气袪湿,陈皮、砂仁、藿香理气和脾袪湿,苍术、法半夏、厚朴燥湿醒脾;稍佐甘温扶阳之品以阳中求阴,加强祛湿作用[17]。梁自平等以祛湿消滞,行气通便为法,用达原饮治疗湿阻便秘[18]。王彦刚认为湿秘首责于脾,次第论肝,勿忘查肾,治疗上选用苍术、厚朴、陈皮等苦温燥湿之品,配伍瓜蒌、杏仁、决明子等滑肠之品以行运脾化湿通便之功,佐以藿香、佩兰以芳香气味醒脾和中,疏肝理气,化湿通便为治法遣药组方,常用药对香橼、佛手,二者合用平肝舒郁,宽中顺气,入肝、脾二经,温肾散寒、化湿通便选用乌药、益智仁、沉香、萆薢药组,取萆薢分清饮“温暖下元、利湿祛浊”之意,乌药辛香温散,入脾肝肾三经,善疏通气机[19]。刘绍能善用气味辛薄、药性升浮之风药治疗便秘,其认为湿阻中焦,脾为湿困,脾胃升降运化失职,肠腑传导失司则大便黏滞不畅,而致湿秘,治疗以理气通腑、祛湿导滞为原则,在总治则上,根据湿邪的热化或寒化,随证治之,然无论使用何法治疗湿秘,据李东垣《脾胃论·脾胃胜衰论》中:“诸风药皆是风能胜湿也”所言,均可加入风药以增强祛湿导滞之力,如防风、威灵仙等[20]。徐艺等认为湿犯三焦,滞而为秘,取三仁汤组方理念,随证化裁,以流气化湿,即宣气化湿法治之,该法虽用于治疗湿热或湿温,但以去除湿邪为主,亦为治湿邪之大法[21]。三焦辨证言:“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其中“下焦如渎”如同沟渠之意,下焦滞而不通可致大便黏腻难解而致便秘,但不离上中下三焦辨证思维,贺平等基于三焦辨证,采三仁汤宣畅三焦气机之法,根据个人经验对湿秘进行临床论治[22]。
5 小结
便秘和泄泻均为常见病,根据二者起病形势来看,可说是症状相对的病症,但从湿邪致病来论述,又发现其中蕴含着相同的规律。这提醒我们,临床治病应把握诊疗核心,不必过于拘泥于固有证则,要发散思维,不断探寻,从而加深对各类疾病的认识,以提高临床疗效。